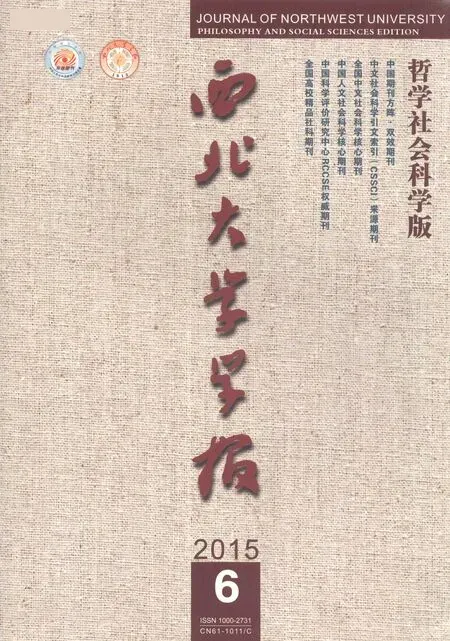有限政府还是有效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
黄 安,张宏邦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有限政府还是有效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
黄安,张宏邦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710049)
摘要: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去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人性假设,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面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人学基础考察,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全面深改”阶段的中国政治社会新常态,不如说是为着更多新的、有价值的政治思想资源和政治制胜方法论。
关键词:政治哲学;自然权利;人性假设;有限理性
一、自然权利理论
政治哲学就其核心论题而言,很重要的是探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边界及其相互关系。自然权利理论认为,个人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和社会存续都是为着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应该是历史的逻辑起点。明确道来,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是人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人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理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如此理论也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认,他们论述道:“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P71)“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P532)。
近代以来,霍布斯(Hobbes)与斯宾诺莎(Spinoza)借用“自我保全”开启自己的自然权利述证。霍布斯说,“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3](P97)。洛克(Locke)则进一步指出,生命、自由和财产当属个人的自然权利,任何别的人都不得侵犯。如此,人的自然权利依靠“自然法”这个超验的东西获得了终极理论支撑。所谓自然法,是相对于人世间的习俗和法制而言,但后者必须服膺于前者。众所周知,在西方古代哲学和近代早期哲学中,“自然”在社会和政治世界中往往等同于某种确定不移的规则与法度,政治论争事实上被符号化为“自然对抗习俗”这个抽象论题。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们大多人奉之为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财产权等为圭臬,所以一当它介入政治哲学,便包孕并展示着如下三个递进原则:
首先,个人权利至上原则。个人优先于社会,这在西方近代哲学上属于一个逻辑上而非时间上谈论“第一性”的惯常做法。洛克认为“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得不到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之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4](P56)。诺齐克(Nozick)则直接主张“最小政府”和“最弱意义的国家”,“最弱意义的国家是能够证明的功能最多的国家。任何比这功能更多的国家都要侵犯人们的权利”[5](P155)。
其次,权利让渡原则。政府权力的获得是通过个人权利的让渡实现的。霍布斯和卢梭(Rousseau)都认为,个人把所有的自然权利都让渡给社会共同体和国家权力,借以保护个人权利。洛克认为个人只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一个人不能使自己受制于另一个人的专断权力;而在自然状态中既然并不享有支配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专断权力,他所享有的只是自然法所给予他的那种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的权力;这就是他所放弃或能放弃给国家的全部权力”[4](P83)。当然,也不得不承认,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为了迎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才否认封建制度下不完全的、有条件的私有制及其形式。正如马克思的间接论述:“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权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1](P132)
第三,有限政府原则。政府原本就是为了个人自然权利的实现或保障自然权利而出场的。因此,侵犯个人自然权利,必然使国家权力与政府仅有和能有的合法性消失殆尽。契约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订立契约集合成国家,不外乎是对一种合乎契约精神的、能带给人安全、自由、平等与财产权保护的政治秩序的吁求。洛克指出:“政治权利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断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4](P4)
看得出来,上述关于自然权利理论介入政治哲学的三大原则——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的简单罗列,旨在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一个基于人学考察层面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论证。三大原则事实上包孕并体现着如下思想语法:个人是唯一“实体”因而具有本原性;社会与国家都是实现意义上的,即都是为了个人权利之“自然性”的实现,因此具有生成性。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看,三大原则支撑和发酵的自然权利理论,还提供了规避国家作“恶”和社会陷入“恶循环”的两条路径:一是以权力(power)制衡权力路径,二是以权利(rights)制约权力路径。前一路径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之“三权分立”奠定了基础,后一路径为资本主义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行为做了舆论先导。
与之相应,我们需要警惕两种路径潜在的制度陷阱:前一路径往往导致政府内耗严重、产生不了有效政府和真正负责任的顶层设计;后一路径可能导致政府只关注形式权利,忽视实质权利,最终导致无所为或不敢作为行为。而无所为或不敢作为行为便是最大的腐败。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权力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集权与分权(或者放权)何以制度化于一个适度范围内,真正用刚性制度托举起“公民性”权利意蕴。
二、人性假设逻辑
哲学史上,基于人性善恶不同的道德判断,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两种截然相反乃至尖锐对立的政府观。一种政府观以性善假设为基础,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也应该是追求终极的至善。譬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这种以最高的善为目的的科学就是政治科学。”[6](P3)另一种政府观则以性本恶为理论支点,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应该是一种避免大恶的作业历程,即国家与政府的存在就在于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想法设法去除这些“不可避免的大恶”。
比较而言,追求至善的政府观及其实践,属于一种“积极自由”思想语法和叙事逻辑。这种思想观念常常秉持浓厚的空想主义成分,在实际运作中常常导致无限政府的大肆扩张政策和行为。而追求防恶的政府观,显然属于一种“消极自由”逻辑框架,在实际操作运营过程中,它更加注重实际效度,讲究收敛策略,要求建立有限政府及其运作模式。
按图索骥,性善假设作用于个体,就置换出人治思想;发用于集体,就勾连出无限政府理念;发酵于政治实践,就是如下理论:政治权力隶属人格至善的统治者,因为统治者的人性、品性是自足的,理应获得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显然,这种人性本善从而政府本善的逻辑,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忽视“制度铁笼”的效用。与之相反,性恶假设断然否定了“君”临尘世的可能性,不但消解了“哲学家王”与“一代名君”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基础,还从肯定法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方面,为惩治他们的“罪恶渊薮”不遗余力。既然人天生带有“原罪”,那么就需要一定的制度来规训和防范人性的诸多弱点。
其实,两种截然相反的政府观从一开始似乎就水火不容,也因而不断引起相互攻讦与辩难。譬如,主张去恶的政府观如是批判扬善政府观,前者认为后者打着以“目的善”证明“手段善”旗号,而事实上沦为“目的善”怂恿“手段恶”的帮凶,最终导致狂热主义和极权主义。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Madison)就尖锐地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7](P164)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波普尔(Popper)如是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该增加。”而“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因为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而能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加以有效限制的制度却将逼迫最坏的统治者去做被统治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事”[8](P491)。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制度问题,是立法框架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向平等的进步只有通过对权力制度化的控制才有可能保证”[9](P151)。
回观历史上曾经的政治实践,我们认为,行善与作恶事实上构成政府作为的两重性面相,且各自都有过精致的发挥。但必须强调,政府行善和作恶之两重性,均源自人性而非出自政府本身。于此,我们就可以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进行如下理论澄明乃至信念积聚:
首先,政府的权力尽管必需,但这种权力本身却异常危险。因此,人们不应该将自身的全部身家性命托付给一代“圣主明君”,即不应该全部寄望于善性从而全能政府上。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防恶才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最佳的政府当是与人的恶本性相匹配的有限政府。也因此,我们认为,惟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抑制人性中的大恶,从而激发和唤起人性中的各种善潜能;也惟有这样的政府,才足够强大到不仅完成其基本职能,而且又不越俎代庖,危及他人的基本权利。
其次,善恶说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以此为基础推论和选择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建构模式,却因时空的变异而同时显现出捉襟见肘的尴尬困境,尽管程度不同。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善假设及其政治逻辑发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恶假设及其政治实际运作,本无可比性,但伴随时空在历时态嬗变中的共时态呈现,两种相应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各自的先天不足。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学理识见:对于人性,我们不应停留在抽象谈论层面,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建基于不同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中西不同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我们理应秉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论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性原本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自然属性当然是指人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属性,它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人的社会属性则是人后天获得的,只有人的社会属性才可言善恶。“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创造出道德、法律、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规范,给人性中的自然欲望及这种欲望在人社会行为中的体现画出一个适度性。个人的社会行为只要保持在适度性之内,便被称作‘善’,超越适度性的则被称之为‘恶’”[10]。当然,这种“适度性”本身也是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而变化的。
再次,性善假设与性恶假设并不能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单向度孕育政治哲学之人性根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即为善和作恶。既然如此,制度设计也就必须充分考虑善恶之双重本性,既要扬善,又要制恶。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例外,同样必须充分考虑这两方面的功能,做到克服传统文化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道德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又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必须坚持去恶优先原则;而在实践层面,民主政治建设势必要将自律和他律的双向规制进行到底。
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完全依赖和建立在人性假设(无论善恶)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体制,都是不自足、不完善的,而是需要彼此互补、相互支撑的。据此我们认为,只有把法律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克服人性的先天不足;只有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
三、有限理性理念
政治哲学除了传统的善恶人性假设基础外,还有一种关于人的某种本质特征的逻辑设定,那就是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不同的断限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理论架构和结论。如果认为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是有限的,那就形成认识论上的有限理性理论和政治实践上的有限政府运作模式;反之,就是认识论上的无限理性理论和政治实践上的全能政府运作体制。
无限理性论肇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对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的强调。用人的理性来抗衡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天启真理原本属于历史的进步,但近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对自己理性能力的顶礼膜拜不断得到固化并最终导致理性万能论和绝对理性主义。进一步,这种“致命的自负”逻辑,使得理性还上升为道德判断的终极标尺。立足于知识论视野,无限政府理论从而全能政府的基本信条是,专制者是全知全能的,被专制者是无知或者知之甚少的人,所以前者奴役宰割后者是天经地义的。惟有拥有所有知识的天才(专制者)才能引领无知者走向新的美丽世界。
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对于这种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的批判声一直就未曾停歇过,尽管可能出于不同视角。休谟(Hume)的怀疑主义、西蒙(Simon)的有限理性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哈耶克(Hayek)的进化理性主义等,是谓代表。他们高举“理性不及”大旗,一致认为,全能理性论过分夸大了理性的作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理性的滥用”,并最终毁掉理性的自由根基。因此,我们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倡导有限理性理念及其政府运作模式。
西蒙这样论述,“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11](P46);哈耶克指出,“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我们渐渐认识到,人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往往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之中”[12](P19)。“人类心智永远也不可能被人类心智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自身能力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无法去了解、预测和控制心智。这种局限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对世界做出一种完全理性的理解。”[13](P77)波普尔更是直接发声:“我们的知识只能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无知必定是无限的。”[8](P41)至于休谟的不可知论,更是彰明较著于哲学史。
如今回观这些思想家们的论述,我们不妨将与无限理性理论相抗衡的有限理性理念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四个方面:(1) 完全形式的知识总体是不存在的,知识总是分散在诸多个体之间;(2) 理性本身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没有绝对真理;(3) 除过理性知识,还有其他重要知识;(4) 人类理性自身的限度决定了不可能存在全知全能的人、组织和政府。尽管这仅仅属于一种知识论立场的判定,但有限政府理念及其实践也确实从中获得了令人服膺的合法性明证。因为无论如何,集中所有分散的知识仅仅属于一种美好预期,而且人们的无知范围也正随着社会的发展成正比例延展。在这个意义上,无限理性与全能政府理念应该属于一种“致命的自负”和“乌托邦社会工程”,更不用说其对人本身自由的漠视与对社会正常秩序的颠覆之可能。
在中国,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民主化为基本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依赖有限理性理念的发微和有限政府实践的运作,获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众所周知的辉煌成就。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实质是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在这其中,一方面要求市场机制灵活运转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的职能更多地集中于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之于目前中国而言,政府必须从步入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渐次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理型、服务型新政府。事实上,伴随“中国道路”的不断开拓,中国建构有限政府的社会条件业已形成,包括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和日益完善的法制体系等等。
回到论题本身,作为一种反思传统家国本位和权力本位的政治制胜分析语汇和叙事方式,有限理性理念同有限政府实践早已深入人心。它以政府自身监视为切入点,深入到政府体制机制内部,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建设,不但突破了早年自由与秩序博弈过程中的诸多理论困境,而且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有限政府理念及其实现途径、体制、机制等,缔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模式”范例。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公共权力制约、政府角色清晰、执政能力强的高效廉洁政府,固然要依赖有限理性理念的持续深入和有限政府形象的不断塑造,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问政”中国,如此“有限”的理念及其实践,是否能够确保如其所求、如其所愿的政府有效生成,尚需再思量。因为,当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要让既得利益让渡权力,要让权力最终回归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要让“老虎苍蝇一起打”,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有效政府而非有限政府的出现和运营,显得是多么弥足珍贵。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当我们坚信只有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才能彻底遏制腐败时,我们该如何调整关于意识形态运作的理念,如何确立与之相应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确立法律的尊严,如何落实人民民主”[14](P18-22)。这就涉及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和机制的道德维度问题。因为在根本上,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必须由权利、平等和道德三个维度共同决定与评判。至于“有效政府”的具体思想经纬和操作运行机理,这实在是一个“民主的陀螺”问题。目前笔者正在阅读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本书,相信从中会找到答案。届时再议。
四、结语与阐发
研究政府治理的基础性问题即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问题,属于政治哲学的应有之义。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为政府治理的合法性设定了人学意义上的限制,而正是如此这般的限制,才使得政府的营运与建构获得了不断自我更新的动力与持久合理性支撑。可以看出,自然权利理论主要立足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逻辑关系;人性假设逻辑主要关注政府的善恶道德基础;有限理性理念则主要倾向人与生俱来的认知范围与能力。三个不同维度共同展开了政治哲学的人学批判,却也勾连出我们关于政府自主性之限度与效度问题的再一次反思。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关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论争,本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理论选择问题。要“重新发现政府”,必须联系与现行政治体制和机制比肩的社会历史传承,在“镶嵌性的有效国家能力”(主要指国家与社会的合宜镶嵌)与“隔离性的有限国家权力”(主要指经济决策部门要最大限度地远离“政治”以避免利益集团的唆使)之间找到良治的黄金分割点。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霍布斯.利维坦[M]. 黎思复,黎廷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 洛克.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6]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 程逢如,在汉,舒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 傅季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9] POPPER K.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umeⅡ[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1945.
[10] 俞吾金.关于人性问题的新探索——儒家人性理论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11]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M]. 杨砾,徐立,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2]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 贾湛,文跃然,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4] 冯平.中国价值论研究范式的现状与转型[J].哲学动态,2014,(4).
[责任编辑陈萍]
【公共管理研究】
Bounded Government or Effective Government: The Humanologic
Ba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UANG An, ZHANG Hong-bang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Natural rights theory, assumption about human nature logic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jointly make up the humanologic ba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three principles such as personal rights supreme, rights assignment and bounded government, natural rights theory testified two paths, which are “to counterbalance power by using power” and “to restrict power by using rights”. We acquired moral judgment ba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propagation and apply of human nature duality-good and evil on public power; but relevant political philosophies and its practice, based on any one of the two human nature assumptions, are not all sufficient and complete. Considering the limit of human cognitive competence and intelligence, bounded rationality epistemology and limited government operation mode, contrary to unlimited rationality theory and omnipotent government practice, are formulated. Analyzing humanology basis u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would be better for having more valuable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relevant methodologies, rather than adapting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stage of all round deepening reform.
Key words:political philosophy; natural rights; assumption about human nature; bounded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