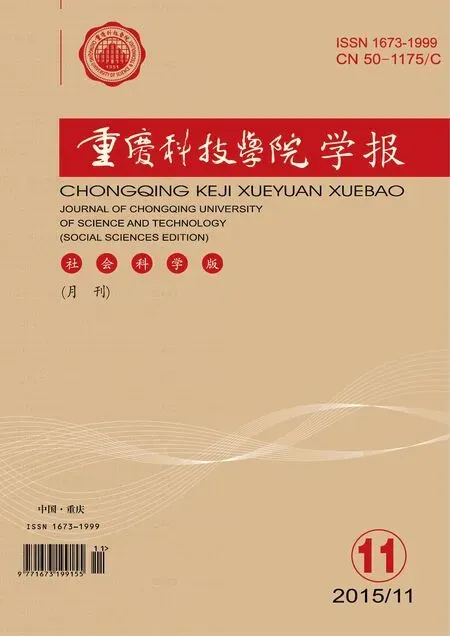“和谐”大观念的先验演绎
张媛媛,谢家建
自从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以来,“和谐”一词逐渐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不仅频繁地出现于各类媒体的宣传报道中,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学术文章中,甚至几乎融入到了每个人的日常对话里。由此可见,“和谐”在当今中国已然成为阿德勒所谓的“大观念”——“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生存的世界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观念”[1]2。但是,“和谐”的被广泛应用却并意味着每个使用者都完全掌握它的意思,而且一些人对该概念的外延肆意扩大,已有使其沦为空概念的危险。为了使这一个 “大观念”保有其特有的含义,有必要对其进行先验演绎。
一、关于先验演绎方法
“先验演绎”源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论。“演绎”是康德从法学领域借用的术语,意指从法律上而非事实上举出理由或根据,据以证明或推演某项权利的合法性。
先验演绎作为一种方法,包括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两部分。主观演绎的目的是找出经验概念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和根据,方法是分析法。康德将该方法定义为:“我们追求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既定的,由此上升到使这个东西得以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2]33。客观演绎则是以主观演绎的先天条件为前提,去论证这种概念的客观能力。因此客观演绎的方法是综合法,即从主观演绎的条件出发,逐步将经验概念重构出来,即康德所谓“力求从理性原始萌芽中开展出知识来”[2]30。
我们对“和谐”观念的演绎也将采取上述方法:先将其先验条件展示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还原作为经验概念的“和谐”观念。
二、对和谐的先验演绎
(一)主观演绎
首先,和谐必须以量的范畴里的总体性为先验条件。和谐,通常被用于描述一个系统,例如宇宙(无论是作为大宇宙的世界,还是作为小宇宙的人)。一个系统必然是具有“单一性的多数性”的整体。作为可被“和谐”修饰的主体,不能仅仅是一个算数上的全集,而必须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和谐是以总体性为先验条件的,尽管作为总体的系统是由部分组成,但其本身又是完整的、成体系的东西。
其次,和谐还必须以协同性为先验条件。协同性属于关系范畴,而和谐所描述的也是一种关系的状态。和谐关系的先验前提之所以不是实体与偶性,也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协同性,原因有二。其一,和谐指称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如果以国家政体进行类比,关系范畴的这三个对子,可以分别比作奴隶制国家(实体与偶性)、封建制国家(原因与结果)、共产主义国家(协同性)。实体与偶性这种关系是一种依存性和从属性的关系:偶性无法独存,只能以隶属于实体的方式存在。实体相当于奴隶制国家的奴隶主,而偶性相当于奴隶,奴隶只能依附于主人存在。原因与结果是一种原因性和依存性的关系,尽管原因决定结果,但原因的实在性总是要大于结果,或者至少等于结果,否则不构成充足理由。这就类似于封建制国家中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诸侯有一定的政治独立性,天子的独立性比诸侯更大,并且决定诸侯。协同性是一种能动者与受动者间的交互作用。在德语里,协同性(Gemeinschaft)本作“共同体”解,就是指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共同体只能由地位平等的实体组成,它们两两双向作用,互为因果。这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平等、自由、协作的关系相似。其二,和谐指称的是一种差异性的整体。由此可见,在和谐这一大观念中,协同性勾连了总体性,而这种差异性的整体正是协同性。康德指出:“协同性在于诸知识交互排斥但却因此而在整体上规定着那个真实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总括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唯一被给予的知识的全部内容。”[3]67和谐就是让所有的可能性都同时存在于整体中,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只有“和而不同”的整体,才可被称作是真正的整体。完全的同一性并非真正的和谐,因为它必然以实体与偶性或原因与结果为前提,并且是一种单向度的关系,最终难逃系统僵死的厄运。
和谐的最后一个先验条件是必然性。必然性提示了一种规律性,而规律性正是和谐的一大特征。然而,“必然性是由可能性本身给予出来的实存性”[3]75。天体在天文学家眼中是最和谐的系统,而这种和谐正是来自天体运行的规律性。天文学家对行星的监测是现实性的,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对所监测的行星轨迹的单纯记录,他们努力追求普遍性,试图揭示天体运行规律,以对未来的星球轨迹进行预测,这就涉及可能性。当可能性成为现实性,必然性就被印证了。这就是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正如协同性勾连了总体性,在和谐这一观念中,必然性也勾连了协同性。只有作为包容所有可能性的整体,才是和谐的;而所有可能性即是必然性,因此可推出必然性亦为和谐的一大先验条件。
(二)客观演绎
1.物理世界的和谐
“头顶的星空”向来是西方哲人惊诧的对象。和谐,作为一个经验性概念的首次亮相,也正是在古希腊哲学家纷繁的宇宙论体系当中。毕达哥拉斯派哲人通过类比,发现统治着天体运动的和谐,正如音乐中的和谐一样,其根源在于秩序。遵循这种秩序,宇宙间各天体按照数字所规定的间隔,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旋转。哲学所探索的永恒存在在数中被找到了。与经验不断变化的事物相对立,数学概念就其内容来说具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有效性标志,而因此又表现了固定的关系。通过数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类比发现,每个个别数字的有限性和数列的无限性,相似于有限的实体和无限的空间。有限和无限中有奇数偶数的对立,结果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在数字“一”中结合起来,因为“一”既有奇数的特性,也在偶数中出现(余数)。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中,所有以奇偶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对立面都在“一”之下统一起来,进而达到和谐,而世界就是数的和谐。可见,毕达哥拉斯所谓的和谐,其实正是一种规律,于此运用了必然性范畴;而以数字“一”统摄对立的思想,尽管稍显穿凿,却提示了和谐概念中的协同性和总体性。毕达哥拉斯的宇宙和谐中言未尽意的这种协同性,被赫拉克利特充分发挥了。赫拉克利特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最初造成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4]他认为宇宙是以逻各斯统一起来的整体。按照逻各斯原则,一切事物都像火那样变动不居,处于永恒的生成变化状态。生成事物之间有以下关系:转化的关系——事物无时无刻不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只是我们感觉不到;和谐的关系——对立的状态或相反的性质共存,产生出和谐;同一的关系——对立面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相对的关系——对事物某一方面的取舍有不同标准,事物的性质因评判标准不同而不同。换句话说,根据形式逻辑的排中律,a和非a已经涵括了所有的可能性,而正是a与非a的共存,使得宇宙在逻各斯(逻辑)中形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便是和谐的。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和谐的条件与其说是必然性,不如说是协同性。后世关于物理世界或宇宙的和谐观念,基本上继承自毕氏和赫氏。唯有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不具“合法性”。莱布尼茨基于唯理论传统,将宇宙视作一整体、一系统的观点,固然运用了总体性范畴,但他以充足理由律推出“上帝”而作为此系统的根据,这样就用因果性替换了协同性。这是以现实的可能性为代价篡夺的绝对必然性,其“合法性”最终被康德通过二律背反所证伪。可见,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各自有所侧重,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物理世界的合法的和谐观念均是以总体性、协同性、必然性为条件。
2.人类世界的和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和谐观念还原为正义,而正义的国家是以“善”的理念为目的。在他看来,既然世界作为整体,是由“善”的理念所统摄,从而形成一种有规律性的共同体,那么,国家要达到和谐,就必须由掌握了“善”的知识的哲学王来统治。哲学王也是一个人,只是由于其灵魂中理性占主导地位,因而方可担当统治者,而意志占主导的灵魂则担当国家的守卫者,欲望占主导的灵魂担当劳动者。这样就穷尽了人类灵魂的所有可能性。三种公民各司其职,各正其位,便形成了一个正义的、和谐的国家。可见柏拉图所谓的和谐,首先是以善这种最高的理念即最大的总体性为目标的;其次,公民尽管资质禀赋各不相同,在一个如此的关系中,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具有协同性的共同体。换句话说,理想国使可能性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性,那么也就达到必然性了(三种灵魂分别达到智慧、勇敢和节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国中尽管秩序井然、等级森严,但哲学王、守卫者、劳动者之间仍是平等和互动的。在整个分流过程中,公民是平等地经历层层选拔,才最终分为这三个类型的。每个公民(包括女性)在幼年时期均接受同等的基础教育,到一定阶段进行一次选拔,根据灵魂中不同的禀赋,甄选出劳动者和潜在的哲学王和守卫者。潜在的哲学王和守卫者继续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经过另一轮甄选,最终确立哲学王。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原因性的平等。在分流完成后,进入实际社会运作时,三种公民对理想国的贡献也是平等的。在理想国里,统治并不意味着特权。为了更好地保证哲学王和守卫者履行自身应尽的责任,他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严格公有化,不仅起居饮食要在一起,甚至生育也要按照国家需要进行。生活用品按需分配,杜绝奢侈之风。劳动者出于生产需要,可以组建家庭,积蓄私产。这是一种结果性的平等。柏拉图的这种和谐观念深深影响了其后的西方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正义论”,始终贯彻着一种对社会和谐的多层面思考,其手段均是把和谐还原为正义。而这种本质和谐论,是以总体性、协同性和必然性为先验前提的。
三、结语
至此,对和谐大观念的先验演绎基本完成。当然,先验演绎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和谐大观念的意义就盖棺定论了。康德有句名言:“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3]52。换句话说,先验演绎只是对和谐大观念的逻辑前提进行澄清:总体性、协同性和必然性只是和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作为一个经验观念的和谐,则需要社会实践主体通过实践所获得的经验来对其进行补充。我们这里所做的仅仅是在基础理论层面对和谐大观念进行逻辑剖析,找出判断和谐观念合法性的标准,希望避免和谐观念因被滥用而沦为无意义的厄运。哲学“是每一个人的事业,是关于大观念的事业”[1]3。对于“和谐”而言,也需要更多的实践主体去丰满这一大观念。
[1]阿德勒.六大观念[M].陈珠泉,杨建国,译.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2]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