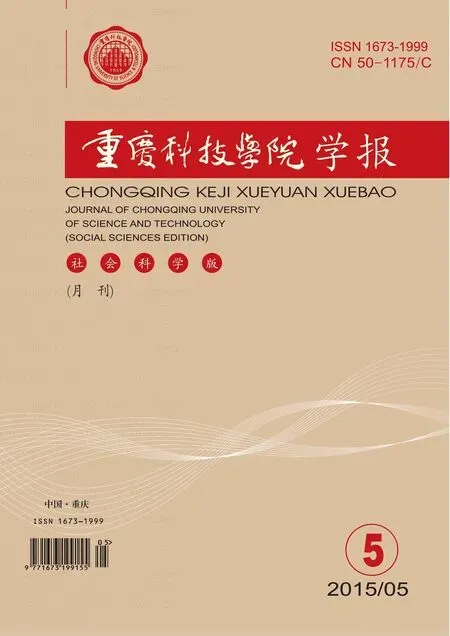朱熹理学思想简评
杨孝青
朱熹理学思想简评
杨孝青
介绍并分析朱熹关于“理”与“气”、与“太极”、与“心”“性”、与万物之关系的论述,以及朱熹的人性修养和“格物致知”论。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也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认识论肯定先验知识的存在又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朱熹;理学;唯心主义;修养;格物致知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四传弟子。在哲学的基本观念方面,他与“二程”特别是与程颐基本一致。朱熹采纳了周敦颐、张载和邵雍的一部分思想,并对“二程”学说加以扩充和发展,形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核心范畴为“理”(又称“太极”或“道”)。朱熹对《易传》“生生”思想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其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之中。
一、“理’与”气”
“理”“气”这两个概念在朱熹哲学体系中非常重要。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既存在着“理”,也存在着“气”。就其性质而言,“理”是化生万物的根本,属于形而上的“道”;“气”是产生万物的工具,属于形而下的“器”。“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就逻辑关系而言,“理”在“气”先。“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卷一)这是从抽象的理论上说“理”与“气”有先后。就实际而言,理与气是不相分离的。“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所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朱子语类》卷一)即“理”“气”相即,有“理”必有“气”、有“气”必有“理”。“理”是生成万物的根本或本源,它不随万物一起生灭,是永恒存在的。“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
天地万物只是一理,理通过气的演化产生万物。“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语类》卷一)“气”的展开分为阴阳二气,二气又分为五行之气(木、火、土、金、水),然后散为万物。“气”是形而下的,它有情、有状,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万物生成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的形式和“气”的质料相统一的产物。“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朱子语类》卷四)人与物都是由“气”所生,不过人与物所得之“气”稍有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朱子语类》卷四)总之,在朱熹看来,“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为先“气”为后,“理”生“气”并且寓于“气”中。
二、“理”与“太极”
朱熹发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无形而有理”。他在《太极图解》中认为“太极”等于“无极”,“无极”就是“太极”。“太极”之中含有万物之理,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及最高标准。“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致耳”(《朱子文集·答程可久》)。朱熹认为,宇宙之中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太极”,它是万物的生成和存在的本源和依据。每一个物自身又都各自存在着“太极”。“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朱子语类》卷一)“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种“太极”包含万理,万理也分别完整地体现“太极”,即是程颐所说的“理一分殊”。罗光指出,朱熹“理一分殊”具有四重内在的逻辑层次关系,即“道一理殊”、“理一气殊”、“理一事殊”和“体一用殊”。其中,“前两层为形上本体论层次,后两层为形下自然科学层次”[1]。
天地之间,理一而殊。天地只有一理,它是完全的,并且包含宇宙万物的理。万物分有天地之理,因而能生出各种物体。天地之理相同,各种物体的理有所不同。这种分殊是物类的分殊。朱熹说:“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朱子语类》卷五十九)人得天地全部的理,物得天地部分之理。天地之理分于物体之中,构成物体的种类。理一而殊的关系,是由于“气”的限制。人有合于人之理的气,犬马有合于犬马之理的气。物体种类之理,来自天地之理。物体种类之理也相互不同,这种差别来自“性”。《中庸》曰“天命谓之性”。天下没有无“性”的物体,一物的“性”就是该物的“理”。“理”不仅表现为天地万物之理,也是日常人伦之理,“如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礼;未有父子,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以此类推,按他的意思,封建等级秩序的设定是先天存在的,也是永恒不变的“天理”。
三、“理”与“心”“性”
在“理”与“心”“性”问题上,张载主张“性本心末”;“二程”主张理即心即性。朱熹一方面认为性即理,另一方面他又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即是天理,天理是绝对的善,所以人的本性也是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的交感,而气有善恶,气有清浊昏明,人禀受的气不同,于是表现出圣、贤、愚与不肖的区别。禀得至纯清气,不为物欲所累者即为圣人。禀得清而不纯之气,稍微为物欲所累,而能加以克除者即是贤人。禀得昏浊之气,为物欲所蒙蔽者,即是愚与不肖。人性没有不同,只是由于禀得气的不同才有善恶。朱子认为,“孟子说性善,只记得大本处,未说到气质之性细碎处”(《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因为孟子只论性不论气,所以不全面。冯友兰先生对此评论道:“朱子以为如此说法,可将自孟荀以来儒家所争论之性善性恶问题,完全解决。”[2]379朱熹从“理”“气”的关系上解决了儒家性善论的依据。
四、“理”与“生生”
朱熹认为天地之理具有化生万物的本心,这种本心生生不穷,且能够在人的心灵中完全显露。“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包着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物得此生物之心为心。”(《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天地的生物之心,在人则可以称为“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宋代理学家首先将“仁”与“生生”联系起来的是周敦颐。他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周敦颐集·顺化》)程颢也将“仁”视为“生生”。他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认为“仁”为爱之理,并将“仁”与“生”联系起来。他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为仁,犹曰行仁……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四书章句集注》卷第一)“发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朱子语类》卷五)
朱熹发挥《易传·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说,将变化的过程总结为:“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变化的根源是阴阳两气的交互作用。“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万物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这种生生之理的变化体现在一切事物中都是对立统一的,也就是朱熹所说的“物无无对”。“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当均平,无无对者。惟道无对。”(《朱子文集·答胡广仲》卷四十二)朱熹认为除了“道”以外,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之中,不但一物与他物彼此对立,一物之中也有对立。他认为万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且变化是有规律性的。同时,他又认为有一个绝对静止不变的“天理”(或“太极”)的存在,而这“天理”表现在人伦之中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这就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永恒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五、修养论
朱熹认为人得全部生命之理,因人的气最为清,气清则表现为精神性,故可以说人的生命是精神性的生命。人心本仁,仁总摄一切善德,心灵的生命即是仁义礼智信的生命。仁义礼智信发于人心,现于人情。情为心之动,动而皆中节谓之善德。圣人因为没有私欲,故具有全体之德,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卦》)。普通人由于受私欲所蒙蔽,不能完全识得天理,就需要通过修养来复其“性”。关于修养的方法,朱熹继承了程颐“主敬”与“致知”的修养论。“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敬”要做的心中“必有事焉”,也就是通过“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在“豁然贯通”之后,“则众物之表里粗精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章》)。
此外,朱熹还从“道心”与“人心”来进一步说明人性的修养问题。所谓“道心”乃是绝对的善,不为物欲所蒙蔽,是从“理”发出来的“心”,故“道心性微”。所谓“人心”,乃是从“气”发出来的“心”。得人心之正乃为天理,不得人心之正乃为“人欲”,故说“人心惟危”。凡圣皆有“道心”和“人心”,都是饮食男女,也都具有“仁义礼智”。圣人之心是“道心”起主导作用,能够克服“人心”的私欲,这就是圣人的修养的方法。朱熹进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其作为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以此恢复人的“天命之性”。这种主张后来被统治者所利用。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在南宋以后,封建统治者利用朱熹关于辨别理、欲的学说,作为严酷地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3]。
六、格物致知论
在认识论上,朱熹的观点与程颐大体一致。程颐认为,“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格物穷理,先是一件一件去求,然后才能做到融会贯通,才能认识理的本质。朱熹在《大学章句》第五章对“格物致知”论作了详尽的诠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粗精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朱熹的认识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心包含有天赋的知识。天赋的知识即是天理。人之所以不能认识天理,是由于受物欲所蒙蔽。人要去掉物欲,反观内心,才能唤醒心中的天理。
第二,致知在“即物而穷其理”,这是一个由内向外求的过程。格物,则由明白物之理进而推到明白内心的天理,是一个由外向内求的过程。二者的结合,即是内外一理,物我一理。“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其实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朱子语类》卷十八)
第三,格物致知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只有用力之久,方有可能“豁然贯通”。这就强调了知识的累积和顿悟的重要性。“朱熹相信只要不断格物穷理,终必能够彻法源底,到达豁然贯通的境界”[4]。
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由博反约”,即在博学的基础上掌握知识的规律性。他还强调“严密理会,铢分毫析”以及“推类以通之”等方法,这些都牵涉到了逻辑分析的方法问题。在知与行的问题上,朱熹强调“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他虽然肯定先验知识的存在,但又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十四)知与行相辅相成。
七、结语
朱熹建立了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学说影响深远,成为南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倡导的正统思想。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已经朝着科学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冯友兰先生认为,朱熹的哲学不是普通的唯心论,而接近于现代的新实在论。但是,朱熹主要关注的是伦理学而非逻辑学,故其格物致知论没有朝着近代科学的方向发展。“惜在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朱子在此方面,亦未着力。故其所谓理,有本只应为逻辑的,而亦与伦理的相混。”[2]390朱熹之后的理学家们都没有发展出严密的逻辑学体系,这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1]罗光.形上生命哲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130.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张岱年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35.
[4]刘述先.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74.
(编辑:米盛)
B244.7
A
1673-1999(2015)05-0004-03
杨孝青(1976-),男,六安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六安237158)思政部讲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2015-02-05
2013年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思想政治教育专项重点课题“自媒体时代高职思政课自主学习模式研究”(2013SZXM122);2013年安徽省青年人才基金项目“高职院校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地域文化运用研究”(2013SQRW143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