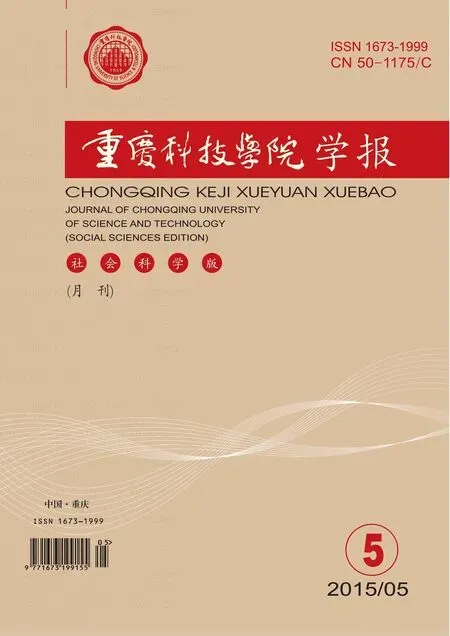西方哲学中的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初探
蔡修翰
西方哲学中的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初探
蔡修翰
身体与灵魂(或心灵)的关系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的一个问题。介绍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斯宾诺莎等人的相关认识。对灵魂高于身体的观念和身体相对于灵魂的作用及灵魂的自由问题等进行了分析。
西方哲学;身体;灵魂;理智;感知
从智者学派将哲人的视线从自然引向人自身以来,身体与灵魂(或心灵)的关系一直就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早在智者学派扬名之前,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经涉及灵魂与身体的问题。信奉灵魂不朽似乎是从神话时代遗留下来的习俗。毕达哥拉斯学派接受了奥尔斯教派的灵魂观念,认为人的死去只是灵魂从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之中,灵魂能够通过哲学这种理智思辨与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得到净化。从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灵魂与身体的一种态度,即灵魂可以不朽而身体会朽。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哲思与音乐视为灵魂净化的手段,开创了灵魂净化的两条道路:理智与艺术。这两条道路不仅直接开启了希腊三贤的哲学思辨,间接影响了基督教哲学,还与千年之后谢林的“艺术直观”和海德格尔的“诗与思”等遥相呼应。正如罗素所言:“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来的。如果不是他,基督徒便不会认为基督就是道。如果不是他,神学家就不会追求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逻辑证明。”[1]
一、灵魂高于身体的观念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认为,灵魂是整个宇宙的主导原则,而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灵魂则是身体的支配力量,是生命的源泉。柏拉图“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灵魂,在他看来,人不是灵魂与身体的复合,而是利用身体达到一定目的之灵魂”[2]53。柏拉图的灵魂说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相近,可见的身体支配可感的感官系统,而不可见的灵魂则负责不可见的理智思考,负责理智的灵魂高于支配感官的肉体。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与欲望3个层次。理性是纯然灵魂的,因此也就处于灵魂的最高层。欲望依附于肉体,因而是灵魂的最低层。在柏拉图看来,身体不仅是可朽的,而且是灵魂堕落后的某种形式。这一点在柏拉图的认识论即灵魂回忆说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原本高高在上的灵魂因为某种原因而堕入肉体,人认识事物的过程便是灵魂在肉体中回忆的过程。这种学说后来影响到基督教哲学,直接与基督教禁欲主义相联系。
在古希腊另一位先贤亚里士多德那里,身体即便不再是灵魂堕落后的器皿,但其地位依旧被置于灵魂之下。亚里士多德将身体与灵魂统摄在其“四因说”下,其中人的躯体是质料和潜能,相应的灵魂则是形式与现实。“隐德来希”(现实)是亚里士多德最关注的概念。海德格尔说:“存在者之存在就在于这种存在状态。而这种存在状态即在场,柏拉图称之为相,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现实。”[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命体是由灵魂与身体的结合,灵魂赋予身体以形式,使身体的潜能转化为一种现实,这种转化正是生命产生的过程。尽管亚里士多德仍然将灵魂描述为“是在原理意义上的实体,它是这样身体是其所是的本质”[4],但在其灵魂说中,灵魂已经不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能够离开身体而独立存在。
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中世纪的神学与哲学,身体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灵魂的质料置于灵魂之下。基督教强调“彼岸”性,加剧了人们对“此岸”身体的轻视。古希腊开始萌芽和成型的灵魂不朽、身体可朽观,在中世纪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笛卡尔的哲学第一命题是“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所有外在的物体性的东西都是不可靠或值得怀疑的,只有精神性的“我思”具有直观的明证性。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一和第二个沉思中,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大致推理过程。首先,由于经验生活的不可靠性,所以不得不抛开所有的固有的认识,并在怀疑一切的基础上重新对世界进行认识与把握。在“感官其实是会骗人的”这一基本前提下,笛卡尔发现,除了“我思”之外,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甚至像“我在这里,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手上拿着这张纸”[5]15这一类从经验生活角度看上去是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因为这可能只是个梦境而变得可疑起来了。然而,“我思”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怀疑的。只要我对任何事物产生思考,只要我对自身的存在萌生考量的思维,那么,“我思”本身就是可以被确定的,这一推断不需要任何辅助说明。因为我会对我的存在进行思考,那么“我”也必然存在;如果连“我”都没有了,那么“我思”就无法产生。“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5]23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基点区分了精神性的思维与物体性的广延,这种身心二分的二元论也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基点。这一基点事实上彻底否定了身体的明证性,而将与精神思维直接相连的灵魂放在了第一性的位置上。这种身心二元论的影响一直在西方哲学中延续着,上承毕达哥拉斯的理智与感官的二分,下启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等。
由此可见,灵魂高于肉身的观念的源远流长与根深蒂固。这种观念能够长期流行,一方面是由于哲人们的思考与宗教的训诫,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的生活经验与美好愿望。生活中力不从心和身不由己的经验,让人倾向于相信灵魂的轻盈与纯粹,倾向于笃定肉身的沉重和欠然。无论是肢体上的残疾还是先天身体条件的欠缺,都使得原本平等的灵魂显示出了差异。当瘸子在梦中获取奔跑的经验,他便开始相信灵魂本身具有奔跑的能力,只是这副残疾的肉身拖累了灵魂。从思想上的灵魂不朽、身体可朽到经验中的灵魂安然、身体欠然,似乎都在验证着“灵魂高于身体”这一古老的观念。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是令人困惑:为什么轻盈的灵魂会堕入到沉重的肉身之中?
二、灵魂的欠然与身体之身位
为什么原本轻盈的灵魂会甘心降临到沉重的肉身之中?双腿残疾的人可以在梦中奔跑,由此可以窥见灵魂脱离肉身的一种形式——做梦。那么,为什么对肉身不满的灵魂不选择永远栖于梦境之中?如果说梦的实现并非一种现实,而仅仅是被禁锢在肉身中的灵魂的一种慰藉,那么死又如何?死是可朽肉身腐朽的开始,难道不是灵魂自由的开始么?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潜意识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残疾人的梦中奔跑,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构建而已。在梦中奔跑和在想象中奔跑,本质上是无异的,都是不真实的。让灵魂栖于梦中,犹如让人沉醉于幻想。如果这是可行的,那服用海洛因等致幻药物在伦理上便是可行的,而这一结论显然与我们日常所受的道德教育截然相反。人们在伦理道德上否定梦与幻觉,其实是在否定梦与幻觉的真实性。
柏拉图说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海德格尔说此在是“向死而生”的。为什么要“练习死亡”和“向死而生”?为什么不直接选择“死”本身?基督教教义说“不可自杀”,那是对摩西十诫中的“不可杀人”的延伸。如果死亡能够使灵魂挣脱身体的禁锢,进而使之自由,那死本身就应该是一种伦理上的善。佛教讲轮回,基督教讲安息,却又反对人自杀。这关于“死亡”的吊诡,也恰恰源于“死亡带来灵魂的自由”这一命题的不真实性。
梦和幻觉之所以不真实,恰恰是因为在梦境或幻觉中灵魂依然是不自由的。这种不自由,并不是由身体带来的,而是灵魂本身的欠然。死亡并不能使灵魂获取自由,摆脱这种先天的欠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认为,人的灵魂会受到外部的影响,产生“同情”;这种“同情”的力量会推动人的行动。在普罗提诺看来,人的灵魂既可以通过思辨和关照追求神,也可以耽于肉体而陷入身体不能自拔,然而这种表面上的“选择”并不是灵魂自由做出的真实的选择,而是由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尽管普罗提诺也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堕落之道,但他至少为我们指出了一种可能,一种灵魂本身欠然的可能。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是否真如普罗提诺所言,肉身仅仅是一条坠落的道路?我们不妨将身体分为纯粹意义上的身体和延伸意义上的身体。纯粹意义上的身体就是一般的肉身概念。就像刘小枫在《性感、死感、歌声》里解读的薇娥丽卡那样,身体的欠然让她永远无法活着成为歌唱家,哪怕她的灵魂住在歌唱家的梦想里。由于身体先天的第一性,所有寓居在肉身里的灵魂都不可能借由他者来完成梦想,尽管我们有时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梦想的影子,但是,每当你独身一人时,灵魂能够清晰的感觉到:我的梦想,并没有在轻盈地飞翔。怀着灵魂的梦想,薇娥丽卡登上了舞台。抱着身体的欠然,薇娥丽卡死在了舞台之上——成了一名死去的歌唱家。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更加笃定:灵魂的飞翔必须以牺牲身体为代价。
身体,对我们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第一性。疼痛、饥饿、口渴,这一切都直接地显现于精神,不可避免地和“我思”捆绑在一起。所有对人而言具有第一给予性的东西,都可称之为身体。即便你的身体不在了,或者被笛卡尔们普遍怀疑掉了,但是,你身体的位格仍将承担起沉重的第一性。这些具有第一性的“身体”像是一个标签,贴在人身上,一旦揭去这些标签,灵魂将无法认识自己的身体,仿佛身子是别人的一样。这种标签式的事物是亘古便有的么?还是与面具(脸谱)化的人生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确实可以相信,对灵魂而言,身体是不可或缺的认识自己的方式。灵魂之所以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不能离开身体单独存在,正是因为灵魂需要借由身体来认识自己。借用亚氏的命题来说,身体在此就不仅仅是质料,它也是一种形式,一种借助自身的位格而成为形式的现实。
三、身体的感知与“身心平行”观
身体的感知是第一性的,是他人无法取代的,是对个人而言独一无二的,是我在的直接表征。身体的感知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在近代经验论者那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洛克认为人类知识的对象是观念,而观念的唯一来源就是感觉经验[6]。在贝克莱那里,这种观念源于经验的观点被表述为“存在即被感知”。然而,身体的感知和经验之间,难道没有经过一层灵魂或是理智的加工程序吗?如果身体的感知需要灵魂的加工才成为经验,那灵魂不是依然得以居于经验之上吗?这样的诘问看似有理,实际上却为身体虚设了一个前提,即感知必须转化为经验。
在公众交往活动中或社会交往体系里,感知确实有必要转化为经验。我们观察天空的颜色后,必须将这一感知转化为公众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经验概念,才能够与人交流,比如我们要对人们说“天空是蓝色的”。可是,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公众的。“我在”本身是一种个人性的体验,正如身体感知的个人性一样。我被刀子割了手,我的身体确实和大家一样会感觉到痛感,但是这种痛感却是私人化的,没有人能够绝对的明白我的痛感,即便他也被刀子割了手。我看到的米饭确实和大家看到的米饭一样是白色的,这是我将感知转化为公众符号系统后的结果;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保证我所看到的白色米饭和他所感知到的白色米饭是一模一样的。个人身体的独特性正在于此。这种纯粹个人“我在”的私密体验不仅是“我在”的直接明证,更是“我在”异于他者的根基所在。近代的唯理论者看到了大家普遍同意的原则,却忽视这些原则并非来源于个人的感知,更忽视了这些普遍同意的原则背后那私密的个人感知。休谟说:“我们全部的个别知觉都是个别的存在物;而且心灵在个别的存在物之间无法知觉到任何实在的联系。”[7]休谟因此被称为温和的怀疑论者。在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个人性体验的参与、选择与实现都与身体的私密感知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存在”是一个只能适用于个人的概念[8]。
关于身体与灵魂的关系,许多古代哲学家都坚持灵魂高于身体的观念。但仔细考量哲学史会发现还有另一条认识路径。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快乐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身体健康,二是心灵宁静。这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不能独存。身体遭受痛苦时,心灵就不能宁静;心灵受到干扰时,身体健康也会受损害[2]85。可见,身体健康与心灵宁静是同等重要的。在近代哲学中,斯宾诺莎提出了“身心平行”观。斯宾诺莎认为人是由心灵和身体构成的,“心灵与身体是同一个体,不过一时由思想这个属性,一时由广延这个属性去认识罢了”[9]。在斯宾诺莎这里,心灵与灵魂是同一个概念(亚里士多德将心灵视为灵魂中用于思维和判断的部分)。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对后世也有重要影响。比如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就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他在其代表作《心的概念》中认为身心不在一个范畴内,因而是平等的不可比较的。
关于身体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的一个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总是会思考身体与灵魂(或心灵)的关系,虽然他们的观点或结论有所不同,但总的倾向是既重视心灵又重视身体。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5.
[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海德格尔选集:上卷[G].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597.
[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5]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8.
[7]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74.
[8]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
[9]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7.
(编辑:米盛)
B016.98
A
1673-1999(2015)05-0011-03
蔡修翰(1990-),男,贵州大学(贵州贵阳550000)外国哲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法哲学。
2015-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