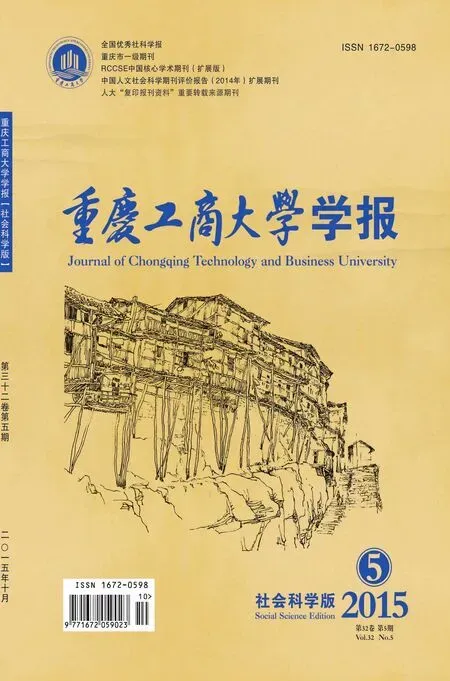《垂死的肉身》中性爱书写的伦理拷问*
杜明业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引言
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犹太作家之一,美国当代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自1959年出版《再见吧,哥伦布》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28部小说。他曾获得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等多项大奖,也是迄今为止第三位在世时就被收录到“美国文库”中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涉及大量露骨的性描写,成为评论界和读者非议的话题。《波特诺的诉怨》(1969)、《欲望教授》(1977)和《垂死的肉身》(2001)等小说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小说体现了怎样的性伦理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苏鑫、黄铁池的论文结合罗斯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分析了罗斯对“性爱的多重理解”,指出“罗斯不断地以一个男人的视角来书写他不同年龄阶段的性欲感受,从最初刻意地以‘性越轨’来反抗犹太传统对新一代青年的束缚到老年时千帆过尽、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1]。而袁雪生则指出,罗斯的小说“充满着对传统犹太文化的继承与悖离,刻画了性爱主题下的伦理拷问、反叛意识里的道德冲突和生存处境下的命运反思,其中包含了犹太社会中家庭伦理道德、宗教伦理道德乃至公共伦理道德的嬗变,体现了深刻的伦理道德指向。”[2]但以上论文对罗斯小说中的性伦理问题并没有展开充分论述。本文拟以《垂死的肉身》为个案研究罗斯的性伦理观。
一、美国性革命的回应和余响
性伦理即性道德,是调整男女两性之间的性行为以及性行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性伦理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伦理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就开始有了包括性关系在内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性伦理也是现代社会中调节两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20世纪中期,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冷战、越南战争、民权运动、肯尼迪遇刺、性革命、女权运动等事件之后,美国人的心理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性革命“使得传统性观念受到公然的挑战,这涉及婚前性关系、避孕、堕胎、同性恋、黄色书刊等一系列问题”[3]。性革命还重新点燃了女权运动之火。女权运动几乎涉及从堕胎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广泛而深刻。新女权运动领导之一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的发行量曾高达100万册。随着曾被称为“色情小说家”D.H.劳伦斯的作品在美国的解禁,被60年代反主流文化誉为自由和性解放的先知——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1934)的出版,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5)的问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性爱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大变化。罗斯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其思想观念也受到影响。这一点在罗斯的《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1988年)中都有提及。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美国60年代爆发的一系列反文化运动,尤其是性革命运动,对罗斯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识到性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与批判力。在他看来,性是属于人的最基本的一种需要。性本能、性心理是作为社会建构物而存在的,最能体现出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方式和人的矛盾心理,对性欲书写能直接而真实地反映出人究竟为何物。在这种创作理念支配下,具有叛逆性的罗斯从《波特诺的诉怨》开始对性欲、性自由有了较多的描写。主人公波特诺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而难以找到发泄处,开始了性的冒险。通过对波特诺变态的性心理和性行为的大胆书写,小说成功地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性革命对年轻人心理的冲击,体现了主人公在与社会的剧烈冲突中所面临的性困惑,成为那一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垂死的肉身》是罗斯“凯普什系列”的一部,讲述了大卫·凯普什(David Kepesh)与康秀拉·卡洛底斯(Consuela Castillo)的一段忘年之恋。小说是凯普什用第一人称“我”以回忆的形式而展开的。小说反复提及霍桑和清教徒时代在涉性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旨在提醒读者关注美国从清教徒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性观念的流变。霍桑的《红字》对迪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白兰的性爱的描写早已为人所熟知。他们对性爱的追求受到了当时清教徒的压抑和惩戒。虽然《垂死的肉身》充满了“肉欲”的叙事,但作者并非对性爱的单纯描写,而是将它放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下予以观照。
凯普什早年和其他女性之间的性爱关系,折射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性革命对普通人伦理道德生活影响的余绪。凯普什声称自己于1956年结婚,是60年代性革命的受害者,他在那个年代被他的妻子给甩了,原因是妻子发现了他和“流浪女孩”在一起。妻子留给他的是“一个42岁的憎恨我的儿子”——肯尼。[4]73珍妮·怀亚特是另外一位60年代富有个人魅力的活跃分子,具有反叛精神,是性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和实践者,与卡罗琳等数人组织成一个“流浪女孩”的小集团,“她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反叛自己”[4]57——吸毒、乱交,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因为“美国60年代珍妮·怀亚特们知道怎么操作那些狼吞虎咽的男人……她们知道去什么地方能得到快乐,而且她们知道怎么无所无惧的放纵情欲。”[4]64-65但到了90年代,当肯尼回忆珍妮·怀亚特的经历时,指责说:“她现在在哪?经历了多少失败的婚姻?多少次精神崩溃?这许多年她住在哪家精神病院里?”[4]99。显然,肯尼对60年代的混乱抱有强烈的斥责态度。当然,肯尼和凯普什一样,也是婚姻不幸的人。步入老年的凯普什曾对自己早年的各种不当行为开始深深的自责与反思,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带给家庭和儿子的不幸:“注意,我已不属于这一年龄。……我用一把很钝的工具达到了我的目的。我给家庭生活及其旁观者带去一把锤子。也将这把锤子带入了肯尼的生活。我还是一个使用锤子的人,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惊奇。”[4]125到了90年代早期,凯普什和康秀拉又产生了不伦的恋情。
这里,我们不能用当下中国的伦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或者是教师职业道德标准去裁决凯普什的性爱行为,必须还原到当时的伦理环境去衡量。聂珍钊教授指出:“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5]如果我们用今天中国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凯普什的性爱行为,会认为他的行径是完全不符合一位大学教授的身份的,与他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极不相符。但是,我们要明白,凯普什的早期各种性爱行为是发生在60年代的美国,他与康秀拉性爱行为发生在90年代的美国。我们显然不能拿现在中国的伦理标准去框套凯普什的行为。另外,康秀拉除了与凯普什之外,还先后与五位青年男性的行为,凯普什的朋友乔治·欧文也先后与数位女性有过性行为,凯普什的儿子肯尼也是如此,对这些人性事的书写,我们也必须回到小说产生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否则,我们的阅读和阐释就有越位之嫌。
我们稍微作一些推测,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1999年,康秀拉32岁,也就是说她出生在1967年。那是美国历史上的“喧哗与骚动”的年代。当然,她一直坚持自己是古巴人,而不是美国人。而在小说的最后,她患上了乳腺癌,这蕴含某种深刻的意义,它暗示美国在性问题上已经出现了病态的征兆——作为一种社会潮流的性革命运动即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衰亡。康秀拉让凯普什为她拍摄的裸露胸部的照片,但是,她并没有交代如何处置这些照片。冲洗出来欣赏?留存下来作为忆念?小说将这些悬念交给了读者。这些照片构成了身体之美的实证,它更像是美国性革命运动走向衰落的遗物。凯普什与康秀拉的性爱关系不是以爱情和婚姻为目的,但又很难说是一种病态的。因为,两人曾经那么如漆似胶,情投意合,两人的性爱关系终结于年龄的差异和衰老的逼近。小说的结尾,两人的身心都受到了重创,最终各人都不得不回归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彼此虽然也获得了满足,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年轻的康秀拉和年老的凯普什之间的性爱跨越了年龄之鸿沟。康秀拉以自己的年轻和魅力吸引和征服了凯普什,从而克服了她与凯普什之间固有的年龄和地位的障碍。而凯普什则在康秀拉那里重拾青春、活力与激情,他在奋力地与时间进行抗争,而性则是他进行抗争的最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性不只是肉体的摩擦、浅薄的玩笑。性还是对死亡的报复。别忘了死亡。千万别忘了它。是的,性也受制于死亡的力量。”[4]78他认为:“腐败的并不是性,而是其他的东西。”[4]69在他看来,性会搅乱正常的生活秩序,影响人的情感。他明白,与外界的社会力量相比,性这种力量实在是有限的,然而什么是比性更大的力量呢?他又找不到。对他而言,性可以打破旧有的秩序,激发生命的活力,也让他直接触摸到了难以克服的死亡力量。
二、犹太传统性伦理观的反叛与张扬
可以说,性是罗斯借以表达人性的重要途径,对与性相关的男性行为意识的刻画反映了罗斯对当代美国犹太人生存概念的理解。根据犹太传统,“性爱是值得肯定的,性欲不是可耻的或者有罪的。如果夫妻互敬互爱,上帝就与他们同在。子女是耶和华的赐福。大量生养在《圣经》中被认为是大福,不生育被认为是悲剧和耻辱,没有子女则是灾难。”[6]而性爱将会带来民族繁衍,和谐的性爱符合犹太教对于完整和智慧的追求。也就是说,罗斯对性的关注符合犹太文化传统中对性的认识,但也充满了某种反叛。虞建华曾经概括了《波特诺的怨诉》《乳房》(1972)和《欲望教授》三部小说的共同之处。其中之一是“小说的主人公都表现出对性的痴迷,把性当作反叛传统文化的武器,以情欲填补空虚,因此小说探讨的是精神危机的主题。”[7]
罗斯的作品中有关性的表述比比皆是。略举数例。在《波特诺的怨诉》中,波特诺一心追逐非犹太女孩,幻想通过征服非犹太女性来征服美国,犹太“好儿子”的概念完全被满脑筋性爱与满口抱怨的“坏小子”波特诺所摧毁;在《欲望教授》中,罗斯描写了年轻时凯普什的混乱的性生活;在《乳房》中,罗斯以卡夫卡和果戈理的笔法写出凯普什一夜之间变形为女性的乳房,变形后的凯普什唯一拥有的快乐是性快感,却并不能自由地享受这份快感;《凡人》(2006年)里的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人对性爱的过分追求毁坏了自己的家庭。
那么,为什么罗斯的作品中要有如此多的性爱书写?罗斯自己曾坦言:“犹太作家,特别是马拉穆德和索尔·贝娄等人,都将犹太人写得过于洒脱,在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显得缺乏性欲,过于道德高尚。”[8]而罗斯则敢于突破这种陈规,在小说中大胆地书写性问题。他更多地从当代美国人的角度去重新认知犹太传统,结合犹太人所处的时代反思犹太传统中相对保守的成分,以开放、坦诚的态度重新审视人的性爱需求,作品中的性爱标志着一种道德上的反叛。同时,性爱也成为他揭示人类个性的重要手段。罗斯曾采访过同样注重性爱主题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这样解释性爱:“目前,性不再是禁忌,仅仅有性描写,已经明显使人乏味。……我感到一个表现身体之爱的场景产生出异常强烈的光芒,突然揭示出人物的本质,总结出他们生活的形式。”[9]两人都是对性有过大量描写的作家,昆德拉的观点为我们理解罗斯作品中的性爱书写提供了参照。
但罗斯对性的书写并非犹太传统中的和谐性爱,相反,在《波特诺的怨诉》《我作为男人的一生》(1974年)和《萨巴斯的剧院》(1995)中,主人公一再地用几乎反常的性言行来表达生存的迷茫与困惑,或者是精神上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看,男主人公对性的控制欲望反映的是犹太个体与美国新教社会的冲突。如果说《欲望教授》中年轻的凯普什过着放荡的生活,在三角恋爱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那么,《垂死的肉身》里的凯普什的角色相对单一。他先后与米兰达、康秀拉·卡洛底斯、卡罗琳·里昂斯、珍妮·怀亚特等多位女性有染,而缺乏真正的爱情。对他而言,性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不曾冒险涉足性行为,那么他一生中就少掉三分之二的问题。”[4]38可见,性爱在凯普什心中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获得性爱,凯普什才能填补因为妻子离去而留下的情感空白。他和康秀拉的交往是最多的,也是时间最久的,在长达一年半的交往中,康秀拉是他课堂里的学生,生活中的情人。因为,从一开始康秀拉就告诉他说她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
在罗斯看来,真正理想的性爱关系应该实现“灵与肉”的统一,《欲望教授》中的凯普什的性游戏违背了传统的爱情伦理与公共伦理,性泛滥造成的心理阴影使他无法拥有真正的爱情。作为一个信仰犹太教的犹太青年,凯普什追求的不是自我与上帝的情感纽带,也不是精神与灵魂的宁静与超然,而是肉体的愉悦。这显然与传统的犹太伦理道德相悖,它体现了年轻一代犹太人在古老传统和现代文明缝隙间生存所导致的自我困惑与人性异化。而在《垂死的肉身》中,凯普什已经步入老年。他和康秀拉初识时已经62岁,而康秀拉只有24岁。两人年龄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段忘年恋将会以悲剧而结束。因为,凯普什时时在提醒自己,年岁已老。在第二次与康秀拉做爱后,他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你绝不是感觉到年轻,而是痛切地感觉到她的无限未来和你自己的有限未来……你极为痛苦地感到了自己的年老,不过以一种新的方式。”[4]39
罗斯笔下塑造了一批犹太男性主人公形象。有研究者指出,“罗斯的主人公以犹太男性为主,与之对应的是性成为了男性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各种表达:性幻想、性自白、性变态。性成为犹太男性表达自我、证实自我、重塑自我、表现力量的文学象征。”[10]在《垂死的肉身》中,凯普什也是这样一位形象。
凯普什是一位大学教授,主持公共广播台星期天早上节目的美学家,纽约电视台权威评论员,“实用批评”课老师,卡夫卡手稿的拥有者……这一系列的头衔、地位和光环为他赚足了学生的眼球。小说开始时,62岁的凯普什和24岁康秀拉发生了一段非同寻常的爱欲关系。双方都迅速坠入爱河,难以自拔。凯普什迷恋康秀拉的身体。在康秀拉身上,凯普什找寻到了曾经失落的激情、逝去的青春、难以遏制的欲望。一次又一次的性爱,给双方都带来了身心和肉体的满足。后来,凯普什感觉自己人已老,也找不到恰当的身份而缺席了康秀拉的毕业典礼,康秀拉失望地离他而去。在康秀拉离开的日子,凯普什极度失落,有许多近乎性变态的行为,如通过手淫获得性满足:“我(凯普什)弹奏贝多芬时我手淫。我弹奏莫扎特时我手淫。我弹奏海顿、舒曼、舒伯特,同时脑子里浮现出她的形象手淫。因为我无法忘记那对乳房,成熟的乳房,乳头,还有她把双乳搭在我的腿上并且抚弄我的方式”[4]114-115这一段近乎色情的描写刻画了这样一位心理严重扭曲的所谓的“教授”。只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凯普什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这一战斗中没有和平和不可能有,因为我们年龄的差异和挥之不去的心酸。”[4]44对他而言,“年龄的伤痕”(the wound of age)越来越大,最终,他意识到自己的衰老与垂死。
三、性爱与死亡的绝望挣扎
凯普什对性爱的追求曾经让他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朋友乔治的突然死亡让凯普什体验到死亡的必然,自己不可避免的衰老和必将到来的死亡。所有这一切让他深感纠结。他感到了日益加深的“年龄的伤痕”和死亡的逼近,但对性爱的渴求又使他在其他女性身上获得满足。然而,“性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寻求,使其结束的不是由于达到了自我满足或由于明智,而仅仅是由于年老体衰。”因此,衰老和死亡改变了凯普什的生活观。对康秀拉而言,疾病与死亡把她更多束缚在孤独中,令人绝望。可以说,小说的后半部表现了这种性爱与死亡的垂死挣扎。
小说中浸透着衰老、疾病和死亡。在这种情景下,凯普什开始逐渐反思自己所追求的性爱自由还能否继续:“不管怎样,难道一个年近七旬的人还应该扮演人类喜剧中耽于肉欲者的角色吗?难道还要不知廉耻地成为一个易于产生性兴奋的纵情声色的老人吗?”[4]41凯普什最终选择了逃避,因为他无法面对业已逝去的青春与活力,无法回避自己的衰老和即将到来的死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普什畏惧的死亡却在年轻的康秀拉身上提前实现了,让读者颇为意外,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和可读性。
凯普什和康秀拉的再次相会被罗斯安排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千禧年来临之际。这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2000即将来到之际。凯普什接到康秀拉的电话——她患了乳腺癌,需要在手术前见他一次!康秀拉的到来是在旧年即将过去时,而离开则是在新年刚刚来临之时,具体说,“她大约是凌晨一点半离开我这里;她来时大约是八点钟。”[4]150相隔数年,两人相见后,相拥、抚摸、叙旧、感伤、拍照等细节的描述让人唏嘘不已。电视上转播着世界各地欢庆新年来临的场面。在其他人眼中,千禧年的到来是一个狂欢的日子,而在凯普什眼中,“新千年的除夕庆贺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大发作”[4]159。他说:“整个晚上,在电视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都是大决战的拙劣模仿,自1945年8月6日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我们家后院掩体里等待着这场大决战。它怎么不会发生呢?即使在那天晚上,尤其是在那天晚上,人们预先准备着最不幸的事情的发生,仿佛这个晚上就是一场漫长的空袭演习。等着令人恐怖的广岛列岛与世界上所有悠久的古老文明同归于尽。”[4]160罗斯把两人的相见设定在千禧年到来的特殊时刻,启发读者的思考:在这举世狂欢的日子,本该也是两人再聚首重续旧情极度喜悦的时刻,康秀拉却患上致命的乳腺癌,这难道预示两人都将终结于灾难之中?就像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一样,人类本身也将遭遇一场大劫难?
这世纪之交的相见非常富有意义。康秀拉已经三十二岁,没有了八年前的“谈吐得体,举止稳重,仪态优雅”[4]4,也没有了八年前的浓黑并富有光泽的头发,“不戴帽子的她看起来很吓人”[4]171。前后变化之大,凯普什感到震惊,认为“这个人已经接近死亡,是个垂死之人”[4]171。凯普什有点绝望的感觉:“死亡本身。这就是死。对死的所有恐惧就在那头上。”[4]172康秀拉选择这个晚上告诉凯普什自己的病情——乳腺癌。在凯普什眼中最美的乳房却遭遇了乳腺癌的侵袭。这不能不说具有巨大的讽刺性。两人在拥抱的过程中,凯普什感觉到了康秀拉的依然丰满的乳房。康秀拉不愿意和凯普什接吻,也没有与他上床,只同意睡在他怀里。康秀拉不介意,甚至想让凯普什多去抚摸几次自己的乳房,让他感受这最后的温柔。凯普什感觉到这种触摸“既有情欲又有温柔,既会使你产生怜悯之情也会激起你的情欲,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况。你既会勃起也会产生怜悯,两种感觉同时产生。”[4]144因为乳腺癌,康秀拉的乳房将被全部切除,美丽、丰满、性感将不复存在。也难怪康秀拉表现出无限的伤感,要凯普什给她拍照留影。而凯普什想到康秀拉的乳房将被破坏,有一种罪恶感:“这样太卑鄙、太无耻了,这对乳房,她的乳房——我只是不停地想,它们不能被破坏了!”[4]150这里,小说的叙事依然聚焦于康秀拉几乎完美的身材、即将割去的整个乳房和她的亚洲女性式的阴毛,但已经摆脱了前期赤裸的性爱场景描写,让读者对主人公的遭遇唏嘘不已。
康秀拉要凯普什给自己拍照片,试图“为如此爱她身体的我提供证明材料,证明她身体的优美和完美。”[4]156在拍摄过程中,康秀拉摆出了各种姿势,而且丝毫不遮掩。秀美的身材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凯普什的镜头前。此时的凯普什已经没有了欲望,有的只是逐渐加深的伤感。三十余张照片与其说是留给凯普什和康秀拉完美身材的回忆,还不如说是记录了人之垂死的进程。凯普什身体健康,但已经年逾70岁;康秀拉虽然年轻,但却有“百分之六十的生和百分之四十的死”[4]143的机会,留给两个生命的时间和机会都已不多,两人都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留恋,然而却又不得不面对“肉身的垂死”。
这次相见给了凯普什重新思考时代的机会,重新发现生命意义的机会。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已使苦难变得平常,人们对苦难的哪怕一点点清醒的认识也被最大的幻想所产生的巨大刺激消磨殆尽。……我感觉这个有钱的世界急于进入繁荣的黑暗时代。人类的一夜快乐宣告了野蛮.com的到来,适合适宜地迎接新千年的糟粕和庸俗。”[4]161面对康秀拉的遭遇,凯普什产生了深切的怜悯,因为死亡在逼近康秀拉。他认为,“她将死在我眼前,她现在就在慢慢地死去”[4]142。此时的康秀拉知道了“年龄的伤痕”,因为对她而言,未来的时日已经不多,只能“以接近死亡的远近来计算时间”[4]164。凯普什甚至想到:“她(康秀拉)坐在我旁边,经受死亡的审判。”[4]165面对死亡的逼近,康秀拉,这位流亡古巴贵族的后裔,表现出了对生命的眷恋和死亡的恐惧:“渴望我的生命。我抚摸自己,我用双手抚摸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是我的身体!它不能离开!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发生!它怎么能离开呢?我不想死!大卫,我怕死!”[4]166
当死亡逼近,时间变得格外的珍贵,小说中使用了关于时间的意象——节拍器。小说中多次写到了节拍、节奏,如“有些曲目如今已得心应手,但大多数乐曲都有大跨度的节拍,这就难为我了”,“是节拍器。小灯闪烁并发出间隙性噪音。那就是它的功能。你可以按你的需要调节节拍”[4]113。节拍器以秒计算,就像心脏。节拍器的停止,也就意味着心脏的停止,死亡的降临。在康秀拉身患癌症时,凯普什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幻想已经破灭,机械刻板的幻想,安慰人的想法,滴滴答答,一切按部就班地发生。她的时间感现在已经和我的一样了,死亡在加快,甚至比我还要绝望。实际上,她已经追上了我。”[4]165在这场性爱与死亡的游戏中,似乎没有获胜者。因为,在死神面前,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
四、结语
作为罗斯性“凯普什系列”中的一部,《垂死的肉身》写出了性的终结。小说中充斥了对身体和性的斑斓的书写,但罗斯绝不是为写性事而写性事的作家,否则他就会真正沦为写“脏书”①早在《波特诺的诉怨》(1969)问世时,因为小说中有大量污言秽语和不少猥亵淫秽的细节描写而被许多评论家称为“脏书”。参见Bernard F Rodgers,Jr.Philip Roth,P80.的人。性事的书写作为推动小说情节演进的助推器,融入了罗斯对性爱的沉思,寄寓了他对性爱伦理的拷问。其中既有对20世纪60—90年代期间美国社会历史的反思,对犹太传统价值观在现代语境中存在方式和意义的追问,也有对生命个体的理性与情感的关注,更是罗斯对包含犹太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生活的深度思考。
[1]苏鑫,黄铁池.“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菲利普·罗斯小说中性爱书写的嬗变[J].外国文学研究,2011(1):48-53.
[2]袁雪生.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J].外国语文,2009(2):42-46.
[3]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美国通史[M].吴金平,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705.
[4]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M].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6]赵锦元,戴佩丽.世界犹太教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38.
[7]虞建华.罗斯的手电筒:照进人心隐秘的深处(代序)[M]∥菲利普·罗斯.欲望教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
[8]苏鑫.死亡逼近下的性爱言说——解读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J].名作欣赏.2010(6):108-110.
[9]菲利·普罗斯:米兰·昆德拉[M]∥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15.
[10]薛春霞.越界、争执与突破[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13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