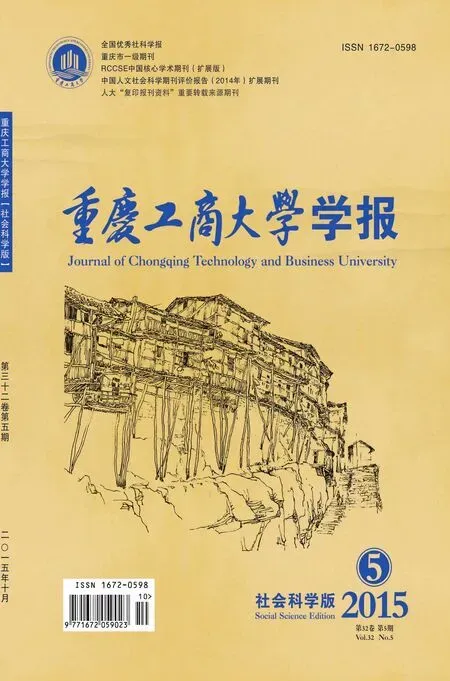刘咸炘韩愈研究述略*
陈开林,魏 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四川双流人。民国著名学者。一生笔耕不辍,勤于著述,虽享寿不用,却成果丰硕,总计著书235部,475卷,名为《推十书》。刘咸炘学贯四部,对文学素有积蕴,颇多灼见。新近整理出版的《推十书》戊辑四册除其自身创作的文学作品外,另有他的文学研究专著多部,如《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等,研治范围极广。对于韩愈,刘咸炘亦素有研讨。
韩愈(768—824)作为中唐时代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和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文人,由于多种原因的交互作用,往往成为后世聚讼的焦点。后人对韩愈其人其文的评价,因时代、评论者而异,其地位起伏极为显著。刘咸炘所作《订韩》,由于生前未曾刊行,不为学界所知。虽然篇幅不多,但极富价值,值得探究。本文拟对该书略作论述,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一、《订韩》撰写的原因及体例
《订韩》一篇,今收入《推十书》丙辑第四册,为未刊稿。题后注“己未二月”、题下一行注“此书成稿甚早,尚须删简,又有引前人说未钞全者”[1]1403。故今本《订韩》似为作者未竟之稿,且文中尚有二处残缺。“魏鹤山《韩愈不如孟子论》”条[1]1405、“史称愈明锐不诡随”条[1]1408,条后均有整理者按语:“以下有空页。”
刘咸炘注明《订韩》成书时间为“己未二月”,即公历1919年2月,成书年代甚早。然而在后人研究的韩愈论著中,《订韩》一直被忽略,故而其学术价值未能彰显。吴文治先生编《韩愈资料汇编》,凡四册,在《凡例》中指出“本书辑录从中唐至‘五四’一千一百余年间有代表性的评述五百三十余家[2]1”,其后汕头大学中文系所编《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中,收有张惠民先生的《1911—1948年间韩愈研究综述》[3]166-178,论列颇详,然均未载录刘咸炘《订韩》的内容。《韩愈集》的相关评注本亦未参考刘咸炘的成果。究其原因,恐为《订韩》未刊的缘故。
关于《订韩》写作的原因,《订韩叙》中有明确的交代。《叙》开篇提出:
唐吏部侍郎文公韩子退之,后世所称道德文章之宗也,从祀于孔子之庙。读书者莫不读其文学者,数三代以下魁儒,指不十屈必及焉。……咸炘读退之之书,窃尝有不惬于心,详而察之,然后知其多不虞之誉。[1]1403
韩愈在后世的地位,自其弟子大肆推尊,及至苏轼倡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4]3113之后,颇为尊崇。然结合具体事实,不难发现其中多有意气之辞,非公允之论。对此,刘咸炘有所指责。他认为:“李翱《行状》、皇甫湜《墓志》《神道碑》,其推退之之文,皆师弟之私。宋子京亦尊韩者,故撰《新书》本传,亦极推之,皆不可信也”[1]1439,对韩愈弟子、史书之记载表示怀疑。
尽管韩愈在后世有着极高的地位,但是对其诋毁污蔑之词亦不少见。要合乎知人论世之道,不仅要对韩愈的“不虞之誉”予以澄清,也要对其“求全之毁”予以辨正。刘咸炘指出:“近百年来汉学兴盛,言理则鄙程朱,言文则薄唐宋,其于韩子又不无过毁”[1]1403,因此,客观公正的态度,即是要做到二者兼顾,方能做到意气平和,不偏不倚。职此之故,刘咸炘在文尾总结道:
佐佑六经,粹然一出于正(《新书》);扶经之心,执圣之权,精能之至,出神入天(《行状》),何其言之易也!至于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新书》);鲸鉴春丽,惊耀天下,然而密栗窈眇,章妥句适(《行状》),则庶几乎!(按:括号内字原为小字。括号乃笔者所加)[1]1439
对于李翱《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韩文公神道碑》、宋祁《新唐书·韩愈传》等文对于韩愈的评价,刘咸炘是用公允的立场予以取舍的。一方面,对于过度地拔高韩愈的形象,夸大其影响的评论,他觉得“言之太易”,认为不太可信;另一方面,对于韩愈捍卫儒学、改良文风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鉴于“积习生常,过枉害直,纵毁誉而乱是非之真”的状况,刘咸炘力持客观的态度,因而“钩考遗书,采集众议,录为一篇”,对韩愈其人其文进行了评价。不过《订韩》内容主要是“多举其瑕而略其瑜”,目的在于“以定韩子之真”。他进而解释“订”的意思为“评议”[1]1403,当是从许慎《说文解字》之本义。这就说明他并非是“喜为掊击”,专为攻韩愈之恶,而是经过寻讨之后,深有洞见之举。
关于《订韩》的体例,主要是采用札记的形式,加以点评。这也是刘咸炘著述一贯的风格。如他所著的《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吕氏春秋发微》《文史通义识语》等,均为此一形式写成。就内容而言,《订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评判韩愈的行谊和平议韩愈的诗文。下文将结合具体文字,从这二个方面进行论述。
二、韩愈行谊的评判
行谊,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有两层含义:一是品行、道义;二是事迹、行为。[5]919韩愈的品行、行为在后世争议较大,用行谊一词较为切合。后人关于韩愈行谊的评价,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崇儒排佛之矛盾;二是其干谒之无耻;三是其撰述内容之失实。对此,刘咸炘均有评判。评判的方法,或独抒己见,或先征引前人文字,间下己意,或驳或赞。兹条列于下:
(1)崇儒排佛,徒有其表。历代学者对韩愈崇儒排佛的议论文字极多,聚讼纷纭。学者所持有的态度大体可以归为三类:肯定排佛的积极意义;从韩愈言行不一否定其排佛;韩愈对佛学有取舍。[2]1-2导致意见分歧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韩愈与僧徒的交往。一方面,韩愈以儒学继承者自居,极力捍卫道统,排斥佛法,撰写了《原道》《论佛骨表》等文章,且险因辟佛而丧命。同时,他又与僧徒频繁往来,甚或对其人称羡不已。这一矛盾的事实集中在韩愈一人身上,颇为费解。对韩愈的道统问题,刘咸炘认为:
韩愈自命接孟子之传,屡见于言。然孟子大本领,韩子全不知。孟子言性善,而退之言性有三品。孟子辟杨墨,退之知之,而《读墨子》则谓“孔、墨必相为用”,是其大旨已乖。况治经非有发明,不如汉儒;学道未窥精微,未及宋儒。其于从祀之例,无一当者,徒以辟佛老耳,徒以宋人称之耳。纵宽取之,亦岂应如是之空滥耶?[1]1405
韩愈在《原道》中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2665,揭橥道统的传承,隐然以道统自命。后世的儒学道统论亦将韩愈纳入传承的谱系之中。刘咸炘从韩愈“接孟子之传”入手,对比了二人之间的区别,论定韩愈与孟子差异较大。下文征引了郑少微之说,指出“孟、韩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己其异五[1]1405”。更何况韩愈“治经非有发明”、“学道未窥精微”,就道统而言,配享孔庙,实为名不副实。
至于辟佛之举,刘咸炘首先指出“辟佛老之误,亦非一言所能辨”,并说其祖刘沅(1768—1855)“《正讹》已取《原道》而详驳之矣”[1]1403。继而征引清人包世臣《书韩文后》,对“退之以辟二氏自任,史氏及后儒推崇皆以此”[1]1403的现象进行了驳斥,并进一步指出“退之与大颠游,盖亦惑于禅家之说”[1]1404。
对于韩愈的道统地位及辟佛行为,主流观点均予以肯定。如《新唐书》本传所云“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6]5269。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先生发表《论韩愈》,指出韩愈的六大功绩,其中就有“建立道统”“排斥佛老”“呵诋释迦”[7]319-332。汤用彤先生亦称“文公一生,志与佛法为敌,尝以孟子辟杨墨自比”[8]26,并论历朝辟佛诸人“用功未有昌黎之勤,议论未若昌黎之酷烈”[8]27。而刘咸炘对韩愈此举,基本持否定态度。当然,刘咸炘并未就此而彻底否定韩愈其人。他一则备录程子(程颢,1032—1085)之说,认为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再则引王安石之诗“可怜无补费精神”,甚为韩愈惋惜。对于“予夺乃大有不同”的矛盾,刘咸炘折衷以己意,认为韩愈“其言常详于外而略于内,其志常极于远大而其行未必能谨于细微”[1]1404,可谓一语中的。
(2)干谒请乞,败坏儒风。近人钱穆(1895—1990)称:“唐代士人干谒之风特盛。姚铉《唐文粹》至专闢《自荐书》两卷。”既此,唐代干谒之风可见一斑。钱穆更论“而韩昌黎《三上宰相书》,乃独为后世所知。”[9]87再翻检历代关于韩愈干谒之文的议论,和钱穆持论相同的不乏其人。在后世的印象里,韩愈此类文章颇遭非议。刘咸炘对韩愈的干谒文章亦颇有微词。他说:
读退之三上宰相、应举与人诸书,何其干乞之无耻也!乞之不能而继以愤怨,炫之不能而继以卑哀。上宰相则举周公以形人之丑,自言其穷饿;上于襄阳则乞刍米仆赁之资;应科目与人书则既摇尾乞怜焉而以为不,何其砚也!唐人多上书自荐,固不止退之一人。然退之固自俨然自谓接孟子之传,其于七篇之书,岂熟视而无睹邪,抑假以为重而言不顾行耶?[1]1405
韩愈干谒之文颇多。刘咸炘曾指出“《上兵部侍郎书》《上于襄阳书》《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上贾滑州书》《上考功崔虞部书》,皆干进之词也”[1]1406。他首先标举“人生大事,莫过于出处”[1]1404,继而对韩愈《上宰相书》《上于襄阳》《应科目时与韦舍人书》等文逐一进行驳斥,并与李白、董仲舒作对比,深刻地鞭笞了韩愈的请乞行为。
关于唐代文人干谒行为,本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妄作评判。钱穆稽考史实,认为当时“固不以此为卑鄙可羞”[9]95。刘咸炘对韩愈干谒的否定,表面上似乎是沿袭前人的态度,夷考其实,则不尽然。他说:
寻绎文中所言,可见刘咸炘并非对韩愈过于苛责,而是有深层的思考和隐忧。干谒之风,不仅有关一人之得失,实则足以败坏儒术。“厚责”韩愈的原因,在于他“持儒义以道自任”的身份。刘咸炘的目的在维系儒术之业不坠,可谓用心良苦,切不可因他表面的责斥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喻义。
(3)持论不公,撰述失实。韩愈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敬六朝,时势动荡,宦海浮沉。一生撰述,多有内容不切事实之处。就其从仕途而言,为谋求职位,不得不行干谒之举,故尔文中多“谀词”。如前举《上于襄阳书》,刘咸炘就指出:“于頔之为人无足取,其文亦何美?而韩子上书乃以有言浑浑噩噩为颂,几于谀矣。”[1]1406此类文章,前已具论。
第二类为“谀墓文”。《韩愈集》中碑铭之作,颇涉谀墓之嫌。韩愈同时的刘叉已经揭橥了这一事实,说韩愈的润笔乃“谀墓中人所得耳”。[10]205北宋司马光(1019—1086)也曾提到韩愈“好悦人以志铭而受其金”[1]1406。对司马光的观点,刘咸炘表示支持。不过这一类文章,往往是应人之请,其内容多为外在的人情世态所决定。正如袁枚所言:“其人虽于世庸庸,于我落落。而无奈其子孙欲展孝思,大辇金币来求吾文,则亦不得不且感且惭,贬其道而为之”[11]331,颇能道出个中缘由。接受了这样的委托,在写作过程中也就难以免俗。对此,无须苛责韩愈。
相较而言,刘咸炘关注的是韩愈的第三类文章,主要与政治书写有关。他说:
退之平生私见失言而乱是非且又玷大节者,莫如《顺宗实录》与《永贞行》。吾读《实录》而大疑之。既读近儒书,乃知已有先我发之者。[1]1408
为了支撑自己对《顺宗实录》的看法,他备录前人之说,“更为推求之”,记有范仲淹、王应麟、阎若璩、何焯、全祖望、赵彦卫、刘克庄、江瀚、王鸣盛、王志坚、孙宜、张燧、贺贻孙、陈祖范、李详、魏了翁,达十六人之多,且多长篇征引。推究刘咸炘立论的依据,集中于《顺宗实录》一书“失言而乱是非”。如韩愈所举逆党,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泰、韩晔、陈谏、房启、凌稚、程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皆精进之士;而李实、俱文珍等奸邪之人,韩愈则大书特书,持论殊为不公。此外,韩愈《上李实书》《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等文对其人大肆吹捧,亦有党同之嫌。前举刘咸炘所言及《永贞行》一诗,陈寅恪即评为“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非公允之论也”[12]308。不过,若纵观全书,刘咸炘也承认该书“详书李实之恶及宫市、乳母、五坊小儿事,书陆贽、阳城事,皆可谓直笔”[1]1436,并非对其一概否定。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韩愈自身的政治主张,则政治书写中的偏颇、失实也是可以理解的。韩愈本来是文人,用“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标准来衡量他,确实悬鹄太高。
三、韩愈诗文的平议
韩愈的诗文成就,《旧唐书》称“自成一家新语”[13]4204、《新唐书》称“深深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6]5265,其诗文创作的独特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学地位经苏轼等倡呼,文集经方崧卿、朱熹等考订,道统又经宋儒等鼓吹,其人其文的地位日益增加,因此在宋代,韩愈除了配享孔庙外,甚至还出现了“五百家注韩”的盛况。
我们开发的新型PHA使用节能节水生产工艺,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绿色生物化工过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PHA 生产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带来更为显著的经济效益。此外,大规模发酵生产有助于创造就业,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PHA产业链,有利于提升我国生物降解材料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不过,对韩愈诗文创作的评价也存有争议。他部分文章独异的风格、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自古就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对。如韩愈颇有特色的《毛颖传》,今日看来实为千古奇文,但在当时就遭到了张籍的否定,认为“驳杂无实”[14]994。《旧唐书·韩愈传》也讥为“文章之甚纰缪者”[13]4205。至于作诗,韩愈独辟蹊径,趋奇尚险,尽管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世界,不过流弊继起,亦给后人以口实。因此,誉之者欲其升天,毁之者欲其入地。双方各执一词,喋喋不休。
刘咸炘对韩愈诗文的平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合具体的诗文,用札记的形式予以评论;二是分为三品,定其高下。
(1)韩愈诗文的品鉴。刘咸炘按照体裁将韩愈作品划分为赋、诗、文三个部分。韩愈赋,今存《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别知赋》四篇,故尔赋类评论文字较短,而评诗、评文则较多。
刘咸炘评论的内容,第一种为归类。如评文部分,他将韩愈的碑铭按一些特质进行了整合,归结为“简质合体者”,计19篇;“用传记法者”,计12篇;“少事迹而矜重者”,计25篇;“有空衍议论而不尽矜重者”,计5篇。评诗部分亦有将数首诗同时进行评论,纠集其共性,如“《东野失子》《落齿》《双鸟》《苦寒》诸篇刻酷而近于戏,恶道也”[1]1424。
第二种为指陈得失。即落实到具体作品,指出该作品的妙处或不足。此类文字最多,亦最有价值。如:
联句诗真所谓“无补费精神”者也。《柏梁》已不足信,况又限之以韵,苦涩强凑,戏而不工,亦何取哉。[1]1424
《争臣论》义正矣而文亦善,其茂畅可置之魏、晋间。[1]1428
《送王含》文笔美而意无聊,乃以酒起兴。[1]1430
限于札记的体例,刘咸炘的评论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说明。但是,点评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尔其只言片语即能切合文章的利弊,要言不烦,言必有中。
第三种为探溯诗文模仿之本源。班固《汉书·艺文志》谓诸子出于王官,推本九流之本始;钟嵘《诗品》,亦追溯诗人之所从出。这种推本溯源的做法,虽然略显牵强,不过由此可以明了学术传承、流变的谱系。刘咸炘精熟传统学术,故对诗文进行品鉴时,往往可以洞悉诗文模仿的痕迹,予以辨析。如:
《郓州溪堂诗》之摹《三百篇》,尤其杰也。[1]1424
歌行短篇学太白,长篇学杜。[1]1425
论著诸篇,大抵学韩非耳。[1]1426
《东晋行状》力摹左史,是用意之作。[1]1436
通过对诗文模仿本源的探讨,一方面可以结合被模仿的作品,来进一步解读韩愈的仿作,加深了解韩愈诗文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韩愈诗文的模仿对象,来体察韩愈的知识结构。这项工作需要品鉴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同时对韩愈作品有较深的体会。刘咸炘将二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并付诸实践,收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5]1的效果。
(2)韩愈诗文的定目。刘咸炘对韩愈诗文平议,最有特色的部分就是《韩文定目》。《韩文定目》将韩愈诗文定为上中下三品,且指出分类标准:上品“与 古 抗 行,可 为 后 世 法”[1]1437、中 品“工能”[1]1438、下品“自作狡狯,不可为法者”[1]1438。各品之内,收有不同体裁的相关作品。浏览此目,即可感知韩愈诗文的宏观印象。翻检《推十书》戊辑,刘咸炘另有《四文定目》一书,分别为《韩文定目》《柳文定目》《近代八家之目》《近代善文目》。由此可见,刘咸炘颇为热衷此道。
中国传统对人进行分等评品的思想起源很早。其后班固在《汉书》中独创《古今人表》,备列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其后,钟嵘《诗品》对此又有吸收,正如郑振铎(1898—1958)所言:“也许是受有《汉书·古今人表》的若干影响吧,故他把五言诗人们分别为上中下三品而讨论之。”[16]183而郭绍虞(1893—1984)则明言《诗品》“本班固九品论人之法以衡诗,分为上中下三等”[17]104。随着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的兴盛,其后逐渐波及艺术的层面,如诗文字画等的品评,且蔚为大观。
刘咸炘《韩文定目》是在对韩愈诗文品鉴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了对作品的品鉴,其艺术成就的高下之分也就一目了然。可以说,定目是品鉴的自然结果,二者的关系就如同瓜熟自然蒂落,水到自然渠成一般。只是历来的论文者对韩文的赏鉴只是停留在单篇字句,而未顾及全书。从这个意义来讲,刘咸炘的《韩文定目》是一个创新,且有独特的价值。
《韩文定目》有两个版本。一个收在《订韩》中,一个收在《四文定目》中。因《四文定目》撰写时间不详,今无从确定二书成书先后。对比二者,略有差别。《订韩》中每品均有“五言古诗”一体,《四文定目》中全无;《四文定目》下品中有“联句诗”一体,但并未罗列相关作品,而《订韩》中无此一类。此外,尚有诗文顺序、题名等不同。
《韩文定目》是刘咸炘对韩愈诗文评价的一种直观呈现。我们可以结合刘咸炘对上中下三品划分所提出的标准,以及他对韩愈部分诗文的具体品鉴,来进一步考察韩愈诗文。比如,韩愈《送孟东野序》一文,入选韩愈诗文选本的频率甚高,且历来饱受赞誉。刘咸炘认为该文“波澜壮阔,便于初学摹效”[1]1430然而,刘咸炘在《韩文定目》中将其归为“下品”。推求其原因,只能从“自作狡狯,不可为法者”入手。
四、小结
韩愈作为诗文名家,开一派风气,向为论文者所关注。因此,关于其人其文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即以民国时期而论,有关韩愈的研究就很多。较著名的如陈登原《韩愈评》、钱基博《韩愈志》《韩愈文读》、陈柱《正韩篇》《礼韩》、范幼夫《韩文毛病举隅》等。这些书籍,坊间大多可以寻访。对于韩愈其人其文,历来持论纷纭,毁誉不一,难免意气用事,流于极端。即使是苏轼一人,对韩愈的评价也前后不一。既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讥其“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18]114。评价人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而刘咸炘对韩愈其人其文的评析,往往毁誉交杂,并非一味驳斥,或一味赞扬。意气平和,持论公允,乃其最大特色。总之,“明韩氏之功罪”[19]5乃其用心之所在。本文就此条举数则,至于其学术价值有待学界进一步研讨。
[1]刘咸炘.订韩//推十书:丙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2]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张惠民.1911—1948年间韩愈研究综述//韩愈研究资料汇编[C].汕头:汕头大学中文系,1986.
[4]韩愈.屈守元,常思春,校注.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5]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3册[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8]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钱穆.读史随劄[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0]辛文房.唐才子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11]袁枚.与翁东如//小仓山房尺牍[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1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9.
[13]刘昫.旧唐书:第1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张籍.徐礼节,余怒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5]章学诚.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16]郑振铎.中国文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1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18]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钱基博.韩愈志[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