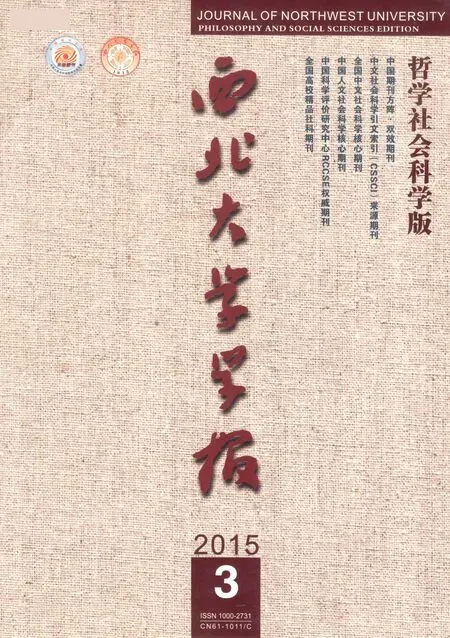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问题研究
袁 彬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是犯罪主体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主要涉及两大因素:生理因素(如又聋又哑)和心理因素(如“精神病”或者“心神丧失和心神耗弱”)[1](P70),对应的心理能力主要是刑事辨认能力和刑事控制能力,评价的是心理的认识过程和意志过程。其中,意志过程强调的是对行为发动与否的控制。在心理学上,强烈的情绪对行动的发起与维持具有重要的作用[2](P60-61),会影响人的心理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考察范围是许多国家刑法的普遍做法。但我国刑法上对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情绪问题涉及较少。正确看待和评价犯罪主体中的情绪问题对于促进我国刑法的科学化和人道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情绪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功能分析
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核心。情绪对犯罪主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情绪对刑事辨认能力的影响
刑事辨认能力是主体辨认自己行为的刑法意义的能力,它是一种认知加工能力,加工的对象是行为人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和后果等[3](P84)。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对认知加工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即情绪影响信息加工的发动、干扰和结束,影响信息的选择性加工,影响人们的注意,影响记忆的准确性[4](P97-105)。具体而言,情绪对认知的影响包括对是否开展认知活动、认知什么对象、认知的速度、认知坚持的持久性以及认知的精确度的影响。试想,在一个犯罪活动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否实施、对什么对象实施、实施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等方面都因情绪的作用而无法认识,其在行为当时的认知能力及其程度就显然不如正常状态下的人。因此,情绪对认知的影响反映在刑法上可具体化为情绪对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等方面认识能力的削弱,容易导致认识偏差,致使假想防卫、假想避险、打击错误、认识疏忽等影响刑事责任评价的情形出现。
(二)情绪对刑事控制能力的影响
刑事控制能力主要解决的是行为实施与否以及行为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控制问题。其中,行为实施与否所涉及的主要是动机的选择问题,因为在犯罪的决策过程中,行为人通常都会面临动机冲突。其中基础的动机冲突是“追求犯罪之利”与“避免刑罚之苦”的冲突。通常而言,在“追求犯罪之利”与“避免刑罚之苦”的动机冲突中,优势动机将决定犯罪行为实施与否。而何种动机占据优势地位,则主要取决于动机的强度差异。在心理学上,情绪是动机的中介子系统,能够整合内、外系统的各种因素,发动、维持和调节行为[5]。内驱力的信号(如食物、水、氧气等生理需要的信号)需要经过一定媒介的放大,才能驱策有机体去行动。这种起放大作用的媒介,就是情绪过程[6](P101-105)。情绪对人的内驱力信号的放大,会促使人们实施一定的趋向或者回避行为。在犯罪情境中,情绪对行为人自身需求(如饥饿、自尊、自我实现)的放大,会加快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反之,情绪对行为人回避刑罚需求(如自由受限制的痛苦等)的放大,则会促使人们尽快放弃犯罪。例如,在正当防卫情境中,对不法侵害行为的恐惧情绪会促使行为人选择更急促、更有力度的防卫行为,进而容易导致防卫过当情形的出现。同理,对法律制裁的害怕、恐惧情绪会放大人们对于实施犯罪与否时的犹豫心理,削弱人们对行为的控制作用,进而导致人们放弃犯罪或者增强犯罪得逞的难度。可见,情绪的动机作用会强化人们实施犯罪或者放弃犯罪的决策选择。
(三)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间接影响
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间接影响主要是指情绪作为精神障碍的内在因素间接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精神障碍是由生物、遗传、心理、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引起的心理或行为障碍,包括神经症和精神病以及人格障碍,精神发育障碍,器质性、中毒性精神病等[7](P27)。精神障碍对人的感觉、知觉、思维、注意、记忆、情感、情绪、意志、意识、智能、欲望、性格都会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8](P122)。情绪情感障碍是精神障碍的具体类型,其中部分精神障碍(如躁狂症、抑郁症等)完全以情绪情感障碍为主导,情绪情感障碍是这类精神障碍人行为障碍的主要原因。鉴于精神障碍人与正常人存在的心理能力差异,国外刑法典大多将精神障碍(含精神病)人纳入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并依精神障碍的程度将其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情绪情感类精神障碍作为精神障碍的具体类型也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方面。刑法对情绪情感类精神障碍的从宽评价,反映了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间接影响。
综上,情绪对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情绪应当被纳入犯罪主体的责任评价范围。
二、域外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之立法与理论考察
(一)域外犯罪主体立法中的情绪评价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在犯罪主体的立法中规定了情绪问题。概括而言,域外犯罪主体的情绪立法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关于正常人的责任评价,情绪是影响其刑事责任能力评价的重要因素。例如,《芬兰刑法典》第三章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如果由于精神疾病、精神不健全、心神不宁或意识混乱,理解其行为的事实性质或违法性的能力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严重削弱(减轻的刑事责任)而根据第二条在刑事上不具可责性,在决定判决时,应当考虑第六章第八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第四款规定:“在评估刑事责任能力时不应考虑醉酒或其他罪犯自己导致的临时性精神不安,除非对此有特别重大的理由。”[9](P22)笔者认为,《芬兰刑法典》的这两项规定包含了以下两层意思:(1)“心神不宁”是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内涵上,“心神不宁”即惴惴不安、焦虑的情绪状态。将“心神不宁”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考量因素,实际上是将部分情绪状态作为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因素。(2)“临时性精神不安”在特定情况下可成为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临时性精神不安”是指行为人的“不安感”,也是一种情绪状态。《芬兰刑法典》分两种情况将“临时性精神不安”纳入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即非行为人自己导致的“临时性精神不安”可作为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行为人自己导致的“临时性精神不安”,当有特别重大的理由时,也可以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在《德国刑法典》中,“深度的意识错乱”是无罪责能力的重要依据。《德国刑法典》第20条规定:“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因为疾病的精神障碍、因为深度的意识错乱或者因为智力低下或者严重的其他精神病态,无能力认识行为的不法或者无能力根据这种认识而行动的,是无责任的行动。”其中,“意识错乱”包括情绪激动的特定形式。而事实上,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引起广泛重视的正是以强烈的情绪激动为基础的无罪责能力[10](P585)。
第二,关于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碍人的责任评价,情绪是刑事责任能力当然的考量因素。在目前能查阅到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中,“精神病”和“精神障碍”都是刑事责任能力的考量因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甚至还对“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碍”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例如,《俄罗斯刑事法典》第21条第一款关于“无刑事责任能力”部分就对精神障碍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使用的“其他精神障碍性心理疾患”表述[11](P14-15),实际上是将所有精神障碍均纳入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类似的规定也体现在《埃及刑法典》第62条规定的“精神错乱”中。从内涵上看,国外刑法典中的“精神病”“精神障碍”或者“精神错乱”都包含了由情绪情感障碍而导致的精神病、精神障碍或者精神错乱。据此,由情绪情感障碍主导的精神障碍也属于精神障碍(或者精神病)的范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和司法实践都将情绪情感型精神障碍(或者精神病)纳入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
(二)域外犯罪主体理论中的情绪评价
域外刑法理论上关于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正常人(包括少部分精神障碍人)的情绪评价上。对此,学者们的分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
一种观点认为,由情绪情感引发的行为意志上的“病症”不应成为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例如,法国刑法学家认为,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所患的是一种意志方面的疾病。这种疾病既不影响行为人的智力,也不影响其理智,而仅仅是可能取消行为人的意志(忧郁症、精神衰弱症)。这种病症可以是间歇性的,或者是特异性病症(例如,偷窃癖、放火癖)。这种病症并不一定具有使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消失的效果,所以不同于精神紊乱,也不同于行为人受到强制。“道德狂”也是这种情形,这种疾病既不损害人的智力,也不影响其意志,而仅仅是损害行为人的“道德意识”或“道德感”。这种疾病的患者符合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的特点,他们对任何“坏事”都不加排斥,但他们完全能够区分好坏,所以这种人在道德上与刑事上都是应当负责任的[12](P384-385)。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刑法典没有将情绪作为刑事责任能力评价的因素作出明确规定,但仍应予考虑。例如,意大利刑法学家杜里奥·帕多瓦尼(Tullio Padovani)认为,意大利1930年刑法典规定冲突和激情状态不排除刑事责任能力,主要是因为当时实践中存在一些非常过分的做法。在该刑法典颁布以前,重罪法庭的陪审官们常常以“为激情所控制”为由,开释那些犯下重大血案的人。现行刑法典第90条只是表明了立法者要求人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来控制自己情感世界的坚决态度。不过,对那些被动型(或压抑性)的激情来说,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似乎也有过于严厉之嫌。与外向性(或爆发性)的激情相比,前者的主体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或者是一种使其受刺激行为所引起(如害怕、恐惧、恐怖),而后者则是驱使主体主动地实施侵犯性行为的动力(如愤怒、性亢奋)[13](P195-196)。在他看来,被动型的激情应当被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目前该观点也是国外多数学者的认识。
三、我国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之现实剖析
(一)我国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现状
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了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四个因素,即年龄、精神病、生理功能丧失和醉酒。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典关于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刑法规范中未对犯罪主体的情绪问题作出直接规定。我国刑法典共使用了三个条文(即第17-19条)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作了规定。从刑法条文的表述上看,我国刑法典并未对情绪作为刑事责任能力评估因素加以规定。但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过错是刑事责任认定所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我国刑法理论上也普遍赞同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犯罪人刑事责任评价的范围。笔者认为,将被害人过错作为刑事责任的考量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对情绪作为刑事责任能力因素的支持态度。事实上,在引发情绪产生的因素中,被害人的过错通常是行为人强烈消极情绪爆发的重要因素。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刑事责任的考量范围,实际上也包括了对由被害人过错引发的行为人的强烈情绪的评价,只不过评价的侧重点是针对情绪的诱发因素,而非行为人的情绪这一心理因素。
第二,刑法对精神病的规定间接体现了刑法对情绪的评价。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典第18条中的“精神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狭义上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据此可以认为,我国刑法典第18条的规定间接体现了刑法对情绪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刑法典第18条评价的情绪仅限于病理性情绪。根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的规定,病理性情绪具体包括心境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癔症、应激相关障碍、神经症以及习惯与冲动控制障碍等。这类人的情绪发生和控制异于常人,他们或者情绪特别容易激发,一点外界因素都能引起其强烈的内心体验,或者情绪特别容易高涨,难以为意志控制。二是并非所有的病理性情绪都可以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因素。刑事责任能力反映的是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在一般意义上,犯罪是一种较之于不道德、普通违法行为更为严重的行为,因此从辨认的角度看,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要较之其认识其行为的道德等其他社会评判意义,更为容易。而行为人对其行为之犯罪意义的认识是其关于自身行为意义认识中最低层次的认识,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病理性情绪虽可能影响人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但并非任何程度上的情绪都可以削弱行为人的刑事辨认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刑法中,只有那些强度较高的病理性情绪因素才能成为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
(二)我国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缺陷
对于我国刑法典关于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笔者认为,它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未明确将正常人的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情绪对人们的认知、意志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对于正常人而言,虽然他在通常情况下都能较好地控制其情绪,但这并不表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控制好自身的情绪。情绪的发生既有心理的原因,但也有外界刺激因素的影响。从责任评价的角度看,以下两种情形要加以特别考虑:一是行为人在长期的不良情境中持续积累了消极情绪,并猛烈爆发;二是行为人在遭受突然的巨大不良刺激而产生突发的强烈消极情绪。例如,在特定情况下,当行为人突然遭受被害人巨大侮辱、虐待时,他可能会爆发强烈的消极情绪(如震怒),进而实施针对被害人本人或者亲属的不法行为。以一般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而言,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为人都可能因强烈消极情绪的作用而失去控制,进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典将正常人的情绪一概排除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不符合刑事责任能力的实际状况。
第二,对精神病的严格限定导致许多病理性情绪难以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我国刑法上的“精神病”是一个内涵相对狭窄的概念,不包括绝大多数的精神障碍。虽然从刑法典第18条第1-3款的表述和相互关系上看,“精神病”包括了部分精神障碍。但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人都没有被纳入精神病人的范围,其中就包括了相当部分的情绪情感型精神障碍。但将病理性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是域外刑法典的普遍做法,我国将相当一部分的病理性情绪排除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不符合这类主体刑事责任能力的实际状况。
四、我国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之立法完善
(一)将情绪因素纳入刑事责任能力评价范围的必要性
情绪对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也是我国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评价范围的理由:
第一,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有利于推动将其他相关心理因素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总体上看,我国刑法典中与刑事责任能力有关的心理因素只有“精神病”这一个因素,而且它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心理素质,即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我国刑法典对此的评价是以病理性因素为基础的,即必须患有精神病。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典对与刑事责任能力有关的心理因素的这种评价是片面的。很多对刑事责任能力具有重大影响的心理因素都被忽略了,如“智力低下”、强烈的消极情绪和严重的意识障碍等。这不符合现代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也与现代人权观念的取向不相吻合。在此背景下,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有利于推动我国刑法将其他对刑事责任能力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因素一并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促进刑法的科学发展。
第二,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有利于贯彻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刑事古典学派强调人性中的理性,认为犯罪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人是有着自由意志的抽象的“理性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在能够选择不犯罪的情况下实施了犯罪,因而应当承担道义上的责任[14](P322)。但事实上,人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理性和绝对的意志自由。“感性”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刑事人类学派注重个体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对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就包括情绪情感因素。这一点也已引起了现代刑法理论的重视和关注。现代刑法的人道主义要求,刑罚的科处和执行必须考虑被告人和被判刑人的个人,以负责任的态度人道地对待被告人或者被判刑人,以便使其能够顺利地重返社会[15](P35-36)。因此,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尊重被告人的个性,是贯彻刑法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二)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评价范围的模式
基于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应在评价模式的选择上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在评价内容上,作为刑事责任能力影响因素的情绪只能是强烈的消极情绪。心理学按照情绪的愉快——不愉快维度,将情绪分为正性情绪(积极情绪)和负性情绪(消极情绪)。负性情绪代表个体对某种消极、厌恶的情绪体验的程度,正性情绪则反映个体积极情绪体验的程度[16]。从对刑事责任能力产生影响的角度看,作为刑事责任能力评价因素的情绪,必须是消极情绪。这是因为负性情绪会减弱个体的行为控制能力,从而导致个体对反应冲突的觉察变慢及对优势反应的抑制过程更长。相反,正性情绪对行为控制过程可能具有促进作用[17]。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控制能力而言,负性情绪较之于正性情绪,更有影响,应当被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同时,作为刑事责任能力评价因素的情绪必须是强烈的负性情绪。一般而言,强度越高的情绪对人的行为影响力越大,因为强度越高的情绪,人们要进行情绪弹性调节以从负性情绪体验中快速恢复过来的难度越大[18]。相反,对强度较低的消极情绪,人们更容易恢复。因此,只有受强烈消极情绪影响的行为,才有必要给予专门的刑法评价。
第二,在评价模式上,宜将情绪和其他相关的心理因素共同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因素。如前所述,情绪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评价的重要因素。不过,应否在立法模式上将情绪作为独立的因素规定在刑事责任能力专条中,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典可以将情绪与其他相关的心理因素共同规定为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因素。具体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情绪并非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唯一心理因素。如前所述,除了精神病,还有其他许多病理性或者非病理性的心理因素会对人们的刑事责任能力产生影响。情绪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一些与认知、意志和动机有关的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刑事责任能力。例如,有研究发现,作案动机、幻觉妄想、有无精神病、情绪低落等因素可作为辨认能力的判别因子,作案动机、有无精神病、情绪低落、精神状态、意识障碍、人格改变、情绪高涨等因素可作为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19]。从刑法立法的角度看,将这些因素规定在一起既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掌握和运用刑法的规定,也符合刑法的科学性、简明性要求。
二是情绪与其他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之间具有共性。从内涵上看,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强烈的消极情绪对人们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一般而言,在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关系中,辨认能力是前提和基础,没有辨认能力的控制无从谈起,而控制能力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核心,有辨认能力但没有控制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也不具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既有对辨认能力的影响,也有对控制能力的影响。不过,无论是从辨认能力还是从控制能力的角度看,行为人都会表现出精神上的高度紧张或者高度不安。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刑法典直接将之表述为“精神不安”“严重的精神不安”“精神错乱”等,这些表述均可包含情绪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
(三)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评价范围的建言
参考域外的立法,可以在现行刑法典第18条第一至三款中将“严重的精神不安”列入其中,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符合“严重的精神不安”与“精神病(精神障碍)”的并列关系。我国现行法典第18条第一至三款已将“精神病”明确规定为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因素。从内涵上看,“严重的精神不安”与“精神病”除了发生原因不同(前者是正常的精神不安,后者是因病理性精神不安或者错乱),两者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即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在机理上完全相同,两者是并列关系,可以将其规定在一起。
第二,这有利于简化“严重的精神不安”的程序性规定。我国刑法典对精神病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即必须“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对于正常的情绪而言,其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在程序上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经法定程序确定确认;二是由法官依经验判定。客观地说,情绪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考察的是案发时的情绪状态,并且主要依据的是“正常人”标准,法官的经验判断并非不能做到。不过,考虑到“严重的精神不安”与“精神病”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机理基本相同,在我国现行刑法典对“精神病”采取是“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这一做法,笔者赞同对“严重的精神不安”采取与“精神病”相同的程序标准。在此基础上,将“严重的精神不安”与“精神病”因素规定在相同的条款中可以避免立法用语的重复。
第三,这有利于统一“严重的精神不安”与“精神病”的处罚。我国刑法典第18条第一款和第三款对精神病规定了两种处罚,即“不负刑事责任”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应然的角度上,“严重的精神不安”通常属于后者,即“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都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减弱而非丧失。但是也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行为人可能因为“严重的精神不安”而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基于此,在刑法处罚上对“严重的精神不安”和“精神病”作相同的规定,而且将“严重的精神不安”与“精神病”规定在相同的刑法条文中也有利于统一两者的刑事处罚。
总之,强烈的消极情绪是导致人们“严重的精神不安”的重要因素。将强烈的消极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刑法评价的科学性和统一性,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促进我国刑事法治的完善。
[1]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叶奕乾,孔克勤.个性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孟昭兰.情绪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唐燕,郑子健.行为的动机系统观初探[J].社会心理科学,2007,(6).
[6]TOMKINS S.Affeet as the primary motivational system[M]∥INARNOLD M.(ed.).Feelings and Emotions.New York:Academie Press,1990.
[7]马世民.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
[8]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芬兰刑法典[S].于志刚,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10]克劳斯·洛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1]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S].赵路,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12]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3]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4]张小虎.刑法的基本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5]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6]黄丽,杨延忠,季忠民.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
[17]辛勇,李红,袁加锦.负性情绪干扰行为抑制控制:一项事件相关电位研究[J].心理学报,2010,(2).
[18]张敏,卢家嵋.青少年情绪弹性问卷的研究报告[J].心理科学,2010,(3).
[19]宋振铎,张志华,李万顺,等.伤害案件中影响精神病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多因素分析[J].山东精神医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