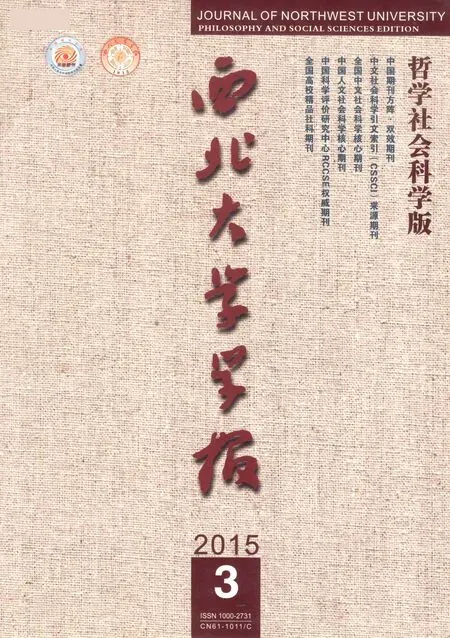当代中国幸福问题的哲学透视
刘喜文,李武装
(1.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2.第四军医大学 护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32;3.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陕西西安 710048)
一、幸福问题的提出与简单分析
(一)问题提出的现实根据
一般认为,当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上升到一定高度,伴随利益多元化的出现,其包孕并负载的伦理道德问题便凸显出来,这也成为人们幸福观发生变化的内在社会根由或幸福观重新建构的重要参考坐标。当代中国幸福观变动从而得以彰显的更深刻的运行机理,在于转型社会“无主时代”的氤氲反拨对“底线价值”的挑战,以及由此而生的对道德高地之“顶层设计”的诸多迷茫和困惑。
比照来看,当代中国幸福问题的突显,多少与希腊晚期哲学所发生的伦理转向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晚期希腊哲学转向所开辟的伦理之路,实际上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了伦理学,由此哲学的主要目标不再是追求智慧,而是追求幸福。
当代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建成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世界公认。但如此这般的成就带来的影响又是多方面的,且毁誉参半:一方面,经济富裕了的中国人需要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方式和新幸福模式;另一方面,曾经一边倒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失范情势,使得幸福问题的厘定愈加棘手和紧迫。一句话,中国“富裕社会”之路的实践和期许,把中国幸福问题推到我们面前,亟待解蔽和澄明。换言之,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乃是当代中国幸福问题再度被关注的根据。
(二)问题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幸福,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家们有过经典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过独特阐发,但时至今日,幸福问题亦然众口各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幸福”可以有不同背景所指。日常生活中人们言说的幸福,实质是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人们可以把幸福和任何“人间四月天”的福祉相匹配。从哲学层面作理性选择,人们所谓的幸福不外乎两种:物本幸福观和人本幸福观。物本幸福观以工具理性思维为依托,以物质财富的占有率(或占有量)为幸福指数构建标准,其后果是“见物不见人”(或者“物的依赖性”)逻辑的全面发用。人本幸福观以价值理性思维为基准,以满足个人的偏好、爱好、欲望、兴趣等为旨归,负载着团体、民族、国家的“个别利益”,其后果是“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的日渐盛行。二者论争的焦点,借用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话语来表述,在于幸福与利害是否有关。
进一步作理性判断,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既没有单纯的物本幸福观,也没有绝对的人本幸福观(相当于“斯宾诺莎幸福”),二者事实上处于交互制约的复调叙事与实践构建当中。德性论(义务论或道义论)幸福观和规范论(目的论或后果论)幸福观的分野抗衡,就是例证。不仅如此,就规范论幸福观而言,我们既可以基于功利(目的)视野,也可以诉诸正义论领域;就功利视野讲又被划分出两种路径:从追求个人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生存愿望出发来确立幸福观,抑或从个人行为符合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出发来确认幸福观。可见,“规划”幸福并确立一种普适性的、既可欲又可行的幸福观,的确并非易事。
这一现实困惑或者理论难题的根本所在,就是一系列“道德—幸福—社会结构”的深层生态关系性所构成的难题。
(三)问题的简单分析
以“道德—幸福”关系为例。在哲学史上,幸福经常是被放置在伦理视野中进行考察的,而伦理本身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道德,因此,幸福言说必然要与一定的道德相联系,从而有了学界“德福一致”的问题谜团。而联系的必然性可能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从学理层面看,面向一种严谨学风本心和习性的秉持,为着一种学术对话、学术交流的便利;二是从实际出发,道德和幸福本身就是一对不可分割、具有很多交叉点或重合面、甚至具有同一所指的畛域。
以“社会结构—幸福”关系为切点,一般意义上,对人而言的幸福都有两个指向:内在灵魂的自由与外在世俗生活的宁静。而无论是对自由的诉求还是对宁静的渴望,既然人是社会的人,那么,对幸福的理解和建构就须臾也不能超越人之为人所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一定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人们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的改变。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合宜地确认当代中国社会的幸福观呢?本文旨在回应和补全当代中国以“公益民生”为本位的“幸福中国”执政理念和诉求愿景,也即当代中国“富裕社会”的幸福观建构。简言之,就是以分配正义视野下的幸福问题为切点,试图彰显一种基于“价值理性之限度”立场的“新伦理本体境界”(指对以财富和富裕为价值优位的正视,但并不等于价值上的全部认可),进而消除“伦理学贫困”和“哲学的贫困”。
二、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幸福追问旨趣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或呈现的幸福观,基本围绕“人”的生成之路展开,因而属于一种“人本幸福观”。《尚书·洪范》篇曾提出了“五福”即五种幸福:“寿(百二十年)、富(财丰备)、康宁(无疾病)、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终命(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不横)。”[1](P193)这可以看作几千年中国文化之“人本幸福观”的雏形。下面以儒家和道家为例,简单分析和评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儒家的幸福观。儒家认为人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自然生命,譬如告子的“食色,性也”;德性层次,譬如孟子的“人性善”;人的主体性层面,譬如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即理”(因为良知、良心和本心等概念所表现的就是人的主体性),从而古代儒家的幸福观就可以被相应归纳为三种:生命幸福、道德幸福和精神幸福。
道家的幸福观。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幸福观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地方,都在于强调“心”的宁静少欲。具体说来有三个层面:
1.名利乃身外之物,幸福乃心灵的自我契合。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庄子说:“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庄子·缮性》)奢求荣华富贵,不是生命本身所求,人身之外的物质之于人而言,实属一种寄托。而这样寄托的物质名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幸福并无多少、大小之分。《庄子·逍遥游》篇中有关于大鹏和小鸟的故事,郭象释曰:“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也。”(《庄子注》)宇宙万物并没有大小强弱的人为区别,幸福本身亦无大小之分。
3.生死对人的幸福建构并无多大影响。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众所周知。庄子认为“明乎坦涂,故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庄子·秋水》)就是说,生与死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不应因为生或死本身而影响对幸福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的价值比生存更重要,更有意义。
(二)西方文化中的幸福观
与中国传统文化单纯的“人本幸福观”建构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幸福观追问,由于主客二元思维与理性分析方法根深蒂固,所以主要流变为对“德福一致”问题的求解。
在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幸福就是生活得“好”或者善。苏格拉底(Socrates)早就指出,人都以好的事物或者善自身作为自己行为的目的,而灵魂的善或者德性是达致幸福的首要条件或先行逻辑,作为灵魂的德性的正义,完全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因此,“一个正义的灵魂和一个正义的人就会生活得好,而不正义的人就会生活的悲惨”[2](P998)。这事实上已经描画出人们关于道德与幸福关系问题的最初摹本——讲道德就是幸福。
柏拉图(Plato)进一步指出,幸福不但在于理性统治下的“心灵的和谐”的生成,而且还要求灵魂去进一步辨识真正的正义和善。按照他的逻辑,若想获得真正的幸福,人们必须走出“洞穴”,进入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并获得“教育”。柏拉图《理想国》(其书副标题是“国家或正义”)理论认为,在一个各阶层秩序井然而又相互和谐的社会里(和谐的手段是通过哲学家的“教育”),社会正义既然得到了维护,那它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这样,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就在逻辑上取得了一致。再其后,亚里士多德(Aristotèlès)指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至善即是幸福”[3](P1102)。
毫无疑问,上述西方学人关于德福一致问题的观念建构,仍然是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抽象界说中进行的。经过西方近代“权利和自由问题”“权利和秩序问题”等一系列学理检讨,德福一致问题才日渐明朗并最终开启了康德(Immanuel Kant)富有见地的理性分析视角。
康德首先指出,道德和幸福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因而是有界限区分的。康德认为,道德和幸福既然分属于“经验世界”和“理智世界”,那么,对于人而言,就有不同的地位和意义。道德和幸福不同的地位和意义也即人们拥有不同的“目的”——“自然目的”和“道德目的”,此即康德的“人是目的”理论。按照康德的逻辑,“自然目的”追求幸福,“道德目的”追求自由。二者既然共居于人,就有可能发生冲突和矛盾。
康德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是人,皆因人的道德性即德性的存在,故而德性勿庸置疑应当在逻辑上优先于幸福。如此这般被设定了前提或条件的幸福,才是大写之人“配享的幸福”——与人的德性相匹配的幸福。人的实践理性的真正使命是产生一个善的意志,意志之善是最高的善、绝对的善,始终限制着幸福的达成,甚至把幸福贬低为无。这种“善的意志就构成了配享幸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本身”[4](P461)。
大抵而言,在西方,从苏格拉底最先朴素的基调定位(道德的就是幸福的),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丰富和完善,历经近代权利和自由问题的间接辨析,最终到康德富有深度的理性剖析,德福一致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理论难题之一。立足于广义社会认识论求解德福一致问题,就不能仅仅面对“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必须把视角延展到人自己建构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体与社会之中,并作更深层次、更细致的探讨。换言之,德福一致问题的求解,理应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相关涉。
三、当代中国“富裕社会”的幸福观建构
所谓“富裕社会”,意指包含一种动态的、可以预期的社会形态:一是不仅指物质丰腴,而且指精神富有,更指社会交往丰富;二是指“共建共享促和谐”的理念及其实践设计。这样的“社会形态”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态势与发展阶段的概括。
诚然,当代中国“富裕社会”这一命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完美且自足的释义,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以下社会事象的闪亮登场中,去捕捉和体悟它的“合理内核”或基本规定。这些社会事象包括:(一)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二)暴富群体;(三)仇富或仇官心理;(四)“共同富裕”的国家社会本质和目标以及“创富奇迹”的合法性问难;(五)追求幸福和富裕的“人性”本根(特别是人的“超越性属性”);(六)“新媒体时代”信息交往多元和丰富现象;(七)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行业差别”(“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机会差别”和“民族发展差别”等导致的“贫富分化陷阱”乃至“制度性贫困”(主要由成本不断对弱势群体的转嫁造成);(八)“明星效应”刺激下的普通人心理不平衡现象;(九)对诸如“国富民强”还是“国进民退”的大讨论;(十)“扶贫公益”社会承诺的大幅度、全方位启动或介入以及“三次分配”的出场。当然还包括由上述“库兹涅茨曲线”①库兹涅茨曲线库是197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的G.N.P.之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于1955年提出的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现代发展经济学命题,又称作“倒U曲线”(Kuznetscurve)。其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延展所积累和积聚的综合性“社会心理疾病”“舆情愤激”等社会难题。
列举凡此种种的社会景观,并不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而是要通达一种的新人学境界所关切的一种面向“新伦理本体境界”的幸福理论诉求。
在当今时代,对处于发展转型期和正加速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而言,“真善美”的追求不能陷入约定俗成乃至自欺欺人的“乌托邦想象”之中,而必须承认“价值理性之限度”,并把问题落实到具体的“利益”(包括觉醒了的利益意识、分化了的利益群体、复杂了的利益关系和正义关切了的利益分配等)之中。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我们不断批判资本本身带来的社会发展“事实”,但谁也不能否认资本为持续拓展全球流动新空间所做的贡献,以及资本执行利润逻辑、文明逻辑和责任逻辑的合法性。
可见,讨论富裕或幸福问题,关键是让它们何以在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基础上,重新安排调整分配问题,尤其是财富分配问题。毕竟“财富中国”并不足以表征“幸福中国”的全部,更难以企及“美丽中国”的高度。问题之解决,固然离不开道德的适度调适,但更为有效和关键的是直面社会结构的强大磁场,大力发挥社会结构自身的基础性调节功能。
如此结论,在于以下两个层面的理据:一方面,“历史只是追求各自利益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自由、平等、职务与地位乃至构成人的尊严的基础部分,都与人自身“利益”的获得和分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与人的幸福观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义问题的核心就是分配正义问题。因为,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John Bordley Kawls)的经典论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5](P3-4)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本身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学者早就指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主的结构性领域。”[6]或者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基础,以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已经无法容纳中国现代化诸要素的成长,也无法承受现代化诸要素成长所带来的社会全面变革。
上述结论和理据在伦理学视野中转化为如下学理判断:一个“富裕社会”围绕的核心问题或者亟待化解的首要问题,就是已经或者即将步入“共富”社会的多元价值冲突及其有效措理①因为在经济社会或市场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的角色、地位及能力各不相同,从而其收入、财富不同甚至差异较大。由财富利益引起的社会矛盾、价值观冲突也就顺势凸现出来。[7]。因此,在多元价值冲突日渐涨裂的社会中,如果还是沿循“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泾渭分明的老路,去求解德福一致问题或者建构幸福文化,显然是不合事宜的。换言之,当代“富裕社会”的幸福文化建构,理当达成某些普遍性乃至原则性共识:第一,尽管幸福不等于富裕,但不正视当代社会“富裕”事相的客观性事实或者“富裕社会”之基本规定的幸福观,一定是不真诚的。第二,不包容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走向富裕的幸福观,绝对是片面的。在“富裕社会”里,“责任伦理”(生存性原则)比“信念伦理”(普遍道德原则)似乎更具有优位性。第三,真正的幸福观,就在于人内心与人的生活世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平衡程度。第四,较之于传统的物质幸福指数和精神幸福指数,交往幸福满意度的合宜生发,对于一个“富裕社会”的文明进步,可能更为棘手,也更为根本。第五,只有以“触及既有利益格局”或者“重新分配社会价值”为重心而确立的幸福,才不至于流于文化人类学或价值现象学的形式和说教,幸福也才能最终落到实处。第六,立足于“富裕社会”幸福文化建构的逻辑向度(主题转换,逻辑先行),社会结构之于幸福,应具有本源意义;道德之于幸福,应具有实现——生成意义,因为社会结构内在地优先于道德(道德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
对于这些普遍性或原则性共识本身,我们应有勇气扪心自问:我们为之倾心领悟、悉数努力、真诚付出、有效践履了没有?
进一步反问,幸福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过得幸福?何谓“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幸福观建构的焦点和难点在哪里?有没有普适性的幸福观?等等。如此这般无非是提醒人们要在以下三方面继续追问:第一,幸福确当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因果关系如何?第二,确立幸福与其行为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第三,确立幸福的行为后果对所在社会的连锁影响又如何?
就当代中国民众普遍的幸福逻辑发生及其实现而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民生缺失陷阱”,伴随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陷阱”和“贫富分化陷阱”②此三大陷阱可称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或凸现的“三大陷阱”。,共同造就并带来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甘心中国“社会智识的平融化”,因此当代中国的幸福观建构、同构或重构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学界普遍的关注并得以堂而皇之地出场和在场。问题在于,这个不得不说却欲说还休的问题,显然不是由某个向度或某种视角一厢情愿地承载、廓清乃至体验而生发的。
追求与践履幸福的价值理念和历史目标是永恒的,但对幸福满意度或幸福指数的厘定,须臾也不能脱离道德和社会结构的双向调适,只是后者的调适更具有基础地位或者在逻辑上优先于前者。因而,有关幸福的追问、探索及其实践,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
[1]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WORKS P C.Edited,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by John[M].Cooper,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1992,11.
[7]李武装,赵建保.现代性:中国文化现代化最基本的理论理性[J].探索,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