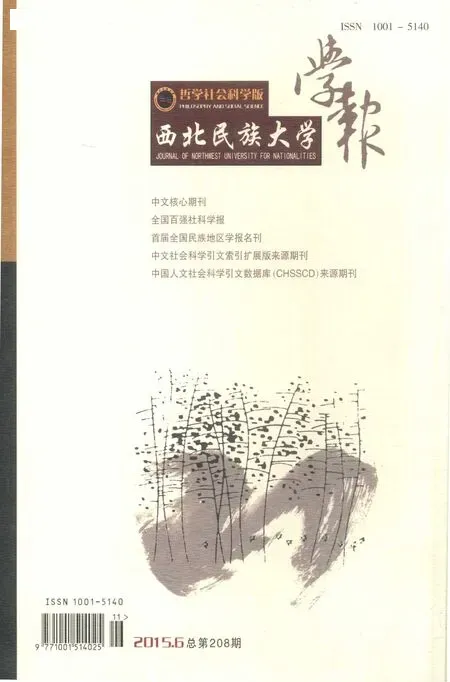金元社会医疗的贡献力量及宗教文化特色
张稚鲲
(南京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江苏 南京210046)
金元时期(1115年—1368年),是多种异域文化交流融汇的时期。多元文化碰撞、冲突,最终得以互补,成就及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这一时期的社会医疗是医、儒、道、佛及其他宗教医学、原始巫祝相互交织,共同维护民族健康的医疗体系。
一、医者兼儒,儒者能医,成为社会医疗的中坚力量
金元名医,儒医居多,医家儒、医兼修,著书立说,成就医名。易水派创始人张元素(1131年~1234年),金代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人,创脏腑辨证理论。其自幼聪敏好学,8岁即应试童子举,27岁应试经义进士,但因犯庙讳而下第,遂弃儒学医,发愤读书,访求名师,勤于临证,医术精进,行医民间,名扬幽燕。李杲(1180年~1251年)字明之,世居东垣地区(今河北保定正安),晚年自号东垣。其出身富家,少年业儒,曾为盐税官,因母罹病,延医无效而逝。李杲深悔己不知医,无法尽孝,遂发奋学医,其以重金拜师学艺,师从易州张元素,苦学数年,尽得其传,医技精湛,宗其学说者众多,著名者如王好古、罗天益等。王好古(1200年~1264年)字进之,河北赵州人,先儒后医,医儒同修,博通经史,以进士为官,兼以行医课徒,著有《阴证略例》,创立阴证学说,倡用温补脾肾之法疗疾救人。罗天益(1220年~1290年)字谦甫,河北正定人,幼承父训,有志经史,先儒后医,师从李杲十余年,潜心苦学,得其真传。其久在民间行医,或出入官府、军旅之间,医名远扬。金元名医朱震亨(1281年~1358年),字彦修,浙江义乌人,故里有小河名丹溪,人称丹溪先生、丹溪翁。朱氏先祖原居陕西平陵,晋代南迁,成为义乌望族,家族儒学功底深厚,世代为官袭爵,祖父为进士,父也有功名。丹溪早慧,初则业儒,才思敏捷,酷爱读书,擅长诗文。其勤动笔墨,每日习字做文不辍,学业大进。当时理学兴盛,丹溪曾去东阳八华山,师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研修理学,悟性甚高,善解义理,为师赞许,人称“东南大儒”,并有史学著作《宋论》、环境学著作《风木问答》等存世。后许谦患病,屡治不效,遂嘱丹溪学医济世。此前,丹溪因母病屡治罔效,感叹世无良医,现又有许谦之托,遂弃儒业医,成就医名,以医术救人。
元代王履(1332年~1391年?)字安道,号奋翁,又号奇叟、抱独老人。少年即丹溪之高徒。医术高明,更以博学多能而名传于世。他曾任秦王府良医正,主管地方医学教育。其思维敏捷,行医临证也以构思奇特、治法多样而闻名,且一生著述颇丰,留有《医经溯洄集》等医学著作。王履所著《古今医统》一百卷,经徐春甫改韵归类增损而成医学名著《古今医统大全》[1]。他博通群籍,教授乡里,善诗文、绘画,尤其擅长山水画,取法南宋名家马远、夏圭,笔墨秀劲,师法自然造化,颇多新意。中年以后,不畏艰险,西出晋陕、秦岭,攀登西岳华山,吟诗作画,留下华山图册48幅,赋诗百余首。王履诗文功底深厚,所作《小易赋》以整齐的韵文阐发全身脏象、名位与机理。明代苏州名士王鏊(1450年~1524年)对王履赞叹有加:“始余读《溯洄集》,知安道之深于医,不知其能诗也;及修《苏州志》,知其能诗,又工于文与画也!”[2]
在我国古代,儒者与医者常不可严格区分。元代学者戴良曾曰:“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为切近”(《九灵山房集·医儒同道》),是说医学治病救人与儒学爱人之仁的价值观高度吻合。其本人不仅通经史百家之说,亦擅医学,所作《丹溪翁传》,流传甚广。医家对儒、医关系的认识与儒者相类,元代医家倪维德在所著《原机启微·序》中曰:“医为儒者一事”。金元时期,朝代更迭,一些儒士报国无门,转读医书,使得儒者为医的现象更为突出。他们结识名医,或拜师学医,也临诊处方遣药,祛病疗伤。严存性,新喻州人,其“年少而力学,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3]。罗诚之,庐陵儒士,“尝以明经三试有司,不一得,遂绝意名禄,而隐于医”[4]。罗诚之平时闭门苦读,后游历金陵,以医救人,凭疗效赢得威望,人皆信之。顾叔原,“居吴门,敦诗书,及壮,嗣医业,凡咬咀药味、炮灸捣磨、刀圭之工,夙夜不倦。且究百家方论证治,岁久乡称善医,求请者无暇日。顾君益贫衣褐,趋走闾巷,亲视赢弱,益不以货财为较,而人亦不以韩伯休视顾君也”[5]。江南士人奔清甫,自幼“即强学自爱,积勤十二年,而国亡科举废,又连遭大丧,征徭风火,巨室瓦解。乃尽弃其田畴,取神农、黄帝之书,日夜读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设,以之察脉视疾,论生死、虚实、寒热,虽世业鲜能过之。四方无贵贱贫富,求者如归市,遂以名医闻。”[6]
金元时期医者兼儒、儒者通医的特点使得儒学与医学互惠互利,儒学促进医家自信自强,著书立说,成就大业,医学施仁,普济众生,暗合儒家的人生追求。儒学重生轻死,淡化神学,重人事,远鬼神,有利于医、巫分离,使医学渐渐剥离不合理成分。文史哲、社科综合素质的提高,使人善思,有利于培养医者的多向性思维,开拓思路,有效处理多变病情,创立多种医疗方法,提高疗效。故精儒大医或通医儒士成为金元社会医疗的中坚力量,并推进了医学的创新与发展。
二、道医养生疗疾,深入社会各阶层
道家,崇尚老、庄哲学,清心寡欲,道法自然,统摄人生。东汉张道陵(35年~156年)在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张角创立太平道,后称为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奉老子李耳为教祖,尊之为太上老君。金元道教的发展与全真道大师丘处机(1148年~1337年)有关。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向丘处机请教长生之道,丘处机从天地阴阳,气之聚散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对成吉思汗提出“人生四十已上,气血已衰,故戒之在色”的劝告,又举金世宗色欲过度,身体极弱,戒色后恢复健康之例加以说明。当成吉思汗问及服食丹药的效果时,丘处机答道:“药为草,精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贮金,旋去金而添铁,久之金尽,囊之虽满,但遗铁耳,服药之理,何异乎是?”[7],陈述服食之过,并斥方士以药害人,表明养生“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的道理。其言论为成吉思汗所重视,也使得全真道成为金元时期道教的主要宗派。
道医治病,符咒是重要形式。符咒最早是道家修炼内丹的一种手段,主要是通过控制自己的呼吸、发声等达到养生健身的目的。后来,道医也常用之为他人疗疾,增加了传奇色彩。金代道士刘德仁,道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人,少时习儒,于金熙宗皇统年间创立“大道教”。主张“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虚心实腹,守气养神。”(《老子·第十七章》)。赵清琳《大道延祥观碑》记载,刘德仁的治病方法是仰面朝天,默默祈祷:“有疾者,符药针艾之事,悉无所用,惟默祷于虚空,以至获愈,复能为世人除邪治病。”[8]刘德仁以祈祷治病远近闻名。求医者络绎不绝。不过,富有医名的道士治病,主要还是靠医疗技能及药物。道教全书《道藏》,收入医药类16部,如石药、内经、急救、仙方等;导引养生67部,如内丹静功、导引动功、气功吐纳、屈伸练气、保精存神、服食房中等内容,集中体现了道医学之成就。
金元时期的名家,儒、道、医兼修者众多。元代道医王珪,儒学功底深厚,琴棋诗画皆精,据《四库总目提要》记载,其曾任辰州(今湖南境内)同知,年未四十,弃官隐居于吴郡虞山之下,人称“隐君”。他醉心于炼丹、养生,尤精于医,元太定四年(1328年)撰成《泰定养生主论》16卷,该书集佛、道、儒养生思想于一体,阐述了人生各阶段的养生原则。另外,该书还系统阐述了痰证,所创“礞石滚痰丸”成为后世治痰名方。赵宜真,道号原阳子,元末明初江西安福人,少时习儒,举进士业,后久病不愈,于是弃儒入道,是净明道传承人中,医术最精者。赵宜真道行亦高,“或为诗歌以自警,犹以医济人”(《岘泉集·卷四》),并著有《仙传外科集验方》《追痨仙方》。其中,《追痨仙方》已用到蛤蚧散、无比丸等方,除补虚治肺外,还筛选使用阿魏、贝母、贯众、雄黄、秋石、童便等治痨专药,并采用灸四花穴、腰眼穴等预防传染[9]。
道医崇尚自由,虽有时也受诏于帝王将相,但主要以民间行医为主,这种价值观在金元时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金代医家刘完素,字“守真”,自号通元处士,儒、道、医兼修,他曾拒绝金章宗完颜璟三次召用,不愿做官,因此被赐号“高尚先生”,其一生行医民间,医名远扬。道医吕道章,曾在金大定年间做过县吏,后弃官修道,居山西洪庆观,治疾疫于民间,治者多效验。
道家追求长生,尤重养生。其养生思想常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尊崇。滑寿,元末著名医家,字伯仁,晚号撄宁生,少时习儒,工诗文,后学医,临证多效,著述甚丰,曾一度为僧,融儒、释、道、医于一身。有诗赞之“欲为散木居官道,故托长桑说上池”(《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是说滑寿不求仕进,专于医术,犹如扁鹊,得长桑君之教、饮上池之水而成名医。其中“散木”二字,源于《庄子·人间世》,散木为不材之木,故能多寿。滑寿晚年自号撄宁生,亦有老庄之意蕴,即在扰动的环境中,仍能保持宁静之态。
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记载,元代著名的道医还有徐复、刘开、徐文中、萨守坚、严子成等。徐复,字可豫,号神翁,华亭南桥人,遇异人授予《扁鹊神镜经》,医术大增,尤精《灵枢》《素问》之学。《南开府志》记载,刘开,字立之,兼修佛、道之学,遇神人授《太素脉》,后被元帝赐号“复真先生”,著有《方脉举要》。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擅针术,治人立效,也以符呪救人,人称神医。萨守坚,元末蜀西河人,会“呪棗”,即对枣念咒,以祛邪治病。严子成,字伯玉,医术高明,元大德年间,元廷曾召其入御药局,被拒绝,行医民间,89岁时自言自己将往“仙府”,无疾而终。
总体来说,道医既有古代祝由符咒等原始医疗形式,也有甚合医理、人理之养生、治病之道,又由于许多医、道兼修的医家的加入,使得道医学得以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医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佛医借医弘佛,普救众生
佛教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六世纪创建于印度,后有大乘、小乘之分,又有诸多宗派。释氏知医,后世封为大医王,其传教过程中,借医弘佛。之后,佛教以悲悯之心,以医济世,敬神救人,成为佛教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佛教于公元前二、三世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同时带来的还有佛教医学。宋代逐渐普及,金元时期盛行,佛教地位提高。《元史》记载:“元兴,崇尚释氏……帝师八思巴者……学富五明……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忽必烈即位后,尊高僧为帝师,并授刻有“元大都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的玉印[10]。元宪宗、世宗皇帝还曾敕命少林寺住持福裕和尚在河北蓟县盘山、号安、太原、洛阳等分别建立五座少林寺,扩大了佛教及佛教医学的影响。
大乘佛教要求僧侣学习“五明”,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医药是必修知识。故不少僧人精于医理,医术高明,有佛医、僧医、医僧之名,并有医学著作传世。福裕撰写《少林金刚延寿功法》,在金刚功法中贯穿阴阳五行学说,阐述人体脏腑与阴阳、肢体活动与阴阳损益的关系,并以五行学说推理金刚功招式,说明习练金刚功可以健体延寿的作用机理[11]。元代僧医继洪,释继洪,又名洪澹寮、澹寮,河南人,儒、释、道、医皆精,不仅撰有佛教著作,且能游历南北,遍施医药以济民。其南游行医,留心各地民俗、病种和治疗方药,著有《岭南卫生方》3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岭南瘴病文集,详述岭南各地治瘴方药,颇有学术价值,历世多次再版。又采集民间秘方验方,分类编次,撰成《澹寮集验秘方》15卷(1283年),成为流行于金元的综合性医书,后世多有引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录澹寮方,其中有江苏镇江甘露寺僧治疗反胃的汤药。方中用药饴糖、生姜、炙甘草、食盐等(《本草纲目·谷部·干饧糟》),体现佛医方药简、便、廉的特点。
寺院医科各有所长。元代僧医德宝,号雪岩,为浙江萧山竹林寺第9世医僧,以女科闻名,慕名前来就诊者众多。所著《竹林寺三禅师女科三种》经竹林寺后世医僧轮应、静光重新考订,增益成书,名为《女科秘要》4卷。后人又加以评按注录,刊入《胎产新书》,可见其学术价值。寺僧隐居山林,养家护院,健身自养,故伤损常有,有些寺院擅长外科、伤科。少林寺不仅自创多种健身养生之法,还以伤科著名,并于金代设立少林药局[12],以医药普救众生。元末慧炬和尚为福裕的弟子,文武双全,尤以气功、禅杖、剑术见长,并擅长推拿按摩。他针对寺僧常见伤损,总结按摩部位、手法及疗效,并绘有穴位图[13]。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伤科僧医还有石岩、宗发等。公元11世纪,高僧阿狄夏所著伤科专著《头部伤固定治疗》也十分有名。
佛家以慈悲为怀,不仅自疗自养,也以悲悯恻隐之心救人,所用药物常价廉易得,有时免费施医赠药,甚得民心。又善借信仰之力,施以心理疗法,精神调节,故信者甚众,成为金元提供社会医疗服务的重要力量之一。
四、回回医药,异域文化参与社会医疗保障
伊斯兰教(回教)源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公元610年,由穆罕默德(570年~632年)创立,为信奉安拉的神教。该教于唐代传入中国,金元统治者提倡该教,故有大量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涌入,同时也带来了富有异域色彩的回回医药,并成为金元时期社会医疗保障的重要力量。
金元时期的回回,包括波斯(伊朗)人、西域人(希腊罗马、印欧人种)、阿拉伯人、犹太人、吉卜赛人等,涉及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或地区。在中国,也包括伊斯兰信徒穆斯林,除回族之外,还有维族、羌族等。金元提倡“胡方胡俗”,重视回回人与回回文化,形成“胡”文化共同体。元政府设立西域医药司、广惠司、回回药物院、回回药局等机构,引进和发展回回医药。
元代陶宗仪笔记体著作《南村辍耕录》,如实反映了元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概况,所记载的元代曲目中,有“眼药孤”“眼药里”“香药车”“风流药院”等涉医曲目名。有学者推测,曲目“眼药孤”“眼药里”等的主题与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绘画《眼药酸》相似。《眼药酸》中,有一人头戴奇特高帽,穿橙色大袖宽袍,高冠上画有一颗绒球样大眼,身上画有许多小眼,斜背的药袋面亦画有浓眉精眸的大眼一只,前后挂满绘有眼睛的幌子[14]。《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条载,宋代不同行业的服装式样都有一定规定,“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目的是方便他人了解业者身份[15]。身着以“眼”为主题的服饰应可以表明画中人眼科郎中的身份。而波斯人以擅治眼疾闻名,故剧中人可能是来自波斯的眼医。
曲目名“香药车”“风流药院”也与回回医疗有关。“香药车”是回回人售卖香料及药物的流动车,四处游走,兜售香料、香药、各种露剂及膏剂,常执铜铃招揽生意,如串雅之流,人称“贾胡”(胡商)。这与中医开药店,坐堂看病、售药的习俗不同。“风流药院”即回回药物院,是元代太医院下辖的掌管伊斯兰医药的部门,人员很多是来自伊斯兰、波斯等国的医药人士。由此看来,这些涉医曲目的主角很可能是被称为回回医的异域医者。这些富有异域色彩的外来医者可以为剧情提供新鲜的素材,更容易吸引观众,故这些医药杂剧应可以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下回回医药参与社会医疗的状况,只可惜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
记载金元时期回回医疗的文献,流传后世的并不多,元末出现的《回回药方》,为汉语著作,但混有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及其译音。书中有中药,也有外来药物,以香燥之品居多。全书不涉及阴阳学说及中医学辨证体系,而是有着十分浓郁的伊斯兰医学特点,书中还涉及古希腊及古印度等传统医学。元代郡侯萨德弥所撰《瑞竹堂验方》,亦反映回回医药成果,其中的经验方多用香药海方,丰富了中药学内容。金元时期进入中国的回回药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各国贡品,但更多的是贸易往来,尤其是元代,海外贸易频繁,大量异域商人涌入,有些商人长期在中国居住或为官,带来了异域医药文化。元代回回医官阿老丁,原为西域巨商,来华后以资财奉献,并从军,曾出任太医辽都事,参与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审定,签署付印过程。据考证,其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丁鹤年(1335年~1424年)的曾祖[16]。丁鹤年生长于中国,幼时习儒,就读于南湖书院,好诗文,亦知医,与滑寿等名医为友,互有切磋,晚年主要生活在杭州、武昌等地。以此可知,回回中有一部分定居中国,最终融入中华民族,而传入中国的回回医药也成为中国医学的组成部分。
元代,回回医药对社会医疗有较大影响。比如香药的使用无论是在宫廷还是民间均十分盛行。《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大元年(1308年),元廷专设御香局,官秩从五品,掌修御用诸香,可见香药的品种及用量均具有一定规模。而在民间,售卖香品、香药的流动货车更是穿行于大街小巷,贴近市井家庭,香品、香药及香露走进厅室厨房及家庭药柜。同时,讲述回回医故事的曲目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也里可温教士施医,以官方医疗活动为主
耶稣创立基督教之始,即有施医施药等医事活动,所到之处,皆以医疗救助为由头。中国唐代有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传入,称为景教,并建波斯寺、大秦寺(大秦便指欧洲地区),即后来的教堂。现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收藏有唐德宗二年修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中记载了景教主僧伊斯(Usu)曾被唐朝赐以“金紫光禄大夫”的称号,并在郭子仪军中担职,官场、教内地位显赫。唐末宋初,中国医生(中医)曾西行巴格达学习盖伦之学,请教名医Rhezes(850年~923年),但不知所踪。金元时期,景教复苏,蒙语呼为也里可温,指基督教或信奉基督教的人。如《元典章》卷三十三载:“大德八年(1304年)……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基督教)教门”[17]《元史·文宗本纪》云:“天历元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基督教徒)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
中国北方民族中,也里可温教徒较多,尤其是辽国契丹人,元代蒙古克烈、乃蛮、汪古等部族。元廷贵族祖居贝加尔湖地区,毗邻欧洲,有些后宫嫔妃信奉基督教,如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旭烈兀汗之妻托古斯等[18]。元廷也招募也里可温教徒为雇佣军,统称为色目人。元廷中,也里可温教徒马薛里吉思善医药,擅长制造舍儿别(又名舍八里、舍利别、解渴水)。舍儿别是以果汁或药物制成的糖浆剂,根据原料的不同,具有不同的保健或治疗作用,后成为中药的剂型之一。元代西班牙籍教徒爱薛为太医院重臣,官至从二品。爱薛通晓多种语言,创建回回医药院体系,执掌回回药物院。元亡后,中国的基督教也开始衰落,直到明清,才又重新兴起。
金元时期,也里可温景教徒的医疗活动多为宫廷或官府服务。《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元统癸酉年(1333年),景教徒聂只儿治愈驸马刚哈剌咱庆王怪病的医案:“今上之长公主之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因坠马,得一奇疾,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乃也里可温人也,尝识此症,遂剪去之。顷间,复生一舌,亦剪之,又于真舌两侧各去一指许,却涂以药而愈。”[19]。虽然据此医案不能确切知道附马到底得了什么病,但回回医的外科水平在当时确实十分有名。不过,也里可温所参与的民间医疗活动比较有限,在汉人聚集区的医事活动不多。故其在民间的影响力远不及儒医、道医、佛医及回回医。
六、原始宗教巫祝医疗盛行于民间
金元时期,巫祝成为民间医疗选择之一,且十分盛行。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云南一些地区,没有真正懂医学知识的人,当地人生病时,就请巫师做法治病[20]。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反映了当时巫祝的流行。金元医学分科有祝由书禁科,以符咒禳病为主,与巫术相近,故常巫祝并称。念法符咒,驱鬼捉妖,其中包括暗示疗法、心理疗法、精神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在特定环境下,若措施得当,也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巫祝参与医疗活动,形式多种,如跨火盆、喊魂等。跨火之俗源于人们对烈性疫病的认识,《说文》曰:“<释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疫病也叫鬼疫、撞鬼,病情暴发时,患者病状相同,犹如撞鬼。因原因在鬼,故医药无效,死亡率高。民间认为,鬼畏火,于家门前置火盆,可驱鬼避害,如果鬼已附身,跨越火盆后,鬼会因惧怕火焰而逃离,从而达到保障健康的目的。后世在婚丧嫁娶时也有跨火盆习俗,总以祈福避祸为目的。
喊魂疗法源于人们对人类灵魂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人们相信,生病或死亡是因为灵魂离开人体,故请神灵沟通者通过喊魂追回离开的灵魂,使其附体,形与魂聚,则可使病体康复。比如北方各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奉灵魂不死,相信灵魂被魔鬼所掳,与身体相分离,不得返身,是致病的主要原因。族群中有人患病,多求助于萨满(男巫师)、巫妪(女巫)。他们沟通神鬼,鸣铃击鼓、绕帐歌舞、执剑疾呼,从神鬼处带回被束缚的灵魂,以疗疾去病,护卫族人。萨满治病以暗示疗法、心理疗法为主,也涉及物理疗法及药物的使用,如火灸、刺血、冰敷及单方单药等。但总体来看,金元时期的萨满治病,其治疗手段及药物的使用主要是为巫祝仪式服务的,医疗作用实在有限。
金元名医也常基于这些民间习俗、信仰,因势利导,借此进行暗示疗法、心理治疗。张子和等人医案中不乏佐证。《儒门事亲·疮疖瘤肿五十一》载有以咒禁治疮疖的方法,咒语为:“龙鬼流兮诸毒肿,痈疮脓血甚被痛,忘心称念大悲呪,三唾毒肿随手消。”并介绍具体念法:“一气念咒三遍,望日月灯火取气一口,吹在疮肿丹瘤之上,右手在疮上虚收虚撮三次,左手不动,每一气念三遍,虚收虚摄三次,百无禁忌。如用之时心正为是。此法得于祖母韩氏,相传一百余年,用之救人,百发百中。若不食荤酒之人,其法更灵”[21]。充满迷信色彩,但其中的“不食荤酒”,又合医理。饮食清淡,有利于疮疖的治疗与康复。此种医、巫混用,亦医亦巫的疗法在金元医疗中并不鲜见。
结 语
忽必烈曾说:“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22]。统治者对不同宗教文化的包容态度,使得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多元发展,体现在医学上,就是医学与多种形式的宗教文化杂陈共存,相互渗透,共同参与社会医疗活动。
金元名医儒士,儒、医兼修,也能从宗教医学中汲取精华,合理运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拥有精湛的医疗技术,祛病疗伤,是病家的最佳选择。故无论是宫廷、官府还是民间乡野,均可见他们的身影,是最重要的社会医疗力量。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追求长生不老,擅长养生之术,历来为医家所重视。医者兼道,道者善医,医疗活动及养生之道触及社会各阶层。佛教虽源于印度,但自进入中国后,即已中国化。佛家慈悲为怀,佛徒必习医术,借医弘佛,慈悲为怀,使医道、人生之道相辅相成,维护僧侣及信徒的身心健康,亦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医疗力量。伊斯兰教带来的回回医药盛行于金元,在药物种类、外科技术及药物剂型等方面对中国医学贡献较大。但金元时期基督教的医疗范围较窄,且以《阿维森纳医典》为宗,医学体系亦具有局限性。直至明清,随着现代西方实验医学体系的发展,才在中国的社会医疗中产生巨大影响。萨满教为原始宗教,巫祝成分较多。笃信鬼神的病家,遇病但求巫祝,也有先求医问药,无效者转而求之于巫祝的。我国早在春秋时期,无神论就开始萌发,出现将鬼神巫祝排斥出病因队列的先例[23],但巫祝文化在我国古代医疗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可见,只要有医学知识无法解释的疾病现象,就会有巫祝参与其中,承载着人们治愈疾病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医疗的组成元素。
宗教的创立与宗教医学的形成同步。有人说,一切宗教都是广义的医学,或称为庙堂医学。宗教经典论医,神职人员知医,通过疗病除灾、行医赠药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借此传播教义。从文化角度分析,宗教文化和民族医学文化密不可分,并互相影响,关乎国家民族的医疗发展取向。它们各有特色,但却各自带着时代的烙印渐行渐远,或风光不再,或发展、融入新的医学体系。而古代医药卫生事业不离宗教,又不同于宗教的文化现象,影响深远,至今不能泯灭。
[1]相鲁闽.王安道医书评释[J].河南中医,2014,(7):1220.
[2]丹波元胤.聿修堂医书选—中国医籍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716.
[3][4][5][6]李修生.全元文·第四十九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266,400,493,521.
[7]丘处机.丘处机集[C].济南:齐鲁书社,2005.442-443.
[8]北京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历代王朝与民族宗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20.
[9]江幼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361.
[10]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4518.
[11]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课题组.争鸣与创新中医学术流派研究[M].华夏出版社,2011.227.
[12]李修生.全元文(第一册)[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06.
[13]德虔,德炎.少林长寿秘诀[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57.
[14]董锡玖,刘峻骧.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修订版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
[15]孟元老撰,王云五主编.东京梦华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89.
[16]白寿彝,王毓铨.中国通史.(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556.
[17]苏鲁格.蒙古族宗教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280.
[18]乌恩.“也里可温”词义新释.蒙古学信息[J].2001,(1):14-16.
[19]陶宗仪.辍耕录[M](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137.
[20][2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Z].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49,87.
[21]张从正.儒门事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47.
[23]王振国.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