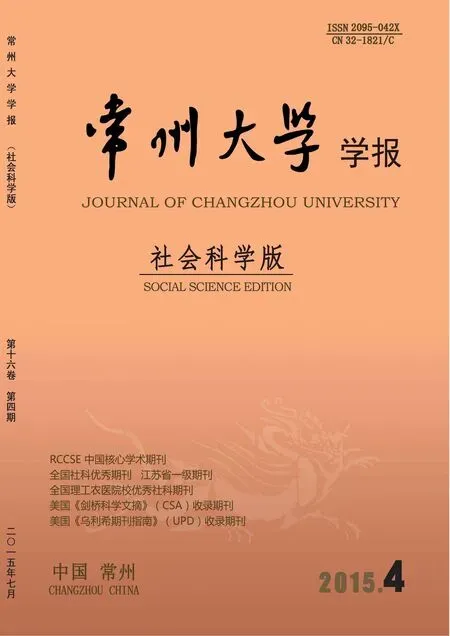仁道司法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李德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一、重新发现仁的意义
仁,是儒家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孔子在《论语》中一共109次谈起“仁”,而每次提到“仁”的意涵都各不相同,可以说“仁”的内涵十分丰富。
首先,孔子的仁是尊重“亲亲”原则,以“爱人”为核心要求的道德范畴,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保护。比如,马厩失火,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伤人乎”,郑玄认为这里反映出了孔子“重人贱畜”的思想,说明孔子最为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孔子的“仁”之论证乃是基于对于人之自然与社会属性的双重观察而得出的,因此,“仁”除了具备形而上的正当化功能外,更具备了日常生活的心理基础,从而为人们以“礼”履“仁”提供了社会与人性基础。孔子将“三年之丧”的周礼,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而又将孝悌建筑在朴素的日常父母之爱上,因而是否行旧礼的基础在于人的内在心理而非外在强制又更非宗教的神秘要求,也就是“今女安,则为之”。
其次,儒家的“仁”同时也具有评价意义,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规范的内容正确性进行评价。所谓以“仁”释“礼”,就是指经由“仁”的塑造,保障“礼”的品质,即社会规范的内容正确性。如果从法理学的视角去看,仁是法律背后更高的价值准则,成为了现实法律的高级法背景。仁之所以能够成为“高级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以证明:首先,孔子对仁的定义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展开的:“仲弓问仁,子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2这是消极的一面,而积极者则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92从以上两句话可以看出,孔子对“仁”的普遍意义上的界定仅仅是在形式上的,并不包含任何特殊的目的和内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孔子对“仁”的这两个界定才能在普遍意义上被适用,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以任何借口来逃脱“仁”的这两个要求。其次,孔子对于“仁”的内涵的实质界定是多元的.在孔子看来,“仁”的具体内容包括:“孝弟”、“爱人”、“先难而后获”、“恭敬忠信”、“恭宽信惠敏”。甚至于,在不同的场合,对于不同的人,孔子对于仁的具体内容的叙述也各不相同。但必须指出的是,孔子的些界定都是在前面所提及的“仁”的形式普遍性意义上展开的,这些具体的内容必须置于上述对“仁”的形式界定之下来进行审查。这样,一方面暗示了“仁”具有多种意义和内涵, “仁”的概念是开放和多元的,不是封闭和唯一的,这样就排除了任何人试图宣称自己掌有对“仁”的绝对且唯一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对仁进行普遍意义上的界定,使仁的概念变得抽象,大大拓展了仁的意义内涵。现实中的人们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仁”新的意义和价值。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仁”的要求贯穿了政治法律的制度与实践,也体现在司法的活动当中。古代司法以“法中求仁”为根本目的,惩治犯罪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司法的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儒家人伦秩序,实现社会的基本正义,最终促进君主“仁政”政治目标的实现。以“法中求仁”为目的的仁道司法核心是在司法活动中贯彻“爱人”的人本思想,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宽宥犯罪的制度措施。另一方面,“仁”也规范司法权行使的道德内容,司法活动应该体现儒家“仁”的思想的要求,只有合乎仁道的司法才能取得公信,司法的结果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仁道司法的实质内涵
(一)仁政与司法的关系
在孔子之“仁”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概念。具体而言,孟子的仁政思想包括了“从民之欲,为民制产”、 “薄税敛”和反对“滥杀”等多个方面。然而,孟子“仁政”思想的真正价值其实并不在于以上概括的一些具体政治主张,而在于其思想实质:人政,即以人为政治之目的。孟子之“仁政”的基础是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统治者将此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的施政过程就是仁政。孟子所说的“推恩”的政治实际就是要让统治者以自己的心理去体察百姓感受,即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其内涵是要将政治的对象——百姓由抽象的芸芸众生转化为有感情、有欲求的人来对待。孔子说仁的本意是爱人,孟子之仁政也可以说是爱人的政治,以人为目的的政治,人本的政治。
孟子从人本的角度提出“仁政”,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就是礼乐与刑政两种统治手段的运用。仁义之所以是为政之本,在于仁政是以人为目的的政治。因此就统治的方式而言,礼乐之治可以移风易俗,使百姓能够形成自我治理的良好风气,而不是依靠严刑峻法的威吓来使百姓臣服。简单以刑政压服百姓的政治,并不合于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理想。在仁政的政治理想中,如何处理礼乐与刑政两种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这就涉及到仁政与司法之间的关系。
首先,实现仁政是司法的根本目的,司法是实现仁政的手段之一。魏征就曾经这样概括仁政与司法的关系,提出“仁义为理之本,刑罚为理之末”的思想。《全唐文》中曾经记载魏征之语:“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己明矣。”这里将刑罚列为末,并不是说刑罚不重要,而是与仁义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地位相比,仁义发挥更为基础性的作用,而刑罚只是实现仁政的手段与措施。
其次,产生犯罪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实现仁政。《论语》引述曾子之言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1]191孔子认为百姓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是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司法官员在量刑的时候应该将犯罪的社会原因考虑在内,对犯罪人根据情况予以一定的宽宥。唐代君臣在总结隋朝法制得失的时候也指出,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制松弛或是司法过于宽缓,而是恰恰是因为隋朝统治者不能“修仁义”,行仁政,因此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因此,唐太宗就说:“隋炀帝岂无甲杖?适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当以德义相辅。”[2]252
最后,在王权大一统的体制下,君主施行仁政是司法宽和的前提。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之好恶深深影响一时的政治风尚,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君主专制时代政治现实的写照。如果专制君主好用重刑治理国家,那么全国的官吏都会以治狱深刻为自己的目标,从而导致刑狱泛滥。汉代路舒温认为,刑讯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重用酷吏,当治狱深刻成为官吏选拔的一项标准的时候,则天下官吏无不以酷吏为自己的榜样。“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3]唐太宗对于酷吏以入人以罪的心理把握的更为清楚,他说:“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问法官刑法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2]446
(二)仁道司法是司法权行使的规范性要求
第一,哀矜折狱、生道杀民的刑事司法观。孔子提出的“哀矜折狱”是与重刑主义相对的刑事司法思想。《论语》引述曾子之言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他要求司法官员在察明事实真相之后,还要予以“哀矜”,考虑百姓犯罪的社会原因。孔子认为百姓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是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司法官员在量刑的时候应该将犯罪的社会原因考虑在内,对犯罪人根据情况予以一定的宽宥。孟子在孔子哀矜折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生道杀民”的刑事司法主张。孟子说:“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1]352赵岐注释道:“杀此罪人者,其意欲生其民,故呈伏罪而死,不怨杀者。”根据赵岐的解释,以“生道杀民”的意义是说司法官员在审理死刑案件时,应以“求其生”之道慎重地处理案件。如果确实罪大恶极,则应该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得已将之处死。“生道杀民”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全人的生命。在儒家看来,刑罚的作用不仅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广大平民的安全,对于犯罪人也要尽量以仁恕之心对待。
儒家所言的哀矜折狱与生道杀民并不是要司法官员毫无原则的宽恕罪犯,而是要根据实情,以法中求仁而不是法中求罪的态度来处理刑事案件。哀矜折狱与生道杀民的基础都是“中”,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中和者,听之绳也”。[4]92荀子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4]188法中求仁并不意味着法外容情,而是使无罪之人免于刑罚,可矜之人得到宽宥,有罪之人罚当其罪。
第二,司法执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论。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执法适中,宽严适度。这个“中”和“度”应是符合科学依据的司法裁量的确定,而不是用刑的任意。儒家并非一意求宽,目的在于法中求仁,一味宽缓的司法如果导致放纵犯罪的结果,显然不是儒家仁政的目的。因此,宋代程朱就一改前代儒家力主司法宽和的观念,主张重刑。他们要求刑事政策应该根据当时实际政治需要所作出的适度调整,其在理论上将重刑与仁爱相联系。朱熹强调刑事司法活动可以抑制人的恶性,震慑犯罪,这本身就蕴含着仁爱的精神,即通过惩罚来劝诫百姓,使民众养成敬畏法律的习惯。比如,朱熹就曾经指出:“惩一人而天下知所劝诫,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5]因此,用刑之宽猛只是儒家权变精神的体现,是统治者在天下大乱之际的权宜之计,并不影响背后司法的目的依然是实现仁政。故而,他说:“天下大乱,民遭陷溺,亦与以权授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就司法而言,宽与严都是成文法的框架内的具体用刑裁量问题。根本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补充而是在准确适用法律前提下的用刑宽缓还是深刻。对于用刑裁量的宽与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司法执中,首先正确保证准确适用法律的规定,然后在量刑时以“法中求仁”的态度对待刑事司法。这就是雍正帝所言的: “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心本宽仁。”比如,在秋审、朝审之中,提倡: “凡情有可原者,务在缓减”,并以此标榜“宽严之用,务在得中”。因此,清代秋审、朝审中出现的诸如停勾、减等、留养承嗣等做法,都是“听狱者,求所以生之”理念的体现。
第三,情法两得的情理司法观念。《论语》中曾记载一段孔子与其弟子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宰我追问孔子“三年之丧”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从孔子与其弟子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将“三年之丧”的周礼,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论语·阳货》)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而又将孝悌建筑在朴素的日常父母之爱上,因而是否行旧礼的基础在于人的内在心理而非外在强制又更非宗教的神秘要求,也就是“今女安,则为之”。礼正是由于取得了这种日常心理的内在依据而趋于人性化,礼的依据和正当性全系于人自身。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由神的准绳命令变而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而变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6]正是由于孔子将社会规范的正当基础直接诉诸于生活情理而非神意,使中国传统法律的合理性直接建立在这种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因而国法与天理、人情才有了沟通的基础。清代名吏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对中国古代的法律运作有一段十分精妙的结论:“读律尚己,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所谓人情,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的伦常纲纪之情。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中人本因素的体现正在于这种基于人间伦常的情理之中。
三、仁道司法的现代价值
(一)以人为中心的实质主义司法理念
中国古代仁道司法的一大特征是以现实中的人为法律规制的中心,在法官的眼中,案件中的人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而且是与其所处的伦理秩序、生活情景、人际情感相联系的个人。传统司法中不存在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根据其所处的人伦秩序的位置而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同时,法官在判决时也会考虑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情景和人际情感联系。
首先,传统司法中的人是处于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人,每个人都按照其所生活的伦理秩序中的位置来承担责任。比如,传统法律中以当事人之间的服制关系来作为决定案件性质和罪行的前提条件,其在刑事法律传统中的表现就是“准五服以制罪”。服制定罪的意义是在立法确定有关亲属相犯行为的罪名刑等时,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尊卑作出区别规定。在亲属之间的伤害案件中,法官就会根据亲属间的尊卑长幼关系的不同来确定每个人不同的法律责任。如果是卑幼殴击尊亲属而未折伤,则根据其所殴击对象的尊卑来确定罪行,殴缌麻尊亲属徒一年,殴小功及大功尊亲属各再加半年,殴齐衰尊亲属徒三年,殴斩衰尊亲属则斩。而反过来,若是尊长欧击卑幼而未折伤,则按照被殴者的身份秩序相应减轻处罚。可见,在亲属间的伤害情形中,尊亲属犯卑亲属,服制关系越重,罪刑越轻;卑亲属犯尊亲属,服制关系越重,则罪刑越重。这样对于不同亲属身份的人给予不同的判决,恰恰体现了儒家“爱有等差”的原则,体现了传统司法中的人往往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人伦关系之中,定罪量刑也需要根据人伦关系的远近而决定。
其次,传统司法中的人是生活中的个人,每个人在案件中都有其具体的生活情景和人际情感联系,法官在裁判时都必须要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理,这样才能做到“情法两尽”。比如在“弟弟为争夺家产而殴打兄长致死”的案件中,法官在裁判中就注意到本案案犯是家中独子这一生活事实,如果判决案犯以死罪,则难免给一个家庭造成绝祀的结局。甚至法官还假设了被害的兄长的想法,认为即便兄长泉下有知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庭因为弟弟犯罪而绝祀。因此,法官不惜违背法律的文本规定对本案中殴死兄长的弟弟进行宽恕。
成文的律令对于犯罪或处罚的规定往往是抽象的且具有普遍性的。比如《宋刑统》对“指斥乘舆”罪的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律文小注曰:“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法律对“指斥乘舆”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模式都作出了普遍性的规定,全体臣民只要有“指斥乘舆”行为的都犯此条,除皇帝本人不可能犯此条外,无一例外。律文小注仅仅排除了因为议论国家政事有乖失而冒犯天子尊严的行为,如果是因议论政事而有过错则需要上请,由中央的司法官员和皇帝作出决断。比如,在“前妻诉丈夫指斥乘舆”的案件中,被告为原告之前夫就是案件中的具体人伦情感关系,而法官在裁判时也正是基于对具体案件中的人伦情感关系的考虑而作出的裁判。法官认为,夫妻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人伦秩序,夫妻之间应该存在深厚的感情和情义。在具体案件中,天子尊严所代表的国家政治秩序和夫妻间的人伦情感发生了冲突,法官的价值取向恰恰是站在了保护夫妻之间的人伦情感关系一边。
与传统司法以现实中的人为规制中心不同,现代司法的着眼点是人的行为。现代司法以人的行为为规制中心,与整个现代法制系统的宗旨相关,体现了法律的进步和发展。首先,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排除了传统法律中对人的思想的规制。在现代法制的体系中,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法律的规范和调整,刑法中废除思想犯,是近代刑法的一大进步。而传统法律以人为规制中心,往往强调原心定罪,其规范的触角往往深入人的思想。历史上,规范和调整思想活动的法律往往打击与当时主流所不符的所谓“异端”思想,对人类思想发展造成了禁锢的作用。同时,以行为为规制中心的法律与以权利为本位、高度抽象化、类型化的现代法律体系是相互依存的,关注行为而不是人,是法律发展史上的进步。然而,以行为作为规制中心的现代司法也有其弊端。比如,以行为作为法律规制的唯一对象,则会造成对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个人的忽视。[7]虽然,现代司法理念以当事人为中心,在程序上赋予当事人各项权利,实体法律上保障当事人各项基本诉讼权利。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所关注的只是当事人所为之客观行为,作为判决对象的当事人只是作为抽象的、高度类型化的形象而存在,司法所关注的只是具备或不具备行为能力或法律资格的抽象的人,而非现实具体存在的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司法以人为中心的特点恰可以弥补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遗忘。仁道司法,在司法中充分重视人情因素的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在司法过程中发现和重视当事人行为背后的现实情理,成文法传统中的立法者重视对行为的抽象和类型化、体系化,而司法者就应该在普遍适用的成文法的规范下考虑具体案件中的特殊情景,在这个将普遍性规则与具体个案的特殊情景相调适的作业中,人情往往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传统法官以情理解释法律、在判决中阐释个案中的人情与法意的经验可以更好地增加普遍性法律在特殊案件中适用的合理性,不仅起到了正确适用法律的作用,而且可以同时做到使当事人口服心服,做到案结事了。
第二,仁道司法使法官认识到具体生活中弱者的真正存在,看到个案中当事人因为身体缺陷或是精神缺陷等情形所造成的具体特性。比如,对于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某项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从主观方面而言,就应该以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条件为标准,而不能以普遍的多数正常人的情形为标准。
第三,仁道司法往往看到案件中所存在的现实中的个人,往往是将人置于其所处的人伦关系中去解决案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情与人伦有互通之处。从一个方面来说,将人置于不同的人伦关系中来确定其法律适用,可以说传统社会有家族而无个人,家族伦理吞噬个人价值,是传统社会个人不具有独立性的体现。但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分析问题,传统司法重视人伦秩序和睦的法律价值,注重保护人际之间的伦理秩序和血缘亲情,在某种程度上说,抵制了王权对家族伦理秩序对渗透,司法在王权与家族之间划上了一条人伦情感、伦理秩序不得侵犯的明确界限。
(二)先教而后杀的司法教育功能
古代社会刑罚严酷,法律的主要功能不在于规范,而是对犯罪者的惩罚。上古传说五刑之属三千,动辄刑人肢体,轻则残疾,重者死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孔子倡导“仁政”,认为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发自内心地接受规范的约束,只会使人丧失廉耻。因此,社会的治理根本在于施行仁政和为政以德,引导百姓自觉遵守社会的一般规范。同时,儒家相信人的本性可以为善,因此,不能放弃后天改造人心的教育努力。也正是由于人性本善的人性假设,儒家普遍相信教化对改造人心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指导下,儒家将拯救时弊的希望寄托于人性的恢复和人情的维护上。人际情感、伦理的维系,则有赖于仁政和“德治”。“仁政”的重要一环,就是推行教化,也就是对百姓进行日常伦理的教育,就法律与教化的关系而言,教化应该为刑罚的先导,刑罚不是目的,最终应该通过司法过程使百姓得到教化,理解圣人人伦、人情之教。
将“仁”的思想贯彻于司法中,体现在儒家十分强调司法与教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儒家强调“教而后诛”。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孟子发挥孔子“先富后教”之说,认为对待百姓首先应该“制民之产”,使百姓有恒产然后有恒心。在此基础之上,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轻。”富与教,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缺乏恒产和基本生活保障,百姓“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而如果富而不教,则会“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孟子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陷民于罪,是“罔民也”。其次,古代儒家还十分重视司法本身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古代州县官吏也往往将教化百姓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此,在古代州县官吏除了要作为行政上的实务官和司法上的审判官两种角色之外,还有肩负教育子民的重要职责。唐代进一步将官员的教化职责法律化。唐代法律规定:官员的考核标准分为“四善”、 “十二最”,其中居“四善”之首就是“德义有闻”,而“十二最”中专门规定“政教之最”,其要求是:“礼义兴行,肃清所部”。[8]
美国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指出:“所有的审判都应该具有教育意义,不只是确定罪行。延长诉讼程序总比责令和嘲弄被告或使其缄口要好。被告的自由陈述也比法院 (依霍姆斯之义)做不体面的事要好。法院的审判应当帮助人精神净化,而不应在我们的尊严之上再施暴行。它应该把蕴含在法律程序中的价值戏剧化,而不是漫画化。”伯尔曼进一步分析了教育之于法律的意义:“法律不应只图方便,它应当致力于培养所有有关人员——当事人,旁观者和公众——的法律情感。”[9]伯尔曼认为,只有当公众在法律程序当中唤起了他们对整个生活的意识和对终极目的的意识的时候,法律才能真正地为公众所尊重。因此,司法应当起到教育公众尊重法律、敬畏法律、信仰法律的作用。传统的司法寓解决纠纷与教化万民的功能于一身,实际上起到了在社会中树立核心价值观念的作用。一方面,传统司法通过法官的教谕行为,劝导百姓遵守儒家的价值观念,通过司法的功能在社会中推行儒家的社会价值观、建立社会共识。而在另一方面,成为社会共识的儒家伦理价值也促进了百姓对于司法判决的信服程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唐]吴兢.贞观政要集校 [M].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3][汉]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9:1810.
[4]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09.
[6]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21.
[7]胡玉鸿.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之调适 [J].法学研究,2010(6):40.
[8][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M].栗劲,译.吉林:长春出版社,1989:254.
[9][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4-35.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