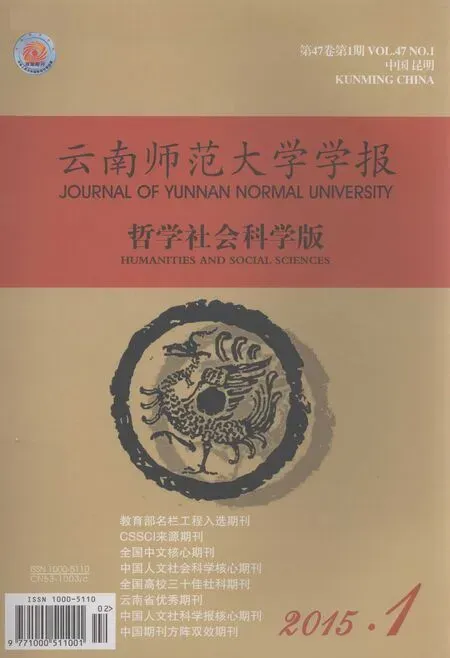中国缘事诗学发凡*
殷学明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中国缘事诗学发凡*
殷学明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就蕴藏着丰富的诗学资源。缘事诗学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资源之一。它滥觞于“结绳记事”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汉代“以事系诗”的《诗》学,发展于唐代“触事兴咏”的《本事诗》,成熟于宋代“论诗及事”的诗话。然而五四以来,中国诗学一般偏重于缘情诗学的转化而相对忽略了缘事资源的开发。发凡缘事诗学,一是要把缘事诗学从中国诗学的隐体系中呈现出来,从而为中国诗学的多元发展提供多种选择;二是要把缘事诗学从西方叙事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为中国诗学本土化发展提供一条路径。
中国;诗学;发凡;缘事诗学
诗是如何产生的?在中国往往言必称“诗缘情”,其实在“情志不通,始作诗”之外,还有“在事为诗”的缘事观念。叙事与缘事不同,前者重文本内部事件的排列,属内部研究;后者重文本与事件间的生成关系,属外部研究。袁行霈指出,中国诗歌缘事而发的“‘事’是触发诗情的契机,诗里可以把这事叙述出来,也可以不把这事叙述出来。‘缘事’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①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16.。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缘事诗学资源,但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对缘事诗学发凡,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传统,而且也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当代诗歌创作与诗学建设。
一、缘事诗学的历史与现实
在中国古代,缘事诗学的概念比较模糊、观点不够明确,整体上比较零乱和琐碎。但经过发凡纂论,缘事诗学还是有迹可循的。它滥觞于“结绳记事”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汉代“以事系诗”的《诗》学,发展于唐代“触事兴咏”的《本事诗》,成熟于宋代“论诗及事”的诗话。
(一)缘事诗学的滥觞。记事和抒情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精神需要,无怪罗兰·巴特把人视为“叙事的动物”,苏珊·朗格把艺术视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众所周知,上古初民一般通过结绳记事增强历史记忆来维护基本的生存需要。《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②宋祚胤注释.周易.[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0:352.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缘事观念大体是这样产生的:人类在历事和言事过程中逐渐形成历史意识,然后在历史意识积淀下逐渐形成缘事观念。“上皇之时,举代淳朴”;“饥者歌食,劳者歌事”,赋予节奏,缘事而发,素朴的诗也就诞生了。“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是诸神总祭之事,同时也是素朴的诗。闻一多在《歌与诗》中明确指出:“‘诗’的本质是记事的”。③闻一多.闻一多讲国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244.最初诗与史或事是浑然一体的,诗就是诗性的事,诗性的事就是诗。正如孔子所云:“文胜质则史”,“史之阙文”犹如“有马者,借人乘之”(《论语·卫灵公》)。一言蔽之,缘事诗学就滥觞于结绳记事的历史活动之中,它是人类历史意识、求真意识的产物。
(二)缘事诗学的萌发。周代乃至两汉,是缘事诗学萌发时期。第一,周代广泛用《诗》为缘事诗学萌发提供了土壤。在缘事献《诗》、赋《诗》、教《诗》和作诗的诗学传统影响下,在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之时,“知人论世”说诞生了。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孟子.孟子[M].刘财元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257.孟子将《诗》、《书》所云之事、所发之情系于其人其事之上,为缘事诗学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汉代普遍的注《诗》活动以及赋予乐府诗的创作活动为缘事诗学萌发提供了契机。汉代齐、鲁、韩、毛四家注《诗》多缘事明诗,以事系诗。陈维昭指出:“《毛诗小序》提供了这种‘本事注经’的典型范例。”②陈维昭.“自传说”与本事注经模式[J].红楼梦学刊,2003,(4).在汉赋和乐府诗的创作活动影响下,班固继承刘歆思想,在《汉书·艺文志》中直接提出:“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③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3:777.汉代缘事诗学虽还处于萌发阶段,但缘事诗学观念已深入人心,它对乐府诗的收集与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缘事诗学的发展。自晋代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诗学命题以来,六朝诗歌多沉浸在“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之中,“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而诗教远矣。”④沈德潜.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6.在这期间虽然有刘勰、初唐四杰对空洞、浮华之情的激烈批判,但无所兴寄的萎靡诗风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这种现象经过杜甫实绩的创作直到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即由白居易、元稹发起的新乐府革新运动才有了较大改观。白居易、元稹等人主张恢复采诗夜诵制度,发扬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效法杜甫“即事名篇”、“因事立题”的创作要求,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到了光启二年(886年),孟棨《本事诗》的出现可谓是缘事诗学发展的里程碑。《四库全书总目》将“诗文评”分五类,其中“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⑤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1779.《本事诗》可谓是结绳记事的历史意识、孟子“知人论世”、汉代“以事系诗”诗学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四)缘事诗学的成熟。章学诚《文史通义》曰:“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⑥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43.诗话意为话诗即“论辞”和“论事”。欧阳修首开宋代“论诗及事”的诗话新形式,后司马光《温公续待话》、释文莹《玉壶诗话》等相为宗之。魏泰提出“诗者述事以寄情”(《临汉隐居诗话》)。王灼认为“古人因事作歌”(《碧鸡漫志》)。赵翼主张“因事起意”(《瓯北诗话》)。可以说,宋代以来“论诗及事”的诗话标志着缘事诗学开始趋向成熟。
(五)缘事诗学的反思。近代以来,在西方叙事观念的强烈冲击下,中国诗学出现了较大的焦虑与反思。不管是黄遵宪对“诗之外有事”的强调、王国维对“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的批判,还是胡适对中国人“只能做有断制、有剪裁的故事诗”的揭示乃至二十世纪20、30年代长篇叙事诗的鼓吹和中国有没有史诗的讨论,为中国缘事诗学反思提供了契机。然而在现代焦虑下反思的中国缘事诗学不仅没有带来自身的复兴,反而带来了更深的掩埋。
时至今日,不用说中国缘事诗学的一些衍生概念比如“正用事”、“反用事”、“借用事”、“泛用事”、“质用事”等我们不甚了解,就是缘事诗学的一些基本术语比如“用事”、“序事”、“事类”、“托事于物”、“缘事而发”我们也感到陌生了,更不用说中国缘事诗学的理论命题和诗学旨趣了。无疑这是缘事诗学的悲哀,也是现实诗学的遗憾。与中国缘情诗学以及西方叙事诗学比较来看,其实诗的发生观念既有“情志不通,始作诗”,也有“在事为诗”的观念;诗的发生起点既有“物感”和“情感”,也有“理感”和“事感”;诗创作既可采用“立象尽意”,也可运用“指事造形”;诗的意境既有“情景交融”,也有“事景相携”;诗言事的方式既有叙事,也有序事。⑦殷学明.序事与叙事——中西不同的话语修辞方式[J].文艺评论,2012,(9).我们将中国缘事诗学的历史和现实呈现出来,就是为中国诗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中国诗歌的多元欣赏与创作提供多种可能的努力。
二、缘事诗学的概念与构成
毋庸置疑,缘事诗学的核心概念是事。何谓“事”呢?《说文解字》曰:“事,职也。叓,古文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事,士也。职,记微也。”也许正基于事的语言构成性,孔子才有“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观念,章学诚才有“事见于言,言以为事”的界定。从分类来看,事有可述与不可述之分。文灿然于“可述之事”,诗默会于“不可述之事”,故文之词达,诗之词婉。叶燮《原诗》曰:“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①叶燮.霍松林校注·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0.从中国诗歌实际看,理是事理,情是事情,物是事物。《诗毛氏传疏》曰:“作诗者之意,先以托事于物,继乃比方于物”。②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室.历代诗话词话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135.《诗镜总论》云:“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③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5.“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有物、理、情,更有事。诗缘情滋养性情,诗缘事诗化记忆。
(一)就诗与事的关系看,诗外有事,诗内亦有事,诗是作为事件存在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歌是由于诗外有事;诗歌之所以有历史感和真实感是由于诗内有事。从诗之外来看,事主要是指促进、推动诗发生、发展的事件。即“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改旧时之俗,故依准旧法,而作诗戒之。”“文因乎事,事万变而文亦万变,事不变而文亦不变。”④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615~616.从诗外有事重新审视诗的话,孟子感叹“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明代俞彦感慨“诗亡然后词作”,当下“文学死了”就不足为怪了。诗外有事是外部事件使然,“知人论世”为其显著代表;诗内有事是内部事件造成,“论诗及辞”为其根本代表。具体来说,指事字和响字以及用事等缘事诗法是诗内有事的主要构建者。
第一,托事于字。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说:“彼其造字之始,本无精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强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⑤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A].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6.《说文解字》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汉字尤其是指事字善于将事融入视而可识字体之中,故钟嵘《诗品序》感慨“众作之有滋味者”“岂不以指事造形”。古诗重炼字,大概就是由于字中有事、有情、有意蕴。诗内有事则主要指字中有事,其方法就是托事于字。譬如“、、”是书契文字代结绳记事。(上)和(下)的构字是一种标示,更是一种行为事态。刘若愚就认为:“人们都不会认为中国诗歌中的汉字形体不会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正如芬诺洛萨所说的那样,一行用汉字写成的诗句,不仅只是像银幕上映出的一幕幕美丽动人的情景,而且也是感受与声音在更高度、更复杂层次上的有机展现。”⑥刘若愚.中国诗学[M].赵帆声,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21.
第二,响字造事。何谓响字?宋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曰:“诗每句中须有一两字响,响字乃妙指。如子美‘身轻一鸟过’、‘飞燕受风斜’,‘过’字、‘受’字皆一句响字也。”⑦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8.响字一般是由读音响亮、形象鲜明的动词构成。由于动作是事的显现者,那么诗内的响字也就构成了诗歌内部的事。以《弹歌》为例,这首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仅八个字,就有四个动作。叙述了制造弹弓和逐射猎物两件事,分别通过“断”和“续”、“飞”和“逐”四个响字来完成。王国维一语道破天机:“‘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⑧王国维.靳德俊笺证.人间词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8.
第三,诗法融事。中国古代有用事、序事、比事、事对等丰富的有关事之诗法。这种类诗法对诗内有事具有重要意义。以用事为例,杨载《诗法家数》曰:“用事:陈古讽今,因彼证此,不可著迹,只使影子可也。”①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725.比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是王勃据冯唐、李广之事以类怀才不遇之义。用事不仅能援古证今,而且还能状溢目前,让人味之无极。周紫芝曰:“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杜少陵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暗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②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346.
(二)就诗学与事的关系看,诗学内外也都有事。一方面,诗学自身构成事件推动诗学发展。譬如《本事诗》之于《续本事诗》的生成。另一方面,外部事件影响诗学发展。譬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提出“唐以诗赋取士,故诗学之盛,莫过于唐。”中国缘事诗学诸如《本事诗》、《本事词》以及各种“论诗及事”的诗话主要就是为了探寻诗歌内外之事以保存诗的历史记忆的,其内在的构成也与事紧密相关即缘事发生、缘事通变、缘事诗法、缘事诗体和缘事诗评五论的基本构成。
1.缘事发生论主要发掘中国古代缘事观念与诗歌产生的关系,从而丰富人们对诗歌发生的理解。“缘事而发”的诗学命题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发展刘歆的思想形成的,后经孟棨《本事诗》“触事兴咏”、白居易《与元九书》“歌诗合为事而作”、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缘事以审情”等人积极倡导下走向成熟的。诗缘事而发才更真实、更感人。缘事发生论是“诗外有事”的扩展。
2.缘事通变论主要围绕着事发掘中国古代诗学对诗歌发展规律的认识。《周易》云:“通变之谓事”。“通变”本为哲学术语,后被刘勰转化为诗学术语。将通变解释为“通变之谓事”更易于理解诗以及诗学的发展规律与流变模式而不至于僵化诗学。不管是从传统历事性观念,还是现代互事观念来看,“通变之谓事”都是诗歌以及诗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缘事通变论是“诗在事中建立”的深化。
3.缘事诗法论主要发掘用事、事对、序事等有关事的诗法。用事又称使事,多陈古讽今。事对是用事的延伸,刘勰《文心雕龙》曰:“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③刘勰.文心雕龙[M].郭晋稀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4:452.,“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是也。序事与叙事不同,叙事是事在时间中展开,序事则是在空间(物与景)中铺排。《史记》首创“寓论断于序事”,这种史学言事方式后被诗学所接受。
4.缘事诗体论主要围绕事对古代诗歌进行文本细读,揭示出中国诗歌形态和类型,为中国诗歌阐释提供理论支持。其类型可分为景中有事、物中蕴事、事中生事、情中藏事、理中有事等。譬如景中有事,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是也;物中蕴事,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是也;事中生事,卢纶《塞下曲》是也。中国叙事诗虽不发达,但序事诗却应有尽有。缘事诗体论是“诗内有事”的展开。
5.缘事诗评论主要探讨缘事诗评的历史和价值。追古溯源,缘事诗评萌芽于汉代“以事系诗”的四家诗,滋养于魏晋“属词比事”的品评之风,成形于唐代“触事兴咏”的《本事诗》,成熟于宋代“论诗及事”的诗话。本研究既益于全面理解中国诗评传统,也益于当代诗歌评论。
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从发生论、通变论、诗体论、诗法论和诗评论等五个方面重构中国缘事诗学实际上是在进行本质主义的建构,这是制造现代神话。然而在我看来,反本质主义未免在中国太“先进”了。其实所谓中国现代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西化的诗学,中国本土诗学并没有全面走向现代。因此,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本土诗学,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本土诗学的建设。中国应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缘事诗学从中国诗学的隐体系中呈现出来是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推动,而不是什么主义的逼迫。
三、缘事诗学的价值与意义
缘事诗学有广、狭之分。广义缘事诗学是指基于人类历事性存在实际而生成的一种历史文化诗学,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记忆、文化记忆与人类生存经验、生命体验的基本规定,进而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各种生产的原则与方法。狭义缘事诗学就是围绕着“事”以诗为对象而生成的一种诗歌理论,其目的是探讨在诗歌叙事的同时揭示诗歌创作及其历史运作的基本机制与内在规律。与之相应,其价值意义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广义的文化生存意义和狭义的诗学建构意义。
(一)文化生存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既有伟大性,又有劣根性。所谓伟大主要指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坚实的凝聚力;所谓劣根主要指中国文化难得糊涂、明哲保身的油滑和冷漠,缺乏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难得糊涂、明哲保身既是一种生存策略,同时也是一种处事态度,“抑事扬情”是它的基本标示。“抑事”主要表现为中国人对事不穷究,缺乏事的准确性、真理性追求;“扬情”主要表现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教育等文化形态多以情志为本。这种文化体制好处自当不用多言,其坏处则在于感情用事。“其父攘羊,子为父隐”,亲情在,公德何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私情在,公平何在?“指鹿为马”,威严在,事实何在?“师命难违”,师情在,真理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有其历史的土壤。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在“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八股文字狱”等文化高压下,对事实自然就会冷漠起来,渐渐地也就养成了难得糊涂、明哲保身的生存态度。在中国,事是“事情”,懂得情才能办成事,否则就会处处碰壁。文化的现实性时时确证着事情的“真理性”,从而将其世代传承着。然而事不以事实为依据是危险的,中华民族的一些灾难多源于此。
毋庸置疑,中国人尤其是史学家也有刚正不阿,实事求是的一面,但整体而言,中国人的实事求是多被感情用事所淹没。西方强调事实真理,追求美和真统一;中国则强调感情,追求美和善合一。当三者发生冲突时,中国人一般取善舍真。善尽管是好的,但将善凌驾于真之上,对生存来说未必是好事。鲁迅先生批判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①鲁迅.论睁开了眼[A].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0.与当下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相反,中国人的文化生存精神并没有彻底改观。欺上瞒下、形式主义之风还有压倒实事求是的可能,这股不正之风如果不加彻底清除,就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缘事诗学发凡的深层意义就在于:颠覆传统文化中“瞒和骗”的生存观念,建构一种真正“实事求是”的生存理念。
(二)诗学建构意义。我们认为,发凡中国缘事诗学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传统,而且也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当代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建设。
第一,对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传统的意义。中国传统诗学往往言必称“诗缘情”,其实在“情志不通,始作诗”之外,还有“在事为诗”的观念。西汉韩婴较早发现古诗言事传统,提出“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命题,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学观点,唐代孟棨《本事诗》主张“触事兴咏”,白居易倡导“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魏泰标举“诗者述事以寄情”,清代叶燮《原诗》提出“理、事、情”的文论思想。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缘事诗学资源,发凡中国缘事诗学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和继承中国的诗学传统。
对中国古代诗歌阐释来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移情于物”“情景交融”等关涉情的评价,而对“托事于物”“事景相偕”等涉及事的评价也应关注。具体来说,诗可以通过对诗外之事的截取、置换、编码等符码化处理,使诗外之事转化为诗内之事,也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自足性的创造事件来构筑诗内之事。“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不仅是杜甫饱受磨难,暂得草堂闲适之事的符码化,更是诗性文本自设事件的隐喻化。清代诗评家黄生在《唐诗评三种》中评价杜甫的《晚出左掖》说:“凡诗写景为实,叙事述意为虚。……凡景中有事有意,名(半景)。”②黄生.何庆善点校.唐诗评三种[M].合肥:黄山书社,1995:240.杜甫的“晨钟云外湿”看似无事,但“事在其中”。叶燮解释说:“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止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①叶燮.霍松林校注.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1~32.
第二,对中国当代诗歌与现代诗学的意义。1998年孙文波在《山花》上发表组诗《母语》写道:“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写它们,/不过是觉得怪诞,可以吓人一跳。/现在,写了十年诗,我才明白,/谁也不会被我吓一跳,搞糟了的/不过是自己。现在,我终学会/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②孙文波.母语[J].山花,1998,(11).这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③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A].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9:6.中国缘事诗学就是让诗回到事物、回到事件化的生活中去感受、理解和创作诗歌。
对中国现代诗学建构来说,中国缘事诗学发凡的意义在于:其一,将历史所遗忘的缘事文献材料以论的方式纂论出来,从而为当下诗歌以及诗学建构提供某种理论支持。其二,基于事所提出的一些诗学观点对当下诗学走出困境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比如“缘事而发”至少对“诗到语言为止”的语言游戏说是一种矫正;“诗作为事件存在”至少能缓和文学终结论纷争;“诗是本事与反本事矛盾斗争的产物”至少为当下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斗争找到历史依据。另外,我们对事物、事情、事理的重新阐释以及提出序事和互事等概念对多角度建构中国诗学也是有帮助的。其三,“诗外有事,诗内有事”的提出也能将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的外部研究与中国当下“诗到语言为止”的内部研究落到实处,从而为中国诗学多元建构提供方法论支持。
总而言之,中国缘事诗学发凡的价值不仅在于钩沉发掘、分析梳理缘事诗学的体系结构、理论主张、观点命题,从而为当下诗歌创作提供理论的支持;而且更在于指向一种真正“实事求是”的文化生存理念,从而在历史记忆、文化记忆与人类生存经验、生命体验之间形成一种有别于缘情与叙事的精神生产新方式。
A study of Chinese event-related poetics
YlN Xue-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China)
Rich in poetic resources,China can be called a country of poetry.Event-related poems are a precious resource of Chinese poetry which emerged in the Han dynasty with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recording important events and developed in the Tang dynasty,and became m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Chinese poetics has often emphas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vent-related poems rather than their development.Thus,the development of event-related poetics relies on both its manifestation in the implicit system of Chinese poetics with multi-orientation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emancipation from the restraints of Western narratology with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poetics;development;event-related poetics
I22
A
1000-5110(2015)01-0143-06
[责任编辑: 杨育彬]
* [作者简介]殷学明,男,山东曲阜人,聊城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本事迁移理论与中国诗歌发展”(2012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