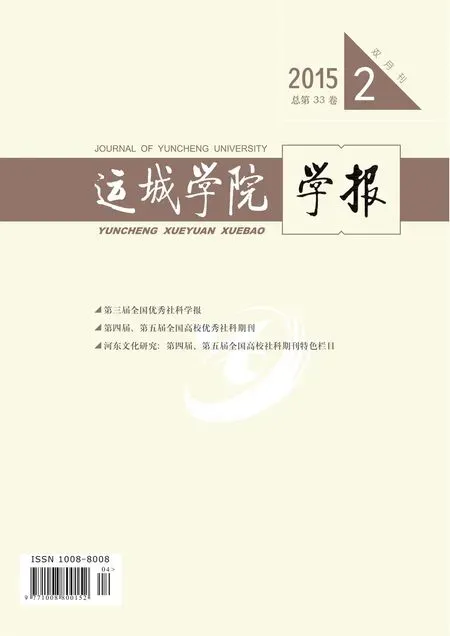论明清传奇双线结构的形成与渊源
杜一驰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论明清传奇双线结构的形成与渊源
杜一驰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纵观明清传奇戏曲的发展,双线结构始终是其典型的结构范式。梳理线性叙事在艺术长河中的发展流变,是理解传奇戏曲双线结构的重要思路。同时,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其形成的内在动因,亦有助于深入挖掘戏曲结构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双线结构;民族思维模式;史传叙事;说话与话本
传奇戏曲本身是一种长篇化的戏曲样式,与篇幅短小精悍的杂剧不同,它蕴含着更为丰富的艺术容量,展示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内容,因而要求构置曲折有致而又井然有序的故事情节。在传奇戏曲结构布局的问题上,文人曲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双线结构,通过两条线索交错展开的方式,使得戏曲结构所具有的叙述优势在明清传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极大的高扬。传奇戏曲之所以倾心于双线结构模式,既根基于二元对立的民族思维心理,又得益于史传文学与话本艺术的影响。
一、对立统一的民族思维模式
追根溯源,明清传奇的双线结构盖源于汉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万事万物皆由两个相互对立面推演而成。据《国语·周语上》记载,早在公元前780年,伯阳父对当时地震发生原因作说明时就透露出世界万物由阴阳运行而成的思想端倪。《周易·系辞上》进一步论述“一阴一阳谓之道”[1]79,阴阳两面既彼此分别又相互联结,既相互违异,又相随相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2]769男女的组合模式即“物生有两”的基本模式,男女结为夫妻则是配偶。曾国藩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有更明确阐述,他认为天地之术固然无独有对,但一生两的同时“两还归一”,“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两而至于一之说也。”[3]如此,万物才能循环流转,生生不息。由是观之,男女的组合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图示,这一图示反映到戏曲中便是生角与旦角的组合。任半塘《唐戏弄》说:“倘独单有女,成何社会?如专门用旦,又成何戏剧?”[4]781故生旦并起,实为情理所应有。因此戏剧中“旦之所至,生则随之;二者之搬演,固然可分,若大致则多相联系”[4]781。唐合生戏《义阳主》、歌舞戏《凤归云》、踏谣娘戏乃至道家俗情戏中,生旦配合皆为常态,到宋杂剧《越娘道人欢》、金院本《兰昌宫》生旦配合已成传统。宋元南曲戏文不仅在角色体制上讲求生旦并重,更形成了生旦俱全、各领一线的结构传统。影响所及,“历来传奇者,大都以一生一旦为全部之主”。[5]生旦贯穿始终的双线结构模式成为明清传奇最为常见的结构。明清传奇这种生旦组合模式不仅是对南戏双线结构传统的继承,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因子——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在戏曲文学上的投影。
孔尚任曾明确指出《桃花扇》传奇在人物设置的构思上包含着对《易》学阴阳对立思维的阐释,传达出对社会人生的抽象理解:“色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而两部之锱铢不爽。气者,兴亡之数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以奇偶计之,而两部之毫发无差。张道士,方外人也,总结兴亡之案;老赞礼,无名氏也,细参离合之场。明如鉴,平如衡,名目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6]全剧分五部:左右两部各8人,每部分正、间、合、润四色,人物关涉侯、李爱情纠葛;奇偶两部共12人,每部分中、戾、馀、煞四气,人物置身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之中;总部由张道士、老赞礼概括全剧,点名题旨。出于照应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主题的需要,孔尚任把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想内涵灌输于全剧的构思原则之中,故而,位于篇首的《桃花扇纲领》既起到分类罗列剧中人物的重要作用,又具有统领全剧整体结构的独特意义。
要之,物生有两,阴阳相和的辩证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着戏曲角色体制的变化与剧作人物的设置,还波及作者架构作品的中心原则。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指出“后期的南戏采取一种二元构成的手法”,“它基于阴阳二元对立的想法”[7]196。这种二元构成的手法运用两条线索展开的手段来处理复杂的情节内容,因而,它一经南曲戏文定型,便为其后鸿篇巨制的传奇戏曲所继承,又经文人之手改造,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日臻完美,成为传奇戏曲结构的典型特征。
二、史传文学的线性叙事与传统
明清传奇戏曲结构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云:“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8]陆景镐评周昂《玉环缘》传奇亦认为“其幽思则《离骚》也,其盛藻则《风诗》也,其装演如画,绝妙傀儡,则又《左氏》也。”(周昂《玉环缘小引》,《玉环缘》传奇卷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样式,传奇戏曲博采众长,甚至达到“无体不备”的境地。在对明清传奇众体兼备的文体认识基础上,文人曲家主要着眼于其诗歌传统与史传渊源。其“旨趣”、“幽思”、“盛藻”本于《诗经》《离骚》,即明清传奇在表情达意、填词制曲方面浸淫着古典诗歌浓厚的抒情传统;而“用笔行文”、“装潢”本于史传,则表明明清传奇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上更多地接续着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
(一)对线性叙事传统的继承
中国古代的文学叙事由历史叙事演化而来。在线性直观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历史叙事一般遵照事件发生的原本次序依次展开,形成线性叙述传统。编年体史书《春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历史事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9]。《左传》为春秋作注,同样如此。以空间为框架构筑成篇的国别体史书亦不例外,诸如《国语》《战国策》,表面上分述各国史实,块状结构是其据以联系的主导,实质上每一大块之内,仍是按时间次序将列国史事加以编订。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本位,叙事更灵活、方便,但叙事顺序仍是如“一条直线将各种时间依次串联”[10],《史记》就是按自然时序将人物的生平事迹结撰成篇,且以《高祖本纪》为例:
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五月,兵皆罢归家。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上述节选材料事系于时,以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为起点,直至刘邦崩于长乐宫中,尊为高皇帝,事件始末在时间流程中清晰展开,同“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11]的编年体史书如出一辙。这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叙述历史事件的线性方式成为史传文学叙事的典范。
中国古典戏曲与史传叙事传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它以时间为轴心结构剧情,呈现出鲜明的线性特征。廖奔、刘彦君认为:“传统戏曲的线性结构在宋元南戏里就已确立”[12],田仲一成进一步指出元杂剧亦是“直线型的构成”[7]196。明清传奇同样秉承了这一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衍生出丰富的变体。不妨随手拈取一篇传奇略加分析,如明代《鸣凤记》,纵观全剧,“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的斗争按时序次第展开,从第三出“夏公命将”拉开矛盾斗争的序幕到第六出夏言与严嵩“二相争朝”,从第五出杨继盛与严嵩党羽赵文华“忠臣异议”到第十四、十五出“灯前修本”“杨公劾奸”,从第二十三出邹应龙、林润“拜谒忠灵”到第二七、二八、二九出董传策、吴时来、张鹤楼众朝臣联名上本,直至第三十六出“邹孙准奏”严嵩倒台、第三十九出“林公理冤”,奸党的罪恶才被彻底清算,最后一出,忠臣受封,真正实现了“朝端纲纪清宁”[13]178,呈现出“四海平康,亿兆欢腾”[13]178的盛景。在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忠直义士戮力激浊扬清,为惩除奸佞、重整朝纲而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不得不指出,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对传奇历史剧的影响尤为深刻,有的剧作家甚至以史籍记载的历史事件为蓝本,以人物行动为主导,按事件的自然展开结构情节。如蒋世铨习惯于借鉴《史记》的历史编纂方式进行创作,《铅山县志》卷十五本传评其传奇剧作云:“写忠节事,运龙门纪传体于古乐府音节中,详明赅洽,仍自伸缩变化,则尤为独开生面,前无古人。”[14]
(二)史传文学的双线叙事
叙事的双线性同样可以追溯到史传文学。双线叙事模式因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很早就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在史传文学中,双线结构的运用已十分普遍,试以《左传》《史记》来说明。
较之微言大义、一字千金的春秋笔法,《左传》的文学叙事性有了质的提升,开始在文体结构上出现复线叙事。首篇《郑伯克段于鄢》记载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角逐较量,郑庄公君臣与武姜、共叔段各领一线,共同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文章伊始武姜“亟请于武公”欲立共叔段,占尽先机,继而“为之请制”、“请京”,咄咄逼人,待共叔段羽翼丰满,又图谋“西鄙北鄙”,收为己邑,“至于廪延”,最终“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发动叛乱;而郑庄公集团表面听之任之,实则欲擒故纵。一面是紧锣密鼓的实施行动,一面是不动声色的掌控全局,孰强孰弱,读者心中一目了然。两条线索平行并置,且每个集团的政治军事活动又分别在各自的叙述线索上自然展开。再看郑庄公集团内部,祭仲、公子吕、子封认为“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则请除之”、“厚将得众”,故而屡次进言,而庄公却云“子姑待之”“无庸”“厚将崩”[2]2-5,淡然应对。一面是臣子对国家安危心急如焚,一面是君主对不轨图谋了如指掌,一冷一热、一张一弛,构成戏剧性的场景。如此种种,难道不是与后世传奇戏曲运用双线交织对立来激化矛盾冲突、调节戏剧节奏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双线叙事的结构方式在《史记》中的运用更灵活、更常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谈及裁辨和遴选史料之难:“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多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15]当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牵涉到众多人物时,在每个人物传记中叙及同一事件就难免交叉重复,为避免叙事的浮滥烦琐,司马迁以“事在某传”、“事见某篇”、“语在某某传中”的方式互见详略,开创了为后来史家所广泛应用的“互见法”。如《萧相国世家》写到萧何向汉王推荐韩信,汉王任命韩信为大将军事,一笔带过,末赘“语在淮阴事中”一句,告诉读者详细的情节内容在《淮阴侯列传》中。鸿门宴一事在项羽、刘邦、樊哙、张良的传记中均有提及,以《项羽本纪》中最为完整,枝叶蔓延的史料则互见于它篇,此详彼略,互为补充,且不失历史真实。“互见法”既是司马迁处理史料所运用的特殊手段,又是其塑造人物、表达史观的重要方法,同时具有“连类对比,两相照应”的结构功能。其不仅用于史著,且经过发展而见诸后世文学。戏曲作品“花开两头,各表一枝”的结构方式与史传文学互见手法虽不尽相同,但“都显示出用文字处理复杂叙事,表现同时态事件中不同人物言行的一种智慧”。[16]
绾结而言,自历史纪事起,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形成了鲜明的线性叙述传统。从根本上讲,史传文学的线性特征表现的是纪事的线性,是在时间流变中事件发展的线性。史家思维的焦点与关注的重心落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上,即便是因人立传的纪传体史书,人物也必须以富有历史意味的事件为依托,形象的凸显总是建立在事件的基础上。这种以事为焦点、有着浓厚情节趣味的叙述方式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潜在的影响。及于明清传奇戏曲,“就催生了文人传奇以情节为中心的艺术构思方式”[17]。由此可见,对于史学家和文人曲家而言,复杂情节的安排与处理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共同课题。经过历代史学家坚持不懈的探索,他们在结构布局方面所做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单线推进式、双线并进式和网状交叉式叙事结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史传文学的叙事结构就有可能为传奇戏曲提供典范和样本。
三、说话伎艺与话本小说
宋元时期,由于商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套曲、说话、杂耍、傀儡以及皮影等民间杂伎日益繁盛,它们于勾栏瓦舍中遇合,彼此之间碰撞吸收,包容渗透,共同推动古典戏曲这一综合程度极高的艺术样式向前发展。
(一)说话伎艺与戏曲的传承关系
据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与吴自牧《梦梁录》载,宋代说话有“四家”之分,一般来讲,“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和声)。其中,小说专门讲说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故事;讲史则述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宋末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云:“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的越久长。”[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五代史平话》时说:“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浑词,以博笑噱。”[19]由此可知,虽然当时的小说和讲史略显粗糙,但皆为叙事性较强的艺术,并且话本的作者和说话艺人已经注意到情节内容的渲染和安排以及叙事节奏的控制和调整。为了吸引更多听众,说话艺人往往以敷演的口吻把一个完整故事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通过增饰、科浑等手段延缓叙事时间,从而扩充故事容量。同样地,戏曲故事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长度,并能于舞台上演出相当长的时间,如若情节内容太少,则需运用“巧”、“神”等特殊手段凑足戏份。通常认为,说话艺术的繁荣极大程度上促进着戏曲叙事趣味的增长,“正是在宋代‘说话’兴盛后,从白话小说中移植了叙事,使叙事成为小说与戏曲的共同点。”[20]说话和戏曲两种伎艺表面上分属不同的艺术范畴,实质上却有着难以言说的血肉联系。况且,早期戏曲所借助的话本故事并非原始意义上的素材,而是蕴含一定叙事思维,具有初步定型的结构形式的题材。因此,说话伎艺的传统形式也可能对戏曲的话语形态、叙述方式乃至结构体制有所启发。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论及小说戏曲之关系时说,中国古典戏曲从“托故事以讽实事”“以所含之意为主”的宋代滑稽戏形态发展演变为“演实事之戏”的元杂剧形态,“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这里的“小说”包含多种文体细目,主要是指“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的宋代说话艺术,尤其是小说、讲史两家,与“但托故事”的滑稽戏迥异,以演述故事为主,“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也。”[21]就说话与戏曲结构上的关系,王国维略有提及,并未深入展开。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了说话伎艺与话本小说在古典戏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除了对题材的袭用,语言艺术的吸收以及“使砌”伎艺的继承,就叙事能力而言,戏曲的曲词和科白保留了部分话本小说的叙事因子,就表演形式来看,戏曲中的上下场诗,题目正名,角色上场时的言说身世及下场道白与话本小说的首尾体制,正文开头的信息陈述及终场套语颇为相似。古典戏曲“无所不知的叙述角度和有头有尾的线型结构”[22],恐怕也是从话本处学来的。
(二)对话本小说双线叙事的继承与改造
说话伎艺是诉诸听觉的、及时性的表演艺术,这自然要求说话艺人把故事讲述得清楚条理,易于接受。由于讲唱的内容转瞬即逝,说话艺人一般不会打乱故事的先后顺序,通常按照事件发生的原本次序将整个故事不蔓不枝地讲述出来,形成一种以顺时叙述为主的线性传统。话本小说由说话伎艺演变而来,其叙述线索大致也是如此。随着文人的不断参与,话本小说逐步摆脱口头文学的属性,进一步规范,成为供人阅读的案头文学,其故事情节也更加纷繁复杂,曲折紧张。由于凌濛初、睡乡居士等人提倡从世俗生活、平凡故事中挖掘小说之奇,话本小说确立了以“耳目前之怪怪奇奇”[23]741为表现对象,以“无奇之所以为奇”[23]为审美追求的艺术传统。(当然,对“耳目之内”“日用起居”[24]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否认“耳目之外”“牛鬼蛇神”[23]741的故事,“三言”“二拍”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专图鬼魅的怪诞之事。)较之于“牛鬼蛇神”之类的荒诞故事,“耳目之内”“闾巷新事”[23]741的题材本身并不具备较强的故事性和离奇性。因此,这类话本小说就必须另辟蹊径,通过精心结撰的故事情节,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话本小说家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给戏曲艺术,尤其是长篇化的传奇戏曲很大的影响。
在情节安排与结构布局上,一部分话本小说突破了单线结构模式,两条甚至多条情节线索同时展开。叙述者“在讲述一系列共时而异地的故事时,尤其在讲述两位主角离散而破镜重圆的故事时,经常要按下一端,待叙完一端,再接着叙述另一端,”以“话分两头”的方式“将自然的历时顺序调节为共时顺序”[25],构成并置空间。诸如“三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临安里钱婆留发记》《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二拍”中《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如《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故夫》,原礼部尚书之子王景隆与京城名妓玉堂春相恋,鸨母把王景隆讨债得来的三万两银账哄骗到手后,将王景隆驱散,二人分离之后,王景隆返回金陵勤学苦读、应试做官;玉堂春被鸨母设计卖于山西商贩沈洪,又遭沈妻皮氏陷害入狱,历经磨难。最终,出任山西巡按的王景隆查明真相,为玉堂春雪冤。全剧采用“话分两头”“却说”“且说”等叙述套语把多个叙事单元连缀起来,实现了王景隆中举为官和玉堂春落难辗转两条情节线索之间的自由切换,从而使全剧形成一个线索清晰而又转接自然的叙述整体。男女主人公因迫害而被迫分离,经周折而破镜重圆,他们处于隔绝状态时故事情节的进展与很多古典长篇戏曲的戏路颇为相似。诸如《白兔记》,刘知远从军远行,发迹变泰;而李三娘却遭兄嫂迫害,日间汲水,夜里推磨,于苦难中产下咬脐郎;再如《琵琶记》,蔡伯喈进京求取功名,一举高中,娶宰相之女;赵五娘在家中苦咽糟糠,剪发埋葬双亲,可谓贫富悬殊,悲喜对照。在明清传奇戏曲中,最早成熟的一生一旦式双线结构,生旦能各领一条叙事线索,构置同一时间、不同情境下对应性的戏剧场面,皆是由于生旦双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处理,这种在共时态中呈现多个事件的独特技法,“是在中国历史散文叙事基础上的一种创造,是由说话艺术而产生的一种叙事技巧”。[26]
此外,还必须提及的是,明清传奇向话本小说取材的现象屡见不鲜。据统计,苏州派剧作家的传奇戏曲由“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改编而来的,达20余种,李玉的代表作“一人永占”,其中两部就得益于话本影响,《人兽关》取材于《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占花魁》取材于《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朱素成《十五贯》(本事源于宋人话本《错斩崔宁》)据《警世恒言》卷二十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李渔的《笠翁十种曲》立意新颖,布局奇巧,情节内容和结构安排均不落俗套,其中《奈何天》《比目鱼》《巧团圆》等剧目即取材于他自己创作的话本小说。在这一过程中,话本小说的叙述思维、结构形态也于无形中融入传奇戏曲。只不过,文人曲家往往于原本故事情节上增设一条武戏线索,与生旦爱情故事遥相呼应,武戏内容往往造成生旦分离,而战争胜利、叛乱平定也为生旦的遇合、团圆埋下伏笔。《占花魁》以靖康之难为故事背景,以家国兴亡为另一条叙事线索;《奈何天》中秦经略剿寇与阙忠守边等故事情节,亦成为一条独立的武戏情节线。如此种种,皆证实了明清传奇戏曲在继承话本小说双线结构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地创造与发展。
绾而言之,双线结构伴随明清传奇戏曲而始终,成就非凡,影响深远。而这一结构模式的形成与阴阳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史传文学的线性叙事以及说话伎艺对戏曲艺术的影响息息相关。
[1]周易[M].靳极苍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2]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李梦生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3]郭超.曾国藩全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4]任半塘.唐戏弄[M].北京: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
[5]王季烈.蟥庐曲谈·论作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6]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7]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8]孔尚任.桃花扇小引[A].秦学人,侯作卿.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9]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冀运鲁.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11.
[11]刘知几.史通[M].曹聚仁校注.上海:梁溪图书馆,1926.
[12]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13]毛晋.六十种曲·第二册·鸣凤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铅山县志·卷十五·蒋世铨传[A].上饶师专中文系历代作家研究室编.蒋士铨研究资料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15]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7]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8]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0]丁芳.中国古典长篇戏曲中的双线结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2]马俊山.论中国戏曲无限时空观的形成于戏曲文学的长篇化[A].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C].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凌濛初.拍案惊奇[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4]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A].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5]李桂奎.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6]朱水涌.历史传奇:史传传统与史诗模式[A].厦门大学中文系编.文艺学:前瞻性建构[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咸增强】
I207.3
A
1008-8008(2015)02-0009-05
2014-12-26
杜一驰(1991-),女,山西晋中人,集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