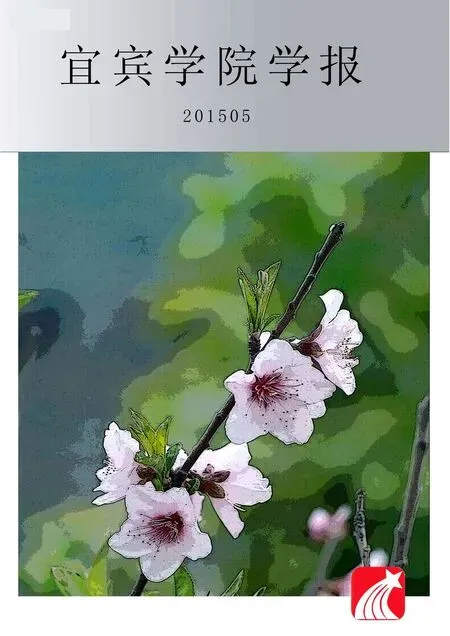阎连科小说中疾病的社会现实隐喻——以《日光流年》与《受活》为例
万良慧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亚·蒲柏说:“疾病是一种早期的老龄。它交给我们现实状态中的脆弱,同时启发我们思考未来,可以说是胜过一千卷哲学和神学家的著作。”[1]57作家阎连科就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多年来被疾病缠绕)融入到作品中,多部文学作品都对疾病进行了书写,使个体疾病体验得到表现。例如,他于199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就是以怪异疾病为题材的,随后又创作的《受活》对各式各样的残疾人进行叙述,《丁庄梦》又关注了艾滋病患者。纵观阎连科的十几年创作可以得知,疾病几乎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对象。
《说文解字》中“病”的本义是“病,疾加也,从疒,丙声”;而对“疾”的解释又是“疾,病也,从疒,矢声”。可见,“疾”“病”本是一个意思,“疾”为轻病,“病”为重疾。阎连科小说《日光流年》的喉堵症与《受活》中的残疾都是疾病的体现。“疾病一旦与文学挂钩,它便不再是疾病本身,隐喻的思维方式赋予了它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2]281它是反观与映射社会的一面镜子,具有深刻的社会隐喻作用。疾病只是作者所构建的一种独特书写方式,是作者以他者的目光对残病进行阐述,用疾病隐喻社会及文化给人带来的灾难,直接将矛头指向社会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疾病”只属于作品的表面现象,而疾病背后则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所在,隐藏着他对乡村社会人情人性的关怀与反思,隐含着他对现代化进程权力进行的质疑,同时也是对农民苦难的书写,寄予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一 寄予作者对民间苦难的表达
“残病是随着生命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生命的非正常状态,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使生命加速走向终点的过程。”[2]1疾病给人的身体与心灵带来不同程度的疼痛、作者以疾病为叙述点,将身体的疾病与民间苦难相联系,使民间苦难得以呈现。例如《日光流年》中发病的疼痛、割肉的疼痛,“卖肉”所带来的精神与身体的疼痛的;《受活》中的绝术团用身体展现自己的价值,这无疑加重了作者对苦难叙事的描述。
贝克尔说:“死的观念和恐惧,比任何事物都更剧烈地折磨着人这种好动物。死是人各种活动的主要动力,而这些活动多半是为逃避死的宿命,否认它是人的最终命运,以此战胜死亡。”[3]1在《日光流年》中,喉堵症如同梦魇一般缠绕着三姓村人。逃离死亡、能活过四十成为他们一代代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因此,他们用异于常人的精神与意志为这个目标努力着,但在追逐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姓村人分别在四任村长,即杜拐子、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的带领下与死亡抗争。杜拐子企图用生孩子的办法使三姓村得以延续,但结果产下许多残疾孩子,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解决长寿的根本途径。司马笑笑任村长时,他从路过的长胡子老头身上得到启发,试图用吃油菜的方法得以长寿。而在自然灾害面前,他做出了舍弃粮食、保护油菜的措施,最终在饥荒时期发生人吃人的惨状,司马笑笑也舍身成为乌鸦的食物,试图帮村民渡过灾难。蓝百岁任村长时,他认为土地是短寿的原因,于是发动村民夜以继日翻土地,导致村民累死。为了获得卢主任的帮助,他甚至牺牲司马桃花与未出嫁的蓝四十的贞洁。土地最终得以翻新,但是三姓村人的寿命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变,仍不断有人死去。第四任村长司马蓝的修渠引水行动更是付出惨重代价。如书中写道:“先后直接因修渠死人(不包括喉堵症死者)18个,断臂少指类的伤残21人,凡参加过修灵隐者,无不流血或者骨碎。为修建灵隐渠凑资,三姓村人共去教火院卖人皮197次,907平方寸,直接因卖人皮死去6人。女人到九都做人肉营生30余人次。最困难时,卖尽村中棺材和树木,卖尽女儿陪嫁和小伙子的迎娶家当,连村里的猪、鸡、羊都一头一只不剩,仅余下一对老牛做耕地之用。”[4]85工程历时 16年,自己的弟弟也在修渠过程中死去。同时,初恋情人蓝四十因“卖肉”染上性病死去,随后,得了喉堵症的司马蓝依偎在蓝四十身边随她而去。而此时,费尽力气修成的渠引来的却是充满恶臭味的污水,三姓村长寿的梦想再次破灭。从文本可以得知,三姓村人求生的过程就是一个历经苦难的过程。
《受活》中由残疾人组成的受活庄本是一个遗世独立、鲜为人知的村落。在受活庄里,身体的残疾并没有给受活人带来太多精神与肉体的痛苦,相反,天生的残疾还使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本领,让他们有机会参加绝术团的演出而生存着。他们过着和谐相处、丰衣足食的生活。而这简单而知足的生活,却因茅枝婆想使受活乡成为双槐县的管辖地而打破了。茅枝婆带领受活庄的人入社,随后,他们便开始了与外界圆全人打交道的历史。但在与圆全人交际的过程中,他们不断遭受着圆全人对其的凌辱与欺骗。短暂的天堂日子之后,受活人经历了铁灾与大劫年。粮食被外界的圆全人抢走,受活人深受饥荒的苦难,随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外界打破了受活庄的宁静,之后茅枝婆为退社做出种种努力,最后以参加绝术团为条件换取受活庄脱离双槐县的管辖以获取自由。
茅枝婆带受活庄入社及退社之间的经历就是一个历经苦难的过程,不仅她自身遭受着苦难,受活庄人也遭受着。他们用身体展示着自己的残缺,成为圆全人赚钱的工具。最后辛苦所挣的钱也被圆全人变相地抢去,四个儒妮子也被羞辱,结局极为沉重。
纵观《日光流年》与《受活》可以得知,作者构建了残缺人在贫困乡村艰难生活的图景,他们遭受着残病带来的磨难同时,也经受着与天灾、与命运、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磨难,他们活在苦难之中,不得不以身体作为代价对命运进行抗争,可以说身体是他们向命运抗争的工具。同时,借助作者对其死亡进行的书写,更是将苦难推向了极致。例如,茅枝婆为摆脱管辖,组织受活人参加绝术团,以身体为代价阻在车前,险些被伤。司马笑笑以身体为诱饵成为乌鸦的食物,以期为三姓村人获得救命的食粮,都体现了农民用身体作为工具,对生活进行抗争的磨难。
二 寄予作者对人性的拷问
在苦难之中,尤其是在残病的折磨下,人性不同程度被扭曲着,这在《日光流年》中有较为深刻的体现。
首先,在权力与疾病面前,人的感情被淡化。喉堵症疾病的存在使三姓村人生活在死神的笼罩下。改变这种现状,追求长寿是三姓村人几代人的梦想。而拥有村长的位置,则意味着拥有权力,意味着能号召群众听从自己的命令,并实施措施完成带领全村人实现梦想的行动。
司马蓝在任村长时,充分利用了蓝四十对他的情感。司马蓝为了当上村长,便抛下了青梅竹马的恋人蓝四十娶了表妹杜竹翠。之后为筹集修渠的资金劝说蓝四十带领村里的寡妇去九都“卖肉”。眼看自己得的喉堵症日益严重,为了筹集自己换皮的费用,他便让女儿去给蓝四十下跪,使蓝四十又一次去九都“卖肉”,致使蓝四十染上性病,并在孤独中死去。最后,司马蓝抱着死去的蓝四十永远没有醒过来。司马蓝是爱蓝四十的,他有着修渠引水、能让蓝四十活过四十的承诺,但是在权力与疾病面前,人的感情被利用了,也淡化了。
其次,传统伦理道德都不存在了。由于饥荒,三姓村人不得不节省食粮求生存,在村长司马笑笑的带领下,他们舍弃了村里十几个残疾的孩子,包括自家的三个儒孩子森、林、木。残疾的孩子被丢到僻远的谷底,成为了乌鸦啄食的对象。文本对这个情节的描写是极为惨烈的:“这儿的死尸横七竖八,每一具的身上都没有一片好肉。每一张脸上都破破烂烂,白骨像剥了皮的树枝裸露着。嘴和鼻子丢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衣服全部被乌鸦啄破了,肠子在肚外流着,心肺脾胃如坏核桃枣样在地上搁滚。破衣满天,腐臭满天,天空拥满了飞毛和叫声。每一具尸体的手里或手边都有一根枝条,粗的像胳膊,细的如手指。他们的身边,男娃尸或者女娃尸,都有几只甚或十几只和他们一样死腐的黑乌鸦。他们不是饿死的。他们是将饿死时,被饿疯了的鸦群啄死的。”[4]363随后,啄食被丢弃残疾孩子的乌鸦又成为三姓村人渡过饥荒所需的食粮,这是一种变相的人吃人的现象。更甚者,杜根与儿子煮食了残疾的女儿才得以活命。
在饥荒面前,他们可以将残疾的孩子丢弃以节省粮食,违背了中国传统的“虎毒不食子”的伦理,而变相人吃人的现象或直接人吃人的现象更是凸显了人在灾难面前的无奈及其人性的丧失。
再次,对民间愚昧、自私人性的揭示。最后,蓝四十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善良、美丽、无私的女性,可以为了恋人与全村人做出牺牲。当初为了司马蓝,为全村人而失贞于卢主任,使翻土的工程得以完成。后来在司马蓝的请求下,同时为了修渠的工程得以完成而去九都“卖肉”,在去之前,村里人对其将要做出的牺牲是极为感激的,但她从九都回来之后,却受到村里人的鄙视,被称为“肉王”,最后,蓝四十也在村民的遗忘中孤独死去。作者对村民前后截然不同态度的展现,是其对人性的拷问。尤其是当初被蓝四十保护的司马藤对其鄙视的态度,更是让人震惊。作者揭示了一个灰暗的人性图景。
此外,在《受活》,由于受活人自身的残疾,使他们在与圆全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处于劣势,他们被歧视,被欺辱。作者对圆全人持批判的态度,也是作者对人性的拷问。
三 质疑现代化进程及权力
第一,对现代化进程的质疑。
《受活》中的受活庄与《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本是相对独立的村落,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不同程度打上时代的烙印,深受现代化社会带来的苦难的影响,处于劣势地位。例如司马蓝带领村里的年轻人去卖皮,他们以牺牲身体的代价换来的不是急需的资金,而是外界文革时所盛行的红本子;又如修渠工程终于竣工,所引来的水已不是十几年前清澈的水,而是受到现代化城市污染恶臭的水,水里有“发黑的污草,泡涨的死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的死畜皮,白的脏毛皮,挤挤搡搡,推推涌涌在水面上又碰又撞。”[4]115-116这细致的描述均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的控诉。
而作者的这种控诉在《受活》中有更为深刻的体现,阎连科在一次访谈中说:“《受活》对我个人来说,意识表达了劳苦人和现实社会之间紧张的关系,二是表达了作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躁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如果说《日光流年》表达了生存的那种焦灼,那么《受活》则表达了历史和社会中人的焦灼和作者的焦灼。”[5]作品正是通过残疾人与圆全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展示劳苦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通过受活庄人与现代社会打交道所产生的悲惨生活经历及他们悲哀的内心展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无可安放及无可适从的内心。
在茅枝婆的带领下,受活庄加入了合作社,至此,受活庄孤立的状态被打破,开始了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受活人经历着外部世界现代化社会经历着的大炼钢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受活人始终处于被欺辱、被支配的不平衡地位。例如在大劫年,圆全人以拿着盖有公章的文件为名,就可以名正言顺抢受活人的粮食,使受活庄的许多人在大劫年中饿死。随着柳鹰雀的到来,受活庄人再次受到以柳鹰雀为代表的圆全人的引诱与欺辱,受活人成为柳鹰雀的挣钱工具,为他那荒诞的设想筹集巨款。同时,受活人被带到城市,成为圆全人观赏的对象,成为他们消遣与娱乐的工具。受活庄人最后所挣的钱也全被圆全人变相抢走。受活人在与圆全人打交道的全部过程充满欺凌与侮辱,而这欺凌与侮辱则凸显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是曲折而艰辛的。
在圆全人的眼中,受活人是残缺的,不仅身体残缺,甚至生活也必须是残缺的,他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比圆全人过得好。这是受活人被现代化社会所不容的写照,也是作者对贫困人民融入现代化社会的一种质疑。用受活人的遭遇控诉现代化进程的不健康发展给人带来的伤害和身心的摧残,用非正常人的角度看到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
第二,对权力的质疑。
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也有外来权力对三姓村人进行的压制。在《受活》中,受活人承受着外来权力给其带来的压力,例如在大炼钢时,铁具都被带走了;在大劫年时,粮食可以被抢走;在文革中,遭受批斗的磨难。之后受活人也是被柳县长所代表的权力所征服。他们可以在没有茅枝婆的主持下让受活庄的节日得以举行,可以不顾茅枝婆的阻挠去城里展示自己身体的残疾。在权力的压制下他们备受压抑,这是作者对权力的质疑。在《日光流年》中,为了留住卢主任帮三姓村翻土,蓝四十付出牺牲贞操的代价。
由此可观之,在权力的制压下,民间百姓是处于压抑的地位,他们用仅有的价值去换取他们认为最大的利益,绝术团中的受活人如此,三姓村人也是如此。
第三,也有对农村内部权力的质疑。
在《日光流年》中,于三姓村人而言,拥有村长的位置意味着在心理上有优越感和生活中享受优厚待遇。因此,三姓村人为了村长的位置钩心斗角。四位村长就是通过钩心斗角的方式取得村长的位置。他们有着为获得权力而在所不惜的决心和行动。司马蓝对权力的追逐更是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受活》中,茅枝婆的革命经历使她在受活庄拥有最高的权力,权力让她决定着整个受活庄人的命运。她的决定不具有民主性,只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受活人身上。因此,她决定着受活庄人入社的命运,也有着让受活庄人脱离双槐县的意志。她的决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她并没有让受活庄获得真正的受活。这是作者对农村内部权力的质疑。
四 赞美生命及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喉堵症在《日光流年》中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疾病,是作者假想的,“初时,他们和别的人世一样,人畜两盛,生寿也都六十岁,甚或八十岁,然而一代一代的出生与消亡,寿限却慢慢锐减下来。早些时候,村人多数都害黑牙病、关节炎,有的弯腰驼背,骨质疏松、肢体变形,甚至瘫痪在床。百余年来,三姓村人又大都死于喉堵症,人的寿限从六十岁减至五十岁,又从五十岁减至四十岁,终于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境地,到了满世界不和三姓村通婚往来的境地。”[4]11作为一种怪异的疾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派的调研人员面对此病也只能惊叹而来,摇头而去。为三姓村留下疑惑,并只有传统意义上活不过四十岁的观念。围绕着这一怪异的病症,三姓村人无从得知科学的治疗方式,而盲目地在四任村长的带领下分别用生孩子、吃油菜、深翻土地、修渠引水等原始的方式与死亡进行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看不到他们的颓废与低沉,更多的是他们对生命的热爱,表现出巨大的生存勇气。这是作者对三姓村人追求生命的赞颂,正如阎连科在《关于〈日光流年〉的对话》中说:“杜拐子临死前对大家说,等我咽气后,让那些孩娃都来守棺,让他们知道死没什么可怕的,人死了就是没气了。这或许是一种豁达,但绝不是无奈的顺从,在生死循环过程中,在知道自己活不到40岁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如种油菜、换地、修渠引水等,都是对死亡的战斗抗拒和奋争。他们这战斗、抗拒、奋争的过程是失败的,而精神是胜利的”[6]。
此外,关于《受活》中受活人对身体的展示,一方面可以说是对尊严的践踏,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身体所具有价值的充分利用。面对身体的残缺,受活人没有为此低沉,尤其在经历圆全人的洗劫之后,他们没有丢弃对生活的希望。槐花是受活人历经磨难后的代表,她生下的女娃也是受活人生命延续的象征。尤其是最后对花嫂坡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不灭的生命希望。受活庄这个乌托邦会依旧存在。
结语
“当文学作品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的语境而处于其中的时候,肉体就会在社会文化的巨大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身体符号则往往成为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当社会文化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问题就会投射到身体上,其表现就是肉体的病态,这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复杂的诸种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2]42-43此时,疾病就指向社会制度,指向社会文化,指向人的精神困境和终极追求。阎连科疾病书写的背后隐含着作者的社会批判、无奈以及严肃的思考。疾病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作者的一种隐喻,即农村的苦难。同时,疾病意象传达出了人生命的悲剧意味,写出了乡村的苦难,在疾病面前农民的无能为力。而没有医者的孤立存在的状况更加剧了农民的苦难,使无力抗争的悲剧性更加浓重。作者来自农村,因此对农村苦难的了解更为深刻。贫困、愚昧、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在疾病面前显得更为脆弱,这是农村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阎连科以疾病为叙述点,使我们从中看到贫困乡村生活图景的同时,看到在疾病的折磨下人性不同程度上的扭曲,看到作者对现代化进程及对权力的质疑。在批判的同时,小说又寄予了作者对乡村苦难的同情,对《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生命追求的歌颂,对《受活》中受活人勤劳、淳朴的性格的赞扬。还寄予了作家的一定的理想,即重建乡村伦理道德的渴望,渴求伦理的回归。
作者对疾病隐喻的书写显示出作者对人存在的思考,对个人精神的关注及对人文关怀的呼唤。阎连科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发言,通过对疾病隐喻的阐释,表达其对社会文化的理解与忧虑,彰显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负荷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林石.疾病的隐喻[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2]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E·贝克尔.反抗死亡[M].林和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4]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5]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J].南方文坛,2004(3).
[6]阎连科,侯丽艳.关于《日光流年》的对话[J].小说评论,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