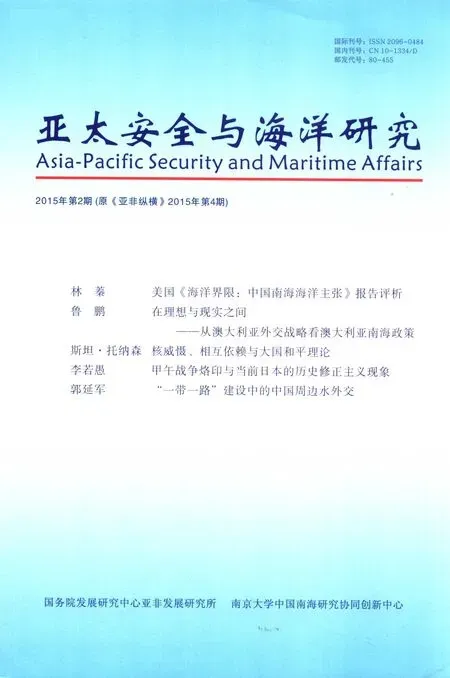核威慑、相互依赖与大国和平理论①
[挪威]斯坦·托纳森
核威慑、相互依赖与大国和平理论①
[挪威]斯坦·托纳森
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随着中国权力逐渐增长,中国和美国注定要发生冲突,一个针对中国的联盟也将形成。在参考了大量近期关于中美权力转移的著作之后,本文试图提出一个融合核威慑和相互依赖在内的大国和平理论。本文试图论证这样一种假设:只要中国和美国能够通过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彼此进行威慑,同时避免采取大幅削减对对方经济依赖的行为,那么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就会很小。如果关键的第三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继续受美国延伸核威慑的保护并通过贸易和跨国生产链与中国和美国进行经济上的融合,那么中美之间的和平将获得更多保障。只有当美国、中国和日本政府出于某种政治动机,采取从根本上减少对彼此的经济依赖这种措施时,它们才有可能陷入激烈的安全竞争之中,从而引发军备竞赛并产生巨大的战争风险。考虑到逐步升级风险因素的存在,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全面战争而且也适用于有限战争。
中国 美国 威慑 相互依赖 和平
2009年10月,在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研讨会上,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了他的大国关系悲剧论,他认为,随着中国权力逐渐增长,中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竞争对手,一个针对中国的均势联盟也将随之形成。这会导致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爆发激烈的安全竞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战争风险将笼罩世间。②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p.4;John J.Mear⁃sheimer,(2006)“China's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April2006,p.160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结合、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以及像日本这样的盟国。米尔斯海默认为,无论政治制度如何,中国必将寻求在东北亚的霸权,因为这是增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好方式①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pp.396-402.。如果中国的权力不断增长并逐渐追平美国的话,美国也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进一步崛起。因此,中国持续的相对崛起在必要条件下将会导致巨大的战争风险。而唯一能防止这种战争风险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放缓或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在人口老龄化、无法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西方遏制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遇挫。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很快就需要放弃其对华接触战略,阻止中国经济的崛起。此次演讲结束后,当他被问到“哪一个对他的理论挑战最大?是否是支持中国持续和平崛起并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水平的理论”时,他回答说:将核威慑理论与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合二为一的理论是对他理论的最大挑战。他当然不会相信这样一种理论会优于他的理论,但至少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的挑战。
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米尔斯海默否认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不对等的巨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在《化敌为友》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一书中的论点极为幼稚。②Charles A.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395.库普乾认为如果规范和规则可以推进东北亚新兴的安全共同体,互谅互让的精神也将孕育美中权力和平转移的乐观前景。相应地,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On China)③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Penguin,2011,p.523.一书中的假设同样幼稚可笑。基辛格认为,正如英国和美国之间曾经发生的和平权力转移一样,中美之间也存在建立“战略信任”的可能性。如果米尔斯海默是正确的,那么中美之间根本不会产生真正的信任。也许有人会提出制度和国际法可以帮助中美建立互信,双方接受共同的全球规则,在国际机构中共享权力。然而,这似乎都不是必然的现象。如果中国想修改全球规则和国际制度,希望人民币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希望增加它在全球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甚至创建自己的金融机构,并要求其他国家尊重它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那该怎么办呢?显然,美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美国想要维持全球秩序的现状。毫无疑问,信任和(或)共同的规范与制度可以巩固和平,但仅指望它们来实现和平似乎有些冒险。然而幸运的是,它们可能不是规避大国战争(great power war)风险的必要条件。米尔斯海默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防止战争爆发的主要手段可能是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虽然许多学者对此已分别做过讨论,但很少有人试图将它们结合在一个单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本文分析了威慑和相互依赖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引用了一些最新的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成果,以此来评估如果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共同作用的话能否阻止战争爆发。
一、核威慑本身是否足以预防战争
萨阿迪亚(Saadia M.Pekkanen)等人编著的《牛津亚洲国际关系手册》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总结了许多学者关于亚洲国际关系的当前思考和看法。其中第三十九章是袁敬东(Jingdong Yuan)关于核政治的分析。他注意到,亚洲是核武器密集程度最高的地区,拥有三个公认的核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一个宣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朝鲜)。一些人认为朝鲜已经具备了通过核武器打击韩国、日本或中国的能力。此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也被认为拥有“核能力”。①J.Yuan,Nuclear Politics in Asia,in Saadia M.Pekkanen,John Ravenhill,Rosemary Foot(Eds.),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505.袁敬东还提及肯尼思·华尔兹关于核武器稳定国际关系局势的观点,②Kenneth N.Waltz,(1981)“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More May Be the Better,”Adelphi Paper171,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但是他认为核战争的风险不仅会迫使各国采取谨慎的政策,也会鼓励本国做出挑衅行为,因为它期待对方比自己更加害怕核战争。他进一步指出,鉴于中国已于1992年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积极履行控制核出口的承诺,并在朝鲜无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及其盟友看来,中美相互威慑的主要挑战是中国不断增加的拒止能力,这使得人们对美国的力量投送能力和危机干预能力产生了质疑。出于对中国精确制导陆基导弹的担心,美国不愿将其航母部署在中国的打击范围内,这会降低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比如,美国保卫盟友的准备这方面的可信度。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能否继续支撑其在亚洲军事存在花销的能力。如果人们对美国延伸核威慑产生严重的怀疑,那么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将选择发展核武器。这也会引起中国强烈的反应,甚至很有可能引发多方参与的军备竞赛。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美国继续在亚洲部署陆基导弹防御系统的话,也会产生同样的风险,因为这会引起中国对其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担忧,从而促使它增加其核力量。美国的行为也会产生类似破坏地区稳定的后果。遗憾的是,袁敬东关于核政治的分析并没有对核威慑本身能确保中美和平共处提供很好的解释。
中国人的威慑思维也不能让人宽慰多少。2003年,中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阎学通试图回答为什么冷战结束后,在美苏均势体系已经让位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状况下,东亚国家间也没有发生任何战争这一现象。尽管中国是一个有核国家,能够抵御美国的全面进攻,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取代苏联成为均势的另一方。阎学通认为冷战后一种新的体系正在形成,他将其称之为“非平衡权力结构下的威慑”。他认为不存在中美权力平衡,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显然次于美国。而且,如果中美权力平衡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苏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均势没有阻止亚洲发生战争。问题在于,和平如何在非均势体系中形成呢?阎学通否定了是大国伙伴关系(如中俄)所导致的结果这一看法。他认为,合作伙伴协议也许能够推进签署国双方之间的关系,但它也会增加其他大国的焦虑。阎学通也否定了是日趋复杂的大国关系导致没有哪个国家敢采取威胁和平行动这一观点。他提出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复杂关系,但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相反,他提出了包括一个基本变量和两个因变量的理论。基本变量是非平衡权力结构下的核威慑。尽管中国是非对称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但它拥有足够的核能力来阻止美国对其进行直接攻击。冷战后东亚的权力结构从美苏均势体系变成非对称体系,但是这一地区的核威慑态势未曾改变。①J.Yuan,Nuclear Politics in Asia,in Saadia M.Pekkanen,John Ravenhill,Rosemary Foot(Eds.),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35.在这样的体系中,核威慑阻止了强国和弱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和战争。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制衡能力,弱国一方往往会避免卷入小国的战争,但是强国则没有这种考虑。结构性因素再加上核威慑,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和邻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阎学通也承认这一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当地区二等国家(中小国家)或与美国存在安全利益冲突时,战争在它们当中也没有发生。如果美国袭击朝鲜、缅甸或马来西亚,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不会选择干预,而且它们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或者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局部战争。阎学通还提出了另外两个阻止小型战争爆发的因变量:东盟的集体安全和韩国的和平统一政策。核威慑及非对称权力关系解释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和平,并阻止了日本发动针对朝鲜的战争,东盟的存在解释了其成员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以及美国自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再也没有军事干预过东南亚。最后,韩国的和平统一政策解释了朝韩及美朝之间的和平。没有韩国的支持,美国无法发动对朝鲜的进攻,因为朝鲜在军事上过于虚弱,根本无力取得对韩战争的胜利,因此如果韩国选择不以武力统一的话,朝鲜半岛将继续维持分裂状态。
考虑到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以及直到今天都经常在东亚和其他地区开战的经历,阎学通主要担忧的是美国威胁就毫不奇怪了。然而,他认为,只要本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自己的领土用作被美国攻击对象的话,美国就不会对该地区的任何国家发起攻击行动。诚然,当美国入侵一个国家时,它常常使用附近的基地作为入侵的跳板。这样以来,东盟的不干涉政策以及韩国的和平统一政策在维持地区和平上就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缅甸1997年需要通过加入东盟来防止美国入侵的可能性。
根据阎学通的分析,不平衡地区体系的主要风险就是中国的虚弱。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通过破坏地区和平的主要基础——中国的核威慑能力——这种方式来破坏地区和平。从阎学通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并没有做明确的说明,如果中国的相对权力大幅增长,并产生一个均势的地区体系,那么相互核威慑不仅会继续维持地区和平,而且还会帮助中国的伙伴国、邻国及友好国来防范美国的威胁。但问题是,如果中美之间的平衡倾斜到使美国的盟友感到不安全时会怎样?这种情形会超越阎学通的分析逻辑并导致战争风险增加,这正是权力转移理论所要表达的内容。
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在《中国的选择》 (The China Choice)①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一书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设想未来的中国将比现在更为强大。基于对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其在亚洲强大的军事存在的怀疑,怀特建议对东亚的安全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在增长,这对阎学通而言是福音,对怀特来说却是担忧。中国自1964年进行首次核实验以来,就不再受制于核讹诈。20世纪70年代,中国研发了既能打击苏联城市也能打击美国城市的战略导弹后,地区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中国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增长:苏联的威胁消失后,中国的兵力可以转移到沿海地区;此外,中国还专门拨款用于现代海军建设。如今中国拥有的不再是最小核威慑力量。通过将核武器对准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中国可以阻止任何常规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延伸核威慑的可信度也在下降。②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63-64,85.怀特建议美国放弃其主导地位,在大国协调的框架内与中国、日本、印度共享权力。他警告,如果美国的优势在大国协调确立前丧失,东亚将被分裂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阵营,处于典型的均势体系中,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既然美国已经允许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角色,那就没有可能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将它扫地出门。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经济反冲,而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华盛顿有三个选择:一是抵抗中国;二是从亚洲撤离;三是与中国共享权力。③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5-6,25-26,98-99.尽管最后一个选择意味着放弃优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亚洲撤退。美国可以在维持在亚洲强势存在的同时允许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海上,这意味着美国放弃制海权的同时也维持着阻止其他人获得制海权的能力。自1945年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控制着中国周边的海域,这一局势将不再继续。中国的海军建设及陆基导弹部署创造了一个“海上拒止”时代。海上强国能够击沉其他国家的船只却无法保护本国的船只。航空母舰再也无法进行力量投射,因为它们必须聚焦于针对自身的威胁。怀特预计日本会承担起自我防御的责任,获得核武器,并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印度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俄罗斯将继续专注于欧洲事务。①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5,72,86-88.美国会继续以大国身份存在于亚洲,但不再主导这一地区。
怀特的建议引发了诸多讨论,但他的权力共享模式想法与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②Layne,Christopher‘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1997.的建议一样都不会为华盛顿所考虑或接受。克里斯托弗·莱恩曾认为美国应该从亚洲大陆撤退,并放弃其离岸平衡的角色。③Layne,Christopher‘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1997,pp.5-51.如果美国由于战略或者预算限制的原因而被迫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那么毫无疑问它将采取渐进的措施,并用华丽的辞藻和新的联盟安排来掩盖这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已经承诺对亚太进行再平衡(或者向亚太“转身”),将其60%的海军兵力部署在那个战区里,这也获得了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的支持。五角大楼在2015年出台的新版《海军战略》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海军实力的上升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威胁。尽管怀特的建议没有被采用,但他关于美国的核威慑正在逐步失去可信度这一观点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
安德鲁·奥尼尔(Andrew O’Neil)在《亚洲、美国与延伸核威慑》(Asia,the US and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一书④Andrew O’Neil,Asia,the US and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Atomic Umbrella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London:Routledge,2013.中一反常态地声称核威慑在亚洲的重要性在逐渐增加。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反而成为了疑问,所以奥尼尔事实上证实而非驳斥了怀特的主张。奥尼尔向人们展示了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多次试图确证美国核威慑的可信性,而这种可信性对于它们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越来越重要,而不是越来越不重要。这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部分原因也在于朝鲜的核计划。冷战期间,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苏联或中国对美国盟友的攻击。因此,美国的亚洲盟国并没有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但现在,美国一直不愿意正式证实其核威慑的任何延伸,它的明确保护对象也只涵盖日本一个国家。韩国、澳大利亚、台湾地区、泰国、印尼和菲律宾都没有获得任何明确的核保护承诺。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遭遇攻击的话,美国是否会进行核反击?尽管奥尼尔也发现美国对韩国做出的延伸核威慑承诺已经愈加明显,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会阻止平壤采取战争水平之下的挑衅行动,①Andrew O’Neil,Asia,the US and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Atomic Umbrella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Routledge,2013,pp.4,68-69.这种挑衅行为总存在着引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奥尼尔发现,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相当矛盾,在公开场合下,日本一直坚持反核政策,但实际上在美国延伸核威慑的问题上,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加主张拥核。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顽固,违背美国要其谨慎行事的建议,可能与东京要求确保美国保卫日本防范来自中国的进攻有关。为了避免落到不得不威胁动用核武器的危险境地,美国可能不太愿意为其盟国出面进行干涉。美国为盟国进行干预的门槛因此而被提高了,这增加了发生有限战争的风险,而有限战争可能会逐步升级。
袁敬东、阎学通、怀特和奥尼尔的分析增加了大家的焦虑和不安。如果中美双方都期望对手先行让步,那么核威慑恐怕无法阻止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盟间的危机升级,而且也无法在第一时间阻止危机的出现。
那么,如果核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结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在他的《争夺霸权的较量》(A Contest for Supremacy)一书②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Norton,2011.中驳斥了核威慑加相互依赖就能够用来维持中美和平的可能性。尽管他承认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核战争的风险有助于降低冲突的可能性,但它们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趋势。他还认为冷战时期核威慑的经历并不能让人放心。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尽管得以避免,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核战争就“近在咫尺”。弗里德伯格承认核毁灭的幽灵使得中美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平息,甚至会刺激双方进行“军事竞争”。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会下降,这使得美国不太可能诉诸于核武器。弗里德伯格由此建议华盛顿专注于提升常规武器能力,并维持对世界海洋的控制权。③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Norton,2011,pp.38,56,278-279.
尽管弗里德伯格认为中美冲突无法避免,但是他的分析中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核威慑与经济相互依赖结合所产生的减震效应。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双方都维持经济开放和一体化政策,这是否会阻止彼此之间的竞争升级为公开的冲突?但是,现在提及康德或关于经济相互依赖本身能否阻止战争的探讨还为时尚早。历史已经证明它不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当国家领导人有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目标时,或者预期他们的国家会在经济竞争中输给潜在的敌对国时,他们也许会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危险行动。①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2,6,14;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2,7.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当国际体系中,既有经济相互依赖又存在核威慑时,可能的结论应该是国家领导人在担心核危机的同时也认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存在同样的担忧,那么他们将减少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担忧,并更愿意继续与潜在的敌对国进行贸易,即使当它们的权力增长了也是如此。这是否能解释中国和美国能够在当初的冷战同盟一去不复返,冲突和互疑时常发生,文化背景(更不用提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仍然能在经济上紧密结合在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和生产网络中?这些因素的存在增加了未来战争的人力、社会和经济成本。这是否意味着大国战争将得到避免,除非美国和(或)中国想背道而驰,决定减少彼此间的经济互动?
二、核威慑相伴下的相互依赖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发生于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系中,这一体系还包括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这或许是被提及最多的亚洲能够维持和平的原因。冲突的代价被认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尽管东亚的和平不是依靠战略信任、制度一体化或共同价值,但是,东亚依旧能够实现和平,这是因为东亚的领导人将经济发展置于了首要地位,他们意识到冲突的代价是极高的,并期望从开放的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兰普顿②David M.Lampton,Following the Leader:Ruling China,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pp.3,7,122,136.认为“全球相互依赖的概念”增进了和平,他还提出了“相互依赖理论”: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缓解了发生冲突的冲动。尽管相互依赖不会使战争永远消失,但至少它使战争变得更具毁灭性,因而提供了一种“可使与主要对手之间的冲突保持可控状态的动力”。如今,中国的外交决策层在相互依赖的现实和自信的民族主义冲动之间进行着艰难抉择的斗争。但是兰普顿并没有具体讨论相互依赖什么时候能阻止战争,什么时候又不能?柯庆生③Thomas 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 NY:W.W.Norton,2015,pp.41-46.则细致地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全球相互依赖与过去不同,并更有可能阻止战争。他提出,跨国生产链使得侵略国必须说服大量的外国投资者、关键零件供应商以及物流公司在入侵他国行为发生后继续与其做生意,可以想象这是何其艰难的一项任务。④关于跨国生产网络方面的专家分析,请参阅:John Ravenhill,“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in Pe⁃kkanen et 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2014,pp.348-368.因此,现在发动战争的动机比以前变少了。柯庆生还提出,尽管跨国生产和相互依赖不一定能保证战争不再爆发,但它仍然是促进和平的主要力量。①Thomas 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 NY:W.W.Norton,2015,p.46.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以及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事实证明了柯庆生关于在入侵他国领土后,重组经济是多么困难,代价多么高昂的观点;但这也表明有些政府更看重地缘政治因素,忽视战争的代价,愿意诉诸于武力(但不使用核武器)来对付一个次等的国家。
尽管怀特②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50-52,55,116.认为相互依赖限制了野心和竞争,但他也怀疑这种限制能否强大到使竞争压力烟消云散。他指出了一个心理学现象:大部分情况下,当权力和地位问题同时存在时,人们通常都会觉得将经济考虑置于首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所以当国际危机发生,选择必须做出的时候,人们“很难会优先考虑经济”。当双方都认为危机会对对方产生比己方更多危害的时候,它们会静观其变,等待对方退缩。由于全球经济的存在,没有哪个大国能在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同时独善其身,但是殊死竞争的态势有可能“在领导人和公众意识到经济后果之前”就已形成。竞争的不断加剧“可以首先侵蚀经济相互依赖,而不是经济相互依赖可以阻止危机升级”。怀特还指出,这肯定意味着相互依赖事实上可以阻止或延缓公开的冲突;只有在政府采取行动减少对对方的相互依赖之后,才能表明它们愿意冒战争之风险。
相反,陈思德(Steve Chan)在他的《持久的竞争》(Enduring Rivalries)一书③Steven Chan,Enduring Rivalries in the Asia-Pacif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中表现得相当乐观。他认为东亚的整体趋势是走向竞争缓和而非竞争激化。由于东亚国家已经将政策重点转向经济发展,领土争端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升级为大规模的冲突。这也创造了一个“限制国内冲突和竞争的协同效应”,联系变得多元化,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受益于稳定的国际政治局势。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它也有兴趣去维持地区稳定。但对美国来说,由于担心资源供应受到限制,美国在向盟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的问题上非常谨慎,这对地区关系两极化不利。陈思德的乐观想法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强调远程投送力量可以创造维持和平的动力。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多元主义推动了利益攸关者(那些受益于政治局势稳定及外交关系扩大的人)的发展,反过来,这些利益攸关方会自发地游说本国政府采取缓和竞争的政策。④Steven Chan,Enduring Rivalries in the Asia - Pacif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20.陈思德认为,大规模战争爆发或升级背后的一般模式都是,非对称关系中的小国做出挑衅行为,希望获得大的保护国的支持。而那些很少有希望获得别国支持,以及那些非常自信能获得盟国支持的国家,相较于那些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不会采取挑衅行动。①Steven Chan,Enduring Rivalries in the Asia-Pacif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08,114,186.鉴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东亚小国的挑衅行为不太可能会升级为大的冲突。朝鲜无法依仗中国的支持来对抗韩国;韩国、日本和菲律宾也受制于美国的“升级控制”(escalation control)机制。陈思德认为,从均势理论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实现更大的权力对等应该会促进国际局势稳定而非破坏稳定。这挑战了米尔斯海默的推论,但支持了阎学通的分析。陈思德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抑制美国独断的单边主义,从而稳定地区关系。而且,中国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就是引发一场昂贵的军事竞赛或仓促使用武力,从而迫使邻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②Steven Chan,Enduring Rivalries in the Asia-Pacif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82,102,104.尽管这看上去很合理,但中国最近几年的行为并不能为陈思德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支持。我们需要知道中国政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考虑危机升级的代价?是谁提出来的?在危机的哪一阶段会提出来?
根据陈思德的理论,东亚地区的人民和政府已经从集权专制国家转变为专注于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体。这意味着“最有力的防范冲突蔓延的防火墙”已经建立起来了。整个区域都转向“经济优先”的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并且“这种成功的政策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被模仿,并被复制”。但是当西方市场无力吸纳大量的亚洲商品时,它们的成功还能继续吗?陈思德最后补充道,当国家预计未来的经济合作会中断或受限时,它们很有可能会停 止合作,并诉诸于战争。③Steven Chan,Enduring Rivalries in the Asia-Pacif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35,140,147,149.
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的“贸易预期理论”④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该理论建立在“动态差异理论”⑤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基础之上。科普兰没有把核威慑纳入他的理论之中(他认为核威慑和传统的威慑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没有特别研究中美关系。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规模战争(major war)的全面理论,这一理论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既包含了自由主义,又强调了安全—经济联系。他的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历史案例的研究上,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科普兰将三种权力纳入到他的理论分析之中: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潜在权力”。潜在权力包括好几项内容,比如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年龄、国民教育程度、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经济发展前景。科普兰近期的著作只关注了潜在的经济前景。他的《大规模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jor War)①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以及《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②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论述了许多问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用来思考今天的中美关系:
大国间战争的风险在两极体系中比在多极体系中更高,这是因为多极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必须提防其他国家合伙起来反对它。③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16,240.这对东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只要以中-俄联盟为一方,以美-日-印联盟为另一方的两极体系不形成,东亚就会处于和平之中。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那样,第三方可能会在挑起两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④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443-444.因此要谨慎处理朝韩关系、大陆和台湾关系、中日争端和中菲争端。
国家领导人通常都是基于对现象的信念而采取行动,而非基于对现实的准确观察来行事。⑤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2;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17.对未来局势走向的信念在外交决策中非常重要,但问题在于谁也无法准确预知未来。
在两极体系中,认为自己正在衰落的国家比正在崛起的国家更容易挑起战争:崛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总是希望避免战争,因为它们可以等到将来拥有更大实力的时候再战。⑥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14,20.因此中美双方都在防止对方产生实力下降的担忧。那些认为自己正逐渐衰落(经济预期低迷)的军事大国尤其危险。⑦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5,13,22,237,241,244;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429.为此,中国要尽量避免与俄罗斯走得太近,同时也不要让美国感到它(美国)在衰落。
在走向战争还是维持和平的政府决策中,动态关系因素(如“潜在实力”或“贸易预期”)比静态因素(如实际贸易水平或政府在单元层次上的治理形式)更为重要。⑧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5-236,238,245;2015:12,14,27-50,435-436.当单元层次差异达到开始起作用的程度时,被入侵国的单元特性要比入侵国的单元特性更为重要:尽管自由主义者认为某些类型的政权要比另一些类型的政权更容易发动战争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是某些类型的政权要比其他类型的政权更容易受到攻击的观点则是正确的。①科普兰并没有用任何民主制度的内在品质去解释“民主和平”现象,而是用成熟的民主国家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来解释“民主和平”现象,所谓成熟的民主国家就是指那些在未来政治上依然民主、经济上依然开放的国家。参阅 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9,245-246;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433-434.为了避免成为攻击对象,国家如果做到行为可预测、政策透明、尊重国际法并开放贸易和投资,将会有所裨益。
在对贸易预期如何影响1790-1991年期间的战争决策的详细研究之后,科普兰对未来的前景非常乐观:只要美国愿意继续维持开放和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体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将长期以和平方式融入其中。至少在最近几十年内,中美两国国内乐观的经济预期将超过悲观的预期。”②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432,444.陈思德和科普兰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全球化持续成功的基础上。如果太平洋两岸的一边或两边经济预期不佳,那么单元层次上的经济优先政策将无法发挥缓和冲突的作用。陈思德证实了经济相互依赖在冲突中的减震效应有赖于经济开放和一体化政策。因此,在评估经济相互依赖是否能继续确保核大国之间的和平这种可能性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全球金融政治和全球发展趋势,以及北京、华盛顿、东京和其他东亚国家首都对经济的预期情况如何。
这里有必要提及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失衡:美国和中国对彼此的共同依赖》(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③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他讨论的中美危机不是军事冲突而是贸易战争(当然,贸易战也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罗奇用“相互依赖” (interdependence)来指代全球贸易体系和跨国生产网络,用“共同依赖”(codependency)来指代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他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是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经济体,而是将它看作东亚“大规模、一体化、泛区域出口机器的中心”,为欧洲和低储蓄率的美国提供廉价的商品。中美被捆绑在一个“共同依赖的网络”中。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美的经济融合使双方各取所需,对彼此都是有益的。但到了21世纪,中美关系“演变为不稳定的共同依赖”,④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p.3,140.贸易失衡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罗奇的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些风险的,他还呼吁中美经济关系重回平衡状态。中国建立了外向型经济,但是个人消费水平很低,外汇盈余也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这使得美国的利率长期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美国消费者也得以维持他们的过度消费:“美国的过度消费支撑了中国的不可持续发展,反之亦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意味着这一方法不再有效,两国对改革都有迫切的需求。罗奇认为中国更有可能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会降低存款利率,减少盈余,降低对以美元为基础的资产的需求。这将使低储蓄率的美国面临资金短缺,并导致它的利率飙升。随之而来的困难也会激发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罗奇的噩梦是美国利用贸易制裁来对抗中国,这将会是美国自1930年以来犯的最大错误。①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p.xi,xiv,130,192,196-200,247-249.相反,美国应该把中国发展中的市场看成是振兴美国出口的机遇。中国对进口货物的限制很少。美国快速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业务是可能的,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这将使世界贸易重回平衡时代,中美贸易战争也将得以避免。
为什么罗奇寄希望于中国而不是美国首先采取措施来平衡世界经济?中国政治体系的批评者们总是认为,让中国做出改变很难,习近平的“中国梦”必将失败。相反,罗奇批评美国的决策体系在阻止变革发生,主要原因不是预算限制或是国会内的政治僵局。他还批评美国的金融政策受到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绑架,而中国则是实用主义当道。罗奇认为,变革受阻的罪魁祸首就是教条主义者,也就是美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他对任何危机的反应都是降低美国的利率。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则高明得多,他总是能抓住时机创造更多的生产和出口。朱镕基的继任者温家宝知道这种方法不可持续,但是也没有对此做出多少改变。格里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沿着格林斯潘的足迹将美国引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罗奇还对两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进行了比较。他提出,中国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巨大,致力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而美国则是缺乏协调、各自为政,是在允许“创造性破坏”的哲学指导下运转。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前景非常悲观。他们指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同时也为中国2001年加入 WTO 铺平了道路。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一方面毫无建树,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大型的经济刺激计划,好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去投资一些几乎没有回报的项目,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债务问题。②Barry Naughton,'China and the two crises:From1997to2009,'in T.J.Pempel,and Keiihi Tsuneka⁃wa,eds,Two Crises,Different Outcomes,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110-134;Thomas 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 NY:W.W.Norton,2015,pp.242-245.相反,罗奇希望习近平能够彻底改革中国经济,并迫使美国紧随其后:“中国的再平衡应该被视为是美国的机会,是美国长期复苏的基础”。在罗奇看来,最的大风险在于,美国没有意识到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反而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从而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现在美国经济岌岌可危的程度并不亚于1929年,世界经济也同样如此。①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p.xiv,28,35,58-59,204,240-244.
贸易战的破坏性极大。当衰落的美国决定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崛起时,贸易战会引发中国的仇恨和攻击行为,米尔斯海默的预言也将成为现实。②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
三、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因素
黎安友(Andrew J.Nathan)和安德鲁·斯科贝尔(Andrew Scobell)在《中国寻求安全》(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一书③Andrew J.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中因将经济因素融合进安全为主导的系统分析中而受人关注。他们在书中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寻求安全的主导。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把区域霸权和全球大国地位看作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黎安友和斯科贝尔则对安全和霸权做出了区分:中国想要获得安全而不是成为全球大国。当中国说它想要和平的时候,其实际意思是它想要稳定,意味着它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④Andrew J.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28.虽然从利益到政策的因果机制可能会被错误信息、错误计算、价值承诺、制度缺陷或领导缺点等因素所扭曲,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最终还是由现实利益主导。他们认为中国会继续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推行维持现状的政策,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华盛顿失去了维持美国权力的经济基础,那么中国有可能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⑤Andrew J.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p.13,346,357.因此,最终拆散整个国际体系的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美国的衰落。他们认为这是主要的风险。如果“西方衰弱到形成一个权力真空”的程度,那么中国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海外基地,并在对外贸易中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美国必须做出决策,是否抵抗,什么时候抵抗,届时战争将一触即发。美国如果想要和平,那么它就应该维持现有的力量,并采取谨慎的外交政策。中国也会基于自身的安全诉求理性行事。⑥Andrew J.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p.xi,359.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不再依赖美国来发展经济,美国也获得了它认为足以赢得一场战争的军事实力,那么战争的风险将会增加。如果我们看到中美双方都有意去减少对彼此的经济相互依赖,这很有可能就是危机演变成战争的信号。
如果我们把黎安友和斯科贝尔的结论与罗奇的金融政治分析和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结合起来,那么结论就是,减少战争风险的关键在于重新平衡国际经济体系,也就是让大国之间保持彼此依赖状态。相互核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结合起来很有可能会维持全球和平,只要没有哪个大国乐见任何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急剧衰落。但是,如果核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单独使用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依赖于威慑的可信度,另外一个依赖于对互惠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中自由流动的预期。
以上引用的观点都属于结构性分析,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即无论中国谁当政,核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都能阻止战争或减低风险。换言之,美国(和日本)都认为没有哪届中国政府愿意发动战争,并承受全球经济衰退的代价。一些学者对结构性分析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应该关注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作用。在中美政治决策中,谁来制定谨慎的政策?是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吗?是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五角大楼还是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总理还是美国财长或是美联储主席?是跨国公司高管?还是媒体、智库以及意见领袖?但是无论怎样,所有的决定最终都要由最高领导人拍板,所以他们的能力、关注和动机都是很重要的,他们正式或非正式的智囊团也非常关键,这些都应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研究政府机构的四种方法,有些可以追溯到一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2014年的一战100周年纪念活动使得人们开始比较1914年的欧洲和2014年的亚洲。罗斯克兰斯和米勒(Rosecrance and Miller)的《下一次大战》(The Next Great War)一书①Richard N.Rosecrance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Next Great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 MA:MIT Press,2015.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他们的主要结论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仅仅是双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不仅在于“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还在于科西拉人袭击了科林斯人,所以斯巴达认为它必须援助它的盟友科林斯,这也使得雅典别无选择,只好援助它的盟国科西拉。②Graham A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in Rosecrance and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2015,pp.73-80;Christopher Coker,The Improbable War: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09.朝鲜很有可能把中国拖入对美国的战争之中,就像1950年那样。日本、台湾或是菲律宾也有可能把美国拖入到对中国的战争之中。最有可能引发与中国战争的方式就是通过一场包括一个或多个美国盟友的争端而引起的武装冲突。③Stephen A.Miller,‘Introduction:The Sarajevo Centenary—1914and the Rise of China,’in Rosecrance and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2015,p.xxi.
在罗斯克兰斯和米勒的书中,理查德·库伯(Richard N.Cooper)讨论了经济相互依赖和战争问题。①Richard N.Cooper,‘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in Richard N.Rosecrance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 MA:MIT Press,2015.他提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一战的爆发证明经济相互依赖无法保证和平。②Richard N.Cooper,‘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in Richard N.Rosecrance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 MA:MIT Press,2015,p.57.他还完善了诺曼·安吉尔在《大幻觉》一书中充满争议性的观点,即如若不是英德开展海军军备竞赛,战争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军备竞赛导致了相互摧毁性的对抗。在比较了欧洲列强在1914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后,库伯还简要分析了奥地利、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在1914年7月份到8月份的政治决策,他认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动员令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库伯强调致命的决策是由一小部分人做出的,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预见到战争的毁灭性:如果领导人能预知战争的实际损失,③实际上,德国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事先的确警告过德国皇帝: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最终将会使得所有大国精疲力竭(Coker2015:26),但是,作为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在1914年还是彻底被他的战争后勤计划所支配(Richard N.Cooper,‘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in Richard N.Rosecrance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 MA:MIT Press,2015,p.64.)。那么他们(即使是平民)毫无疑问也会采取行动尽力避免战争。④Richard N.Cooper,‘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in Richard N.Rosecrance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 MA:MIT Press,2015,p.69.这样的历史性错误很难在今天或是以后重复了。核武器的存在、一战和二战的惨痛经历、古巴导弹危机的末日惊险以及对各国(美、中、日、俄、印)常规武器能力的认知,使得今天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都会认识到全面战争将会导致相互确保摧毁的悲剧。因此,任何理智的领导人都不会做出故意挑起全面战争的行动。那么剩下的风险就是有的国家愿意赌一把,希望对方国在危机中让步,这样它就能成功挑衅并免于处罚,或是赢得一场有限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这样的例子,当时美国、苏联、中国(从1964年开始)都是亚洲仅有的核大国。今天事情变得有些复杂,因为有限战争也有可能采取网络战的形式。
克里斯托弗·柯克尔(Christopher Coker)的《不可能的战争》(The Improb⁃able War)一书⑤Christopher Coker,The Improbable War: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柯克尔认为我们正在犯1914年同样的错误,我们那个时候也认为国内战争已成历史,这是对大国冲突的盲目无知。他提出,物质因素本身不能解释冲突的发生,因为冲突还受到观念、激情和信念的引导。中美之间一个大问题就是“怨恨” (resentment)。①Christopher Coker,The Improbable War: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18-19,65.讲述大量危险的故事也会导致战争。比如,中国总是讲述自己有关过去的屈辱故事,并以基本冲突的观点来看待未来。“现在看上去中国正在准备与日本长期对抗”。美国总是给自己讲述修昔底德陷阱的故事,因而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感到不安,“冲突是美国的预设模式,是美国独特的文化风格。”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无论物质因素如何,战争都不可避免。世界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规范共识”,需要在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问题上进行一次“建设性的文化对话”。②Christopher Coker,The Improbable War: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80,119,181.
尽管这与科普兰的主要观点背道而驰,他的主要观点是任何战争都具有因果关系,并不取决于“单元层次”(unit level)③Richard N.Cooper,‘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in Richard N.Rosecrance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 MA:MIT Press,2015,p.435.,但是,从库珀和柯克尔的分析中,我们必须要研究单元层次上的决策动力。在《牛津亚洲国际关系手册》中,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提出了有力的分析来论证外交政策分析(FPA)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替代或是必要的补充。他说,如果我们要理解东亚的相对和平和经济动态,或者两者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威胁认知、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以及领导力这些因素。国际关系的新现实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东亚地区拥有相对和平和稳定这种现象。“解释这个问题时,只有外交政策分析变量,而不是国际结构才能派上用场。他发现东亚地区的和平是地区领导人更替的结果,因为新任领导人上台后总会在特定的节点上推行促进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反过来也给政治决策者更多的动力来避免采取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然而,不幸的是,同样也是经济增长使得政府可以大量投资现代武器,这也导致美国在亚洲必须维持强势的经济和军事存在。
爱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④Etel Solingen,‘Domestic Coalitions,Internationalization,and War:Then and Now,’in Rosecrance and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2015.进一步比较了二战前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她提出相互依赖本身并没有阻止战争,相互依赖既能阻止也能引发战争。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联盟主导了国内政治?是在国际化过程中积极作为的联盟还是努力保护本国免受外国影响的联盟?国际化战略强调获得国际市场、资本、技术、进行地区合作并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稳定。这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鼓励储蓄,并增加国际和国内投资。①Etel Solingen,‘Domestic Coalitions,Internationalization,and War:Then and Now,’in Rosecrance and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2015,p.130.相反,内向模式(inward -looking models)受益于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保护主义者和军工复合体的活力。她发现二战前的德国属于内向模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愿意走向战争。如今主导中国政治的社会-经济联盟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帝国主义德国的农业-工业-军事复合体。它们主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快速的社会经济变革、停滞的政治制度以及经常使用专断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化武器。②Etel Solingen,‘Domestic Coalitions,Internationalization,and War:Then and Now,’in Rosecrance and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2015,p.138.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不同于帝国主义德国,因为它的军队由文官控制,而且它积极融入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全球市场,拥有跨国产业链,并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中国的国际化主义者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一样在促进全球经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未来中国走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不会是零”。③Etel Solingen,‘Domestic Coalitions,Internationalization,and War:Then and Now,’in Rosecrance and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2015,p.146.
值得注意的是,索林根并没有对美国的社会-经济联盟做出任何说明。与罗奇不同,她似乎假设威胁和平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在这一点上,她也与科普兰不同,④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科普兰认为一般是衰落国挑起战争,米尔斯海默也认为中国试图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这将迫使美国采取措施遏制它的崛起,并削弱它的实力。
结 论
近期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核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在什么情况下并以什么样方式减少两个大国冲突风险的认识。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至少四条结论:一是相互依赖既能抑制冲突也能引发冲突。一方面,相互依赖全面增加了冲突的代价,但另一方面,非对称和不平衡的依赖或者悲观的贸易预期也可能会引起冲突,并导致相互依赖国之间爆发贸易战,反过来,这将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⑤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Dale C.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1,14,437.如果相互依赖的一国受内向型的社会-经济联盟主导,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大。⑥Etel Solingen,‘Domestic Coalitions,Internationalization,and War:Then and Now,’in Rosecrance and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2015.二是对中美战争风险的评估不应是双边的,还应把各自的盟国和伙伴国包含在内,因为第三方国家有可能把中国或是美国拖入到冲突中去。三是东北亚三大经济体(中国、日本和韩国)都通过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生产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令人欣慰。①Hidetaka Yoshimatsu,‘Economic-Security Linkages in Asia,’in Pekkanen et 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2014,p.576;John Ravenhill,‘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in Pekkanen et 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2014.四是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权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中,他们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做出是战还是和的决定。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融入外交政策分析,这样才能了解国家决策层重视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它们对风险和机会的评估。如果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开始担心或估计他们的国家在衰落,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外部过度依赖的结果,他们会诉诸于排外情绪,开始考虑使用武力来获得尊重和荣誉,同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并最终拒绝在核威慑或社会经济浩劫预期面前做出让步。这些危险的转变可能会瞬间发生,比如,在第三方的煽动之下,或者出于反对第三方的需要。
只要有核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同时存在,东亚的冲突就不太可能升级为战争。正如陈思德所论述的那样,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意识到,当他们采取挑衅行动的时候,他们不能指望来自中国或是美国的帮助。②Steven Chan,Enduring Rivalries in the Asia-Pacif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目前东亚面临的最大风险不在于领土主权冲突导致的战争,而在于世界经济变化对国家间和平产生的影响。如果中国和美国无力再平衡其金融和贸易关系,③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那么贸易战就有可能发生,从而破坏跨国生产网络,引发社会仇恨,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这对安全领域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使得核武器成为挽救我们走向末日最后的但也是不怎么可靠的手段,因为威慑有可能失去可信度:比如,两个大国可能会赌对方会在网络战或常规性有限战争中首先做出让步,或者第三方国家彼此陷入相互冲突之中,并认为此举会迫使中国或美国为了它们的利益而进行干预。
毫无疑问,增进全球和平的最好方法就是多种手段并用:通过全面加强经济相互依赖、政治和好、政治信任、制度化合作和共有国际规范的方式,创建一个太平洋安全共同体。但是,即使不能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核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的结合也足以阻止大国间的战争,因为核武装国家的领导人担心国家陷入到只能依赖核威慑来维持和平的境地,而且他们也清楚敌对国也有同样的恐惧,为此他们可能会接受经济上必须依赖他国所带来的风险。届时,无论是贸易战或真枪实弹的热战都不会存在了,剩下来的只有各种纠纷和外交活动了。
[修回日期:2015-06-25]
[责任编辑:秦恺]
斯坦·托纳森(Stein Tønnesson),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教授、前所长,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系教授
2015-05-22]
①斯坦·托纳森教授目前领导一个由多国学者参与的“东亚和平” (East Asian Peace)研究项目。本文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其中部分内容的英文版将发表于《国际区域研究评论》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之上。关于中美和平的基础到底是核威慑还是相互依赖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看法不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本文作者斯坦·托纳森通过对核威慑和相互依赖问题深入系统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文对他的观点做出自己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