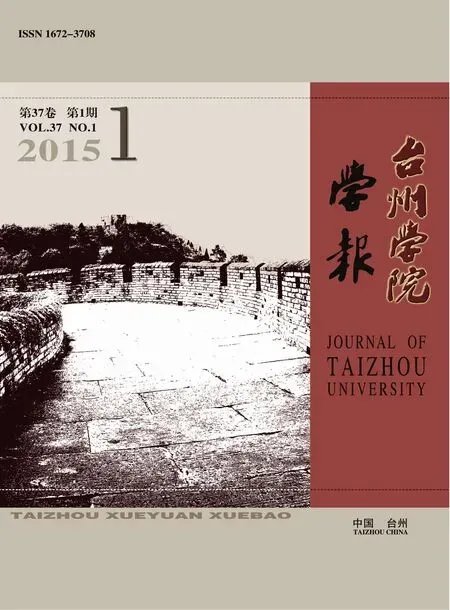疯癫·激情·语言
——《遍地枭雄》和《堂吉诃德》中的疯癫形象探析
苗变丽
疯癫·激情·语言
——《遍地枭雄》和《堂吉诃德》中的疯癫形象探析
苗变丽
(河南大学 民生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遍地枭雄》和《堂吉诃德》中的两大疯癫形象——大王和堂吉诃德,其共同且深层的心理本质特征为:谵妄的执迷。而人物的疯癫体现为:疯癫总是伴随着激情的燃烧、疯癫是语言着魔的过程两大基本特征。
疯癫;激情;语言;《遍地枭雄》;《堂吉诃德》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安忆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她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巨大的再生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成熟状态以来至今每个时期都屡有佳作,因“高质“和“高产“而在当代小说家中位置凸显。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遍地枭雄》是又一篇佳作,该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众多批评者的广泛注意,他们大都认为该小说是对一种诗意人生的人性向往。但是笔者认为,这诚然是这部小说的寓意指向之一,但由于该小说形式与内容的丰富意味提供了大量话题,不是一种批评方法和批评角度就所能够涵盖全的。小说寓意的箭还射向其他的光影之间,这是一个藏匿和显现同时并举的过程,其中的沉默和缝隙还有待于进一步被激活。
如果借助于福柯的疯癫理论来观照阐释该文本,就我个人而言,不失为一次视野上的有效解放,更能挖掘出其文本深掩的潜在意义,让我们窥视到小说人物的精神生活中最危险、最隐秘的地带。恰恰又是这一运思角度又把我的视线引向了另一小说文本《堂吉诃德》,从比较文学的立场来看,《遍地枭雄》和《堂吉诃德》有多方重影之处。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前者就具有后者不朽的文学史价值,是在承认这两部小说在形式结构、语言形态、艺术特色方面的各自独特性的前提下,认为它们具有人物塑造、内在灵魂气韵上一定的呼应性、相似性,把它们合在一起阐释也许是件大胆的批评新尝试。
一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遍地枭雄》和《堂吉诃德》这两部小说并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全面、丰满和复杂性,而是追求人物性格的单一自危性——抓住人物情感逻辑的起点:谵妄的执迷——以体现主题。这一人物情感逻辑就是这两部作品内在的结构力、感应力、支撑力,维系着人物和故事、画面和场景的和谐统一。
在《遍地枭雄》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奇异的形象——大王,大王一介流民身无正业,靠打劫为生,然而这个强徒却具有着涵括历史风云的雄心,他尊崇的是历史上成就帝王霸业的千古风流人物,如朱元璋、诸葛亮、隋炀帝、毛泽东等人。他知识渊博,满腹哲理,在给手下三人讲演这些历史名人伟绩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对于大王来说,这些历史伟人是一个语义模型的他者,他把自我塑造的范型框定在这些历史名人上,试图在这个位移上实现自我成就的期许。他像一个真正的伟人一样,豪气雄风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自负地观照人世间,世俗的烙印、社会的气味都会使他鄙夷。同时,这种豪气也是一种男性友谊的表现,如在南京燕子矶盟约之时,大王、二王、三王、韩燕来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深层的转化,他们铁血盟誓,肝胆相照,存交重义,有着伍子胥和专诸之间的“知遇之恩“。从表面上来看,大王身上的个人精神气质接近于陈平原所界定的“侠“的精神气质——独立苍茫,傲视千古,注重个人意志,追求个性舒展,绝不愿为世俗的种种准则规范所束缚[1]。大王沉溺于这种虚幻的豪侠精神中不能自拔,这种信念和心象的组合构成了他精神的谵妄。但荒唐的是,大王率领手下“起而行侠“的实践之道却是劫持强掳、违法犯禁,时间一长他势必像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那样陷入罪恶之中,而罪恶在本性上又和追寻意义的诗性生活目标相冲突。这是主人公精神乱象中黑暗的一部分,导致其将自己与最吊诡的极端联系起来,只能在“一端是死亡一端是疯狂“两极间游移。
正如桑丘受到堂吉诃德的感召和教导一样,韩燕来受到大王精神的浪漫主义启蒙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了解到韩燕来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生活态度和内心欲望有助于我们认清这种激变,韩燕来人生之途的转捩突变都是因了一条心理固着点的驱使所致。韩来燕的心理固着点是情感自由性追求,自由情感的产生根源来自于他童年的农耕生产方式。韩燕来生活在上海市郊的一个城乡结合部,童年留在他模糊记忆中的是“在一片毛豆地里奔跑。豆棵刮在裤腿上,即便是隔了牛仔裤,小腿和脚踝上依然能感觉坚硬的刺痛。熟透的豆荚炸开了,豆粒四下里飞溅出来,奇怪地发出铃铛般的清脆。[2]“这种对故乡的诗意记忆成为韩燕来自由情感中最坚久的部分,在诱惑着他偏离常态,所以他最终从三王的受害对象,摇身成为他们的追随者,一脚跌入一种异样的生存境地。如果说这是一次放逐,那么它不是“他者“对“自我“的放逐,而是“自我“的主动放逐。韩燕来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三王们浪漫精神的牧游寻乡契合他自由的情感倾向。但这场促使他新生的自我选择一开始就是险恶的、绝望的,使个人以后的故事遭际充溢着吊诡的意味。
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主人公堂吉诃德最初生活于枯燥的现实和藏书大多为骑士小说的书房所构成的二重世界中。一方面:“他那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他日常吃的沙锅杂烩里,牛肉比羊肉多些,晚餐往往是剩肉凉拌葱头,星期六吃煎腌肉和摊鸡蛋;星期五吃扁豆;星期日添只小鸽子:这就花了他一年四分之三的收入。“[3]另一方面,他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为买那些书甚至变卖了大部分家产。他所理解的那种骑士文学与他不得不面对的生活是极不协调的。很快,堂吉诃德就失陷于内心的紊乱,沉溺于一种谵妄的执迷之中,以书房的传奇世界完全取代了枯燥的真实世界。堂吉诃德想以阿马迪斯为楷模过一种理想的骑士生活。
堂吉诃德有一种能力,他可以从内部生长出一切,将环境转化,在自己的周围制造一个新世界,即他能将生活转化成对于骑士传奇的想象,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堂吉诃德过上了一种假想的骑士生活:他把一个粗俗的村姑假想为梦中佳人;把旋转的风车假想为巨人;把不起眼的客栈假想为城堡;把羊群假想为萨拉森军队;把理发师的铜盆假想为有魔法的曼布里诺头盔;把佩德罗博的傀儡戏假想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并冲上去把偶人们当成真的摩尔军队狂劈乱砍,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一系列构成其有机形式的事件中,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能够导致谵妄的力量。这些假定性事件在置于理性之中的读者看来因为过于离奇而显得荒唐,但并不妨碍堂吉诃德在这些奇情异想中过着真实的骑士生活,只有如此,堂吉诃德才能确定自己已经变得和阿马迪斯一样真实。堂吉诃德的整个存在,他的生存理由,他对于现实的感受,都是以骑士传奇为依据的。堂吉诃德的思想完全陷于这个固定想法,恰是他身上的这种定向思维使他既不绝望,又不恢复理智。
在这两部小说中,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大王,他们本身就是某种精神观念的载体——这种精神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关于幻觉和心象的概念——游侠精神占据了大王的思想,堂吉诃德偏执于骑士精神。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就是其观念的外露和锋芒,是激情幻想浪漫思想奇妙人生观夸张的结果,他们都是自己心灵的囚徒,因极度地陷于对某种心象的冥思苦想之中以致不能关心真实存在的实际状态,失去了对物质世界的真实感受,也失去了对自然的一切真实关系的感受。这种幻象意志的表现代表了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大拒绝“,是一种实践性的“大拒绝“。相反,虚幻摆脱了真实及其束缚而浮现出来,他们从谵妄的信念出发“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做史诗“。布鲁姆给堂吉诃德下过这样的定语:“堂·吉诃德的动机来自于要获得不朽的声名,或者可以解释为‘时空里的一种人格扩张’。“[4]这句话同样适合《遍地枭雄》中的大王。人物所追求的不朽声名从客观上讲,是很虚幻的,但从角色本身来讲,这种追求的过程却是很真诚的,角色在这虚幻的真诚境界中是很痴迷的,是执迷不悟的,导致了一种“诚实的灵魂与分裂的意识“(特里林语)的产生。
二
在《遍地枭雄》中,大王这种情感上、行为上过激的表现,是理智还是疯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认为,疯癫主题的框架中盛满着所有的理性对立面,所有的理性排斥物,所有的理性敌视者,是一大堆近似词的换喻:小偷、罪犯、梦想家、越轨者、放荡者、精神错乱者,所有这些都具有疯癫的要素,疯癫不再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医院病例,不再是大街上的骚扰因素,疯癫是启蒙理性狂妄自信的一连串反证[5]。用福柯意义上的“疯癫“来指称大王们的状态也许合题。而小说《堂吉诃德》自问世以来,主人公就被视为疯癫者的不朽形象之一。“唐诘诃德的疯癫真伟大,原因在于产生疯癫的根源也伟大,即永不熄灭的生存渴望,这是最张狂的傻事和最英勇的行为的源头。“[4]101对于大王和堂吉诃德而言,他们的疯癫都是文学性的,疯癫总是伴随着激情的燃烧。事实上,激情是在疯癫中燃烧着,复燃着,正是激情的存在才酝酿出疯癫的爆发和壮举。
在《遍地枭雄》中,大王、二王、三王这些草泽英雄们的社会行为不计后果,不计成败得失,仅考虑行为的审美意识价值。他们的生存态度是:“凡是现实里的严肃问题,他们都抱有轻松戏谑的态度,相反,凡是游戏玩耍,他们都郑重其事,来不得半点含糊。“[2]167-168对于打家劫舍这件事,他们是按心的律动行事,抱着游戏的态度去施为的,而非是生活切实的功利目的使然。如果用道德界面去勘定,很明显,在这种游侠行为中有一种社会学的违法犯禁,但是人真正的形而上的命运不是表现在道德伦理中而是表现在艺术中,所以我们要超越道德范畴、法律观念及其所支配的评价。对于他们的社会行为,我们应撇开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角度,而只从价值理性行为来观看,就会发觉,在日常生活的黑暗中,在社会制度的禁锢中,他们的自由选择、美学的诗性存在犹如灯塔一样照亮着周围阔大无边的黑暗区域。诚如大王所说:“现在,我们就像站在灯塔上,站在黑暗中的光明里。“[2]153对于率领手下干的劫持强掳勾当,大王就是这样赋其一种自由的光辉气韵,为他们的阴暗生活建立了自己的道德体系和合理性的。这样一来,“伦理角度上善的光明的正常秩序却成为美学、哲学存在意义上的黑暗,而恶的暗的反面秩序却成为哲学上自由枭雄的光明,成为‘灯塔上的光明’来照亮被庸常秩序所遮蔽的存在。“[6]这一切正应和了赫拉克利特那句著名的话,下降的路与上升的路是同一条路。这种有罪的激情是文本叙事的吊诡之处,使文本叙事出现一个断裂,带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三王他们都是自由选择的自由英雄。自由选择是自由意志的实现,人根据自身进行的自由选择,绝对地与命运完全一致。这种自由选择给韩燕来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把他引入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的空间,使他摆脱了刻板化的认知和日常行为的种种强制,从压抑的秩序天地和道德规范中逃逸出来。三王们的浪漫精神和自由人性成为韩燕来一个精神繁殖的原点后,韩燕来于是恢复了童年那种自由人性,在自由中找回了自我,诚如后来的他在作文里已经能够想像自己是藏羚羊,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生存,自由地远离人群生活。借助一次冒险之旅,韩燕来实现了一种精神上的解放。
当韩燕来踏上这条冒险之旅时,文本的整个激情叙事才开始像一道急流那样汹涌倾泻。这些流寇英雄们放意自恣游行村市,由木渎到常州、南京、徐州、济南……直至最后埋形于寂无人居的草泽山野间。在作者笔下,这里的游侠世界不具有地域人文、风情的考据价值和社会性的异地风味,而全然是一派水墨写意笔法。穿乡走镇的大半个中国被转换成了一场精神漫游,现实道路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隐喻意义上的心灵道路。他们游散取乐的出行记演绎成一种纯粹的精神漫游,是一种遗忘外物空间的向内的“游心“,其间充溢着激情的迸发,人物也沉浸在只有饱满的激情才能制造出的那种自由的快乐之中。
在《堂吉诃德》中,小说主人公在对游侠骑士的扮演中把自己提升到理想的时空,忠于自由、忠于非功利性和兼善天下,试图以一种拯救的欲望重建骑士生活的激情。这一切都体现在其现实中的践行——堂吉诃德离开村庄投入巨大激情开始不可预料的冒险经历,第一次历险、第二次历险、第三次历险,“冒险最普遍的特征在于它落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之外,落在日常的常规之外。“[7]堂吉诃德沉迷的是这追寻的历险过程,更是一场灵魂的激情冒险。堂吉诃德在绝对的意义上将生活变成了艺术,在言行举止、体格风度方面尽情表演他自身的激情。对于他来说,生活成为其丰溢充沛的生命力外露,该人物也成为汪洋恣肆的人类激情表征。
从以上两部作品来看,其主人公都超越于凡庸沉寂平淡无奇的日常状态,带有奋进的精神和豪迈的气魄去实践他们奉行的精神,带给读者的印象是不顾一切、驾临一切的生命激情。可以说,这里的疯癫与激情共生相随,扭结纠缠于小说情节之中。对疯癫/激情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的确认使我们得知,这里的疯癫根本不是一种疾病,疾病是一种丧失,疯癫则是最终充分实现的健康,是一种激情充盈的人生实现。人物身上这种疯癫的激情对于日常生活理性化是一种解放性体验,诚然,对于我们的文明和理性而言,还有比疯癫更恰切的东西来暴露它的阴郁面吗?所以特里林说疯狂“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某种消失的真理[8]“。拉康也曾说过疯狂是理智的效果之一。
这些疯癫者不需要治好他们个人的疾病,他们的疾病正是他们应该指望的东西,这种疾病体现了他们身上的伟大和勇气,他们因而成为作家所属意的智者、仁者、勇者甚至圣者的化身,他们身上潜隐着的对生活诗性意义的激情探求和质询使得这些人物充满不屈不挠的内在力量。但无须讳言的是,这种激情含义明显带有盲从的狂热,虚幻的欺骗,而这样一种情感或心态,又包含着深重的歧义性,文本叙事不断增进的强度就取决于其不稳定性的聚合,往往随着叙述的展开疯癫与激情的关系会变得更加悖论、异化、混乱,更加不可排遣,凸现了多种矛盾的纠结状态。也正如此,我们在对之下断语时必定如履薄冰犹豫徘徊,结论也只能是猜测性的。
三
在《遍地枭雄》中,语言游戏伴随着三王们行踪的始终,他们一味地沉醉在话语里,用坐而论道的清谈阐述灵魂。从一开始的词语接龙,到成语接龙,故事接龙,从“记一个难忘的人“命题作文,到“记我们的生活“作文、“我们的未来“作文,以及众多的知识竞赛、辩论、讲演等等。这些话语游戏使他们经历了一场场语言丛林里的精神迷幻和话语狂热。以大王为例,大王的自行演说占据了小说相当的篇幅,他经常把书里看到的知识和典故,一些道听途说的逸闻,以他特有的逻辑和方式杂糅起来,在这些纵横捭阖、慷慨天下中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有效空间。在大王话语表述里总有一种豪气涌溢而出,染着浮夸的激情和想象。通过借助于语言的这种想象状态,大王完成改造自我的愿望,完成自我风格化的态度和意志,将自身塑造成历史伟人的气质的意图。
在《堂吉诃德》中,西班牙拉·曼却地区一个名字不详(或吉沙达或吉哈达)的老乡绅在即将开始文学史上最为不朽的历险旅程前,先期赋予自己的拯救渴望以一种语言表述。他仿照骑士文学的惯例为自己、自己的意中人及自己的马分别取名为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杜尔西内娅、驽难得。这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命名“过程。由于语言使人着魔的特质,这些名字在堂吉诃德的头脑中改变了实际事物的意义、价值和色调,“每一个名字都不只是粗鄙现实的面具:事实上,这些名字把‘是’变为了‘可能是’。“[9]命名中一个穷弱乡绅成为一位显赫贵族骑士,一个粗俗的乡姑成为绝世佳人,一匹老弱的羸马成为千里驹。在堂吉诃德看来,这些人或物,已转换了世俗真实的身份状态,成为一桩激情事业的执行者。也就是说,在以后的冒险中,堂吉诃德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对这些“命名“加以追认。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文本起始的这一段对于从总体上理解这本书是极端重要的。这些虚幻的名字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发挥了其能指的强大作用,一系列“命名“实际上就确定了后来的情节序列发展态势。堂吉诃德从家出发,一脚迈进了自我语言虚构的世界,他行动、扮演着他所设计的那个自我,并且用语言虚构出的光晕照亮了身边的人和事,使现实的世界屈就语言虚构的法则。这种语言策略的结果使堂吉诃德把自己变成了故事,把经历变成了小说。通过语言,“堂吉诃德试图在生活中经历文学,成为他自己故事的主角,而且,在他能控制事件发展的范围内,成为它的作者“[9]14。叙事体现为一种语言的魔力,事件既真实又虚幻,使读者感受到该小说一直处于现实和虚构的圈套之中,在大王和堂吉诃德身上出现了很强的表演性,他们就像一位出色的演员,世界是他们的一个舞台,供他们作出种种夸张的、故作激烈的表演。而语言,正是舞台上供他们表演的器物。福柯曾说:“语言是疯癫最初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疯癫借以明确表达自身性质的所有演变都基于语言。“[10]对于大王和堂吉诃德来说,疯癫的过程亦即语言着魔的过程,他们谵妄的语言伴随疯癫的始终,到了疯癫这一伟大症候消失的时候,也是语言解除魔力的时刻。无疑,大王和堂吉诃德谵妄的语言是现实黑暗中心象的一种解放,“这种语言使激情摆脱了一切限制,并用其全部强制性的肯定力量来维持自我放纵的心象。“[10]97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伊格尔顿篡改了它,他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定的社会生活。“但不管怎么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那么,言说的方式也就是存在的方式。所以有论者才这样评定《遍地枭雄》中的大王们:“对他们来说,语言的冒险就是他们的冒险,语言的成长就是他们的成长,语言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才乐此不疲,甚至充满理想,充满自信,与语言一起成长起来。对于语言的沉迷,也使这些枭雄具有了哈姆雷特式的焦虑和堂·吉诃德式的虚妄色彩,使之焕发出哲理剧的虚幻可笑性……当盗贼与诗人的身份重合起来时,那么,语言的重合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他们共同的语言构成了存在的共同的家,他们在其中生活。“[6]99
诚然,在生活中很少会有人像大王和堂吉诃德那样讲话和行动,但在典型的意义上、艺术的意义上,他们用语言进行表演的,不正是寄寓理想人格与理想生存方式的图景——一种理想生命存在的自我表征形式么?不正是处境学而非事象学意义上人类的终极生存问题的反映吗?!
结 语
总的看来,这两部作品与谵妄、梦幻、激情纠缠在一起,与黑夜的经验纠缠在一起,这种黑夜就是其人物所体现出的道德态度与精神态度的极限,就是人类灵魂的巅峰体验和深渊体验。可以说大王和堂吉诃德是同一精神态度的不同结晶,这一精神态度的决定因素是精神的疯狂,这种精神的疯狂使他们处于某种精神与环境的分离之中,一种心造的梦靥幻影成为诱惑的对象,正是这种心象蛊惑了疯癫者的目光,致使他们的目光始终停留在那虚幻的心象之中,同之进行一种精神的交媾。他们的确不渝地信守这些可怕的、纠缠不清的虚妄心象,而且坦然地赖之以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对镜求索的俘虏。正应和了福柯的那句话:“这种疯癫象征从此成为一面镜子,它不反映任何现实,而是秘密地向自我观照的人提供自以为是的梦幻。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知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10]27-28大王和堂吉诃德这两个疯癫者是文学形象世界的一种形态、一种丰姿,象征了一种存在状态、一种存在方式,他们代表着人类精神、活力、期盼、向往中所固有的自由,代表着意识本身及其无限矛盾之中所固有的自由,体现出某种不寻常的英雄气概——既有浮士德式的激情、超人式的狂傲,又有西西弗斯式的倔强。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塞万提斯就对人类疯癫的忧郁性真理做出了一次杰出的情感探索。数个世纪过去了,当代作家王安忆从时代的人文环境中再度察觉到这些原始问题,并运用独特的叙述方式使疯癫故事再一次敞开其存在的性质。也正由此,我们今天才有机会怀着忧郁与沉默在人心底的黑暗的深渊上俯瞰一下,在那巨大而又幽暗的深渊中,再一次体验到了晕眩。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么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3.
[2]王安忆.遍地枭雄[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1.
[3]塞万提斯.堂吉诃德[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9.
[4]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8.
[5]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3.
[6]白浩.自由英雄与“灯塔上的光明”——析《遍地枭雄》的诗性存在冲击波[J].当代文坛,2007(5):99.
[7]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3.
[8]特里林.诚与真[M].刘佳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62.
[9]安德烈·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M].汪洪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
[10]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达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97.
Madness Passion language——An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madness on Machiavellian everywhere and Quixote
Miao bianli
(Minsheng Colleg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Henan,China)
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analysis of“Machiavellian everywhere“and“Quixote“in the two images of madness king and Quixote,to explain the deep psychological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de⁃lirium obsession.Moreover,the characters of madness also manifested two characteristics:one is the madness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fire;two is the madness is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possessed.
Madness;passion;language;Machiavellian everywhere;Quixote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1.009
2014-10-23
本文属于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教改项目“开放性教学时空观下的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MSJG2013-13。
苗变丽(1977-),女,河南兰考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