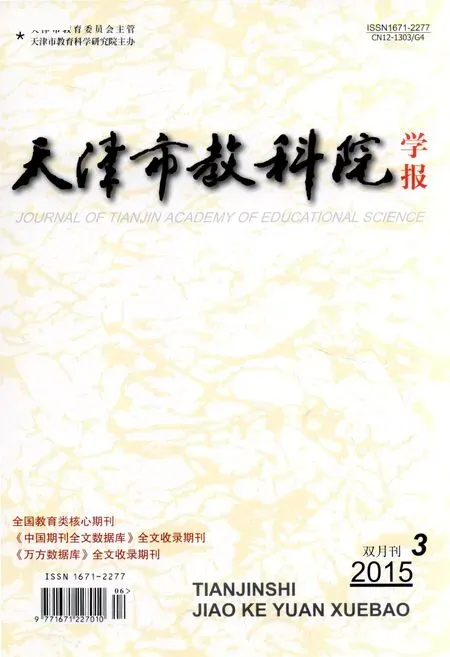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刍议
马开剑,杨 旭
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一场重大变革,都是出于革除旧弊或摆脱危机的需要。1983年,美国政府发表《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并随即出台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就是一个经典例证。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不例外,“是危机引发了改革:因为存在课程危机,我们才策划改革”。[1]“大破大立”的新课程改革“根据又何在?”[2]根据在于传统教育中的危机——在于传统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扼杀,使我们对新生代国民素质能否迎接未来挑战有了担忧;在于长期以来传统课程的各种积弊以及人们痛定思痛之后的深切反思。这些危机的存在证明了传统课程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必须寻求改革。
一、有关课改理论基础问题的争鸣
进行课程改革要不要理论基础?回答似乎是肯定的,但又远不是那么简单。以2001年我国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例,改革启动不久,就有靳玉乐、艾兴两位学者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下称靳文)这一问题,全国教育界围绕这一问题曾进行过激烈争论,当年的《中国教育报》在5到9月间发表了意见不同的系列文章。
靳文认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模糊的,将导致实践上的混乱,指出“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3]同时认为课程改革不能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并提及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以作为佐证。高天明随后发表文章,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的理论基础”为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课程理论涉及课程与知识、课程与文化、课程与社会等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课程理论首先必须在知识、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去解决课程建构的理论大厦”。[4]与高天明同时发表文章的还有马福迎,他认为“我国这次的新课程改革,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理论基础厚实,具有时代性、全球化的视野,是正确的”。[5]马福迎认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不仅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靳文)”以及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等,还有教育部组织多方专家学者广泛吸收的一线教师的意见。与靳文相反,马福迎认为新课程改革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而罗槐先生则力陈“多数实验教师的教育实践还处于‘穿新鞋走老路’的状态”、“教育工作者对培训中接受的基本教育理论的‘消化不良’”以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并‘自律’于改革前的一元理论(主要是凯洛夫教育理论)”等基层教育实践中的不良现象,[6]以支持靳文观点。王华生则在同版发文批评“靳、艾两位既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并为一体,又将多元论与多样化混为一义”,提出“新课程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基础相结合的原则”。[7]可以想象,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后续过程,仍然会充满类似的争议。
二、课改实践不会有统一完备的理论基础
真正伟大的创造性实践往往事先并没有完备理论,实践越是复杂、规模越是宏大、涉及面越广,情况就越是这样。不是先有了统一完备的理论,然后才去实践,而大多是先有了危机意识、改革需求和某方面的理论引导,然后再在实践中创生、完善和发展其理论体系。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就属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也没有什么完备统一的理论,甚至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依然还是不完善的,而改革实践所产生的成效却是举世瞩目的。
作为一种实践过程,课程改革往往也是这样。类似2001年启动的基础教育课改,其创造性、复杂性就是空前的。它以全新的话语系统规划了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蓝图,反映了当今时代课程理论和课程改革实践的进步趋势。不仅推出了“三级课程管理”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而且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出了一整套推进大众主义教育的改革方略,包括教师专业成长、关注人文素养、确立课程与教学新范式等。它与以往前七次改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本次改革的综合性、整体性,作为实践过程,它并不是一个从已知公式或理论出发进行已知—求解—作答的简单执行过程,也不是一个按照某一理论比着葫芦画瓢的工艺流程,不是一个按照理论假设进行实验求证的小打小闹的一般教育实验,而是一场以课程为支点橇动整个教育体系的综合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小打小闹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又回到了老路上。
基于此,就前述有关“新课程”理论基础的争议,“以笔者观之,有不少人将新课程与新课程改革相混淆,将对新课程改革的看法‘移情’到了新课程身上。而实际上,改革是一种决策,是决策的实施与行动,是属于政策领域的问题,它本身要考虑多种视角的论说与影响,但并不受制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向改革本身要理论基础或许是不适当的。因为任何改革都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它是指向问题的……而且,越是宏大的改革、越是复杂的工程,越是难以找到一个所谓的理论基础,这或许是争议所忽略的关键问题”。[8]这也是本文想强调、并与前述所有争议均不相同的新观点。任何课改实践都不是因为有了统一完备的理论基础才开始实施,而是因为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有了改革的呼声,当然也可以有一点基础理论。对于课改实践,不能还没有启动或刚走几步路,就对其所谓理论基础求全责备。
三、课改实践伴随多层面的概念重建和理论创新
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实践过程,课改实践不会有统一完备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整个实践过程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都不存在理论基础,恰恰相反,课改实践涉及培养目标调整、教材编制改革、课程管理改革、培养模式改革等具体层面,而其间的每一层面,当主张要怎样改革时,确实都有相应的理论基础。
(一)课改实践必然伴随概念重建
思想、理论、观念、理念、概念具有同一属性,当我们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时,相应的概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反之亦然。课改理念既然不同于传统教育思想,那么也一定表现为一系列的概念重建。概念重建是理论创新的核心。
1.概念重建的学术意味
概念重建并不神秘,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对某些熟悉的人和事进行着概念重建,当我们因某事对某友人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时,概念重建就发生了,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来,我还得重新看待它(人或事或物)”。又如我们经常讲“更新思想、转变观念”,其意思也是概念重建。不过,“概念重建”比“更新思想”来得更加明快,更加鲜明。
但是,概念重建并不意味着新术语完全排斥传统的理论成果,在意义上也未必是百分之百地推倒重来,并不意味着推倒打碎然后再凭空重新建立,而是有机地将吻合新课程意义的成分融于其中。正如“劳动与技术教育”概念的积极价值也被整合进“综合实践活动中”,并被赋予新的内涵。课程改革中的概念重建其实质是转换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后,再重新审视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那些概念和观念,诸如课程、教学、教师、学生、知识、学习等这些早已成为定论甚至已近于常识的概念,一旦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则它的涵义就会发生变化,变得不再是我们惯常的那种认识,于是,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再定义,这就是概念重建的意蕴。
2.概念重建的语境意义
概念术语创生于具体的、特定的语境,也反过来带有它出生、成长的语境烙印,是特定的语境意义的语词表述形式。人们对概念术语的认知与理解,往往首先获得概念术语的原生语境信息,并以此为认知起点。没有概念术语的重建与更新,就难以让读者从其原生语境中摆脱出来,观念难以更新、理论难以创新发展。由此,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必须在新的境遇中重新思考原有的理论与概念。经常的情况是要提出新概念以替代旧观念、旧思想,这是理论创新与发展的自然规律。
3.新术语、新表述是概念重建与理论创新的标志
概念重建与术语创新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概念重建与理论创新的标志就是术语或表述语句的创新,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理论发展。甚至一些社会生活用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教育理论的发展也是一样,总要随着教育创新实践的进步自然地作出更替、调整和创生。“研究性学习”“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等概念,就是这种更替、调整和创生的自然结果。
(二)课改实践伴生的理论是多维度、多层面的
课改实践包含不同的层面,改革的每个层面,都会伴生相应的理论基础。以学生获取知识这一点为例,传统教学认识论对于“学生究竟是怎样能动反映客观事物的”这样的问题就解答不好,而建构主义理论透过“情境”“对话”“协作”“建构”等概念连同它们所包含的发现与主张,至少在解释学生如何获取知识等问题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其对教育情境中学习机制的解释及对教学的指导力,也明显比传统的教学认识论精细和有力得多,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知识问题,知道了知识的境遇性和知识习得的个体性以及学生心智方式的多样性。由此,建构主义获得了课改实践的青睐,反过来它也影响了课改实践的教与学。与之类似,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必须高于生活经验、高于现实生活,但又不能与之脱离太远,以致远离了现实生活的根基,让形式化的科学世界掩蔽了生活世界的本真面目。若学生只专注于那些抽象的、剥离了鲜活经验的书本知识,就容易导致误将书本知识当成生活世界本身。所以,课程改革的现实任务就是要重新找回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结,“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也应定位在这个理解上。由此,生活世界理论也成了课改实践的“伴娘”。
这些课改实践不同层面上的理论基础,虽然各自内部自成一体,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却在共同支撑着课改实践的步履。
[1]钟启泉.中国课程改革:挑战与反思[J].比较教育研究,2005(12):18-23.
[2]孙振东.学校知识的性质与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J].教育学报,2006(2):11-24.
[3]靳玉乐,艾兴.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N].中国教育报,2005-5-28.
[4]高天明.应从哲学层面探讨[N].中国教育报,2005-8-13.
[5]马福迎.对《靳文》有些观点不敢苟同[N].中国教育报,2005-8-13.
[6]罗槐.坚持马克思主义保证课改方向[N].中国教育报,2005-9-17.
[7]王华生.澄清几个概念才能进行对话[N].中国教育报,2005-9-17.
[8]马开剑.新课程背景下对传统教学认识论的三点认识[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