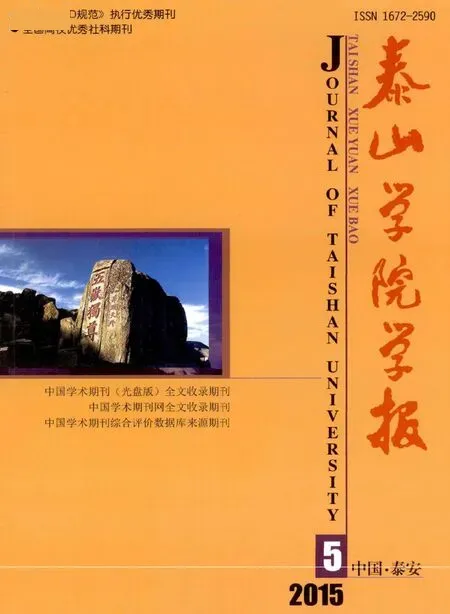1915年国体讨论中的学理问题探析
李云波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1915年国体讨论中的学理问题探析
李云波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1915年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何者更适于中国的国体讨论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讨论中各界学人为论证自己所提出的君主抑或共和主张的合理性,着重就国体政体的概念、国体讨论的合法性等基础学理性问题展开探讨,虽当时其政治智识还不成熟且意见不一,但讨论中多数论者基本都意识到西方先进政治理论和法理常识在该问题上的运用,为国人进一步明晰国体问题的本质和法理属性,并为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和逻辑性的思辨奠定了基础,其在讨论中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思考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怀对民初国人具有重要启蒙作用。
国体讨论;政体;君主制;共和制
1912年2月12日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并没有完全从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阴影中走出来,部分醉心于旧王朝旧体制的前清官僚、立宪党人甚至多数习惯于历代以来君尊民卑观念的底层民众都怀有走回王权社会的情结。本来这种观念在共和建立后的一段时间理应通过必要的政治新举措和国民自身的共和实践来逐步消除,但由于在制宪过程中制宪议员的操作不当以及党派之间的相互倾轧导致这一矛盾加剧。1913年10月袁世凯开始摆脱《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对总统行政权力过分束缚的窘境转而寻求在体制外非法扩张其个人权力,1915年新的《大总统选举法》颁布后其取得终身大总统的资格,在地位上已与专制皇帝相差无几。与此同时,一直以来对共和缺乏信心的民众也在白朗起义和二次革命血的教训以及社会舆论对共和体制的声讨声中纷纷倡言复辟言论。
1913年初湖北商民裘平治上书袁世凯称:“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1](P170)。同年,前清立宪党人康有为在其所办《不忍》杂志中接连发表《中华救国论》、《救亡论》等旧作攻击共和体制鼓吹君主制。[2](P670-678,699-731)而前清遗老劳乃宣则于1914年将其所著《正续共和解》呈送袁世凯直言恢复清朝统治。至1914年底,北京的复辟旧朝之说已甚嚣尘上。
1915年4月,杨度将长达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呈送袁世凯,称“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3](P569),此文事后被日本媒体披露导致袁世凯意图称帝的传言传遍南方,而7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和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的发表,导致这种猜疑进一步扩大。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古德诺认为国体本身无优劣之分,其采用君主还是共和取决于一国历史习惯及社会经济条件,而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缺乏自治的长期实践,因此中国“如用君主制(指君主立宪制,笔者注),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8月3日北京《亚细亚日报》披露该文,之后国内舆论开始广泛就袁世凯是否要称帝、现行的共和国体是适合中国以及中国应进行怎样的政治变革等展开议论。8月23日杨度等人在征引古德诺主张的基础上发起成立筹安会,宣称专就君主、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进行学理和事实的探讨[4](P130-131),国体讨论运动至此浮出水面。此后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各政、学、商、新闻界人士都公开参与其中,一时间“举国言论,支离驳杂,异异同同,同同异异,纷纷扰扰,扰扰纷纷,如饮狂泉,如迷醇酒,奔走张皇,争相告语,咸莫不以国体为空前绝后之问题”[5](P1)。从讨论的具体情况来看,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前者以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其操控下的部分政界要人、各省公民团体为主,而后者以徐佛苏、梁启超、贺振雄、李诲、孙中山等对共和体制始终抱有坚定信心的人为主,而“外国列强对袁的帝制运动始则各怀目的,后来出于其利益需要,决计采取倒袁的方针”[6](P324)。
国体讨论持续前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期间君主论者和共和论者围绕立宪、政权转移问题对君主制、共和制的优劣展开激烈争论,但在讨论后期其逐渐脱离此前所标榜的学术讨论范围于9月后一再电告各省文武官员及各团体指派代表进京请愿,同时制造所谓民意劝说袁世凯实行帝制,国体讨论运动实际演变为一场政治劝进运动。12月,通过极具戏剧化的全国性“投票”和“选举”袁世凯最终接受帝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实际“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决;所谓拥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7](P23-24)。虽然此次讨论最终没能避免袁世凯走上帝制的道路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帝制阴谋起了客观的推波助澜作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讨论本身的价值,“尤其是很多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人参与论争,使反对帝制的回应文字具有相当的学理性和理论思辨色彩”[8](P434)。在具体的讨论过程中,部分学人纷纷就国体、政体的区别及国体讨论的合法性等基础学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成为这次国体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一、国体与政体:概念界定
“国体”一词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典籍,当时指国家状态(以纲常礼制为主的封建典章体制)、朝廷体面(天朝观、夷夏观)等。国体作为真正法政意义上的概念出现则始于日本明治时期,当时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国体主义者突破之前国体概念仅限于伦理、文化概念的束缚,将“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明定于明治宪法中,伊藤博文谓之为日本“固有之国体”[9](P1),意指日本的国家形态和建国原理。在此之后,穗积八束(1860-1912)对国体的内涵进行了宪法学的严谨诠释,其在充分吸收西方有关政体的学说的基础上初创性地将国体、政体两个概念进行了二元区分,认为国家具有主权,但因国家组织中的“主权存在之体制”不同,故国体可分为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而“政体由统治权行使之形式而分”,可分为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其认为国体不能轻易变动否则将意味着革命与反叛,而政体则可因时势而变迁[10](P70)。此后,虽然穗积八束的国体论随着立宪主义的发展受到“国体为历史文化概念而非法学概念,君主共和均为政体”的批评[10](P72),但其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却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20世纪初国体一词随着日本公法著作如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高田早苗《宪法要义》等中译本的刊行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07年10月到1908年7月第二批赴日学习宪政的达寿(时任学部右侍郎)在日本得到穗积八束、有贺长雄等学界名宿有关日本宪法和国体理论的指导,回国后其对国体学说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所谓国体者,指国家统治之权,或在君主之手,或在人民之手。统治权在君主之手中者,谓之君主国体,统治权在人民之手者,谓之民主国体。而所谓政体者,不过立宪与专制之分耳。国体根于历史以为断,不因政体之变革而相妨。政体视乎时势以转移,非如国体之固定而难改”[11](P56)。显然这种观点与穗积八束的国体论别无二致。之后不久,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模仿明治宪法第一条的国体条款,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12](P357)。基于以上的认识习惯,民国建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天坛宪草》中亦专设《国体》一章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12](P389)。
梁启超在晚清民国政治思想领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其对国体问题的一些认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们的普遍看法,1902年其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认为“主权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国体之所属而生差别”[13](P3)。后来其又将国体阐述为“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分为君主、民主两种,而“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之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制限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14](P37、38)显然这也是受到了当时日本国体理论的影响,并与清末立宪中国体、政体的相关论说基本相似。
1915年的这次国体讨论承继了以往学界关于国体的论说,稍有不同的是其将国体表述为君主制与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和民主制,如杨度、古德诺、梁启超等多数人的文章中都采用这种表述。而实际这种区分法在之前也出现过,1907年10月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即数次使用“共和国体”概念[15](P20)(当时正值立宪派和革命派论战时期)。1912年8月发布的《国民党宣言》中也指出:“不必论其国体之为君主共和,政体之为专制立宪……”云云[16](P396)。笔者以为1915年的这次国体讨论同时受晚清以来关于国体主流学说和民国肇始以后“共和”概念日深这一现状的双重影响,其实质则与以往国体概念的本质相差无几,这一点从梁启超在此次讨论中认同君主和共和的分法也可以看出。不过在辩论中仍有一部分人对国体的概念提出不同意见,有论者坚持以往君主、民主的分法,如上海《时事新报》、广州《国华报》等都曾刊文表达此种观点。[17]民初著名政论家章士钊(曾用笔名“秋桐”创办《甲寅》杂志)则引入形式和精神的概念,认为国体为形式,政体为精神,“共和之形式,民主之谓也。精神,立宪之谓也。”[18]而精神重于形式。与上皆不同的是,历史学家李剑农(当时是《新中华》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根据国体政体概念从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国的流变过程认为国体是有歧义的,“一则别国体政体为两,国体专指主权体,政体则指政府之形体;一则合国体政体为一,国体即指政府之形体”[19]。而张东荪(曾用笔名“圣心”,创办《新中华》杂志)则更直接地指出,世界各国没有国体之分,只有政体之分。国体、政体之争者,一半是因为不知道国家和政府的区别,一半则是因为不知道法律与政治的区别。其认为“政府有差别,而国家无差别,易言之,即有政体而无国体”。此外政体分类是法律上的产物,离开法律无政体,因此现代社会只有两种政体即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而专制不过是国家发展的畸形,不能被称为政体。[20]民初学人郭守七亦同样认为君主、共和实际为政体概念,但他对国体的看法与章士钊、李剑农、张东荪等人都不同,其认为国体与一国之人民、土地被统属的状态相关,可分为联邦制、混一制两种,“故必以合众国而采用英法日俄之制,方为国体之变更,必有人主张以中国为瑞士之联邦,方可谓为变更国体”[21](P20)。而君主和共和则属于政体的范围。
除了对国体概念的不同认识,相关论者还就国体、政体的矛盾关系进行了分析,杨度认为可以通过改行君主制来实现宪政。而梁启超则认为,“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22](P240)况且“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22](P249),所以梁启超认为为不致引起流血革命坚决不能通过改行君主制来实现立宪政体,同时指出“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22](P236)。
尽管以上论者对于国体、政体的基本概念、关系等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总体来说其讨论的主题仍围绕君主、共和展开。由于讨论中各论者基本都使用西方政治学术语并征引西方学者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8](P436),因此他们的诸多分析都具有现代政治学的较强学理性,不仅有利于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国体问题的本质,且为人们提出君主抑或共和的主张提供了基础学理支撑。在讨论中,总体来说君主论者在国体、政体的划分问题上较为一致,且多强调国体在国家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而共和论者在国体、政体问题上有很多分歧,且更多强调政体选择的主动性。
二、影响国体的因素
国体的决定因素问题也是此次国体讨论的一个重要学理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界定有利于分析评断国体讨论的必要性。在讨论中有人主张国体是自然生成的,有的则主张国体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古德诺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指出,一国国体“无论其为君主,或为共和,往往非由于人力,其于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社会经济之情状,必有相宜者,而国体乃定。假其不宜,则虽定于一时,而不久必复以其他之相宜之国体代之,此必然之理也”,而在决定国体的因素中,其认为“威力”是最重要的。[23](P148)梁启超也认为,国体“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源”,即由时势作用的结果,而非学理和人为意志所能决定。虽然古德诺与梁启超的观点相似,但二者的立论点却截然不同,古德诺认为君主制才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当前实际的国体形式,而共和制则是辛亥革命后人为操纵的结果,是不能长久的。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当前共和制的形成是时势作用的结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现在试图通过简单的学理讨论就加以人为的改变势必会带来祸乱。
对于古德诺的观点有论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张东荪在1915年8月27的《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一文中指出,历史习惯是存于人民心中的,社会组织、经济状态也无一不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谓国民对于国体无能有所选择,真谬论也”[24](P133)。汪馥炎则进一步指出,适合一国国情的国体“无异国民意志之已选择其相宜者也”[25],因此必然是符合历史习惯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在二者看来,主观意志与客观条件不应强作割裂,国体由众意聚合而成,而非“威力”等简单作用的结果。日本法学博士副岛义一也指出“佛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以及文明诸国采用立宪政体,悉出于先觉者之唱导,或其国民之自觉的选择,殆无疑义;故一国国体之确立,绝不能纯视为历史上发达之物也”[26]。
在国体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上,无论共和论者还是君主论者,都较多地强调历史习惯、国情时势等客观因素对国体的影响,不同的是二者对中国当今国体的看法不一,梁启超等共和论者认为共和制是适合中国的,是国情时势的体现;而古德诺、杨度等君主论者则认为共和制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并不与中国国情相符,所以需要改制。二者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必然会引起在国体变更问题上的更大争议。
三、理、法之间:关于国体的讨论
国体讨论的合法性问题是有关基础学理问题讨论中意见分歧最大的议题,在1913年复辟论初起时政府曾对讨论国体予以坚决抵制,舆论也同样认为讨论该议题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但到1915年筹安会发起国体讨论后杨度等人竟以学术研究自任予以公然讨论,政府方面亦一反常态予以承认并积极参与其中,前后的巨大反差使政、学两界及舆论界对该问题的法理属性展开争论。
袁世凯曾被问及对国体讨论问题的态度,其认为“共和原理,本当集大众之心思才力,以谋大众之安乐幸福,此等开会讨论之举,于共和原理初不相背,何从横加干涉乎”,另外“此种研究之举,只可视为学人之事,如不扰及秩序,自无干涉之必要也。”[27](P6)检察厅、肃政厅等法律监察机关为迎合袁世凯的意图亦对此事漠然视之。
君主论者对该问题的态度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如单纯从学理上来讲国体讨论是一种学理的研究,与实际政治无关,因此“研究学理与变更政体,二者不能并为一谈。若谓政体之良否,无研究之余地,则世界各种学说,又将从何发明”[28](P14)。其二,国体讨论既然为学术研究,则“按之约法,人民言论自由,与法律尚不为抵触”[29](P9),况且我国现存法律本身即是有问题的,如“《临时约法》既非出于全国人民之本心,不过少数党人之私意,且任意改易,狡诈欺罔,久失大信,故无所谓破坏也”[30](P11)。那么在旧宪法(指约法或宪法草案)和国体不合理而新宪法(指正式宪法)未拟定之时,“讨论国体以发表民意,自为正当,并无与约法抵触不抵触之可言”[21](P18)。其三,讨论国体是各国之通例,在西方民主国中其称道君主者不知凡几。[31](P99)所以“以各国久经确定之政体,固容人比较优劣,何以我国政体,独无讨论之余地耶,理想之优劣,即有理想之取舍,何能止人之多言耶?”[32](P134)其四,国体讨论是我国当今时势的必然要求,当前共和制度已显露诸多弊端,而作为国民,其对于国家“既负纳税当兵之义务,即应享受国家保护之权利”,倘各界学人能“参预其间,互相印证,无论国体如何,能顾念国情,引伸民权,就过去成绩检点比较,适者留之,否者更之”,[33](P81-82)将有利于国民。
多数共和论者与君主论者持不同意见,他们首先认为国体讨论是不合法的。虽然君主论者一再强调讨论国体是学术行为,但此前《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第四款曾明确规定“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12](P381),然其“法律范围内”概指“凡所集之会,所结之社,皆必在法律范围以内”,因此筹安会公然讨论国体显然已逸出法律范围并与宪政正义相违背。[34](P143-144)又《报纸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淆乱政体者报纸不得登载”,否则“禁止其发行,没收其报纸及营业器具,处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以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35](P729-731),更加说明国体是不容任何人和媒体置喙的。除此之外,有人指出1914年11月24日袁世凯曾申令,“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36],基于此,有人认为检察厅等司法机关应对筹安会的行为加以制止,否则“法之不存,国何以立”[37](P7)。更为甚者,“言论为事实之母,鼓吹即实行之媒,涓涓不绝,将成江河”[38](P15),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从法律条文上给予有力反驳,共和论者还就国体的事实利害等进行分析,指出议更国体可能引发国内革命并给列强以可乘之机。章士钊即认为筹安会谈论国体“正与革命为媒”[39];梁启超则认为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一则国体非政论家所能左右,二则擅议国体会破坏原来已有的政治基础而建立与国情不符的政治体制遗患无穷。徐佛苏也同样认为,对于政体人民可以自由讨论,而国体只有在国家经历革命而新国体未建或全国民意机关应时势要求而不得不为国家谋生存时,方可议更,除此之外“无经讨论改变国体之余地”,中国“今日既无大革命大变乱之事实,又未闻以特种法令组织代表全国民意机关”[40](P19),因此筹安会以少数人之集会公然倡议变更国体与民意相违背,与倡导革命无异。
在关于国体讨论的合法性问题上还有论者提出与君主、共和论者均不相同的观点,指出国体讨论并没有合法不合法之分,只是该问题“无讨论之价值也”[41](P108),当前中国的急务应是发展国力,增强国民文明程度等关乎国家存立的事宜,若“惟就国体形式讨论,无论变更若何,终不能脱贫弱之苦境也”[41](P108)。李佳白则认为,国体讨论中万不能掺杂些许个人私利和政治压迫及暴力钳制等手段。换言之,君主论者要细察反对者之词意及全国人民之趋向;共和论者则要允许各方之提议不能行革命之举动。否则“此事发现之日,即为日本又得进步之时。其下焉者,必以扶助同志重立共和为名,直演辛亥革命之举;其上焉者,且必以保护政府代平内乱为任,偿其实行干预之私”[42](P25),所以,国体能否讨论的关键在于是否对中国当前和未来政局发展有益。
可见,在国体讨论的合法性问题上,各位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论证,目的是借此来支持自己对于国体变更的态度。尽管如此,多数论者在讨论中利用西方最新的政治理论和法理常识对中国的现实利害问题进行分析,充分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学人虽政治智识还不成熟,但已认识到宪政的重要性,其对中国当前局势的思考和关怀值得后人肯定。
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处在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宪政过渡的转型期,在中外思想激烈交锋和共和体制不稳的大环境下,各界学人围绕国体政体的概念、国体讨论的合法性等基础学理性问题展开讨论,为国人进一步明晰国体问题的本质及其法理属性起到了启蒙作用,同时为各位论者进一步展开有针对性和逻辑性的关于君主还是共和更适于中国的思想辩论奠定了基础。国体讨论虽最终演变为一场袁世凯伪造民意的称帝运动,然而讨论本身所包含的学理性及其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使其在民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1]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刘晴波.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A].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三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一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序言).
[6]公丕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A].盾鼻集(第二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1917-12(四).
[8]邓丽兰.君主与共和:国体之争的再认识——以《甲寅》、《新中华》为中心的考察[A].刘泽华,罗宗强.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A].戴昌熙.日本宪法义解[M].上海:金粟斋译行,光绪辛丑年.
[10]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2013,(3).
[11]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2]陈荷夫.中国宪法类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文集之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国体问题之疑问[N].时事新报,1915,(8):24;国体与政体[N].国华报,1915,(8):21.
[18]秋桐.复辟平议[J].甲寅(1卷5号),1915,(5):10.
[19]剑农.国体与政治(上)[J].新中华(1卷4号),1916,(1).
[20]圣心.国本[J].新中华(1卷4号),1916,(1).
[21]国体问题之面面观[A].鹤唳声.最近国体风云录[M].“国体类”(杂录).[出版者不详],1915.
[22]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A].侯宜杰.梁启超文选(注释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3][美]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A].古德诺.解析中国[M].蔡向阳,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24]张东荪.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A].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二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25]汪馥炎.国体最终之评判[J].甲寅(1卷10号),1915,(10):10.
[26][日]副岛义一.评古德诺氏国体论[J].余生,译.新中华(1卷2号),1915.
[27]大总统对于筹安会之意见[N].亚细亚报,1915-8-16.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一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28]筹安会之要闻[N].民视报,1915-8-18.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一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29]筹安会与古德诺之主张.民视报[N].1915-8-17.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一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30]杨缵绪王建忠杨增炳致筹安会书[A].鹤唳声.最近国体风云录[M].“国体类”(函件).[出版者不详],1915.
[31]林卜琳.有不满意筹安会者乎[A].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二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32]某报之时评[N].亚细亚报,1915-8-13.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一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33]刘艺舟.我之筹安会观[A].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二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34]竹冠.讨论国体之先决问题[N].天民报,1915-8-18.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一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35]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校内用书,1980.
[36][民国]政府公报·命令[R].1914-11-24.
[37]李诲告发筹安会之原呈[A].1915-8-18.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二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38]梁觉弹劾筹安会原呈[A].1915-8-20.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二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39]秋桐.帝政驳义[J].甲寅(1卷9号),1915,(9):10.
[40]徐佛苏对于筹安会之意见[A].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二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41]中国之无诚意说[N].日文新支那报,1915-8-26.南华居士.国体问题(第二册)[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5.
[42]李佳白.论变更国体问题之影响[A].鹤唳声.最近国体风云录[M].“国体类”(外论).[出版者不详],1915.
(责任编辑 梅焕钧)
An Initial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Logical Basis of Discussion of State System in 1915
LIYunbo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Humaniti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Discussion of suitability of Chin's state system between constitutionalmonarchy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in 1915 was a great event in Chinese history.To bolster up their case,scholars of all areas focused on the theoretic-logical basis to explore such as the concept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system and legitimacy of the discussions.Although the politicalwisdom of commentators'knowledgewas notmature and they even disagreed on the issue,they were all aware of the use of advanced political theory in theWest and the knowledge of jurisprudence.Consequently,their discussions laid the deep foundation for people to further clarify the nature and legal property of the state system,so that,the others could also carry out targeted and logical debates.Commentators'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political reality and concern for China's future and destiny enlightened people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iscussion of State System;Government system;Monarchy;Republic
K06
A
1672-2590(2015)05-0100-06
2015-08-09
李云波(1986-),男,山东泰安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3级专门史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