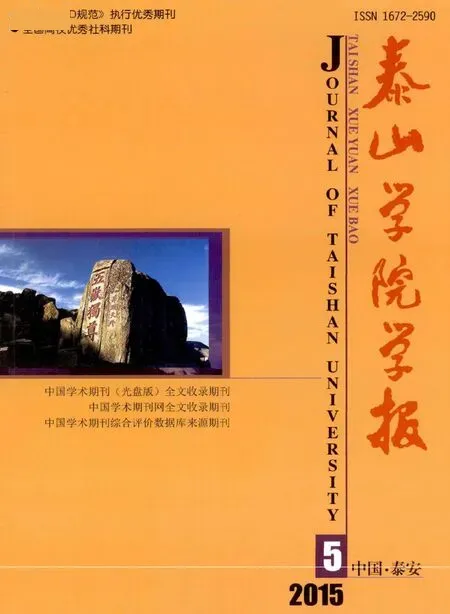泰山国家祭祀史论
刘兴顺,姜亭亭
(1.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泰山研究院,山东泰安 271021;2.泰山中学,山东泰安 271000)
泰山国家祭祀史论
刘兴顺1,姜亭亭2
(1.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泰山研究院,山东泰安 271021;2.泰山中学,山东泰安 271000)
五岳之首的泰山在传统社会国家祭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泰山国家祭祀肇始于先秦。西周建国之始,即展开泰山祭祀。随着西汉郊祀礼的改革,元始五年,泰山作为天下山岳的唯一代表,首次从祀于国家南北郊祀,这标志着泰山超越了地方性,成为国家山岳的代表性符号。从此,泰山国家祭祀形成了泰山所在地与京城两大系统。京城国家泰山祭祀包括从祀于郊祀、腊祭百神、专门祭祀等,所在地国家祭祀包括每年定期的常规祭祀与国有大事、遣官告祭等非常规祭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1928年,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神祠存废标准》,废止五岳四渎、碧霞元君信仰,泰山国家祭祀才明确画上了句号。
泰山;国家祭祀;所在地;京城;历史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祭祀对国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山岳祭祀又是传统社会国家祭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众山之首的泰山,更是国家山岳祭祀中的重中之重。
所谓国家祭祀,詹鄞鑫认为,它是与道教和民间(包括少数民族)遗存的“在野”的宗教相对立的“在朝的宗教”。“它具有严密的制度和大体不变的承传,并与国家的政治礼制合为一体,是一种‘国家宗教’,我们称之为‘正统宗教’。”[1](P4)
作为与民间祭祀相对立的概念,从内涵上看,国家祭祀是指纳入国家祀典的正祀。郑丽航认为,“‘正祀’是指获得官方承认的祠神或祭祀活动,纳入官方祭祀体系的神祇即称为正祀之神,而没有获得官方承认的不合法的祠神或祭祀活动,即‘淫祀’。官方对祠祀之神的承认方式有两种:一是纳入祀典;二是由朝廷进行赐额或封号。……祀典包含两层含义,一指记载祭祀仪礼的典籍,二即祭祀仪礼。”[2](P583)
从外延上看,雷闻认为,国家祭祀是指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其中既包括由皇帝在京城举行的一系列国家级祭祀礼仪,也包括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因为相对于民众而言,地方政府本身就代表国家。[3](P3)
据此,我们将泰山国家祭祀定义为,指传统社会中,与民间社会祭祀泰山相对立的、纳入国家祀典的祭祀泰山礼仪,主要包括泰山所在地政府、皇帝遣使至泰山所在地、京城皇帝举行的祭祀泰山仪式活动。
泰山国家祭祀,从祭祀地点看,分为本地(所在地)泰山祭祀和京城(非所在地)泰山祭祀;从祭祀的周期性看,分为常规祭祀与非常规祭祀;从祭祀的方式看,有专祀,有从祀;从承祭者看,有皇帝亲祭,有遣使致祭,有所在地有司致祭等。本文将对所在地泰山常规与非常规国家祭祀,以及非所在地京城泰山专祀与从祀等内容进行梳理考论。
一、先秦泰山国家祭祀
泰山国家祭祀起源于先秦。从先秦文献看,先秦时期的泰山称“泰山”、“太山”、“大山”、“岱山”、“岱”等,而不称岳。直到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宣帝颁布山川祭祀制度,《汉书·郊祀志》载:“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4](P1034)才开始称泰山为东岳。所以,先秦时期,泰山并不称岳或东岳。
先秦时期的泰山国家祭祀,西周以前无载。西周建国之始,即行泰山祭祀,并在泰山下设诸侯的汤沐邑以助祭泰山。表明泰山在西周时,已经属于中央祭祀的山岳,地位与价值自然显赫。而随着周天子的衰微,中央已无力对泰山进行祭祀。周桓王五年(前715),“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5](P58)标志着周天子泰山祭祀活动的终结。
春秋初年,虽然周天子泰山祭祀活动中断,诸侯国的泰山祭祀并未停止。泰山在鲁国境内,鲁国因其特殊的身份而拥有泰山的祭祀权。而春秋战国之时,频繁的战争导致泰山的管辖权多次易手,因泰山具有巨大的文化与政治影响,经常占领泰山的齐国,以及后来灭掉鲁国的楚国,都曾对泰山进行祭祀。
这一时期,泰山神形完成了从最初的自然神灵、至早期的半人半兽、到春秋以后的人格化的神灵形象转化。祭祀泰山礼仪采取了设尸、塑像以像泰山神形的方式,其牺牲制度散见于《山海经》等典籍。《山海经·东山经》所记载泰山祭祀,是以血祭的方式祭祀泰山神,以“人身龙首”的偶像为泰山神形。
先秦时期泰山祭祀礼仪,是建立泰山信仰基础之上的,前者为外在的果,后者为内在的因。通过对诸子百家对泰山认识的考查,我们看到泰山的意义丰富多元。泰山作为宏大比喻的喻体,显示出极重、极高、极大、极厚的含义;泰山是山岳中出类拔萃者,负载了特殊的政治与哲学含义,是象征永恒不变的道的宏大载体,是神灵的家园;而且泰山与高天并列,成为天子君主的隐喻;泰山封禅观念的出现,更加突出了这样的认识与信仰。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泰山国家祭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建立起秦帝国。汉高祖五年(前202),西汉代秦,继续着统一帝国的建设。秦汉都努力建设大规模统一的国家,他们都采取了郡县制的行政制度,不同的是汉初继续实施分封,郡国并行。秦汉帝国通过思想、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的建设,构筑大一统的观念文化。
秦汉时期,从所在地的泰山祭祀看,秦时太祝致祭;高祖六年(前201)后,由齐地诸侯国祭祀泰山;文帝十六年(前164),收回名山大川的祭祀权,泰山回归国家祭祀;宣帝神爵元年(前61),确定了山川祭祀制度,皇帝派遣使者持节至泰山侍祠,泰山在国家山岳中祭祀规格最高,每年分春、夏、秋、冬、腊五次祭祀,从此,确立了泰山在国家山川祭祀体系中的首山地位;到东汉时,随着光武帝刘秀省减礼俗,祭祀由每年五次,调整为三次,承祭者也由皇帝使者改为泰山郡太守,泰山祭祀更加方便、稳定。
从秦汉时期国家祭祀体系来看,秦时的泰山祭祀局限于所在地,并未进入雍地郊祀系统,汉初仍然如此。西汉末期郊祀礼改革,平帝元始五年(5)的南北郊祀中,泰山因其特殊的地位,在众多的名山之中遴选出来,作为天下山岳的唯一代表从祀于南郊合祭天地、北郊祭地。这表明泰山从一个地方性的山岳,转变为超地方性的山岳代表符号,进入国家的郊祀之中。在长安的五部郊兆,五方山川各因其方从祀,泰山自然从祀于东方帝太昊。
从此以后,泰山国家祭祀形成了所在地与京城两大系统,一直延续到清代而不变。京城泰山国家祭祀的出现,的的确确是泰山祭祀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自从成为郊祀的对象后,五岳以及那些名山便跨越了地域限制,成为政权存在的一种合法性体现”。[6](P80)五岳之首的泰山,突破了以往的区域性限制,进入到国家郊祀的“万神殿”,成为此后历朝历代政权政治合法性的神圣政治与宗教来源。
东汉光武帝刘秀继续元始故事,在南郊与北郊礼仪中,泰山之外的其它四岳也开始超越其区域性,从祀于京城郊祀中营。同时,泰山从祀于五郊在东汉继续延续。
在按照儒家理论设计的郊祀中,泰山祭祀形制依照木主的神形与坛祭的方式从祀。这种郊祀化的泰山祭祀形制,对所在地泰山偶像化庙祭的形制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所在地泰山祭祀出现了坛祭与庙祭相混合的祭祀形制,也拉开了延续近两千年的泰山祭祀形制争议不休的序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大动荡、大融合时期,也是极易产生新文化现象的时期。这一时期,长期分裂混战,北方民族混战,南北对峙。泰山郡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更替频繁。这样的时势,促使泰山祭祀闪现出新的色彩。
从所在地泰山祭祀的角度来看,因时局动荡不已,所在地泰山常规祭祀难以持续。梁满仓认为:“国家祭祀山水需要如下几个条件:第一,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地域版图,或者起码有相对统一的地域版图。第二,国家必须有一套稳定的礼仪制度体系。第三,国家必须有稳定的社会环境。”[7](P206)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段,确实缺乏如梁满仓所言的三个条件,导致所在地泰山常规祭祀很难、乃至无法正常展开。
既然泰山常规祭祀难以正常展开,临时的非常规祭祀就成为各个政权的最好选择。只要时间、地点、机遇合适,就要进行及时的泰山祭祀。这一时期,所在地泰山祭祀更多的是非常规的帝王亲临祭祀、遣使致祭、祈祷雨晴之祭等,这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不绝如缕。
与所在地泰山祭祀相比,这一时期,非所在地泰山祭祀要丰富得多,制度建设也较为完备。非所在泰山祭祀主要有如下几种:(1)在泰山所在地之外为泰山立庙祭祀,如北魏五岳四渎庙;(2)从祀于京城祭地,如东晋、宋、齐、梁、陈等;(3)从祀于五部郊兆,如北周;⑷皇帝即位致祭,如曹丕即位阼燎东岳;随政权所在地而多处并存,或随首都转移而连动,成为这一时期非所在地泰山祭祀的突出特点。
时代多难而泰山祭祀不绝,是因为两汉以来,泰山等五岳列在祀典,尤其是西汉末年以来,泰山等五岳从祀于京城郊祀,使泰山从一座区域性的山岳演变为超区域性的山岳,从而成为政权合法化的神圣来源。这一时期,泰山等五岳从祀于郊祀的传统更加深入到不同政权的政治与国家版图意识。“祭祀山水还具有版图领有的象征意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远长于统一的时期,其中北方分裂的时间最长。在国家祭祀的众神中,南北各有自己的体系……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个体系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双方都有的,如五岳、五镇、四渎。另一部分是双方各自独有的……五岳、五镇、四海、四渎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早已确定的山水祭祀神灵,祭祀体系中没有他们,不足以表明其继承先人的正统性。”[7](P216-217)西汉末年创立的京城泰山祭祀礼仪制度,也直接为这类泰山祭祀提供了模版与范式。在这样的局势下,随皇都而转移的泰山祭祀既合乎传统,又相对稳定与方便。
这一时期,泰山无疑为华夏的统一和凝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的山岳符号。虽然政局纷争,相互分裂,不同政权不管是否真正占有泰山,不约而同,甚至是争先恐后地祭祀泰山,显示了他们的共同追求:拥有泰山等五岳的祭祀权力,以向天下宣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三、隋唐五代泰山国家祭祀
隋代是泰山国家祭祀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对泰山祭祀制度多有开创。首先,设岳令管理东岳庙,从而把泰山管理纳入政府行政的体系。其次,将从祀于五部郊兆的泰山等五岳,改为迎气日遣使至所在地致祭。遣使之制是对西汉“使者持节侍祠”之制的恢复。第三,在泰山庙为泰山神设像,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对泰山神像加以保护。自然就宣布了泰山神像脱离郊祀化的影响,人格化偶像致祭合法化了。最后,随着三祀制度的确立,隋代也明确了从祀方丘的泰山为中祀。
唐代所在地泰山常规祭祀在隋代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开创了泰山封爵制度。首先,唐代继承了隋代创立的立春年别一祭泰山的制度,同时又特别要求与京城东郊迎气之祭同时进行,更加明确了所在地泰山祭祀对京城望祭泰山的取代。
其次,常规祭祀祠官由隋代的遣使,改为本地守土官员,这实际上是对东汉之制的恢复。
第三,国家对泰山祭祀的管理更加规范成熟。以岳令常驻地方,辅之以祝史、斋郎,对东岳祠进行日常管理。有公廨田补充公用,有职分田供俸禄,从而使东岳庙得到良好的管理。为泰山祭祀奠定了扎实的物质保障基础。
第四,唐代将所在地泰山祭祀列入中祀,使所在地泰山常规祭祀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等级规格更加明显突出。与其它中祀相比,受时间地点等条件影响,祭祀时不用乐。
第五,唐代开创山川封爵,“五岳视三公”的人神比喻,被山岳封爵的方式,演化成了现实,山岳自然神深染人格神的色彩,从而引发了泰山等五岳册祝制度的改变。泰山神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并且表现出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这些改变,虽然没有贯穿有唐一代的始终,且对唐代正规的官方泰山祭祀影响有限。但它毕竟是对传统泰山祭祀之制的有力挑战,而且其巨大影响,至宋元时期仍然延续。
最后,《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国家祀典,在历史上首次细致而精确地记载了泰山常规祭祀仪式程序。从《大唐开元礼》泰山祭祀仪注看,仍然要求泰山所在地以坛祭的方式祭祀泰山。实际上,隋代泰山所在地祭祀已经采用了偶像化庙祭的形制,且得到法律保护,唐代泰山所在地祭祀形制也以此为主流。所以祀典的要求与现实的祭祀实践有着重大的冲突,面对这种现实,此后改变国家祀典,有条件地对这种现实形制予以接纳。贞元九年(793)颁布的《大唐郊祀录》就规定:“近代修庙宇,为素象,则就祭之,今准礼,但设一坛位,为图其形,余推之即可悉也。”[8](P787-788)表明唐代偶像化庙祭泰山形制已经成为大趋势,倒逼国家祀典不得不进行改变。而且唐代山川封爵,御署祝版的争论,更加助推和强化了泰山神人格化偶像庙祭的现实。
除常规的泰山祭祀外,唐代帝王也会随时遣使致祭泰山。所谓国有大事,必告泰山,已经形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干旱时节,祈雨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五岳之宗的泰山之神是重要的祈祷对象。唐代的所在地非常规祭祀,使泰山成为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的纽结点,通过祭祀泰山等岳镇海渎的仪式活动,既是向神灵报告,同时也可以“布告遐迩,咸使知闻”[9](P989)。这样,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泰山等岳渎与国家同喜同忧,在国家宗教领域与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唐代京城的泰山祭祀,包括从祀方丘、合祭蜡百神、时旱祈雨等形式,由于有《大唐开元礼》的存在,我们得以窥其全貌。
汉代以来,泰山就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道教名山。唐代以前,道教与泰山虽然关系密切,其行道活动并不在国家祀典。唐代道教成为国家宗教,唐玄宗御敕编撰的《唐六典》,将道教斋醮列为国家祀典,道教参与泰山国家祭祀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开元十九年(731),是泰山祭祀史上非常重要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泰山祭祀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道教虽于泰山多次行道,但其斋醮的主神显然是天尊、老君等道教大神。如果说有醮祭泰山的成分的话,只是在其中的礼忏科仪中东岳神灵才会得到敬奉。当然其中也有五岳醮、供养岳灵等以泰山为主神的醮祭活动,但毕竟是支流而非主流。所以发生在岱岳观等处的泰山行道,应称之为行道于泰山比较合适,其与醮祭泰山虽有关联,但只不过是道教“国家保安宗社,金籙籍文,设罗天之醮,投金龙玉简于天下名山洞府”[10](P9703)的常规性科仪而已。
而开元十九年,玄宗接受道士司马承祯的主张,敕令五岳各立真君祠庙。道教借助皇帝之力,通过否定传统五岳祭祀的非“正真”性,最终设计出了自己的五岳祭祀系统。这一系统包括确立五岳真君、建立五岳真君祠、按时醮祭等。此后,泰山祭祀就有了传统祭祀与道教醮祭两个系统,并且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对后世的泰山祭祀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平元年(907),后梁朱温代唐称帝,拉开了五代(907-960)的序幕。这一时期,基本上延续了唐代的泰山祭祀制度。其中最大的亮点,当属延续唐时的山川封爵事项。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封泰山三郎为“威雄大将军”,并立庙祭祀。这是国家祭祀中,泰山神圣家族出现的第二位成员。这昭示着泰山神开始走向家族化、人格化甚至世俗化。泰山三郎的封号来自于泰山神向唐明宗的祈求,显示着泰山神从被祈请者,演化为祈请者,其神圣性、纯洁性正在慢慢丧失。
四、北宋泰山国家祭祀
建隆元年(960),宋受周禅,后周之州县尽入宋。北宋泰山所在地常规祭祀继承了唐代传统,如立春祭祀泰山、以地方长吏为献官、祭祀不用乐等,又有较为明显发展变化。
首先,自太祖至英宗时期,视泰山等五岳为大祀,这在泰山祭祀史上绝无仅有,显示出对泰山等五岳的重视。熙宁四年(1071)之后,国家开始于京城望祭山川,而泰山所在地常规祭祀则参照中祀的规格进行。直到元丰三年(1080)以后,京城与泰山所在地的祭祀才全部复归中祀规格。
其次,泰山祭祀中首次出现了用香的记载,包括常规祭祀、非常规遣官致祭。
再次,北宋时期延续着唐代以来的封爵制度,自真宗开始,对泰山神不断加封,由唐代的天齐王,到天齐仁圣王,再到天齐仁圣帝。而且北宋的加封惠及泰山神夫人及其子嗣,从真宗至哲宗,为泰山神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神圣家族。
此前争论不休的人格化偶像庙祭泰山的形制,成为北宋时期所在地泰山国家祭祀的正制,《宋史》明确记载了泰山神人格化偶像化衣着神形,北宋国家祀典《政和五礼新仪》载:“立春日祭东岳泰山于兖州界。前享三日,有司设行事执事官次于庙门外,前一日,掌庙者扫除庙之内外,其祭器左十笾,右十豆,祭献于堂上行礼。”[11](卷96)表明北宋已经非常明确地将庙祭泰山载入国家祀典,而不再像唐代那样,遮遮掩掩地以坛祭作表面文章。并且从北宋祭祀泰山的祝文来看,用“皇帝某”取代了唐代“子嗣天子某”的称呼,即用人格神的称呼替代了天地自然神的称呼。这一切,更加清楚地显示着,北宋时期所在地泰山祭祀已经完全摆脱了郊祀化的祭祀形制,回归人格化偶像庙祭。
这样的祭祀形制必然招致理学家的极力反抗,陈淳也正是从人格化偶像、庙祭这两个方面,对当时的泰山国家祭祀予以批判。但正是这样的批判,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北宋时期泰山祭祀的突出特色。
北宋的东岳庙维护中,四方人士的施利供奉占据重要地位,经济是社会中极其重要的话语力量,这必然导致东岳的常规祭祀对民间力量的依赖,依赖越大,国家对泰山祭祀的影响力就越小,这样,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双向交融之中,泰山常规祭祀的形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郊祀化的形式终于让位于人格化偶像庙祭形制。
北宋所在地泰山非常规国家祭祀主要包括国有大事之祭告与水旱祈报于泰山。如果说常规祭祀是一种固定的程式化的规律性的仪式,那么非常规祭祀则是一种非固定化无规律的仪式活动,通过对它整理,更能体现出这一时期国家的重大事项,如郊祀活动、军事行动、黄河水情、帝王身体状况,尤其是于泰山所在地的祈晴祈雨活动,更可见北宋时期的气候与灾异状况。
北宋水旱祈报泰山的制度有许多创新之处。与泰山有关的水旱祈报有六项:(1)京城会灵观(又称五岳观、集禧观)、(2)京城岳镇海渎坛、(3)东京天齐仁圣帝庙、(4)东岳庙、(5)会真宫、(6)东岳真君观。其中前三项为京城,后三项为泰山所在地。泰山所在地的水旱祈报,既有儒家的传统形式,也有道教的斋醮科仪。如太祖建隆四年(963)五月一日,“以旱,命近臣祷天地、社稷、宗庙、宫观、神祠、寺,遣中使驰驿祷于岳渎。自是凡水旱皆遣官祈祷,唯有变常礼则别录”。[12](P734)北宋一朝的自然现实,与国家祀典的规定结束在一起,造成了北宋一朝泰山祈晴祈雨活动频繁举行,泰山成为国家风调雨顺的重要信仰保障。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泰山与国家的重要政治宗教的关系之上的。
与前代相比,北宋一朝京城泰山国家祭祀继承中有变化,更有创新。五岳观的创立、天齐庙的设立、从祀于南郊、明堂、设坛望祭岳镇海渎等,都是北宋独具特色的京城泰山祭祀。
具体而言,随着“宋真宗封禅泰山,敕天下建行祠”,[13](卷下)全国各地纷纷立东岳庙,京城也立东岳天齐仁圣帝庙。与其它东岳行宫相比,天齐仁圣帝庙位列中祀,是泰山祭祀史上首例列入国家祀典的京城东岳庙,成为国家重要的专祀泰山场所。
神宗元丰三年(1080),将隋代下放所在地的五岳祭祀,重新收回京城,在京城四郊立坛望祭五方岳镇海渎。并且将西汉末以来,五方岳镇海渎从祀于五部郊兆之制,改变为单独祭祀岳镇海渎,有着较大的发展创新。
北宋国家最高等级的三种祭祀形式:冬至南郊合祭天地、季秋明堂大享、夏至北郊方丘,泰山都从祀其中。尤其从祀方丘,泰山等五岳的地位不断提升,其神位由最初的内壝之内,至绍圣四年(1097)升格到坛之第二层,崇宁二年(1103)又提升到方丘坛之第一层,显示着泰山神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逐步提高。
合祭于蜡百神与唐代相比也有新的变化,从最初的合祭蜡百神于南郊,至元丰时期四郊各为一坛,泰山从祀于东蜡。
自秦汉以来,五岳列在祀典,为国家祭祀之重要神祇;五岳也为道教的名山灵地,有着自己的祭祀体系,两类祭祀系统一直各行其是。祥符五年(1012),在京城设五岳观,在五岳道教与国家祭祀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东京开封五岳观,以五岳之神为奉祀主体,其与五岳所在地国家祭祀的五岳之神有着明显的一一对应关系,在其所在地祭祀时,五岳之神是按儒家或准儒家的祭祀理论进行的,而宋真宗将它们集中到京城后,归入道观,成为灵宝天尊的下位神,纳入道教神系。表明儒教与道教的五岳神同时为国家接纳,并在京城五岳观将儒道二教之神合二为一,实现了道教与儒教传统五岳神的首次完美融合。
此举与两汉将泰山等五岳从祀于郊祀极为相似。汉平帝元始五年(5)郊祀中,泰山作为山岳的唯一代表首次进入了国家郊祀系统。北宋五岳观的设立,则是将儒教化的所在地五岳神移至京城,将其纳入道教系统,同样是五岳祭祀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件。
因朝廷着力于将泰山神向着道教化神祇转换,而且传统泰山神因历史的积累,其影响力非司马承祯所创造的五岳真神可比。北宋时期,所在地东岳真君虽然仍被国家按礼祭祀,但其影响力衰退则是不争的事实。宣和四年(1122),大梁李氏以民间之力,在青帝观后创设真君殿,如果国家重视东岳真君,怎能容民间染指同地重建。至于东岳真君观史书少有记录,以至连其宫观原址都无从追寻,就可以理解了。
五、南宋金元泰山国家祭祀
靖康二年(1127)四月,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也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即皇帝位,改称建炎元年。十月,高宗至扬州。从此偏安江南,是为南宋。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金人攻破袭庆府(今兖州),泰山为金占领。
葛兆光认为:“一个体现权力的‘政府’也有三种形式,一依靠宗教或传统的力量建立金字塔式的结构,二是依靠武力行使其控制力,三是依赖一种真理或理想式的东西产生和维持民众对它的认同。然而,在古代中国,这三种统治形式也是政治动作中同时被使用的……所以,每一个古代中国王朝,都经由天地宇宙神鬼的确认、历史传统与真理系统的拥有和军事政治的有郊控制与管理,它才能获得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就是皇室、士绅与民众暂时的‘共识’。”[14](第2册,P268)
被金人压迫于南方的南宋政权,虽然丧失了大片土地,但为了表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宗教建设上表示出自己的政权来自于正统的北宋,不遗余力地把北宋的祭祀制度全部照搬到南方行在。
具体到泰山祭祀,南宋政府几乎将北宋的泰山祭祀全部继承过来,如从祀于南郊合祭天地,如从祀于明堂大享,如合祭于蜡百神等。至于其中的无奈之处,如泰山不在其境,为道路未通去处,不可能赴其所在地致祭,则采取了变通的方法,如望祭,如至行在的东岳行宫致祭祈祷等。继续坚持着对泰山的祭祀权,并且在祝文中表达了这种无奈选择的充分理由。如“王略未复,柴燎莫亲。肃瞻岩岩,神岂予远”,[12](P638)如“虽道路之未夷,扣威灵而敢告”,[15](第822册,P142)如“矧惟方望之祠,曾是封疆之阻。敢告成于熙事,冀垂鉴于遐悰”,[15](第822册,P146)表达泰山神祇虽不在我南宋境,不能亲自至其所在地祭祀,但岩岩泰山,仍然是南宋的守护之神。南宋对泰山神的祭祀,继承远大于创新,即使有所改变,也只是迫于现实的无奈而已。
金代于收国元年(1115,徽宗政和五年)建国,天会三年(1125,徽宗宣和七年)灭辽。天会四年(1126、钦宗靖康元年)攻陷东京。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金人攻破袭庆府(今兖州),泰山为金占领。至1234年为蒙古所灭,国祚一百二十年,其中与南宋对峙百余年。
金作为北方之游牧民族,以武力入主中原,并与南宋对峙,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表示自己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金人尽携北宋礼乐典章北去,可见其早有准备,于是大定年间改造了拜天习俗,并宣称自己“据天下之正”,采取中原传统的南郊合祭天地等礼仪制度。同时,金人对五岳等文化资源亦加以充分利用。首先,他们关注到中原文化历史形成的五岳乃王权正统性地理认同的标志,所以拟通过重新更改五岳的方式,将燕京纳入五岳空间之内,虽然未能实施,却颇显其用心。其次,金人高度重视五岳祭祀,认为方岳之神,是国家的依靠。于是展开了对泰山等五岳的常规与非常规祭祀,包括立春祭泰山于泰山所在地、国有大事祭告泰山、祈雨祈晴于泰山、泰山从祀于南北郊等。可以说,金代全面接受并实施了唐宋泰山祭祀的制度。其理由,正如金世宗完颜雍所说:“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16](P452-453)金人正是通过全盘接受唐宋以来的山岳祭祀制度,与南宋分庭抗礼,并向天下宣示,自己才是天下的正统。
当然,金代的泰山祭祀也有了新的发展。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将东岳真君纳入东岳庙,附祀东岳天齐仁圣帝,并且让道士住持东岳庙,使泰山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道教化宫观化色彩。这显然是受北宋五岳观的影响。
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多次攻占泰安。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东平严实率领泰安,彻底归降蒙古。泰山为蒙古国拥有。
海迷失后元年(1249),蒙古国首次祭祀泰山,此后派遣道士代祭泰山,这在泰山祭祀史上确实是开一代之风气。此前,虽有金人以道士住持东岳庙之举,但毕竟只是岳庙的日常管理者。蒙古汗此举,显示了宋元之时,随着全真道等道派的影响逐渐强大,道教对泰山等五岳国家祭祀进行了深入地渗透,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由蒙古汗开创的派遣道士代祭泰山的做法,对元代代祀泰山等岳镇海渎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是元代代祀制度的萌芽。
由金人以道士主持管理东岳庙,至蒙古国以道士代祭东岳之神,所在地泰山国家祭祀的传统祭祀特点逐渐乃至完全淡化,而道教化特点得到充分放大强化,东岳庙道教宫观色彩更加浓厚,并成为道教著名宫观。一般人甚至有的学者以为东岳庙为道教奉祀东岳大帝之处,当发端于此。
元代东岳泰山的祭祀分为使者代祀与有司常祀两类。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的惯例,正式建元“中统”,含义为中原王朝正统,忽必烈以此年号,表明自己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在建元中统诏书中,忽必烈指出自己的王朝,“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17](P43)“这两种表述的前半部分指要继承蒙古的祖制,后半部分则申明要改采汉官仪文。元朝的制度,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传统的仪文制度为主干,参考辽、金制度,而又糅合并保存了大量蒙古旧制的成分而成的”。[18](P267)蒙古国时期,对岳镇海渎的祭祀主要由皇帝派遣道士至所在地致祭,此为岳镇海渎祭祀之列圣洪规,而传统王朝祭祀岳镇海渎,则采用派遣使者岁时致祭的方式。可以认为遣使致祭的代祀,相当于继承蒙古的祖制,而由所在地守土官主持的常祀,则为采用汉官仪文。所以,世祖初期,即将泰山等岳镇海渎之祭祀定制为二。
世祖中统二年(1261),确立了元代特有的遣使致祭岳镇海渎的代祀制度。每年按例降旨,分道遣使持皇帝诏书、香、幡、币等礼物至岳镇海渎所在地代表皇帝致祭,使者一般由重臣、名儒、习于祭祀的道士等构成。元代将前代的非常规的特定祭告祈祷也纳入了代祀,我们将其称之为非常规代祀,泰山属元代分道代祀之东道。
与蒙古时期多以道教醮祭的方式代祀岳渎不同,这一时期,除以道士为主要使者的代祀一般采用道教科仪外,大量采用传统三献、牺牲血祭的祭祀形式,这显示了传统泰山祭祀的强大生命力,也表现了元代帝王对传统祭祀仪式的接纳与认同。由金代道士住持东岳庙,到蒙元时期以道士为致祭泰山使者,开启了一种崭新的遣使致祭泰山的方式。
元代延续了唐代以来的山川封爵制度,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加封泰山为“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从代祀祝文看,其称呼为“嗣天子”,显示了元代视泰山神为自然之神,且与传统的天地神祇中祀规格相同,倍加崇敬。而五镇祝文却称“皇帝”,与此前礼仪对照,此视五镇为人格神,且属小祀系列。可见元代祭祀制度确实存在着乖异之处,也表明泰山祭祀正在走向自然神的复归过程中。这样的称呼显然与北宋不同,与唐代也异,而与金代几乎完全一致,可以断定,金代对元代泰山祭祀影响更大。
元代的泰山常祀,是由所在地有司每年在立春前土王日按时致祭。这种常祀制度虽然与前代大体相同,但元代常祀完全由守土官遵照国家祀典按时致祭,地方官员开始在泰山常祀中扮演主角,由于没有御署祝版等,皇帝的身影在常祀中始隐身或者退出,再加上每年遣使代祀的映衬,元代的常祀颇有衰落的感觉。东岳庙作为祭祀泰山的处所,在金元之际的战火中毁坏严重,至世祖时开始进行大规模地修复,而本次修复由全真道士张志纯具体负责。同时这一时期的东岳庙由全真道士为提点、住持,负责东岳庙的全面日常管理及祭祀之事。既有道士代祀东岳,又有道士具体管理东岳庙。蒙元时期,东岳庙终于成为著名道教宫观。[19](P182)
六、明代泰山国家祭祀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在《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号诏》中指出:“永惟为治之道,必本于礼。”[20](卷53,洪武三年六月癸亥)将礼制列为治国之本,并将岳镇海渎的祭祀列为礼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朱元璋对岳镇海渎祭祀的恢复与建设可谓用心颇诚敬,用力颇多,成果也颇丰富。
明人周洪谟将明代的泰山祭祀概括为五种形式:“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则遣官祭告,每岁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坛,俱有合祭之礼,盖以山川灵气有发生之功故也。今朝阳门外有前元东岳旧庙,国朝因而不废,其后岁以三月二十八日及万寿圣节,遣官致祭。”[21](卷13,弘治元年四月庚戌)即①有司春秋致祭、②有事遣官祭告、③每年南郊从祀、④山川坛合祭、⑤京城东岳庙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及万寿节遣官致祭。这五种形式,有前两类为所在地泰山祭祀,后三种全部发生在京城。
明初将自唐以来所封的泰山神爵全部废除,重定泰山神号为“东岳泰山之神”,确实是泰山祭祀史上的大事。表面看来,朱元璋去历代泰山封爵,恢复儒家传统的泰山自然神格,但却保留了偶像庙祭的形制,所以这只是一次带有明朝特色的不彻底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回到传统儒家祭祀礼制的轨道上来。
明代以遣官代祀、所在地官员常规祭祀的形式在泰山所在地展开国家祭祀。明显地体现了“明承元制”的特点。遣使致祭主祭者为皇帝,祭祀等级为中祀,且延续了御署祝版制度。地方有司每年二月、八月,在“丁祭”前一天,按国家颁布的固定仪式,诵读固定不变的祝文,体现着国家的在场。
自元代开始,将传统的所在地泰山常规祭祀一分为二,即遣使代祀与守土官常祀,前者传承了西汉持节使者侍祠、隋代遣官致祭,并将御署祝版制度存留于遣使致祭;后者则延续了东汉、唐宋所在地长吏致祭。如果说元代的改变是因为京城没有泰山专祀的无奈之举,那么明代则是因为朱元璋对泰山等岳镇海渎祭祀的高度重视。所以元明二代的守土官常祀,形似而神不似。
朱元璋实行三教并行的宗教制度,继承了元代派遣道士代祀岳镇海渎,以及由道士住持东岳庙的传统,但在继承的同时也有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代祀仪式基本上采用了儒家的血祭传统,而非像元代那样不时采用道教的斋醮科仪,即使是完全由道士充当使者的时候也是如此;明代道士更多情况下,只是奉送御署祝版、御赐香帛的使者,并不充当祭祀献官。
派遣道士致祭泰山的制度,止于隆庆朝以后。清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抑制的态度。到乾隆时,更是限制道教的活动,道教在清朝所在地泰山国家祭祀中销声匿迹了。
元代中断的京城泰山祭祀,在明代得到良好地恢复,明廷以山川坛合祭、从祀郊祀、京城东岳庙祭祀等形式展开京城的泰山祭祀
首先,朱元璋于南京城南建山川坛,将天下山川等集中于此合祭,昭示着皇帝对天下山川祭祀权力的独享,从宗教领域表示着天下教主的身份。这一制度可视为自南宋以来中断百年的京城望祭泰山等岳镇海渎制度的恢复。但时事变迁,朱元璋设计的山川坛制度与传统已经大相径庭。南京的山川合祭,从祭祀形制上看,洪武初年,合祭于城南享祀之所,没有坛壝专祀;洪武二年(1369),建山川坛,合祭岳镇海渎等地祇之神于一坛;洪武三年(1370),分坛而祭,五岳合祭于一坛;洪武九年(1376),建殿庑,五岳等祭于正殿五岳坛,与前代京城设坛望祭名山大川制度相比,可谓一大创举,也可以视为一大异例。从祭祀时间上看,洪武二年(1369),每年清明、霜降两次祭祀泰山等岳镇海渎;洪武三年(1370),调整为春季惊蛰后三日,秋季秋分后三日致祭;洪武二十一年(1388),改为八月中旬一次祭祀。其间,无论如何演变,皇帝亲自致祭泰山等岳镇海渎之制没有改变。自洪武三年(1370)至三十年(1397)二十八年间,亲自致祭四十六次,能做到这一点,这恐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帝王了。
其次,元代中断的郊祀制度在朱元璋时得到恢复,京城泰山祭祀得以重新延续。具体而言,洪武初期,天地分祀,泰山首先从祀于方丘。而至洪武七年(1374)又将泰山从祀于圜丘。直至洪武十年(1377),开始合祭天地于大祀殿,于殿宇中合祭天地,这在中国礼制史上也属首例,颇有石破天惊之感。从此每年正月中旬,泰山从祀于大祀殿,直至嘉靖九年(1530)郊祀礼改革。可以说,朱元璋为明代奠定了一百五十四年的祭祀祖制。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朱元璋创始的礼制复制于北京。嘉靖九年(1530)的郊祀礼改革,首先将山川坛更名为地祇坛,并将泰山等五岳归入地祇坛露天致祭,这是对朱元璋山川坛祭祀形制的一次修正,更加合乎儒家礼制的要求。
此后万历年间,将神祇坛改为先农坛。穆宗隆庆元年(1567)罢神祇坛祭。经过了整整二百年的历程后,这一极具特色的泰山祭祀制度在国家祭祀中消失了。
北京东岳庙是明代京城专祀泰山的祭祀场所。前已述及,元魏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北宋于东京建五岳观、天齐仁圣帝庙,已经开始了将泰山等岳镇海渎集中于京城祭祀的历程。元魏的五岳四渎庙史料记载不清,北宋五岳观属于道观,与国家正宗的儒教礼制颇有乖异之处。天齐仁圣帝庙开在京城单独为东岳神立庙且享国家中祀之先例,明英宗在北京重建元代创始的东岳庙,可以说是延续了北宋的传统。北京东岳庙,由太常寺遣官致祭,从内容到形式完整地将泰山所在地泰山神庙复制于北京。隆庆元年罢地祇坛祭之后,北京东岳庙单独承担了京城专祀泰山的重任。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完全继承南京的大祀殿合祭天地制度,泰山从祀于大祀殿合祭天地制度不变。嘉靖九年(1530),世宗进行郊祀礼改革,分祀天地,在京城北建方泽祭地。泰山等五岳从祀方泽坛之第二层。
七、清代泰山国家祭祀
“清承明制”是清朝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泰山祭祀上,明承清制的色彩甚至更重。清代泰山祭祀形式包括:(1)配享方泽坛、(2)祈睛祈雨于地祇坛、(3)京城东岳庙致祭、(4)所在有司春秋致祭、(5)时巡展祭、(6)因事遣告等。与明代的泰山祭祀形式相比,基本相同。清代与明代泰山祭祀的最大不同,当属康熙、乾隆时巡祭祀泰山与碧霞元君列入国家祭祀。
从所在地有司岁时致祭泰山看,与明代比较起来,清代泰山所在地常规祭祀变化不大,或者可以说,顺治几乎完全延续了明代的所在地有司常规祭祀制度,包括祭祀等级、祭祀时间、祭祀仪式等,尤其是祭祀祝文,几乎照抄了明代。
但是,平静中有惊雷,乾隆三十五年(1770),御制《重修岱庙碑记》横空出世,让争论一千六百多年的泰山所在地祭祀形制问题最终得到裁决。乾隆重事实而轻理论,截断众说,以帝王的身份,首次宣布了泰山本地设像庙祭泰山神的合理合法性。
明朝,碧霞元君成为泰山的重要神祇,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东岳泰山神,但并没有获得国家正祀的地位,文化精英常常视碧霞元君之祀为淫祀。明廷却并不取缔碧霞元君之祀,成化十五年(1479),命太监陈喜致祭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正式拉开了明代皇帝遣宦官内臣致祭碧霞元君的序幕,周郢认为,这属于明廷皇家祭祀,还不属国家祀典,但开启的遣使致祭碧霞元君制度却已是“国家化”的先声。[22](P42-43)正德十一年(1516),国家则开始对碧霞元君信众收取香税,这一举措,实际上标示着明廷对碧霞元君祭祀的半公开的肯定。
清初,碧霞元君性质地位模糊不清的问题依然存在。清初没有延续明代遣内臣致祭碧霞元君的制度,直到康熙皇帝于二十三年(1684)东巡山东时,在岱顶两次祭祀碧霞元君,表明碧霞元君在清廷心目中的地位并不减于明朝。乾隆时巡泰山,也八次亲自行礼于碧霞宫。康、乾二帝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包含着清廷对碧霞元君的认同。尤其是乾隆皇帝自乾隆元年(1736)起,就不断地对碧霞元君撰文发声,清楚地展示了他对碧霞元君的认识过程。乾隆三十五年(1770)《重修碧霞元君庙碑记》,从理念上彻底解决了传统泰山神与碧霞元君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篇御制碑文中,乾隆阐明了碧霞元君与泰山之神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一体神,这为碧霞元君列入国家正祀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此后,乾隆四十五(1780)年开始,“每年皇帝遣侍卫大臣一员,于四月十七日斋宿岱顶。十八日黎明,诣碧霞宫拈香,岁为常例”。[23](P51)从现存泰山石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廷每年遣使致祭碧霞元君,一直坚持到宣统二年(1910)。这一系列的举措,标示着碧霞元君正式列入国家正祀,碧霞元君国家祭祀的性质得以明确。
碧霞元君纳入国家正祀,自然形成了所在地泰山祭祀的两大系统:(1)行礼于岱庙的传统的泰山之祭、(2)进香致祭于碧霞宫的碧霞元君之祀。前者包括地方守土官承祭的常规祭祀、时巡致祭与因事遣官致祭等非常规祭祀,后者则主要是每年四月皇帝遣官常规代祀。而且,自清初中断的常规遣使代祀泰山神的礼仪,在每年四月遣官致祭碧霞元君仪式中复活了,并成为一种崭新的所在地泰山常规祭祀。如咸丰六年(1856)泰安知县张延龄《重修万仙楼碑记》称:“碧霞元君之庙……我朝东封之典尤隆,每孟夏有钦颁香供,由省派大员躬代往祭。”[24](P727)并且乾隆皇帝巡幸泰山时,六次登顶,八次祭祀碧霞元君,这实为碧霞元君的非常规祭祀。于是,原来祭祀泰山神的常规与非常规祭祀,在泰山女神碧霞元君身上都具体体现出来。
与前代帝王相比,康熙皇帝对泰山这一中原文化的典型山岳符号,有着更加深入的政治宗教文化思考,其撰制《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又称《泰山龙脉论》)一文,将其崇祀泰山的用意昭示于天下。在这篇奇文中,康熙力证泰山龙脉发龙于长白山。长白山为满族爱新觉部的发祥地,泰山为五岳之首,将两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且认定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康熙显然是要向天下表示满清与中原文化发脉一体的观念。这一判断,对消弭当时紧张的满汉文化冲突有着巨大的意义,同时也暗示着满族为先、汉族为后的康熙的文化自尊意识。
以这样的理念作基础,康熙、乾隆二帝不断地时巡泰山,或亲自致祭,或遣官致祭,或亲至岳庙、碧霞宫等拈香行礼,成为这一时期泰山祭祀的一大亮点。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亲自至泰山所在地躬祀东岳之神。此距宋真宗1008年皇帝亲至泰山已经过去了677年。康熙要仿照古帝王东巡狩泰山之制,所以,将第一次南巡最初称为东巡。康熙要通过东巡泰山,在躬祀泰山神的仪式中,将满清统治神圣化、合法化。此后,康熙又于二十八年(1689)、四十二年(1703年)南巡至泰山。
时至乾隆,“循圣祖之家法,溯虞夏之遗规”,[25](第12册,P621)九次巡狩至泰山,将皇帝祭祀泰山之举推向高潮,不断地强化着泰山在民族国家中的重要影响,彰显了泰山在国家政治宗教文化中的神圣地位。康、乾之举,也只有汉、唐两代的泰山之祀能达到如此境界。
清代遣官致祭泰山与京城泰山祭祀,几乎全是“清承明制”,缺少新意。只是在京城泰山祭祀方面有所改变,如保留了明代的山川坛(地祇坛),将其作为水旱祈报之处。如东岳庙之祭只保留了万寿圣节致祭。其它基本上没有特色可言。
八、余论
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二日,清帝宣统退位。随着清廷的灭亡,其国家祀典自然也一起陪葬。此后,共和精神高涨,旧时的礼仪逐渐被废除。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祀天典礼,复辟帝制。从其仪式看,这一典礼与岳镇海渎无涉。
1928年,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神祠存废标准》,指出:“今则不仅神权已成过去之名词,即君权已为世人所诟病,我最优秀之神农华胄,若犹日日乞灵于泥塑木雕之前,以锢蔽其聪明,贻笑于世界,而欲与列强最后之胜利,谋民族永久之生存,抑亦难矣。现查旧日祭祀天地山川之仪式,一律不能适用。”[26](第5辑第1编“文化”之①,P506)从根本上动摇了岳镇海渎的祭祀理念,将五岳四渎列在废止之列,又将东岳大帝、东岳行宫与东岳庙阎罗殿信仰一律废止,并将碧霞元君送子的职司视为淫祠,可以说是将泰山信仰连根拔起,并附带枝叶,全部去除,不留一丝。终将泰山从国家祀典中逐出,泰山国家祭祀至此才算是明确画上了句号。
]
[1]詹鄞鑫.神灵与祭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2]郑丽航.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J].海南大学学报,2009,(5).
[3]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朱溢.汉唐间官方山岳祭祀的变迁——以祭祀场所的考察为中心[J].东吴历史学报,2006,(15).
[7]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9][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0][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政和五礼新仪[Z].商务印书馆景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3][清]邹柏森.严州金石录[Z].吴兴刘氏嘉业堂光绪二十八年刊本.
[1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5]《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周良宵,顾菊英.元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9]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2.
[20]明太祖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版.
[21]明孝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版.
[22]周郢.泰山碧霞元君祭:从民间祭祀到国家祭祀——以清代“四月十八日遣祭”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2,(5).
[23][清]金棨.泰山志[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
[24]袁明英.泰山石刻[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5]清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梅焕钧)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Sacrifice of Taishan
LIU Xingshun,JIANG Tingting
(1.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Taishan University,Taian,Shandong 271021;2.Taishan Middle school,Taian,Shandong 271000)
Taisha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of national sacrifice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s the first of the five sacred mountains.The national sacrifice of Taishan originated from Pre-Qin dynasty and developed from theWestern Zhou Dynasty.With the reform of the outskirts sacrifice ceremony in Western Han Dynasty,in the fifth year of Yuanshi,Taishan became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untains in the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only inferior to the national North and South outskirts sacrifice.Thismarks that Taishan had surpassed the local symbol,becoming the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alpine symbol.Since then,the national sacrifice of Taishan formed two systems:one is the location of Taishan;the other is the capital.The national sacrifice of Taishan in the capital contained outskirts sacrifice,sacrificial offering god and special sacrifice.The sacrifice in the location of Taishan included regular annual routine sacrifice and unconventional sacrifice of the state affairs and sending official sacrifice.This tradition had continued to the end of Qing dynasty.In 1928,The abolition standard of the shrinewas issu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which abolished the belief of five sacredmountains and four rivers,and Bixia Yuan Jun.Since then,The national sacrifice of Taishan had clearly ended.
Taishan;national sacrifices;location;Beijing;History
G127;B9
A
1672-2590(2015)05-0001-10
2015-08-20
刘兴顺(1965-),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泰山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