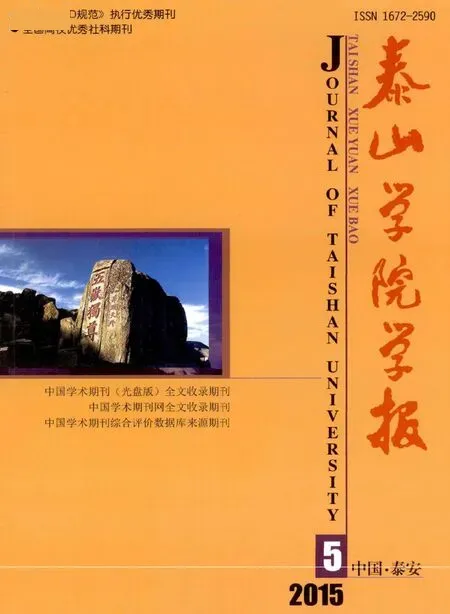自虐的诗意与精神的救赎
——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评析
刘 欣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自虐的诗意与精神的救赎
——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评析
刘 欣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重要短篇小说,也是卡夫卡一生文学创作和艺术追求的归纳和总结。它既是卡夫卡自虐式的作家生活的写照,又是其进行自我精神救赎的一篇象征性寓言。
卡夫卡;《饥饿艺术家》;自虐;救赎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重要短篇小说,作家以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描写了一个纯粹艺术家的生存境遇以及其荒诞的人生悲剧。这篇小说故事完整,却歧义颇多,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阅读后产生深深的困惑和无尽的思索,也带来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知道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K,带有卡夫卡自己的影子,而饥饿艺术家我们不妨看作是卡夫卡的自况,饥饿艺术家的一生也是卡夫卡一生文学创作和艺术追求的归纳和总结。它既是卡夫卡自虐式的作家生活的写照,又是其进行自我精神救赎的一篇象征性寓言。
一、自虐的诗意
自虐的“虐”,在《说文解字》中,对“虐”字的解释是“虐,残也。从虎,爪人,虎足反爪人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虐”意思是“残暴狠毒”,而“虐待”即“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待人”,从字面的意思讲,“自虐”就是自己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对待自己。这是字典上较权威的含义,也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
在心理学上讲,是一种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主客同体的虐待。它属于自己制造痛苦自己接受的行为,即施虐的主体又是受虐的客体,受虐的客体同样是施虐的主体。在人类社会中,自残、自伤以及自杀等现象均属于自虐行为。这类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自虐按照人们接受的意愿为标准可以划分出主动型自虐和被动型自虐两种。主动型自虐是指受虐者心甘情愿地、主动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的自虐行为。事实上,这类自虐者自觉自愿地、有意识地、主动地进行自虐行为在整个自虐行为中占的比例较小,绝大多数的自虐行为都属于被动型自虐。而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的表演却是属于主动型的自虐,这种艺术表演的行为方式是饥饿艺术家自主习得的,而非外人强加的。
卡夫卡,Kafka,希伯来语,意思是“穴鸟”。鸟是渴望飞翔的,穴是鸟栖息的窝。而穴鸟这一名字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的生存困境和人生的悖谬。“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1]。在他的短片小说《地洞》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为自己精心营造安全的生存环境——地洞的小动物。这个地洞用力之大耗时之长,建造的非常结实牢固耐用,而这个小动物却无时不刻地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顾虑忡忡,惊恐万状,“即使从墙上掉下来一粒沙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然而,“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个地洞的处境恰恰是卡夫卡自己生存处境的象征性写照。意味着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劫难逃,他的寓意是深刻的。地洞中的这只小动物可以说是卡夫卡的自况。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信中曾真实描述过自己理想的生存处境:“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呀!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2]卡夫卡对自己的生活几乎到了非常苛刻的程度,从来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只追求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在生活上是个极简主义者,有着较为浓厚的自虐倾向。他完全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窖中,仿佛就像饥饿艺术家把自己装在铁笼子一样,自娱自乐地享受着自己的艺术表演,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其中忘却自我,自虐并快乐着。叶廷芳认为卡夫卡有这种倾向:他赞美磨难,把磨难视为人生的内在积极因素。因此,他愿意接受苦行僧似的自我折磨。
在《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为了达到饥饿艺术的极致,他不顾自己身体的忍受力和承受力,执意要突破饥饿艺术表演的最高期限40天。他严格恪守艺术的最高法则,在这40天之内,没有点滴进食,自觉自愿地忍受各种痛苦和折磨,他既是自虐的主体,又是积极主动地自己对自己进行施虐,既是受虐者又是施虐者,在饥饿表演过程当中,看守人故意制造一些机会,留有一些时间和空间,让他可以有机会添加一些流食让他保存体力,以便可以延长他饥饿表演的时间。可他硬是坚持点滴不尽,因为那样的话就违背自己一直坚守的艺术家的职业操守,是他自己无论怎样都不会去做的。因为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饥饿艺术是饥饿表演的最高境界,为了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他完全可以一直饥饿下去,乃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他是饥饿艺术的殉道者,用自虐的方式为饥饿艺术表演献身,以此做为求证自身存在价值的方式。正如贝克考特在《文化的精神分析》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社会中的人们的强迫症的癖好,来自超我的惩罚性,而超我则隐含于唯一的上帝之中”。[3]饥饿艺术家对饥饿艺术表演的强迫症的癖好,无异于犹太教徒对上帝耶和华的崇拜和爱戴。
饥饿艺术家为艺术献身,就像卡夫卡为写作而献身一样,他的创作即是他的生活,写作成为了卡夫卡的一种生存方式。在生活方式上他别无所求,只要能够不影响他的写作,他可以舍弃一切,完全沉浸在孤独、恐惧、负罪、与世隔绝的生活中,画出自己“存在地图”。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他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全都萎缩了。”“外界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扰我的写作。我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即使就其褒义而言也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4]卡夫卡为了写作拒绝了生活中的一切友情、爱情、婚姻和家庭,曾经三次订婚又三次退婚,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和恐惧,他把写作看得高于一切,不允许任何世俗的杂念玷污他的创作,他对写作的完美追求又近乎绝望。就像饥饿艺术家对饥饿的表演一样。
他的作品都不是凭作家的技巧“做”出来的文章,而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一如他笔下的那位“饥饿艺术家”,表演的无限性和艺术的完美性是他唯一的追求,至于因此他的生命会消失他是全然不顾的。实际上他是在用生命换取表演(在卡夫卡是写作)的可能性。[5]这位现代艺术的探险家,仿佛是上天降大任于斯人,为了文学艺术,他把“一切生之欢乐”都搭上了,这是一个艺术殉难者的形象。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力和毅力,甚至需要把性命都豁出去的牺牲精神。
二、精神的救赎
卡夫卡视写作为生命,写作是他内心祈祷的方式,当成“砸碎我们心中冰海的斧子”[6],成了“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推进”的手段,他感到只有写作才“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是一种巨大的幸福”[7]。卡夫卡生活的时代西方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信仰,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哲学家尼采口出狂言宣布“上帝死了”,整个西方现代社会陷入了万物枯死的精神荒原。卡夫卡作为一个特别敏感的作家,他以自己的切肤感受和深刻体验洞悉了西方社会的这一切。而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人生经历使他离群索居,走进灵魂的“城堡”,他是个犹太人,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又对犹太教义持异议;作为一个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一个捷克人,他又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作为一个白领人,他不属于资产阶级,而作为一个资产者的儿子却又不属于劳动者;作为一个职员,他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可作为一个作家,他既无法完全从事创作也不珍惜自己的作品;他的内心成了一个多元的世界,他无所归依,是一个生活的局外人和异乡者,在精神上成了孤独无依的精神流浪汉和漂泊者。在卡夫卡看来,身外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是荒诞的,人们甚至不能通过对外在的行动的选择来确定自身的存在的意义;而对于我们的内心能否支撑起生命意义的沉重,他也是犹豫不决的。“这世界和我的自我在难解难分的搏斗中,看来非撕破我的躯体不可。”[8]由此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处于“搏斗中”的关系,表明了他对通往自身存在之路的一种选择困境。
在《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一刻不停地与自己的内心在作斗争。起初饥饿艺术家的表演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是很受观众欢迎并风靡全城,“全城的人都在为饥饿表演忙忙碌碌,观众与日俱增,人们都渴望至少观看一次饥饿艺术家的表演。”然而几十年后,情形完全不一样了,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了,被那些热闹上瘾的观众忘却了。原来用于饥饿表演的小小铁笼子居于舞台的中央位置,小笼子前观众围得水泄不通,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后来被一个大马戏团招聘了去,安插在场外一个离兽场很近的的交通要道上,笼子周围是一圈琳琅满目的广告,彩色的美术体大字令人一看便知道那里可以看见什么。人们在看兽畜表演时顺便经过,稍停片刻,小小的铁笼子前,人烟稀少,冷落萧条。外部的世界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艺术家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喜悲人生,但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执着的信念始终未变,坚守着艺术的纯洁和神圣。最后饿到了骨瘦如柴,皮包骨头,终于倒在了艺术的舞台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死前他说了一句“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9]
饥饿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信仰可以看做是基督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和膜拜,通过这种方式以期死后得到精神的拯救。卡夫卡也像饥饿艺术家那样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最佳生存方式而又苦于找不到,他是人类最早感知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作家。在他的心头充溢一种对人类生存的危机感,他像饥饿艺术家那样在用生命做了体味和证实。因此他的内心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借助于文学手段将它宣泄出来,成为他“巨大的幸福”。
饥饿艺术家企图以一种内在的“不可摧毁的东西”来顶住“上帝”死后的可怖现实。然而,人们不再相信有坚定的信仰。只有他依然执拗地固守着那些信仰,凄然悲惨地死去。正如尼采所说:“上帝只是人的一种猜测,饮了猜测的折磨,谁能不死去?”即使是你的愿望再善良,雄心再坚定,自我克制的精神再伟大,个人是根本不可能阻挡住住历史时代前进的步伐,改变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饥饿艺术家的悲剧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卡夫卡曾这样描述他的写作动机的:“我将不顾一切的写作,绝对地,它是为自我保护而进行的斗争。”[10]“如果我不从事写作,情形会变得更坏,更令人无法忍受。我肯定要以疯癫终其一生。”[11]“有一种巨大的渴望,想把完全出自我的一切焦虑写下来,把它写进纸的深处,正像它出自我的内心深处那样,或者用这种方式把它写下来。能把写下来的东西完全吸收到我的身上去,这并不是艺术方面的渴望。”[12]由此可见,卡夫卡进行艺术创作的深层动机并非出于对纯美学意义上的艺术追求,而是通过写作释放内心的痛苦,获得内心的宁静,为自己寻找到一条精神的救赎之路。
卡夫卡始终在寻找一种精神皈依,他在日记中写到:“相信存在着一个目标,人们通过经历各种不幸而朝它前进”,[13]他曾说“人不能活着而没有一种对他自己内心中不可毁灭的东西怀有恒久的信仰”,“可能表现这种隐秘形式之一是对一位别人不知道的神的信仰”。[14]这体现了卡夫卡精神人格的独立性和个性。他不愿从众,更不愿媚俗,他需要的不是人人都信奉的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而是能真正满足他精神需要的私人化宗教。作为一个渴望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救赎的生命个体,卡夫卡拒绝接受这种每一个出身犹太家庭的人都拥有的犹太教,他不愿意成为一个大众化宗教意义上的犹太教徒,而要成为在精神信仰方面保持自己生命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独立。
现代哲人尼采说过: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卡夫卡通过饥饿艺术家对艺术极致的苦苦追寻简直到了令人灵魂发颤的地步,甚至陷入到对个人的罪恶拷问和心灵忏悔。卡夫卡就是通过描写人物心理上的自虐性的宣泄和病态的自我折磨,进而在人格分裂的炼狱中对人物的灵魂进行着烤问和批判。卡夫卡用这种残忍的对自我心灵的透视方法,从对世界的怀疑与神秘的处罚把苦难理想化,并且在宗教的热忱和原罪意识的忏悔下触发对人类灵魂的深入剖析,进而达到清洗人的心灵,净化拯救自己灵魂的终极意义的关怀,即试图以回归人性使自己的灵魂获得精神的救赎。正是在这种深度上卡夫卡的苦难追寻已经上升到对自我追寻的灵魂救赎。
]
[1]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卡夫卡.致菲利斯[A].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5][8][9]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德]瓦根巴赫.卡夫卡传[M].韩瑞祥,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7]叶廷芳.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J].文艺研究,1982,(6).
[10][12][13][14]卡夫卡.卡夫卡日记[M].阎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11][德]贝勒克.向死而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责任编辑闵军)
The Motion of Self-abuse and the Redemption of Spirit——An analysis of Franz Kafka's novel A Hunger Artist
LIU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Taishan University,Taian,Shandong 271021)
A Hunger Artist is a very important short novelwrote by Franz Kafka in his late life.It is also a summary and conclusion of hiswhole life's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art pursuit.This novel is notonly a picture of Kafka's writing life of self-abuse,but also a symbolic fable of self-redemption of spirit.
Kafka;A Hunger Artist;self-abuse;self-redemption
I3/074
A
1672-2590(2015)05-0059-04
2015-09-02
刘欣(1965-),女,山东文登人,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