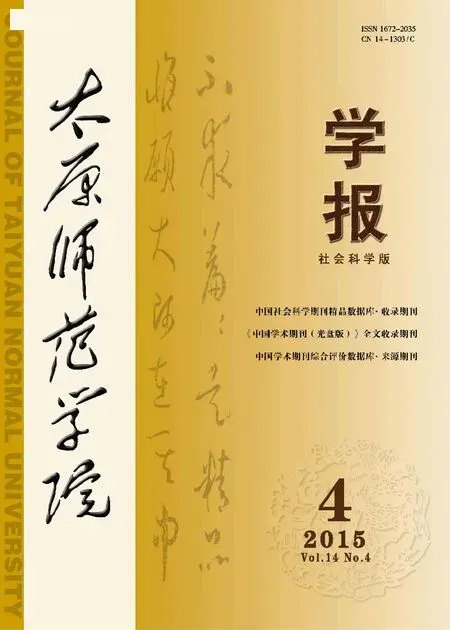论“百姓日用即道”作为消费文化本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刘满华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 江苏 泰州 225300)
“第一个为本体下定义的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本体是关于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然、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1]189“本体论和本体是一对悠久的概念,意义却宽泛不一,有的意在探讨物质或精神,有的本体论或本体旨在论述世界的根据、本原、始基,有的则专门研究‘神’,有的以人的生存和幸福为根本出发点,介绍和评价人学本体。”[2]4
文化是指人类创造与传承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人是社会存在物又是自然存在物,文化也相应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文明与进化标志的社会属性文化,二是满足人的自然生存与生理需要的自然属性文化。
一、文化的建构特性
文化产生于生存和生产实践。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文化的重心由自然生成转向社会共同体,文化实践的最重要导向变成政治利益与人类共同进步。政治利益与社会进步是与某种社会形式或范式密切相关的。这种社会形式或范式的认知是从维持共同体认同性的社会规训的权威中习得的,这使得某种文化范式的知识成为“一个传统权威的范式”,于是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文化类型。而文化的基本理论范式的转换依赖于语境的推理和评价标准的实现,并对不断增长的关于实在的知识做出相应的理性回应,所以文化的形成过程必然具有建构性。
文化形式或范式的建构必须建立在现有的社会实践获得的理性认知基础之上,形成普遍的社会信念,如果不能形成某种社会信念,不被社会认可,这种文化建构就会被淘汰。所以,文化建构是建构主体的政治诉求与人类社会进步两个方面知识形成与相互作用的结果。
现有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形成的共同认知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对人类生存与进步、对社会政治利益的诉求是有益的知识被当作真理,成为社会共同信念,是文化建构的基础。先贤们必须按照两个基本点来引导人类与社会迅速成长或更快进步,建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必须符合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与人类共同进步的要求。不利于人类共同生存需求,就会遭到唾弃,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认知信念;如果这种理论与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相去太远,也不会被社会接纳,不会形成“权威的范式”并加以传承。
人类从认识了的世界总结经验,视这种经验为真理,同时推知未知的世界,为未来制定计划。这是文化建构的认识论基础。人类之所以确认其真理性,是因为找到了构成真理的内在原因,并在现实中加以证实。人类追求世界终极知识与最大利益的本性,坚信宇宙世界是一个理性体系,只要找到其构成的最后依据,关于宇宙和生命的一切问题及其知识体系都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这种认知信念从来都是人类探索世界动力的源泉。人类确信可以掌握世界、改造世界,对未来产生无穷希望,现世今生也有了寄托。于是无数先贤预设许多关于世界的最后因,即关于世界的“本体”,在这种本体的基础上推演物理世界的前因后果,推演其内在联系,依据这种预设的理性逻辑,创造理论体系。如果这种建构的理论体系符合人类进步的共同愿望,同时有利于统治集团的政治诉求,这种体系就会形成“传统权威的范式”,一种文化类型,比如东方儒家文化传统、西方理性文化传统、佛教文化、基督教文明等。
人类依据自身的理性认知心理,类推宇宙的理性构成,建构理论体系,一方面有其盲目性与认识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及其文化具有建构特性。文化的“真”和客观世界的真是有差别的,社会的进步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必然有人为引导。
二、文化与本体:灵与肉的关系
假如,人类从古至今都理智而坚定地认为宇宙是一个偶然过程,没有最后因,即“本体”,人类就不可能得到最后真理性认知,也无法完全理解进而掌握世界,当然也无所谓预期未来。那么,人类生存与社会生活就会盲目而毫无寄托。这肯定是一种灾难性预设。纵观人类历史,凡是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都有本体支撑。
本体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的根;文化是本体的肉体,是生命基础。人类建构某种理论体系,取得大众的广泛认同,成为社会信念,是因为人们确信某种“本体”是世界的最后因,世界是根据这种本体演绎生成的结果,而理论体系是这种逻辑过程的描述。人们依据这种理论体系作为生存依托和坚定信念生活、繁衍。当这种文化体系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时候,文化就会衰落,人们对支撑该文化的本体失去信任,整个文化范式必然被其他文化样式取代。
在西方,理性文化的范式构成两千多年的社会信念。柏拉图之前就有基本元素说、基本粒子说等,柏拉图提出“理式”说,认为理式是物理世界的本质或本体,是世界的最后依据或终极实在,其理论体系是《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把永恒、静止的“实体”作为宇宙的“本体”或“本源”,这种实体是第一实体,是存在的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自我实现,自然世界的所有变化最终都是“本体”的自我实现。这样,物理世界就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与实践最终成为可能。
笛卡尔提出“心”、“物”二元论,“我思故我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理性信念,于是,人们充满信心地走向理性启蒙,为欧洲的强盛确定方向,提供信念支撑。康德对形而上学本体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形而上学与本体论起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3]164但康德赋予物自体以永恒不变的威望,视物自体为本体,是世界的最后因,尽管规定这种自在之物是无法认识的,其明晰的理论体系同样赋予人类认知自信与人生寄托。
黑格尔学说的强大历史感与辩证过程来自“理念”是世界演变的终极原因与动力;物理世界的变化是理念自身对立面转化的结果,因而物理世界是理性的,是可以认知的;理念由低级走向高级,人类社会走向进步,而且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实证主义确认世界有“本体”或“本质”,物理世界及其规律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当人类的认识与这种规律一致的时候,认识就是真理。
存在主义从反叛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出发,打破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禁锢,却以新的“存在”为本体建立新的“文化体系”。马丁·海德格尔试图打破“遮蔽”走向“敞亮”。他认为存在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所有人都深陷其中以致没顶的某种东西,存在就是人类在其中生活、运动的那种日常状态的存在。“存在远非十分遥远、十分抽象的观念;它十分具体,同现实息息相关,的的确确关系到每一个人。……它仍然晦暗不明,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对其置疑。”[4]2010
东方,老子明确提出本体概念“道”并加以体系化,理论作品是《道德经》。道是宇宙的本体或最后因,物理世界是一个有规律并且可以认知的世界。儒家文化的内核是“仁”,是社会行为规范的最后依据。孔子是这样定义解释“仁”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就是忠恕之道,教人如何做人。
宋明理学把“道”与“仁”的思想统一起来,形成了理学的“理”。理学中的“理”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脱离事物独立的实在,是事物的根本,并在事物之先。程朱理学所讲的理“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基本标准。实际上,他们把封建道德标准绝对化永恒化,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宇宙的根本、一切事物的根源。”[5]205中国的封建文化以“理”为本体,理论体系影响深远。王阳明认为,道德观念就是人人心中固有的先验意识,即心中之理,这种“忠孝之理”是人人头脑中所固有的。
王艮把世界的“本体”即“道”思想与儒家的“万物一体”统一起来。但王艮否定“道”的先验性,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论思想,正确地揭示了“道”的来源,符合时代发展,得到人民的赞同与拥护。
本体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与世俗文化基本一致。“佛”最初的意思是“觉悟”,悟到了绝对真理。佛教创造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佛不灭”等理论体系,以“佛”为最高教主,以超越轮回,进入极乐世界即成佛为最高目标。人们通过修行,达到超脱尘世而成佛的目的。当人们对佛的客观实在性提出质疑的时候,六祖慧能提出“本性是佛”作为禅宗的本体,“佛”就是人的本性,人要靠自己的“灵知”,刹那间领悟到心本来就是空的,立即达到“佛”的境界。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同时制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最初,上帝是客观的实体,人们虔诚地信奉上帝。当人们无法证实上帝的客观存在性时,只好像爱因斯坦那样坦诚而无奈地给自己制造个上帝,把灵魂交给他。
三、“百姓日用即道”作为消费文化本体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历史上所有对人类历史演进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具有强大而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类型都有“本体”支撑;本体是人们确信这种文化合理性的最后认知依据。它说明该文化生存与存在的合理性,也是这种文化范式形成权威传统的保证,更是其健康发展的动力。
人类已经或正在进入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消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已是大势所趋;然而消费文化的无根性、平面化特性导致其既无人文、道德内涵,也缺少正确的引导。所以,消费文化需要建构,需要植入人文之“根”——本体,为其充实人文、道德内容,规约消费文化的发展。
消费文化的本体必须与消费社会的产生具有同根同源的亲缘关系。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论是明中叶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产物,又是对商品经济与文化的总结与建构,与消费文化天然契合。同时,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本体论思想是儒家的“万物一体”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儒家的“万物一体”思想,以宇宙一体、天道自然、一体归仁、生命感通、生生和谐,达到天下大同为其基本内容。不同的是,王艮思想产生于明中叶以后兴起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同时,王艮坚持“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否认“道”的先验性,揭示了“道”来源于百姓的购物、消费、生活方式与情感欲望,适应消费文化发展的需要,为消费社会大众理解、接受与认同,被誉为“日用中之布帛粟菽”(王元翰《王艮传》)。
为了进一步论证“百姓日用”与道的关系,王艮把人性之“体”与天性之“体”、“良知之体”等同起来。这样,“百姓日用”既是“人欲”与人性的依据,又是“道”的来源。同时,王艮坚持“百姓日用”就是“体用一源”,论证了“百姓日用”之“道”与天地万物中的“理”同源同体,即天地人同体,使“百姓日用”之“道”与儒家、理学的“道”对接。同时,“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还彰显了“百姓”与“日用”的首要地位,充分肯定了消费与享受生活的合理性与人人平等的民主理想。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适应消费社会发展的另一个进步意义在于,把“道”从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辨实体变成客观的具体实在,由无形无象的观念变成了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由极端的神秘变成了日常琐事。就像王艮在《年谱》中所言: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这样,百姓日用的道就是不用思索与矫饰的自然实在,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流露的自然本能就是本真的“道”。
把“百姓日用”作为消费文化的“本体”,既为消费文化树立了天然而坚固的“根”,为消费文化找到了认知基础,树立了权威的社会信念,又为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确立了人文、道德内涵与方向。首先,“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论思想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是明中叶以降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百姓日用即道”与消费文化具有同根同源关系,对消费文化内涵的解读与校正贴切到位。其次,“道”、“仁”的思想已经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灵魂,“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继承了传统儒道的进步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只是清代阻断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发展与影响受到阻隔。但这种观点与信念已经对传统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民居民俗等的形成与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百姓日用即道”中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深得人民理解与拥戴,已经融入现代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的血脉。第四,“百姓日用即道”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特征,为人们真切地体验、领会。第五,“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鼓励人们追求幸福、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剔除“恶欲”,规约人性与消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使人自然而本真地消费与生活,具有积极的人文精神内涵,也为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正确坚实的根基,树立了明确的消费文化观念。
四、用“百姓日用即道”规约消费文化的必要性
消费文化的社会基础是物质产品空前丰盛,文化特征是购物和消费城市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购物与消费成为人们除工作和家庭生活外的全部内容和终极目的。然而,人们倾心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代表的符号和象征,体现消费身份,彰显消费阶层与个性。消费文化的价值观极度稀释社会人文与道德内涵,却主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领域和日常活动,控制与主宰大众道德、思想、观念,对人类精神和文化造成严重危害。
消费文化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助长恶欲,人们在对物的追逐之中丧失了高尚的人生追求,人文精神与道德缺失,导致社会文化的平面化、无深度、无中心、无历史、机械复制与庸俗化;昔日人们心中的“崇高”、“理想”、“终极关怀”等观念和信仰被享乐主义冲刷销蚀。
文化需要建构,消费文化也不例外。消费文化的兴起有其社会物质基础,却没有一种权威的社会信念可以规避其消极、负面的行为观念,引导消费文化健康发展。消费文化在认知心理上需要一种核心理念的支撑,这种理念应当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与道德底蕴,同时与消费文化完美对接,为人们认可、接受。
王艮从儒道文化传统中的“仁”、“道”理念出发,合理地发展了“天地万物一体”思想,修正了阳明心学的良知观念,认为自然万物与人的欲望都是自然赋予的禀性,具有天然合理性,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论思想。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这种观点产生的社会基础。在商品经济的萌芽阶段,王艮就敏锐地觉察到其人文、道德弊端,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论思想,以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促进商品文化健康发展。
王艮认为,顺应本性自然要求,追求享受与快乐,合乎自然的发展要求,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但他在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合理性的同时,坚决反对“私欲”,如“不孝、不弟、不睦、不渊、不任、不恤”等“造言乱道”的恶欲。(《王道论》)
充分肯定符合自然生存需要的欲望的合理性,剔除恶欲是王艮启蒙与民主思想的自然延伸,也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剔除“恶欲”,恢复、保持了儒家理想的“中和”。王艮要求人们不要为“恶欲”束缚,把私欲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做到“知本”、“知止”,正切中消费文化的要害,是修正其平面化的良药,是规约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文化基础。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谢维营.本体论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张志伟.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杨照明,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郑红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