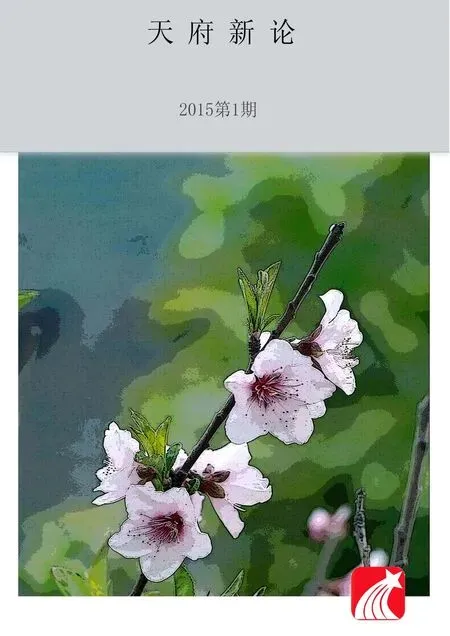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跨界之旅——评李左人的长篇小说 《女儿谷:1937》
张建锋
(作者:张建锋,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李左人的长篇小说《女儿谷:1937》,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观照扎坝鲜水河走婚大峡谷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田野调查的实证与文学想象的虚构杂糅,文学性与学术性融合,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
李左人长期在走婚的鲜水河峡谷扎巴人和泸沽湖、利家嘴摩梭人的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结合历史资料、民俗史料,以文化人类学为学理支撑创作了《女儿谷:1937》。小说还原了1937年扎坝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现实,成为目前扎坝唯一的历史生活画卷和“活”的“文化原生态”记录,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小说”。
作者将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融合起来,记实与虚构二位一体。虚构的人物、故事、情节与历史事件、生活场景、社会现实相融相生。小说依傍史实,演绎故事,借助人类学立场对历史纵向的严谨考察和文学神游冥想的翅膀飞翔,寻求故事虚构性与社会人文环境记实性的统一,从而回到“1937”(时间)“女儿谷”(空间)的“历史现场”,“回到”当时当地,以虚拟的人物、故事、情节为线,串联起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实施改土归流、民国年间废黜土司头人、红军长征过道孚、诺那事变、特派人员在扎坝救灾推行保甲制等历史事实,和扎坝大峡谷的风土人情、扎巴人的走婚、偷婚、母系大家庭、头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等世俗生活,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丰富的世俗生活构成历史景象的再现,具有历史的“现场感”。作者多次深入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及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实地考察,获得了真实的体验和感悟。田野调查让“虚构”的世俗生活“落地”,让描写具有记实性,成为“活”的生活形态。
作者的田野调查,本是出于学术志向,想厘清扎巴族群的文化样态、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历程,捕捉走婚原生形态,考察扎坝传统文化的变迁兴衰。从作者发表的《扎巴人的婚姻、家庭和性》、《鲜水河走婚大峡谷调查与思考》、《走婚与四川藏区的“爬墙文化”》、《“走婚大峡谷”:飞檐走壁的浪漫爱情》等多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用力之勤,用功之深。而小说创作盘活了作者对扎巴文化的人类学思考,作者把学术上的见解融和进去,探究扎巴人性本质,解读人类深层的隐秘、人类的文化基因。作者自觉将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杂糅在一起,有意识地在文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游走,站在文化多样性立场,将扎巴文化作为非主流的“文化他者”来反映,是对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视角的一种颠覆。这是“还原性”书写,是借他鉴我,而不是像历史小说那样记录历史、展现历史,或以历史题材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从而使小说具有了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价值。
二、走婚文化的深度“勘探”
李左人对走婚文化的“勘探”体现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视野,小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独特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学者怀着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厌恶和对落后国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尊重文化之间的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尊重多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价值,强调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不去轻易评判和摧毁那些与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
康藏地区的“走婚文化”,被“外来者”以猎奇的眼光记录并评头品足,而李左人从文化传统、文化环境方面来展现走婚现象,又从理论上揭示走婚文化的实质。小说的主要人物钟秋果不单是刘文辉的秘书、西康建省委员会特派员,还有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人类学专业背景,随身携带着他的老师近代藏学研究先驱任筱庄(任乃强)的《西康图经》。钟秋果“看” “走婚” (视角),“想”“走婚”(思考),还“行”“走婚”(实践)。作者没有停留在“走婚文化”的现象描述上,而是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和阅读的历史文献,尽力展现扎坝走婚产生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背景及其演变形态,揭示出“走婚文化”的精神实质。作者始终突出表现母系社会环境和走婚习俗的文化氛围对于扎坝人的影响。钟秋果主动走近母系大家庭,不仅弄清了扎巴人坚持走婚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的严重制约和母系文化的强大惯性,而且了解到他们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观念与内地完全不同,并对扎坝的多样婚姻形态持肯定态度。小说从经济、社会、文化的各方面来揭示“走婚文化”,厘清其文化的源流、体系,说明其历史的传承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视野,有助于矫正当下偏狭的或者霸权的各种“文化主义”。
三、凸现康藏女性的文化品格
《女儿谷:1937》描写走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时时进行藏汉两地文化的对比。“尼玛所代表的扎巴性意识,崇尚自由、自主、平等,是一种伙伴关系性伦理。小翠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在她身上体现的依从、被动、依附,是夫权社会男尊女卑观念衍生出来的性道德。”文化的并置和对照具有明确的借彼为镜、反观自身的自觉批判倾向。作者自觉地突出描写康藏女性的地域文化品格,体现出反思中国正统文化的倾向。
作者立足于扎坝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走婚文化,塑造出了特色鲜明的康藏女性形象,丰富了巴蜀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小说中塑造的主要女性形象有嘎玛卓嘎、巴桑、桑姆、泽仁旺姆、尼玛、玉珠、志玛、央金卓玛、扎西娜姆、巴玛、阿追等。其中,泽仁旺姆、尼玛母女的形象具有代表性。母女二人不仅身份特殊、背景复杂、经历丰富,而且与钟秋果形成了“三角”情感纠葛。其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让她们的形象更生动、更丰满,更具有地域文化的特异色彩。泽仁旺姆身上贯注着康藏文化的元素。她说:“凭什么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的事自己不能做主?”“为啥子只能守着一个男人,凭什么要女人为丈夫守节?女人为啥不可以多找几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在汉文化圈里人们习以为常的婚姻观念在女儿谷的“语境”里遭遇“吐槽”。自以为正统的汉文化遭到扎坝人的质疑问难,一时间集体“失语”。泽仁旺姆不只是把“口号”喊得响,而且自觉“实施”自己雄伟的“征服男人”、“征服女儿谷”的计划。这些品性蓄积着康藏地区的文化基因,又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磨炼出新的特色。
作为泽仁旺姆的女儿,尼玛在县城受过一点新式教育,追求自己的爱情更主动,接收新观念更快。从外表上看去,尼玛一身小蛮女打扮,活脱脱一个放肆的野丫头。她对爱情的追求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坚决果敢,勇往直前,行动任性随性,语言斩钉截铁,其大胆是惊人的。尼玛在女儿谷走婚文化的浸润下早通人事,曾经沧海更知水为何物,不仅具有少女天生的丽质,还绽放着成熟女性迷人的风韵。在走婚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康藏女性,顺着天性,自由自在。作为“世外”之域, “化外”之地的女儿谷,很少受到所谓“文明”的污染,扎巴人没有被现代社会“异化”失去自然的人格,离人的本我更近,更像真正的人。“蓝天作帐,草坡为床,把爱写在荒野里。原始与现代,野性与文明,火与水,刚与柔,动与静,生与死,混成天衍大气,万代不灭,直至永恒。”正是鲜水河扎坝女儿谷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基因铸就了康藏女性的文化品格。
四、跨界的限度与未完成的探索
《女儿谷:1937》是一次“跨界”的艺术探索,寻求文学性与学术性的融合。作者游走在文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但跨界之旅还有可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小说对扎坝走婚大峡谷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方面的描写,对扎坝人的体形体质、穿衣打扮、房舍建筑、饮食习性、娱乐方式、交通出行等方面的描写,都有相当精彩的笔墨,对于展现扎坝母系制婚姻家庭的特点、人物的性格都有渲染、烘托作用,能为扎巴文化铺垫上厚重的地域底色。但有些描写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细节、突出特色、展示亮点,以“活”的“原生态”形式来反映走婚文化的独特性。小说触及到走婚文化面临的生存困境,但对于历史风云、时代潮流对扎巴人及其走婚文化的影响的揭示还有开拓的空间。比如央金卓玛的杂货店,是扎坝瞭望“外面世界”的“窗口”。小说对此的描写稍嫌简单,没有完全发挥出“窗口”传播文化的功能。如果能像描写钟秋果的照相机、金笔,泽仁旺姆的雪花膏,还有电灯、电报、电影、广告等那样处理,艺术效果会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