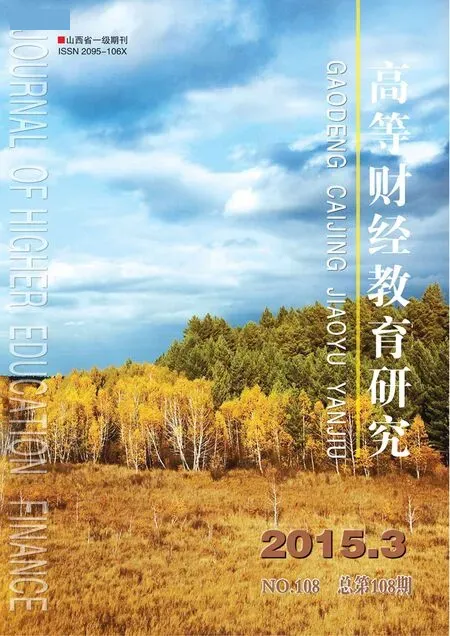从《论语》中“士”的英译看跨文化传播的实现
陈丽君
(中华女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北京 100101)
从《论语》中“士”的英译看跨文化传播的实现
陈丽君
(中华女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北京 100101)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思想、主张的重要著作,其影响源远流长。自1893年理雅各的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问世以来的200多年中,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英译版本。本文试以理雅格、亚瑟·韦利、刘殿爵、雷蒙·道森和安乐哲的《论语》的五种英译的不同版本中“士”的翻译,分析中西背景下对“士”的不同理解,从而探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的效果和影响对文化传播影响。
《论语》英译;“士”;跨文化传播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寓意,其影响源远流长。《论语》的英译也一直没有间断过,自1893年理雅各的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问世以来的近200多年中,西方一直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英译本。翻译作为介绍中国文化的必要手段,在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庸质疑的,但翻译涉及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文化的内涵靠语言层面的翻译是无法来获取的。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源头。翻译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意义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的一种互动和碰撞。
本文试以西方译者的五种不同版本的《论语》中“士”的英文翻译的对比,来分析中西背景下对“士”的不同理解。
一、《论语》中的“士”的含义
(一)“士”的历史渊源
“士”在《论语》中一共出现过15次,分布在11个章节中。对于“士”字的起源,学者也众说纷纭。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牡》一文谓:“卜辞中牡字皆从⊥,⊥字正|(古字十字)一之合矣。”王氏以为牡为雄畜与士为男子相合,且仍拘泥于“推十合一”之说。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之《释祖妣》一文中提出,“余谓士、且、土实同为牡器之象形”,以阳物象征男性;又指出士与“王”字同出一源,并以早期“皇”字从士不从王为证。
“士”的最基本的含义是成年男子。“士”的起源较早,上起春秋,下迄清代,长达两千多年,历经各代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其含义也有所不同。商周时代,“士”多为武士、卿大夫家臣,《论语》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士”阶层兴起的时期。据刘泽华统计,在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有名词,约有百余种[1]。有文士、谋士、勇士、巧士、辩士、处士、使士、察士、廉士、礼教之士、法术之士、技艺之士,等等,非常庞杂。自汉代的“士大夫”、魏晋六朝隋唐的“士族”,至两宋时的“士人”、明清的“绅士”,“士”在中国史上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士”的传统才宣告结束。
由于本文分析的是《论语》的英译问题,所以我们只考察孔子时代前后“士”的含义。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士”的身份和地位,历史学家历来有不同的意见。
顾颉刚先生认为,西周和春秋前期,“士”来源于武士,“士为低级之贵族”[2]。孟子关于周室班爵之制的叙述便为明证:“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更确切地讲,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低级贵族。
陈启云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精英领导阶层——是“地主、学士、官员”三合一的领导层。
阎步克将“士”作为“士大夫”整体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设定,“士大夫”是文人角色与官僚角色的结合,达到了赖文逊所谓“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利的辉煌的象征性结合”[3]。
余英时认为,在周朝时,“士”是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在“大夫”与“庶人”之间,社会流动性小,身份较固定,大多担任邑宰、府吏、下级军官等职位。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彼此之间的战争大大加速了阶层的流动。春秋晚期,由于贵族下降和平民上升,“士”的数量激增,士庶合流,“士”从固定的封建身份中获得解放,变成了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也成为后来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历史来源。这些人,有的是贵族余孽,有的是从底层上来的佼佼者,他们处于上下之间,发挥着纽带桥梁的作用。
(二)《论语》中对“士”的阐释
《论语》中“士”共出现过15次,除了3次泛指一般人士(“虽执鞭之士”;“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其余12次均指向这一特殊阶层。
在第一次出现“士”的里仁篇第四-9中,孔子直接提出了“士志于道”的思想。道是孔子最主要的思想之一。孔子以“士志于道”,作为终生志向。孔子说:“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卫灵公》)这些说法意思都相通,都是在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孔子要求每一个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他努力给他们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进而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士”要有志于道,方能称为“士”,他们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也就是将“道”作为自己终生努力实践的目标。
例如:子路篇第十三—20,在问及孔子“士”的标准时说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依次回答了三条:1.“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2.“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3.“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贡又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很不屑地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的回答,提出了三个层次的士的不同标准。第一等级的士,不做有辱自己人格的事情。他们代表国君,出使各国,操纵国际形势,完成国君交给他们的任务。第二个等级的士,能做到“在家族,孝敬长辈,在家乡,团结友爱”,也就可以啦!第三个等级的士,只要做到“说话必须讲信誉,行动必须有结果”,就行了。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孔子说:“就是傻瓜一样出力干活的人,也可以称得上是下等的士了。”
例如:宪问篇第十四—2,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如果一个士,总是怀念故居,想过舒适的生活,那么,他就称不上是个士了。”
例如:子张篇第十九-1,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孔子的学生子张说:“一个士,如果能做到:在危机的时刻,能牺牲自己的生命;见到好处的时候,能考虑仁义;祭奠仪式上,恭恭敬敬的;遇到丧事的时候,心里哀伤。那么,就可以啦!”
归结起来,“士”必须做到三点:首先,立足于自身,要做到“忠”和“恕”,即“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其次,立足于自己的宗族,要做到“孝”和“悌”,即“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再次,立足于政治,要做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语·子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论语·颜渊》)。
孔子对春秋时期中国新兴的阶层——“士”,赋予了一种极其庄严也是极其艰巨的使命——志于道。孔子对于“士”的阐释及其所赋予的精神价值,开启了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士”之传统,对后世的“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士阶层“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历史上有许多印证,无论是天下有道还是天下无道,士人们都在自觉实践着自己的价值追求。
总之,“士”的含义可以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1)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和阶层;(2)是有知识的,讲求修养的;(3)不管是否是贵族,是有一定权力或依附于一定的权力的;(4)是立志于管理国家大事的,具有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个阶层。
二、五种英译本中对“士”的翻译和理解
“士”是一个丰富而具有流动性的概念,它有着漫长的演变历史。传统典籍翻译中的文化成分是最难译的,这又涉及到了文化成分的翻译问题。那么,作为《论语》中富含文化寓意的词汇之一——“士”,它的英译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士”的本意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译者给与“士”的不同的翻译和理解。
里仁篇第四-9,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理雅各译作:Chap.Ⅸ.The Master said,‘A scholar,whose mind is set on truth,and who is ashamed of bad clothes and bad food,is not fit to be discoursed with.’
刘殿爵译作:9.The master said,“There is no point in seeking the views of a Gentleman who, though he sets his heart on the way,is ashamed of poor food and poor clothes.”
亚瑟·韦利译作:9.The Master said,A Knight whose heart is set the Way,but who is ashamed of wearing shabby clothes and eating coarse food,is not worth calling into counsel.
Raymond Dawson译作:9.The master said:‘A public servant who is intent on the Way,but is ashamed of bad clothes and bad food,is not at all fit to be consulted.’
安乐哲译作:9.The Master said,“Those scholar-apprentices(shi士)who,having set their purposes on walking the way(dao道),are ashamed of rude clothing and coarse food,are not worth engaging in discussion.”
在本章节中,孔子开宗明义的指出“士志于道”。古文本身言简意赅,可以有多重理解。原文本的开放性给每个译者提供了多样选择的可能,翻译者们对它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都采取了各自不同的译法:理雅各在此将“士”翻译成了“scholar”;刘殿爵译成了大写的“Gentleman”,并注释:Throughout his book,“Gentleman”is used as a equivalent for Shi士while“gentle man”is used for jun zi(君子);亚瑟·韦利译成了Knight;Raymond Dawson译成public servant;安乐哲和罗思文在他们的翻译中将其翻译成scholar-apprentices。
对《论语》中出现的15次“士”的五种不同译法的统计。理雅各:Scholar(7次),Officer(5次),其他(3次);刘殿爵:Gentleman(13次),其他(2次);亚瑟·韦利:Knight(3次),knight(9次),gentleman(1次),其他(2次);罗蒙·道森:public servant(13次),其他(2次);安乐哲:scholar-apprentices(shi士,12次),Teacher(2次),其他(1次)。
我们可以看出,理雅各将“士”分别翻译成“scholar”(在他的翻译版本中出现了7次)和“officer”(5次),显然,理雅各理解了“士”既与古代的知识阶层有关,又与政府的统治有关。但是,在里仁篇第四-9中,将“士”译成“scholar”,而在下面四个章节,将“士”都译成“officer”。
泰伯篇第八-7: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颜渊篇第十二-20: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时文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路篇第十三-20: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微子篇第十八-11。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在子路篇第十三章中,第20与28同在一节,20中的“士”译成“officer”,而28又译成“scholar”(子路篇第十三-28.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理雅各显然认为“士”可以指向两种不同的群体,而实际上,泰伯篇第八-7、颜渊篇第十二-20、子路篇第十三-20与28都是对里仁篇第四-9中“士志于道”的重要阐释。
刘殿爵用大写的“Gentleman”来翻译“士”(13次),并在注释中说:Throughout his book,“Gentleman”is used as a equivalent for Shi士while“gentle man”is used for jun zi(君子)。“士”和“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士”是君子的初级阶段,君子是“士”发展提高的优秀者。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亚瑟·韦利将“士”翻译成knight(12次),其中,里仁篇第四-9、泰伯篇第八-7、微子篇第十八-11三个章节中,是大写的Knight(3次)。“士”可以用来指封君属下的低级武士官吏,这与古代英国的knight相类似,这可能就是韦力的理解吧。
Raymond Dawson将“士”译成了“public servant”(13次)。
安乐哲认为,在《论语》的大多数章节中,“士”都是某种初学者,他们将会随着时日渐趋精进。我们不妨将这些文辞理解成对于为“士”之道的指导:“士”刚刚踏上了一条漫漫长路,需要面对无数的考验与磨难[4]。安乐哲将“士”看成是精神之路的探索者,这也许就是将“士”译成“scholar-apprentices”的原因吧。
总之,以上各种不同的译法体现了不同学者对原始文本基于不同角度的不同理解,同时译文本身也体现出了翻译者对原始文本进行的显性或者隐性的评论,不同时期的译者对这一词语的翻译可以被视作是对这一文化性词语的不同的历史看法。除了理雅各以外,翻译者们对这一被翻译的词语基本上都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性理解。
三、“士”和它的译文的对比分析
面对《论语》中如此复杂的“士”,西方的翻译者们都挖掘出了多个内涵,他们试图根据不同的情境,用不同的英语词汇或者短语来对它进行翻译。有如此之多的词语关系到这同一个汉字“士”,我们有必要对“士”和它的主要译法进行对比性分析。
(一)语言层面的翻译分析
翻译属于比较语言学的范围。卡尔福特认为,两种语言只要具有“空间的、时间的、社会的或其他的关系,都可以建立翻译等值关系”[5]。这就是说,翻译不仅包括不同语种之间的转换,同时还包括不同的方言变体、同种语言不同时期语言变体、不同社会阶层语言变体、不同行业或专业语言变体之间的转换。翻译的过程就如同一个寻求对等的过程,在目标语言中通过这种对等的诉求来转述原文的含义。
理雅各、刘殿爵、亚瑟·韦利、Raymond Dawson和安乐哲对“士”的英译是否在两种语言中找到了它的对等成分。本文以《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和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词典》的英文解释作为依据。
1.理雅各的“士”之一——scholar。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Scholar:(1)(尤指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者;(2)(英)奖学金获得者;(3)有学术能力的人;(4)[古义][口]能说会写的人;(5)[古义](中、小学的)学生。
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词典》的解释。Definition of SCHOLAR:(1)a person who attends a school or studies under a teacher:pupil.(2)a:a person who has done advanced study in a special field ;b:a learned person 3:a holder of a scholarship.
从以上的注释,我们可以看到,“scholar”的含义中包含了两个最基本的意思,即学者、学习者,一个是学有所成的,一个是正在学习的人。《论语》中的“士”正具备这样的特点,孔子有弟子三千,他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这样的“士”和君子,希望通过这些“士”、君子的从政(仕)而影响和掌握国家的命运,实现仁政和德治。中文的许多注释者,也注释成为“读书人”、“学习者”等,比如杨伯峻、李泽厚。
2.理雅各的“士”之二——officer。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Officer:(1)军官,(商船或客船的)船长;(2)男(女)警察;(3)(社团、组织中的)主席、干事,职员;(4)担任公共(民间或教会)职务的人,(王室任命的)部长,(任命或选举的)官员;(5)a bailiff法警;(6)(英帝国)四等勋爵士。
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词典》的解释。Definition of OFFICER:(1)a obsolete:agent;b:one charged with police duties.(2)one who holds an office of trust,authority,or command〈the officers of the bank>〈chief executive officer>.(3)a:one who holds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or command in the armed forces;specifically:commissionedofficer;b:the master or any of the mates of a merchant or passenger ship.
officer本意是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如前所述,“士”最早就是低级的官吏,后来“士”的范围扩大了,但他们仍是积极入士的,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许多“士”成为了王侯的门客,或者担任了重要的职位,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理雅各将“士”分别翻译成“scholar”(在他的翻译版本中出现了7次)和“officer”(5次),他在注解中指出:The necessity to the officer of compass and vigour of mind.士,a learned man,‘a scholar’;but in all ages learning has been the qualification for,and passport to,official employment in China,hence it is also a general designation for‘an officer’.
这说明,理雅各理解了“士”既与古代的知识阶层有关,又与政府的统治有关,但在同一文本中出现了两种译法,显然容易造成误解,认为是两种社会群体。
2.刘殿爵的“士”——gentleman。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gentleman:(1)(礼貌或正式用法)男人;(2)有风度(礼貌或者教养)的男人;(3)有身份的男人,上流人士;(4)与王室有关联的名门贵族;(5)(作复数)用于对男性的尊称。
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词典》的解释。Definition of Gentleman:(1)a man who treats other people in a proper and polite way;(2)MAN—used especially in polite speech or when speaking to a group of men;(3)old-fashioned:a man of high social status.
gentleman通常被译成“绅士”。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6]中专门论述了绅士的社会特质,他认为,绅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绅士是指通过考试、捐纳等途径而取得功名者及其家族成员,狭义的绅士则仅指取得功名者。从社会特性看,绅士与官职和地产联系紧密,“他们构成以地产为基础的家族阶层”,作为个人的绅士是政府官员,掌管政权和行政事务,但也是处在家族关系中的成员,并依靠家族关系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应该说,gentleman的含义最接近“士”的本义,与功名相关,有一定的特权,是一个既不同于官员又不同于一般平民的独特的阶层。但是,同西方的绅士相比,中国绅士的身份是不可继承的,西方的绅士要求严格、酷嗜骑马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绅士典型的学者生涯形成鲜明对照。
3.亚瑟·韦利的“士”——Knight。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knight:(1)(非世袭的)爵士;(2)[史义](通常为贵族,尤指在当了侍从或护卫后被君王提升至高级军阶的)(中世纪)骑士,勇士;(3)(女人、事业等的)忠实拥护者;(4)[棋类](国际象棋中的)马(通常形似马头);(5)[罗马][史]骑士(此阶层原为古罗马的骑兵队),[希] [史]骑士(雅典第二等级的公民);(6)(下议院中的)郡选议员。
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词典》的解释。Definition of KNIGHT:(1)①a mounted man-atarms serving a feudal superior,especially:a man ceremoniallyinductedintospecialmilitaryrank usually after completing service as page and squire;②a man honored by a sovereign for merit and in Great Britain ranking below a baronet;③a person of antiquity equal to a knight in rank;④a man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f a lady as her attendant or champion;⑤a member of an order or society.(2)either of two pieces of each color in a set of chessmen having the power to make an L-shaped move of two squares in one row and one square in a perpendicular row over squares that may be occupied.
亚瑟·韦利将“士”译成了knight,意为骑士。骑士是西方中世纪的一种贵族封号,获得这一封号即宣告了个人成功地进入了上层社会,从而可以获得封建贵族的特权。Knight和“士”都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均拥有自我认同的无上尊严,效忠宗主,具有等级性的特征。骑士身份一般是世袭的,他们行为冲动,具有勇武、忠诚、慷慨、侠义、正直和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与中国文人为主的“士”阶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4.罗蒙·道森的“士”——public servant。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Servant:(1)(通常指领取一定薪酬的)仆人,佣人;(2)虔诚的追随者,甘做(某人)侍从的人。
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词典》的解释。Definition of SERVAN:(1)a person who is hired to do household or personal duties such as cleaning and cooking?domestic/household servants—see also CIVIL SERVANT,PUBLIC SERVANT;(2)a person who is devoted to or guided by something—often+ of?a servant of the truth.
显然,这里Raymond Dawson是选取servant的第二种含义来翻译“士”的。devoted follower与“士”的“士志于道”的思想相吻合,但通常servant的地位低下,这又与“士”的实际情况相悖。
(5)安乐哲的“士”——scholar-apprentices。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Apprentices:(1)学徒,徒弟;(2)初学者,新手。
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词典》的解释。Definition of APPRENTICE:(1)a:one bound by indenture to serve another for a prescribed period with a view to learning an art or trade;b:one who is learning by practical experience under skilled workers a trade,art,or calling.(2)an inexperienced person: novice〈an apprentice in cooking>
Apprentice的意思为初学者,scholarapprentices意为学者以及初学者。如前文所叙的安乐哲的观点,“士”刚刚踏上了一条漫漫长路,他需要面对无数的考验与磨难[4]。安乐哲将“士”看成是精神之路的探索者,但scholar-apprentices显然反映不出“士”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地位与等级状况。
(二)文化层面的翻译分析
自从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飨宴》一书里提出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后,翻译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翻译活动具有“文化传播性”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有自身的独特生存环境和发展历程,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符号转换的手段,也是以文化价值的传递和文化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交际活动。王佐良先生曾指出:“他(指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要处理,而在处理小文化的过程中,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这两大片文化,一片是源语文本所包含、所反映的文化及其根植于其中的特定文化,另一片文化就是译语所属的特定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文化。”[7]这从一个侧面阐述了翻译的性质,也说明文化的内涵是无法靠语言层面的翻译来获取的。文化不可译的原因是,“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绝对的翻译是不存在的,翻译总是存在着某种可译性限度
纵观以上六种对“士”的英译,他们的翻译都只是翻译出了“士”的含义的一个侧面,都没能全面反映出中国文化中“士”的深刻蕴义。但是,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所选择的各种各样的代名词,即“scholar”、“gentleman”、“officer”、“Knight”、“public servant”,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符合孔子所说的:“士”的“志于道”的精神。
“士”的一个重要身份是“scholar”,是专门化知识角色的代表,以“学以居位”为特征。学而优则仕的“士”,获取了功名又成为了“officer”。所以,正如前文所述,这三者是合为一体的。那么,作为“scholar”的“士”和作为“officer”的“士”也同样具有“志于道”的精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中西都有“gentleman”阶层,中国的绅士是“士”的延伸,认为是“士”与“大夫”的结合,在整个社会阶层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们有学识,大部分人有财力,因而有一定的政治权力,支配着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等方面,是各种重大变革及斗争努力争取的力量。西方的“gentleman”,在英国盛行并发展到极致,绅士风度即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外化,又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某些价值观融和而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用中西都有的这样的概念作为翻译中对应的词汇,无疑对于理解“士”是很有帮助的。
“Knight”、“public servant”都是西方的概念,骑士精神是西方上流社会的文化精神。骑士作为一种贵族封号,它必须经过长期的服役,并通过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他们从小就会被灌输宗教和道德教育,尚武好德,并且在阶层内部形成公认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他们忠君爱国,看重身份,注意修养,恪守诺言,尊重法规。在这一点上,骑士与“士”是一致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五种译法各有千秋,都有各自的道理。苏联翻译家费道罗夫认为,翻译某些个别特殊语言现象时,虽不能完全传达到译文语言里,但至少对词语在原文中所起的某些作用还是能传达的[8]。因此,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者来说,忠实于原文的风格和精神要难于忠实于原文的句子和词汇,前者是一种最高境界和最理想的忠实。
由此可见,翻译中对等的选择,决不是来源于同一个层面,更重要的应该是文化上的对等。
四、对“士”的翻译的思考
洪堡特在一篇译叙中指出,不懂古代语言的人,若要通过翻译了解古人,最好是阅读多个译本而不是仅一个。不同的译文反映出同一精神的不同面貌,因为每个译文只能传达出各自所能获取并表现的那份精神,而原文真正的精神依然寓于原文之中[9]。洪堡特的论点旨在强调原作精神的不可译性,但他同时也不经意地指出了一条可以趋近原作的途径:通过多个译本重建原作的风貌。
将每一种译法放在语境中加以适当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可能是正确的选择。通过对整个文本的阅读,以及对翻译词语的分析,我们观察到中国文字在大多数情境下比英文词汇所包含的意义要更为丰富。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士”的内涵历经时间长河大有改变,这不仅影响了阅读者对中文经典典籍的理解,也影响了对它们的英文翻译。
同时,这也反映出了翻译的尴尬和文化差异力量的巨大,也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典籍用文言文写成,文字艰深,典故丰富,经常为翻译者们带来许多障碍,尤其是外籍翻译者。要做到准确地读懂中国传统典籍并用英语传递原文信息,翻译者们必须在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对比,从而研究出这些文化性词汇原始的、历史的意义。
总之,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转换。翻译在中国文化对外播种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道,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结晶,担当对外文化传播重任的翻译人员,应当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尽可能多地传递中国文化的内涵,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反之,如果翻译不能达到传播效果,“传而不通”,或效果不佳,就失去了对外文化传播的意义。因此,中国文化能走出去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通过典籍翻译向世界各国人民传播介绍华夏文明,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刘泽华.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21.
[2]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M].北京:中华书局,1963:85.
[3]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Volume On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4][美]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M].余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
[5]Catford,J.A.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M].Lo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6][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EB/OL].[2011-11-05].http://blog.163.com/ybxldh@126/blog/Static/htm.
[7]王佐良.翻译:思考与笔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85.
[8]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学院出版社,2004:151.
[9]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责任编辑:冯霞]
Discussion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s of“Shi”in Five English Versions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CHEN Li-jun
(Depart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China Women’s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The“Analects of Confucius”(Lun Yu),a collection of the works and deed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ical works in China.During the 200 years since James Legge’s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of“Analects of Confucius”was published in 1893,numerous English versions of“Analects of Confucius”have emerged,and the work of translation still continues.Translation is regarded as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conversion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it creates an interaction and collusion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Therefore,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shi”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influences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James Legge,Arthur Waley, D.C.Lau,Raymond Dawson and Roger T.Ames’s five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s of“Analects of Confucius”,to establish how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English translation of“Analects of Confucius”;“Shi”;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642
A
2095-106X(2015)03-0065-09
10.13782/j.cnki.2095-106X.2015.03.013
2015-08-16
陈丽君(1969-),女,山东潍坊人,中华女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跨文化交际、女性高等教育。
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