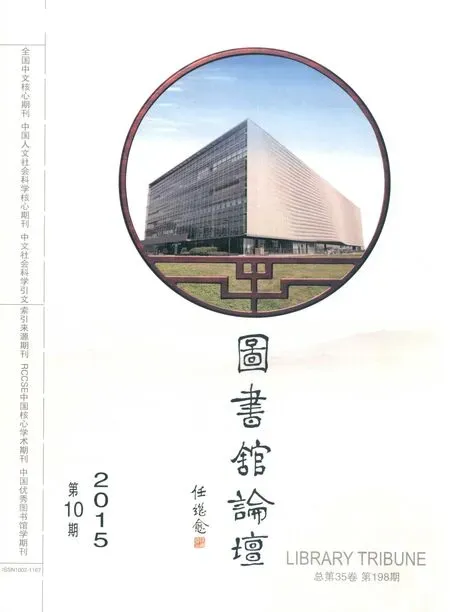《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谫论*
李福标,黄芳
《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谫论*
李福标,黄芳
《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收录佛教文献约60种,反映了岭南佛教发展的历史和各宗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存在状况。这些文献的著述者以广州地区籍贯为主体,也有不少域外高僧和流寓高僧。著述的内容涉及译经、注疏、语录、纂集等各类目,底本来源广泛,《广州大典》采取“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原则一并收录,最大程度地抢救和保护了珍贵文献,为岭南佛教文献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本。
广州大典 佛教 著述方式 文献保护 文献学
《广州大典》是近年来编辑的、我国收书最多的大型地域丛书之一,它按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格局,以现代影印技术,囊括广州地区(指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等地) 2200余年历史中(下限至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2000余位作者(含寓贤)的著述4450余种,辑录为540册,它无疑是研究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的宝藏。研究岭南地区宗教文化一门,自然也离不开这部大丛书。本文试对《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的收录内容、编印特点及其价值进行论述,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批评。
1 《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的收录内容
《广州大典》所收广州本土或外籍流寓、住持过广州寺庙的历代高僧著述约60种,其内容涉及佛教多个宗派:
(1)以禅宗著述为最盛。由于菩提达摩最先将印度佛教的禅宗传入广州,而中国佛教禅宗的创立者慧能生于广东,且在广州寺院剃发为僧,故学界有人认为广州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发祥地。慧能所创的顿宗,其简单务实的教风为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岭南得禅宗风气之先,故禅宗著述自唐代而后代代不绝;尤其在明清之际,广州曹洞宗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辈出,禅学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广州大典》所收的禅宗著述总计约30种,约占总数的50%。在这为数众多的禅宗著述中,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大乘佛教色彩浓厚。围绕《六祖坛经》而出现的注疏类著述有7种,与《金刚经》《心经》《楞严经》《楞伽经》《妙法莲华经》《圆觉经》等大乘佛教经典有关的注疏类著述有10余种。海云系高僧宗宝道独的《长庆语录》一种,虽主张“孤峰独宿”的修行方式,似乎为小乘思想,但其体现了“步步踏实地去,有余于己,乃可及物”的大乘菩萨精神。
二是流寓高僧和居士的著述弥足珍贵。比如,明万历年间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流寓岭表10余年,大力弘扬南派禅宗,中兴南华祖庭,并有众多著述;清初海云系高僧澹归今释不但开辟韶关丹霞道场,也留下了大量诗文和佛学著述。《广州大典》收录有流寓禅僧的著述约10种,占释家类文献16%,其中憨山《观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记四卷略科》一卷、《观楞伽经记》八卷、《妙法莲华经击节》一卷、《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直解》二卷等著述,无疑是岭南禅宗的瑰宝,深刻影响了岭南本土禅宗的发展方向。
(2)除禅宗之外,明清之际曹洞宗鼎湖系高僧行“博山钟板”“云栖规矩”,禅、净、律兼修。鼎湖山庆云寺第二代主持在犙弘赞针对禅宗内部“狂禅满地”的现象,乃援用律学以振兴禅宗,当时号称禅门的“律学巨子”。《广州大典》收其个人律学著述20余种,尽管其内容有明显的禅宗印记,然按佛教文献分类法,则大部分应该划入律宗的范畴(如《沙门日用》),约占总数的30%;小部分应划入净土宗的范畴(如《观音慈林集》),约占总数的5%。
(3)《广州大典》收录南朝真谛译《三无性论》二卷,它是古唯识宗方面的重要著述。又收录有唐般刺密帝译、房融在光孝寺笔授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此为密宗的经典。
岭南地区在五代时期,有释文偃创办的云门宗,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很大,惜无著述流传。
2 《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的编印特点
2.1 分类编排,脉络清晰
《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的编辑,首先按其内容分为译经和撰疏两大类,其后又按各宗派著述进行细分;每类之中又按其出现的时间先后进行排比,可谓纵横兼顾,措置得宜,严谨而科学。
广州作为唐前佛教由海上输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东汉就有胡僧浮海而来,弘扬佛法。这些僧人带来众多的佛经原典,不少译经活动就是在岭南地区展开的。据统计,岭南所译经典有数十部,《广州大典》收有真谛于制旨寺所译《三无性论》二卷。隋、唐两代是岭南佛教的鼎盛时期,名僧辈出,最著名者有南派禅宗创始人慧能。《广州大典》收有禅宗重要经典《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附一卷、《金刚经释义》二卷。唐代的译经活动依旧很盛,《广州大典》收录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就是中宗时中天竺僧般刺密谛携来广州,房融在光孝寺笔受翻译的。宋元时期,岭南佛教逊于前朝,可谓盛极难继。《广州大典》收录文献仅二部,即宋释子璇编撰《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二卷、《金刚经疏论纂要刊定记》四卷。明代中叶以后岭南理学盛行,而全国佛教界的风气不振,发展滞碍,岭南也不例外。明清易代之际,岭南佛教出现历史上又一高峰,活跃于岭南佛门的是禅宗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教徒规模庞大,弘化之热忱前所未有,且远超北方地区,直与江南、滇南相抗,为佛教三大中心之一。《广州大典》所收鼎湖系文献有释弘赞《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添足》一卷、《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会释》三卷、《六道集》五卷、《沩山警策句释记》二卷、《兜率龟镜集》三卷、《沙门日用》二卷、《归戒要集》三卷、《观音慈林集》三卷,释一鹫撰《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附反切韵法》,释成鹫撰《金刚经直说》一卷等近20种;所收海云系文献有释道独述《华严宝镜》一卷、《长庆宗宝道独禅师语录》六卷,释函昰撰《楞伽经心印》八卷、《楞严经直指》十卷、《天然昰禅师语录》十二卷、《天然和尚同住训略》一卷,释函可撰《千山剩人禅师语录》四卷,释今无撰《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二卷,释今释撰《菩萨戒疏随见录》一卷,释传晟撰《楞严经集注》十卷等10余种。总计所收此期两系佛教文献,约占整个《广州大典》子部所收佛教文献的60%。总体看,这约60种文献中有唐前著述1种,唐宋著述15种,明清著述40余种,可谓广州地区佛教各历史发展阶段的代表性著述,清晰地反映了广州佛教的特点和存在状态。
2.2 广收众本,从宽处理
《广州大典》佛教文献影印的底本,来源比较广泛,其中有各历史时期的刻本、抄本、影印本、铅印本等。除单行本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从《嘉兴大藏经》《中华大藏经》《卍续藏经》等各通行大藏经中择出的丛书零种。以某种文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又出现名人题跋本。刻本中,以刻书地而言,以广州本地寺院刻本为最有特色,例如有广州海幢经坊刻本、海云寺刻本。当然并不限于广州本地,还有省内其他地区刻本(如肇庆鼎湖山经房刻本),也有省外刻本(如吴中休休庵刻本、常州天宁寺刻本、江北刻经处刻本),还有域外刻本(如日本)。这些传本的藏存地分布在各地,除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之外,还有寺院藏书(如福建省泉州开元寺)。这从传播学的维度上曲折地反映岭南佛教发展的复杂性,非常值得重视。
在对一般文献的处理上,《广州大典》编辑者严格遵循“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不干预”原则,将原底本的本来面目真实、完整地呈现给读者。鉴于子部释家文献流传较少、损毁较严重等原因,编者在具体工作中对“底本征集要全”“底本选择把关要严”的编纂方针上有着“从宽”的灵活处理,即一种文献倘若存在多种版本,既有初刻本或早期刻本和较好的翻刻本,一般均予以收录,以供研究之用。当一书在内容上有变化而出现多种传本时,更是兼容并收。比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由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译、房融笔授、乌长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该书有明刻本,作十卷,藏福建省泉州开元寺;除十卷本之外,又流行五卷本,有清光绪七年(1881)海幢寺刻本,《广州大典》同时收录了十卷本和五卷本。唐慧能《坛经》版本众多,《六祖坛经考证》云:“清代所刻《坛经》种类繁多,惟岭南流传最广的,莫如康熙间海幢铁关上人所刻的本子。原板藏鼎湖庆云寺,咸丰十一年毁于火。同治元年刘钝根重刻。”①《广州大典》收录了《坛经》的明刻本、明抄本、清刻本、日本刻本和名人题跋本多种。鼎湖山庆云寺二代住持弘赞所撰《沙弥律仪要略增注》,最初作二卷,有清康熙刻本。此书乾隆二十七年(1762)海幢经坊刻本作六卷,前有释心鉴序云:“在昔云栖法师搜经律之秘诠,摄法藏之要略,以为初学入德之门。先以十戒法为纪纲,后以二十四篇为羽翼,神而明之。则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庶几乎包括矣。草堂在参和尚复为增注焉。草堂兼疏通之学,具情洽之才,以发云栖所未发之余。约者广之,微者显之,幽者喻之。采辑精要重注详明,诚入圣之津梁,后学之旨归者也。奈板藏鼎湖,欲览者艰,于是海幢有好乐者捐资重刊,以广流传。”②《广州大典》将二卷本和六卷本也同时收录,以有助于考察清代岭南禅宗海云法系和鼎湖法系之间的关系及交流活动。
2.3 力搜珍本,利于研究
倘某种文献仅存孤本或珍稀之本,《广州大典》力为搜求和收录。例如,明末清初释道独所撰《华严宝镜》一卷,先有清顺治十三年(1656)广州海幢经坊刻本;释函昰所撰《天然和尚同住训略》一卷,先有清顺治广州海云寺刻本。然在清乾隆四十年(1775)澹归案发后,海云系高僧的著述大部分都被禁毁,此二书自然不能免其厄运。清道光后,文网松弛,《华严宝镜》方于清道光六年(1826)重刊,而《天然和尚同住训略》至民国年间才经汪宗衍先生发现并手抄一本。此二种出自海云系宗师之手的珍贵著述,对于深入、全面考察明末清初岭南禅宗海云系僧团的宗教生活及宗教思想至关重要。然在各书目中均不见著录,今只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藏,历来不为人所注意,新近出版的《中华律藏》“清规部”也未收入此书。《广州大典》将它们收入,不但保存了濒临失传的文献,并使一个岭南佛教重要的历史环节得以还原,以引起学界注意。
3 《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文化事业也相应出现大繁荣局面。“盛世修典”是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作为最高规格的国家行为,20世纪90年代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就是其典型代表。随后各地也陆续出现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地域历史文献丛书,如湖南有《湖湘文库》、江西有《豫章丛书》。而《广州大典》这样一部以一座城市命名的大型丛书,收录内容之广、规模之大,尚无其比。其子部释家类所收约60种文献,尽管在《广州大典》整部丛书中仅仅占一个零头,但在数量、品种与质量上,和其他综合性地域文化丛书中的同类文献相比毫不逊色,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兹仅略举数端:
(1)促使广州地区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迈上新台阶。岭南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学术领域,历来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在《广州大典》出现之前,广州地区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大型丛书编刻活动,第一次为清嘉道年间两广总督阮元主持的学海堂丛刻;第二次为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主持的广雅书局刻书,此后百余年间未有大规模的书籍编印活动。广州作为佛教颇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历代出现了众多释家类文献,但无论是阮元还是张之洞的刻书,都未暇顾及释家类文献。广州历史上也未曾编辑过专科的佛教丛书,故释家典籍一直处在零乱分散收藏的状态。又由于战乱、禁毁和自然老化、虫蛀等原因,好多重要佛教著述失传,且文献流失的情形仍在持续,尤其令人痛心。1950年代,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之佛教著述部分,从大约50种方志、书目、文集中发现多种已被遗忘的释家文献,共收录了广东佛教文献112家223种,可谓基本摸清了“家底”。然仅录所知见之版本及其序跋,考其作者大致行实,而对文献本身的内容特点、版本流传一般不作深入考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为中心,组织了一批学者从事《岭南名寺志·古寺系列》《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等系列文献的校点工作,但集中在明清佛教史传和高僧诗文别集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涉及其他时期佛教经论等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甚少。
《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收罗广州佛教文献,是广州地区有史以来对佛教现存典籍的第一次集中、全面的收录。尽管对某些佛教文献或许仍有漏收情况,然终究为广州地区佛教文献的深入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又以其涵盖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宗派,不惟使学界对初具规模的岭南禅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走向深入,而且将引起学者对岭南其他宗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强烈关注。学者不但可以对这约60种佛教文献进行深层的文本整理,例如点校、选辑、翻译和其他普及工作,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深入发掘出各种研究课题。例如,从著述方式来看,《广州大典》所收佛教文献除4种为译经之外,其余均为撰疏(包括注疏、语录、史传等)。译经,多集中在唐前;注疏,唐宋以后各时期均有,而以明清之际居多;语录及佛教史传,也多集中出现在明清之际。这些译经、注疏、语录和史传著作,有何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无疑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又,从撰述者籍贯而言,《广州大典》所收佛教文献既有本土高僧所著,还有流寓高僧所著,流寓高僧中又多有域外高僧。唐前译经的著述者多为域外高僧,本土僧人几无著述留存。唐代本土高僧以禅宗六祖慧能为最著名。晚明有著名流寓高僧憨山德清。明末清初,岭南本土高僧一时群起云集,出现了道丘、道独、弘赞、函星、函可及所谓的“海云十今”等大批高僧大德。彼时流放外地的高僧函可和流寓广州的高僧今释,是两个特别的例子。函可因修私史而触法,充配沈阳,主持各大刹,大振禅风于关外,增强了岭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佛教交流。今释字澹归,浙江仁和人,为“南明五虎”之一,虽在南明王朝辗转各地,最后选择广州海云寺落发,并开创了著名的韶关丹霞道场,亦颇有传奇色彩。对这些撰述者的生平经历和其撰述背景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促使岭南佛教文化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中国佛教禅宗的研究历来就是全世界佛教研究的学术热点,因为广州为中国禅宗的发祥地,故广州禅宗文化也一直为学界所瞩目。然而,禅宗文化并不是广州地区佛教文化的全部,广州禅宗文化也不仅仅局限于唐代慧能等宗师,明清之际禅宗的复兴同样在佛教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尽管有学者已涉足于此③。
注释
①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引述,载《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②清释弘赞《沙弥律仪要略增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海幢经坊刻本。
③例如,民国年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剩人和尚年谱》、王汉章《澹归禅师年谱》等著述,直接或间接涉及明末清初广州海云系禅史。上世纪末,周齐、姜伯勤、蔡鸿生等学者涉足明清之际岭南禅宗的研究领域,在历史学和宗教文化学的高度上有所突破。
[1]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目录(未刊稿)[Z].广州:《广州大典》编辑部,2013.
[2]程焕文.历史文献传承与城市文化传播——《广州大典》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发掘[J].图书馆论坛,2013(6):51-55.
[3]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陈垣.清初僧诤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钱海岳.南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冼玉清.冼玉清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7]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8]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
[9]钟东.悲智传响——海云寺与别传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
[10]杨权.天然之光——纪念函昰禅师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
[11]传印法师.中华律藏[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Study on the Documentation Collected in“ZiBu·ShiJiaLei”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Canton
LI Fu-biao,HUANG Fang
About 60 kinds of Buddhism documentation are collected in“Zi Bu·ShiJiaLei”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Canton,clearly reflecting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Lingnan as well as the situation of its various sect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Authors of the documentation mainly took origin in Guangzhou and many of them were hierarchs from abroad.Although the documentation were complied differently and enjoyed wide sources of master copies,they were collected in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Canton on the principle of“no selecting,no compiling,no checking and no punctuating”and to the largest extent,were saved and protected,becoming the indispensable documents for bibliography on Lingnan Buddhism.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Canton;Buddhism;compiling ways;documentation protection;bibliography
格式 李福标,黄芳.《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谫论[J].图书馆论坛,2015(10):107-111.
李福标(1969-),男,博士,中山大学图书馆副教授;黄芳(1987-),女,硕士,中山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2015-02-26
*本文系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项目“《广州大典》子部释家类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412002-05020-4222009)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