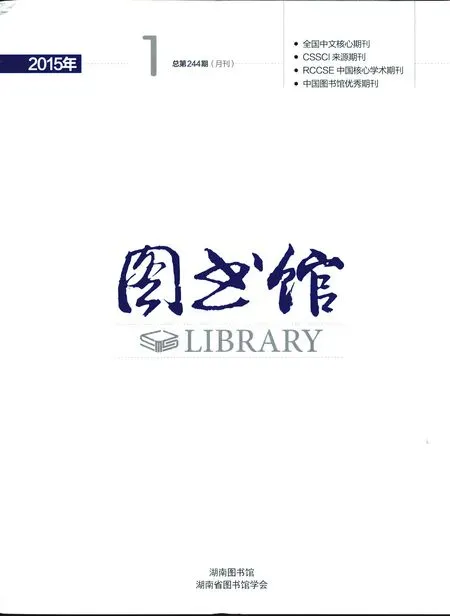中西学术之争与我国近代书目分类的历史演进*
傅荣贤
(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被洋务重臣李鸿章描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近代,若单纯从文献及其书目分类的角度来看,此一“变局”主要体现为传统四部分类不能从容应对日益“东渐”的西学新书。“西学东渐,新书迭出,旧有部类,势难统摄,当时之时,书籍之分类,在中国乃成为一大问题。”[1]总体上,面对西学新书品种益滋、数量日增的近代境遇,书目所选择的分类形态,反映了人们看待中西学术的基本态度,而分类形态的发展过程,则大致对应于人们看待中西学术的历史演进过程。文章拟重点分析1840年以讫1919年间中西学术之争导致的书目分类的历史变迁。而这一学术努力,又必须追溯到《四库总目》对西学书籍的基本态度。
1 “西学中源”理念与《四库总目》对西学书籍的分类
自西汉《七略》以来的我国古代书目,其分类对象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世俗文献。南朝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书目虽曾兼收佛教文献,但佛教文献旋即被类似东晋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等专门性的宗教目录所取代,深刻地反映了目录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边界。佛教文献之见黜,是世俗目录固守自我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清晰表征。
然而,清乾隆年间的《四库总目》在“子部·天文算法类”中收录了数十部明清西方传教士及中土人士译著的西方科学书籍,如利玛窦的《乾坤体义》、熊三拔的《表度说》、阳玛诺的《天问略》、徐光启的《新法算书》等。这批典籍虽主要局限于天文、算学,但“溺水一瓢”,反映的却是近代西方科学知识观念:以学术分科为原则、以客观方法为手段从事知识的理性研究。而中国古代的天文、算学迥异于此,“从目验的天象推论至微妙的玄理,又从微妙的玄理推广于具体的生活,才是中国人处理所有问题的总体框架”[2];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以及与之“表里”的算术,不仅包含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分曹测验,具有实征”的客观知识,还包含“妙契天元”、“精研化本”的超越内涵。相应地,由“测验”、“实征”而转入“天元”、“化本”的过程,亦绝非单纯的理性科学方法所能胜任。
将非自我的西方学术典籍融入《总目》,其理论基础是“西学中源”。清初学者梅文鼎引康熙《御制三角形论》之语曰:“西学实源于中法。”梅氏又曰:“算术本自中土传自远西,而彼中学者专心致志,群萃州处而为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出于水而寒于水。”[3]
“西学中源”说,不仅解决了作为中国古典书目体系的《总目》何以能够分类西学文献的问题,也暗含了以中学知识观念解读西学知识的取向。例如,《总目》在阳玛诺所著《天问略》的提要中指出:“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
2 “中体西用”理念下的书目分类
“西学中源”论有助于消解国人在学习西方知识时的民族自尊,有一定的社会影响。1880年,张自牧即指出:“今欲制机器,测量万物,运用水火,诚不能不取资三角八线及化气电火诸艺术,然名之为西学,则儒者动以非类为羞,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是在乎正其名而已。”[4]然而,近代西学渊源有自,“中源”之说不啻自欺欺人。诚如徐仁铸所云:“西人艺学原本希腊,政学原出罗马,惟能继续而发明之,遂成富强。”[5]
于是,“中体西用”论应运而生。冯桂芬《采西学议》首倡“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6]张之洞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于愚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7]显见,“中体西用”的本质是在固守中学之“道体”的同时,兼修西学之“器用”。广义上的“西学中源”已经包含“中体西用”的思想,但前者强调中学对于西学的本源地位,而后者更强调中西二学之“异”以及西学的独特之“用”。
正是在“中体西用”理念的指导下,1875年张之洞以二千多种传统书籍为主,但在史部地理类下酌收《职方外纪》、《新译地理备考》以及在子部天文算法类下酌收《新法算书》、《几何原本》等西学书籍,反映了张氏以传统经史为“体”,以西方地理、天文算法之学为“用”,并将西学之“用”纳入中学之“体”的思想。正如姚名达指出:“以其平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态度卜之,殆亦未能进一步而废弃《四部》也。”[8]
然而,将西学书籍强“就”中国传统书目体系之“范”,在当时即遭到了质疑:“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以何为当?”[9]这里,献疑的本质是:以中学知识为边界的传统书目,能否分类西学书籍。用姚名达的话说:“《四库》的分类法在现代之所以行不通,一方面却固然是因为其本身的分类不精密,而其大部分的原因则在乎西洋许多新进来的学术,非《四库》所能包得住的缘故。”[10]它深刻地说明,今人所总结的“文献保证”、“用户保证”等分类法编制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同步”的分类法修订原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于是,在“中体西用”理念未被突破的背景下,近代书目分类只能采取重新界定中学之知识边界的形式以容纳西书。姚名达曰:“对中外新旧之学术综合条理而分为若干科目者,据吾所知,以袁昶为最先。昶以光绪二十年主讲中江书院,略仿当时‘四明之辨志文会、沪上之求是书院、鄂渚之两湖书院,分科设目’,计十有五。‘每目之中,再分子目。曰经学,小学、韵学附焉。曰通礼学,乐律附焉。曰理学。曰九流学。曰通鉴三通政典之学,历代正史,则系传分代,史志分门,部居散隶,以便检阅善败起讫与夫因革损益之迹焉。曰舆地学(宜详于图表)。曰掌故学,宜详于国朝,以为根柢,渐推上溯,以至于近代。曰词章学,金石碑版附焉。曰兵家学(宜有图),仍略仿班《志》形势、技巧、权谋、阴阳四目,宜添制造一门。曰测算学。曰边务学。曰律令学,吏治书分类附焉。曰医方学。曰考工学。曰农家学。此十五目皆有益国故政要,民生日用。”[11]该目编制于1894年,所分十五目虽突破了传统四部,但仍以经学、通礼学、理学等传统类目为根柢;制造、测算学、边务学等类目,显然是考虑到“有益国故政要,民生日用”的现实之“用”而增设的。这些新增类目既方便容纳西学书籍,但又在中学之“体”的规约之下,堪称用心良苦的书目创新,亦反映了西学之“用”对于中学之“体”的反向能动作用。并且,袁昶书目的类名皆缀以“学”字——如改“经”为“经学”,也是西学反作用于中学的表征。
袁昶书目考虑到传统四部分类不能容纳西书而增益类目,同时又固守了“中体西用”的理念。1902年编制的《杭州藏书楼书目》实为其嗣响。该目将中外典籍统一分为九类:经学,小学附;史学,掌故、舆地附;性理,哲学家言附;辞典;时务;格致,医学附;通学,即丛书;报章;图表。其中,经学、性理等以古籍为主兼收西书;而辞典、格致等则以西书为主而兼收古籍。
综上,“中体西用”理念下的书目,或对反映西学的类目作出基于传统分类的理解(如“兵家学,仍略仿班《志》”);或将新增西学类目从属于传统类目(如在兵家学下“添制造一门”);或用针对西学的新类名同时兼收中学书籍(如“律令学,吏治书分类附焉”);或将针对西学的新类名缘饰以中学术语(如医方学、考工学、农家学),明显具有将作为异质文化的西学书籍纳入中学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用意。另一方面,这类书目对传统四部分类的“突破”也为最终颠覆“中体西用”理念及其相关书目分类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郭嵩焘最早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始务其末者。”[12]倡言“中体西用”的张之洞也明确指出,尽管中学是“体”是“源”,但不能代替西学,他说:“然谓圣经皆以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用西人之法,则非”;中西二学应该“各司其职”,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3]由西学自有体用、中学不足以包容西学的观念,进一步导致了“中西异学”思想的产生。罗振玉所谓“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14]也是要强调中西之学实属“歧二”而非“统一”。
3 “中西异学”理念下的书目分类
面对“学术乃歧为二”的现实,吴汝纶于1899年指出:“人无兼材,中、西势难并进,学堂自以西学为主。西学入门,自以语言文字为主,此不刊之宝法。他处名为西学,仍欲以中学为重,又欲以宋贤义理为宗,皆谬见也。”[15]强调应该对自有体用的西学予以专门研究,而不应受到中学的羁绊。严复亦认为:“今日所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危当务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16]总体上,“中西异学”理念下的书目分类概有两大类型:
3.1 西书独立编目
所谓“西书独立编目”,是完全以西学书籍为对象而编制的目录。这类目录因不涉中学典籍,所以,类目设计也完全脱离了四部分类体系。
1878年英国人傅兰雅编制《江南制造局译书事略·西书提要》,收录西学书籍138部,设15个类目。蔡元培《东西学书录·序》曰:“英傅兰雅所作《译书事略》,尝著其目,盖从‘释教录’之派,而参以‘答问’之旨者也。其后或本之以为‘表’,别部居,补遗逸,揭精诂,系读法,骎骎乎蓝胜而冰寒矣。”[17]所谓“从‘释教录’之派”,是指傅目对纯属西学的书籍单独编目,类似《综理众经目录》等佛教专门目录;所谓“参以‘答问’之旨”,是说傅目兼有导读性质,与张之洞《书目答问》堪称同调;所谓“其后或本之以为‘表’”云云,是强调傅目对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示范和影响作用;所谓“骎骎乎蓝胜而冰寒矣”,是说由傅目肇端的西方分类日趋壮大,逐步取代了传统书目分类的主体地位。
傅目之后,1889年王韬《泰西著述考》、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7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903年沈兆袆《新学书目提要》等皆是西书独立编目的成果。“徐维则又撰《东西学书录》,顾燮光补充之,于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一再刊行,分类凡三十八。及三十年,燮光复续一编,近年始刊为《译书经眼录》。”[18]也是典型的西书独立编目。此外,1902年渐斋主人收集西书,“分辑各门,为《新学备纂》一书,”[19]将“诸科学所应习者”分为天学、地质等26门;1903年《新学大丛书》将当时翻译到中国之西书分10大类77小类,并合刊印行,[20]也都具有西书独立编目的性质。这批书目中,以《西学书目表》影响最大,“颇有仿行之者”[21]。该目将三百余种西学书籍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28小类。
三大类大致相当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西学书目表序例》曰:“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
总体上,以上书目的文献著录对象主要是传入中国或译为汉文的西书,而不包括传统中学典籍。并且,这批书目皆强调西学所具有的个性特征逸出了中学的知识边界,西书分类完全可以摆脱传统四部体系的樊篱,从而也令人质疑:“西学中源”理念下将西书纳入传统分类体系或“中体西用”理念下将西书纳入稍事更张但本质仍属于传统体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西书独立编目在凸显西书个性特征的同时,也回避了与中学书籍的关系问题,更不可能成为以兼收中西书籍为常态的当时绝大多数图书馆的书目分类原则。于是,秉承“中西异学”理念,将中西书籍分列于一编遂成为当时大多数图书馆首选的书目分类策略。
3.2 中西分列于一编
所谓“中西分列于一编”是以四部法分类旧籍,别立“西学部”以分类西书,并将两者合编于一目。
1898年黄庆澄所编《普通学书目录》,“原为指授初学,融贯中西而设。虽非藏书目录,且浅之无甚精义。然混合新旧之目录于一编者,固未之或先也。是后遂有以新书为‘时务部’,列于四部之后者。流风所扇,入民国后犹有若干公立图书馆习用此种新旧分列之办法”[22]。该目将中外图书分为三部分:卷一为中学入门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中学丛刻书;卷二为西学入门书、算学、电学、化学、声光学、汽机学、动植学、矿学、制造学、图绘学、航海学、工程学、理财学、兵学、史学、公法学、律例学、外交学、言语学、教门学、寓言学、西学丛刻书;卷三为天学、地学、人学(即医学)。
显然,《普通学书目录》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书籍分别编目,并将两者机械地组合为“一编”,中学书籍基本以传统四部分类为依据,而西学书籍主要以学术分科为类别原则。该目对现实图书馆如何统一编目与管理中西书籍提供了思路,“流风所扇”,影响甚广,几乎成为清末民初兴办的新型藏书楼及近代图书馆书目分类的不祧之祖。例如,1907年《浙江藏书楼书目》分甲乙二编,“甲编收旧学之书,分四部,设有子目。……乙编为新译书,分十六类,附日文书。”[23]1911年《黄岩九峰图书馆书目》“分五卷,前四卷为经、史、子、集四部古籍,按四部分类法编排,第五卷为‘科学书’”;[24]1914年《京师图书分馆藏书目》“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古籍图书,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编排,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五部分。……第二部分图书为中文类与外国文学类。其中前者又分政法类和科学类两类”;[25]1915年《教育部图书目录》“共八卷。第一卷为经部书籍,第二、三、四卷为史部书籍,第五卷为世界史及科技类书籍等,第六卷为子部书籍,第七卷为集部书籍,第八卷为丛部书籍”;[26]1915年《山东图书馆书目》将馆藏图书分为经、史、子、集、丛、科学、外国文、山东文艺、补遗9部;[27]1917年《河南图书馆藏书总目》将馆藏图书分为经、史、子、集、丛、时务六部;[28]1917年《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书目续编》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丛、“新”六部;[29]民国时期的京师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旧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新书分为总汇、精神科学、历史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七部”。[30]
总体上,中西书籍分列于一编,以经史子集为主的类目只收旧籍而不收西书;“科学”、“新学”或“时务”类则只收西书而不收中籍,两者各行其道,不相统摄,因而只是对两者简单的叠加和生硬的凑泊,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然而,“新旧二字,并无绝对界限;且平行之制,管理上颇多不便,此则以上诸法之根本缺点耳”[31]。并且,“新旧之书,标准难定,类分多无所依据,管理上亦多有困难”[32]。诚然,今天之“古籍”概以时间(1911年)为断,然1911年之前既有同文馆等翻译的西籍,也有中国人(如徐寿、华衡芳)撰写的西学著作;1911年以后,罗振玉、王国维、叶德辉、章太炎之伦又每有旧学书籍问世。
4 “学无中西”理念下的书目分类
“中西异学”褪尽了“中学西源”、“中体西用”赋予中学的光环,但过分强调中西二学之“异”,未能有效沟通两者之间的学理联系;“中西异学”规约下的书目分类也将中西书籍分封画疆为两个不相闻问的独立领域,这无疑既不便于中西二学的沟通,也不利于图书馆的文献管理。于是,“学无中西”理念下的书目分类便应运而生了。孙宝瑄认为天下学术约分穷理之学、探赜之学、习法之学三大类,所谓中西、新旧,皆无所逃乎是。他说:“愚谓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是地球之公理通矣,而何有中西,何有古今。”[33]王国维则指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学问之事,本无中西。”[34]
“学无中西”强调学术是古今中外“天下人”的学术,所谓中西、新旧之别,只反映了针对“天下”学术的对象聚焦与研究取径的差异。相应的,书目应该对中西图书予以统一分类,即在统筹考虑中西书籍现状的基础上,编制统一的类表、确立共同的类目。总体上,“学无中西”理念下的书目分类概分二系。
4.1 以中学为主建构书目分类体系
徐树兰以“存古”和“开新”为宗旨,于1904年创建古越藏书楼,其《藏书章程》曰:“学问必求贯通。何以谓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而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乎平等,而杜偏驳之弊。”[35]这是典型的“学无中西”的理念。相应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分学、政二部、47类、331子目。
正如作者徐树兰指出:“明道之书,经为之首,凡伦理、政治、教育诸说悉该焉。包涵甚广,故不得已而括之曰学部。诸子,六经之支流,文章则所以载道,而骈文词曲亦关文明觇世运,故亦不得蔑弃。至实业各书,中国此类著作甚少,附入政类中。”[36]总之,《古越藏书楼书目》从“天下”中西书籍总体系的高度予以统一分类,“学部”既包括易学、书学、诗学等典型的中学类目,也包括生理学、物理学等典型的西学类目;“政部”既包括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等典型的中学类目,也包括外史、外交、教育、军政、法律、农业、工业等以西学为主的类目,从而强调“学无中西”,无论中学、西学,皆含学、政(即“学理及实用”)二端。不仅如此,诸如中外各派哲学、名学、法学、小学、文学、教育、军政、法律、农业、工业、美术等类目也不再为中学或西学所专有。例如,“名学”既收中国先秦公孙龙等“名家”(诸子百家之一)著作,也收西方逻辑学著作。
另一方面,《古越藏书楼书目》虽然“自学理及实用二义分部,而中外学术,则归于平等,实较前人或勉强列入四部,或新旧分目较为进步,”[37]但仍是以中学为主体的。例如,学部以易学、书学等为首,政部以正史、编年史等为首,尊经重道仍然是其思想根柢。当然,他又将易、书、诗、礼等这些典型的传统类目缀以“学”字,改为“易学”、“书学”、“诗学”、“礼学”,并改子部为哲学、改集部为文学,等等,则又是以西方学理为尺度的大胆改造,暗含了从西方学术分科的角度解读中国传统学术的取向。而这一取向的进一步发展,则导致了以西学为主建构书目分类体系的尝试。
4.2 以西学为主建构书目分类体系
1903年,倡言“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奏定大学堂章程》新学制中提出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八科方案”,虽仍以“经学”居首,但实际上却是以西学框架配置中学知识,反映了中西二学真正的现实社会地位。观云于1905年指出:“近日有唱中国一切学问,皆当学于西洋,惟伦理为中国所固有,不必用新说者。是言也,其为投中国人之时好而言与?……夫今日中国之待新伦理学,实与他种学科,其需用有同等之急。”[38]这里,作为中学最后底线的“伦理”,也濒临颠覆的边缘。顾颉刚则云:“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39]强调应以西方学术体系分类古籍。在此背景下,以西法统一分编中西书籍也就变得水到渠成了。诚如刘国钧指出:“近世学术,侧重专门,故西方之图书分类亦主精详。中土学风,素尊赅博。故图书类部,常厌繁琐。窥测将来之学术界,则分工研究,殆为不二之途。”[40]
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用近代学科分类整理中西文献。该目分为哲学、教育、文学、历史地理、政法、理科、数学、实业、医学、兵事、美术、家政、丛书、杂书14类,“每一类中,各有子目。在十进法未输入我国以前,此《涵芬楼新目》实为新书分类之最精最详者”[41]。与上述《古越藏书楼书目》一样,西学书籍不再是附录外编、凑泊而已。并且,其“哲学”、“教育”等14个类名皆兼收中西书籍。但不同的是,《古越藏书楼书目》的类表设计具有明显的中学特色,类名的选择也大多取自传统书目;而《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则完全以西方学术分科理念为原则,类名的选用也完全不见传统书目的痕迹。
综上,在“西学东渐”的近代语境下,书目分类的历史演进,集中反映了传统四部分类益趋式微、西方学术分类逐渐蔚为大观的史实,这是与整个中西学术地位此消彼长的现实密切联系的。然而,上述书目分类尚没有出现分类标识;其类目等级亦多以二级为主,超出三级类目者概付阙如,等等,说明它们与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传统四部分类法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而“到西洋杜威十进法传入我国,经过改良以使适合部次我国典籍后,这些过渡时期所创订的分类,遂归于淘汰,没有人再沿用它们。”[42]
所谓“十分法”,即美国人杜威于1876年创制的《杜威十进分类法》,该目于1909年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根据新法,混合中西”而成《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分图书总目为十类,以一千号数为次序,如零到九数,分总目为十类”,其中,零为总类,其余为:一哲学,二宗教,三社会科学,四政治,五科学,六医学,七美术,八文学,九历史。“每类分十部,每部分十项,例如五百为科学类,五百一十为算学部,五百一十一为珠算项,余以此类推;如某项书多,十数不能容纳,则于十数之后,以小数志点之法代之以济,例如四百为政治类,四百八十为财政部,四百八十三为租税项,四百八十三又点一为海关税,余亦以此类推。据此编法,所有书籍均以类、部、项三者依次分别,以某数目,代表某书名,开明某数,取阅某书,较为简便。”[43]于兹而还,杜氏十进分类法逐渐为各图书馆所采用,并出现了大量的仿杜、补杜、改杜等形式有别但本质相同的书目。
以《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代表的这批书目,在图书分类的西方化道路上远迈《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等“过渡时期所创订的分类”,集中表现在:
第一,类表的总体设计和类名的选用基本做到了彻底“去中国化”,以此分类中西书籍,本质上意味着对中学书籍的西方化解读。正如吴康指出曰:“我以为要从最新式的分类,如分哲学、文学、社会学、博物学……等学,旧日经史子集纪中国图书馆的分类法。……按照现在的分类法做来,《易经》要归哲学类,《诗经》要归文学类,《书经》、《礼经》要归政治学、社会学、风俗学等。而旧日的分类,只用一‘经’字括之,‘简则简矣,其如不明何。’”[44]这意味着,对古籍从而对中学的西方学术分科化解读。
第二,类目等级化。例如,“四百八十三又点一为海关税”即达到了四级类目,从而意味着,除了上述学科属性原则之外,西方式的形式逻辑成为图书分类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换言之,类名与类名之间、以及文献与文献之间是有逻辑层次关系的。相比而言,中国传统分类的类名虽有等级层次,但文献与文献之间并没有等级关系。在传统书目中,一个类目只要能划分出下位类,例如《四库总目》子部—[天文算法(推步、算书)],则只有最下位类(推步、算书)具有安置文献的职能,如《周髀算经》入“推步”、《九章算术》入“算书”,而没有任何文献被安置在“子部”或“天文算法”等可以划分出下位类的类名之下。这样,类目之间的等级关系并不映射到被类分的文献之上。亦即,文献主题并不随着类名而作形式逻辑类项上的划分。
第三,由阿拉伯数字(以及拉丁字母)结构而成的分类标识,一方面强化了类目以及文献之间的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以某数目,代表某书名,开明某数,取阅某书,较为简便”,既方便了排架,也方便了文献检索,从而在技术层面上回应了近代public library的“公共”特征。从大处说,也为近代图书馆“开启民智”的诉求提供了技术可能。
第四,杜威式分类以文献整理和检索的现实效用为目标,以完善分类标识等技术为取向,在形式上不涉及到提要、序言等内容;在本质上也对中国古代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至“大弘文教”、“申明大道”的内涵一瞑不视。更为重要的是,以学科属性和文献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为核心的分类本质,事实上并不能揭示中学典籍的全部意蕴。例如,中国古代的《诗》既是文学作品意义上的“歌诗”,又包括“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志·诗赋略序》)的内容;《天文》既是“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的一门技艺,又可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汉志·天文序》)。从西方学科角度对《诗经》和天文著作的分类,无疑丢失了它们各自“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和“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的内涵。就此而言,今天的图书馆古籍分类仍以四部书目为主体,当非偶然。
总体上,西方近现代学术重视分科治学和理性精神。分科治学以培养学有专长的专家为职志,强调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而理性精神则要求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客观确定性。相比而言,中国学术强调赅博,以培养“全面人”为职志,尤其重视在治学中砥励个人品德;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中的客观性原则亦每每让位于价值原则,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求“善”的目标高于“求真”和“求美”的动机。就此而言,杜威式分类体系(包括事实上具有国标地位的《中图法》)是否具有必然的正当性,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来稿时间:2014年6月)
1.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37:139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51
3.梅文鼎.测算力圭序.//绩学堂文钞(卷二).安徽古籍丛书本
4.张自牧.瀛海论.//朱克敬编.边事续钞(卷6).光绪庚辰年(1880)石印本
5.徐仁铸.輶轩今语.//中西学门径书七种.上海:上海大同译书局光绪二十四(1898)年石印本
6.冯桂芬.采西学议.//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8
7.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文襄公全·奏议(四十七).海王邨古籍丛刊本
8,9,11,18,21,22,4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上海:上海书店,1984:140-142
10.姚名达.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47
12.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345
13.张之洞.劝学篇·会通.两湖书院,1898年刊印本
14.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论(第五章).//上虞罗氏辽居杂著乙编.1933年石印本
15.吴汝纶.与余寿平.//吴汝纶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195
16.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562
1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224
19.渐斋主人.新学备纂.天津:天津开文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本
20.明夷,等.新学大丛书.上海: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年石印本
23.(日)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梅宪华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84
24-29.郝润华,侯富芳.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
30.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民国七、八年度年终工作报告.教育公报,1920(5):13-17
31.金敏甫.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广州:广州图书馆协会,1929:37
32.刘简.中文古籍整理分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203
3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0
34.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367
35-37,42.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228
38.观云.平等说与中国旧伦理之冲突.新民丛报,1905.12.11
39.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31-32
40.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55
43.沈祖荣.仿杜威书目十类法·自序.武汉:汉口圣教书局,1917:1-2
44.吴康.“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之商榷.北京大学日刊(第6分册),1920.9.16
——以图情领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