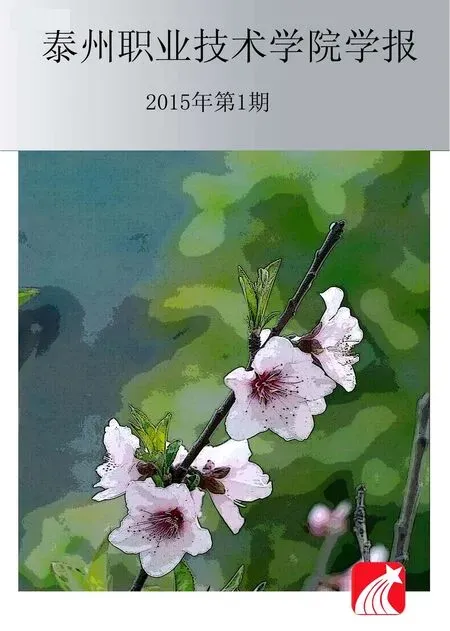论昌耀前期诗歌的 “寻父”主题
陈曙娟,赵龙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期刊社,江苏 南京 211168)
论昌耀前期诗歌的 “寻父”主题
陈曙娟,赵龙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期刊社,江苏 南京 211168)
昌耀前期诗歌以西部劳动人民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主体形象构筑了“父性神话”,“父性神话”又反过来为主体形象指引了不断努力的方向。“父性神话”是诗人由恋父情结向男子汉情结转化的表现,贯穿其始终的“寻父”主题,既根植于西部高原的父性文化传统,也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信仰相呼应,是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和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追寻。
西部;寻父;英雄主体形象;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
1957年昌耀创作伊始,其诗歌便展开一对扑棱棱的翅膀高高翱翔于相对独立的精神领空。无限的心灵自由和远眺的审美目光,并不意味着昌耀与时代的隔绝,他的写作是对时代无限敞开的。昌耀的诗歌转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转型后的各种现象大量呈现而基本完成。以1986年为临界点,昌耀的诗歌大致分为前期(1957-1986)和后期(1986-2000),本文以前期为论述对象。富有力量感和动作感的阳刚之美,在西部高原特有的父性文化传统中得到强烈的印证,也在西部的文学创作中得以集中呈现。昌耀作为西部诗坛的杰出代表之一,在前期创作中以鲜明的个人方式,叙写了具有较高艺术创造性的“父性神话”。那一首首弥漫着浓郁英雄气息的诗作,凸现了血性沉雄粗犷豪迈的英雄主体形象,是昌耀在个人的逆境和民族的苦难中对青春理想的高歌。
1 “寻父”主题的表现
西部大自然景观催发了昌耀充溢昂扬之气的主体生命意识的萌动。雄鹰、雄风、大山、大河等大西北的雄性物象,唤醒并照亮了诗人的男子汉情结和英雄气概。“雄性”的性别展示与充斥阳刚之气的大自然的描述相衬托,传递出诗人自我生命参与的炽热情感和深沉思考。
烧黑的砾石、败北的河流、烤红的河床——旷原之野所展现的大自然原生力量的酷烈,挑战着人们的极限。诗人一方面感受到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脆弱,另一方面则体会到一种勇于与痛苦和灾难相抗衡的悲剧快感:“我”像虫子一样,谦卑而敬畏地蠕动在山的一侧,在“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在锈蚀的岩壁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峨日朵雪峰之侧》)
朝圣大自然的谦卑和敬畏在诗人的血脉里流淌,更多时候转换为一种豪放、粗犷的情愫:“啊,边隆的山,/正是你闭塞一角的风云,/造就我心胸的块垒峥嵘。/正是你胶粘无华的乡土,/催发我情愫的粗放不修。”(《山旅》)“我”走在自然界诸多强大的生命之列,体内贮满了一种与大自然相匹配的威力:“我以多茧的双手拼读大河砰然的轰鸣,/胸腔复唤起摇撼的风涛。”(《断章》)“我”不满足于静望和惊叹,而要“放牧雄风”,做征服大自然的“风的牧者”:“在风靡的旷原迎风伫立/一个个虎背熊腰、批银冠金,只有风的牧者。”(《雄风》)
昌耀所作出的那种“人的强力的象征性显示”也出现在牧人、铁匠、征夫、水手们的劳动和生活里。如《鹰·雪·牧人》中的牧人:“在灰白的雾霭/飞鹰消失,/大草原上裸臂的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品尝了/初雪的滋味。”如《寄语三章》中的铁匠:“在他的眉梢,在他的肩项和肌块突起的/前胸,铁的火屑如花怒放,/而他自锻砧更凌厉地抡响了铁锤。/他以铁一般铮铮的灵肉与火魂共舞。”如《激流》中的征夫:“激流/带着雪谷的凉意以一路浩波抛下九曲连环,/为原野壮色为大山图影为征夫洗尘为英雄挥泪。”……在这些西部汉子身上,昌耀寄予了他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以及理想追求。他赋予这些人物英雄的品格,这是脚踏在大地上的平凡的英雄。
被打为“右派”的诗人,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曾被迫从事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段屈辱、艰辛的生活,使他更贴近西部底层人民,从而对命运的乖戾和生命力的强韧有了进一步理解。他在劳动的同时,感受到了勤恳、勇敢的体力劳动者的美好:“劳动者/无梦的睡眠是美好的。/富有好梦的劳动者的睡眠不亦同样美好?”“但从睡眠中醒来了的劳动者自己更美好。/走向土地与牛的那个早起的劳动者更美好。”(《晨兴:走向土地与牛》)作为新加入的草芥平民中的一员,诗人是自豪而快乐的:“我亦走进自己流汗的队列。”“黑河险峻的堤岸/是流汗者群踏出的人行古道。”(《黑河》)“我的生命是在风雨吹打中奔行在长远的道路。/我爱上了强健的肉体,脑颅和握惯镰刀的手。”(《这虔诚的红衣僧人》)
于人烟罕见的山谷、荒原、监狱、农场间流徙的昌耀,始终坚守自己的英雄情结和理想信念。他在诗歌中塑造的英雄人格是一种强烈的主体属性,和那种振臂一呼而走红于市的“公众人物”式的“英雄”毫不相干[1]。昌耀熟悉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人民,并且自觉地把自己也归类于其中。他不加掩饰地给予新中国底层建设者热情的赞美,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化的颅骨,真正的男子汉和英雄。
就连西部底层民众平时使用的牛挽或马挽的大木轮车——高车这一极普通的运输工具,在诗人眼中竟也拥有气势磅礴的英雄属性:“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高车》)当然,高车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和一些动态的叙事——使用它的人们付出力量、勇气和智慧去征服一切困难的过程是连贯的整体。
昌耀以他粗壮的诗笔,描绘了西部雄奇的山川景物和紧张快乐的社会劳动,描绘了牧人、铁匠、水手、鼓手、筏子客、伐木者、制陶工等具有剽悍的力量和顽强的意志的西部汉子,这是充盈着阳刚之气和英雄精神的乐章——昌耀以此构筑了他的“父性神话”。
2 “寻父”主题的成因
2.1个人因素
就昌耀的个体生命体验而论,他在初涉诗坛时便倾向于“父性神话”叙述,这恐怕还源于他对“父亲”的景仰和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或者说在这种生命机制下,他产生了强烈的“寻父”冲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寻父’是一种以仰视的姿态对某种卡里斯玛(christmas)式所在(人物符码或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的期待和呼唤,它表面上描述的是家族内部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实际上已形成一种类似于‘宏大叙事’的倾向,它往往构成了人类生存最深刻的部分,体现出生命密码的递转和文化基因的重编,对父亲的态度包含我们对自我对生命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文化全部复杂的感情。”[2]
昌耀的“寻父”冲动最初是沿着家族内部父辈的足迹而萌生的。无意于宴居的父辈们,离乡背井去实行自己的抱负,幼年昌耀在只有女眷留守的老宅里,饱尝一种空空落落的寂寞。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情结起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子女要是被迫与自己的父亲分开,这就可能导致他形成一种持久的恋父情结。
小学教师卢先生是幼年昌耀接触较多的屈指可数的几位成年男子之一,他那临危不乱的男子汉形象昌耀直到晚年仍然不能忘怀,这至少可以证明,在幼年昌耀心中恋父情结已经悄悄转化为一种男子汉情结。纷纷走向时代广阔天地的父辈对昌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向昌耀传递出一种召唤——一种英勇的男子汉形象和人格魅力的召唤。为了紧追父辈的足迹,昌耀在十四岁那样一个稚嫩的年龄,便毅然挣脱母爱的牵绊以参军的形式离家出走。他远赴朝鲜战场的前线,负伤回国后不久又投身于西部热火朝天的建设生活,可以说,男子汉的使命感一次次左右了少年昌耀人生之路的方向。
2.2时代因素
“父亲”成为昌耀超越个体血缘的精神慰藉和表露自我情怀的创作动力,在他的诗歌中象征了一种阳性的理想和行动,一种为超越苦难而进行的反抗。与社会规范的要求相一致的男性或女性的性别特征,体现了一个人的基本性别取向。不同的气质特征尽管与男女的生理特征有一定关系,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们实际是社会化的产物,它们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结构密切相关。作为可以成为自己的对象的自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结构。社会经验过程和社会活动过程,在主体的内心体验中多少会留下一些印痕。因此诗人朝向“父亲”这一目标自我不断成长和趋近的机缘,除去先天性的因素,主要是从外在得来的。
“通过这种关系,个体就处于不断的自我超越、自我确定之中而达到个体,并且,在这种关系中,普遍性就不再是外在的、僵硬的原则,而是促使个体自我实现的内在信念——心中的上帝。”[3]诗人坦言:“唯有那位年高德勋的水手长占有我们。”“水手长”与“我们”的这种关系便是诗人“心中的上帝”或“父亲”与主体形象的关系的一个精彩譬喻。就时代机缘而言,“那位年高德勋的水手长”喻指诗人的上一代人。
毛泽东是这代人的杰出代表,描写和歌颂过毛泽东的诗人不在少数。例如,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艾青便作了一首《毛泽东》。此类呈现给“人民的领袖”的颂歌,在其他诗人的笔下也连绵不断地产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及毛泽东逝世时达到高潮。
毛泽东既是高悬九天普照大地的红日,又是人民精神上一致认可的可敬可亲的父亲。李广田这样歌颂:“我们,我们六万万人民,/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4]柯平这样写道:“孩子流着眼泪/对父亲说/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 父亲。”[5]毛泽东成了人们精神的寄托和象征,初次享受崭新生活的诗人们除了对之进行歌颂,似乎无以更精确地表述自己的感恩戴德之情。回顾那个特殊的年月,谁也不能怀疑他们的真诚,这种感情异常醇厚地浓缩在人民心中,甚至承受住了十年浩劫的严酷考验。
随着时间的冲刷,理智最终占了情感的上风,被歌颂对象的光芒遮蔽的主体逐渐苏醒了。时至今日,诗人们更多地反省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后来者仍然尊重和爱戴伟大领袖毛泽东,但是对他身上附加的至上权威发出质疑:“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成了父亲?/一个人民可以依靠的父亲/也受其规范的父亲。”[6]因为“受其规范”,所以鲜活的个体生命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千篇一律的颂辞,出于心甘情愿也好,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遏制也罢,总之,“为了追随一位领袖/我们丢失了自己”[7]。
3 “寻父”主题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诸多诗人让“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时候,昌耀却依然把“毛泽东”供奉在神坛上,他在《毛泽东》一诗中这样写道:“一篇颂辞对于我是一桩心意的了却。/对于世纪是不可被完成的情结。”然而,这篇“颂辞”已非以往那种简单的个人崇拜,它的别具一格之处在于诗人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突破。与其说这里的“毛泽东”确指某位历史人物,不如说象征了一种时代精神。“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曾经产生过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在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那个特定年代的精神信仰的代名词?所谓“毛泽东时代”就是指那段红旗招展、激情澎湃的岁月,那段属于理想主义者的黄金岁月。可以看出,昌耀身上具有追随“毛泽东”赴汤蹈火的“好汉”情结,“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诗人所向往和追求的精神之父。
在我国当代大多数诗人那里,意识形态与主体性艰难而顽强地对抗着,两者不可调和、顾此失彼。对抗的结果往往不外乎两种形式: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被集体话语所遮蔽,或个体生命从时代大背景中逃离。但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普遍规律对昌耀却失去了有效的阐释作用。昌耀赋予“毛泽东”一种超越意义,并不意味着他向意识形态的皈依,而意味着他与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时代精神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契合。
昌耀把个人命运置于博大宏阔的时代背景中加以关照,进而在一种大意义场上书写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大意义场,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圣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那些理想、信仰、追求虽然是时代和社会作用的结果,但毕竟是他与时代和社会相互内化后他认可、需要、接纳了的高度。”[8]如诗人自己所言,“一篇颂辞对于我是一桩心意的了却。”这首作于1993年的《毛泽东》,展现了时代机缘为诗人提供的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人生旅途的精神追求。
“寻父”叙事大概有两种倾向:或者以“寻父”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精神需求;或者缅怀父性神话的光辉(颂父),在景仰父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成长为新一代父亲[2]。昌耀的“寻父”叙事结构朝后一种倾向发展,“那位年高德勋的水手长”占有了“我们”,“而我们也完全地占有他。”昌耀写道,“我成长。/我的眉额显示出思辨的光泽。/荒原注意到了一个走来的强男子。”(《断章》)其诗歌中的主体形象在经历了一番“寻父”的精神苦旅后,终于确证自我,成为一名“强男子”。
必须强调的是,抵达青海的最初两年,昌耀和多数人一样,充其量只是漂浮在洪亮的大合唱中的一个弱小的音符。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跌入生活最底层后,昌耀的生命才陡然变得沉重,其人生观和诗歌观犹如一棵移植的树,这时才真正在西部这片土地上成活。昌耀发现人生是一个不屈不挠搏斗的过程,而诗歌则是其沉甸甸的载体。若没有1957年的命运逆转,这个过继给北国的孩子,便很难在内质上与地域机缘所提供的精神之父相遇,他也许永远都不可能有机会如此坚定地宣布:“我们被这块土地所雕刻。/是北部古老森林的义子。”(《家族》)“我是这土地的儿子。”“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将不能/在冥思中同样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凶年逸稿》)
总之,在昌耀的前期诗歌中,“父性神话”的光辉不仅是主体形象不断努力的动力,而且为其确立了努力的方向。这种方向“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一种悬在的、规范的人的定义或‘本质’,毋宁说它是一种规范性、理想性,它的作用不在于提供具体标准,而是给生存提供一种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确认的意识,它使自我在使自身向之努力的关系中,进入生存。”[3]主体形象正是在不断抗争、不断完善的成长过程中,获得了其生存的价值。
[1]骆一禾,张玞.太阳说:来,朝前走[M]//董生龙.昌耀:阵痛的灵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2]杨经健.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J].文艺评论,2005,(5):20-24.
[3]李钧.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4]李广田.他在各处行走[M]//阿古拉泰.一百个诗人笔下的毛泽东.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5]柯平.诗人毛泽东[M]//阿古拉泰.一百个诗人笔下的毛泽东.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6]九水.儿子与父亲[M]//阿古拉泰.一百个诗人笔下的毛泽东.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7]蒙原.领袖毛泽东[M]//阿古拉泰.一百个诗人笔下的毛泽东.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8]薛卫民.我所认识的毛泽东[M]//阿古拉泰.一百个诗人笔下的毛泽东.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刘红)
The Theme of Changyao’s Early Poem“Finding Father”
CHEN Shu-juan,ZHAO Long-xiang
(Jiangsu Institute of Commerce,Nanjing Jiangsu 211168,China)
Chang Yao’s early poems are based on the working people of the west,he built the“myth of father”by shaping the prototype into main image,the other way round,the“myth of father”guided the continuous efforts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main body image.The“myth of father”ref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lectra Complex to man complex.The theme“Finding Father”ran through all along the poem,it both rooted in the western highlands of fatherhood cultural traditions,also was with“Mao era”in the spirit of faith echoes,which is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writing and pursuit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value beyond ideological basis.
west;finding father;hero body image;Mao era;ideology
I207.22
B
1671-0142(2015)01-0039-04
陈曙娟(1981-),女,汉族,江苏东台人,编辑,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出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