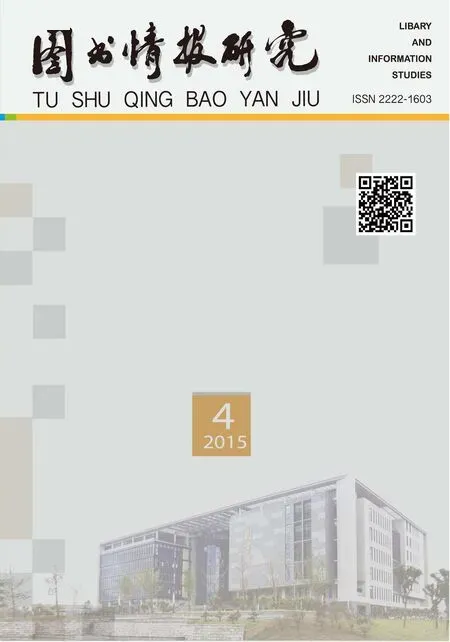谈谈《京报》“贺岁版”
钱承军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97)
谈谈《京报》“贺岁版”
钱承军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97)
从1923年开始,《京报》进入鼎盛期后,在版面的处理方法上发生了一些革新性变化,其中,改革“贺岁版”即是一项重要举措,且意义不凡,影响深远。本文从“贺岁版”的开辟、跨年度用头版、恪守本位突出、载录《京报》同人及社会关系详情几个角度研究报刊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最后,介绍《京报》“贺岁版”与“京报同人”吴鼎相关的信息。
京报 “贺岁版”“京报同人” 邵飘萍 吴鼎
上世纪20年代,时值中国报业蓬勃兴起,每年恭逢新年来临之际,各家报纸一般均会留出一定版面,登出诸如“岁首辞”短文或本报及社会各界的“恭祝新年”、“恭贺新喜”之类的贺岁词,以增节庆气氛并示对读者尊重之意。对此惯例,《京报》在创办之初及其后较长时段内无异业内同行,然而进入鼎盛期后,却在具体处理的方式方法上发生了重大革新性变化,且意义不凡,影响深远。由于年代过久,后人对这一《京报》史上的特殊现象从未给予关注和研究,故本文试以此为议题谈谈几点看法。
1 “贺岁版”的开辟
《京报》于1918年10月创刊,1919年8月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停刊,1920年9月“复活”,如同驶入快车道的列车,仅用短短两三年时间便发展成为北京地区数一数二的一张大报,乃至在全国也颇具一定影响力。这一时期,《京报》不仅在编辑采访、写作内容、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有瞩目建树,而且在标题、版面和栏目上敢于打破常规,力求推陈出新。其中,开辟“贺岁版”即为一项强有力的措施。
《京报》自创刊以来一直将头版设为广告版,每逢新年第一天,该版都会穿插刊登一些庆贺新年的内容,但所占比例并不大,主要内容仍以广告为主,这一与其他大报相似的惯常做法截止到1923年底,发生了令广大读者耳目一新的重大变化。
1923年12 月31日,《京报》头版特辟二分之一(上半部)的版面篇幅专门用来庆贺新年,尤在安排与设计上颇为独具匠心。首先,由社长邵飘萍以个人名义在醒目位置亲笔大字手书新年贺词:“恭祝各界新年进步,恕不另柬,邵振青拜”①注:“振青”为邵飘萍的字。;其次,以京报社和编译社(实为《京报》两块招牌一套班子)的单位名义并列紧随邵之后,亦用大字手书体分别致新年贺词:“恭贺新喜,京报社同人”②“同人”指情趣相投、志同道合之友。“同人办报”,意即私人以自愿的形式结合起来创办报刊。、“恭祝新年进步,新闻编译社同人”。接着,用小号印刷字体刊出以个人名义“恭贺新年”并“鞠躬”者共22人;以单位名义“恭贺新喜”并“敬贺”者计10家。第二天,也即192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京报》头版上半部刊载的内容与前一天完全相同。
如果说,《京报》在这一年辞旧迎新、庆贺新年的二日内用半个头版刊载贺新年内容的举措尚不能称作“改版”,那么再看看此后两年的1925年新年和1926年新年的《京报》头版便一目了然,该报不仅采用同样方法在岁末岁首二日的头版上刊出贺新年内容,而且占用了整整一个版面,从而使得平日的广告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贺岁版”。这一独树一帜的做法,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报界别无二家,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一种创新,究其原委,则与当年由社会开放力度加大而造成的中国报业民间化趋势有关。相对于之前官方或半官方③官方报纸如《邸抄》,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是朝廷传知朝政和臣僚知晓朝廷动态、政情的重要媒介。半官方报纸如清朝在北京出版的《京报》,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以及洋人所办的报纸,民间报纸的经营和编辑方针多由该报的社长、经理和主笔制定掌控,由此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新闻的时效性、准确性得以提高,而且在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社论或论坛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面貌。由此,《京报》“贺岁版”应视为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典范。
2 跨年度用头版
前已叙,从刊登各种“恭贺新年”信息的时间节点上看,其他大报均在新年首日,而《京报》却打破常规,在旧年岁末这一天提前刊登贺岁内容,其创意旨在提醒和增添“辞旧迎新”的喜庆氛围;而第二天的新年首日继续刊登同样内容,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恭贺新年”了,个中奥妙让读者眼前一亮,心领神会,也令内行暗自钦佩。更重要的是,《京报》跨年度贺岁,虽然只比其他报纸提前并多出一天时间,却充分体现出它对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尊重。众所周知,报馆是要靠广告来赚钱的,少登一条广告绝非小事一桩,而《京报》在连续两天的头版上少登或完全不登广告则是什么概念?经济上损失几多?明眼人不会不清楚这一点。那么其它大报对于一年一次的新年贺岁又是如何具体安排版次和版面的呢?且以当年赫赫有名的天津大报《大公报》为例参照,1925年1月1日,该报只是在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岁之希望》的论评,另有寥寥数条单位和个人的贺岁词,两者相加所占版面仅为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版面则为广告、启事和专电等内容占用。再以同日出版的上海《申报》为例,虽然该报在第一版以较多篇幅刊登了贺岁内容,但还是有一些广告、通告和启事参杂其中,故根本不能将其视为“贺岁版”。
各大报对于新年贺岁在时间节点和版次版面上相似或不同的处置方法,反映出它们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重视程度、经济考量和战略眼光诸方面的差别。相对而言,《京报》的办报理念显得更先进,眼光更长远,为了赢得读者的尊重和信任,它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而是风物长宜放远量,始终将心系读者、与民同乐置于首位考虑,何况读者的信任度与报纸销量是成正比的,此为《京报》的高人一筹之处。细节决定成败,《京报》之所以能在复刊三五年后便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销售量达到6千份,并自筹资金盖起了京城唯一的新报馆楼房,原因固然多方面,但我们从上述做法中却不难窥见一斑。
3 恪守本位突出
本位突出,也即以“我”为主,这是《京报》“贺岁版”看上去相当显眼的亮点,此处之“我”是个复数概念,一指京报社社长邵飘萍,二指京报社同人。从1923年底至1926年初,邵飘萍以个人名义在《京报》头版头条上先后6次“恭祝各界新年进步”,首次时间为1923年12月31日,其余5次依次为: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926年1月1日。反观同时期国内各大报纸,报社负责人在新年之际以个人名义参与他报贺岁似不鲜见,但将自己的大名赫然登在本报上贺岁实则罕见,更不用说是放在头版头条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了。
上述反差如此之大,固然与邵飘萍本人豪放张扬的个性,一贯特立独行的风格有关,同时,“因为当时国内各家报纸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党派报纸,民间独立的报纸不是没有,但鲜有影响”[1],而《京报》则是一张真正独立的民间大报,作为一报社长的邵飘萍,可谓“为民兼为国,无党又无私”[2],无需听人指挥或瞧人眼色行事。相比之下,若仍以1925年1月1日《大公报》第3版为例,上登参与贺岁的单位及个人,排在最前面的是驻军天津的奉系军阀将领郭松龄及少帅张学良,排在最后的才是大公报同人,个中缘由不言而喻。
至于如何突出第二个“我”,《京报》用整个头版篇幅刊登新年贺岁内容是在1925年新年和1926年新年这两年,但相较于1924年新年头版,邵飘萍及京报同人虽仍以手书体大字并列其上,但“京报社编译社同人鞠躬”却位于“邵振青鞠躬”之前,可见《京报》这一小变动更加突出了本报同人这个“大我”,此其一。再看随后用小号印刷体刊出的个人贺岁名单,据笔者统计,1924年为22人,其中京报社同人11人;1925年为35人,其中京报社同人15人;1926年为35人,其中京报社同人12人。从以上数据中不难析出:加上邵飘萍本人及因囿于版面而未登报的少数报社同人,那几年京报馆工作人员的人数约保持在15人左右。进而言之,京报社同人基本都登上了“贺岁版”,这种在当年各大报中独一无二的做法,用当下话语诠释,即彰显了《京报》非常重视团队力量和关心群众的一种管理理念,此其二。
4 载录详情介析
4.1 披露京报社同人组成情况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并进行仔细查核,1924年登上“贺岁版”的11位京报社同人是:汤修慧(邵飘萍夫人)、吴定九(《京报》创办人之一,报社经理)、王小隐(《京报》重要撰稿人)、姚钧民(编辑)、马秉乾(编辑)、王懿年(记者)、许邦璋(记者)、童蒙正(经济版编辑)、朱鸣凤(编辑)、徐凌霄(《京报》特约编辑,副刊主笔)、唐林(经济版编辑)。
1925 年登上“贺岁版”的15位京报社同人是:汤修慧、吴定九、王小隐、凌霄汉阁主(徐凌霄)、姚钧民、邵新昌(编辑、总务)、王生瑄(编辑)、马秉乾、唐林、沈江(记者)、孙伏园(《京报副刊》主编)、邵逸轩(美术版编辑)、许邦璋、邢墨卿(《京报副刊》编辑)、郑寿铭(记者)。
1926 年登上“贺岁版”的12位京报社同人是:汤修慧、吴定九、邵新昌、马秉乾、孙伏园、吴平涛、王生瑄、张汉徽(记者)、徐彬彬(徐凌霄)、沈江、朱鸣凤、许邦璋。
从名单上人员的排列顺序和出现频次可以看出,汤修慧和吴定九二人的名字位置靠前,出现频次高,他们是京报馆内仅次于邵飘萍的角色,这也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符。
4.2 反映《京报》社会关系情况
从目前已掌握材料划分,包括京报社同人在内的参与贺岁人员的身份来源及与《京报》之关系,大致可分以下两种类型。
一为京报社主要负责人的亲属、同乡、同学、友人。社长邵飘萍方面有:夫人汤修慧、汤念曾(汤家亲戚)、堂弟邵新昌、堂侄邵逸轩、施履本(日本东京法政学校校友,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任秘书)、邢端(日本东京政法学校同学,曾任北洋政府工商司司长)、汪厥明(浙江金华同乡,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经理吴定九方面有:岳父杨若、弟弟吴平涛、妻弟杨光暄,另有戴蔼庐(南洋中学同学,《银行周报》主笔)、袁英辛(英瑞炼乳公司经理,长女吴大年干爹)、戴兆鉴(南洋中学同学,浙江商界知名人士)、瘳世经(江苏嘉定同乡,曾任奉天检察厅长和驻朝鲜外交官)、瘳世纶(江苏嘉定同乡,曾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工艺局局长)。
二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教育界有:林众可(法学教授、学者)、石学万(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代表)、陈顾远(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师,上海《民国日报》撰稿人)、沈兼士(沈尹默之弟,北平大学教授,语言文字学家)、沈步洲(北大预科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孙柳溪(北京医科大学校长,耳鼻咽喉科专家)、顾名(平民大学教师,戏剧评论家)。报业同行有:王伯衡(《申报》名记者)、龚珏(《京报副刊》撰稿人)。金融界有:邓文藻(北京汇丰银行经理)、李远钦(大陆银行会计主任)。戏剧界有:马连良(京剧名伶)、韩世昌(昆曲名伶)、刘步堂(戏剧评论家)、吴象乾(京剧名票友)。
其他方面有:马志振(法学界人士,《京报副刊》撰稿人)、吕咸(财政界人士)、秦曾铖(山西建昌煤矿公司工程师)、林椿年(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椿年医院院长)谭孔新(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科毕业生,可能时在京报社实习)、陈迪修(上海中华学艺社成员)。
需加说明的是,以上两种分法的界限并非十分明晰,因为第一类中不少人也是各方知名人士;第二类中一些人,如韩世昌和马连良则是邵、吴的共同朋友。又因年代久远,目前尚无法将“贺岁版”名单上每个人与《京报》的渊源关系完全梳理清楚,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除贺岁个人,参与贺岁的单位共计38家,其中银行12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孚银行、银行公会、中华汇业银行、北京商业银行、北京华威银行、盐业银行、察哈尔兴业银行、聚兴城银行。书刊出版机构5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北京银行月刊社、戊辰杂志社。医院和药店6家:博爱医院、山本医院、慈育兽医院、寰西医院、椿年医院、华安药房。企业9家:佳丽鞋庄、南洋公司兄弟烟草公司、协和烟公司、正昌烟公司、北京电车公司、精益眼镜公司、中央饭店、英商炼乳公司、通易信托公司。学校2所: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剧院3家:真光剧场、开明剧院、中天电影院。通讯社1家:亚陆通讯社。
详细载录参与贺岁的个人和单位,如实反映《京报》人员组成,使得今人能够直观地了解当年《京报》人气之高、涉面之广的兴旺景况,这正是“贺岁版”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所在。
5 “京报同人”吴鼎
“贺岁版”是产生于《京报》鼎盛时期的一个特殊版面,它从一个侧面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京报》提供了一份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我们以此为新切入点加深对“京报同人”的再认识。归根结底,《京报》之所以重视同人作用,是因为它作为一张无党无官背景的民间大报,走的是一条同人自由办报的独立路线。其实,在当时法律许可下,几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联合发起并创办一份报纸并不鲜见,不过要办成像《京报》那样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影响的大报,在京城乃至全国却是寥寥无几,二者区别就在于同人之间是否能真正做到自始至终志同道合。《京报》做到了这一点,它在这一时期对此要素的把握和处理相当到位得体,报馆同人之间团结合作,和谐友爱,在业内令人羡慕,堪称楷模。
同人办报,恰如俗话所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京报》创造的骄人业绩与邵飘萍这个名字不可分,同时也与京报社的几个关键人物紧相联。《京报》自创刊至1926年4月邵遇害前后这段时期可称为“邵飘萍时期”,其时除贤内助汤修慧和几个家乡亲戚外,先后有潘公弼、吴鼎、潘少昂、孙伏园、徐凌霄等友情笃深的同人协助邵飘萍编撰报纸和经营报社管理,他们为《京报》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不过,这些人中从头到尾一直伴随在邵左右,并与其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的只有吴鼎(字定九)一人。
关于吴鼎其人及与邵飘萍之深交关系,笔者曾专门撰文介绍过其生平事迹[3],散木先生的《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一书中亦有多处涉及,此处不重复赘言,仅就“贺岁版”中新透露出的相关信息略介。
如上述,从贺岁个人名单中可知,来自邵飘萍方面的亲友有7人;来自吴定九方面的亲友有8人。这一方面映衬出那个时代同人办报的一种亲缘维系特点,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表明吴在京报馆中的地位,作为邵最重要、最得力的助手,吴主要负责报社经营管理并兼编辑记者于一身,苦心经营《京报》十多年,其身份实质上是京报馆二把手,而其他同人尚达不到这一程度。
另外,有关《京报》报头出自谁之手笔,素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邵飘萍手迹,另一说为吴定九手迹,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笔者之前亦曾为此迷惑,但通过考证“贺岁版”却顺带找到了答案。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正确,但也都不够全面。查阅1924年新年贺岁版可知,其报头“京报”二字无疑出自邵飘萍之手,即便回溯到1918年10月创刊时进行比对均无大变化。但从1924年12月31日这天起,《京报》报头却明显换成另一人手迹,经笔者请有关专家比对吴现存其他手迹,该“京报”二字确实为吴定九手迹,此后直至1937年7月《京报》停刊,其报头字迹未再有任何变化。为何1924年底《京报》报头要将邵的手迹换成吴的手迹呢?现有史料未见记载,不好随意下结论,但恐最合乎情理的解释,莫过于此事是由邵、吴二人生死与共、亲如手足的挚友关系所决定的,而其他人同样达不到这一程度。
6 结语
1926年4 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京报馆被查封,此为《京报》由盛转衰之分水岭。1928年8月《京报》第二次“复活”,四个多月后的1929年1月1日,《京报》沿循传统复辟“贺岁版”。然此“贺岁版”远非彼“贺岁版”,上面除登出以京报同人的集体名义和以报社负责人汤修慧个人名义的贺岁词外,其他个人和单位的贺岁词加起来不过12条,相比三年前犹如天壤之别,显得格外淒清落漠,给人以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怜惜之感。如此落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继任者有心却无力续写昔日《京报》辉煌的一种无奈窘况,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后邵飘萍时期《京报》的发展遭遇哪些瓶颈?京报同人们都有哪些变化?这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究。
[1] 散 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M].广州:南方出版社,2006:174.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东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邵飘萍史料专辑[G].东阳:[出版者不详],1985:263.
[3] 钱承军.京报元勋吴定九[J].新闻大学,1995(3):38-39.
(责任编校 田丽丽)
The New-Year-Celebrating Version of Peking Press
Qian Chengjun
Library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Starting from 1923,Peking Press began a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and there were some innovative changes in the processing method of layouts,wherein,the reform of the new-year-celebrating version was an important measure,and ha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The present article studies this special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newspapers from several aspects,which are creation of the new-year-celebrating version,the cross-year front page, highlighting its own responsibility,and listing in detail the colleagues and social relations.Finally,it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information on the new-year-celebrating version of Peking Press in relation to Wu Ding.
Peking Press;the new-year-celebrating version;Peking Press colleague;Shao Piaoping;Wu Ding
G219.29
钱承军,男,1958年生,研究馆员,发表论文数篇,著有《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书海巡舟》等。
——新年贺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