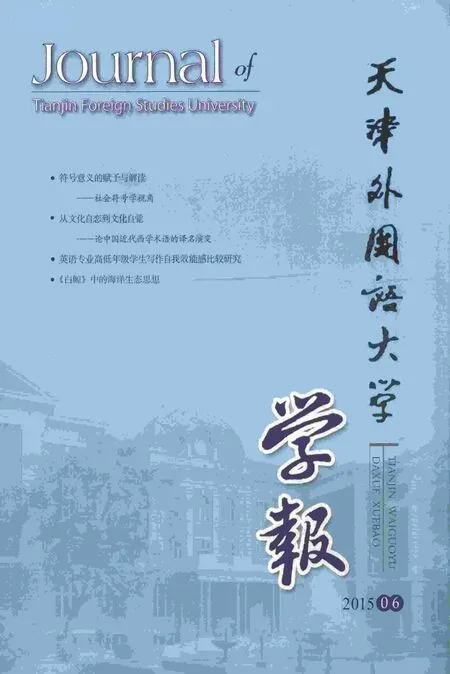身体的言说——身体作为社会符号
丁建新,刘向东
(1. 湖南城市学院,湖南益阳 413002;2.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3.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一、引言
当代文化研究把身体作为一个重要视角。这个视角下,身体不只是物质实体、生物数据或是生理学事实,而是作为社会符号的身体。符号化的身体与其他符号具有同质异构性,都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现实的身体作为能指,表征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此外,符号化的身体除了反映社会文化,还建构社会文化。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体的文化研究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与后现代思想中反逻各斯、多元、解构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追踪身体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阐释身体的社会符号学内涵。研究发现,人类认识对待身体的态度反映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范式。身体的背后是人类不断更迭的社会、文化体系,通过对身体的考查,可以发掘隐藏在身体符号背后的社会、文化内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身体具有了社会符号学内涵,身体建构文化的功能源自身体的社会符号属性。
二、身体史与文化史
1 身体的压制:理性主义
身体除了作为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从古自今,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反映人类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反过来,通过对身体的塑造,甚至改变,人类也建构着不同范式的社会文化。正如卡瓦拉罗(2006:96-97)所说:“尽管具有不稳定性,身体在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我们对社会身份的假设和我们对知识的获得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角色。”Turner(1996:6)也明言:“我们主要的政治和道德问题都通过人类身体的渠道进行表达。”
自古希腊时代到现代主义,西方世界的思想基本是以理性主义为主导。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对身体的贬斥。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开拓者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表现出对身体的不屑。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灵魂才是永恒存在,身体是人类回归灵魂的羁绊。所以他在面对死亡时微笑坦然,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所毁灭的仅仅是肉体,灵魂是无法毁灭的。柏拉图(2000:7,15)对身体的歧视与敌意更是直言不讳:“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要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
中世纪的西方文化强调灵与肉的对立。这一时期,古希腊时代的灵魂化身为上帝,整个中世纪思想史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成为理性的化身。《约翰福音》明确宣称生命是属灵和永恒的,肉体的存在则短暂易逝,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罗马书》中也强调:“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生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尼采,1997:27-28)所以,在这种身体与灵魂对立思想的统治下,出现了西方中世纪文化的禁欲理念。要通达灵魂和上帝就必须克服肉体的种种欲望,肉体与上帝是敌对关系。漫长的中世纪文化史就是身体备受冷落的文化史。在现实中,人们通过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等方式达到祛除欲望的目的,从人类世界走向上帝世界。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的统治地位慢慢淡出,人类的注意力回到人本身。启蒙时期,人类的注意力对身体有所关注。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用各种方式展示人体、人性之美。但是,相对于理性而言,身体还是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启蒙时代语境下的身体被看成是一个感性事件,是通达理性的途径。这一传统被现代性哲学的代表笛卡尔、黑格尔发展到极致。笛卡尔的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把人的理性思维提升到了人的本体存在的高度。在他那里,身体是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幻想的代表,心灵则是理性、稳定性、确切性和真理的代表。笛卡尔(1986:90,228)说:“人的精神或灵魂与肉体是完全不同的”,“在肉体的概念里边不包含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反过来,在精神的概念里边不包含任何属于肉体的东西。”黑格尔哲学的精髓是“绝对精神”、“绝对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人的本质也被抽象为一种绝对的意识和精神,成为一种“思辨人”,其本质是“抽象的人”。人的历史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的历史,身体陷入了人类历史的无尽黑暗之中。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对人的论述时说:“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2009 :207)。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史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对身体进行压制,身体相较于本质的、永恒的存在根本微不足道。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逻辑的思考和推理才能获得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理性的羁绊——身体,要么被彻底排斥,要么在为理性认识服务完后被扔进思维的垃圾桶。
2 回归身体:从尼采到福柯
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其结果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两次世界大战空前的破坏性与毁灭性、理性主义操控下的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对自然的破坏,诸如此类问题开始让人类反思理性,重新思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以及感性的重要性。在这一语境下,身体作为感性认识的物质载体,在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中上升到主导位置,哲学家们开始把身体作为武器,来挑战理性主义的权威。
尼采提出了身体一元论,把人的精神、意识、思维、认知都归为身体。(张之沧,2008)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与启蒙思想不是表现出对身体的压制,就是表现出对身体的反感,都对身体不以为然。只不过是,前者借用了上帝的名义,后者则借用理性的名义。于是尼采开始了动物化身体的叙事,他刻意嘲笑身体与意识的二元对立,他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拒绝“灵魂假设”,他想用他的激情、才华与能力,力图拯救一个真正的“人”。他激烈地批判作为形而上学典范模式的二元对立,从而将身体置于突出的地位。“无数的错误皆源于意识……简单地说,只用意识,人类必定会走向崩溃和毁灭。”(尼采,1984:71)“我憎恨狭窄的灵魂有如魔鬼,那些灵魂既不生善,亦不生恶”;“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身体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义。是一战斗与一和平,是一牧群与一牧者。兄弟啊,你的一点小理智,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兄弟啊,在你的思想与感情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 一个不认识的智者——这名叫自我。他寄寓在你的身体中, 他便是你的身体。”(尼采,1992:27-28,39)
福柯对待身体的态度也是反理性主义的,但与尼采不同的是,福柯把身体置于人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考查,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对身体的改造,强调权利向身体的进犯。如果说福柯之前的身体理论是在强调身体作为文化符号的一维的象征关系的话,那么福柯就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了二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身体象征文化,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类不同文明时期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文化,通过对身体施加作用而进行巩固、改造和建构。在身体与权利和政治的关系上,福柯强调后者对前者的规训:既有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模式通过对身体实施不同方式的惩戒,来达到巩固和延续这种既有社会体制的目的。在福柯 (1997:27-28)看来:“身体或者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每当我想到权力结构,我便想到它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谢里登,1997:281)。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通过对身体的控制、干预等方式,获得复制和再生产,社会生产身体的过程也就是生产权利的过程,权利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可以通过社会中各主体间的身体关系来构建。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就从一种单纯的物理性或生物性存在上升为一种社会存在,发挥社会符号的功能。事实上,身体对社会文化的表征与建构,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所具有的社会符号学价值。以下我们做详细的探讨。
三、身体作为社会符号
1 身体作为能指
人类是符号性的动物。符号的使用使人类在意识中把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使人类自身能够脱离主体的躯壳,站在客体的位置去审视自我的存在。这样,人类不仅可以活在当下,还可以回到过去、思考未来。
索绪尔(1996:102)把语言符号分析为一体两面的一对概念:能指和所指。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两者的结合成为符号。索绪尔是从语言系统出发来阐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事实上,符号学作为一个大系统处处都存在这种能指与所指的表征关系,正如巴尔特(1988:135)所言:“符号学的记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它也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例如在公路规则中绿灯的颜色表示通行的指令)。”就身体而言,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肉体,其背后是一个无形的、庞大的文化体系。这样身体就是一个广义上的符号,有形的肉体是符号能指,无形的文化内涵是符号所指。
把身体与其背后所表征的文化意义作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对待,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洞悉身体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可以用社会符号学的理论来进一步研究身体的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身体与人类语言一样,无时无刻都不在言说。就本体论而言,言说的身体才是人类身体真正的存在方式。这与海德格尔说的作为语言本体存在方式的“言说的语言”是一致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的本质在于“语言说”。“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我们答曰:语言说。”(海德格尔,1999:2)而人说的语言是在语言自身的言说中进行,这就构成了他著名的论断“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思者与诗人是这一家园的看家人。”(海德格尔,1987:201)实际上,海德格尔所说的“言说的语言”就是存在于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层面上。社会生活通过符号的方式来约定、运行、巩固、变革,所以人通过符号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中。身体作为文化的能指,其背后是对身体文化意义的约定俗成。反过来,已经约定俗称的身体的社会意义又通过身体能指得以表征,个体的身体行为也只有在社会身体的语境下才能获得有效的表征与解读——身体不说但又无时无刻不在述说。
2 身体表征与建构社会文化
社会符号学认为,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就是一座意义的大厦——一个符号结构,很多话语都会遵循一定的程序,受社会规范的制约。除了探讨语言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外,社会符号学还试图解释社会成员构建社会符号、社会现实被塑造、限制、修改的过程。而这些过程对社会现实的构建并不如理想所描述的那样,相反,往往会对短视、偏见、误解视而不见甚至制度化(Halliday,1984:2-4,125-126)。这就是说,一切符号都承载着文化信息,符号不仅表征社会文化内涵,而且反过来具有建构社会文化的作用。吕红周(2014)指出:“人以符号的方式感知世界、理解自然,并且同样以符号行为给世界命名,正是以语言的可理解性为基础,人类方能不断的解读出宇宙中遮蔽着的秘密,人的符号化行为就其总体来看是给整个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当然这也是对人类拓展空间的符号记录。”Fairclough(1992:64)认为,一方面,话语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受到社会结构的塑形和约束;另一方面,话语又建构社会。作为符号的身体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族群对待身体的态度凸显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对身体的规训与教化与对语言的规训与教化一样,是社会制度巩固与自身再生产的方式。
首先,从历时维度看,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身体文化。在没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作为肉体的身体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有机体,都在进行着亘古不变的化学反应。但是,一旦人类从普遍的动物界脱离出来,从原始人柳叶遮羞那一刻开始,身体就开始负载文化内容。而且,这种文化内容是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变而演变的。所以,肉体还是那样的肉体,而肉体背后的文化信息却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唐代,女性身体是以胖为美的。可是到了现代,纤细的腰肢与凸显的锁骨才是美女的特征。“待字闺中”的封建文化,用对女性身体的约束来体现其男权地位、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而对女性的解放,也是通过其身体的解放实现的。解放后,中国女性开始从近乎自虐的缠足制度中解放出来,体现了新时代女性地位的提高。所以,身体表征文化。反过来,一种社会制度通过建立与推广主流的身体文化,使这一文化在人们中间形成集体的无意识,巩固与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例如,生在封建社会的女性,会以大脚、见生人为耻。要是想在公众场合露面,还要女扮男装。西方也不例外,从维多利亚时期把身体包裹的严严实实到现代超短裙,不同时代的时尚元素通过对女性身体的作用而建构女性的身份特征。所以,一部身体史就是一部文化史,这其中充斥着文化对身体的约束与身体不断突破文化约束的辩证关系。
其次,从共时维度看,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以及同一社会制度中不同的族群之间,存在不同的身体文化。对身体不同的符号化方式反映出不同文化的主体性特征,也是身处这一文化范式中的人们寻求文化身份、文化归属的方式。就个体而言,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会按照这个文化群体的规范去展示并塑造自己的身体,以强调自我文化身份的独特性。就种群而言,一个社会或一个种群会对其成员进行身体的约束或改造,来保持并加强这一文化群体的独特性。所以身体是人类寻求文化身份与归属的现实基础,不同的人和人群通过对身体做出不同的改造,来凸显自己文化的特质。例如,在同性恋人群中,人们通过变性手术,人为地改变身体的自然状态,试图获得反面性别的身份认同。也有女性通过做处女膜修复术,来迎合现存的社会价值体系对女性价值的评判方式。
再次,从范时空的维度看,人类通过对自己身体进行标新立异的改造,达到与主流文化相对垒、反抗主流文化乃至突破主流文化的目的。丁建新(2010)曾经从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角度探讨过“反语言”问题:“反语言不仅是一种相对于主流语言具有不同词汇特征的语言形式,更本质的是反文化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范式的更迭与斗争中起着同样的作用。与主流语言相联系的是主流身体,与反语言相联系的是反身体。例如,rap歌词中充斥了非正式的俚语的用法,而rap歌手也会相应地将这种特殊身份在形体塑造上体现出来。这种形体塑造表达对主流乐坛的一种反制。
总之,作为能指的身体,其背后的文化所指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普遍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一个血肉之躯就获得了社会存在。而个人的身体作为社会身体的一员反映个人的文化身份、社会关系、价值观等社会存在。这样,由个体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成为一个社会身体的集合,依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有特定的结构、行为规约,使身体获得社会意义的同时又建构社会意义。反过来,对身体的改造一方面巩固即有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其进行反制甚至超越,在建构新文化范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3 身体的后现代建构
身体作为社会符号的作用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背景下获得最大的凸显。究其原因,是因为后现代思想对传统哲学中中心论、二元说的反制。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作为社会文化意义的表征也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
3.1 后现代思想与身体
现代思想以结构主义、理性中心、逻各斯中心为导向,强调事物的共性以及事物背后有条不紊的秩序和结构。到了后现代,这种思想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被无情地解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方法,试图超越物质与意识的界限,主张哲学研究应该以“现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胡塞尔,2007:88)。这就把事物的本质从客观理性主义拉回到主体意识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强调差异、无限延宕。本来具有固定结构、中心思想的文本被德里达解构为“不再是完成的作品集,也不再是一本书内的内容,而是一张差异网,一张不断指向自身以外其它东西,指向其它差异踪迹的踪迹网”(Bloom et al.,1979:83)。总而言之,后现代思想主要以反中心、反理性、反逻各斯为主,强调文化的多元、异质和人的主体意识,总体上是一种人本主义。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身体作为人类自然存在的第一基础,就毫无疑问地承担起反制传统的职责,在对身体的解放中体现其后现代特征。
3.2 多元文化中的身体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状况下,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其他知识领域,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对普遍性、一元性、同一性、确定性等的追求的合法性已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对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异性的肯定和崇尚(刘放桐,2000:612)。多元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各种相互差别又相互交织的文化模式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诉求。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每一种社会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都希望在文化交往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过去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各类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不再以主流文化的马首是瞻,而是通过强调差异性、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建构自我的存在价值。
作为文化表征的身体,在多元文化的舞台上也获得了新的表征内容。身体与文化的关系永远是相辅相成的。多元文化建构多元身体,又通过多元身体建构自身。就种群而言,每一种文化范式都希望通过对身体的改造与加工,凸显自我的价值。年轻人通过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各种颜色,在身体上纹各种图案、穿刺等来表达他们的时代元素。一些特定的文化人群,如同性恋、素食主义者,甚至通过裸奔来表达其精神诉求。就个人而言,每一个人都试图通过对身体的装饰与改造,在人群中凸现出来。曾经象征一个时代的整齐划一的中山装,象征学生身份的校服,再也不会成为大众标榜的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服饰和对撞衫的反感。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多元时代,包括政治的多极,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作为文化能指的身体也通过自身的进化,获得了新的文化所指。这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多元文化不是要否定主流文化,多元身体也不是要否定主流身体,而是建构有意义的“他者”的一种方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民主意识的提升。
3.3 消费主义中的身体
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消费主义的崇尚。后现代思想对理性的反叛和对感性的推崇表现在身体上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达到对感官的刺激,“感官的盛宴”是后现代身体文化的典型特征。人类的几大感觉器官再也不满足于受理性操控、压抑、甚至灭杀的禁锢,在一场场“感官的盛宴”中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在这一时代,身体再也不是人类通达真善美的藩篱,身体本身就是真善美,来自身体的各种欲望应该得到合理的满足。正如费瑟斯通所言:“在消费文化中,人们宣称身体是快乐的载体:它悦人心意而又充满欲望,真真切切的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美丽、结实的理想化身,他就越具有交流价值。消费文化容许毫无羞耻感地表现身体。”(汪民安,陈永国,2011:284)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流文化的舞台。
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强调身体的共时性、建构性、广告性。因为失去了理性的压制,所以人们只能诉诸感性来找寻存在的意义。解放了的身体通过各种对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改造,最大限度地刺激身体的感觉器官,努力使身体的各种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种“活在当下”的身体意识,把人分解成一个个细小的碎片,作为整体存在的人弱化了。吸毒、摇滚、重金属使人在感官的极端刺激下获得即时的、愉悦的享受;过度包装、眼花缭乱的广告通过各种媒体引诱人们为满足身体欲望而消费。在消费社会,人的欲望被无限放大,而理性变得式微。人为了满足身体的无限欲望而无限地消费着。可是,从理性的禁锢下解放出来的身体又进入另一个极端:对身体欲望的无节制的追求,这就又使得身体陷入了感性、欲望的牢笼。例如,为了吸引异性的关注,现代女士穿的鞋跟越来越高,有时甚至去做美容手术。如果说人的身体以前是理性的奴仆的话,那么现在俨然变成了感性的奴仆,处处为感官的愉悦而受到奴役、甚至摧残。
四、身体建构文化的动态特征:互为身体性
Kristeva(1986:36)受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影响提出了文本的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不管是“复调”还是“互文性”,其理论要旨都是强调文本语义的动态性——包括读者、文本在内的各种声音在一个共时空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意义。这样,一个文本再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存在,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一次次获得新的文本身份的过程。究其原因,是文本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作为社会符号的身体使身体成为一种社会文本,就像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一样,社会中每天都在进行着“身体的叙事”。身体建构文化的过程也是互文的,我们可以把这种过程称作互为身体性。作为实体存在的生理性身体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其基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作为文化符号的身体是社会性的,在身体与身体之间的互动中建构自我的身份,进而建构社会文化。互为身体性把人的身体纳入一个社会文化的网络,在与网络中其他身体的互动中建构自身的身份。这样,每一个身体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其存在方式充斥着他人身体的种种印痕。就个体自身而言,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是一个连续体,其现有身体的文化特征往往会反映成长过程中某一时刻其身体的存在状态。例如,人在成年时期所表现的身体行为特征可能与童年时身体的经验有关,这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说的很清楚。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体身体蕴含着许多他人身体的特征。例如,在家庭关系中,子女除了从父母那里获得一个生理性身体外,还通过父母对其身体的教化,获得父母身体的某些文化特征。这一点,在穿着和饮食等行为习惯上体现得很明显。所以,个体身体之间存在一种“互为身体性”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决定着个体身体的文化特征。最后形成一个身体的网络,建构社会文化。
五、结语
身体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是一个社会符号。其存在方式、历史演变与其他符号一样,体现着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内涵。对身体的规训与教化是对人文化的规训与教化,是社会文化巩固、变革、建构的必要方式。通过对身体的考查,可以洞悉文化发展脉络、不同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种群的文化特质。就个人而言,其许多行为方式都可以在他的身体文化特征中找到答案。身体虽然默默不语,但时时处处都在言说着人,言说着人类的文化。
[1] Bloom, H. et al. 1979.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3] Halliday, M. A. K. 1984.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Heinemann.
[4] Kristeva, J. 1986.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A]. In T. Moi(ed.) The Kristeva Reader[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5] Turner, B. 1996. The Body and Society [M]. London: Sage.
[6] 巴尔特. 1988.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
[7] 柏拉图. 2000.斐多[M].杨绛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
[8] 笛卡尔. 1986.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 丁建新. 2010.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J].外语学刊, (2): 76-83.
[10] 福柯. 2003.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
[11] 海德格尔. 1987.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12] 海德格尔. 1999.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3] 胡塞尔. 2007.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4] 卡瓦拉罗. 2006.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5] 刘放桐等. 2000.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16] 吕红周,单红. 2014.斯捷潘诺夫的符号学思想阐释[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6): 8-13.
[17] 马克思,恩格斯. 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18] 尼采. 199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 尼采. 1984.快乐的科学[M].台北:志文出版社.
[20] 尼采. 1997.苏鲁支语录[M].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1] 索绪尔. 1996.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2] 汪民安,陈永国.2011.后身体:文化、权利和生命政治学[C].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3] 谢里登. 1997.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M].尚志英,许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4] 张之沧. 2008.对身体的整体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 (5): 4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