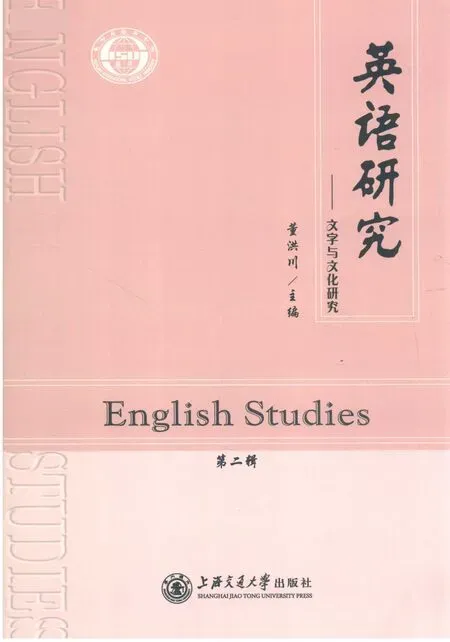作者的大脑如何建构故事?①
——论泰戈尔短篇故事的情感与伦理
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著 汤轶丽译
(1.康涅狄格大学英语系,美国康涅狄格州203860;2.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40)
作者的大脑如何建构故事?①
——论泰戈尔短篇故事的情感与伦理
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著 汤轶丽译
(1.康涅狄格大学英语系,美国康涅狄格州203860;2.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40)
对于多数人而言,作者以个人习语的叙事方式编织故事。个人习语的叙事是一系列原则,它们使可能有因果联系事件的模仿得以实现为故事的产物,其中囊括原型,即定义故事种类的结构。这些原型,或曰原故事,是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复杂融合,引导人们对真实世界中的事件以及虚构故事产物的解读。相差无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拥有一系列的原故事,其中占据重要特殊地位的类型便是基于情感依恋的原故事,这种情感依恋最初以父母与孩童的关系为特征。此类型的原故事着眼于情感依恋关系的搭建与伦理和政治维度的违反。具体言之,泰戈尔对于伦理以及政治的想象很大程度受稳固发展的依恋规范指引,并迸发出对原则的偏离,在故事的叙述中得以详细说明。这些偏离缘于情感依恋的威胁与缺失。要而论之,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展现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质——情感依恋敏感性,以及情感依恋开放性。反之,它也承担着为社会产物——羞耻所影响的风险,且这种羞耻感常与性别意识相关。
情感依恋开放性;情感依恋敏感性;作者想象;文学创作;个人习语叙事;原故事;羞耻;模仿;泰戈尔
说话者不免都是以个人习语的语言系统遣字造句,这一套复杂的规则定义了我们个人内在的语法体系。正如笔者在《作者的大脑如何建构故事》(2013)一书中所述,故事讲述者以个人习语的叙事方式讲述故事,这套复杂的原则使我们的讲述得以实现。个人习语的叙事包括定义了故事种类的原型——即“原故事”(参见Hogan 2011c)。原故事是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复杂融合,指导着我们对于过去与现在事件的解读、对于未来事件的期待、对于假设或反事实事件的模仿以及我们对于这些事件的情感反应。原故事使一些更基础的认知结构,如插画式记忆、语义原型和情感倾向等,与范围更广的叙事复合物融合。他们对于我们生活的诠释、现状的分析以及憧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道德评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我们似乎经常受这些一定数量的原故事引导,他们在不同情境下活动或与不同的希望与紧张之感“藕断丝连”。这些原故事通常都会与跨文化的叙事结构如爱的浪漫情节并驾齐驱,与社会、爱人的分离等戈矛相见。然而除去这些共通的特征,原故事也会被贴上异质的认识标签。
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内,原故事不仅仅指引我们理解自身与父母和同事的关系,或是对在日常口语式的故事讲述中,政治家道德或非道德行为的衡量,除这些日常普通的应用外,原故事也是文学叙事作品的指引师。事实上,翻阅一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原故事具有与作品高度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诚然,如果作者是成功的“能工巧匠”,那么这两种性质必将在作品中得以部分体现。如果作者不是一直重复自我的话,作品中的一致性须要有足够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性,我们或许能将其视为可变因子或是参数的复杂作用。作者故事中的这些原则多为大同小异,然而,每一则故事对于参数的设置都将有不同程度的差异。②论及原故事的特殊性,可以确信的是主宰原故事的原则复合物不具有异质性。定义作者原故事认知和情感维度下的网络对于读者来说也必须具有可达性,唯有如此读者方能跟随他们自身独有的故事情节,体验适当的情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推断相关主题的含义。
与他人一样,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有一系列原故事,并指引着他对世界以及自身故事叙述的理解。然而其中一则原故事或是一种原故事类型,对他而言,举足轻重,至少在他的短篇小说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一原故事类型基于情感依恋,着眼于情感关系的搭建与伦理和政治维度的背叛。情感依恋的温情纽带最常见于父母与孩童之间,梵文学者将其称之为vātsalya。这种情感似乎也成为泰戈尔的主旋律。换言之,在他的作品中,这种情感依恋担当着最基本的阐释性角色,不仅在叙事方面,在审美、伦理甚至是政治方面都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嫁妆制度)。
具体来讲,在之前的作品中,笔者曾指出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展现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性——情感依恋敏感性以及情感依恋开放性。(Hogan,2011c、2011b)。情感依恋敏感性是对于情感依恋纽带的认同与尊重,包括其背叛之痛和对于人类福祉本质重要性的接受。情感依恋开放性则是对于他者独立于他们社会类别或地位的情感角色认同。社会分类通常包括将一些人置于圈外(通过种姓、种族、宗教、国籍或者其他身份类别),以此将其从可能的情感联系中驱逐。这种驱逐通常包括将圈外成员厌恶化,而这种厌恶则是情感依恋的对立面。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笔者将从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的全景描绘以及其伦理和政治结果入手。对于泰戈尔作品的聚焦出于三个重要理由:其一,泰戈尔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主题紧密相关联的作品,恰到好处并不冗长,避免了诸如抒情诗(因为其故事结构而不能得到完全发展)或小说(有长度的极端化以及数量少的倾向)的弊端。第二,泰戈尔的故事在笔者看来,是现代文学中的巨著,值得不断重复和深入地研究。卸下诺贝尔奖的光环,泰戈尔作品在孟加拉文学圈外并未得到充分的赏识和正确的评价。最后,基于笔者自身对于泰戈尔作品的情感和伦理性研究,泰戈尔对于情感依恋敏感性和开放性的强调,对于身份类别对峙的相似态度,在当下似乎大可借鉴。
1.威压与意识形态: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的基本参数
与所有的原故事一样,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折射了一个理想化的喜剧轨迹,简言之便是事物在无阻碍前提下的运作。为了定义其结构,我们需要从变化及其意义排异的轨迹范式入手。这种喜剧式的叙事以父母/孩子的稳定依恋或是vātsalya为起点,并逐渐自然地发展为夫妻之爱。传承此脉络,人物富有伦理上的积极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情感依恋的敏感性和开放性有自然倾向性。通常来说,这一基本的叙事序列并不会塑造故事。其自然属性的预设使其不具可述性,它更多意义上是可述性的背景,因为一系列事件或许能充分调动听者与读者的兴趣。而当这一理想化的轨迹遭遇分裂瓦解,可述性应运而生。在泰戈尔的例子中,可述性出现在情感依恋的持续和发展受到威胁之时(如对于父母/孩子关系的维护产生危机或是以夫妻之爱代替父母之爱)。这一类的威胁有很多潜在的源头,这些源头为泰戈尔故事的变化线索提供了参数。对于泰戈尔而言,在众多因子中我们应首先聚焦于社会地位和规范的功能,具体而言即威压和意识形态。
威压,并不仅仅指涉武力和字面意义的监管,也包含物质和重要的经济因素。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会破坏父母/孩子的情感依恋(如因贫穷而无家可归的孤儿)或者是减少婚姻的成功率(如当女孩没有嫁妆)。进一步而言,经济的制约会加剧情感依恋的脆弱度。泰戈尔原故事的一大特点便是没有对贪婪的房东或者剥削的资本主义者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反之,泰戈尔更倾向于将强弱两级的角色配对。另一方面,泰戈尔的原故事强调了情感依恋的非敏感性,驱逐了弱者的角色以及他们紧随的理性解释。这一点在短篇故事《邮政局长》中得以体现。故事中的邮政局长对于年轻助理勒袒,一位入不敷出的孤儿产生了依恋的情感。在离别之际,他尝到了隐约的苦涩,当片刻的罪恶感战胜了离别的苦涩,他思索到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的哲思,并以此缓解了自己的内疚③。
进一步分析,当较为弱势的角色表现情感依恋的敏感性和开放性,维系这种依恋并没有实际的可能性。就如在《邮政局长》中,结局或许就是社会的谴责,而不是理性的解释。在《妻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妻子姆里纳尔发现并接受了年轻孤女宾杜对她的依恋。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情感的牵连并没有将宾杜从一段糟糕的婚姻中解救出来。在宾杜悲剧性地自杀后,对于引发这场悲剧的社会规范,姆里纳尔并没有继续支持,她主张将自身的自由作为反抗这些社会规范的最初动机。
第二种威胁的类型来自个人内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性别意识。在此,我们邂逅了社会渊源的情感依恋非敏感性和撤移(这样引起了情感依恋开放性的缺失)。这种非敏感性和撤移并不是天然赋予的,而是呈现了被依恋关怀敌对阵营的社会行动者所规训的倾向。当我们再次走进泰戈尔原故事的世界,我们找到了那些通过对他者的羞辱践行性别认同原则的角色,并以此否定了情感依恋稳定的自然发展。《家庭主妇》便是显著的例子。故事中小男孩阿苏与妹妹一起玩洋娃娃,这种磨灭男性特征的行为遭到了老师斯巴司的羞辱,而这种羞耻感也是阿苏男性意识启蒙的一部分。
故事《笔记本》对于情感依恋的意识形态部分亦有深刻描绘,与前者不同的是受辱的性别由男孩换至女孩。故事呈现了女孩欲将其情感依恋关系转至书写的普通愿望。自然而然,这种书写在她的笔记本中存在,也传递给了她的依恋对象,以此成为情感分享重要过程的一部分(Rimé,2005)。此外,她关于依恋对象的书写包括他们的非敏感性和情感迁移。然而她的丈夫拿走了她的笔记本,并羞辱她让其放弃这种想象性的表达。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泰戈尔原故事的价值。社会的描绘大抵是一边倒向于男孩和男人的依恋画面(就如阿苏的例子),对于女性和女生却采用看待弱者的姿态,然而泰戈尔的原故事更为复杂,社会意识在其看来扭曲了对于男女性别依恋那阳光普照般的自然发展,如在《妻子的信》中,姆里纳尔被阻断了依恋稳定关系中的情感分享,甚至对于这种情感分享的想象创作也难逃厄运。事实上,这种认识对于她最终的解放至关重要。
2.控制者、中间者与受控者角色
在威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政治性分类,包括社会等级制度的区分,特别是性别等级,在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类型的分析中举足轻重。然而对于分类的发展存在很多参数,如之前提及的强势和弱势角色的影响,其中一个参数便是关于控制者和受控者阵营的划分(如男女之分)。另一参数涉及道德行为者角色,即道德决策制定者,与前者控制者/受控者的参数互相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被赋予首要道德行为者的角色通常占据控制者的地位,他/她展现情感依恋的非敏感性,如《邮政局长》一文中,邮政局长在性别、阶级和年龄中位处控制者的位置,同时也是道德决策的行动者,因为在他们关系中,勒坦有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感。局长所表现的依恋非敏感性清晰可见,特别是当勒坦无意识的羞耻感出现时这种非敏感性愈加突显。例如当勒坦欲与局长一同回家之时,他为之一笑,而这笑声一直萦绕在勒坦的耳边(p.45)。
同样在《笔记本》中,我们在乌玛和她哥哥的关系中亦能窥见控制性的道德行为者。当乌玛被硬生生困在姻亲家中时,故事感人的泪点也达至高峰。她在笔记本中写下:(哥哥),我祈求你,就这一次,把我带回家吧——我并非惹怒你而是向你祈求(p.143)。当然,戈宾德拉尔是无法看到妹妹在笔记本中的文字的,然而对于妹妹文字诉求上的不闻不见是因为戈宾德拉尔无法听见她的需求,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征兆。
另一方面,所有控制者的角色都逃脱不了依恋非敏感性的命运,这种说辞未免有失偏颇。一些控制者角色的经历受自身依恋经历的影响并随之改变。就如在《编者》的故事中,一位鳏夫卖文为生,为其女儿的嫁妆做一部分储备。从这层面上看,嫁妆体系扎根于他们的离别。然而,他很快沉迷于讽刺创作的成功之中,这一份迷恋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忽略甚至虐待女儿——帕拉巴哈,从而导致她变得害怕父亲(p.123)。依恋关系的瓦解如此显而易见也如此的深刻,最终他的女儿遭受病痛的折磨。在泰戈尔的故事中,读者对于弃妇(弃女)的死亡并不陌生,并为这最坏的情形所堪忧。然而这里并没有社会约束,没有控制者第三方要求的牺牲,也没有给女儿的选择,这里存在的仅仅是依恋关系的两者。当帕拉巴哈向父亲恳求时,他潜藏的依恋之感再度觉醒:我现在意识到女孩被病痛折磨,渴望她父亲满心的关怀和情感(p.124)。
在此,父亲面临了道德选择的境遇: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为女儿奉献自身,他可以在自私自利的道路渐行渐远,也可以做出牺牲,最终他决定选择牺牲并金盆洗手(p.124)。然而,这种牺牲与许多女性的牺牲并不相同,不带悲剧色彩,事实上,牺牲带给他难以想象的快乐(p.124)。
这也为我们的目录添加了另一参数,在依恋关系中,控制者角色不仅需要非敏感性和合理的解释,当外界不存在严重的限制和压迫时,控制者角色也会被唤醒情感依恋的敏感性,进而受到依恋关系的影响。反之,这也会带来两方的喜剧式牺牲。
此类型的另一则故事便是《喀布尔的水果商》。事实上这则故事异常重要,因为其彰显和体现的依恋敏感性并不存在于家庭之中,而跨越了国籍和宗教。故事的情节复杂,围绕于一位贫穷的阿富汗男性哈玛和上层中产阶级孟加拉作家的家庭。哈玛为了赚钱养家而来到加尔各答,种族、贫穷和教育缺失的背景使他身处孟加拉家庭的下层,事实上也使其成为了“圈外人”。尽管如此,他与家中的小女孩米妮成为好朋友。他们渐渐建立起依恋关系的纽带,而这颇为反常。哈玛因为报酬与一位客户争执不下并刺伤了客户,从而锒铛入狱。若干年后哈玛出狱,他来到那家人希望能见米妮“片刻”(p.118),他的到来正值米妮的婚礼,孟加拉作家解释到在这重要的一天哈玛应该离开,换言之,他暗示道哈玛就像遗妇一般不祥。当哈玛将一小份水果递呈给作家,拜托他将其转交给米妮时,作家试着向他支付水果钱。到此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泰戈尔标准的原故事再现,依恋关系也得以呈现,第三方人物为了减少依恋关系的代价而将依恋关系中的双方分离。回到这个标准版本的故事,哈玛拒绝了这笔钱。
然而,故事却在此转折。哈玛和米妮之间依恋关系从未完全清晰地浮出水面。如今哈玛解释到在阿富汗他有一个女儿,与米妮的相见使他陷入对女儿的回忆。他从衬衣中拿出了陪伴多年的陈旧的纸——他女儿的手印。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最基本的情感依恋关系是哈玛和其女儿,因为贫穷而导致了这场重要的离别,也因为养家糊口他才来到了加尔各答。至此,存在于孟加拉作家和哈玛之间的圈内圈外之分也得以消解。思忆起自己和女儿的情感依恋,作家讲述到:“我忘记了他是阿富汗的葡萄商贩,我是孟加拉先生,我也在那时懂得他是一位父亲正如我一样(p.119)。他称哈玛的女儿为帕尔瓦蒂,一如之前他称自己女儿为杜尔伽(p.118)。这是同一位女神的两个名字,而这个女神在许多孟加拉歌曲中都品尝了亲人离别的滋味(MeDermott,2001:123-151)。
另一个转折也再次降临,控制者角色在自身情感依恋感受的影响下做出了抉择,首先他遗忘了之前对于哈玛不详现身的担心,呼唤着他的女儿。在她走之后,他也决定做出牺牲,赠予哈玛回家路费。他尝试修复情感依恋的关系,而不是将人类的关系金钱化,将情感依恋纳入价格的范畴。正如之前编者发现自己的牺牲比写作更为愉悦,作家也感受到了,较之驱赶拒绝这位原以为不吉祥的伙计,为其牺牲获得的精神福祉远远大得多。因为哈玛的经济救济,他不得不在婚礼盛宴中缩减开支。然而,他向哈玛解释道:你和女儿神圣的团聚也会庇佑米妮(p.120)。
相比于更为直接明了的控制者和受控者角色,文本世界也存在中间者角色,例如,上层阶级的女性与较低阶级的女性相比在社会地位上更为优越,但俯首于上层阶级男性。当她们处于依恋关系之外时,愈显恶意和敌对,更像控制者角色,就如乌玛的姻亲姐姐们,在《笔记本》中嘲笑讽刺她,又如《得与失》中尼鲁帕玛残忍的婆母(下文将分析此故事)。与此相反,当中间者角色身处依恋关系中,他或她或许没有控制者那般非敏感。
让我们再一次分析《妻子的信》中的姆里纳尔。她比婚姻中的宾杜更显社会层级的优越性,然而她和宾杜作为男权结构中的女性共享受控者的地位。毋庸多言,这并不保证情感依恋的敏感性,就像宾杜的姐姐,与姆里纳尔同享已婚身份却低处姆里纳尔和宾杜女性身份之下,对待宾杜态度恶劣。姆里纳尔或许未必像宾杜对待困境一样这般敏感,她或许能够做一些事阻止宾杜糟糕的婚姻。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取而代之的只是为自己在这场悲剧事件所处的位置而寻找理由(正如邮政局长所为)。当然在事件发生时她做出了道德选择进而追寻自身的解放,或许反之能鼓励他者,从而避免宾杜式的悲剧再次发生。这种选择也许是由她作为中间者境遇的部分职责所致,不论是控制者抑或是受控者。
控制者和中间者角色体现的主体能动性并不能说明受控者的无能为力。在一些例子中,他们成为故事道德行动者的中心。这一例证也将马上得以陈述,甚至在勒坦这一例子中,我们可见她们并不是被完全限制,她们能够并且也做出了道德选择,只是这些选择非常有限。她们经常与两项选择相关:①与依恋纽带破坏制度的同谋;②自我牺牲。在泰戈尔许多故事中,有时候情感依恋的受控者角色会有做出真正道德或政治性选择的可能性,这一刻或带有戏剧色彩。对于勒坦,当邮政局长给她钱时,她面临着道德选择——她应该同意他们的关系是未付报酬的劳动,简化为金钱交易?还是应该牺牲她迫切需要的金钱保障?最终她选择了牺牲,这种牺牲保护了她的尊严却丢失了物质的富足。
在《邮政局长》一文中,泰戈尔意欲暗指嫁妆是压迫女性的实践表现(勒坦贫穷孤儿的身份已经显示了其嫁妆的缺少),在另一些故事中,他矛头直指寡居期出现的问题。在泰戈尔写作生涯中,遗孀所承受的严重缺失感一直是其思考的话题。在孟加拉国,那时候孀妇通常不能再婚,不能打扮装饰自己或穿鲜艳的衣物,不能分享人生普通的乐事,例如品尝一些食物。遗孀,正如兰姆说道,甚至是危险不详的象征(1999:542),在泰戈尔的揭露批评后,这一说法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实际上,遗孀也将自身视为行尸走肉而非鲜活的生命。
在《生者与死者》这则故事中,泰戈尔将这个说辞作为遗孀的隐喻。故事的开篇提到了与莎拉达沙克家族同住的遗孀——卡当比尼。对于这个家庭而言她并不是路人甲,与寻常家庭一般,她与姻亲同住,然而她并不是家庭中真正的一部分。故事的第一篇章建立了卡当比尼和她侄子紧密深厚的依恋关系,第二篇章告知了卡当比尼死亡的噩耗,事实上她仍健在,然而被误认为死亡并差一点被火化。尽管最终避免了火化的结局,她仍然认为:“我不再属于世上存活的人类,我是可怕的邪恶诱引。”(p.34)从表面上看,这种想法颇为怪异,她似乎对于死亡与生存的状态苦恼迷惑,事实上这描绘了当时遗孀普遍的生存画面。
当最终踏入家门时,她仿佛是家庭中的鬼魂。年轻的侄子接受了她并让她保证“不会再次去世”(p.40)。这种行为符合了情感依恋纽带和中间者角色(部分控制者,部分受控者)的特征,在这个例子中,侄子是男性(因而为控制者),但他又是孩童(因而为受控者)。这类人物试图接受情感依恋的感受并为之报答。然而部分成年控制者相继暴露了社会的暴行与疯狂,并制造了孩童的创伤。家庭成员谴责卡当比尼对于孩子的恶劣影响(p.41),在他们看来她的身份不是幽魂便是不详的遗孀。之后她试图宣告自己的存在。表面上,她意识到自己并未死亡,然而,从隐喻的角度看来,这一位女性面对着给予她生命意义的依恋关系,决定宣告驳斥自己并不是一位死亡的遗孀,但这活生生的人却比任何人更具不祥之感。
不幸的是,卡当比尼似乎并未找到方式证明自己的生命,公开的宣告也经受不住家庭和社会的谴责。事实上,姻亲对于遗孀的冷酷以及盼死的心情是寻常不过的。吊诡的是,在她死后,他们却对她宾礼相待,首先是葬礼仪式的举行——这重大的场合展示了人们的责任感,不管在人死前他们的责任感有多渺小。卡当比尼拥有最受限制的狭隘选择,如勒坦一般,她选择牺牲,石沉大海。泰戈尔的尾句看起来有些简单但却是一个明智的悖论——卡当比尼用她的死亡证明她并未死去(p.41),但这一点确是遗孀的亲身经历。
在泰戈尔情感依恋的原故事中,《得与失》更能清晰体现这点伦理性的发展。故事带我们回到万恶的嫁妆制度,并详细展现了控制者角色完全掌控道德选择的能力。兰山达有5个儿子,还有老幺女儿。当女儿尼鲁帕玛到了适婚年龄,兰山达找到一位出身名门之家冠以“雷尔巴哈杜尔”之姓的新郎。(p.48)不幸的是,他的宝贝女儿进入婚姻的门槛如此之高——嫁妆异常丰厚。仪式举行之际,兰山达筹得的嫁妆甚至还未有总数的一半。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及的一般原则,名门之家的父亲恶言相对。他本可以对兰山达和尼鲁帕玛进行羞辱,在最后一刻拒绝这场婚姻,但新郎阻止了他。结婚后,年轻的新郎需要离开,在和姻亲的相处中,尼鲁帕玛饱受冷眼相待,她的父亲在看望女儿时不断蒙羞(p.49)。
故事中,父女之间的关系是主要的情感依恋纽带,(但)因为嫁妆却被姻亲分离。父亲意识到唯有一种方式能终结羞辱并能自由地见女儿,那便是嫁妆的全额支付。他千方百计筹集却仍只筹得总数的一部分,并换来了再一次的羞辱,亲家表示部分的支付对他来说毫无作用(p.50)。最终,兰山达决定变卖房子,即使这会让他的儿子们无家可归(p.49)。
当尼鲁帕玛听说了此事,她面临着道德难题并有能力做出选择:她可以接受这一笔钱或者放弃,拒绝与制度的苟合。毫无疑问,她选择放弃并作出牺牲。然而她表达决定的方式至关重要。与泰戈尔其他故事类似,羞辱是强化性别标准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在这则故事中,性别标准与阶级等级制度互相影响,因为父亲试图撵出儿子们而增加其阶级优越感。兰山达在与尼鲁帕玛解释卖房时辩护道:“倘若我不支付这笔钱,我将永远蒙羞,你也如此。”(p.52)这里的羞耻意指社会界的鄙视,特别是富裕的雷尔巴哈杜尔一家,“如果你付了钱那么羞辱会更大”,这句话中的羞辱则意指道德错误——敲诈的合理解释。
与勒坦一样,尼鲁帕玛选择捍卫家庭以及自身的尊严,然而代价之大可想而知。知晓她对其父亲的建议后,尼鲁帕玛的姻亲对她的态度愈加恶劣,致使她最终因为未就医而抱病身亡。尼鲁帕玛对于金钱的牺牲导致了生命的逝去,融合了《邮政局长》和《生者与死者》的两种牺牲方式,首先放弃了物质的富足继而放弃她的生命。雷尔巴哈杜尔一家停止了他们的虐待,为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惩罚》的故事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道德伦理性。故事中的两个兄弟:杜克汉姆和赤丹被拉做农田工壮丁,在劳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遭到了指责和羞辱(p.126)。回家后,杜克汉姆因为没钱买食物而遭到妻子的羞辱,“我必须走到大街上去挣钱吗?”(p.126),经历了一天的蒙羞之后(p.126),杜克汉姆的怒火终于在对其男性尊严的侮辱中点燃。他粗暴地殴打妻子,结束了她的生命。在此我们重逢了不断出现的原故事元素,性别制度的偏离总是会被羞辱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在这个案例中,羞辱部分来自女性(这同样出现在其他的故事,如《傻子的黄金》,当丈夫无法履行性别角色时)。虽然如此,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暴力倾向于从控制者这方下滑至受控者个体或团体中。杜克汉姆的受辱直接作用于妻子,尽管他最终的羞辱来自经济体系,迫使其从事这份蒙羞的无报酬工作。
赤丹同时也面临了两难境地。他与弟弟有着深厚的依恋纽带,并对其有道德上的责任,这些促使他帮助弟弟逃离诉讼。当弟妹之死被发现后,他责怪自己的妻子仙朵拉——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p.128)。社会等级中的暴力下滑现象将仙朵拉置于道德尴尬的处境,一方面,这使她成为道德的能动者,但同时却严重限制了她的选择。泰戈尔重描了仙朵拉与赤丹的纽带联结,引导我们将赤丹的控告视为依恋关系的背叛而非错误,因而仙朵拉以伤后自尊的情感给予回应(p.131),并对这种背叛愤恨不已。这与《邮政局长》中勒坦对于经济救济的反映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次的叛离更为深刻。事实上,故事的叙述者似乎将仙朵拉一系列行为全部归因为这种自尊心,然而就此看来,叙述者并非可靠。
具体看来,仙朵拉有三个选择:首先,她可以说出真相——她的小叔子杀了他的妻子,选择的后果则是小叔子的死亡,这不仅违背了家庭的使命,也与殖民体系的法律制度同流合污,而这套制度引发的剥削和羞辱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第二个选择是归咎于弟妹,例如可以辩护自己因受其攻击而自卫。然而这种诽谤死者的行为损害了仙朵拉的名声,甚至会扭曲她的精神人格,因为她不会接受被弟妹袭击的说辞(p.131)。最后的选择便是牺牲,这也是她最终的选择。这种牺牲深层次牵连的依恋缺失浮现在故事的末尾几行,在绞刑之前,她欲见其母亲(p.133)。
然而这又成为故事被忽略的难题,文章的标题为《惩罚》,很明显最终受罚的是仙朵拉,但同时存在另一个惩罚——赤丹的痛苦,他并不愿意将妻子送上刑台,并试图帮助其脱罪。事实上,故事的结尾他想见妻子,但是妻子愤怒地拒绝了这个请求。仙朵拉是对赤丹夸张的非敏感性的一部分惩罚,这是一个线索。他的非敏感性体现在他甚至丝毫没有意识自己的控告将伤害仙朵拉,他考虑了弟弟的精神状态和环境,但却可能因为男/女性别认同的二分而忽略了妻子。无论如何,这种牺牲没有逃脱报复,但痕迹却愈变愈淡。
在故事《骷髅》中我们发现了这类原故事的变化,故事带我们重新回到寡居的话题,讲述了一个鬼魂萦绕在叙述者的家中,一晚,他们促膝相谈,鬼魂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婚后两个月,她便开始了悲惨的寡居生活。她的姻亲将丈夫之死归责于她,并把她送回娘家。作为遗孀,她并不安分,偷偷地穿着鲜艳的纱丽,发际带着花环(p.87),因为受限于对外界的接触,她只能见到一位家族外的男性,年轻的医生、弟弟的朋友。医生的瞩目表达了对这位年轻女性的情愫,她也慢慢坠入情网并确信两情相悦的事实,尽管诉说衷肠在她的立场看来困难重重。直到得知他将要结婚并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跟随原故事套路的走势,她感受到了背叛,尽管我们不能精确的辨明她感受背叛的程度。医生自在地与这位年轻遗孀打交道,因为她寡居的事实,他有着很多暗示,唯独没有将其作为配偶的想法。无论如何,对于她日增的依恋,医生感受到了非敏感性的惯例罪恶感。
从这点看来,年轻遗孀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清晰明了,如何面对在她看来是背叛的非敏感性呢?在此,泰戈尔在《惩罚》中提及的报复再一次得到升华。年轻遗孀对医生下毒,以此作为他背叛的惩罚,同时阻止这种背叛。不出意料,报复并不形单影只,他的出现伴随了牺牲,即自杀。年轻遗孀用传统结婚的行头,给头发染了色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此又邂逅了《生者与死者》相似的隐喻结尾:这位年轻女子只有以尸体的躯壳成为新娘。她最终达致圆满,并非与她深爱的医生,而是死后与其他医生,她的骨架被用作解剖学的示范道具。
3.泰戈尔的道德复杂性:自由和正道(Dharma)④的种类
对于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的细节,我们已经接触不少。几乎每一个例子我们都会发现社会等级和身份类别约束着依恋的敏感性和开放性,并造成痛苦的依恋缺失。然而泰戈尔对于世界的模仿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原故事或依恋基础的理想化。事实上,甚至于他的依恋原故事都包含了许多其他的价值隐意,有时候这些价值特别是与依恋开放性所折射的承诺格格不入。
例如《假日》这则故事,在很大部分与情感依恋相关内容无关。故事中,朝气蓬勃的男孩法缇克被送去叔叔家接受教育。与母亲分离后,他发现自己不受待见,无人关爱,甚至在叔叔看来是不详的“恶魔之星”(p.110)(社会阶层的底端人物在泰戈尔笔下大抵都是不详的,因为经常是被羞辱的对象)。叔叔家反对的氛围和经常试图羞辱他的老师(p.111)对他的成长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迫切地需要母亲,无心学习,也成为了班级里最“愚蠢和怠慢”的孩子(p.110)。当他发烧时,他不敢告诉任何人并试图回家。而回家的途中他的病情愈加严重,在与母亲团聚不久后他便去世。
正如综述所点明的那般,《假日》契合了我们所考虑的结构,然而故事的细节同样也暗示了一些另外的内容。整个情感依恋的违反和接踵而至的悲剧都是男孩因他的调皮不受训而遭受的惩罚(p.109)。换言之,依恋的破坏不是等级和贫穷,而是对孩子“自由”的限制(p.110)——倘若故事中的自由与情感依恋的安全感密不可分。
其他一些故事亦有对自信和自由的聚焦。《妻子的信》是其中颇为有趣的例子之一,故事预设了情感依恋和自由的潜在矛盾。具体来说,姆利纳尔离开丈夫的决定带来了一系列与自由、职责和正道相关的问题。印度的伦理传统与正道的不同分支有所区别,包括家族正道的不同种类,如夫妻之间的正道。对于正统的伦理学家来说,当存在互相矛盾的职责时,家族或是自性(Swadharma),即特指由家族的地位或种姓等决定的正道,应优先考虑(O’Flaherty,1978:97)。然而,大体上一些自性也会有颇具争议的违反现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濒临灾难或危机。在一些情境下,寻常的道德原则不再适用,倘若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没有渠道获得食物,那么(有人或许会有争议)危机情况就会战胜普众道德观念下的勿偷窃警示,⑤这种情形就会引起危机正道——只在千钧一发时刻被允许的行为(Monier-Williams,1986:143)。
姆利纳尔离开的决定毫无疑问与普遍的家庭法则相违背,或许这种违背更具新意,因为它印刻了泰戈尔对于家庭正道变化版本的解读即依恋敏感性。具体言之,15年家庭的朝夕相处并没有建立起些许的情感依恋关系,这似乎不太可能,在此,关系一词似乎定义了泰戈尔道德关怀的前沿。如何调和姆利纳尔对于情感依恋的明显忽视和泰戈尔故事蕴含的普世伦理及情感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一种方法便是以危机的视角考虑。宾杜并不是简单的自杀,而是整一个制度诱发了她的自杀,因为危机的情境源于婚姻制度。姆利纳尔试图从这个制度逃离,在此情况下,她放弃了自身的依恋纽带——她的安全感——这便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不仅给予这位女性更多自尊,也给予她基本的自主。
这也将我们带至最后的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触及了我们所讨论的正道,故事更确切地讲,以“危机”(Āpad)命名。故事中,年轻女性基兰与丈夫沙拉特结伴前往金德讷格尔疗养。在恢复期,她邂逅了一位年轻男孩尼尔康塔,旅行乐家的一成员(p.163)。基兰与男孩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依恋纽带。事实上,两者关系与勒坦和局长之间的关系并不背道而驰。泰戈尔解释道,在他们相处期,尼尔康塔完成了青春期向成人的过渡,18岁领域的跨入使他们的情感愈加成熟。因而当基兰仍以与对待男孩的方式与他相处时,尼尔康塔颇为受伤和尴尬(p.165)。
与其他中间者角色(尤其女性)一样,基兰对尼尔康塔的感受仅仅是部分的非敏感。实际上,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悲痛地意识到对一个终将离别之人产生短暂情感是多么严重的错误(p.168)。当离别的时刻到来时,她欲与男孩同行。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点与局长有着明显差异。故事中,基兰与依恋关系外的受控者角色也有很明显的差异。她的丈夫,沙拉特对男孩怀有敌意,屡次有意无意的打他(p.169)。沙拉特的弟弟萨迪仕不仅呈现对于男孩的依恋非敏感性,甚至对其不屑一顾,断言萨迪仕对于他们离开的痛苦其实源于物质的贪婪(p.168)——一个重复出现的动机。遗憾的是,基兰并没有一直坚持与尼尔康塔的陪伴,而是向丈夫和弟弟妥协。这也反映了中间者角色的问题——他们有一定的敏感性,然而无法随心而动,抑或总是错过时机。《妻子的信》中的姆里耐尔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在他们离开之前,基兰试图赠送尼尔康塔礼物,表面上,这与邮政局长有一些相似点。然而,基兰的爱心礼物(p.170)表达了她的情感,而不是将他们的关系化为金钱交易。为了避免尴尬,她将礼物放到了他的盒子,却不幸的引起了误会。男孩自觉不能保留这个盒子,礼物也无缘相伴。因此他做出了普遍的牺牲——“净身出户”,就像勒坦做出的物质的牺牲。
但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并不是对范式的契合,而是决定我们标题的附加因素和道德复杂性。当萨迪仕在基兰前羞辱尼尔康塔后,尼尔康塔从萨迪仕桌中偷走了他尤为珍爱的墨水瓶。沙拉特和萨迪仕指控尼尔康塔,基兰为其辩护,当两兄弟提出搜尼尔康塔房间时,她坚决抵制,做出了最初的道德选择并坚定了自己的自主性。在她把礼物放在尼尔康塔的盒子中时,基兰偶然看到了墨水瓶,尼尔康塔碰巧看到了这一幕,也促使他抛弃这个盒子选择离开,以此向基兰证明他并没有偷墨水瓶,并对萨迪仕残酷的行为作出回应(毕竟,倘若他真的贪婪,也会保留这个墨水瓶)。基兰的境地更为复杂。从正道的角度来看,她似乎有义务说出发现的真相(而不是保守谎言),并将墨水瓶物归原主(而非与小偷保持统一战线)。然而,她都未做到。在尼尔康塔离开之后,她仍拒绝对其房间进行搜查。之后她处理了墨水瓶,违反了正道的普遍规则,至少在与沙拉特和萨迪仕的情感依恋纽带中做出了叛离的行为。但隐含作者似乎对她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赞同,在标题中给出了支持的理由,即正道的普遍规则并不适合危急情形下的情境。
依恋原故事与危机正道(āpaddharma)是有保持一致的可能性。危机是来源于萨迪仕最初对尼尔康塔的羞辱和基兰早期的依恋非敏感性。对于男孩的再次羞辱是错误的,即使他不在,但重复证实这些道德错误也有失偏颇。唯一能确认的是沙拉特和萨迪仕的偏见以及未来对于情感依恋纽带伦理和情感维度的叛离。
然而基兰的行为同样也阻止了对于男孩任何的追求和惩罚,给予了他离开的自由,也巩固了基兰自身的自主权。因而故事不仅告诉我们,依恋敏感性给予了其他依恋纽带违背破坏的生存空间,同时自由与自主也取代了依恋基础上的职责。
1985年早期,“Āpad”一词问世。同年之后,泰戈尔发表了另一则讲述相似事件的故事《宾客》,但却给予不同的结局和意义(Radice,2005:300)。这则故事同样讲述了一个剧团的成员,一位年轻男孩塔拉巴塔,被另一个家庭所领养。故事中,他对家庭中叛逆的女儿查璐产生了感情。纵使有冲突,查璐也对他的感情愈渐清晰明了。最终,这个家庭帮他找到了真正的家,并欲让两位年轻人结婚。然而,当婚礼即将开始时塔拉巴塔消失了。
某种程度上,这种情节符合泰戈尔原故事的惯例。依恋关系因为抛弃年轻女性的年长男性所表现的依恋非敏感性而被破坏。然而,故事中,塔拉巴塔并非犯了明显的错误,事实上,在结尾处能看到暗示,捍卫找寻自由的权利无可厚非:在爱情和情感纽带禁锢之前他逃离了(p.211)。在塔拉巴塔和神灵奎师那(K爟a)的联系中这一点得到进一步深化,并一跃从吹长笛转换到声名远扬“偷心贼”的形象(p.211)。奎师那是一个虔诚的爱情追寻者,然而从未得到完美的生活,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冷漠,事实上他富有爱心,就像塔拉巴塔。但即使如他也无法在这个物质世界中达致圆满。这并不是说塔拉巴塔就是奎师那,毋宁说泰戈尔将两者联系,并以此使塔拉巴塔的离开更易接受。
这则故事似乎与我们探讨的普遍模式相悖,然而当泰戈尔讲述道德断层是他最致命的弱点和他最大的力量时④,这种不一致或许正是他所追求的。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承担着风险,即依恋纽带战胜了其他一切因素,包括自由。当依恋的关系被扭曲甚至被阶级等级制度、父权制(父权制影响下的嫁妆制度和寡居禁忌)和其他社会压迫结构破坏时,泰戈尔似乎意识到保护受控者的情感依恋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仅考虑这一点远远不够,正如《宾客》故事这般部分抵消了与泰戈尔其他故事的伦理不平衡性。泰戈尔将情感依恋视为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关键甚至是中心和主要点,但也认识到就像任何人性的美好,它并不绝对。事实上,这反应了另一类型原故事的存在,以及泰戈尔理解和对情境回馈随机应变的另一方式,这种复合结构的类型我们都拥有,它们不一定完全始终如一,或许会引导我们以矛盾的方式理解情境。
4.结语
总而言之,故事的讲述就像演讲,个人习语原则编织出了个人故事中往复的模式,故事讲述便是其结果。模式兼具认知性和情感性,他们不仅包含了个人利益,也包括了伦理和其他原则。这些原则根据故事讲述者的一定变化而变化。不同故事中呈现的特殊性起因于原则的分列,他们一定程度上通过故事轨迹和整体轮廓下参数的不同设定而形成。通常情况下,这些原则定义了伴随一系列破坏理想可能性的理想轨迹。一套既定的理想化和中断的可能性,用更准确地话来说,个人习语的叙事原则和参数共同催生了与一系列定义“原故事”相关的故事。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频繁展现了以情感依恋纽带为基础的原故事因素。这类原故事预设了一个惯例,即父母/子女的情感依恋为之深化并会被成年的婚姻纽带所取代。可述性故事(展现叙事性的故事)会在惯例打破时出现。这种打破包括依恋缺失或者依恋脆弱性的短暂缺失,两者情况的出现都会加剧伦理决策需求的出现。在这类原故事的指引下,泰戈尔提出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性——情感依恋敏感性(即对他者情感依恋需求的专注度)以及情感依恋开放性(即愿意将他者视为关心和情感纽带的对象,无论他们是什么种姓、性别或者其他身份类别)。这些道德原则的闪光点激发了限制依恋弱性的行为并阻止或弥补了情感依恋的缺失。
泰戈尔的原故事包含了许多参数,其中一个便是关于物质约束(如经济地位所引起的)和意识形态约束(主要包括由性别制度所催生的)的不同。泰戈尔作品向我们道明了意识形态的约束限制会破坏情感依恋的关系,并主要通过羞辱扭曲人类的情感,从而巩固范畴的分类。
另一系列可变因素作用于道德行动者,对于这些角色相互的关系有一项重要的区分,即控制者、受控者和中间者。控制者无疑倾向巩固身份类别,然而他们的行为一部分取决于他们与受害者有无依恋纽带。中间者角色的行为形形色色,但更倾向于开篇展示的情感依恋的开放性和敏感性。
原故事关于道德行动者最有趣的角色便是受控者,特别是遭受羞辱的依恋威胁受害者。他们或许与伤害他们情感纽带的制度格格不入,并普遍作出自我牺牲。自我牺牲的内容或是物质的富足甚至是生命。然而这种牺牲也是面对社会羞辱时维护自尊的方式,有时候伴随着报复的行为。
泰戈尔的一些作品也展示了不同类别的原故事。这类原故事将重点放在个人的自由而非情感依恋。在一些例子中,这一类原故事与依恋型原故事相冲突。自由类型的原故事折射出了自我提升的规准,并挣脱于家庭或其他循规蹈矩富有使命感的依恋关系的束缚。
最终,倘若这些原故事并未对社会转型中不公平的等级制度作出合力,那么也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对于像《妻子的信》中姆里耐尔最终的反抗,文中也给出了一些建议。然而只停留在晦涩的暗示,并没有得到展开和强调。这或许是因为对于身份类别的厌恶使泰戈尔无法想象非身份基础上的合力,因而富有消极的色彩。尽管如此,泰戈尔的一些角色展现了依恋关怀衍生出的人道和移情因素,例如从姆里耐尔到宾杜,纵使在一些例子中并没有成功,这些关怀或许仍是非身份基础上合作的模式。这种强调情感依恋敏感性和开放性的合作模式能团结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从而抗衡圈内圈外的模式以及由此产生不可避免的羞耻感。
注释:
①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6月份在上海交通大学“文学叙事中的情感研究工作坊”(A Workshop on Emotions in Literary Narrative)上的发言稿。在此,我要感谢组织者:甘尼萨·慕克吉和尚必武先生,感谢他们给予我这次机会与读者分享拙见,感谢他们对本文的评价和建议。
②在此,笔者引入了语言学原则——参数理论,并作出一定明显的变化(如原则并非固有和普遍,参数在早期童年期的关键时期并不持久不变)。Surányi 2011对此理论有介绍。笔者在Hogan2013第四篇章对文学性个人习语的原则和参数有深入讨论。
③如无特殊注明,泰戈尔作品的引用均来自Radice,2005。
④在此,译者将Dharma翻译为“正道”,即存在的法则。
⑤严格来讲它并没有与自性(swadharma)相冲突,而是与sādhāran·adharma相冲突,即普世的正道(等同于mānavdharma,人类正道),此正道适用于所有人,包括诸如不能偷窃等规范(参见Parekh 1989:16)。
⑥参见Modern Review(September 1941):212和Visva-Bharati News 28.11(May 1960):190.
[1]Chaudhuri,Sukanta.Rabindranath Tagore:Selected Short Stories[M].New Delhi,Ind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Hogan,Patrick Colm.Affective Narratology: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M].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1a.
[3]Hogan,Patrick Colm.What Literature Teaches Us About Emo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b.
[4]Hogan,Patrick Colm.Why Ratan Fell in Love Unnoticed and Why Ashu was Ashamed:Tagore’s Short Fiction and the Ethics of Feeling[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2011c.34:89-99.
[5]Hogan,Patrick Colm.How Authors’Minds Make Stor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6]Lamb,Sarah.Aging,Gender and Widowhood:Perspectives from Rural West Bengal[M]//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1999.33:541-570.
[7]McDermott,Rachel Fell,ed.Singing to the Goddess:Poems to Kālī and Umā from Bengal[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8]Monier-Williams,Monier.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M].Delhi:MotilalBanarsidass,1986.
[9]O’Flaherty,Wendy Doniger.The Clash Between Relative and Absolute Duty:The Dharma of Demons[M]//Wendy O’Flaherty and J.Duncan M.Derrett.The Concept of Duty in South Asia,1978:96-106.
[10]Parekh,Bhikhu.Colonialism,Tradition,and Reform:An Analysis of Gandhi’s Political Discourse[M].New Delhi:Sage,1989.
[11]Phelan,James.Rhetoric/Ethics[M]//David Herma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203-216.
[12]Radice,William(ed.).Rabindranath Tagore:Selected Short Stories[M].New York:Penguin,2005.(文中只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13]Rimé,Bernard.Le partage social des émotions[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5.
[14]Surányi,Balázs.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M]//Patrick Colm Hogan.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666-670.
责任编辑:陈宁
How an Auther’s Mind Makes Stories: Emotion and Ethics in Tagere’s Short Fiction
Patrick Colm HOGANtrans.by TANG Yili
Authors may be understood as producing stories from their narrative idiolects.Narrative idiolects are sets of principles that enable the simulation of possible sequences of causally connected events.Such idiolects include prototypes that define classes of stories.These prototypes or proto-stories are complexes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structures that guide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world events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of fictions.Like everyone,Rabindranath Tagore had a range of proto-stories.Butone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him.This was a proto-story based on attachment,the sort of bonding that first of all characterizes the relations of parents and young children.This proto-story centers on the formation and violation of attachment relations,with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at surround such violation.Specifically,Tagore’s ethical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 largely guided by the norm of securely developing attachment.It was elaborated into stories by reference to deviations from that norm.Those deviations are caused by attachment threat or loss.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points,Tagore’s attachment proto-story suggests two key ethical virtues—attachment sensitivity and attachment openness.These,in turn,may be disturbed by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hame,often in relation to gender ideology.
attachment openness;attachment sensitivity;authorial imagination;literary creation; narrative idiolect;proto-story;shame;simulation;Rabindranath Tagore
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认知批评、后殖民理论研究。汤轶丽,女,浙江海宁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叙事学、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