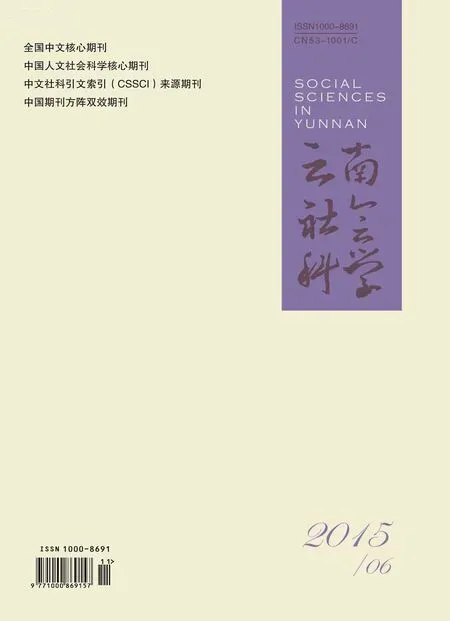儒学现代化发展三个层面的前提性问题
韩 静 雷龙乾
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会通、融合西学以谋取儒学现代化的现代新儒家为中国传统儒学走向现代化做了各种尝试和探索。在当代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复兴儒学”已悄然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体现着对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尊重。因此,“复兴儒学”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 在现代化背景下讨论“复兴儒学”,需要从三个基本层次来处理异质性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一是理论关怀层面,二是思维方法层面,三是价值信念层面。这三个层面的理解不仅关系到儒学现代化的话语方向,也关系到现代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因而是比“复兴儒学”更为优先的前提性问题。
一、理论关怀层面:中西文化偶合中儒学现代化发展能否表达中华优秀文化的现代生命旨趣和中国人的生存发展要求
儒学现代化问题是在中国社会走向危机时产生的,那么,儒学现代化建构的内在根据与基本目的是什么?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儒学的建构就可能会沦为一种所谓标签化和流俗化的“意见”。然而,要对这一根本性问题做出切实回答,就必须对儒家思想演变进行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儒学命运与历史遭遇是紧密相连的,而构成这种历史遭遇与核心命运的是儒学自我的危机,以及在时代变迁中对儒学现代化发展的极其迫切的要求。儒学的自我危机是构建儒学现代化的内在根据;而重构儒学自我,对文化的发展和现代人的生活本身产生作用,则是儒学现代化的追求和目的。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学的生存境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儒学由主流文化变为裂散的、边缘化的文化碎片。建立在数千年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核心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由丰沃变得贫瘠,从鸦片战争的第一声炮响起,政治救亡的迫切情态就发出强烈的文化哀怨,由此而来的是将儒学认定为中国瘠弱的罪魁祸首。至此,批判和哀怨接踵而来、连绵不绝,儒学不得不隐退到现世的边缘,被附着许多难以洗去的污迹。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裂散之后,儒学已彻底地走出了经学范式,形成了包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怀有现代理论气质的新儒学。只有深刻领悟时代语境下儒学这一思想演变过程,才能对儒学之“现代化”做出适度的评估。
儒学发展到晚清,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西潮东渐,外部的冲击使得儒学内部发生了很多裂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未绝如缕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8页。随着汉学的衰败,是宋学复振的呼声,经学崛起和诸子学的繁盛,正是在汉宋之争、经与子的重估中,儒学权威一步步走向瓦解,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终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实则可视为经学终结的标志。梁启超在总结“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术另辟新地;二是将孔子抽象化为一创造精神;三是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一切皆可怀疑批判;四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别黑白定一尊的观念完全被打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第72页。晚清经学的解体,使儒学一下子处于飘散的状态。
接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传统儒学完全丧失了回应能力。面临着连根拔起的态势,陈独秀断言:“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所以“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就儒学而言,“五四”是对儒学的极端反动,是对儒学的极端否定。如果说清末的烧经是空谷足音,让人震惊;那么,此时的废孔之议,就无须诧异了。传统学术的崩溃,使得儒家思想屏障全失,受到致命性打击,可以说是气绝命丧了。从20世纪20年代起,儒学已是历史名词,经学更成绝响。似乎短短20年间,便已经恍如隔世,如此遥远了。
面对“五四”批孔如潮,第一个站出来为儒家说话的是梁漱溟。1917年,梁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他声称:“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5 页。由于受到批孔潮流的触动,原本信仰佛教的梁转向儒家,努力通过中西文化融通的办法,重新诠释儒学的优长,促使儒学复兴,这样一来,他就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即现代新儒学方向。自那以后,根据中国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法,形成了科学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之争。中国学术领域向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条路向发展,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竭力暴露中国文化的缺点和不足,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由此陷入了完全否定中国文化及全盘西化的泥沼。而以梁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儒家人文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即创造,创造即复兴。两种思潮的对立并存、相互消长,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新儒家一派。无论是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还是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唐君毅的超越论,牟宗三的存在伦,一言蔽之,它们都是在新的文化激荡下新的学术回应,“以西释中”是它们共同的路径。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返本开新”的文化运动,确认儒家道统在中国文化的“一本性”是其“返本”的重心。它们要返的儒学之“本”,就是树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心性之学,又称“内圣”之学。“此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而上学等而一之者。”*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第124页。以此心性之学为基本的价值观必然是重道轻器、贵义践利,与之相关还有好古践今、存理去欲、重人治轻法治、重和谐轻竞争、重道德轻知识等等。这显然与现代科学、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可以说,从历史中走来的现代新儒学毕竟还是“儒学”,它的儒学底色仍在于它比任何其他现代思想流派都更强调道德的价值,都更有意去说明道德的形上根基。这其中当然蕴含着当代中国人非常重视的文化遗产,对于中国人的生存和社会的自我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仅此要真正地完成儒学现代化,它又显得力不从心,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的“现代”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现代性”的追求和建构,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和中国社会的面目,建设一个不同于传统“‘血缘宗族社会’的‘现代公民社会’,是自近代以来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年,第12页。“血缘宗族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儒学,需要重新立足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在理论关怀、思维方式、价值信念层面给予重新地体认和转化,形成内涵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儒学。因此,儒学现代化发展,不应该只用西方的理论知识去更新传统儒学,而需要将儒学的内涵、精神和智慧,真正关注到现代人的生活中并产生实际的影响,对现代中国人目前和未来的生存发展提供积极智慧,用理论知识和方法,来关怀现代人当前及未来生活之意义价值,创造发展儒学所内含的现代智慧和精神。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儒学能否承担起这一责任,是儒学现代化发展的极大挑战。如果它不能表达和满足这种要求,或者与此背道而驰,那么,它即使存在于现代社会,也许会显赫一时,历史也不会承认它具有儒学的精神品格达到“现代”的思想水平。
二、思维方式层面:历史嬗变中儒学现代化发展能否自觉抵御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规避思想自我异化
“人的可悲不在于他缺乏知识,人的悲剧不是认识论上的缺乏,而是人的偏见和虚伪。”*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6页。从儒学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看,儒学文化并非一贯扮演完美无缺的角色,它常常是把“双刃剑”,既有可能推动人走向自由和解放,又有可能使人受到专制和奴役,既有可能促社会文明进步,有又可能嬗变为僵化教条阻碍社会文明。简而言之,儒学具有“双面性”,它是一种内涵“双重品格”的复杂存在,蕴含着思想自我异化的可能。儒学现代化发展能否在历史嬗变中自觉地反思与批判,合理规避思想异化风险,将是儒学现代化发展的一大挑战。
儒家思想自我异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
1.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儒学曾作为最高真理代表者,从先验原则出发,把针对特殊问题产生的思想理论搬到不同历史语境中去,用之规范这一语境下的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发展,产生思想异化的风险。
儒学的“损益”思想为其后儒学更新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儒学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形态,获得新的生命力。然而,汉代初年,黄老之学取代儒法得以盛行,儒学因不能与现实社会结合,满足政治需要,而面临很多大挑战。汉代儒生普遍赞成“强干弱枝”,维护中央统治,唯有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王道大一统理论进行损益,继承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观,重建了以天子为至高无上统治者的等级社会结构,董仲舒还对先秦儒家的一些思想(如孟子民本思想)作了减损,将道、法,阴阳家的思想加以改造,提出了“天人感应””阳尊阴卑””性三品”等学说。董仲舒的思想为当时西汉中央政权阻止诸侯分裂,维护统一政权提供了长远可行的统治方案,较好地解决了学与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先秦儒学在新形势下获得了更新和发展,使儒学走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复兴之路。然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与孔、孟、荀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次的儒学复兴,是以经学形式出现,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儒学,用神学路数来发展儒学,将德治建立在灾异、谴告的基础上,把人格的建立溯源于天,使汉代儒学成了兼阴阳、名、法之学的不同于早期儒学的新的思想体系,从而造成了早期儒家世俗精神在汉代的失落,使得儒学丧失了感染民众人心的影响力,让普通百姓难以在其中寻盼精神寄托。加之经学注疏烦琐、内部派别的纷争不断,导致汉末这种经学化的儒学不断衰落。
到了宋代,儒学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复兴,由周敦颐开创的宋明理学,经由邵雍发展到张载、二程而正式形成,到南宋朱熹而成熟;由陆九渊开创,到明代王阳明完成了心学,构建了丰富而宏大的思想体系。比起先秦儒学和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可谓使儒学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影响接近近代。审视宋明理学,其内容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理学”“心学”都是依据传统儒学而增益传统超出儒学的,如孔子对“性与天道”很少涉及,而他们则主要讨论“性与天道”;孟子对“心性”问题论述较为简略,他们则把心性发展为各种理论体系。然而,另一方面,宋明理学也同时使原始儒家的思想异化到了极致,“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学说,“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的节气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个人崇拜色彩,都背离了原始儒家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由理学发展到“心学”所呈现的禅宗化及空疏无用的形式主义,使得当时的儒学已经异化到了极致,迅速走向衰败。由此可见,儒学一次又一次的复兴并非像标榜的那样回归孔、孟,反而走向了超世俗的路向。超世俗的儒学发展路向背离了原始儒家精神取向,最终导致儒学变成无形的精神束缚,加深了与民众生活的疏离,使儒学一再陷入生存危机。
到了当代,“返本开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思想纲领,然而他们所“返”之“本”主要是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事实上,宋明理学只是儒家之流,非源;心性之学也仅仅是儒学在宋明时期发展的路向而已,非儒学整体本身。而他们之“开新”也只是试图开出民主科学或“儒家资本主义”,这并非现代真正之“新”。有学者指出:“‘返本’就是要返回先秦乃至中华文明之源头的夏商周,追本溯源,寻求中华文明和儒学的真精神。‘开新’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在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华大地,集中华夏文化圈华人的智慧,真正开出华夏文明的新时代。”*祝瑞开:《儒学与21世纪中国—构建、发展“当代新儒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年,第20页。
2.儒学曾以最高价值的终极立法者自居,拒斥质疑与批判,成为与各种权力结盟、维护专制的工具,原本应该作为“治疗”抑或“解毒”专制权力的儒家思想,在历史现实中,却成了权力与利益的卑奴,思想发生自我异化。
一种学术思想一旦与权力结盟,就会变成“唯我独尊”的强制性真理,不再是形而上、思辨的、充满智慧的思想产物。这种结盟必然要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使思想本身发生异化,使普遍必然的“真见”,成为随历史潮流朝升夕灭的现实制度的漂浮物。
儒家思想与权力结合,发生意识形态的转变是在秦汉之际。好儒学的汉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果断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统治天下的利器。董氏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诗并进。邪辟之说息,而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表彰六艺之举,自然确定了儒学一尊的局面,然而儒学“独尊”的地位,导致了思想的僵化与凝固,好比草木界百花齐放后,至秋冬而叶落而萎谢矣。在唯一“真理”面前,一切自由创造性的思想都被蒸馏为一种形式,丰富性与多样性逐渐被强制性和规范性替代,人的现实生活必将走向封闭化和抽象化。当儒学成为统治工具时,其妥协与修正表现出其思想异化风险。在宇宙论上,儒学表现出对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佛家思想的妥协;在个人行为上,表现出与佛道相融合;在社会治术上,表现于对法制的让步。陶希圣曾认为,孔子思想有七个阶段的变化发展:“封建贵族的固定身份制度的实践伦理学说,一变为自由地主阶级向残余贵族争取统治的民本政治学说与集团国家理论;再变为取得社会统治地位地主阶级之帝王之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为神化的伟大人格;三变而拥抱道教佛教,孔子又空为真人圣人及菩萨;四变而道士化;五变而禅学化;六变而孔子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所留存者,伟大的孔子,为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集团之保护神。”*《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页。可见,到近代,儒家在政治舞台上已经难辨其本来面目。
近代以来,现代新儒家对于传统儒学的价值系统作了某些调试,使仁心的发用亦涵括了科学理性精神。但是,在保持德性优位性,强调仁以统智上,它们依然与传统儒家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正如唐君毅归纳的:“中国文化本身之需要,只是要充量发展其仁教。因此一切科学之价值,都只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湾: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56页。同时,现代新儒家将儒家道统的“一本性”确定为具有永恒价值、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然后推论从儒学之“本”中能开出现代科学民主之花来。这种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将一切结论都包含在抽象的原则之中的方法,是非科学的。它不是从现代化的需要来衡定传统儒学的价值,而是在肯定儒学永恒价值的基础上给它装进现代化的内容。不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发展儒学,而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改造现世。如此,不同价值系统的传统和现代的内容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始终难以克服“返本”和“开新”之间的矛盾。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儒学与现代化的争辩中,独断论与教条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依然不时浮现出来,成为人们自由思想的梦魇,它们坚持儒家“道统论”不变,依旧以孔孟程朱陆王为“正统”,把墨、道、法诸家排除在民族文化传统之外,把儒家中真正富有人文主义精神和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排除在儒学现代化之外,这种思想史观虽然出现在现代中国社会,但其思想和语言却充满僵化与迂腐。
由此而言,儒学现代化发展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儒学思维方式的狭隘性,那么,它在精神气质上就仍然不具有“现代”儒学应有的品质,就好比一个在“现代”生活的人不具有“现代人”的素养和品质一样,虽二者似有交叉,但本质上说,现代化的儒学应该是更高层次上儒学的现代发展,即实现了的儒学的现代化转型,生成能够作为当代世界文化内在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化新形态。
上面列举了儒家思想异化可能的表现,意在说明,儒学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必须祛除观念形态和非观念形态对儒学思想的主宰,使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摆脱独断论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支配,通过自觉的反思、批评,规避思想异化。这种反思、批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批判,目的是祛除虚假意识对人的生活发展的束缚,对现实社会生活的遮蔽,防止独断论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导致的思想异化。二是社会现实批判,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反省、批判,揭露思想存在与人的价值和社会的存在发展相背离的性质品质,分析其原因及根源,促使人们从异化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当然,没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一经确定便永恒不变的。对儒学文化的反思、批判也不可能是从唯一永恒标准出发的超历史的审判,而是一种承担着历史责任感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活动,这种历史性活动应该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获取具体的主题,是一种永不终结、与人和社会存在终身相伴的思想活动。
三、价值信念层面:沟通、交流中儒学现代化能否形成与世界文化具有可对话性的存在形式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文化是其确认独立身份的最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其现代化发展必将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过程中,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学能否在形成与世界文化具有可对话性的存在形式,成为全球多元化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应该成为儒学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之一。
如同马克思指出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在此语境中,儒学要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真正具有“现代”精神,则必须具备与世界文化的可对话性。全球化浪潮翻滚不允许儒学自限其小,任何一种“独善其身”自我封闭的民族文化,都难以具有对现代人的生活充分的解释力与启示性。然而,回归历史,从20世纪初西学东渐至今,儒学与西学之间的沟通、交流无论在理论关怀还是思维方式层面上,都一直没有间断过,今日大概不会有人抱残守缺到完全地拒斥西方文化的地步。可是,为什么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却一次又一次的陷入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相对主义之中呢?为什么至今我们仍在探讨和呼吁儒学与西学的融合呢?这种呼吁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这种呼吁表征了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更深入的沟通、更高层次的对话需求,而在这一层次上,价值信念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中西文化在思想路径、理论原则、表现形式等方面各有旨趣, 但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都在以一种理性的形式表达着对于生命本性的理解,蕴含着对于生命价值的反思以及通过反思形成系统的信念。在此意义上,中西文化虽然在知识内容与思维方式上有区别,但它们都是不同民族文化立足于其现世生活世界和经验,对生命意义、价值与理想生活的自我觉悟,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学与西学在其异质性与差别性背后存有共同性和相通性,使得儒学与世界文化对话具有可能性。
较之理论关怀和思维方式而言,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是中西文化中的深层次维度,也是最为困难的维度。这是因为,首先,文化认同对个体而言如庄子所言“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没有两个人的认同会是完全一致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个体和群体,对于生命价值都有资格形成自己的信念,因此,关于“真”“善”“美”的追求不再有统一的终极答案。现代社会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自觉地意识到:“有很多合乎理性的学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并非它们全都可以为真(事实上,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为真)。任何理性的个人所认可的学说,仅仅是诸多其他学说中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学说。”*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3页。其次,中西文化都表达了对人“生活样式”的自我理解,凝聚了本民族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构成了人们生存、行动的终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价值信念规定着人们对世界的处理方式和情感态度,它要求超越所有异质的、复杂的知识,达到最高统一性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得,中西文化间在价值信念层面上的沟通、交流始终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维护各自“民族性”的情结,使得儒学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变得障碍重重。例如,现代新儒家中存在的儒学复兴说,梁漱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14页。在他看来,西洋文化所走的路向是人类文化之处的第一条路向,而中国文化路向是人类文化的第二条路向,西方物质文化是低形态的文化,中国精神文化是高形态的文化,西洋文化之后便是中国文化复兴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与儒学复兴说印证的是儒学救世论,熊十力说:“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自适天性、所必由之结果。吾人意欲救人类,非倡明东方学术不可。”*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二》,台北:台北明文书局,1989年,第288页。虽然熊十力也承认西方哲学有其优点,但在价值趋向上,始终认为中国儒学要高于西方哲学,对人类文化的未来,担负着开辟新路的责任。“人类如终不自毁,其必率由吾六艺之教焉无疑也。”*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二》,第252页。
儒学与西方文化在价值层面上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现代性”现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原发型的,而是后发型的。在传统社会,儒学的价值信念占据“独尊”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空间中同时存在,于是,中西文化表达的价值信念的冲突和争议就成为一个时代课题。这种冲突和争议蕴含着不同民族文化各自的感情和体验,表达着不同条件下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信念,中西文化异质性价值在同一时空交集,产生冲突与焦虑是难以避免的。近现代发展史上儒学曾经以“拒绝对话”的方式对待中西价值信念层面冲突,导致价值一元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究其原因,进入现代社会,中西文化同时交映在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之中,使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不再是单一和纯粹的,而是充满复杂性、异质性。在此情况下,拒绝对话的方式与现代社会人的真实经验是相悖的。传统儒学凝聚了人们对人生境界与生命态度的领悟,是人们感悟生命价值的内在根据。然而,传统儒学生存基础是前现代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它所表达的生命精神、价值信念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情感已经不相适应。与此相对,西方文化强调的个人主体价值、理性主义精神,是传统儒学所欠缺的,但并不意味传统儒学代表的价值信念失去了当代价值,相反,它对人道德能动性的规制,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境界的领悟等,同样是西方文化欠缺的。在此意义上,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是儒学与世界文化联结的纽带或基础, 这种价值层面的深度对话是立足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精神,推动中国人对生命存在的价值理解,推动儒学文化融入世界的重要内容。只有实现中西文化价值信念层面对话,才能避免囿于对理想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自我理解,使儒学“自觉地融入世界,但却运转如道之恒动,动而愈出,以至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才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的最深精义与最高境界”*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一卷·论中西哲学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评《中国现代化论》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