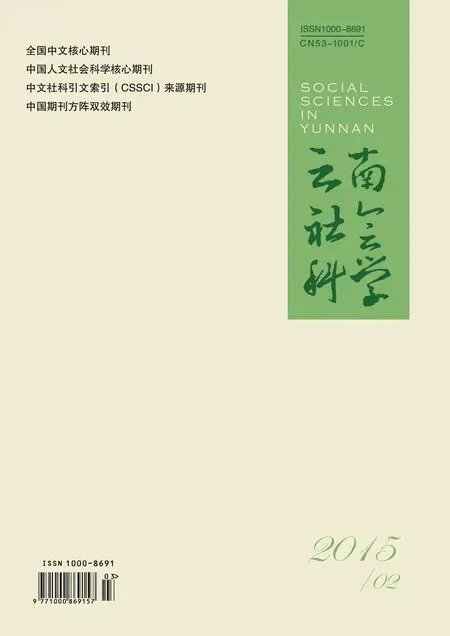西方文艺批评中戏仿功能的历史演变探析
龚芳敏
戏仿(parody)在西方文艺批评中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批评概念。戏仿虽古已有之,但对其内涵的阐释和理解却因人而异,批评家贝利斯(Martha Bayless)曾指出:“戏仿是一个特别难以捉摸的文学术语,而且批评家在关于它的精确定义的问题上很少能达成共识。”*Bayless,Martha:“Parody in the Middle Ages:The Latin Tradi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作家、批评家为何要运用戏仿,作用何在,有何功能等问题的回答和理解就差异甚大。恰如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所言:“戏仿随文化而改变;它的形式、它与其‘目标’(target)的关系、它的意图,在当代北美与在18世纪的英格兰都不会是相同的。”*Hutcheon,Linda:“A Theory of Parody: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New York:Methuen,1985.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文艺批评史的视角,考察戏仿从古典时期到后现代时期其功能的演变,并以社会文化转型理论为参照,探寻这种历史演变背后的文化、思维与美学原因。
一、古典时期:致敬与暴露的双重统一
历史地看,对戏仿功能的追问和系统的分析,自古希腊就拉开了帷幕。这可从批评界对戏仿这个词语的内涵阐释中见到一斑。批评界对戏仿的阐释,常常从词源学入手,戏仿在古希腊时期的书写形式是“parodia”,是由前缀“para”和词根“odes”组成,其中“odes”是歌曲的意思,但前缀“para”却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语义指向,本身具有很强的矛盾性和含混性,其中的一种语义是:伴随,在旁边(beside);另一种语义则是:反对与对抗(counter/against)*Hutcheon,Linda:“A Theory of Parody: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1985.。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期,同一个“parodia”可以表征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而且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蕴含在同一个词语之中。这也直接投射出当时文艺创作者对戏仿在创作中产生的作用和功能在认知上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回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的史实语境,可以发现,戏仿一般是在两个维度上被使用,其一是以“相对之歌”的意义使用,其二是以“滑稽模仿”的意义使用。而且,在古典时期,西方批评界对于戏仿功能的建构也基本沿着这两种差异甚大的使用方法来展开。
在西方古典时期,以模仿说为核心的文艺批评解释体系占据着主导地位。批评界将模仿作为人们学习文艺创作和进行技巧训练的主要方式。只有通过模仿,艺术家才能无限地逼近“美”本身,其创作的作品才具有艺术价值。戏仿作为模仿的一种具体形态,与严肃模仿相对应。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模仿,在古典时期,都隐含着对模仿对象的致敬和崇高地位的认可。因为只有神圣的或者经典的文艺作品,人们才会去模仿。从这个维度而言,虽然戏仿是一种不同于严肃模仿的模仿形式,但戏仿这种模仿形式建构的“相对之歌”依然隐藏着向神圣与经典学习与表达敬意的功能。另一个方面,通过戏仿行为,客观上也使戏仿的源文本的规范和价值取向被中心化和神圣化。
戏仿作为模仿的一种形态,除了向模仿的源文本表达景仰和敬意外,但它毕竟有别于严肃的模仿形态,其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认可那些神圣的史诗与悲剧作品的规范与价值的同时,其功能还在于通过其滑稽性的模仿,揭示和暴露那些神圣和经典作品的局限与不足。英国批评家罗斯就指出:“‘parodia’可以模仿英雄史诗的形式和内容,通过重写情节或人物创造幽默效果,以至与作品更‘严肃’的史诗形式形成滑稽的对比,并且/或者将史诗更严肃的方面和角色与日常生活或者动物世界滑稽低级不适宜的角色混合,创造喜剧。”*玛格丽特·A·罗斯:《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王海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也就是说,戏仿通过模仿行为制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使那些严肃的、正襟危坐的神圣作品和经典作品本身的缺点和局限得到凸显,让人们看到被神圣化、崇高化了的作品的不完满性。在这种意义上,戏仿具有一种去神圣化的功能。即通过对源文本的戏仿,作家破除人们对神圣作品和经典作品的盲从和迷信,凸显了神圣与经典作品本身的建构性。当然,在古典时期,戏仿者对神圣与经典文本的戏仿,除了暴露和揭示这些作品的局限之外,并无价值和情感的偏袒性和取向性,显得较为客观和中立。
从古希腊肇始的古典戏仿功能观,与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有关。也就是说,在古典时期,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着矛盾的双重性,显示着事物内在矛盾统一的思维,这对矛盾是共存的,而不是排他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依相随,将看似不可统一的两种对立的性质与特征统一在一起。换句话说,在古典时期,戏仿本身同时具有既肯定又否定的功能与力量。这种对戏仿功能的理解和认知,与古典时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观念相一致。
二、现代时期:从双重性向否定性蜕变
现代以来,文艺批评界对戏仿功能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古典时期那种事物本身矛盾的双重性被现代性的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所替代。戏仿本身含混的双重性功能被纯净化,被一种单一性功能所取代。正如英国批评家罗斯指出的一样:“文艺复兴之后的批评者没有将戏仿中的‘para’总是译为既与目标相反又相近;它经常变成要么相反,要么一致——例如在德语中戏仿成为‘反歌’或‘副歌’。”*玛格丽特·A·罗斯:《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2013年,第48页。也就是说,在现代性早期戏仿要么就被理解为一致,要么就被理解为相反。就戏仿的功能而言,要么就是一种肯定性的致敬,要么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戏谑、嘲笑或者蔑视。换句话说,戏仿既具有肯定性又具有否定性功能的这种双重性在现代性运动中,变成了要么只有肯定性,要么就只有否定性。历史地看,戏仿的肯定性功能和否定性功能在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得到同等的机会被同时作为一种思想遗产继承下来,没有被同等重要地建构到相应的文艺批评观念体系与创作思想体系中。戏仿对源文本认可与致敬的肯定性功能被人们慢慢淡忘,否定性的功能在文艺实践和批评领域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并占据主导地位。
戏仿功能的现代阐释始于文艺复兴,1516年,批评家斯卡里杰尔认为戏仿是对另一首歌的转化,通过转化其目的是使源文本变得滑稽可笑。1616年,本·约翰逊认为戏仿是对诗歌的模仿,通过戏仿使诗歌变得“更荒诞”。1738年,菲泽利耶则认为戏仿是对虚假的批评。而到1828年,艾萨克·迪斯雷利则进一步指出戏仿是对一部作品的改变和批评虚假的方法;应用范围从滑稽幻想、讽刺到恶意地将原作降低到荒唐层面。*玛格丽特·A·罗斯:《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2013年,第281页。根据豪斯霍尔德的考证,戏仿的原初意义其实并不具有嘲笑、幽默和荒诞的内涵,大致到了16世纪才有了嘲笑的意义,到17世纪以后进而有了戏谑的语义和内涵,因此,对其戏仿对象的贬低也由此而生*Householder,Fred,“Parody”,Journal of Classical Philology,39.1( 1944).。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以来,“那种认为人们仅戏仿自己所爱的作品的广为流传的看法只是部分正确。戏仿更经常的是一种厌腻感的症状。对被传播的文本的否定态度决定戏仿,它倾向于反对,对被传播的文本进行抗议。厌倦、腻味或缺乏信任都在笑声中倾诉出来”*Rohrich,Lutz,“Gebarde-Metapher-Parodie Studien zur Sprache und Volksdichtung”,Burlington:University of Vermont ,2006.。现代以来的批评家,已经将戏仿视为批评与自己文艺观点、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相对的文艺思想、文艺流派、文艺作品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武器。戏仿的目的与功能主要就是讽刺、嘲笑甚至侮辱源文本。
现代性是一场自律性运动。在现代性语境中,批评界对于戏仿功能的理解主要是从戏仿对文艺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入手,一般不会超越文艺本身。也就是说,虽然戏仿对源文本的嘲笑、蔑视甚至贬低是全方位的,但一般是就文学作品戏仿文学作品。在现代时期,戏仿既有内容层面的,也有形式层面,还有价值观念层面的,涉及语言使用、叙事技巧、人物形象和故事主题等方方面面。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性的早期,在启蒙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戏仿主要着眼于对源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叙事主题以及思想观念的嘲笑、讽刺和贬低,诸如大量的戏仿作品将维吉尔的英雄主题降低为醉汉主题或者动物主题等等。20世纪以后,文艺批评对于文学艺术的分析主要着眼于文学内部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形式结构。在此背景下,戏仿从对人物形象、叙事主题和思想观念的嘲笑与讽刺中,转向了对文本的文体特征和形式结构的揭露,从嘲笑文本的内容转向嘲笑文本的形式和存在方式。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戏仿就是“暴露其他技巧的技巧”。这种技巧的暴露,其目的也就是维克托洛维奇所指出的:“嘲笑对立的文学流派,破坏并揭露它的美学体系。”*Tomashevsky,“Boris Viktorovich.Teoriya Literatury”,Leninggard,1925.因此,人们通过“戏仿的方法使原作试图实现的规范失败,也就是说,将原作中具有规范性地位的事物降为一种习惯和技巧”*Shlonsky,Tuvia,“Literary Parody:Ramarks on its Method and Funct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1964,edited by Franoois Jost.2.2(The Hague,1966).。在20世纪的形式主义运动中,戏仿的功能主要是揭示文艺作品的形式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形式存在的特殊性。同时,也使那些神圣文本的表达方式、叙事技巧、结构逻辑中存在的缺点暴露得一览无余,使那些神圣文本写作的所谓高明之处不再那么高深莫测,甚至使其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就此而言,这时的戏仿除了带有嘲笑和讽刺的色彩之外,还具有极强的元小说的作用和功能。
总之,在现代性语境中,文艺创作和批评界对于戏仿功能的理解从古典时期的含混性、矛盾性理解转向了排他性的单一否定性的理解。戏仿的功能在现代性语境中也仅仅成了批判、讽刺和嘲笑敌对作家、流派以及观念的重要武器与手段。戏仿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功能得到了单向度的发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尤其是20世纪以降,批评界对戏仿功能的理解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戏仿的对象从前期的内容批评所关注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逐渐转向后期的形式批评所关注的语言、叙事与结构,甚至于对文类本身的戏仿,这直接开启了后现代对戏仿功能理解的另外一种视角和思路。
三、后现代时期:超越源文本的文化抵抗
如果说在现代时期,文艺批评以一种自律的视角着眼于戏仿对源文本的作用来理解戏仿的功能,主要强调戏仿对源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嘲笑与贬低。那么到了后现代时期,文艺批评对戏仿功能的理解,显然不同于现代时期。按照后现代的文化逻辑,此前被现代性以自律的名义割断的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后现代时期得以重建。因此,在后现代时期,批评界对戏仿功能的理解除了戏仿对源文本发生作用,产生效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与文艺作品的外部世界产生关联,注意到戏仿对外部世界产生的作用。如果说,在现代时期,批评界主要看到的是戏仿的否定性的力量,那么,在现代性向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戏仿本身的肯定性力量又再一次被挖掘出来,正如琳达·哈琴指出的:“后现代讽拟(即戏仿),既是解构地批判性的,亦是建设地创作性的。”*莲达·赫哲仁(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刘自荃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当然这种肯定性不同于古典时期以戏仿的方式与手段去习得一些写作的技巧与技能的肯定性。在后现代语境中戏仿不仅仅是通过对源文本的戏仿使自身的局限与缺陷暴露就够了,而是通过暴露使源文本从内容到形式呈现出一定的荒谬性,但这种荒谬性不单纯是一种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力量,而是使这种荒谬性转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批评家看到了戏仿有着一种通过将事物按其逻辑将其推到极致、本身的否定性力量向肯定性力量转化的可能性。
后现代时期,戏仿的肯定性力量主要聚焦于文艺创作背后的成规以及揭示这些成规带来的压迫感和话语权力。戏仿的源文本,一般而言,都是那些经典化的或者神圣化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代表着某种美学观念和文本规范,以及表达风格,在文艺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被各种权力资本建构起来,并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些神圣或者经典文本的地位是通过这些文艺之外的资本与力量建构起来的,但它们往往又容易被一种自然而然性或者以艺术或者美学的名义所遮蔽。在后现代语境中,在批评家看来,艺术家就是要通过戏仿这种方式或者技巧,使那些被遮蔽的成规及其形成的暴力暴露出来,看到这些成规对文艺创作或者后世作家的压制与暴力。正如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指出的那样,戏仿有着两套代码,“( 现实)可在两套代码交叉时被揭示,因为两套代码的同时在场有助于我们看到成规性框架如何制约着我们的理解”*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家通过戏仿的方式,使那些经典文本、神圣文本隐性的权力呈现出来,“暴露其中的规训机制,并引起人们的质疑与反抗,从而在颠覆中完成某种反思和重构”*刘桂茹:《“戏仿”与后现代美学》,《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因为,只有使这些源文本的暴力机制呈现出来,才有可能让破除这些暴力压制的行为成为可能。
就此而言,后现代时期戏仿的功能跟古典时期戏仿的功能就明显现出了分野。如果说古典乃至于现代时期,戏仿有着向历史和成规致敬的文化意味的话,那么后现代时期的戏仿显然与其功能和价值诉求背道而驰,在后现代时期“戏仿不仅是要恢复历史和记忆,而且要质疑一切写作行为的权威性,所采用的方式是将历史和小说的话语置于一张不断向外扩张的互文网络之中,这一网络嘲讽单一来源或者简单因果关系的概念……后现代主义通过使用正典表明自己依赖于正典,但是又通过反讽式的误用来揭示对其反抗”*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因此,后现代的戏仿与古典时期的戏仿不一样,它不以无限接近或者相似源文本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而是在戏仿源文本的时候,时刻保持了一种与源文本保持差异的清醒的意识,“戏仿就是模仿这种话语,但是通过重新组织、重新建构而使它不再具有它隐含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观念”*O’Grady,Kathleen,“Theorizing Feminism,and Postmodernity:A Conversation with Linda Hutcheon”,Rampike .9.2(199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性的戏仿是一种有差异和保持距离的重复,与古典时期戏仿的趋同性和接近性的重复要大相径庭。
显然,后现代时期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对戏仿功能的理解,已经跳出了戏仿对文学艺术本身产生的影响和具有的价值,而是从戏仿对文艺之外的外部世界和社会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在后现代视野中,作家与批评家通过戏仿使压制作家的那些文化成规、话语霸权、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彰显,使他们看到了自己被压制的情状,后现代戏仿“在阐明自己的同时,艺术作品也清楚展示了审美概念化的形成过程以及艺术的社会学状况……即使自觉意识最强、戏仿色彩最浓的当代艺术作品也没有试图摆脱它们过去、现在和未来赖以生存的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反倒是凸显了上述因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2009年,第33-34页。。后现代戏仿往往“以反讽的口气揭示,在传统延续的核心部分里传统中断了,在相似性的中心里存在着差异。从某些意义上看,戏仿是后现代主义一个完美的表现形式,因为它自相矛盾,既包含又质疑了其所戏仿的事物”*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2009年,第10页。。因此,可以这么说,在后现代时期,戏仿确实已经超越了文学艺术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实践形式,它表达着对文化成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抵抗和解构的诉求,成为弱势阶层和亚文化表达自我、抵抗同质化、保持差异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其文化政治功能在这种语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