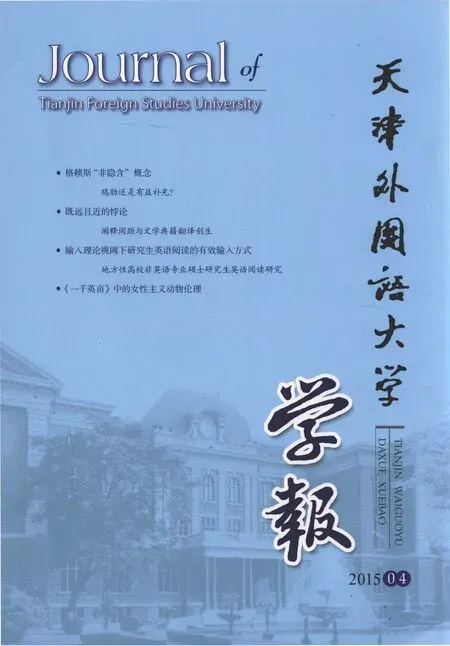走出哥特小说的困境——评析《呼啸山庄》的艺术创作路径
王 喆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达州 635000)
一、引言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是维多利亚时期名震英伦三岛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其代表作《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1847)如同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一般,对生与死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复仇本身,被西方评论家视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女作家在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中成功地运用了哥特手法和哥特模式,更使作品具有了超时空的恒久性和神奇的魅力。她那独特的想象和奇异的构思为传统哥特形式注入了现实的内容和激烈的情感,这也使得这部独树一帜的撼世之作远远超越了传统哥特模式,自立于时代文学主流之外。“如果我们只认为 《呼啸山庄》仅仅是一部哥特传奇剧的话,我们就将自动地将其排除在是对人类命运思考这一主题的范畴之外。”(Watson,1949:88)也正如英国作家、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前辈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艺术贡献所高度赞扬的那样,艾米莉•勃朗特对哥特小说的继承和创新同样也是无愧于“接过的是砖,留下的是玉”(常耀信,2006:90)。
二、哥特的影响
原指建筑风格的一词“哥特”用于英语国家的文学艺术作品可追溯到18世纪,“主要具有野蛮、中世纪和超自然一种含义”(李伟昉,2005:2)。到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长篇小说的一个新的品种,以描写古堡里发生的神秘恐怖事件为特征,因此被称为哥特小说或哥特传奇”(高继海,2003:9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英国作家、文化界风云人物贺拉斯•沃尔普尔(Horace Walpole)发表的非现实主义小说《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开创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哥特小说的先河。随后这一文学形式蔚然成风,一批重要的哥特作家和影响深远的哥特名作相继出现,如雷德克利弗夫人(Mrs. Ann Radcliffe)的《乌多尔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 和《 意 大 利 人 》(The Italian,1797)、 刘 易 斯(Mathew Gregory Lewis)的《修道士》(The Monk,1796)、雪莱(Mary Godwin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7)等。这类作品主题大多是通过家族间的长期怨恨、继承权的争敚来向世人揭示人性的卑污和龌龊面,故事情节上肆意表露残暴和惊惧。“英国哥特小说虽然不旨在对理想社会和价值观念作正确表现……但是其作为一股道义力量从未泯灭,始终与恶冲突搏斗,伴随着紧张的道德探索。”(李伟昉,2005:13)哥特小说的出现和普及为当时沉闷的英国社会带来了“它所急迫需要的激情、活力和宏大的精神”(Punter,1980:6)。由于哥特小说不仅大量展现激情、感受、诡秘和超能量现象,同时也让遐想随意飞奔。当时浓郁的哥特色彩“除了影响浪漫主义诗歌之外,还对勃朗特姐妹及其他19世纪小说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赋宁、刘意青、罗经国,1999 :438)。
19世纪的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国力极其强盛,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女性不但工作机会增多,受教育的机会也随之提高。虽然生活在约克郡偏僻的小乡村里,勃朗特姐妹也因此有机会染指文学。小时候父亲就把她们带到一家神职人员女儿专门去的学校学习,青年时期又到布鲁塞尔留学多半年。这些难得的机遇使“她不仅阅读了各种文学经典,而且阅读了布莱克伍德(Blackwood)和弗雷泽(Fraser)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刊登各种各样情节紧张、恐怖而激动人心的故事和诗歌”(邓颖玲,2005:85)。在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里专修德语时,艾米莉接触到了霍夫曼(E. T. A. Hoffman)①的作品。这些德国浪漫主义的离奇传说带给她极不寻常的影响,使她形成了奇特的联想空间。这些异国他乡的哥特传奇为她后来的作品揭开了人类自然天性中奥秘、情感泛滥的一面: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无理由的鲁莽和梦靥般的畏怯。“不论按照任何艺术标准,‘恐怖’故事的价值如何,它吸引了坚强的有才智的人,而它的影响上升到更高的艺术领域,影响到司各特和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和雪莱的诗歌。”(埃文斯,1984:260)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小说和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诗歌同样也影响着勃朗特姐妹的创作。司各特的小说《威弗利》(Waverley,1814)呈现给我们的正是哥特式的城堡、残缺不全的修道院、幽灵、巫师等。从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说中勃朗特姐妹“学会了讲故事的艺术,欣赏到了住有强壮而富有冒险精神角色的激情四溢、浪漫的风景之地”(奥尼尔,2004:86)。而拜伦的影子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主人公身上也有所体现。《呼啸山庄》中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就是拜伦式的英雄,女主人公凯瑟琳也与拜伦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为情所忧,相互间的痴迷都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同时又带来了破坏性的力量。可以说“从内容到情节,《呼啸山庄》的文学源泉很有可能取材于拜伦的叙述诗歌”(Holland,2009:32)。
三、哥特的继承
《呼啸山庄》代表性地展示了哥特小说的一些主要特点,即难以捉摸、幽森阴暗、超越现实。勃朗特成功运用了一系列的哥特叙事策略来突出小说主旨,营造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描绘了非同寻常的主人公形象,勾勒出迥然不同的两庄环境,揭示出各色人物激烈的情感纠葛,使得这部旷世奇作恰似蒙娜丽莎的微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女作家大大增加了小说的传统哥特元素——受虐、死亡和恐怖,使得许多迷雾有待不断挖掘。
在哥特小说里,人物塑造通常是用来呈现哥特要素的主要手段。《呼啸山庄》中就有形形色色的可怕人物。小说主人公之一希斯克利夫的行为举止无不犁刻着哥特的印迹:残忍、傲慢、不择手段,如同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呼啸山庄一般荒凉而顽固不化。神秘和冷漠是他留给前来造访的房客洛克伍德的第一印象:“当我骑马走进他跟前,看见他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猜忌的望着我,而当我通报自己的姓名时,他的手更深地藏到背心里。”(勃朗特,2001:1)。这位风暴之子更像山庄荒原边的岩石、山庄上空肆意的狂风和捉摸不定的天气。“他对凯瑟琳的爱是一种猛烈的非人间的感情:那是一种热情,能够在一个恶魔的邪恶本质里沸腾燃烧……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地狱同行。”(勃朗特 b,1983:27)。这样的猛烈突袭与悬河泻水般的豪情带来的是一种摧古拉朽的消亡,这种哥特般的一举一动使他更像弥尔顿笔下《失乐园》里的撒旦,最终不仅导致了呼啸山庄的掌门人恩肖和画眉田庄的主人林顿两个家族的澌灭,同时也造成了两代人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伊莎贝拉对恶棍英雄希斯克利夫火一般的激情神魂颠倒而最终四面楚歌,沦为了他雪耻的替代品。无论从伊莎贝拉异想天开的思想、任性愚蠢的性格,还是从后来被希斯克利夫囚禁在屋,又逃跑到伦敦等细节来看,伊莎贝拉都是哥特式女主人公的典型。
小说在主题表现方面同样继承了哥特手法。无论是希斯克利夫在婚后对伊莎贝拉的肆意虐待,通过赌博方式霸占土豪辛德雷所有的财富,促使自负的辛德雷早早在激愤和入不敷出中饮恨而终,还是以诱骗加强迫的手段促使小凯瑟琳嫁给小林顿,以此攫取画眉山庄的继承权,同时对辛德雷的儿子小哈里顿和小凯瑟琳的肉体折磨以及精神摧残,女作家都成功地将哥特元素——愤恚、鬼蜮伎俩和继承权的强占演绎得淋漓尽致。“事实上,《呼啸山庄》中有不少情节是潜在的哥特式题材。”(钱青,2006:330)
在背景的建构和离奇的意象描写上《呼啸山庄》更是处处都散发出强烈的传统哥特味道。山庄“狭窄的窗户都深深嵌入墙里,墙角有大块凸出的石头保护”(勃朗特,2001:2),山庄里面更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森可怕,还不时冒着阵阵寒气。女作家用诗人尖锐的眼光和超现实的想象牢牢地锁住世间的朴素意象,使得人物的精神面貌夹杂着不可确定的无名力量,向读者描绘出那足以包罗万象、吞噬宇宙的高大形象。
哥特小说的超自然元素在《呼啸山庄》中也尽显其能。洛克伍德在山庄里的梦魇让人读起来毛骨悚然。这一幕与惨淡冷清的背景互为关联,给夜晚的山庄增添了更加诡异的不安,继而将小说的哥特气氛推向高潮。小说结尾山庄的放牧者时常碰见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鬼魂在荒原上、教堂附近及院子周围流浪。这些描写无不充满了浓厚的哥特意味,使得作品更像解不开的斯芬克斯之谜。
四、哥特的超越
这部小说虽然处处闪耀着哥特的火花,但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现实邪恶的鞭挞“与更加传统的哥特式情感的似是而非相比较,《呼啸山庄》至少是一首真实世界中的美与神秘的赞歌。它将‘真实的’与‘浪漫的/怪诞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障碍化解掉。宇宙之中似乎没有超越一切的上帝,有的只是超越所谓‘死亡’的强烈、巨大的人类感情。”(尔欧茨,2006:210)因此,《呼啸山庄》虽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却在众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超越这个传统时代的精神风貌,更趋向现实主义。勃朗特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人间奇葩已经摆脱了传统哥特小说的困境,走在了她的时代的前列。
1 冲破传统的哥特人物刻画
传统哥特小说很少涉及人类伟大非凡的爱,主人公们的爱只会被挤压或忽视,故事结尾往往遵循劝善惩恶的传统道德理念,但“在《呼啸山庄》中,传统道德并未占上风”(Adams,1958:58)。艾米莉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拥有更加真实的情感和生气勃勃的活力。女作家一方面怜悯并歌颂这种不受任何工业文明制度与非情感羁绊的人间激情,生动地刻画了把整个人生癫疯般集中在唯一对象的执著的个人,另一方面又描绘了这种激情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她的字里行间使得哥特小说固有的僵化的人物变成了丰满而活泼的艺术形象。希斯克利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幼年经历了人间的各种不幸,形成了性情刚强而又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性格让他对爱和家更加渴望。他和凯瑟琳之间的爱超出了一般人的常态,这种爱的冲动性和破坏性太直接、专一,他们之间的亲吻常常犹如互相愤怒地撕扯。在得知凯瑟琳的死讯后,希斯克利夫更是“用头撞那多节的树干,抬起眼睛,嚎叫着,不像是一个人,倒像是一头野兽快要给刀尖和长矛捅死了”(勃朗特,2001:219)。希斯克利夫是最陈旧、最粗犷、最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的化身,他痛恨责任、人性、怜悯、慈善,对传统习惯和道德约束切齿腐心,他的灵魂和身躯与凄凉、乌云弥漫的荒原相一致,既冷峻、严酷、骚动却又充满无限活力。他就像一个拜伦式的英雄,阴郁、孤傲、我行我素,但又仍不失为经天纬地般的英雄。他富有果敢和决心,对传统的伦理道德高傲不屈,与命运殊死搏斗,与欺压和不公平进行着顽强的拼争,期盼一个更高尚、更自由的心境,以此僭越生命的极点。他同时又浑身散发着恶魔的邪恶气,与正统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认为上帝令他失去挚爱,与上帝争吵,连死后也不采纳基督教的葬礼。这只会把自己置于与人为敌的位置,进而异化成一名食尸鬼。勃朗特一反维多利亚时期作家对人物的创作思维取向,将视野投向了遥远的未来,笔下的人物不再仅仅体现传统的哥特思维方式,常理不再作为他们的身份符号,因为他们已非常人,其自身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由于对强烈的、不加控制的激情的描述,使得艾米莉的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显得与众不同。”(何其莘、张剑、侯毅凌,2004:630)也正是艾米莉对希斯克利夫这种复杂性格的深刻挖掘,才使得传统恶魔式的哥特人物得以深化,更具独特的艺术魅力。“勃朗特超越了生与死的传统浪漫传奇,超越了爱与险的传统哥特模式”(Mckinstry,1985:141),预示着几十年后左拉自然主义思潮的兴起。
2 赶超时代的环境描写
女作家笔下光怪陆离的人物刻画是与贯穿全书的环境描写密切呼应的。小说尽管启用了传统的哥特手法,但故事情节不是发生在远古的13或14世纪,而是将镜头转换到了女作家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期,描写了一个不同于她的时代。狄更斯、萨克雷等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喧嚣忙乱的世界根本没有进入艾米莉的视野。她所描绘的不仅是一片充满原始气息和蛮荒自然之地,同时分享了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华兹华斯的创作原则,即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是自然神秘主义的典范”(Williams,1985:105)。借用这种不同于典型哥特风格的别致手法的确有助于突出这部经典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
艾米莉终其一生都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哈沃斯这个贫穷的小城里度过,她喜欢这里的自然风景。虽然在别人眼中约克郡荒原的景色并无什么诗情画意,“但在她眼中,最幽暗的石南丛会开放出比玫瑰还要娇艳的花;在她心里,铅灰色的山坡上一处黑沉沉的溪谷,会变成人间乐园”(勃朗特a,1983:31)。在这片荒原上几乎看不见树木,即使有几棵也因常年的严寒和大风而弯腰斜倚在山边。为了抵御狂风,农民的房子几乎都是用浅色或棕色的石头砌成的。“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约克郡人们突出的性格,他们长期与这恶劣的环境斗争,因而性格独立而坚定……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他们认识到要尊重事实,因而他们很实在……这荒原,这人民,影响着勃朗特姐妹,影响着她们的品格,她们的为人,她们的思想,以及她们的作品。”(张耘,2002:3)艾米莉运用对空间和时间成功把握,把自己对生活的情感和生存经验的思考浇灌到故事里的大自然中去,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一道悲欢离合。“在 《呼啸山庄》中,想象就是直觉,它以神秘现象的具体化形式对抗着理性和传统道德的朦胧感觉。她对现实的认识挑战着1847年的那种唯物主义的、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Smith,1992:516)在身体虚弱的老恩肖突然去世的那天傍晚,“狂风绕屋咆哮,并在烟囱里怒吼”(勃朗特,2001:51);在年轻的希斯克利夫愤然离开山庄的那天深夜,“暴风雨以其全部的狂怒向山庄呼啸着袭来”(同上:108);在希斯克利夫带着忏悔离开人间的那天晚上,“倾盆大雨一直下到黎明时分”(同上:438)。女作家笔下的自然景象绝非简单的主人公们演出的舞台,而是一种现实的、具有魔幻意象的大自然,具有一种难于预测的超自然力量,这为传统哥特形式注入了现实的内容和强烈的情感。就连希斯克利夫的复仇好像也是自然而然,像自然界中的溪流时而迂缓、时而亢奋地向前流动,一旦遇到险阻就会改变流向,有时也会泛滥造成洪灾,但最终还是归于大海。
《呼啸山庄》凝聚了女作家对家乡生活和特定地域的思考,描摹的明丽自然景物都是耳濡目染的家乡美景,主人公们也都是生长在约克郡的远亲近邻。我们既能被强大的超自然力所震撼,也可体会到自然景物的亲切及故事人物的血肉丰满。正如洛克伍德在逃离了苦难,回到了文明,最后一次造访山庄时看到第二代的凯瑟琳和未婚夫哈里顿幸福地在一起那样,“浪漫和哥特的要素在阳光普照的理想世界中,已很难长存”(Oates,1982:437)。女作家在实现一种转化,即从传统小说到浪漫传奇,从黑夜王国到日常生活。
五、结语
无论是司各特所要求的以“浪漫主义手法解决其主题”,还是18世纪以来的文学传统所要求的“对真实生活之表面给予平面镜般的反映”(利维斯,2002:46),都被艾米莉发人深省地彻底打破了。作为独立于19世纪文学主流的另类作家,她的创作风格清晰明了却又充满着无限的活力。传统哥特手法的运用不仅仅是营造恐怖气氛,让读者充满疑惑和神秘,还是为了建构更加自然合理的情节框架,使得人物的复杂心理在深度上更具独特的艺术魅力。“《呼啸山庄》出现的鬼魂既非哥特式的鬼魂,也非维多利亚杂志上的鬼魂,他们代表着另类鬼魂的萦绕——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对被他们自己贬为平民的恐惧的作祟。”(Krebs,1998:41)。女作家那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创造性地使传统的哥特题材服务于她的目的,即发现并抒发新的情感,提高情感的强度。典型的传统哥特风格被人们戏称为黑色浪漫主义,但女作家却把浪漫主义移植到了现实的沃土上,给陈旧的哥特形式注入了激烈的情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赋予了传统哥特小说一个广阔的新领域和新特色。这既是对哥特小说的继承和超越,同时也为困境中的哥特小说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是对哥特小说成功的扬弃。“《呼啸山庄》已被普遍认为是传统哥特、浪漫传奇和现实主义小说的混合体。”(刁克利,2008:168)
注释:
① 霍夫曼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擅写魔幻小说,其作品常具神秘、诡诞之色彩。
[1] Adams, R. Wuthering Heights: The Land East of Eden[J].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958, (1): 58-62.
[2] Holland, M. Lord Byron’s ‘The Dream’ and Wuthering Heights[J]. Bronte Studies, 2009, (1): 31-46.
[3] Krebs, P. Folklore, Fear, and the Feminine: Ghosts and Old Wives' Tales in Wuthering Heights[A]. In J. Maynard (ed.)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C].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98.
[4] Mckinstry, S. Desires Dreams: Power and Passion in Wuthering Heights[J]. College Literature, 1985, (2): 141-146.
[5] Oates, J. The Magnanimity of Wuthering Heights[J]. Critical Inquiry, 1982, (2): 435-449.
[6] Punter, D. The Literature of Terror[M]. London: Longman, 1980.
[7] Smith, S. The Supernatural in Wuthering Heights and Its Debts to the Traditional Ballad[J].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1992,(172): 498-517.
[8] Walton, M. Tempest in the Soul: The Theme and Structure of Wuthering Heights[J].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949, (2): 87-100.
[9] Williams, A.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in Wuthering Heights[J]. Studies in Philology, 1985, (1): 104-127.
[10] 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史[M].北京:人们文学出版社, 1984.
[11]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 ].王蕙君,王蕙玲译.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1.
[12] 常耀信.英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13] 邓颖玲.论艾米莉勃朗特对哥特传统的发展[J].外语教学, 2005, (4): 84-87.
[14] 刁克利.英国文学经典选读(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15] 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2.
[16] 高继海.英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7] 何其莘,张剑,侯毅凌.英国文学选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18] 简·奥尼尔. 勃朗特姐妹的世界——他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M].叶婉华译.海南:三环出版社, 2004.
[19] 李赋宁,刘意青,罗经国.欧洲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20] 李伟昉.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1] 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22]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直言不讳[M].徐颖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23] 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诗选》序[A].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a.
[24] 夏洛蒂·勃朗特.《呼啸山庄》再版序[A].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b.
[25] 张耕.荒原上短暂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