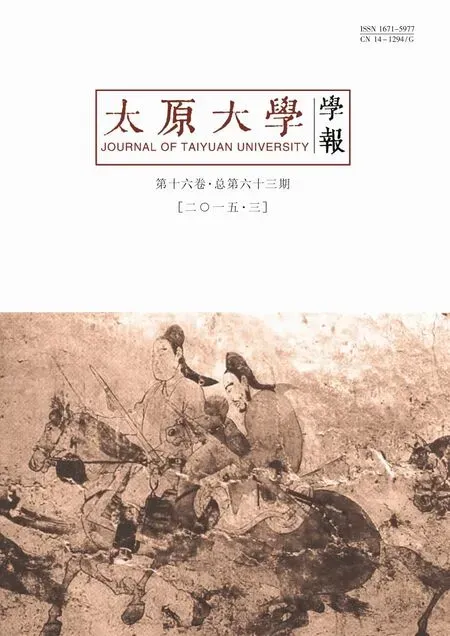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呼愁”之伤
——“80后”作家笔下的城市青春叙事
孙 潇,顾 玮
(1.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部,北京 100083;2.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呼愁”之伤
——“80后”作家笔下的城市青春叙事
孙 潇1,顾 玮2
(1.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部,北京 100083;2.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80后”作家的青春写作以城市记忆作为写作资源。在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后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等深深影响了“80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改变了文学生产机制。“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书写体现出独特的城市经验,充满了青春的“呼愁”之伤,承载了他们对爱情的追寻和追寻不得的忧伤;由中国社会变迁、西方文化涌入带来的文化震惊与心灵失衡感带来的忧伤;无法实现理想生活,无法接近信仰、梦想的忧伤。“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叙事中看得见的是城市中的物质细节,看不见的是“80后”作家对城市的思考与反思,以及对成长的宣泄与记忆。
“80后”作家;呼愁之城;城市青春叙事
城市是复杂的人类生存空间,是现代化的一种载体,人建造了城市,城市也在改造着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现实改变着国人的生存语境,由此,文坛出现“个人化写作”,表现出解构和疏离宏大叙事,高扬个体生命价值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姿态,为“80后”文学的个体化、本真性写作提供了有效路径。“80后”作家的写作特质被定义为青春叙事,一方面因为他们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的年龄较早,更是因为他们的文字多是围绕当下一代人成长的展开,表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年轻人在城市中的成长体验、生存困惑等,其基调多是忧伤的。“80后”作家以城市青春写作对城市进行多维的文化解读,他们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理念、创作法则,将城市景观与小说情节相连,将地缘文化与成长体验融合,使城市成为刻画人物和阐释主题的方法手段。从能指的角度来说,城市青春叙事就是小说中出现的城市街景、各种场所。从所指的角度来说就是其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理念,作家的成长记忆、价值观等等。
“80”后作家笔下的城市多是充满忧郁色调的“呼愁之城”,“呼愁”一词来自土耳其语,与忧伤相近,大致引申出三个意思:对欲望的过度渴求引发的忧伤;对伊斯坦布尔曾经辉煌的怀念与西化改革引发的尴尬境地而忧伤;因为不能领悟真主而哀愁。此处借用“呼愁”的意象,指的是在“80后”作家笔下的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对爱情的追寻和追寻不得的忧伤;由中国社会变迁、西方文化涌入带来的文化震惊与心理失衡感引发的忧伤;无法实现理想生活、无法接近信仰、梦想的忧伤。在李傻傻、张悦然、郭敬明、笛安等“80后”作家的笔下,城市“呼愁”是对这“游荡之城”、“残酷之城”、“魅惑之城”、“乡愁之城”的忧伤生活体验。在他们的小说中,城市里的一切景观都像是博古架上的摆件,可见的每一件收藏品之后都有一段故事或者记忆,不可见的是这段故事中游离的“80后”一代人的情绪与执着:青春成长的叛逆与忧郁,爱情的美好与背叛,人情的冷漠,生存的艰难与迷惘,理想与现实,灵与肉的矛盾等等。
一、城市青春叙事的文化背景与象征意义
在“80后”作家的文本中,城市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故事背景,呈现出一种客观的地理位置,又作为一种虚构的理想世界,表现了年轻人在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物质的现实城市体验与精神的理想城市幻想之间的复杂联系。纵观城市叙事出现在现代文学中的历史以及其文化背景,首先可以看到城市叙事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有密切联系。其次,90年代中国文化转型,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青年亚文化的传播改变了“80后”一代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城市青春写作。
(一)城市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乡土意识一直是国人的主流意识。建国后至70年代,城市叙事基本上是以乡村视角关照城市生活或者以城市工业题材写作为主。到了80年代经济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近代工业大繁荣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人口和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都市型转化。城市化不仅为城市叙事提供了现实基础与文化环境,重新构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影响着“80后”一代人的心理结构、生活方式与观念,比如金钱至上和精神的流浪,欲望的膨胀和理想主义的萎缩,崇尚个性与“嗜酷”风潮等等。 其次,在城市中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高科技滋生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批量复制产品;以大众媒介为文化传播形式,以现代技术手段为文化生产模式;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受众,具有娱乐性与时尚性。在其影响下,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包括文学政策、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批评、文学传播和消费等文化机制都有相应的改变。文学抄袭、作家的偶像化、明星化,媒介掌握批评话语权从而更多地干预着文学场中的规则和走向。文学生产主体除了主流作家还有网络写手和学生等,文学生产转向以出版为主导。“传媒策略、娱乐精神和文学导购成为主要手段的评价机制,商业利润成为文学生产的原始动力,文学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强。”[1]
此外,后现代主义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构成“80后”一代人成长的文化背景,“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解构性、反理性、反权威、边缘化、通俗化、大众化、颠覆元叙事等特点。而“青年亚文化”作为亚文化的分支,以年龄为界,依据此时的生理、心理特点,它的显著特征就是颠覆性、流行性和通俗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在青年亚文化圈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同时中国青年亚文化又是以后现代主义的面貌出现,因此,当二者相结合之后,很快就在“80后”一代人的文化生活中传播并蔓延开来,加之商家的推波助澜,迅速扩张到各大中小城市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多以价值认同为视角,研究的是青年群体抵抗以父辈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的亚文化现象。”[2]因此“80后”作家以写作来表达解构权威、逆反、孤独、以个人为中心叙事等叛逆情绪和成长经历,并热衷于描绘城市生活的物质细节,比如各种城市景观、名牌消费品等,这样的城市青春叙事隐喻了作家的自我意识在其中。
(二)城市青春叙事的象征意义
“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写作象征隐喻了高速发展的经济与城市化潮流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困境。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生活与社会构建的一系列变化:高度同一性的生活不复存在,多元化文化和价值观冲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崇高的革命信仰淹没在物质生活的平凡中,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刺激着年轻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有人迎风而上、奋斗不息,有人渐渐麻木、随波逐流,有人愤世嫉俗、格格不入,多种文化景观融汇在城市之中。“80后”作家以其敏感的神经捕捉城市生活中年青一代人的生存现状与精神状态,描绘他们的校园生活、成长见闻、心理历程,并以他们的眼睛反观与思考社会和文化。
“80后”城市青春叙事也隐喻着新生代作家对文学写作本身的继承与创新。在内容上有意继承90年代“私人化写作”,注重表现当下年轻人的个体生命体验,私人观念与叛逆意志;在叙事方式上表现为一种“小我叙事”,不写时代历史的黄钟大吕,站在“独一代”的角度去写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求学、工作、谋生,并且指向个人的心灵与秘密,或采用独白式叙事姿态,或用意识流、时空跳跃拼贴、幻觉等手法,注入童话因素,以愤世嫉俗或阴郁华丽的文字吸引读者;在写作动机上,主要是为了心理和精神满足的需要,宣泄青春感受,包括朦胧的性、单纯而绝望的爱情、成人世界的残酷、童年的伤害、物质世界的生存体验等。“80后”作家以群体为现象,面对来自主流文学界的关注和批评,他们或报以冷眼旁观,或回之以唇枪舌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与凌厉,他们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与市场。
无论是郭敬明,朋克青春作家春树,玉女作家张悦然,叛逆顽主韩寒,少年沈从文李傻傻,还是新锐作家笛安、蒋峰、小饭、孙睿等,他们的青春叙事多数以城市为写作背景,写校园、家庭、城市景观、消费品、爱情、友情等人情冷暖,字里行间隐藏的是他们内心对于城市生活的体验,并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人与城的故事里青春期固有的种种情绪如墨入水化于字里行间,仿佛青春就应该是这样。城市青春写作是“80后”作家登上文坛的起点,也是他们和以往青春写作沟通的藩篱。首先,校园生活中的青春诉求,梦想与爱情,在精神与身体上的开启都较之前的作家有很大突破。其次,像《北京娃娃》、《梦里花落知多少》、《水仙已乘鲤鱼去》、《活不明白》、《草样年华》、《红×》等,其中塑造的人物具有的精神特点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代表性,代表了一个时期的青春文学形象。再者,对于青春期身体与欲望的描写更加正面与自然,引发人们对新时代下青春与性本身的思考。
总之,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加速,大众文化与现代媒体的共谋以及“浅阅读风潮”的影响,结合视觉化、图像化的精美包装,作家明星化的包装宣传,贴标签生产等文学生产运作手段,使得“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文本畅销于图书市场。在他们的文本中,现代城市是一座座“呼愁之城”:是魅惑的、残酷的、世俗的、永不停歇的,其现代城市生活体验是现实的、孤独的,他们或在其中游荡、寻找,或享受、挣扎,或以脉脉温情排解那份对乡土情怀、人情冷暖的乡愁情结。
二、“呼愁”之城
当一座城市发展起来,伫立在时间的长河中,目送了天空与大地的变换,见证了万物的枯荣代谢,城市就拥有了一定的品格与记忆,光阴荏苒,城市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本雅明说过,把事物呈献给现在的真正方法是在我们的空间里再现它们。以下将以李傻傻、张悦然、郭敬明、笛安以及他们的主要代表性作品为分析对象,一窥“80后”城市青春叙事所传达出的城市“呼愁”体验。
(一) 李傻傻——游荡之城
李傻傻原名蒲荔子,其城市青春写作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他的乡土成长背景与入城求学经历,以“少年沈从文”成名的他文字中有更多的质朴与灵性。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乡村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开始破碎,进城谋生诱惑着乡村中的人陆续走进城市。来自乡村的主人公似幽灵般流浪,徘徊在城市中,城市在李傻傻的笔下是一座游荡之城。游荡是《两个少年》中的乡下男孩在城市中的迷失和格格不入,当他学会了在城市中生存却失去了话语权,他无法用合适的语言表达所谓单纯悲凉的乡村经验,也无法传达出刺激的城市体验,失语是他的流浪;游荡是《红×》中的沈铁生在城市里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流浪,他游荡在城市里,在学校周围的各条街道与溜冰场里,他尝遍了行窃、性爱与玩世不恭带来的短暂的优越感与快乐,只是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之后便是对心灵摧毁性的黑暗与灵魂的放逐之苦。
来自乡村的男孩游荡在城市底层,渴望能很快适应城市生活,赚到钱,得到爱,不过他们往往剑走偏锋。游荡是自尊高于生命,经历生存的残酷,理想与现实的冰冷,是青春路途上经过的一片晦暗的风景,那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会打破少年的单纯初衷与玩世不恭。正如沈铁生在城市中的游荡青春,在无所事事中开始,在不了了之中结束。游荡是李傻傻激进的叙事态度,也是来自乡村的孩子渴望融入城市的姿态。李傻傻的敏感暴露了初涉社会的年轻人对生命本身的恐惧以及对城市法则的抵抗。伴随着他的成长,他必将走向妥协,结束游荡的状态,融入体制与社会。这也是一部分“80后”在城市成长过程中的无奈与自我救赎之举。
(二)张悦然——残酷之城
张悦然笔下的城市青春叙事没有明确局限于哪几座城市,城市经验真正内化为作者的一种生存体悟,隐没在文字的深处,成为一种情绪,一种氛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在对爱的不停寻求之中演变为残酷的伤害,成为施虐者和被虐者:《红鞋》中女孩和杀手的故事,就是围绕爱的施虐与受虐;《宿水城的鬼事》中女鬼对穷书生的痴情与奉献;《竖琴与白骨精》中小白骨精对痴迷于做琴的丈夫的无私之爱,爱到贡献出自己的所有骨头;《誓鸟》中宵行对爱的隐忍,春迟对承载着爱之记忆的贝壳的痴迷;《葵花走失在1890》中那朵花对梵高如宗教献身般的迷恋等等,这些爱都是凄美绝艳而锋利残酷的,直到一方付出生命或双双死亡。“80后”一代人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面对物质与信息的快速催熟,对于爱的渴求,对人情冷暖的冷漠与不信任,普通家庭的生存压力,教育体制的压抑等等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残酷面,张悦然以敏感的心灵捕捉这些再加以童话般的创造,呈现出她笔下的残酷之城。
这座“呼愁之城”空灵而残酷,她塑造的人物自我意识强烈,他们都对爱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疯狂,比如《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丛薇和璟,《誓鸟》中的春迟,这是张悦然对当今城市生活中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的痛诉与反思,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彰显和自恋的表现,通过借助其他人物形象的陪衬或男性角色的垂青,甚至借更多残酷的牺牲来祭奠女性的美与崇高。 因此,血液、献身、酷虐等频繁出现在张悦然的文本中,阴郁华丽而鬼气迷蒙是她的显著特色,时代环境的压抑和独自漂洋过海的求学经历使得她的内心积聚了更多的感伤与孤独,张悦然在文字中宣泄“80后”在城市生活中的彷徨与寂寞,社会的种种不公与冷漠。虽然“悲观主义解决不了悲剧,悲剧倒往往促使人跨越悲观”[3],但一味地消极沉溺并不可取,文坛和社会同样需要正能量,青少年需要健康价值观的指引,这也是“80后”作家的努力方向。
(三)郭敬明——魅惑之城
郭敬明是四川人,但在他笔下展示“魅”、与“惑”的城市不是“天府”成都而是“魔都”上海。《小时代》里的上海是精英掌控的命运巨轮,是暧昧又冷酷的死神之镰。这里的林萧、顾里、南湘、宫洺们青春鲜活,光鲜亮丽,鲍德里亚称之为“后工业时代的贵族气质”,却始终徘徊在动荡与劫难的边缘。《小时代》的文字与影视作品对当下年轻人来说就是一场华丽的盛宴,几乎可以满足他们对未来所谓“成功”的所有美好幻想,但是这里每个人都各怀秘密,亲情、友情、爱情敌不过金钱,光鲜的表面下有太多人性的无奈与自私,在物质面前一切都变得虚无而不真实。在这座物质时代的“魅惑之城”里,“成功就是赚钱”是郭敬明眼中的游戏规则,生活得最舒服的“永远是金融家和有钱人,普通人会活得很压抑”。[4]
郭敬明创作《小时代》,故意以残忍、赤裸的口吻讨论问题,刺痛人的神经,他遵从内心的出发点去创作,记录他眼中的上海,刻意血淋淋地挑起矛盾。因此,上海在郭敬明的笔下就成了充满魅惑的物质之都,成功人士和精英的天堂。一部《小时代》充斥了无数名牌和奢侈品,这些城市物质细节被赋予了丰富的联想,同时,书中“夸张过头的情节折射出了资本对于空间消费毋庸置疑的主导权,这会导致居住隔离和空间剥夺等负外部性,即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5]长此以往,便会加剧社会不公平和贫富两极分化。诚然《小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郭敬明奋斗和成功经历不可复制,书中描绘的精英上海也许会给广大青少年励志奋斗的鼓舞,但大量浮夸奢华的描写难免会引导青少年追求物质生活。郭敬明推崇的这种“唯成功论”是当今社会崇尚金钱拜物,现代人精神空虚和大众文化与资本共谋的产物,更是对当下年轻人价值观的严重扭曲。当物质生活清减而集体主义至上的大时代淡出历史,狂热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社会价值观的建构,个人主义和物质至上的小时代就来临,《小时代》针对当下年轻人面临的物质和情感的双重焦虑而生,是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奢华美梦,醒来却没有实现的路径,因此文本内外注定是个虚无的悲剧。
(四)笛安——乡愁之城
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种人情氛围和情感模式。笛安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主办的“亚洲青少年流行文化”研讨会上说过:“我认为‘都市文学’指的并不全是描写工业化或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不全是描写大城市里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可能诞生于都市中的情感模式,用我自己更为文艺腔的表达,所谓的都市写作,一定要有的,是对于都市的乡愁。”笛安最畅销的“龙城三部曲”就被她设置在一个冬天有冰冷的空气,清晨有藏蓝的天空,有着灰色、肃静的深秋,春天刮着沙尘暴,夏天可以制造白色云彩的北方工业城市——龙城。
笛安是山西太原人,“遗风因唐远,积德本周深。王气缠西北,真人虎视偏”,这首描写太原的古诗,名字就叫《龙城》,这也许是笛安对乡愁的表达。发生在龙城的郑家人的故事,围绕着家族的恩恩怨怨,男女的爱恨情仇,血缘与亲情,欲望和救赎展开,与幸福有关却与圆满无缘。笛安围绕西决、东霓和南音的成长经历来叙述人生种种,讨论人性和心灵,谈论爱和悲悯。通过展示这“乡愁之城”里人们的悲欢无常,去触摸生命的终极命题——命运与无奈,这是笛安对当今时代年轻人生命的思考。“80后”甚至“90后”一代的成长环境与其父辈有很大的不同,父辈的时代有城市却没有都市生活,更何谈回忆,像笛安这样的“80后”作家在他们的都市青春叙事文本中提供了一种当下年轻人熟悉的都市情感模式,可以让青少年读者回味、幻想,引起情感的共鸣。这也许就是笛安所说的乡愁之城。
李傻傻、张悦然、郭敬明、笛安等“80后”作家生活在城市中,他们以各种形式关注当下生活在“呼愁之城”中的年轻人,关注他们在都市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矛盾,关注年轻的漂泊者的生活状态,关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年轻的寻梦者的心理历程,关注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人文精神,都市中的情感和生命。构建当前的都市和个体在中国文学中的意象和关系,价值和意义等。尽管风格各异,但是这一个个独立的世界组成了“80后”作家群体笔下的中国“呼愁之城”组图,概括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一个时代的精神诉求。
三、城市青春叙事的局限与未来
“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叙事是对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生活状态和精神困惑的探索。城市青春文学对城市以及城乡过渡带的表现,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居住地的感情,体现了人与生存空间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品着力表现当下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对爱情的追寻和追寻不得的忧伤;由中国社会变迁、西方文化涌入带来的文化震惊与心灵失衡感带来的忧伤;无法实现理想生活,无法接近信仰、梦想的忧伤。无论是与大众市场结合紧密的郭敬明、笛安笔下的充满魅惑与乡愁的城市,亦或是游离于市场与主流文学边缘的李傻傻的笔下游荡在孤独城市中寻觅爱的人,“人与城”是“80后”城市青春文学的焦点。
小说是作者对生活表层经验的提炼与再创作,“80后”作家大多生活在城市中,感受着城市中的点点滴滴,强烈的倾诉欲望被市场催熟,正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一样,他们对城市生活经验的累积还没有达到故事的层面,所以故事多有明显的自恋倾向和虚构夸张色彩,他们极尽微弱之力维持故事开头那曾经的理想与信仰,面子是悲壮的,里子却是狼狈的。他们的故事贴着城市中年轻人的青春迷茫、叛逆等标签来满足大众尤其是青春期读者的情绪发泄与陌生化期待,书中充斥着时尚、欲望、隐私、性、嗜酷、教育体制批判、杀人、乱伦等刺激性体验,因为这些容易满足现代人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中积攒的压抑苦恼与无处排解的痛苦体验。也许很多人在看“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叙事文本时,都能体会到书中人物的感受和情绪,进而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而对其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不太关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生之路上,没有几个人能复制他们的经历,真正过书中的生活,这样作品是浮在生活表层,缺乏普世性的关怀,也使得他们在不断重复自己的某种青春情结中,有神经过敏与无病呻吟之嫌。叛逆与早熟是青春标签,苦难与伤害是反抗手段,健康正常生活的缺位容易导致矫情与造作,也容易引导年轻读者走向误区,这是绝大多数“80后”作家城市青春叙事的硬伤。
在他们的小说中最真实的部分就是作家渗透于其中的人生态度、生活经历与心理状态,“80后”作家想要在文本中表达自我,但实践表明个人真实的生活经验虽然能为创作提供方便的文学素材,但是也容易限制对生活材料的加工和再创造的可能性,尤其是对春树、张悦然这样的女性作家而言,没有节制的私人话语,出售个人成长经历或者沉浸在幻想与童话式色调的阴森氛围中,容易造成心理的自恋和叙事模式的重复,而市场化的文学生产机制也会利用受众的猎奇与偷窥心理为这种审美倾向推波助澜,从而降低了其文学发展品质。另外,一味地取悦消费者是不利于作家自身艺术水平的提高的,郭敬明曾说:“只要你以相同的姿态阅读,我们就能彼此安慰。”他们的小说发行动辄达数百万册,靠写作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让很多一辈子爬格子却还为生计发愁的作家们望洋兴叹。但是根据笔者通过实地和网络对大学生和高中生的阅读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读者是被大肆的宣传或者其华美的包装吸引,为了获得阅读快感以宣泄青春的情绪而阅读“80后”作家的作品,大多数人对其中的情节表示可以理解,但不认同,大多数人不会二次阅读。
在城市化的加速与改革中,城乡的界限开始模糊,“呼愁之城”的游荡、残酷、魅惑、乡愁能否持久存在?试想这一批“80后”作家逐渐步入中年,失去了青春话语,他们将如何转型,他们的创作力还有什么可以开发的空间?这些都值得当下大部分“80后”作家和普罗大众思考。因此,“80后”作家应该思考自身的定位与追求目标,青春写作是他们崭露头角的开端,不应该长久地靠出卖青春话语为生,一味地沉溺于市场也无法在文学上走得更远;在金钱、名声的诱惑和大众媒体的包装追捧下,“80后”作家更应该保持对文学,对社会的赤子之心,增强责任感,引导当下年轻人形成正确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另外来自主流文坛的相互理解和必要交流的缺席,使得“80后”作家除去在文学市场上的闯荡甚至自生自灭之外,一时还没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出路,这值得引起重视。“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叙事在广大学生群体中备受追捧的现象,根源还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的今天,更应该促进家庭和睦,改革学校教育,以缓解当下年轻人在情感与物质上的渴望和焦虑,同时改良社会文化氛围和市场出版机制方是引导和促进“80后”文学健康发展的长久之策。
[1]张伯存,卢衍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57.
[2]郑婷.从“80后”写作看青年亚文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3]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57.
[4]张卓,张捷.明利场[J].人物,2013(7).
[5]雷环捷,朱路遥.《小时代》电影三部曲:奢侈品的想象与梦想的虚无[J].创作与评论,2014(8).
[责任编辑:何瑞芳]
“Worrying” Hurt——City Youth Narratives in “80 after” Writers’ Works
SUN Xiao1,GU Wei2
(1.P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Beijing Language&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2.School of Liberature, Zaozhuang College, Zaozhuang 277160, China)
The youth writings of “80 after” writers take city memory as writing resources. Promoted by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has changed the city appearance of China. Postmodernist culture and youth subculture, together with mass media and cultural industry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ifestyle and values of the “80 after” people and change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mechanism. The city youth writings of the “80 after” writers express their unique city appearances filling with their city “worrying” hurt and carrying with their pursuing for love and all their worrying such as; the worrying about the love they can not get: the worrying for the cultural shock and the spiritual imbalance caused by China’s social changes and western cultural invasion: the worrying about the ideal life that can not be realized: and the worrying about the belief and dreams that they can not be close to. In the city youth narration of the “80 after” writers, we can see many material details, but we can’t see their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ir cities and their catharsis and memories to their growth.
“80 after” writers;worrying city;city youth narration
2015-09-13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80后’作家的青春叙事研究”(311190102)
孙潇(1992-),女,山东淄博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中国古代文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1671-5977(2015)03-0097-05
I24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