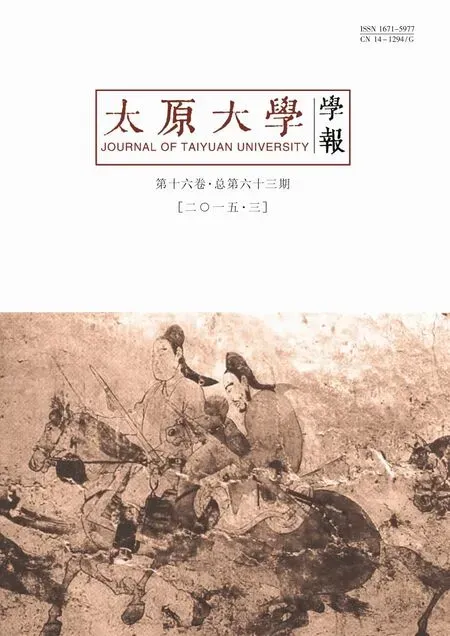清初东北流人诗的情感剖析与文化阐释
胡 新 华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清初东北流人诗的情感剖析与文化阐释
胡 新 华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清初东北流人在经受住身心的重创之后,他们顽强的生存下来。他们远在酷寒的东北,饱受思乡之苦,为了缓减悲痛,流人之间诗词互慰,他们因为共同的悲惨命运而建立了惺惺相惜的深情厚谊。流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们积极向上,重新审视生活,对人生有了全新的体悟,在流人的诗作中可以窥见他们的情感、精神面貌,同时这些诗作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清初;东北流人;文化流人;情感;文化阐释
张玉兴先生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中对“流人”的解释是被流放的人,而李兴盛先生在《东北流人史》中对“流人”下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义,他认为:“流人就是反抗封建统治或触犯封建刑律,而被统治者强制迁徙至边远之地以服劳役,借以专政或实边,从而成为该地的一种客籍居民之人。”[1]3笔者在这里分析的“流人”则主要指“文化流人”。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领汉族的封建时代,女真族的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各部落之后,建立了后金,定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东北地区是满族统治者的大后方和根据地,他们在江山稳固之后,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发展大后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因此,一大批来自江南的文士因为各种罪名被发配到东北这片蛮荒之地。
一、清初东北流人的概况
清初流人数目之多让我们触目惊心,在“一人犯法,诛灭九族”的封建社会中,流人往往不是一个人被遣戍,而是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人。如清初左懋泰遣戍辽东,全家上百人因此获罪被遣。顺治十六年(1659)遣戍到宁古塔的钱威说:“塞外流人,不啻数千。”学者王渊在为杨宾《柳边纪略》作序时道:“数十年庶士遣此土者,殆不可以数计。”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被遣戍流人的数目之大。清初流人遣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分析文化流人被遣的原因。
首先,清朝满族统治者领导汉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使得大部分汉族人民不满,因此“反清复明”的思想一直充斥在汉族人民的心中,这就不乏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反清复明奔走,企图复明的志士们终归失败,有的领导者壮烈牺牲、为国殉难,而大多数参与者则因斗争失败被流放东北。如清初的通海案牵涉到大批流人,最著名的是杨越、祁班孙等人。虽然有的人并没有亲自参加起义或斗争,可是他们在诗文中流露出些许对满清统治的不满情绪,也因此获罪遣戍,这就是文字狱对文人的打击,如僧人函可、郝浴等。
其次,因科场案被遣戍的流人,如顺治十四年(1657)的科场案是清廷借以打击汉族地主阶级势力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行动。谢国桢在《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详列了这次科场案,“四月辛卯,谕刑部等衙门,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旸、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2]16清廷江山初定,北方基本已处于满族统治之下,而南方各种明朝的旧势力依然活跃,为了打击南方汉族旧势力,清廷通过科举制造事端就显得名正言顺多了。
再次,因《逃人法》和抗粮案、哭庙案牵涉而落罪的流人。抗粮案、奏销案和哭庙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因这些案件连累的流人上百,最后被遣戍到尚阳堡、宁古塔等地。
最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充满复杂激烈的派系之争、朋党之争,失势的一方被遣戍到东北,陈名夏和陈之遴可以说是这些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二、东北流人诗的情感剖析
这些因各种罪名被遣戍到东北的文化流人,个人身份出现了天壤之别,他们的心理状态百般复杂,绝不是单一平面化的,获罪之前他们是上层士大夫的佼佼者,生活安逸,有着文化人特有的孤傲和清高,而遭到此番打击之后,当他们或只身或举家遣戍到东北后,心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一)东北流人的生存境遇
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流人在遭遇不幸之前大多生活优越,而当遭受流放的劫难后他们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流人在流放途中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沿途荆棘丛生,沟壑坎坷。方孝标在《十八岭》前面的一段小序中有过具体的描写:“峻岭相连,尽日在深溪乱石间,俗称为十八岭,其实不止十八也。岭麓皆插大河中,两岭相接处必有浅濑界之。濑尽处则皆淖泥,土人译为虾塘,深凡数十尺,浅亦数尺。徒车皆不能渡,必缚薪或为桥、或布土乃可过。”[3]322这段文字记录了辽东地区的艰难险阻。函可在《闻同难民为虎所食》写道:“何须今日方怜若,一度边关即鬼门。身死不烦蝇作吊,年凶唯见虎加飨。只愁老瘦重遭斥,但免饥寒亦感恩!白雪一杯魂未远,料应笑我骨犹存。”[3]25函可的这首诗将叙述和议论紧密结合,“一度边关即鬼门”更是道破了边地的恶劣环境,流人们不仅仅面对饥寒,还要提防老虎等各种野生动物,其困苦难以想象。
(二)流人诗作中复杂多样的情感呈现
“文学即是人学”,在历代文学作品之中,爱、恨、愁、苦、怨、怒等情感体验冲撞着文人的心灵。在东北流人的诗作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愁和怨,他们自身的悲惨遭遇酿就了每个人心中绵延不绝的悲愁哀怨。当然也有一些流人在归期无望后安于现状,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教育、经济、军事建设,在一些作品中也流露出昂扬向上的情怀。
1.思乡的悲苦心情
东北地寒偏远,流人被流戍在那里,远离故土,他们饱受思乡之苦。他们思念家乡的景物与亲友。来自身体上的伤害一般随着时间推移可以减轻,而思念家乡亲人这种精神性折磨则是与日俱增。函可诗《偶感》云:“迁客亦为感,况兼秋有声。天风吹木叶,一夜满边城。是处皆肠断,无时免泪零。不知何事切,未必尽乡情。”[3]13秋季落叶飘零终有根,这就使他的思乡情愁更浓,东北边地的酷寒和家乡的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肝肠寸断,泪如雨下。另一首《立秋后一日孤雁忽飞去四首》(之四)“上林非夙昔,系帛亦徒劳。尔去从漂泊,余心转郁陶。空庭添寂寂,中泽总嗷嗷。何日清江海,孤云许共翱。”在秋天看到大雁南飞,诗人也会联想到自己流放异地,不能像大雁一样自由飞翔,有去有归,虽然知道没有回归之可能,但仍然盼望终有一日会世事大变获得自由。左懋泰《读丽中师自粤寄梅花诗》云:“美人入梦多迟暮,孤客招魂半野烟。无待笛声吹彻处,天山雪落已凄然。”自己的意中人因为自己流放而美人迟暮,笛声不再悠扬,更引起了自己的无限思乡之愁。吴兆骞在诗中也写道:“年年此夕遐荒外,肠断穿针故国楼。”在流人留下的诗作中他们都有着浓郁的思乡之情,地处冰天雪地中更加怀念江南的秀丽景色。有的流人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了家乡,而大多数流人则客死他乡。
2.流人与友人的深情厚谊
“世事文章贱,交情患难真。”流人因为有着共同的不幸遭遇而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这份友情真诚感人、弥足珍贵。古人重情谊,虽然当时交通不便,很多家乡的朋友也翻山越岭千里迢迢来戍所看望友人。李呈祥在诗中曾写过“矫首云霄兄弟少,埋身冰壑友朋多。”他在被流放后,还有友人从山东来看望他,其诗《高含章至》坦言:“破帽冲寒自里门,天涯握手月黄昏。可怜潦倒同学子,万里相寻咬菜根。”[3]76同学高含章听闻李呈祥被流放后,独自一人前去探望,李呈祥十分感动,赋诗表达久别之后见到友人的欣慰以及因生活困窘而不能招待友人内心羞愧复杂的情感。函可称赞他“有至性”,李呈祥在函可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这在他的诗《问剩师病》中表露出来,“边城雪后冷无端,蹇卫深渐滑路难。地结冻云三日卧,天余布衲一僧寒。椒汤药裹时须进,粪火泥炉夜莫残。翘首祗园方丈里,铃声应已报平安”。[3]71由此可知他对朋友关怀备至,嘱咐他按时吃药喝汤,卧床休息三日,不要熄灭炉火,点点滴滴的关怀看出流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让他们的心灵贴得更近。
吴兆骞在去戍所的路上得到过陈之遴的帮助,获得了车马衣物,此后书信不断。他在《寄怀陈子长》中写道:“雪霁山城月色新,天涯怜汝倍沾巾。家残已恨无归日,道远空怜梦故人。尺素三秋凭去雁,短衣十月叹悬鹑。伤心同是他乡客,偏是相思隔塞尘。”[3]232诗中感情真挚,对陈子长家残难归的处境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同时也抒发了他乡戍羁的深沉感慨。吴兆骞与方拱乾在狱中相识,共同流放宁古塔,又在当地共同生活两年多。“每啜糜之暇,辄与龙眠诸君子商榷图史,酬唱诗歌。”[4]271共同的遭遇让他们惺惺相惜,在彼此诗词唱和中得以排忧解闷。方拱乾作诗《问汉槎病》“倾城争问病,病小见情深。故国无家信,天涯独子心。凭谁堪七发,好我莫孤吟。沥沥檐前雨,如闻枕上音。”[3]306平常诗作中可见相交相惜,真可谓“患难见真情”。方拱乾在宁古塔三年时期写有诗歌千余首,与吴兆骞酬唱应答之作就有一百四十多首,可见双方在流放地交往唱和频繁,正是这种文化流人之间的相互唱和交流温暖了他们彼此枯寒的心灵,使得他们能在精神上保持愉悦。人生在任何时刻都需要知己,共同的命运将这些失意的文化流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互相关怀、互相鼓励,从中获得摆脱灵魂困境的全新力量。
3.互敬互助,与当地人民友好往来
流人在适应环境之后慢慢融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放弃了之前书生模样,自给自足,亲自从事农业活动,并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李呈祥在《除日》中写道:“万丈寒冰皎绝尘,雪中松柏用精神。残躯那得闲无事,自写春联送四邻。”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流人和当地人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经常在一起聊天、饮酒,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陈之遴在《饮郊外》中写道:“野人今渐狎,杯酌屡逢迎。塞酒兼甘酢,村庖半熟生。日长余暮色,波暖动春声。共卜西成好,清明永昼晴。”[3]120陈之遴在流放之前位居高官,像他这样的人也开始了田园生活,和农人饮酒话家常。当地的土人和流人相处融洽,互相帮助,流人大多是读书人,他们缺乏一些基本的生产技能,这时候,当地人民热心帮助,季开生诗云:“每愧野人勤给米,久劳邻媪代炊薪。”
4.积极向上,苦中作乐的超脱情怀
诗僧函可在流放盛京期间,组织了冰天诗社,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他经历坎坷,命运凄惨,虽身处绝塞荒域,却绝不自暴自弃而消沉,他不断追求,在苦难的环境中坚持自己忠贞不二的爱国操守,他的精神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的人格典范,他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也点燃了那些流人冰冷枯寂的心灵。他在《解嘲》一诗中写道:“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3]23这首诗以李白自喻,李白因为被贬谪而有了夜郎题诗,自己因为有流放盛京的经历而写出更多动人的诗篇。在《辛卯生日》这首诗中他表达自己的壮志豪情和一片爱国赤情。“裂裾欲续西征记,破帽长歌正气篇。自笑出家余习在,人间斯道只如线。”他不屈不挠养人间浩然之气,不与世同流合污。在《寄江南诸同舍四首》(其四)中写有“无罪还应出塞来,石头旧社长蒿莱。会稽禹穴饶探遍,不到天山眼不开”[3]30这种豪迈旷达的情怀正是函可人格精神的写照。
郝浴因得罪平西王吴三桂被贬谪到铁岭,尽管在这里生活艰苦,可是他不畏困难,筹款兴建银冈书院,一面聚徒讲学,一面研究学问,为当地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银园》一诗中写道:“遮莫空栏落雨频,几枝绿树压清晨。争知白屋还归我,是此青山不负人。燕出疏帘花欲笑,客投双鲤墨犹新。银园敢谓同西洛,实有书随不藉身。”[3]97这首诗说自己虽被流放铁岭这严寒偏远之地,但幸能筹建银园,教书授课,做一介书生,这也算是“青山不负人”了,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忍辱负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5. 在逆境中的抗争和反省
流人们身处东北恶劣的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不屈不挠,在逆境中求生存,慢慢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开始新的生活,并认为“殊方风俗渐相安”,高唱“莫言穷塞苦,随俗即吾乡”。有一些流人在诗歌中吐露心声,对科举入仕带来的灾难深刻反省。丁澎因科场案而被流徙尚阳堡,在戍所期间,他反省几十年的官场生涯,终于悟透其中的风险,《东冈》一诗叙写流放生活平和宁静,和他结交的是村夫野老,少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灌木阴已静,诛茅远市城。榆烟消鹿塞,谷雨换禽声。客久如无岁,山多不辨名。杖黎随野老,竟日少逢迎”。[3]182陈之遴在《冬日书怀同汉槎作》中也幡然悔悟道:“名污轻性命,身废怨诗书。”[3]130其实因科场案、文字狱流放的文人数不胜数,丁澎、季开生、李呈祥、孙旸、诸豫、方拱乾等等,他们的内心都是悔恨交织,充满对贪恋功名的悔悟。
6. 流人的爱国情怀
流人遭受流放之苦,可是他们怀着热爱之情歌咏祖国的大好河山。虽然受到统治者不公平的待遇,自己的命运也生死未卜,依然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在沙俄侵略我国东北边疆的时候与军民同仇敌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很多流人在诗作中热情歌颂抗敌将领,最为突出的是吴兆骞,他以高昂的激情全面地讴歌了保家卫国的抗俄斗争。“破羌流尽征人血,好进温貂报国恩。”、“羁戍自关军国计,岂将筋力怨长征”、“军容直历无雷地,战气初消盛雪天。”这些豪迈之词都可以看出流人的满腔热血,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当祖国面临外敌入侵之际,他们积极响应,彰显了一种大我情怀。
三、东北流人诗的文化阐释
李兴盛先生在《艰难创业话流人》自序中写道:“世间才子半流人,业绩每于谪后闻。”以罪被发遣到东北的流人文士,尤其是因科场案和文字狱而遭流放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往往是博学多才的饱学之士,虽然遭受巨大的不幸,他们并不消沉,仍勤于治学,攻读不息。他们的诗作中蕴藏着深广的文化内涵。
(一)东北流人诗中的儒家文化阐释
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忠”“义”“孝”,东北文化流人大多接受了儒家的诗教礼仪,他们恪守儒家的思想规范,在他们的诗作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和“外求不得反求诸己”观念。
函可在《冰天诗社》序言中开宗明义阐明冰天诗社的宗旨,“尽东南西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既不费远公蓄酒,亦岂容灵云杂心,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续东林之盛事”[5]598,函可所倡导的“节义文章”的宗旨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忠孝观念。冰天诗社的成员大多是明朝故老,远在边疆,将诗社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们忠贞不二,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古来报国岁身完,憔悴孤吟见泪漙。未到投荒肝已裂,只今留息骨先寒。”诗人悔恨无以报国,如今流落边荒之地,仍不改故国之志。“百炼曾经骨愈坚,孤身迢递出长关。死生既了人伦系,忠义仍凭祖道传。”[5]599诗人们远戍边荒,历经磨难,但“人伦”“忠义”所赋予的道德精神,始终是不可磨灭的。“骨头欲比岩岩石,意气仍留浩浩波。”这些既是流人人格精神的写照,又给其苦难生活注入了昂扬向上的生命力量。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外求不得反求诸身”的观念,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积极入仕道路行不通时,他们开始反观自省。孙旸在《同陆子渊新筑同子长赋》中写道:“柴门斜背凤城开,松菊花栏取次栽。一缕碧泉当槛出,千峰翠霭入窗来。栖迟岁月凭棋局,潦倒生涯付酒杯。三径祗堪求仲过,莫教车马破苍苔。”[3]152这首诗中多了一种归隐自适、怡然自乐的情怀,处在东北苦寒之地,诗人能有这样的情怀也是儒家文化中“修身养性”的一种外在表现。陈志纪的《塞外岁暮枕上作》“普天皆王土,万里犹比邻。狂言不加诛,蒙恩为戍民”,诗人忏悔自己,因为自己的罪过而遭流放,深感有愧于朝廷的信任,并感激皇帝的不杀之恩。这种感激皇帝的不杀之恩在很多流人作品中都有表现。陈梦雷的“读书课业儒生事,牛马行藏圣主恩”,孙旸的“自惭人物非东观,微末何缘系圣情。”这些都是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表现。
(二)东北流人诗中的道家文化阐释
在东北文化流人的诗作中,他们有很多人表现出一种在逆境中达观自适的态度,这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神内涵。
函可愤世嫉俗,执着追求,不同流俗,不肯苟合的个性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为了坚持自己的操守,他宁死不屈,这点和庄子如出一辙。在《寄龚韩二子》中他写道:“平生无半面,祸患每过寻。乱肆两枯骨,枯桐一片心。道同顽处合,诗向酒中深。后夜相思处,开门月满林。”[3]19在这首诗中他表现出对儒家某种规范、秩序的怀疑,“道同顽处合,诗向酒中深。”体现了道家不苟流俗,遗世独立的操守。函可多次提及生死,如《即事十首》(之十)云:“身死亦足悲,身辱亦足耻。与其辱以生,毋宁饥以死。”[3]28这首诗显示出诗人面对死亡道家式的旷达和超脱,他对生死淡然处之,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和道家的生死观相结合,从而超越了生死,真正做到了道家的虚静。
在流人的诗作中同时也体现了道家安然自适、超然物外的精神思想。李呈祥《又寄陈明府》中写道:“荒城禅舍晓开衙,古树新巢抱乳鸦。乍理琴弦闻鼓吹,初封井屋见桑麻。”这分明就是陶渊明笔下的理想世界,虽然地处荒原,诗人在内心把它假想成一片理想的生存之地,并在尾联道出:“倘许荷锄分半亩,愿随鸡犬傍山车。”在这片蛮荒之地中,他们用道家的恬适自然的态度对待生活,不怨天尤人,乐天知命,怡然自得。
(三)东北流人诗中的民俗文化阐释
流人大多都是出生南方,面对异乡风俗景物有着浓厚的好奇心,在这种好奇心的驱动下他们或登山临水,歌咏塞外的山水景物;或访问故老,收集佚闻;或凭吊古迹,考察旧俗,从而写出许多诗文和学术创作。他们的诗文记录了东北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山川物产等。方拱乾在《冰河行》歌颂了宁古塔地区满族拔河戏的习俗。“满风春望拔河戏,燕支影落冰痕睡。女子联翩男子观,倾营穿灯摇鞭至。日高人散客来迟,冰床如马凌冰驶。掌大雪花接雪堆,耳寒酒热中流醉。旅况无端听睹新,感时抚地为欢易。长安今夜月盈街,千门环印婵娟臂。”[3]294满族的习俗不同于汉族,除了拔河戏,还有捕鱼、打貂等民俗。方登峰的《迎神词》、《灯官曲 》、《打貂行》、《打鹰歌》、《糜子米》分别详尽地记录了迎神杀猪宴宾客的习俗、元宵节前后民间放灯活动的习俗、打貂、打鹰的活动。这些诗作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为民俗研究作了第一手的资料记载。
流人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威胁,最终在流放地大放异彩,可以说正是这种别样的人生经历丰富了他们的阅历,从而创作出流传千古的诗篇。
[1]李兴盛.东北流人史[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0.[2]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M].上海:开明书店,1948.
[3]张玉兴.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M].沈阳:辽沈书社,1988.
[4]吴兆骞.秋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清)函可.千山诗集.卷二十[C]//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4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岳林海]
Emotional Analysi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Northeast Immigrants Poems in Early Qing Dynasty
HU Xin-hua
(School of Literary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In early Qing Dynasty, northeast immigrants stubbornly survived from heavy physical and mental losses. This process interweaved their emotion of blood and tears. They were in cold northeast far away from home and suffered from homesickness. In order to help relieve grief, they comforted each other with poems. They established profound friendship because of the common tragic fate. In the hard environment, the immigrants were not depressed, but they tried actively upwards, rethought of their life, and got new comprehension to their life. In their poems, we can see their emotion and spirit status. Meanwhile, their poems have important cultural significance.
early Qing Dynasty; northeast immigrants; cultural immigrants; emoti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2015-07-12 作者简介: 胡新华(1987-),女,山西朔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1671-5977(2015)03-0069-05
I207.22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