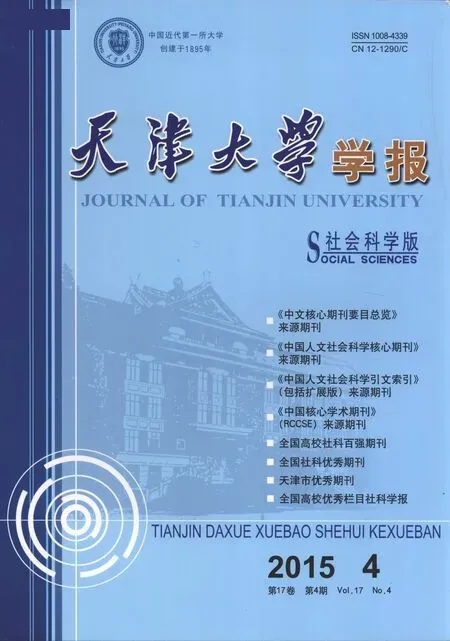再谈印刷汉字字形规范化问题
作者简介:段维彤(1972— ),女,副教授.
通讯作者:段维彤,hannah_duan@126.com.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2015)04-324-05
收稿日期: 2014-10-20.
基金项目:国家级特色专业第6批高等学校建设基金资助项目(TS11882).
孔子学院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从2014年开始,我国还将每年的9月27日指定为孔子学院日。
近年来,随着“汉语热”的升温,孔子学院得到快速发展壮大。但是,与社会快速发展相伴,孔子学院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在部分东道国,向往中国文化的高层人士往往更愿意直接去中国本土(而不是当地孔子学院)学习,造成孔子学院的传播影响力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一些中国企业与海外华人虽向往孔子学院,但没有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加入到孔子学院的建设中去 [1];由于与东道国缺乏深层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许多国家对孔子学院心存疑虑,甚至出现“文化侵略”的负面报道 [2]等。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是未来最好的老师,如果人们仔细研究海外中文教育传播机构的发展史,就可以找到解决上述问题与挑战的途径。人们常常把2004年11月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的孔子学院,视作中国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孔子学院。那么在“国家汉办”主导的孔子学院成立之前,海外是否存在相似机构呢?著名学者孟昭毅认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学院)堪称中国最早的孔子学院 [3]。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因为成立于1937年的中国学院是由当时中国政府出资,在海外建立的从事中文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的机构 ①。与中国学院的成就相比,目前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在文化融合、文化传播和在东道国影响力等方面都还有相当的差距,例如,印度的中国学院曾经得到过中印两国领袖人物和社会各界名流的高度重视,印度第一任总统、副总统以及教育部长,都曾先后来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参观。我国的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等众多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先后造访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建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学院在许多方面都能够成为孔子学院的榜样,值得孔子学院学习借鉴。虽然印度中国学院理应为孔子学院提供宝贵的启示与示范,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很少有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的研究将中国学院能够为孔子学院提供的启示分为4个方面,即师资与东道国合作机构的配置、学院目标与课程设置、文化学会的创办,并且逐一就这3个方面进行阐述与论证,指出了孔子学院存在的优势与劣势,为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师资与东道国合作机构的配置
如何配备师资与选择东道国合作机构,是决定一所海外教育机构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其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优秀师资是任何一所教育机构的最重要资产,由于海外教育机构身处异国他乡,需要承担中外文化交流的重任,因此对师资的要求就会更为严格;另一方面,海外教育机构在东道国需要有当地的合作伙伴,良好的当地合作机构能够使海外教育机构快速熟悉东道国情况,降低其在东道国作为“外来者”的风险与压力。印度中国学院不仅拥有谭云山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师资,并且有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作为合作机构,这些都为孔子学院提供了宝贵的示范作用。
印度文豪泰戈尔(1861—1941)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他在印度西孟加拉邦Santiniketan(可直译为圣地尼克坦或译为“和平乡”,也曾译为“寂乡”)创办了印度国际大学(梵文Visva-Bharati,其含义是“世界鸟巢”),他将国际大学视作“使世界聚会的鸟巢学府”,致力于世界文化融合。泰戈尔具有深厚的“中国情结” [4],因此一直以来向往中国文化,希望恢复并延续中印两大文明的历史交往。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充满热忱,他注重中国研究并提出设立中国学院的最初设想,并多次努力寻求中国学者到印度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与中文教学。1924年,他曾与梁启超等人洽谈派遣中国教师来印事宜,也曾力邀济南青年于道泉等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直到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时遇到谭云山,才终于为印度国际大学找到了最合适的中国教师。
谭云山(1898—1983)被后人誉为“现代玄奘”,于右任称他是“中印民族与中印文化之联络者 ②”。谭云山与泰戈尔关系十分密切,他是泰戈尔的学生、同事、崇拜者与好朋友。谭云山之所以被泰戈尔任用,成为中国学院的创始人,与谭云山对印度的向往和对泰戈尔的景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谭云山出国之前,他有机会结识了高僧太虚法师,后者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热情接待了泰戈尔并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交流过后,太虚法师到谭云山所在的船山学社开办了专门讲座 [5],这次讲座加深了谭云山对印度文化的理解与热爱。
谭云山能够协助泰戈尔创办中国学院,也与他的吃苦耐劳精神与社会活动能力有关。印度国际大学虽然在当时颇有声望、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但性质上仍属于“民办大学”,缺乏政府资助导致学校财政紧张,国际大学教师往往薪资极低,学校里许多印度著名学者、甚至一些欧洲来的学者生活十分清苦。因此,谭云山在国际大学最初三年未领工资,义务工作,由夫人在马来西亚教书资助生活。不仅如此,资金缺乏还导致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进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系列计划难以推行。为了解决印度国际大学的资金问题,谭云山曾经试图争取新加坡著名华商胡文虎的资助,但几经周折后没有成功。但是谭云山并没有气馁,而继续在中印学会的平台下进行不懈的努力,终于筹建中国学院的计划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与资助,解决了建设中国学院的资金问题。
1937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终于正式落成。在成立庆典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因身体抱恙,派女儿英迪拉前往宣读他的祝词,其中说道:“我始终认为中国学院的成立,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们迄今未忘中印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关系,重新开创一条使两国人民更加接近的通道。” [6]印度“圣雄”甘地也对学院的建成表示鼓励并寄予厚望。
中国学院成立之后,很快就成为中印文化与中印学术交流的前沿阵地。谭云山邀请了许多著名印度学者住进中国学院,其中包括Gokhale (郭克雷)在1937—1938年间担任梵文兼藏文教授,Shastri(夏斯特利)在1938—1945年间担任研究部主任,Bagchi(师觉月)在1945—1947年间担任研究部主任,著名佛学家兼汉学家Bapat(巴帕提)在1945—1948年间担任教授。Bagchi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印度访问学者,回印度后就担任国际大学研究部主任,以及成为国立大学后的国际大学第一任校长。1956年,印度按照尼赫鲁总理的指示特地在德里大学建立佛学系,其第一、第二任系主任就是Bapat和Gokhale。中国学院的雄厚印度研究实力显而易见。中国学院的奖学金与住宿吸引了大批国际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其中包括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和学者金克木。
综上所述,在师资与东道国合作机构的配置方面,印度中国学院可以为孔子学院提供以下3点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政府可以采用资助海外原有中文教学研究机构的方式来组建孔子学院。经过10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中外合作机制,每一个孔子学院在东道国都有声誉良好的外国合作院校。如果孔子学院能够像印度中国学院一样,一方面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另一方面是在海外原有中文教学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的,则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孔子学院自然成为贯穿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纽带,降低在东道国引起反感的可能性,更有利于避免“文化侵略”的负面印象。
第二,选择东道国合作机构的标准,可以综合考虑其原有中文教学研究的基础、其在东道国的影响力、能否促进中国与东道国的友好关系等因素。目前,孔子学院已经拥有比较成功的外国合作院校筛选机制。如果孔子学院能够选择像印度国际大学这样的机构作为海外合作伙伴,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更好效果。
第三,在孔子学院中方师资配置问题上,孔子学院教师可以考虑以印度中国学院创办人谭云山为榜样。目前,孔子学院中方教师普遍精通外语和海外汉语教学,并受到了良好的培训。如果孔子学院能以谭云山为榜样,鼓励中方教师不仅熟知、热爱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语言,还要充分了解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交往历史,并且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与一定的社交能力,这样才有助于迅速融入东道国社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举例来说,如果是设立在拉丁美洲的孔子学院,中方师资最好能够了解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及印第安人文化与历史;如果是设立在非洲的孔子学院,其中方师资最好能够熟悉中非友好交往的历史。
二、学院目标与课程设置
任何一所教育机构都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目标是其所有工作的归宿与出发点。体现教育机构目标的一项核心工作就是课程设置。对于国家资助的海外教育机构而言,其目标应该是通过文化融合与文化交流来促进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课程设置必须要体现这一目标。
泰戈尔将国际大学视为“世界鸟巢”,其本意就是将国际大学的学校目标定位为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互相融合。与此相对应,中国学院以中印文化融合为学院目标,谭云山为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拟定的目标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为体现这一目标,中国学院课程设置的重要突破口就是梵文和佛学。
梵文是中国学院课程与研究的重心。梵文是印度的古代语言,但是由于古印度没有纸,佛经都是写在贝叶或树皮上,因此在印度本土较少有保存完好的梵文资料。中国由于有大量古代印度输入的佛经,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印度之外最大的梵文大国。从古至今,中国都有许多研究梵文的专家:在古代,中国拥有以法显、玄奘和义净为代表的著名梵文佛经翻译大师,一千多年来,由梵文翻译成中文的佛经累计近万卷,而这些佛经的梵文原本大部分却已失传;在现代,季羡林先生用10年的心血翻译了《罗摩衍那》史诗,获得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 [7],印度媒体将这意义特殊的颁奖形容为“‘莲花奖’首次跨越喜马拉雅山”。谭云山根据佛教在中国和印度的交流的状况,专门设计了一个“从中文和藏文的著作中重新找寻失去的梵文”的项目,并着手翻译中文与梵文著作 [8]。中国学院拥有丰富的佛学典藏,如宋版及清版《大藏经》等,成为进行佛学及梵文研究的圣地。
泰戈尔认为,佛学是中印自古以来文明交往的灵魂,希望中国学院对佛学研究予以重视,因此佛学在中国学院课程设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自汉代到明代中印主要的文化交流都与佛学有关,并且先后经历了由吸收到融合再到同化三个阶段。例如唐代玄奘则将中印佛学文化交流推向了高潮。他不仅将印度佛典译入中国,还将中国的典籍译成梵文传往印度,引领了中印文化的交汇与互动。佛学在中国经过同化,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佛学在中国的兴旺发展也为其在印度的复苏注入了新的活力 [9]。
作为中国的海外教学与文化传播机构,中国学院也同时开展了中文教育、大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例如,谭云山在他的重要著作《什么是中国教》中,向印度介绍了以孔子和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中国学院课程设置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其重要性低于佛学与梵文,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有深刻的用意:如果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定位于学院首要工作,必然有“文化输出”的嫌疑,达不到“文化融合”的学院目标。
在21世纪的今天,印度中国学院的课程设置注重与时俱进,课程设计上充分体现国际化与现代化。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加,中国学院的课程增加了经济交流、口语翻译等方面内容。自2010年起,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中国的云南大学开展了校际合作项目,云南大学派往中国学院对外汉语教师作为外教,同时接收来自中国学院的教师到云南大学进修。
综上所述,在学院目标与课程设置方面,印度中国学院可以为孔子学院提供以下3点重要启示。
第一,孔子学院的目标应该定位于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融合,通过文化交流来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孔子学院应该努力推广传播中华文化,但这项工作应该服从于文化融合的学院整体目标。如果单纯强调中华文化输出、忽视文化融合,则难以避免东道国会有“文化侵略”的错误印象。
第二,在课程设置上,孔子学院应该切实体现上述文化融合的学院目标,借鉴中国学院的成功经验,将课程安排与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挂钩,强调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尊重东道国的历史文化。
第三,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应该注重与时俱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课程中可以加入经济、贸易等内容,为东道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三、创办文化学会、吸引两国高层精英
与一般的教育机构不同,受到政府资助的海外教育机构肩负着文化融合与促进两国友好交往的目标,因此其工作范围不应只局限在课堂上、校园中。海外教育机构应该积极组织两国间的文化学会,并吸引两个国家有影响力的上层人士加入,为文化外交打好基础。一所海外教育机构能否成功组织两国间的文化学会,与本文第一部分“师资与东道国合作机构的配置”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作为文化学会的组织者,海外教育机构的骨干师资需要具有很强的社交、演讲、说服能力;另一方面,如果东道国合作机构在东道国有着良好的信誉与声望,那么文化学会的组织工作就会相对顺利。
在创办文化学会方面,中国学院堪称海外教育机构的典范。中国学院对中印两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印度国际大学校园,而是通过中印(印中)文化学会拓展到当时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许多领域。借助中印(印中)文化学会的平台,两国许多(包括国际领导人在内的)高层精英加入到中印交流的队伍中来,文化学会是中国学院影响力的重要延伸。可以说,中国学院与中印(印中)文化学会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一方面,如果没有泰戈尔和谭云山创办中国学院的计划,就不可能有中印(印中)文化学会的诞生;另一方面,恰恰是通过中印(印中)文化学会,创办中国学院的计划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同与资助,中国学院才能在1937年正式落成。
早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泰戈尔和中国友人就有成立中印文化学会的意向,但一直没有机会正式组建。谭云山来到印度国际大学之后,他受泰戈尔之托,分别与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和领导人沟通合作,分别在中国和印度Santiniketan设立了中印和印中文化学会,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1934年5月,常设于印度国际大学的印中学会宣布成立,泰戈尔任主席,尼赫鲁任名誉主席。1935年5月,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宣布成立,蔡元培担任理事会主席。由于谭云山的努力与泰戈尔的名望,中印(印中)文化学会吸引了两国在各个文化领域的精英人士,并得到两国高层人士的大力支持,为两国文化的沟通对话创造了更为自由的空间。中印学会成立后向印中学会捐赠共计十万多册图书,并筹集到下一步在国际大学创建中国学院的资金 [10]。
当时中国和印度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参与了中印(印中)文化学会: 1941年泰戈尔去世以后,尼赫鲁答应了谭云山的要求,成为印中学会的名誉主席,他还于1945年亲自到中国学院主持过印中学会的年会。印度独立之后,很多印中学会的会员都成为国家领导人或上层人士,其中包括:印度独立后印度临时政府总督Rajagopalachari(拉贾戈巴拉查理)、印度第一任总统Prasad(普拉萨德)、第二任总统Radhakrishnan(拉达克里希南)和第三任总统Husain(侯赛因),他们都是印中学会的印度普通会员。
中印(印中)文化学会很快成为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平台,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创建文化学会方面,中国学院是孔子学院最好的榜样,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为了达到文化融合、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目标,孔子学院的工作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与校园。孔子学院应当借鉴中国学院创办文化学会的举措,建立文化交流性质的组织机构,吸引我国及东道国的知名学者、高层精英加入,扩大孔子学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促进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要成功地创建文化学会,既需要谭云山这样的学院骨干师资的超强社交、演说能力,也需要东道国合作机构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四、结语
中国学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海外教育机构和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孔子学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本文将这些启示总结为以下3个方面:一是在师资与东道国合作机构的配置方面,国家汉办可以采用资助东道国具有良好声望的中文教学研究机构的方式来组建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教师应该熟知、热爱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语言,还要充分了解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交往历史;二是在学院目标与课程设置方面,孔子学院的目标应该定位于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融合,将课程设置与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挂钩,强调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尊重东道国的历史文化,并做到与时俱进;三是在创办文化学会、吸引两国高层精英方面,孔子学院的工作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与校园。孔子学院应当借鉴中国学院创办文化学会的举措,建立文化交流性质的组织机构,吸引我国及东道国的知名学者、高层精英加入,扩大孔子学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中国学院的成功,也有其特殊性与不可复制性,因此孔子学院也不能简单地全盘照搬中国学院的经验。中国学院与孔子学院相比,有三个显著的不同之处:第一,国际形势的差异。中国学院创建于1937年,当时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两个国家迫切需要对方的支持,恢复自古以来的文化交往。此外,由于印度尚未独立,为了不激怒英国殖民当局,中印两国都乐于通过中国学院和中印学会开展文化外交。今天的孔子学院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独特的国际环境。第二,人力资源与法律环境的差异。谭云山作为中国学院的创始人和主要管理者,3年未领工资,由夫人资助生活,他不图名利的奉献精神可见一斑。由于时代的不同,当今的孔子学院不可能不发工资,这于情于法都不可行。其实,象谭云山这样淡泊名利的教师在当时的印度国际大学并非孤例,许多学者甘愿放弃物质享受、专心学术。而今天的孔子学院不可能不为教师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东道国合作机构的差异。中国学院的印方发起人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非白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对印度当时的影响力仅次于圣雄甘地,在世界上也享有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目前在外方师资引进方面,孔子学院很难吸引到如此有影响力的精英人物加入。
尽管中国学院有这些特殊性,它仍是孔子学院最好的学习、借鉴的对象,因为中国学院与孔子学院一样,都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在海外建立的,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与海外中文教学的机构,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孔子学院。除此之外,与中国学院相比,孔子学院也有着众多的优势:中国学院创建于1937年,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则有了极大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改善,中国学生的外语水平、国际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全世界的信息化水平今非昔比……。中国学院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前瞻性的中印文化传播平台,为孔子学院树立起伟岸的榜样。在新时代,孔子学院应站在中国学院这一“巨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力求取得长足的发展。
孔子学院今后要朝着特色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努力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平台,真正实现谭云山为中国学院拟定的“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的目标,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贡献力量。
注 释:
①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部分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存在着一些中文教学与研究机构,但这些机构往往属于民间性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资助。例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设立的“中国文化讲座”与中国图书馆,1928年在德国建立的孔子学院等。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由中国政府资助,与一般的海外中文教学研究机构有根本区别。
②1931年4月27日,谭云山在印度巴多利拜会甘地,回国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印度周游记》。该书由蔡元培题写书名,于右任题词“中华民族与中印文化之联络者”,于193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