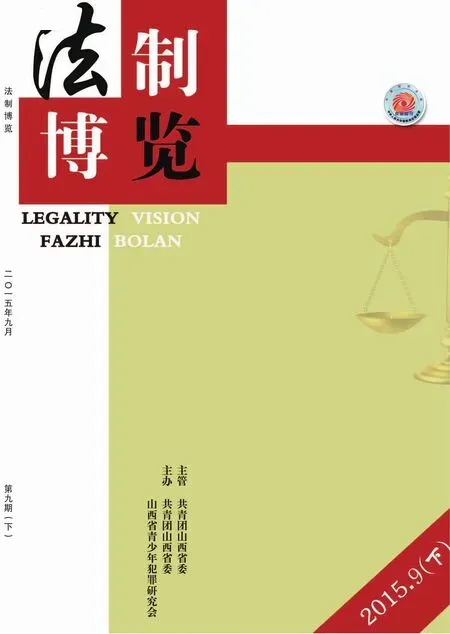简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吴静华 程轶寒
1.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福建 泉州 362000;
2.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福建 泉州 362000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在刑法原第338条中争议不大,基本都认定为过失,然《刑法修正案(八)》的重大修改,删除了原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等表征过失的情节,变更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加之将罪名由原来的“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至少在外观上已经褪去“过失”的色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解释》),其中对该罪具体情形的解读,进一步导致其罪过形式争议的升温。
一、关于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争议
对于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的争议,主要有过失说、混合罪过说和故意说等学说。
(一)过失说
过失说为多数学者所支持。①主要三点理由:其一,该罪前身为“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从文义解释的角度,“事故”是指“意外的变故或灾祸”,表征了其不希望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与过失犯罪的特点相符;②其二,该罪的刑罚最高仅为七年有期徒刑,与其他过失犯罪的处罚幅度相符,若该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则罪刑不相协调。③其三,根据立法意图,《刑法修正案(八)》完善该罪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环境和人身、财产的保护,加大对污染环境行为的处罚力度,为此必须打击过失犯罪。其四,对于其他学者对过失说可能导致处罚漏洞的质疑,支持的学者认为,故意的污染环境行为可以运用当然解释的方法,将其纳入污染环境罪的规制范围,这样的做法,就可以规避处罚漏洞。
(二)混合罪过说
混合罪过说,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其理由在于《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原意是“使经过修正后的环境污染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实际上,《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解释》对污染环境的主观状态语焉不详,也正是基于此观点,欲将故意和过失的污染环境行为纳入其中。
(三)故意罪过说
故意罪过说也不乏支持者,张明楷教授认为:“本罪原本为过失犯罪,但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本罪的责任形式应为故意。”④实际上这种观点能够在一系列的法理和条文中找到合适的依据,也正是本文所持的观点。
二、关于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争议观点的评析
(一)污染环境罪过失说的缺陷
1.罪状不符合过失犯罪的惯常表述
过失犯罪的表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条文中明确地以“过失”等用词表明,另一种是使用具备过失色彩的用词,例如“事故”“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等用词来体现过失的心态。《刑法修正案(八)》只使用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的,并弃用过失色彩罪名的“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使得该罪的过失色彩消失殆尽。这就使得“过失说”的文义解释的理由不再具有法条依据。
2.导致无法处理共同犯罪的漏洞
采用过失说,而没有在刑法中另行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罪,将导致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既不能用污染环境罪来规制,同时又没有专门的故意污染环境罪来处罚该行为,导致无法处理共同犯罪的漏洞。这将使得《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解释》第7条成为违法,“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二)污染环境罪混合罪过的缺陷
1.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只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并没有规定混合罪过的罪过形式。在罪过形式上,刑法只明文确立了故意与过失两种心态,混合罪过有违罪行法定原则。根据刑法第15条,“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据此,如果不是明文规定为过失犯罪,那么就是故意犯罪,不存在既是故意犯罪,又是过失犯罪的可能。司法解释仅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确立了一个罪名,不仅从条文中无法区分故意和过失两种不同的行为,也无法从现行刑法的实际为其找到相似的立法实例作支撑,因此,混合罪过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2.立法原意的理由,在方法论上存在疑问
立法原意是立法集体的意思,是立足于立法时对过往案件经验的总结、对将来案件可能发生情况的设想而形成的集体意思。立法原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过度强调要遵循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也不利于刑法的不断发展完善。⑤对刑法,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客观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该罪罪名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而且删去了表明该罪主观方面为过失的“造成重大污染环境事故”和表明结果要件的“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如果做立法原意的推理,也只能得出已经不再是过失犯罪的结论,并不能得出立法原意是要使其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
此外,立法区分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是因为不同的罪过形式反映的主观恶性、受到刑法否定性评价和谴责程度不同,针对过失心态的非难可能性明显小于故意。如果将一个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解释为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这实质上就消除了罪过形式相区分的意义,不符合罪行法定的原则;而故意说则能够成功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三、污染环境罪故意说之证成
(一)在文义解释上污染环境罪属于故意的犯罪
刑法第15条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说明,我国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只有当“法律”对过失犯罪行为的处罚有“规定”时,才有需要对该过失行为进行刑事处罚。“法律有规定”是指,包括在条文中明确地以“过失”等用词表明,或者通过条文的逻辑意思可推知主观为过失的情况。⑥“过失”、“事故”、“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等用词被用于体现过失的心态。后者虽然没有明显用词标志,但是可以通过前后文的逻辑推知其属于过失犯罪。⑦
但“污染环境罪”的罪状中并无表明过失的要件,而且从主观心态指向的客体——危害结果来看,“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也不能排除主观方面故意心态的成立。⑧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将该罪解释为故意犯罪不会超出法条的文义,也符合预测可能性和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
(二)故意说符合审判实务的实际
我国刑法中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针对的都是“危害社会的后果”而言。污染环境罪的“严重污染环境”,是因为所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对象是“有害的”物质,且该罪所涉及的物质都被收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如《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或者属于典型的铅、汞、镉等重金属。作为相关行业的从事者,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对其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行为所会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必定有所认识。一些实务案例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即犯罪行为都共有某些特点——多次排放、长期排放、排放量巨大,这些特点都印证了行为人都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存在认识,且对其行为可能会造成“污染环境”的结果显然存在至少是放任的心理状态。所以从司法实际的维度来看,应采用故意说。
(三)故意说是扩大处罚,减少漏洞的需要
故意说可以扩大处罚范围并且减少处罚漏洞,加大对环境权益的保护力度,回应民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如此,在有狭义共犯的情况下,仅实行教唆、帮助行为的犯罪人将无法作为单独的过失犯处罚,不利于保护环境权益,但如果将本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为故意,共同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当然可以认定为共同犯罪,到达保护法益的目的。
[ 注 释 ]
①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77.
②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三版)[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567.
③冯军,李永伟.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6.
④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95.
⑤肖中华.刑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J].法学评论,2006(5).
⑥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7.
⑦杨宁,黎宏.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J].人民检察,2013(11).
⑧陈庆,孙力.“有关污染环境罪的法律思考——兼论<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的修改”[J].理论探索,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