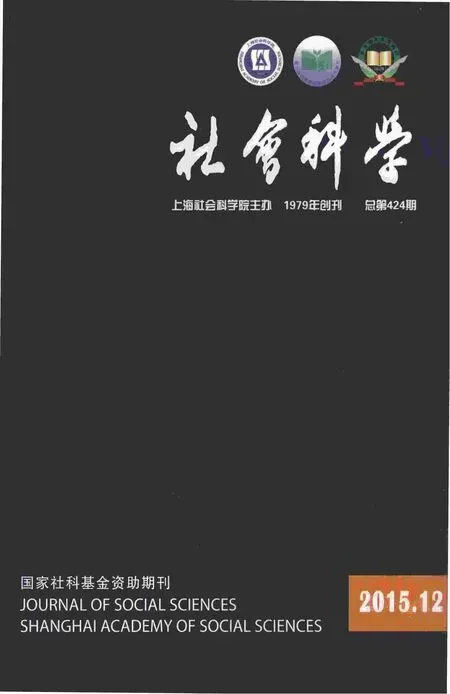伍非百的先秦名学研究与新名学的可能性
晋荣东
中国古代曾出现过一个围绕“名”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的广泛论说与持续争辩。如果用“名学”来指称这一论说与争辩,举凡先秦以降直至中国近代以前有关名实、名分、正名、名言、形名、名理、名法、名辩、名守、刑名、名教诸论题的学问,均可纳入名学的范围。从总体上看,近现代名学研究以“名学逻辑化”为主导方法,视名学为中国本土逻辑。不过进入1990年代,这一进路开始受到广泛质疑,学者们纷纷撰文对“名学逻辑化”展开批判反思,以期有助于名学研究的深化。在此背景下,伍非百的先秦名学研究无疑是一项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1916年,伍氏率先将“名辩”一词引入先秦名学研究,并在1920年代对名辩之学的内容及其组成进行了明确论述。在1949年完成、1962年基本改定的《中国古名家言》中,他把研究视野从先秦名辩扩展至整个先秦形名之学,并根据论“名”之要旨的不同,把后者进一步区分为形名六派。相较于近代以来那种以“名学逻辑化”为主导方法的旧名学研究,伍非百对名辩之学乃至整个形名之学的理解可以说为当代新名学的开拓提供了可能。
一、“名辩”的引入与使用
名辩是中国古代论“名”的一项重要内容。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达到高潮。秦汉以降,对名辩的讨论虽不复昔日之盛,但并未亡绝。随着诸子学在明末清初的兴起,有清一代陆续出现了不少对于先秦名辩著作的整理,并在晚清开启了对名辩的义理诠释。
从名实关系看,名辩之实早在先秦即已存在,但“名辩”一词何时出现?又在何时被引入名学研究?①详见晋荣东《e-考据与中国近代逻辑史疑难考辩》,《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117—119页。此文发表后,我发现顾有信(Joachim Kurtz)主张“名辩”和“名辩学”最早可追溯到1936年杜守素(即杜国庠)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秦诸子思想》,参见Joachim Kurtz,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Logic,Koninklijke Brill NV,2011,pp.354-355.不过,此说不确。杜氏此书实由生活书店于民国35年(1946年)9 月初版,其中第80—114页为第九章“名辩”;次年6 月由生活书店再版。显然,顾有信不仅弄错了出版社,而且把再版本误认为初版本,更为严重的是把再版时间“民国36年”误认为是公元“1936年”。根据我的考证,章太炎很可能是使用“名辩”这一名词的第一人,但率先将其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引入学术界的则是伍非百。②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在1916年为《墨辩解诂》撰写的《再叙》中,他指出:“近世德清俞樾、湘潭王闿运、瑞安孙诒让,并治此书(指《墨经》——引者注),瑞安实集其成。然数子校勘虽勤,章句间误。且不悉名辩学术,诠释多儒者义,颇琐碎,不类名家者言。”③伍非百:《再叙》,《墨辩解诂》,中国大学晨光社1923年版,第2、1、9页。这段论述要点有二:第一,俞、王、孙等人不熟悉名辩学术,往往立足儒家学说来诠释《墨经》,颇为琐碎,不得要领;第二,名辩学术是阐明《墨经》义理乃至古名家言之本质的钥匙。
关于《墨经》及古名家言,伍非百指出:
此《经》系名家言,世为别墨诵习。秦汉学者,病名学艰深难读,篇籍颇多散亡。唯此《经》与《墨子》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周秦文学复兴,诸子之学,间有讨论。而欧洲逻辑、印度因明,蔚然列为专科。中土名籍,赖有此经。发挥光大,责在后学。……以复兴中夏旧有名学一派。④伍非百:《再叙》,《墨辩解诂》,中国大学晨光社1923年版,第2、1、9页。
伍氏这一论说值得注意:前文说不少学者因不熟悉名辩学术而在注解《墨经》时不得要领,故名辩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古名家言的本质;此处又说古名家言之衰微在于“名学艰深难读”,而研究《墨经》有助于复兴旧有名学。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名辩学术与旧有名学的关系,进一步的追问则牵涉如何理解“旧有名学”中的“名学”一词的含义。
“名辩”一词多次出现在《墨辩解诂》的目录与正文之中。按伍氏之见,“战国治名辩者数家,庄墨荀均识此义(指‘知识’的定义——引者注)”⑤伍非百:《再叙》,《墨辩解诂》,中国大学晨光社1923年版,第2、1、9页。,即对名辩的论说并非仅有墨家为之,战国时期至少有儒、墨、道等学派卷入其中。在论及如何补订和解释《墨经》脱误的专门名词时,伍非百提出“以同时诸子关于‘名辩学’所下之界说为标准”⑥伍非百:《墨辩释例》,《学艺杂志》1922年第四卷第3 号,第2页。,这也说明存在着一个由《墨经》作者及其同时代诸子共同参与的针对名辩的论说与争辩。
在1940年代以前,除了章太炎、伍非百使用过“名辩”一词,谭戒甫在1936年发表的《墨子大取篇校释》中也指出,“战国晚世名辩之说甚盛,其思虑恢弘,已非墨子旧义所能范围”。⑦谭戒甫:《墨子大取篇校释》,《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6年第五卷第4期,第761页。“墨子”二字原作“子墨”,今据文义校改。谭氏虽未解释何谓“名辩之说”,但云其“甚盛”、“思虑恢弘”,似已有见于名辩思潮在战国晚期的波澜壮阔及其所争所论的范围广博。
就我所见到的正式出版材料,在1940年代以前似乎也就只有章、伍、谭三人使用了“名辩”这一术语。不过,随着1945年郭沫若《名辩思潮的批判》一文的发表,⑧郭沫若:《名辩思潮的批判》,《中华论坛》1945年第1 卷第2—3期;后收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5年版。“名辩”、“名辩思潮”等术语开始为学术界所知晓并逐渐得到广泛的使用。
二、名辩学:狭义的与广义的
从《墨辩解诂》所附《辩经目录》不难发现,伍非百其实已把经文所论编缀成为一个名辩学系统,⑨有鉴于此,梁启超称伍氏“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为系统的组织”为墨学研究的“一大创作”。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1页。但《解诂》并未对“名辩”进行任何界说。在1922年的《墨辩释例》一文中,伍氏对名辩学进行了最初的说明:“《辩经》研究之范围,为名、辞、说、辩四事。然亦非仅四者之原理及方法而已。而关于原理之材料,及应用方法解决之问题,亦附其中。……或诘难百家之论,或标明自宗之说,虽非名辩本论,要亦有附论之价值焉。”①伍非百:《墨辩释例》,《学艺杂志》1922年第四卷第3 号,第2—4页。据此,《墨经》所论名辩之学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可称为“名辩本论”,指关于名、辞、说、辩四者的原理与方法;其二可叫做“名辩附论”,内容涉及有关名辩原理的材料以及运用名辩方法所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同年发表的《墨辩定名答客问》中,伍非百把名辩本论的研究范围更为明确地规定为正名、达辞、立说、明辩。他不仅引用荀子《正名》来表明名、辞、说、辩四者,“各有等伦”,而且援引后期墨家的《小取》来阐明这四者的关系:“以名举实者,正名之事也;以辞抒意者,达辞之事也;以说出故者,立说之事也。三者皆明辩之所有事。不能正名,无以达辞;不能达辞,无以立说;不能立说,无以明辩。”按伍氏之见,荀子以“正名”命篇,是“原其始”;墨徒以“辩经”称篇,是“要其终”;“其实一也。”②参见伍非百《墨辩定名答客问》,《学艺杂志》1922年第四卷第2 号,第2—4页。这就是说,虽各有侧重,荀子论“名”与后期墨家论“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名辩本论的具体形态。
在1962年撰写的《中国古名家言·总序》中,伍非百对名辩本论进一步做了申说,认为这种狭义的名辩学旨在“研究‘名’、‘辞’、‘说’、‘辩’四者之原理和应用的,详言之,就是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有时亦涉及思维和存在的问题。”③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至于名、辞、说、辩四者,“名、辞、说,为构成‘辩’之三要件”,分别指名词、命题和推理。进而言之:
名、辞、说、辩四者层累而上。“名”也者,所以举实也。“辞”也者,兼两名而抒一意也。“说”也者,兼两辞而明其故也。“辩”也者,兼两说而判其是非也。名、辞、说、辩为古代名学之四级,本文(《小取——引者注》)仅举名、辞、说,而不及辩者,因辩为第四级,包名、辞、说在内。本文主旨在明辩,其全篇内容皆叙述辩之要义,故不赘也。④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437—442、746页。
关于说与辩,更为明确的说明是:“‘说’为兼两辞而成之独语体,‘辩’则兼两说而成之对语体也。……说为或正或反,只须具有一面。而辩则一正一反,必须具有两面。”⑤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437—442、746页。既然独语之“说”已被解释为推理,对语之“辩”就应该指展开于立场相对的双方之间的论辩。
虽然伍非百主要立足《小取》《正名》来解说狭义名辩学的对象与主旨,但先秦名家一派的所思所论在很大程度上亦可为其所涵摄。在他看来,《公孙龙子》旨在讨论名实之辩,故其论说可归于对正名的规律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尹文子》上篇虽然与惠施、公孙龙异趣,但与《正名》为近,故其中的形名之论亦可归于对正名的论说。这就是说,名辩本论或狭义名辩学,其实是对先秦各家(至少是名家、后期墨家和荀子)有关由正名而析辞而立说而明辩之过程的论说的一种概括和总结。
名辩本论与名辩附论的总体,则可视作广义的名辩学。按伍氏之见,《墨经》“用极精简的文字,极有系统的组织,将邓析至墨子时代所有‘名家’相訾相应之说,及名家与各家对诤的问题、术语、原理、原则都一一加以审核、标志”。这个“极有系统的组织”,就是广义的名辩学。《墨经》所体现的这一“组织”,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大部分是属于“名辩”的,包括古代名家所专门研究的名、辞、说、辩四者的原理和应用。另一部分则是辩“名理”的,即古代学者对自然现象所发明的力、光、数、形的抽象理论,和一些关于知识论、宇宙论(时、空)的朴素见解。还有一部分则是周秦诸子各家学派所争辩的问题和论式。⑥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12—13页。此所谓“名辩”指名辩本论或狭义的名辩学;名理之学以及先秦诸子各派所争辩的问题和论式,因其关乎狭义名辩之学的材料和运用名辩方法所解决的问题,当属于名辩附论的范畴。
在《中国古名家言》中,伍非百按经文原有次第,以义类相从,假为标题,编制了《新考定墨子辩经目录》,相较于1923年版《墨辩解诂》所附《辩经目录》,更为直观地展现了《墨经》的广义名辩学体系。简言之,《辩经上》旨在正名,《辩经下》旨在立说。在正名部分,相对于散名,“专名”指“名辩学术用语”,可进一步分为两大类:关于辩之理则的术语与有关辩之方术的术语。立说部分则包括名辩本论、名理遗说与名辩问题三方面的内容。名辩本论,即狭义的名辩学;名理遗说主要指“研究物理之精微者”,属于科学的范围,也包括一些讨论宇宙论、认识论问题的内容;名辩问题,即“当日‘别墨’与各家学派所辩论之学术问题也。其事多属于哲学范围,以关于名辩学者为主,间有涉及各学派之根本义者”①参见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7—16页。。质言之。《辩经下》欲立之说,正是广义的名辩学。
从1916年将“名辩”一词率先引入先秦名学研究,到1922年初论名辩之学的内容与组成,再到1960年代初明确规定狭义名辩学的对象与主旨,伍非百对“名辩”含义的自觉追问、对名辩学术的系统梳理,可以说发前人所未发,独步一时。他立足《小取》《正名》论述的狭义名辩之学,更是史上对先秦名辩的第一次系统重构,对后世研究影响深远。②在1981年《〈吕氏春秋〉的名辩思想》一文中,刘培育继伍非百之后再一次对“名辩学”的内涵进行了表述:“关于正名、析辞、明说、论辩的原理、方法和规律的学问,也就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很明显,这段文字与伍氏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参见刘培育《〈吕氏春秋〉的名辩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编《逻辑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三、从名辩学到形名之学
需要指出的是,名辩之学并不能完全涵盖先秦各家各派对“名”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说与争辩。在《中国古名家言》中,伍非百把研究视野从先秦名辩扩展至整个先秦“古名家言”。从字面上看,“古名家言”指的是古代名家的著述。那么何谓“名家”呢?类似于章太炎、张尔田等人的理解,③参见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载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230页;张尔田:《原名》,《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伍氏也认为“名家”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用法:前者指汉儒所说的名家七子;后者的范围甚广,“专门研究与这个‘名’有关的学术问题,如名法、名理、名言、名辩、名分、名守、形名、正名等等学问的皆是”。④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5页。
综观伍氏的用词法,“名家”一词主要是在广义的用法上来使用的。在他看来,“形名”与“名”乃古今称谓之殊,并非在名家之外还有形名家。⑤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6页。伍氏认为,后世学者以“名家”专称好辩之徒,尤其是辩“坚白”“无厚”之言者,远非“形名家”之古谊。(第10页)由于“名家”与“形名家”异名而同实,名家之学也就是形名之学。关于形名学之流衍,他指出:
形名之为学,“以形察名,以名察形”,其术实通于百家。自郑人邓析倡其学,流风被于三晋(韩、赵、魏),其后商鞅、申不害皆好之,遂成“法、术”二家。其流入东方者,与正名之儒、谈说之墨相摩荡,遂为“儒墨之辩”。其流入于南方者,与道家之有名、无名及墨家之辩者相结合,遂为“杨墨之辩”。至是交光互映,前波后荡,在齐则有邹衍、慎到;在宋则有兒说;在赵则有毛公、公孙龙、荀卿;在魏则有惠施、季真;在楚则有庄周、桓团;在韩则有韩非,皆有所取资于“形名家”。⑥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9页。
综其要旨,形名之学或广义的名家之学可以分为以下六派:⑦参见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9—10页。伍氏在《总序》中还提到广义名家在先秦最流行、最显著的有名法(申不害、商鞅等)、名理和名辩三派(第5页)。(1)韩非、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一派,基本主张是“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赏罚乃生。”(2)商鞅为代表的重法一派,基本主张是“言者名也,事者形也。言与事合,名与形应。”(3)尹文为代表的重名分、名守一派,基本主张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顺言,使万物群伦各当其名,各守其分,不相惑乱。”(4)墨翟、邹衍、荀卿为代表的重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名辩一派,基本主张是“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秩然有序,范然有型。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5)邓析、别墨、惠施、季真、公孙龙为代表的名理一派,基本特点是“游心于坚白同异之言,窜句于觭偶不仵之辞。上智之所难知,人事之所不用。耗精冥索,穷年于‘心’‘物’‘力’之推求。”(6)庄周、慎到代表的主齐物一派,基本特点是“以不辩为大辩,以不言为至言。刳心于滑疑之耀,著语于是非之表。”
就“名家”与“形名家”异名而同谓说,“古名家言”当指古代论形名之学的著述;就形名之学分为六派看,“古名家言”理应涵盖形名六派的全部著述。不过,尽管重术一派的《韩非子》、重法一派的《商君书》、主齐物一派的《慎子》等著作尚存于世或并未尽佚,伍氏却说现存古名家言仅有《墨辩》《尹文子》《公孙龙子》《庄子·齐物论》《荀子·正名》,其他短章单句散见诸子书中者以及伪书《邓析子》。①参见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11—12、17—18页。显然,“古名家言”的字面含义与伍氏对这个词的实际用法并不一致。
事实上,《中国古名家言》校释的古名家言,主要是名辩和名理两派的著述,且有以名辩统摄名理之意。这一点可从该书关于现存古名家言之大意的介绍中窥得一斑。②参见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13—16页;《中国古名家言》,第471页。伍氏之所以把狭义名家之学(名理)归于广义的名辩学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认为在形名学内部存在着一个有关名辩的共同话语:“’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盛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荀卿,前后历二百年,蔚然成为大观,在先秦诸子学术中放一异彩,与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立为三。”③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7、7、17页。“名家”在此既非狭义上汉儒所说的名家七子,亦非广义的名家即形名家之全体,而主要指形名家中的名辩(含名理)一派;相应地,“名家之学”指的也不是形名学之全体,而主要指其中与名辩(含名理)一派相关的广义名辩之学。
从被视为先秦形名之学集大成者的荀子来反观名辩话语,伍非百认为,《正名》的正面立论承继了《墨经》《公孙龙子》和《庄子》三家论“辩”的精华,对“三惑”的批判针对的则是邓析、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的错误之例,而荀子的最大成就是:“把从邓析、孔子以来发展的由正名而析辞而立说而明辩的过程,明白清楚地指出为‘名’、‘辞’、‘说’、‘辩’四级,使我们从学术思想上,知道由孔子的‘正名’发展到墨子《辩经》,及再由墨家之‘辩’,回到荀子之‘正名’,是一线相承,回环往复的。”④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7、7、17页。
尽管《中国古名家言》主要是对现存先秦名辩(含名理)篇籍的校勘和诠释,对于荀子之后名辩学术乃至整个形名之学的余绪,伍氏亦有简要的提示:其一,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弃其辩说之要妙者,而纳其名实之综核者,融‘法术’‘形名’于一炉而冶之。‘形名’中绝,‘刑法’代兴”。⑤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753页。“代兴”,原文误植为“代舆”;据上下文意,当为“代興”,简写即是“代兴”。其二,“《齐物论》后流为魏、晋间之清谈名理”。⑥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7、7、17页。其三,作为儒家正统之学的《正名》,其后流为春秋学之“正名分”、董仲舒之“深察名号”。此一余绪之弊在汉代表现为标榜“名节”;在魏晋之初表现为夸饰“名教”,至于《人物志》等在此时俱归入名家著述,则标志着“古代名家学”或先秦形名之学的彻底亡绝。⑦参见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11—12、17—18页。
前文论及1916年伍非百曾强调不懂名辩学术就无法准确阐释《墨经》,认为《墨经》是古名家言的代表,研究《墨经》有助于复兴旧有名学。针对伍氏的这一看法,我曾追问:如何理解名辩学术与旧有名学的关系?如何理解“旧有名学”中“名学”一词的含义?
综观《中国古名家言》全书,“名学”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其一,“名学”乃“形名之学”或“名家之学”的省称,亦即本文所说的围绕“名”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的论说与争辩。例如,《墨辩解诂》在论及“知材”之“知”时曰:“此‘知’之有无真伪,中土名家多置诸存而不论之列。惟庄子怀疑于此知之有无真伪,故其非毁名家,常自用其怀疑之名学,以诋各派辩言之无根,《齐物论》即其名著也。”①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25、17、20、25、80、748页。这里,“中土名家”无疑泛指形名各派,而庄子所持“怀疑之名学”则是形名学之一种。其二,“名学”与“逻辑”、“论理”异名而同谓。《解诂》释《经上》首条,“故”指思辩之根据或理由,相当于因明之“因”、演绎推理之“前提”,亦即常语所谓的“所以然”。而“‘所以然’一词,关于名学方法论最巨”。“今俗言‘故’,则曰‘所以然’,而不知其自出。盖沿用名学之例,而不自知也。”②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25、17、20、25、80、748页。很明显,与“所以然”相关的“名学”,与“逻辑”同义,并非泛指形名诸家的论说。
以“名学”的两种含义为前提,就名学之为形名学而言,旧有名学与名辩学术之间无疑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为名辩与名理在形名六派中仅占其二,名学还包括有关名法、名言、名分、名守、形名、正名等论题的论说与争辩;就名学之为逻辑来看,旧有名学(即中国本土逻辑)反过来却成为了名辩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后面一点,既涉及伍非百研究古名家言之缘起,也关乎如何把握名辩学术的本质,当详细论之。
伍氏之所以研究以《墨经》为代表的古名家言,主要是受到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已“蔚然列为专科”的刺激,希望能借此复兴旧有名学,以证成后者与前两者的鼎立之势。就此而言,如果说名辩学术是阐明现存古名家言之本质的钥匙,那么要准确阐明名辩学术的理论特质,显然就难以绕开逻辑。
先看狭义名辩学与逻辑的关系。由于伍非百把“名”、“辞”、“说”、“辩”释作名词、命题、推理和论辩,而且主要援引逻辑、因明来阐明《小取》《正名》中的名辩论说,因此把对逻辑问题的讨论视作狭义名辩学的主体或核心是可以成立的。不过,逻辑并不构成狭义名辩学的全部内容,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伍氏明确指出,狭义名辩学有时还要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后者显然不属于通常所理解的逻辑的问题域。第二,就《墨辩》《正名》的实际论说看,对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的研究还牵涉认识论的内容:
辩也者,所以求真理也。而求真理之器,在“知”。是故“知”之本体观念如何,乃思辩方法所由生也。
“何者为知?”“云何有知?”“所知为何?”此三问题,为知识论所急欲解决之问题,亦即名学根本上所急欲解决之问题也。③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25、17、20、25、80、748页。
“知”之本体观念是思辩方法(逻辑方法)得以可能的前提、知识论的问题亦即名学(逻辑)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讲逻辑离不开认识论。进而言之,对正名、析辞、立说、明辩之规律的研究,也必须以认识论为前提:“《解蔽》与《正名》,互为表里。欲正其名之惑,必先解其心之蔽。蔽解则智生,为正名、析辞、立说、明辩之本。”④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25、17、20、25、80、748页。
就广义名辩学与逻辑的关系看,尽管逻辑构成了狭义名辩学的主体或核心,但作为广义名辩学的其余两项内容,名理之学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理论,也有一些讨论宇宙论、认识论问题的内容;而名辩问题主要属于哲学的论域,间或有涉及各学派之根本宗旨的内容。就此而言,广义名辩学的内容更非逻辑所能范围。
四、从伍非百的先秦名学研究看新名学的可能性
伍非百的先秦名学研究未必尽数合乎历史之真实,也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他对形名之学的理解,对于反思近现代名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探索当代新名学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意义。①沈有鼎认为,《中国古名家言》“以敏锐的眼光,紧紧抓住了逻辑学和其他学问所以不同的特点,因此能不囿于俗见,对古书时有独创的新解。古代中国的逻辑学说和有关逻辑的学说,所有不同的家数和歧异的方向,在书中都已一一阐明”。这一评论似囿于“名学逻辑化”的视域,未能充分论及伍氏有关形名之学的理解在深化名学研究方面的意义。参见沈有鼎《序》,《中国古名家言》,第3—4页。
“名学”本是中国旧有名词,在严复用它翻译“logic”之前,②严复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中用“名学”来称逻辑:“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见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这一语词既与逻辑无涉,也与中国古代围绕“名”所展开的论说与争辩无关。③“名学”的本义是著名学者,如《三国志·吴志·华核传》:“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译名的“名学”与本土关于“名”的论说不存在联系。事实上,严复就曾援引先秦正名之论来解释以“名学”译“logic”的正当性,认为汉语中只有“名”的内涵庶几与“logos”——“logic”的希腊文词源——的“奥衍精博”相同;而逻辑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恰如中国文化所主张的“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④参见穆勒《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亦可参见晋荣东《逻辑的名辩化及其成绩与问题》,《哲学分析》2011年第6期,第61—64页。
作为译名的“名学”是逻辑东渐的结果,后者直接刺激了近代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关于“名”的种种论说,希望从中发现中国本土逻辑。如严复认为“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⑤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6页。。王延直提出正名之说与论理学或名学本质相同:“春秋之季,孔子首倡正名之说。……(所谓正名者,其所见与今之论理固无以异也。论理学亦可译作名学)。”⑥王延直:《普通应用论理学》,贵阳论理学社1912年版,第9页。胡适则把博士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的中文名称定为“先秦名学史”。更有甚者如虞愚,主张在“逻辑”与“因明”已分别专指西方逻辑与印度逻辑的情况下,应该把“名学”确定为指称中国本土逻辑的专有名词。⑦参见虞愚《自序》,《中国名学》,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3页。关于用“名学”来称呼中国本土逻辑,更为详细的历史梳理,可以参见周云之《名辩学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3页。
我认为,以寻找中国本土逻辑为目的,近现代学者在梳理与诠释中国古代关于“名”的种种论说与争辩时,在总体上表现出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以“名学逻辑化”为主导方法,即运用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诠释名学,在名学语汇与逻辑术语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并通过这种“据西释中”来梳理名学的主要内容,勘定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地位。不过,在聚焦于如何以逻辑释名学的同时,这一方法对逻辑与名学各自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这些因素对它们的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名学逻辑化”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哲学史的内容排除在对名学的逻辑研究之外,哪怕被排除的那些内容本身就属于名学的范畴。⑧例如,刘培育就曾主张唯有同作为思维形式的辞、说、辩等相联系的名,才是名辩之逻辑研究的对象。五卷本《中国逻辑史》也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逻辑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区别开来。”参见刘培育《〈吕氏春秋〉的名辩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编:《逻辑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中国古代关于“名”的论说,内容庞杂,往往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这种以证成中国本土有逻辑为目的的研究,将名学窄化为名辩之学,并把对后者的研究窄化为对其中所含逻辑之理的研究,从而遮蔽了对名学之多重内涵的全面把握。
第三,在研究成果上,把名学或名辩之学的理论本质勘定为中国本土逻辑。这不仅表现在“名学”一词被视作指称中国本土逻辑之专名,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普遍认同“在中国特殊的古代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是实质上的同义语”。①纪玄冰(即赵纪彬):《名辩与逻辑——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与古代逻辑的名辩形态》,《新中华》1949年第12 卷第4期,第29页。但是,把名学或名辩之学等同于中国本土逻辑,并将后者视作西方传统逻辑在中国本土的等同物或副本,严重忽视了二者在目的、对象、内容和性质上的相异。
第四,在研究心态上,为了维护本土文化的自尊,名学研究者往往“耻于步武后尘”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为斯皆古先所尝有”。受此影响,他们更为注重名学与逻辑之同而忽略了二者之异,希望通过证成名学或名辩之学也是“逻辑”大家庭中的一员,来赢得西方文化的承认。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逻辑与名学的简单附会、牵强比附,甚至是对后者的过度诠释。
进入1990年代,最初是一批名辩逻辑研究者,而后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先后对近现代名学研究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性反思。②参见崔清田《中国逻辑史研究世纪谈》,《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第7—11页;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4页;曾祥云《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拒斥名辩逻辑》,《江海学刊》2000年第6期,第72—73页;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第59—64页;等等。要克服近现代名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伍非百对形名之学的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毋庸讳言,伍氏对古名家言的研究亦源于西方逻辑的刺激,而且他所理解的狭义名辩学的核心或主体就是逻辑,但如前所述,其名学研究并未如“名学逻辑化”进路那样窄化名学的多重内涵,并未将中国古代围绕“名”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的论说与争辩简单归结为中国本土对逻辑问题的讨论。举凡对名实、名分、正名、名言、形名、名理、名法、名辩、名守、刑名、名教诸论题的论说,均属于伍非百所谓“古名家言”或“形名之学”的范围,而这些内容显然非逻辑所能涵盖。
与名家有广狭二义相应,伍氏认为古名家言有的是“间接的兼业的名家篇籍”,有的是“直接的专门的名家篇籍”③参见伍非百《总序》,《中国古名家言》,第11页。。受此影响,崔清田强调先秦名家与名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名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既有重政治、伦理的一面,也有相对重智和抽象的一面;既有名实关系的讨论,也有宇宙观问题的分析;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④参见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22页。曹峰认为伍氏将广义名家区分为名法、名理与名辩三派是“很有见地的想法”,并指出战国秦汉之际存在两种名家,即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从事“事实判断”的名家与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注重“价值判断”的名家。⑤参见曹峰《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109、104—107页。
在重申名家与名学的广义理解的基础上,崔清田、曹峰等又从研究方法、内容和心态诸方面对如何深化名学研究进行了思考与探索。例如,崔清田提出“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希望借此改变“名学逻辑化”不重视名学和逻辑所由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它们的影响这一缺陷,强调名学与逻辑的比较必须建立在对二者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基础之上。⑥参见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第11页。从研究内容上说,对名学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必然要求将其还原到它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从不同角度对催生和制约名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考察,为此就有必要运用不同方法对名学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研究心态上看,“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引入,预示名学研究可能无须再诉诸“名学逻辑化”来证成中国本土有逻辑以维护中国文化的自尊,赢得西方文化的承认,而可以通过强调名学之为逻辑的平等他者、突出名学的本土特点来追求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⑦不满于把墨家辩学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张斌峰提出应该立足于墨辩所由以产生的文化背景,通过弄清它所由以生成并受其制约的政治、经济、哲学(本体论、知识论、思维方式)、文化等诸多因素,来研究墨辩自身的内容及其特点,认为“这种研究不仅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研究《墨辩》,而且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认同与确认”。参见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第366—375、272页。曹峰不仅赞成崔氏对以“据西释中”为核心的“名学逻辑化”的批判,而且认同“名学逻辑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名学与逻辑的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强调名学研究应该回归思想史的正途,唯有“同时展开逻辑学语言学意义上的‘名’思想和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思想两条路线,不偏不倚齐头并进,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合理的成果”。①曹峰:《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110页。
如果把1990年代以前的近现代名学研究称为“旧名学”,那么以崔清田、曹峰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这种旧名学的批判反思、对深化当代名学研究所做的思考与探索,可以说就是在开拓一种新的名学。②“新名学”这一表述来自于苟东锋博士。虽然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未必与我相同,但不敢掠美,特此说明。又,刘梁剑博士亦使用过“新名学”一语,意指汉语言哲学,即基于汉语经验的语言哲学。详见刘粱剑《汉语言哲学发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简言之,就研究心态说,新名学把中国古代关于“名”的种种论说视为西方逻辑乃至西方文化的平等他者,希望通过强调其本土特点来追求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从研究方法看,新名学要求超越“名学逻辑化”,对围绕“名”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的论说进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在此基础上进行求同明异兼顾的本土名学与外域文化的比较研究;从研究内容说,新名学要求把中国古代关于“名”的论说还原到它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运用多元方法对其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既不否认其中所包含的逻辑之理,更要重视其伦理政治之维;就本质勘定言,新名学不再把关于“名”的种种论说归结为中国本土逻辑,也无意将其归属于现存的某(些)门学科,然后把这(些)门学科视作其本质,而是呼吁首先从不同角度对其多重内涵进行全面把握与准确阐释。
旧名学存在的问题表明了新名学的必要,伍非百对名辩之学乃至整个形名之学的理解,以及崔、曹等人对伍氏观点的肯定与发挥,则表明新名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止于此,近年来围绕中国古代关于“名”的种种论说出版的一些著作、发表的若干论文以及答辩通过的一批博士论文,表明新名学不再仅仅是一种研究构想,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术研究的现实。③例如,崔磊:《韩非名学与法思想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赵炎峰:《先秦名家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雷东:《语言维度下的先秦墨家名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苟东锋:《孔子正名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周晓东:《先秦道家名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孟凯:《正名与正道——荀子名学与伦理政治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吴保平:《韩非刑名逻辑思想的渊源及演进历程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