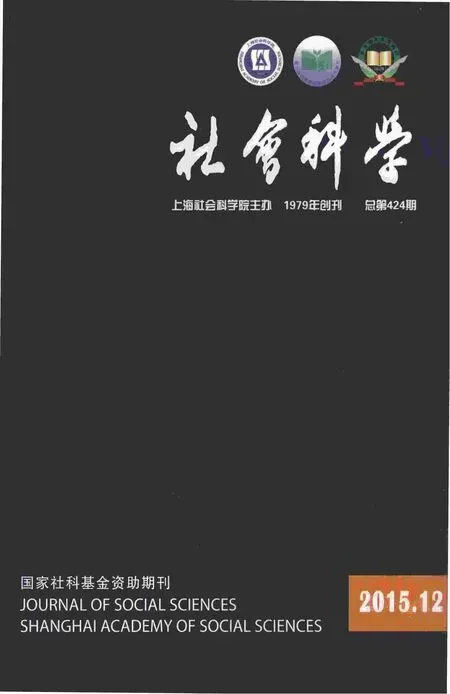社会选择理论与社会冲突的治理之道
顾 昕
社会冲突存在于任何一个时期的所有人类社会。当然,在一个处于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伦理文化价值变迁的转型国家,社会冲突的广度和烈度都有可能超过非转型国家。当今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小到广场舞和转基因食品争议,中到各种群体性事件,大到地区性甚至国际间人群冲突,各种层级的社会冲突可谓层出不穷。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都有两个共同点,即当事各方的偏好具有很大的异质性,而且支撑其偏好类型的价值观具有很强的韧性。冲突各方皆认为己方的价值观不可动摇,且坚信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行事乃是不可让渡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管控社会冲突,使之不至升级而形成僵局,甚至找到冲突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尽管社会冲突可能发生在人际、群际、组织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其根源和内容也可能千差万别,但社会科学家们相信,总能找到一些“可以贯穿并阐明大部分或所有冲突现象的概括性理论”①[美]狄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王凡妹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当然,不同的理论是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探究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即本文所探索的“治理之道”。其中,作为“对集体决策的一种分析”②Wulf Gaerthner,A Primer in Social Choice Theory,revise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社会选择理论能为我们的这一探索提供有益的思想和智识启示。毕竟,无论社会冲突的治理之道为何,都离不开集体决策过程,因此致力于分析集体决策与个体偏好关系的社会选择理论,无疑应该能为我们提供有力的分析框架和工具。
在学术思想史上,社会选择理论首先是在经济学中得到发展,被视为福利经济学的逻辑基础①Allan M.Feldman and Roberto Serrano,Welfare Economics and Social Choice Theory,2nd Edition,New York:Springer Science+Media,Inc.,2006.,而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问题就是如何对各种可以相互替代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设计、实施和评判②Kenneth J.Arrow,Amartya K.Sen and Kotaro Suzumura,ed.,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Vol.1,Introduction,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 B.V.,2002.p.1.。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J.Arrow)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K.Sen),均主要因其对社会选择理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在经济学中发育成熟之后,社会选择理论就进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成为一个横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但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运用社会选择理论于社会治理的学术性努力,并不多见。本文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运用社会选择理论对社会冲突的治理之道进行一些尝试性的讨论。
社会选择理论的具体研究课题林林总总,但其核心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个体的偏好如何加总为集体的偏好,或如阿罗本人所说,“施加在加总程序中的合理条件是什么”③Kenneth J.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2nd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John Wiley & Sons,1963.p.103.。这里的“条件”,就是集体决策的规则,而不同规则“合理”与否或在何种意义上“合理”,首先必须满足理性的要求,至少要合乎逻辑,其次也体现了规则制定者的价值观。所有社会冲突的治理,都可归结为如何处理引发冲突的行为,而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构成了社会选择理论中所谓的“选项”(Alternatives)。社会冲突之所以存在,自然是有关行为引发了当事各方“感知到的利益分歧”④[美]狄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王凡妹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而当事各方对利益分歧的不同处理方式(即不同的选项)有着不同的偏好,那么社会冲突的治理就是要设法在这种情况下找到协调诸方利益的一种解决方案,即冲突各方必须至少先要达成某种理性的集体性决策,继而还要有效地实施业已达成的决策。
一般认为,理性的集体决策规是明确的,即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决策与服从是可以分开研究的两个课题,而任何集体决策的达成必须通过多数赞同的游戏规则即“多数决规则”(Majority Rules)。多数决规则实际上有很多种,而最简单的只需多数比少数多一人即可,被称为“简单多数决规则”。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中,多数决都被普遍视为“民主的”决策规则。这一规则不仅存在于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存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各类需要做出决策的会议,都难免要进行表决。无论具体的利益分歧有多大,大家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多数决”是集体决策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决策如果不能获得多数的赞同,就不配称之为“集体决策”。但问题在于,社会选择理论证明,“多数决”并不是集体决策的充分条件,即在很多情况下,单靠“多数决”,理性的集体决策无法达成;或者说,此种情况下达成多数赞同的决策可能存在着非理性的成分。因此,要达成理性的集体决策,必须在“多数决”之外附加一些其他的条件,而附加什么条件,就构成了集体决策(或具体到本文讨论的冲突管控)的不同治理模式。
一、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多数决”的局限性
“多数决”并非理性集体决策的充分条件,这一观点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石,而奠基者就是阿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阿罗在兰德公司参加了一项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探讨政府如何基于民众的不同偏好制定国防政策。然而,出乎阿罗自己意料的是,他的研究结论竟然是:很难办。因为只要选项超过两个,且不限制民众对选项有不同的偏好,那么多数决不可能做到集体决策必定基于民众偏好的加总。1950年,阿罗在《政治经济学学刊》上发表了题为“社会福利概念的一个困难”的论文①Kenneth J.Arrow,“A Difficulty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Welfa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No.4,1950.pp.328-346.,提出了后来被命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简称“阿罗定理”或“阿罗悖论”)。紧接着,阿罗在此论文的基础上完成其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并于1951年出版②Kenneth J.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1st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John Wiley & Sons,1951.,旋即成为一部经典。此后,无数经济学学者,包括许多重量级经济学家,围绕着阿罗定理开展了海量的研讨③Donald E.Campbell and Jerry S.Kelly,“Impossibility Theorems in the Arrovian Framework”,in Kenneth J.Arrow,Amartya Sen and Kotaro Suzumura,ed.,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Vol.1,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 B.V.,2002.pp.35-94.。尤其是在1960年,另一位后来因其他理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给出了阿罗定理的完整数学证明④William Vickery,“Utility,Strategy and Social Decision Rul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4,No.4,1960.pp.507-535.,社会选择理论大厦的逻辑根基由此坚如磐石。
阿罗定理揭示了民主制度内含的一个矛盾,即民主固然可以被视为集体决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后来,对这一矛盾的分析成为学术界各种各样“民主悖论”研究的逻辑起点⑤Richard Wollheim,“A Paradox i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in Peter Laslett and W.G.Runciman,ed.,Essay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Society,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62.pp.71-87.。当时,阿罗定理的发现在经济学家(也包括阿罗自己)当中造成的即刻反应是巨大的震撼和困惑,尤其是对福利经济学,阿罗定理引发的社会选择理论研究,如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William Baumol)所说,散发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讣告气味”⑥William Baumol,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2nd Ed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事实上,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提出迅速激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并激发其他学者很快发现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不可能性定理”,一时间让集体选择、社会福利甚至民主制度都蒙上了森所说的“建设性悲观主义”⑦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67-69.。当然,之所以有“建设性”,意味着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并不会让有关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变得毫无意义,也不会让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决策变得不再理性,更不会让本文所关注的社会冲突的理性治理变得不可能。事实上,通过严谨的分析,社会选择的研究者们已经在理论上分辨出哪些游戏规则能够帮助何种组成的社群就哪些类型的事项可以卓有成效地达成集体决策。特别是森,在探究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学术成就无疑可以为我们认识并分析社会冲突的民主治理之道开辟思想的道路。
在当今中国,很少有人认为决策不应该民主(即认可民主是决策的必要条件),但很多人会感觉甚至嘲笑民主决策效率低,经常处在议而不决、决而不断的尴尬境地(即民主不是充分条件),只不过他们并不了解,在六十多年前,有一位美国学者竟然用集合论的基本原理证明了他们的感觉,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也有不少中国人思维短路,直接从民主决策低效的现象跳跃到主张“一把手说了算”的振振有词,而且身体力行。但是,乾纲独断的后果真是五花八门,且不说不少决策只不过是“拍脑袋”,不少当初“说了算”的“一把手们”后来却锒铛入狱,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其治下的社会都没有多少理性可言。他们或者不愿意了解、或者没有能力了解、或者根本不屑于了解西方学者已经就民主低效问题所开展的深入研究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如何完善民主制度,修正其低效决策的弊端,以便同时做到既尊重个人偏好又能有效地进行理性的集体决策,这既是无数西方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的研究课题,当然也是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必需面对的严肃挑战。中国自然无法例外于这一挑战,也就不可能无视或忽视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要探究这一严肃议题,关键在于深究民主决策的条件。阿罗为其定理所设定条件是他自己认为任何民主的集体决策过程所必需遵守的规则,这些条件在社会选择理论所采用的逻辑分析体系中被称为“公设”(Postulates)或“公理”(Axioms),而不同条件的组合形成不同的“公理结构”(Axiomatic Structure)。因此,为了探究如何既尊重个人的偏好又能达成理性的集体决策,我们有必要以阿罗定理为起点,展开我们的分析。为了让没有受过数理逻辑训练的读者也能了解社会选择理论的精髓,本文放弃使用数学符号,而采用文字表述和图表解析的方式。
阿罗定理可以用一个三人(甲、乙、丙)组成的社群对三个不同选项(x、y、z)如何进行集体决策来加以展示(见表1)。这样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极为常见的,这里的选项可以是不同的餐馆(川菜、粤菜、鲁菜),不同的活动(看球赛、看电影、看话剧),也可以是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选项,例如广场舞声浪争议、公共场所禁烟、影视作品分级、内地游客香港自由行人数限制、污染物排放限制(如雾霾治理)、公共资源(如石油和煤炭)收益的处置方式,等等。我们采用公共场所禁烟进行分析。所谓社会选择问题,即这个社群的所有人首先要对所有的选项给出自己的偏好排序(即个人排序),进而通过一个集体决策过程产生集体偏好(又称“社会排序”)。
对于从个人排序到社会排序的集体决策过程,阿罗给出了五个条件(公设):1、非独裁性,没有人能在自己的偏好遭到其他人反对时,仍能让自己的偏好保留在社会排序之中;2、传递性,即如果在最终的社会排序中,多数偏好x 更甚于y,偏好y 更甚于z,那么也就必然意味着偏好x更甚于z;3、一致同意性(或无异议性),如果一个人的某个偏好获得其他人的一致同意(或其他人无人反对),那么这个偏好自然就成为集体偏好或进入社会排序;4、不相干选项的独立性,对任意两个选项的社会排序,不能根据对其他选项的排序而定;5、选项不受限性,任何人的任何偏好(个人排序)都可以成为选项。阿罗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限数量的个人所组成的社群,并且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选项,那么就不可能在同时满足上述五个条件的情况下达成社会排序①参见Dennis C.Mueller,Public Choice II,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583-584。。
从表1 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选项x、y、z 的任何一种排序,都不可能在同时满足上述五个条件的情形下获得简单多数的赞成。例如,考虑一下个体排序x>y>z 是否能成为最后的社会排序。表1 显示,其中x>y 获得了两人(甲和丙)赞同,y>z 也获得了两人(甲和乙)赞同,依照可传递性的理性要求,x>y>z 要成为社会排序,必须要有两人赞同x>z,可是在这个社群中,恰恰有两人(乙和丙)赞同的是相反偏好:z>x。这种情形,被称为“偏好循环”或“投票循环”。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采用的这个图示及其所揭示的问题,早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就由法国数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孔多赛(Marquis de Condorcet)提出了,因此在当代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这一问题被称为“孔多赛投票悖论”②Joseph E.Stiglitz,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3rd Edi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163.。阿罗以及社会选择理论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了孔多赛的思想,并且系统深入地探究这一思想对于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广泛意涵。

表1 三人社群对公共场所禁烟选项的社会选择
在阿罗给出的五个条件中,前四个主要关涉集体决策理性与否,而违反这四个条件也就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了。当然,合乎理性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众所认可的价值观①Niko Kolodny,“Why Be Rational”,Mind,Vol.114,No.455,2005.pp.509-563.,以及理性本身是否蕴含着某些其他价值观②David J.Bartholomew,Uncertain Belief:Is It Rational to be a Christi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哲学问题。
第一个条件“非独裁性”的措辞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但细查其内容,其实无非是“多数决”规则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或者说,这一条件的给出,只不过是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设定为遵循多数决规则进行的集体决策。社会选择理论研究者们当然知道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少数做出的、但也获得多数当时顺从并且有可能事后认可并赞扬的“社会选择”。阿罗在其经典之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中就此说明,即便是在民主社会中,社会决策有时也是由单个人或小群体做出的,有时则是通过一组无所不包的传统规则(例如宗教戒律)给出的,这两种社会选择的方式,就是独裁和惯例③Kenneth J.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2nd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John Wiley & Sons,1963.pp.1-2.。
因此,“非独裁性”条件作为公设,只不过限定了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围。正如前文所述,多数决一般被视为集体决策的必要条件,而社会选择理论关心的研究问题就是多数决是否是集体决策的充分条件,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多数决能促成一个社群有效地做出集体决策。可以说,社会选择理论对这一研究问题的确立,必然引致“非独裁性”的公设,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如果将这一公设的设定理解为阿罗对自由主义的辩护,则是一种误解。
第二个条件把“传递性”作为偏好或决策理性与否的判断标准,这在很多人那里是无需证明的,甚至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很多社会选择的权威性论著干脆不把这一条件单列出来,从而把阿罗的五条件变成了四条件④参见Amartya K.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San Francisco:Holden-Day,Inc.,1970.pp.37-38;Wulf Gaerthner,A Primer in Social Choice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0-21。。
第三个条件“一致同意性”(Unanimity),又被称为“帕累托准则”,作为公理的正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一条件还包含两种可能性:一是所有人都认为x>y,那么这些人组成的集体(社群或社会)自然也应该认为x>y,这是阿罗定理所表述的内容;二是至少有一个个体认为x>y,而其他个体不反对,即既有可能认为x>y,也有可能认为x 与y 无差异,这就是“无异议性”。由于第二种情形包含了第一种情形,因此阿罗定理中所表述的第一种情形,又在很多文献中被称为“弱帕累托原则”⑤关于“一致同意性”条件的细节,森给出了详细的讨论,参见Amartya K.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San Francisco:Holden-Day,Inc.,1970.chapter 2。。
第四个条件“不相干选项的独立性”,其实也可以陈述为“不相干选项的不相干性”,这也是理性本身的要求之一:如果不相干选项其实是相干的,那么这显然不合理性。如果两个“选项”之间有某种相干性,那么在进行集体表决之前,应该先把这两个“选项”合并为一个备选方案,这才合乎情理。
我们将在下文详述,以上四个条件都体现了理性内涵的游戏规则,其确立也是社会选择理论关注集体决策是否理性的一种体现。这些游戏规则的澄清,无非是确保集体决策具有理性。在文明的人类生活中,以理性行事的期待或要求,不仅适用于个体,也应该适用于集体行动者,例如群体、组织和国家。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人类社会所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因为合乎理性本身就以一定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为支撑。
第五个条件“选项不受限条件”集中而突出地体现了阿罗以及很多学者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其正当性“很像要求选择自由或表达自由”⑥Dennis C.Mueller,Public Choice III,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589.。或者说,这一条件集中体现了价值多元主义的理念,依照这种理念,哪怕是在其他人看来“极为怪异”的个人偏好(个人排序)也不应该被排斥于社会选择之外①Wulf Gaerthner,A Primer in Social Choice Theory,revise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例如,表1 中丙的偏好类型乍看起来有点儿“怪异”(远谈不上“极为怪异”),即此人有非此即彼的偏好倾向,不大喜欢中间路线,但就这么一点儿“小任性”已经足以使集体决策无法达成了。很显然,具有这种偏好类型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而且他们这一偏好类型的形成并不见得是没有道理的或非理性的。譬如说,他们或许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y选项最不可取,因为要做到“有条件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会很难,要么条件不容易设定,要么条件不容易达成(如纳锐人付出更高的税金),因此他们最不偏好y 选项。很显然,没有理由认定这种偏好类型不能纳入社会选择的考虑范围。
阿罗定理看起来抽象,更不要说其论证的抽象性了,但其内容实际上只是对现实世界中民主决策决而不断现象的一种逻辑展示而已。在现实世界中,不同人对任一选项的偏好程度对其个体以及整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涉及到少数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多样性时,尤为分明。
二、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拓展信息基础和凝聚价值偏好的重要性
自阿罗定理提出之后,社会选择理论的大量文献主要围绕着放松阿罗条件而展开。很显然,在现实世界中以及在可以设想的现实改革中,集体决策并不一定依照阿罗设定的条件进行,这意味着,阿罗条件的每一种放松,便可成为民主集体决策制度架构的一种改革思路。由于多数决是民主集体决策的必要条件,因此如前所述“非独裁性”条件对社会选择研究者们来说无法放松。至于传递性条件,最多也只能放松到准传递性,否则就会陷入非理性的境地②Gordon Tullock,“The Irrationality of Intransitivity”,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16,No.3,1964.pp.401-406.,如果放弃准传递性这一条件,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将会产生混乱③William H.Riker,“The Paradox of Voting and Congressional Rules for Voting on Amendment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2,No.2,1958.pp.349-366.。因此,我们下文只讨论放松另外三种阿罗条件后的若干情形。
(一)一致同意性条件的放松
一致同意性条件(弱帕累托条件)的放松乍看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理性的最低要求之一,也理应是一个所有人都可达成共识的条件。一旦放松,这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集体癫狂的情境。一个人(人群)的偏好明明是其他人(人群)都同意的,却依然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这表明该社会的其他成员就是讨厌这个人(人群),无论其偏好是什么以及其基于偏好的行动多么无损于甚至有利于大家的利益。很显然,这种情况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歧视,而这样的情境不仅发生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程度不等地发生在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常社会冲突之中,例如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地域攻击、宗教冲突等。这说明,帕累托原则(一致同意性条件)其实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即反歧视的价值观④Xu Yongsheng,“Non-Discrimination and the Pareto Principle”,Economic Review,Vol.51,No.1,2000.pp.54-60.。从常识来判断,反歧视的价值观并非为每一个人都真心接受,只不过在文明社会中赞成歧视的价值观是无法宣之于口的。例如,在中港冲突中,部分港人对内地游客的歧视与攻击,其社会心理根源就在于这些港人维护自身优越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香港人”的“族群化”⑤张健:《香港社会政治觉醒的动因:阶级关系、参政需求、族群认同》,《二十一世纪》2015年2 月。,而在这一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中,多数香港人所持的反歧视价值观,当然并非为每一个香港人所接受,只不过这些人常常会把反反歧视的价值观通过各种其他貌似有理甚至冠冕堂皇的理由伪装起来。
(二)不相干选项独立性条件的放松
“不相干选项的独立性”这一条件从逻辑上看是一清二楚的,但问题在于这一理性的约束条件在现实世界中并非一清二楚,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多多少少是相干的,或者人们总能找到一些理由论证原来不相干的事情其实是相干的。那么在进行集体决策时,基于什么理由把那些不那么相干但也不是完全不相干的选项纳入社会排序的考虑,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面对貌似不同的选项,一方认定应该一码归一码,而另一方认为其中若干选项其实是一码事,在现实世界中就体现为没完没了的扯皮。许多社会冲突,包括不少很琐碎的人际冲突,从理论上来分析,其实都缘于相干性争议。
对于相干性难题,森认为,这显示出信息在社会选择中的重要性,即人们基于什么信息以及多少信息来判断哪些选项与哪些选项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相干,深刻影响着集体决策。首先,森区分了“效用信息”和“非效用信息”,前者是人们判断选项对其幸福或福祉如何产生影响的信息,而后者则与此无关;其次,森讨论了在社会选择中信息排除(Informational Exclusions)与信息纳入(Informational Inclusions)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对于不同选项进行社会选择之前必须开展一轮有关不同信息选择的社会选择,而阿罗定理已经预设当事人对于效用信息有了充分的了解,并将这些信息纳入偏好形成和展示的过程之中;最后,森强调,非效用信息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关于特定选项促成效用达成需要何种条件的信息。因此,森主张,为了促成理性的社会选择,扩大并强化选择的信息基础是最为关键的①Amartya K.Sen,“The Informational Basis of Social Choice”,in Kenneth J.Arrow,Amartya K.Sen and Kotaro Suzumura,ed.,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Vol.II,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 B.V.,2010.pp.29-46.。
森关于扩大社会选择信息基础的主张,实际上为公共管理中有关政府施政信息的公开透明性以及公共政策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的相应研究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有关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信息(尤其是政府施政信息)的公开透明性对于冲突解决的重要意义,也得到了足够的描绘②Christopher Hood and David Heald,ed.,Transparency:The Key to Better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但这些描绘多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
(三)选项不受限条件的放松
关于“选项不受限条件”的分析和讨论,是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重心。如前所述,这一条件的设定是价值多元主义的体现。这一条件的严格呈现,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社会情境模拟,这种情境就是“大家都很任性”。显然,在付诸集体决策之时,经常出现的社会情境是大家不会都很任性。因此,放松“选项不受限条件”,即考虑某些类型的选项及偏好出现在社会选择中的各类情形,有助于我们了解基于多数决的民主决策在什么情况下有效。
一种情形是所谓的“单峰偏好”,即针对那些能够沿着单一维度进行排序的选项所形成的偏好。早在1948年,也就是在阿罗提出阿罗定理之前,一位曾专门致力于委员会表决问题研究、后来被誉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学者布莱克(Duncan Black),就发表论文证明了奇数人群就单峰偏好进行集体决策的可能性③Duncan Black,“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6,No.1,1948.pp.23-34.。阿罗在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一书中也单辟一节,详细证明并阐释了布莱克的研究结论④Kenneth J.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2nd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John Wiley & Sons,1963.pp.75-80.。这使得社会选择理论的“不可能世界”中终于有了一点儿“可能性”,让悲观主义的气息淡化了一些。
设想一下,如果表1 中的x、y、z 限定为能够按照左、中、右进行排序的任何选项,那么丙的偏好排序(即右>左>中)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在现实世界中要么不会产生,要么肯定只是极少数人的偏好,最终在集体决策中根本不可能对多数决构成实质性影响。这一逻辑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许多议会民主政治中总会出现左翼、中间、右翼并存的政党结构。其实,在很多非政治性的集体决策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
在这里,单一维度显然可以有很多种。例如,当不同选项可以简化为依照数量多寡、面积大小、代价高低来排列时,集体决策必然可以在参与者为奇数的情况下达成,这一点对于有关公共物品提供的政策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政府对公园面积的规划①Wulf Gaerthner,A Primer in Social Choice Theory,revise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49.,例如上文提及的内地游客香港自由行人数限制,等等。这一发现同时说明了“少数服从多数”作为民主决策规则的优势和劣势,即导致社会冲突的事项如果单一且简单的话,那么民主表决的确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一旦所涉事项具有多维性,那么依然采用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策极有可能是简单粗暴的,不仅无助于冲突解决,而且常常会引发进一步的冲突。
另一种放松“选项不受限条件”的思路是森首先提出的,他称之为“价值观受到约束下的偏好”。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森提出,如果一个社群所有成员能够在集体决策前凝聚一定的共识,即大家都认定某一个选项要么不是最优、要么不是最差、要么不在中间位置,那么简单多数决规则是从个体排序到社会排序的一个必要充分条件②Amartya K.Sen,“A Possibility Theorem on Majority Decisions”,Econometrica,Vol.34,No.2,1966.pp.491-499.。这样定义的条件把单峰偏好和极值限制都囊括进去了,或者说,单峰偏好和极值限制是这一条件的两种特例。森的这一发现将民主可能性的条件彻底澄清了。
无论是单峰偏好还是价值观受到约束下的偏好,无非都暗含着不同程度的偏好同质性。在这里,同质性有可能向两个方向展开,要么趋同,要么趋异。如果一个社群的成员接受或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共的价值观,那么在面对具体的选项时,容易形成相似的偏好类型,自然也就容易做出集体决策。俱乐部(或协会)和用脚投票的理论都描绘了有着同质偏好的社群的形成过程。这表明,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一种制度环境,确保人民能够与志同道合的同伴自由地组成社团,保证社团的活动不对其他社团或其他人造成负的外部性,并且促进不同社团成员之间保持良好的流动性,那么阿罗困境是可以得到避免的③Dennis C.Mueller,Public Choice III,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590.。
森给出的“价值观受到约束”的情形,是以否定句式来表达,包含了很多种社会情境。其中的一种情境可以用正向句式表达,即如果社群所有成员认定某一个选项要么是最优、要么是最差、要么在中间位置,那么根据森给出的可能性定理,这个社群采用简单多数决规则可以从个体排序获得社会排序。森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到,如果一个社会能就某些选项是不是最优或最差,尤其是何种选项为最差,达成多数赞同的意见,甚至达成共识,这对于社会正义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在森的笔下,攻占巴士底狱的巴黎市民、抵制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圣雄甘地、反抗种族歧视的马丁·路德·金,“并不是在追求实现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而是“更希望尽其所能消除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公正”④Amartya K.Sen,The Idea of Just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vii.。
让我们用图解的方式来说明一下森的这一重要思想。表2 展示了一个三人社群对于政府干预饥荒的社会选择问题。一种选项(z)是政府任凭饥荒蔓延而放任不管,这一选项恐怕连昏庸如晋惠帝者也是不赞同的,他的确很想为灾民们做点儿事,只不过其“解决方案”是“何不食肉糜”。因此,即便z 这一选项进入社会排序的考虑之中,那么也会被所有人排在最后一位。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社群的社会选择实际上就是在两个选项之间进行,而两个选项之间多数决必定能促成社会选择,这早在十八世纪就由孔多赛证明了,因此现代社会选择理论也就无需再用数学表达了。例如,x 选项为政府建立救灾应急体系和公共救助体系,y 选项为政府只救灾(赈灾)而不扶贫,支撑两个选项的价值观分别为“救急也救穷”和“救急不救穷”。事实上,将赈灾(y 选项)视为朝廷的责任(即所谓“荒政”),在中华帝国有着悠久的传统⑤[法]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而“救急不救穷”也是为很多中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救急也救穷”的价值观,是人类进入现代之后才逐渐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而在公共政策上体现为救灾与扶贫并举,也是现代世界中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当然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各国政府履行这一职能的能力和效力各有不同。
森公认的最伟大学术成就之一,是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权利保障与饥荒治理的关系进行的杰出研究①[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更为重要的是,森关于价值观受到约束条件下偏好形成以及社会选择可能性的研究,还为后来由著名精神与政治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提出的②Thomas Nage,l“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33,No.2,2005.pp.113-147.、森本人大力弘扬的最低人道主义道德或正义(Minimal Humanitarian Morality or Justice)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理论确认,如果全社会能对何种境况最不能接受达成共识,那么无论是政府进行干预还是社会付出努力以防止最差境况的发生,这就是社会正义的一种体现。森特别强调,他自己倡导的以正义实践现实化为核心的社会选择研究思路,“能让人们更容易明白消除世界上赤裸裸的不公正的重要性,而不是去寻找完美的公正”③Amartya K.Sen,The Idea of Just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1.。

表2 具有一定共识的三人社群在反饥荒问题上的社会选择
无论如何,选项受限的情形,意味着并非坚持彻底的价值多元主义,而是集体成员对特定选项所基于的价值观具有某些特定的看法。当然,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社会选择理论研究者所讨论的选项受限的情形,并非出于个人或少数人独断的结果。无论是特定类型的偏好出现在还是无法出现在社会选择之中,其缘由有可能出自理性的前一轮民主的社会选择,有可能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选择情境,有可能是既定的理性社会习俗使然,也有可能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结论
1998年12 月8 日,阿马蒂亚·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演讲辞中援引了古罗马大诗人贺拉斯(Horace,拉丁语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名言,“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偏好”④Amartya K.Sen,“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Choi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9,No.3,1999.p.349.。偏好的多样性,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在一个经济与社会正在发生转型的国度,不同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价值观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由此产生更大程度的偏好多样性,更是一种新常态。当某些未得到满足的偏好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之时,社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看是否能在适当尊重个体偏好多样性的前提下有效地管控甚至解决社会冲突。
为了管控并解决社会冲突,集体决策是必须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以多数决为核心游戏规则的民主机制并不能有效地带来合适的集体决策。在集体决策上民主的低效,为形形色色的独断偏好留下了巨大的社会空间。例如,即便在很多强悍的地方政府“一把手”因违纪和腐败而锒铛入狱之后,坊间的诸多议论依然对他们曾经的强势领导作风津津乐道。对民主的怀疑甚至藐视,即便是在执政党将“民主”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之后⑤2013年12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其官方解读,可参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员干部学习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民主也并未在不少人的价值观体系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当然,贬低甚至漠视民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绝不仅仅扎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而是如森所说,相当流行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亚洲①[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章。。
然而,个人偏好多样性存在的现实,以及尊重个人多元偏好的社会价值观,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的失灵。即便不是万众一心,理性的集体决策依然有可能达成。以民主低效为由行独断专行之实,绝非社会冲突解决和社会矛盾治理的正道。
实际上,对这一重大问题,社会选择理论在逻辑坚实的发展道路上早已给出了明确的解答。在许多社会选择理论研究者的努力之下,森所憧憬的介入民主事业的学术研究早已结出了累累硕果。即便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以及后续学者给出的数十个不可能性定理,实际上也能为提升民主决策的效力提供正能量:这些理论研究深入挖掘了民主决策低效甚至无效的条件,为我们避免多数人实施简单粗暴的集体决策并漠视少数人的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可贵的是,有许多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阐明了民主决策有效运行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尤其是森本人的研究,从拓展社会选择的信息基础和凝聚社会选择的价值基础两个方面,论证了理性集体决策的可行条件。他的研究成果,澄清了我们在面对社会冲突之时如何能有效运用民主机制达成解决方案。在这方面,与个人选择相关的信息,包括那些影响个人判断并形成其偏好的信息和那些有关个人达成其目标所需条件的信息,是否公开透明,是否能得到理性的充分讨论,是否能得到理性的处理和筛选,对于集体决策的最终形成,并进一步促成社会冲突的解决,尤为重要。
限于篇幅,本文对于社会选择理论的讨论,仅限于其学术大厦的几块基石而已。事实上,社会选择理论大厦中各种美轮美奂而又功能各异的房间,例如权利界定的集体选择、模糊偏好的社会选择、虚假偏好显示的防范、公平与平等机会的提供、补偿与责任的确定,等等,都同社会冲突的治理之道密切相关。总之,社会选择理论理应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社会冲突治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而对于治理之道的理论研究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不是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