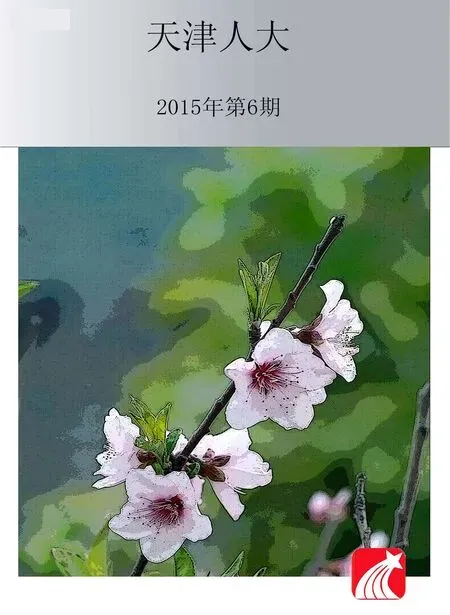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
陈学明 黄力之 吴新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
陈学明 黄力之 吴新文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以文化的地域为理由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的说法屡见不鲜,只是最近一些人对这种说法特别感兴趣。其实一部完整的文化史,既标示出文化的民族差异,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正是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扩张的大背景之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本土的文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中国人栽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长成参天大树?乃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的土地,解决了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本土化转换、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世界影响这一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成功的一个历史成果。而从文化演变的角度看,则是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与扬弃的结果。
1.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的历史必然要求
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屡屡失败于西方,“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此后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人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西方。从总体上说,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呈不断加剧之势。西方既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将中国逼向亡国的边缘。
对这一状态,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描述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可以救中国的先进的文化,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的过程,毛泽东本人早年有一说法,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之《毛泽东传》有如下叙述:
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他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这样回顾道,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在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自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对于“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到1920年,在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后,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毛泽东的选择并非只具个体意义,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走向,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有一公正的论述: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做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看做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针的出路所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变革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也面临着解决外来文化应经过本土化的转换、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国指导思想的过程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外来文化简单植入的问题,而是同样遵循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并非是一个物理过程之发生,而是化学过程之发生,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
为什么会发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呢?这里首先存在文化主体的本土性问题,即在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任何主体都存在自己的本土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在1935年,毛泽东决不是空着脑袋到达陕北的。”他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陕北开创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模式之前,已经有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再往前推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也与其他同时代人一样,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拥护者们的灵魂深处。应该说,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正常而必然的。
当然,如果只讨论文化主体的本土性,那么我们充其量只是研究了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从毛泽东自身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毕竟还是历史的自觉意识之表现。1938 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意识,可追溯到1920年夏天,他在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接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提供解决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的方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运用,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而不能教条主义地搬用。
到了北伐战争期间,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就意识到正确的方法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中国的现实。他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历史已经证明,这就是毛泽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1930年5月,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三十年后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篇文章本来已经散失,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3月11日,毛泽东还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谓教条主义之害,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一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教条主义之发生,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形而上学有关。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时,产生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的倾向,认为西方的思想是绝对新的、好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绝对旧的、落后的,必须无条件地用西方的思想文化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此外也与俄国与中国的实际关系有关。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组织程序上说要接受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指示。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很容易产生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盲目崇拜和遵循,形成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
中共党史的一般说法是,自1934年准备反国民党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开始,毛泽东本人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逐渐被排挤出局,“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给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历史证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不是对他个人的排斥,而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的排斥。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认为,毛泽东在延安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从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而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被称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谦虚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于中国的特定情况。
3.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表述
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表述上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对此提出的中国表述是“实事求是”。他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称“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实事求是”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题,源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本意是指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实践理性精神,经过毛泽东的重新阐释,上升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观、实践的认识论和“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于是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实事求是”中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改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原理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毛泽东深知这是一个与教条主义者争论不清的事情,美国人海伦·斯诺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回顾毛泽东的“中国化”意志,就是毛泽东如何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阐释。这种思维模式,即毛泽东所主张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1944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谈话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系统地形成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不等于完全否认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完美地结合起来。
应该说,经过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常纯熟地掌握了这一文化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始终不脱离中国问题的视野,根据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使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立场:一方面,马克思、列宁这些“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哪里有让13亿人“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的意思呢?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虽然当下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但是人们依然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文献中不断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其生命力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系《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选载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