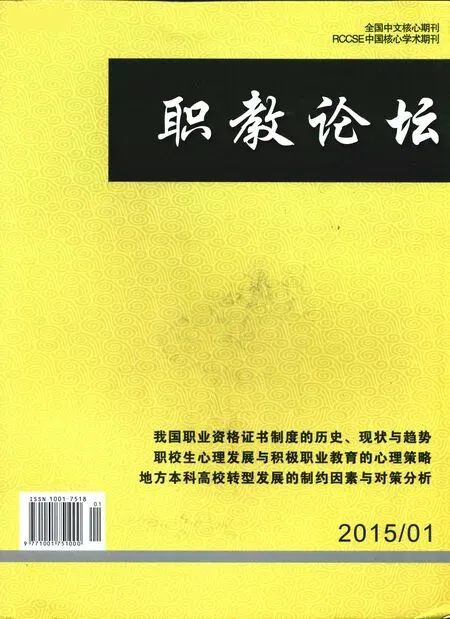学徒制VS学校制——我国商学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李明武
学徒制VS学校制——我国商学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李明武
学徒制是我国早期商学教育的主要形式。清末民初学校教育的兴起对我国商学教育的普及、发展以及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实呼唤商学教育向学徒制模式和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对传统商业学徒制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学校制的基础上探索和建立“现代商业学徒制”。
学徒制;学校教育;商学教育;现代商业学徒制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商学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发展最快的教育类型,而清末民初商学教育从“学徒制”到“学校制”的转变,对我国商学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商学教育模式兴衰、变迁的历史分析,对于现代商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颇有启迪。
一、学徒制——我国早期商学教育的主要形式
(一)我国早期商学教育的历史描述
我国的商学教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商业很不发达,商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传统的学徒制。古时候并无商学的学校教育,商学教育是通过师傅的传帮带,使学徒获得经商技能;二是靠民间流传的一些记载经商之道的商业书籍传播商业知识。在这两种方式中,学徒制是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商学教育模式。
在我国古代工商业发展中,学徒制作为一种职业教育形式广泛存在,被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1]。在封建社会,一般人若要入行经商并获得认可,大多要先到店中当学徒,否则很难在这一行业立足。明清时期“行会”组织的盛行,催生了行会学徒制,学徒经历成为经营工商业资格的重要条件[2]。如史料所述:“商事尚无学堂,必须投入商号学习。故各种商号,皆收徒弟”[3]。由于我国素有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文化传统,商号掌柜的事业继承和经商秘籍的传授,表现出很强的“血缘”、“地缘”特征,行业帮会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号掌柜在录用学徒时,会先选择自己家族的后代或者乡邻,一般人想进入商号学习,必须要一位有名望、有信誉的人保举。如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商帮之一,晋商在录用学徒时就采用严格的“保举制”[4]。当时商业学徒制教育的形式通常是受过一定启蒙教育的学徒,寄居店东家中,由店东提供衣食住行,店徒在跟随资深店员或店东掌柜的经商实践中,靠“前辈”们的言传身教,接受从跑堂、司酒、敬茶等基本商务礼仪训练到记账核算、鉴认金银品色、识别货品真伪和等级等专业培训,乃至商业道德操守的培养。经过一定的培养期(通常是三年),学徒结业后,可被留用或另立分号。如在明清徽商学徒制中,学徒结业被留用,就可升为“伙计”,如果经营有方,还可能进一步提升为 “掌计”(相当于经理)。比如歙县(徽州府治所在地)典商许氏,在江浙一带拥有质库40多所,聘用的掌计、伙计等管理人员将近两千人[5],足见学徒制人才培养方式在当时的商业教育中很盛行。
(二)商业学徒制流行的原因分析
早期商业学徒制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简单、实用,而且有效,符合当时的商业发展需要。入行的学徒“于不知不识之间,逐渐明晰买卖的要务,通晓商品需供之实际,理会商业经营之缓急”。再加上“徒弟与主师,亲若父子,俨然家族,彼此之间,于道艺外,犹多密切感情,其能得圆满之效果”[6];其次是因为当时的商学知识简单、零散,尚不能构成商学体系。“商业规模狭小,组织简单,贩路不出乎一地,市场无模范的经营,内外关系盲然莫察,惟就其局部之事,心会躬行,则已绰有余裕,至科学的研究实非必要”[6];再者是受“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教人如何赢利、如何记录和核算账目的商学,难以作为堂皇的 “学问”而登“大雅之堂”,只能以师徒制方式在民间传承。时人评曰:“中国素来以农业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7];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学徒经历对入行立足和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店东在学徒期不仅传授学徒经商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徒诚信、正直、谦让、吃苦、勤俭的优良品质。如晋商对学徒有非常严格的职业道德教育,学徒 “出班”(意味着学徒生涯结束)要接受各种严格的道德考验。也就是说,学徒期实际上是一个道德教育和人才筛选过程。没有经过学徒期种种能力和道德考验的人,则难以得到业界同行的认可和客户的信任,其职业发展就会举步维艰。
二、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学徒制的衰落
(一)学校制取代学徒制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分析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先后开通了数十个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生。西学东渐之风也冲击着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经济思想,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不仅“技”弱,而且“商”贫,“商为国本”、“商提四民之纲”等重商思潮兴起,晚晴政府也认识到 “商务关乎富强之大计”,并开始实行“恤商惠工”、“振兴商务”的经济政策。而“商战即学战,振兴商务必先兴办商学”也已成为朝野共识。《知新报》1899年的一篇文章认为,西人 “夺我利权,洋货之物,遍于行省,其故何哉”?“盖在学与不学之分”。“西人商务之学,具有专门”[8];商部左参议王清穆也曾上奏朝廷:“洋商之来华者,类皆谙习商法,洞明财政,为各国商业学堂卒业之士。我国商人未当学问,于阜通货贿之义,盈虚消息之机,未能洞悉,彼明此闇,形见绌细,互市数十年动为洋商所持者以此”[9];更有官员指出:“方今为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故商业学校尤为外洋振兴商务之基”[10]。兴办商学成为国家振兴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在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的洗礼中,行商坐贾为主的中国传统商人,逐渐发展为官商、买办,再到洋行大班和民族资本家,基于血缘、地缘和行帮的商业组织形式也转变为近代的公司制。封建商业向资本主义商业的转型需要大量懂得现代商业知识与技能的新式商业从业人员,进一步催生了商业学校教育这种规模化的商业人才培养方式。
从根本上讲,学校制培养方式取代商业学徒制,是近代商业、商学以及商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到了近代,商业组织日益复杂,涉及银行、运输、保险、仓储、海关等诸多部门,时代发展对商人的知识结构与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商业运营、理财核算、组织管理的法则与理论复杂化程度与日俱增,导致了“商学”作为一门“科学”而由此产生。商学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之后,商业教育的内容就从单纯的商业“技能”教育扩展到商业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传统的学徒制下,“洒扫奔走、伺应行礼、服役种种,甚且携涤溺器……综言之,即一奴隶功课而已”[11]。商业学徒制更多的是一种技艺的训练而非原理的学习。而近代商业发展需要的是大量掌握系统的商业知识和理论的新式商人,学校教育是培养这类人才的最好途径。而学徒制模式下,学徒在长年学徒服役期间学到的是一些零星的商业知识和技能,无论是从理论的系统性,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还是从人才培养规模方面来看,这种漫无系统的、分散式的教授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商学教育发展要求。
(二)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发展概略
19世纪后期兴起的商业补习教育,是我国商业学校教育的萌芽状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市场,在与西方商人的经贸交往中,新一代的中国商人必须要熟悉西方商业知识规则,掌握外国语言文字,这种要求显然是传统商业学徒制度所难以达到的。在这一背景下,在上海、广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兴起了一些以教授外语与商务知识为主的书馆、夜校和补习班。比如,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上海出现的各类英文书馆、英语夜校、英语培训班多达36所[12];其教学内容以英语为主,辅以其它的商业知识和技能,主要培养适应涉外经贸发展需要的新型商业人才;学生多为绅商子弟,还有很多商人、买办以及学徒[13]。
大量涌现的各类商业补习学校、培训班等,教育形式周期短,针对性强,见效快,但仍然难以满足社会对新型商业人才、尤其是涉外经营人才的巨大需求。由于社会各界的呼吁,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发展商业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确定的“壬寅学制”中,首次将商学教育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它将普通教育分为六级: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大学预科及高等学堂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年限不定;相应地将商学教育分为简易商业学堂、中学堂的商科和中等商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商科四级。简易商业学堂的学生来自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毕业可成为中学堂的商科生,高等小学堂和简易商业学堂毕业可进入中等商业学堂学习,而高等商业学堂的生源则来自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的商科学生,大学商科的生源来自大学预科。
从清末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到民国的壬子学制、壬子癸丑学制、辛酉学制、壬戌学制,我国的教育体系和学制不断完善,商科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学科门类。壬戌学制将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商业教育最低一级相当于中等教育,商业高等教育则分为专门商业学校和大学商科两类,壬戌学制及其商学教育体系基本被后世所沿袭。
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商业师范教育和商业普及教育,如在实业师范学校内设立商业教员养成科,为中等商业学校培养师资;将商业课列入高等小学、中学教育的随意课,甚至必修课;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商学,如北洋政府1913年颁布的蒙藏学校章程亦规定要学习商法、交通政策、簿记学等课[14]。而学校形态的商业普及教育也很受欢迎,“上海高、初各小学学生,商家子弟居其多数,故所授课程无不参以商业,教以珠算”,上海尚公小学在初小三年级便把商业课列为必修课[14]。
商业学校教育的兴办,一方面是靠政府积极推动,另一方面也靠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晚清政府提出“通商繁盛之区宜设商业学堂”,民国教育部也通令各省民政长,要求各地推广设立商业学校[15]。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就开设“商务”课程,随后又开设江南储才学堂,分农政、交涉、工艺、商务四门,而1904年由商务大臣盛宣怀创建的南洋高等商务学堂,标志着我国商科高等教育的开端。在民间,一些商会组织、教会,甚至商人个人出资兴办学校教育的热情也很高。各地商会纷纷开办商业学校,如天津商务总会创建的中等商业学堂,江西商务总会兴办的商徒启智学校,还有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主办的银行专科及教育学校,苏州经纬业商人也案呈商会,兴建苏省经纬业公立初级小学堂,招收本业子弟及各店学徒[16]。而教会兴商学最著名的当属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是由美国南浸会和北浸会1906年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它的商科在国内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17]。在上海的另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也设有“商业与经济部”[18]。此外,富贾绅商个人发起兴办的商业学校也不少,如1904年汉口商界名流李正源等兴办的商务中等学校,1906年天津商人王永泰发起的民立第一初等商业学堂,1919年无锡荣氏家族企业兴建的公益工商中学等。由此,以学校为场所培养商业人才的“学校制”逐步取代传统的商业学徒制方式,新式企业里有学校教育背景的员工越来越多,上海银行通过自己办的实业学校培训的职员就占到职员总数的一半[15]。
三、商业学校教育兴起的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的商业学校教育发展虽然还十分有限,但它表现出诸多近代教育的特点,是对传统的商学教育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学徒制模式下是个别教学,而且是“工作第一,教学第二”,学徒是在自然的工作过程中随机地学习,教学效率低下。而且到后来师徒关系慢慢“变味”为师傅将学徒当成了廉价劳动力,师徒关系演化为一种带有“剥削”性质的雇佣关系,商业学徒制的教学过程和教学功能被大大弱化。而学校形态的商业教育采取集中、系统的教学方式,无论从教育规模、教学效率、教学的主体地位,还是从传授知识的系统性与先进性方面看,学校制教育方式是传统的商业学徒制所无法企及的。此外,传统的商业学徒制具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师徒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学校教育制度下,师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相比而言,学校教育制度顺应了现代公民意识、平等自由思想的发展潮流。
从商业学徒制向学校制教育方式的转变,开启了商学的大众化教育时代,普及了商学知识,唤醒了全民的商业意识。同时,通过学校教育造就的新式商人,在商业学理、知识结构、思想境界与传统的经验型商人不可同日而语。新一代商人具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其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国际化意识,以及“实业救国”的社会责任感更强。所有这些,对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呼唤现代商业学徒制:学校教育与学徒制的结合
在学校教育诞生以前,商业学徒制一直是商学教育的主要手段,民国时期是我国商业学校教育正式形成和商业学徒制逐渐衰落的过程。但是,商学教育从学徒制走向学校制,只是这个时期商学教育模式转变的方向,并不意味着学徒制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商业学徒制仍然以不同形式保留和发展。在当今我们所提倡的“半工半读”、“校企合作”的模式中,就可以看到古老的商业学徒制中所隐含的实践性教学因子。事实上,这两种教育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
建国后,我国商学教育发展很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教育层次上,商科都是最热门的学科。迅速膨胀的商学教育从规模上基本能满足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但商科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素质却广为用人单位所诟病。在学校教育制度下,商学教育越来越“正规化”和“学科化”,却忽视了商学教育的实践性,单纯的学校培养方式难以消除教育脱离实践的“顽疾”,导致了学校制商学教育与社会实践、与企业的需求相脱节。而古老的商业学徒制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其实践能力培养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是学校教育不能比拟的。现实呼唤着商学教育向学徒制模式回归,但这种回归绝不是对传统商业学徒制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学校制的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商业学徒制”。现代商业学徒制应该是一种综合了传统学徒制和现代学校制优点的新型商学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商科人才的培养由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完成。学校主要负责向学生传授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而职业岗位实践知识与技能则由企业导师进行传、帮、带。在现代商业学徒制中,学徒制如何与正规教育融合,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加强“商”“学”合作,学生(学徒)、教师(师傅)的角色如何定位,……一系列的问题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从传统的商业学徒制到商业学校教育,再到现代商业学徒制,展示了商学教育模式之间的传承关系、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现代商业学徒制都是商学教育面临的新课题,我们期待更多的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出现。
[1]袁福洪.商业教育之理论与实施[M].台北:世界书局,1977:22.
[2]刘晓.我国学徒制发展的历史考略[J].职业技术教育,2011(9):72-75.
[3]彭泽益.中国近代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527.
[4]殷俊玲.晋商学徒制习俗礼仪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73-77.
[5]刘诗能.徽商商业教育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分析[J].职教论坛,2005(4):61-64.
[6]各商会商人应留意商业教育[J].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第3年(1916年)第9,10号合刊.
[7]赵靖.穆藕初文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1.
[8]吴玉伦.商业教育的近代缘起[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09-113.
[9]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169.
[10]虞和平,夏良才.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01.
[11]今日之实业教育[J].中国实业杂志,第7年(1916年)第9期.
[12]熊月之.上海通史·晚清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97.
[13]常国良.买办与中国近代商业教育[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6):45-49.
[14]刘秀生.中国近代商学教育的发展[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4(1):52-56.
[15]严昌洪.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122-129.
[16]赵洪宝.清末商会兴商学活动述论[J].历史档案,1997(1):112-116.
[17]王立诚.沪江大学与近代商科教育[A].近代中国(第六辑)[C].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41-61.
[18]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M].珠海出版社,1999:31.
责任编辑王春桂
李明武(1968-),男,湖北仙桃人,长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贸经济、高等教育。
G719.29
A
1001-7158(2015)01-00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