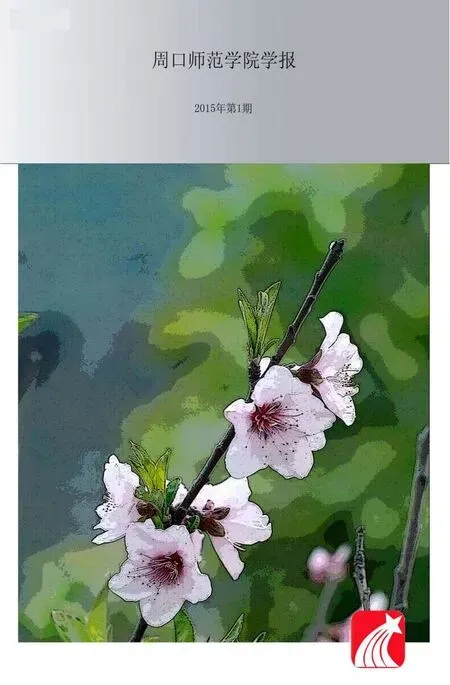走出欲望的迷宫
——墨白长篇小说《欲望》的精神分析式阅读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走出欲望的迷宫
——墨白长篇小说《欲望》的精神分析式阅读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墨白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先锋小说家,一个真正的现代派。在耗费十几年心血完成的扛鼎之作《欲望》中,墨白巧妙地将历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编织进性的叙事和言说中,描述了社会转型期的欲望膨胀所导致的人性的沉沦与蜕变,揭示了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畸形权力格局给个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的精神创伤,并艰难地思索、追寻精神重建的可能和路径。正确解读墨白的欲望叙事对理解他和他的作品至关重要,对此,精神分析学说可为我们提供诸多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墨白;欲望;精神分析;精神成长
作为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墨白的写作一直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他被称为先锋小说家,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现代文学技巧和形式。他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派”,用生命写作,执着地对存在和灵魂进行拷问。阅读墨白的作品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无边的沉重和压抑常常给人梦魇一般的感觉。他总是把笔触深入到历史、社会以及人的心灵的隐秘处,挖掘里面掩藏的阴暗和丑恶。和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样,他也热衷于书写人的非理性的、偏执的、变态的行为和感受,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本人对此并不抱原始主义的态度,而是理性地从社会历史层面找寻根源,艰难而执着地寻找着救赎的希望和路径。
“欲望”可以说一直是墨白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关键词,他对历史、存在、人性的种种追问几乎都依托欲望展开。2012年9月在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墨白谈道:“‘欲望’是一个简单却无比辽阔的词。在词典里对‘欲望’的解释十分简单,其实这个词与我们人类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几乎一切都和欲望有关,可以说现实社会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统领。”[1]1992年,墨白从执教11年的乡村小学调入周口市文联,开始构思宏大的“欲望三部曲”。2013年,墨白的三部各自成章而又在精神和时空上相互承续的长篇小说以一部完整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版,总名为《欲望》,三部小说《裸奔的年代》《欲望和恐惧》《别人的房间》,分别构成了《欲望》的“红卷”“黄卷”“蓝卷”。《欲望》描述了谭渔、吴西玉、黄秋雨三个同一天出生的颍河镇子弟,艰难地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所历经的迷茫、挣扎、苦痛乃至死亡。颍河镇是墨白精心营造的文学家园,是乡土中国的隐喻,但墨白很“残忍”地剥掉了浪漫主义者蒙在乡土故园上的纯洁、质朴和牧歌情调,致力于揭示触目惊心的贫困、苦难、权力运作及其带给人的精神的麻木、愚昧,表现了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谭渔等三人似乎是成功的逃离者,他们体面地进入了城市,然而,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创伤,却使他们在获得城市认同感的过程中极为挣扎,陷入精神的焦虑和痛苦中。
性是这部扛鼎之作的切入点,也是小说叙事的主线。围绕性的叙事和言说,墨白巧妙地将历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编织进来,描述了社会转型期的欲望膨胀导致的人性的沉沦和蜕变,揭示了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畸形权力格局给个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的精神创伤。
一、欲望:动物性本能还是社会的产物
关于欲望,弗洛伊德的解释无疑影响是最大的,他接受了达尔文的生物学立场,把欲望的内核解释为性欲,即人的一种本能的能量和冲动——“力比多”,它不断地产生,不断地寻求释放和满足。对于这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人类想尽种种解数,一方面构建起道德和法律进行约束,另一方面通过艺术、科学等活动对其进行升华,以防止其冲决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秩序和文明。然而,无论是压制还是升华,都不能达到一种理想效果,“力比多”总能冲破种种限制以宣泄自己,或者以扭曲的、变态的方式,或者直接挣脱道德和法律的束缚。对于本能和人性,弗洛伊德的看法是阴郁的、悲观的,他走向了黑暗的霍布斯主义,对社会控制持赞赏态度,而且很遗憾无法达到对本能的绝对控制。所以,悲剧——罪恶或者变态——是无法避免的。很多现代主义文学,致力于书写人性中非理性的狂暴与丑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墨白不否认性在生命中的地位,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曾多次对性的顽强、热辣和粗鄙进行书写,颇有原始主义的色彩。然而,墨白并不把性的欲望看作是本能的、自然的。《蓝卷》中黄秋雨对《手性欲》那幅草图的说明中包含这样的文字,“这是一种临时性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和癌症等疾病一样,只在灰暗无光的房间里传染。那些呼吸纯净空气、吃食简单的野蛮人,从不受它的侵扰”[2]365。
野蛮人有出自本能的性冲动,但没有和人一样的对于性的欲望,可见欲望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卢梭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野蛮人只有自然的性冲动,这种冲动可以在任何一个不加选择的异性身上得到满足,一旦满足,欲望便随之消失。所以,原始人很少受欲念所累,性情温和。人则不同,人的偏爱心、虚荣心等会刺激这种冲动,使之不断膨胀而无法满足。“对异性的爱,同其他欲望一样,是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后才发展到狂热的程度,从而给人类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3]
一生致力于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修正的弗洛姆站在了卢梭的立场上,并对人的欲念的产生进行了更加精辟的阐释。他宣称,人的行为最强大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人的动物性本能,而是来自于人与动物的相异之处——人类独特的生存状况。动物的存在特征在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没有自我意识、死亡意识,如卢梭所言,它的需要不会超出身体的需要。人则不同,“在人具有了理性和想象力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独、隔离、无能和渺小,他的生与死的偶然。他一刻也不能面对这种现实,如果他不能找到与同类的新的联系纽带以代替有本能控制的旧的关系的话。即使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他也会觉得自己像关在孤独与自我的监狱之中,他必须冲出这个监狱才能保留理智的健全”[4]。这样,与他人、世界结合、产生联系的需要,代替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成为人的行动的巨大推动力,成为人的内在的、本源性的需要。显然,这种与他人、世界结合的需要和愿望,本身并不意味着欲望和罪恶,相反,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我们才会产生爱的情感——亲情、爱情、友情,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世界的亲密关系。
弗洛姆进而指出,爱是在保持自身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外在的某人某物的结合,它可以使人获得真正的满足。然而,如果不良的社会环境阻碍人产生爱的情感,那么人就会寻求其他的结合方式以获得满足,比如臣服和统治。臣服是放弃自身的独立和自由与他所臣服的权力合一从而超越个体存在的隔离性,统治则是通过将他人和世界强行纳入自身从而获得这种超越。由于二者都使人变得依附他人——他所臣服的或统治的人,不能给人以自我确定和认同感,因而不能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只会滋生出更多的臣服和统治的需要。这样,与他人及世界结合的需要就会沦为“欲望”,永无餍足。我们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他人和世界,是爱还是欲望,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体,它与社会是否健全有着密切的干系。只有意识到这一层面,我们才能理解墨白对“欲望三部曲”中苦苦挣扎在欲望漩涡中的个体所给予的同情和悲悯,才能对谭渔、黄秋雨等做出正确的评价,才能理解墨白所说的“精神成长”意味着什么。
二、《红卷》:“进入”的艰难与欲望的沉沦
“欲望三部曲”中,《红卷》中谭渔的经历可能最具有普遍意义。一个农村小学教师,靠写作上的成功调进了文联,从而进入城市;之后他爱上了城市知识女性叶秋,为此抛妻弃子,荒唐的是他不仅深藏着对初恋周锦的怀念,还同时与小红、小慧、赵静存在情感上的纠葛;最终由于应对世事的笨拙,他在工作上、情感上都受到挫败,无家可归。看上去似乎是陈世美的现代版本,作者也在行文中对谭渔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讽刺。然而,如果仅止于从婚姻道德上对谭渔进行批判,抨击其炽烈的欲望及其必然带来的灾变,那就远没有把握作品的意旨。
《裸奔的年代》第二部的第一部分,曾先以《进入城市》为题发表过。因为渴盼,才要进入。城乡二元格局给谭渔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使得他们的进入带有一种征服、复仇的畅意感,这注定了他们将来寻求认同的艰难。谭渔第一次去锦城文联改稿时,“像一个讨饭的叫花子立在灰暗的楼道里”;办公室里两个长发女孩对他的注视、讥笑让他感到“无地自容”;掏出车票请求报销的胆怯、寒酸,以及由此遭遇到的不耐烦,都刺激着他那颗敏感的心。强烈的挫败感化作无边无垠的秋雨,“那场弥荡着忧愁凄楚的秋雨在他的感觉里下了好多年,那场浇灌了一颗倔强树苗的秋雨一直在他的感觉里下了许多年”,直到他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了那间使他遭受屈辱的办公室,“那一场落了多年的秋雨突然戛然而止”[2]100。然而,这只是进入城市的第一步,很快谭渔便陷入了新的生存困境: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极为陌生,居然没有一个可通电话的人,他不理解同事汪洋为了钱而放弃文学去搞什么大学生爱情诗集,内心也不能适应官僚主义无处不在的侵扰,贫困依然不时制造点窘迫提醒他自己根在哪里……谭渔发现自己依然没有进入到这个城市的内部,寂寞、孤独、渴望交流的愿望困扰着他。
回头已无可能。“项县之旅”和“周末雪夜步行回家”作为两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宣示了这一点。在“项县之旅”中,得知周锦离开人世,谭渔的心被痛苦撕裂,冒着纷飞的大雪连夜逃离了那里。在另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满怀思念和期待步行几十里回到家中,却在房门上摸到一把铁锁,“那一刻他的心刷的一下仿佛也被铁锁锁住了”。过去的人和地方,都已对他关闭,他只能向前,在城市中寻找认同和归属感。
和叶秋的恋情可以视作谭渔寻求被城市认同的努力,叶秋的优雅、高贵正是城市文明的代表。墨白意味深长地把叶秋的眼睛比作一潭秋水,谭渔这个常在颍河里洗澡的鱼儿更渴望在这潭秋水中游泳,“他知道自己已深深地爱上这潭秋水了,他知道他已经是个不可救药的溺水者了。那秋水清澈透明,却使他探不到底,那潭他望不穿的秋水呀!”[2]96在另一处,墨白以迷宫来隐喻城市:“这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他知道他没法走通这个迷宫,我一个文弱书生一个从乡间赶来的农民的后代,在这座迷宫里最终将被折磨得筋疲力尽。”[2]111谭渔无法走通城市的迷宫,也无法穿透那一潭秋水,进入女人是进入城市的象征。然而,正如谭渔无法从精神上融入城市,他最终也没有真正进入叶秋的世界。
关于谭渔和叶秋之间的感情破裂,墨白交代得很含混。谭渔和小红的“出轨”似乎只是作者的一个叙事上的设置,是为了让叙事进行下去随便找到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就是二人家庭、工作方面的种种牵绊,用这些来解释两个相爱的人的分离也有些牵强。也许二人之间还有更深层的障碍,这些是谭渔本人意识不到,而立足谭渔的内聚焦叙事也不便讲述的。先说说那个行踪诡异的赵静,她和谭渔重访项县时没有见到的一个女同学重名,因而很可能是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巧妙地设置的一个叙事圈套。如果与赵静的交往是谭渔本人的一个幻梦,那么赵静就是谭渔理想中的恋人,她是叶秋和兰草的合体,优雅、浪漫,富于包容和牺牲精神,她对谭渔非常崇拜并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然而,叶秋不是赵静,她深得如一潭秋水,不会对谭渔言听计从,如同这个城市,接纳了他却又不属于他。也就是说,尽管谭渔自认为深爱着叶秋,但依然存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敏感和脆弱使他无法和叶秋建立起一种彼此平等、理解、信赖的深厚情感,因而,当叶秋因调到省城和他暂时分开时,他虽能理解但仍然生出了无限的怨恨和伤感,以致立刻踏上了寻找小慧的旅程。
弗洛姆告诉我们,性的欲望的放纵是克服孤独感的一种方式,但效果并不理想,往往是在纵欲之后他们的孤独感却加剧了,所以不得不更经常地,更强烈地去重复纵欲行为[5]14-15。来自过去的精神重负和创伤使谭渔难以在精神上进入城市,也使他无法真正进入叶秋的世界,当他不能从与叶秋的关系中获得满足而走向小慧时,他已经沉沦在欲望的迷途之中了。以爱的名义寻找小慧,却轻率地和小红发生关系,“爱情的面孔”昭然若揭。或许,这也是他和叶秋关系的真相。
我们不能把谭渔和叶秋的分手归咎于叶秋,在这篇以谭渔为聚焦展开叙事的小说中她是失语的。把责任推给谭渔,指责他咎由自取,也不合适。墨白和谭渔是一代人,他真诚地向我们展示那一代由乡入城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而且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的今天,无数人依然会承受着和谭渔一样的焦灼、孤独和迷失。理解谭渔就是理解我们自己,唯有此我们才有可能清醒地检视我们的时代境况,省察并割除我们的精神固瘤,进而培养起健全的人性。
三、《黄卷》:被欲望笼罩的城市生存图景
和谭渔相比,《黄卷》中吴西玉进入城市的道路要平坦得多:受惠于“文革”平反后调回省城的岳父,他从锦城团市委副书记到省城某高校团委副书记,再到陈州挂职副县长,可谓官运亨通。他比谭渔更深地进入了城市的内部。对谭渔来说,城市是一个令他眩晕的迷宫,他和在他的故事中出场的吴艳灵、雷秀梅等一样生存在城市的外围,代表城市的叶秋、小慧的世界他没有真正进去,赵静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至于汪洋、方圣、二郎等人,代表了让他头破血流的城市生存法则,处于和他对立的一方。而吴西玉则不同,他真正“攻陷”了城市,有着令人艳羡的职位和背景,和他来往的一干同学于天夫、白煦然、钱大用等也都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如果说他的老婆牛文藻还有一半的血统在农村,那么尹琳、杨景环都是“纯正”的城市人。然而,吴西玉的焦虑、迷惘却更甚于谭渔。通过他的视野和感受,一幅为欲望所支配、纷乱颓废的城市生存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吴西玉比谭渔更清晰、更触目地表明,精神创伤是如何影响人格的完整和健全的。当他通过进入杨景环的身体象征性地完成了对城市的复仇时,“那颗仇恨的种子在黑暗之中开花长高,果子结得跟俺爹种的倭瓜一样大,那倭瓜在阳光下放着金子般的光芒,硕大无比!那金色的光芒照花了我的眼睛,使我迷失了方向,在我的眼里,到处都是雨水,雨声四处响起,在幻觉里,我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茫茫雨水里奔走,我知道那个孩子就是我”[2]324。这里没有爱,只有仇恨的种子结出的“倭瓜”,只有丑陋的、令人迷失的欲望。
牛文藻同样深受精神创伤的困扰。极端屈辱的经历扭曲了她的性情,导致了她对性极端的冷淡和仇视。性冷淡是没有能力给予爱的体现[5]29,牛文藻也的确丧失了任何爱的能力,对吴西玉、女儿和她的病人都是。和吴西玉结婚,一方面是应对世俗的压力,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和折磨他以报复自己所遭受的屈辱。人际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沙利文指出,人格是为了适应人际环境而形成的[6]。仇恨使牛文藻成了一个统治者,一个施虐狂,她没有推翻而是延续了那种迫害、欺凌她的权力逻辑。过去是牛文藻的噩梦,现在她是吴西玉的噩梦。悲剧总是一再重演,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那段疯狂的历史,我们依然生存于一个病态的社会之中。不同之处在于,权力收敛了过去那种肆无忌惮的荒诞行迹,以科学、规范和隐蔽的形式继续对人性进行压制和规训。在精神病院里,吴西玉看到,医生只需要对亢奋中的精神病患者盯上一会,他们便会平静下来,目光变得畏缩。“我想他的眼睛里肯定有一种使那几个精神病患者感到恐惧的东西……这和我在看到了牛文藻的目光之后所有的心理反应相同。我和这些精神病患者有什么不同呢?”[2]290这种被注视下的猥琐目光也出现在《蓝卷》中黄秋雨的家属眼中,当时他们面对的是刑警队长方立言。另外,我们这个社会还对金钱格外狂热。金钱和权力扭结在一起,带来的自然是变态的人格、无尽滋长的欲望。
《黄卷》和《红卷》的故事时间大致一致,但二者并非平行关系,在空间和主题上,《黄卷》都对《红卷》作了拓展延伸。对于城市,谭渔由于无法进入其内部,尚能保留一点想象和希望,吴西玉则目睹了其掩盖在华丽外表之后的丑陋和苍白。于天夫、白煦然、钱大用、田达……出场的这些各色人物,都和吴西玉一样迷失在各种各样的欲望之中——权力、金钱、肉体,等等。“……这就是一个女人全部的秘密吗,二十多年来我一心想报复的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吗?她的肉体是那样的丑陋!”[2]325这是杨景环的裸体,也是城市的真实图景的隐喻。谭渔面对迷宫般的城市感到乏力和眩晕,而深入其中的吴西玉感受到的是颓废和绝望。
尹琳这个人物的设置也意味深长地向我们喻示了红黄两卷之间的关系。前面我们谈到,赵静是谭渔的理想,而尹琳是现实中的赵静,她与吴西玉的相识完全是赵静和谭渔的翻版。尹琳性感、浪漫、富有激情,崇拜和包容吴西玉,在性爱方面的表现可谓无与伦比。然而,即便拥有了这个尤物,吴西玉也不能得到解脱。不在尹琳身边,他感到孤独,渴念她的身体;和尹琳在一起的时候,又会感到烦躁和压抑,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个中缘由在于,没有爱情的纵欲是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满足的,尹琳对于吴西玉来说就只是性的对象。尹琳说,“等有一天我不想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2]170,便隐含这一玄机。吴西玉并不真的了解尹琳,他从不关心对方想要什么,因为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在弗洛姆的意义上,他丧失了爱的能力,对于尹琳只有欲望。一切希望和想象都被打破:《红卷》尚能让我们感受到些许红色的激情和渴望,而《黄卷》呈现的只有黄色那令人心悸的焦灼和幻灭。
四、《蓝卷》:房间诗学与精神成长
在《欲望》的后记中,墨白写道:“欲望的力量是强大的。对金钱的欲望,对肉体的欲望,对生存的欲望,欲望像洪水一样冲击着我们,欲望的海洋淹没了人间无数的生命,有的人直到被欲望窒息的那一刻,自我和独立的精神都没有觉醒;而有的人则从‘欲望’的海洋里挣脱出来,看到由人的尊严生长出来的绿色丛林。我称这种因欲望而产生的蜕变为精神重建,或者叫做精神成长。”[2]568在《红卷》和《黄卷》中,谭渔、吴西玉在欲望的海洋中苦苦挣扎,找不到出路,他们没有能力将自己超脱出欲望的支配。直到《蓝卷》,墨白才通过黄秋雨展现出了不同的精神图景,向我们诠释了“精神成长”的含义。
《红卷》和《黄卷》中,谭渔和吴西玉主要是沉溺在自身的失落、焦虑和苦痛中,黄秋雨则不同,他在忍受个体生命中的苦痛的同时还把深邃的目光投向历史、现实和未来,承受起了整个民族的苦难。脑瘤或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是由那些巨大的痛苦凝结而成。他的作品《手的十种语言》的历史部分向我们钩沉出那些正在被遗忘的历史,疯狂的、荒诞的、苦涩的历史。因为遗忘,因为麻木,历史的阴影并没有散去,现实依然为权力和欲望的法则所支配,人的尊严依然无处安放——黄秋雨本人死亡的真相也因此而被掩埋。
历史是一个房间,他人也是一个房间。只有进入历史的隐秘地带,我们才能辨识和切断那来自过去的黑暗之流。只有进入他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才能产生同情、理解和爱。谭渔和吴西玉都只在身体上而没有在精神上进入他人,他们并不真的了解叶秋、尹琳。黄秋雨则不同,他在艺术上致力于探索人的灵魂,对于生命中的女性,他也关心、尊重,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小说给我们展示了米慧、栗楠那么多的书信,是要我们明白:她们从黄秋雨那里获得了爱。弗洛姆说,爱意味着给予,“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他人,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5]30。尽管在婚姻上无能为力,但黄秋雨是有能力给予爱的,他也一直在寻找真正的爱情。如果单纯为了欲望的满足,他不会“铤而走险”选择林桂舒。虽然无法得到世俗认可,但黄秋雨和米慧们的关系绝不肮脏。他们都热爱自由和生命,有着孤独的、纯洁的、超尘绝俗的灵魂。在令人窒息的污浊现实中,这些灵魂一旦相遇,会马上认出对方,爱便不可阻挡地滋生出来,性只是爱的自然延伸。
在现有的道德观念下,为黄秋雨“多姿多彩”的感情生活做辩护只能自讨没趣,谭渔也只能避开其私生活而强调他的艺术追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黄秋雨是一个花心的人,传说中他生活里有无数个女人,可是又有谁知道他是为艺术而献身?其实,从这个意义上,黄秋雨就是个殉道者。……他就是人间苦难的见证者和经历者。”[2]527一个殉道者绝不可能是一个道德败坏者。设想一下,如果黄秋雨和米慧们仅仅在精神上相互依恋和交融,还会有人指责他不忠吗?估计不会。所谓的不忠,原来只是针对肉体。那么,精神和肉体到底孰轻孰重?如果精神上的出轨可以谅解,身体的背叛真的就那么难以容忍吗?我们当然应该同情金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也理解黄秋雨。在这里,存在的困境深刻地揭示出来。
墨白痛心地写道:“我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内心的巨大痛苦,是怎样被我们这些麻木的灵魂所忽视,世界到了黄秋雨这里,彻底呈现出了无限的冷漠。”[2]568显然,墨白是把黄秋雨作为一个理想人物加以塑造的,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和现实,他的痛苦源于他的清醒和深刻,激荡于他生命中的是爱而不是欲望。相对前两卷中谭渔和吴西玉带给我们的迷惘、焦虑、恐惧,黄秋雨让我们感受到深邃、孤独、纯净和安详,这也许是墨白将这一卷命名为《蓝卷》的匠心所在。不能理解黄秋雨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墨白希望,我们能够跟随方立言,进入黄秋雨的“房间”,理解他,认可他,追随他。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欲望的迷宫,走上精神重建之路。
[1]范得.墨白:用记忆为故乡着色[N].文艺报,2012-09-03(1).
[2]墨白.欲望[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3]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8.
[4]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王大庆,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34.
[5]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M].陈祉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1.
I207.4
:A
:1671-9476(2015)01-0034-05
10.13450/j.cnki j.zknu.2015.01.009
2014-05-04
杨文臣(1980-),男,山东兖州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 《印象:我所认识的墨白》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