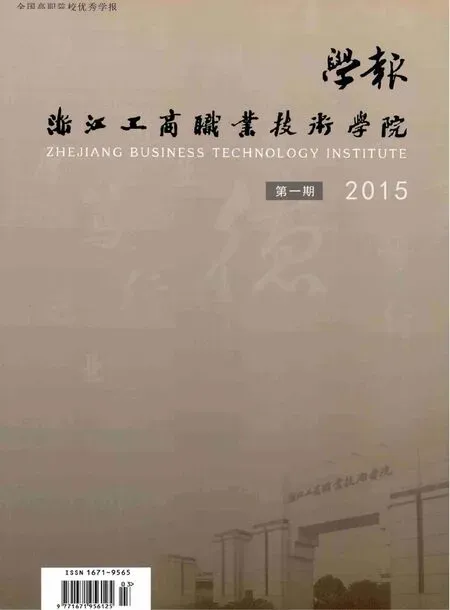《内经》的语言特征及其对翻译的规约
杨勇萍 毛和荣 章程鹏
(湖北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内经》的语言特征及其对翻译的规约
杨勇萍 毛和荣 章程鹏
(湖北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通过从音韵学、文体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与阐释学等角度对《内经》语言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内经》语言具有如下特征:从音韵学视角看,《内经》形成了“散中带韵”的文体风格;表达风格上,《内经》文本具有简洁凝练的突出特点,体现于省略、指代、单音节词的大量使用上;从词义分析角度观之,《内经》的用词表现出灵活独特和善比同异的特征;从语法特征与语言演变的视角看,《内经》具有语言固化的特点,体现在词法上为词类活用的普遍性,表现在句法上为语序倒置的大量使用;从修辞学视角来看,《内经》善用文学手法表达医学内容,使得《内经》文本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学色彩;由阐释学视角考察,“医哲交融”,即医学内容的哲学用语表达,成为《内经》这部医学经典的突出特点。这些都对《内经》的翻译提高了要求,增加了《内经》翻译的难度,导致意译方法成为目前《内经》与中医翻译的主要手段,造成了中医名词术语由于信息密度过大而难以进入现代科学术语体系,使得许多中医名词术语至今难以有规范化、统一性的权威译法。
内经;语言学;中医语言;中医翻译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黄帝内经》(下称《内经》)汇集了中国先人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与医学知识,为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内经》全书言简意赅,风格警秀,为医家千古之绝唱。①班兆贤.《黄帝内经》修辞研究·前言[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5.因此,从语言学视角审视之,作为医学名著的《内经》某种程度上也堪称为一部语言经典。因而,只有从语言学视角对《内经》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内经》文本的深刻内涵。然而,当前学界关于《内经》的语言研究仍相当薄弱,其中钱超尘的专著《内经语言研究》可谓目前研究之翘楚。他从训诂、音韵与语法三个视角对《内经》语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且观点独到深刻,论据有力充分。
《内经》译者李照国指出,“目前中医翻译界之所以仍处于‘各家学说’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医的语言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对中医翻译工作者来说,认真研究和领会中医语言的实质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中医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实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①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31.因此,对《内经》语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深刻地理解《内经》文本,而且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医翻译事业的发展。鉴于此,本文将从音韵学、文体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与阐释学等视角对《内经》语言进行分析解读,以期发现《内经》语言的主要特征。
1 文体风格:散中带韵
从音韵学角度看,《内经》总体而言系一部散文著作。但具体而微地对该书的语言进行分析观察,在以散文体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中,又有许多、甚至是大量的有韵之文。无论是《素问》还是《灵枢》,这一写作特点表现得都极为鲜明。②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228.《内经语言研究》的作者钱超尘认为,在散文体的理论著作里,穿插许多押韵的文句,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表现方法。因为史料说明,在经史诸子之书中,确实存在大量押韵的段落或句子。从先秦到两汉,都保留着这种写作体例。③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231.明末人冯舒曾在《诗纪匡谬》中指出:“《素问》一书,通篇有韵”。 《素问》现存 79篇中,除《宣明五气篇》、《刺齐论》等无韵外,其他大部分篇章都存在韵文,约1500余条。④赵阳,施蕴中.〈素问〉音韵英译研究[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9,(4).因此,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子当中,融合进韵律和谐的韵文,这种散中带韵的行文风格构成了《内经》文本的一个突出特点。
韵是字音的收声。⑤班兆贤.〈黄帝内经〉修辞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10.《内经》的韵分为韵脚与虚字脚两类。韵脚,即入韵字被置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上。这种押韵在《内经》中很普遍,如:
凡刺寒邪曰以温,徐往疾出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也。(《灵枢·刺节真邪》)
《内经》押韵以韵脚为主,《内经》的虚字脚押韵主要是“之字脚”,但不如韵脚那么普遍典型。
《内经》的韵式多变,可分为每句韵、隔句韵、换韵、交错韵等,如隔句韵例:
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上下左右,无有恒常。(《灵枢·邪气脏腑病形》)
音韵的大量使用,使得《内经》经文语音和谐悦耳,增加了经文的美感与表现力。此外,《内经》还选用了许多双声、叠韵字以及叠字,从而使经文显得音调和谐,朗朗上口,极大增强了经文的音乐美与表现力。如下例:
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此例中,“阴阳”双声词与“居处”叠韵词连用。
需要指出的是,“散中带韵”的特征,虽增加了《内经》文本的表现力与可读性,但对《内经》的翻译无疑也提高了要求,增加了《内经》翻译的难度。音韵因素,即大量韵文在《内经》的存在,暗示我们在翻译《内经》文本时要适时从音韵学的视角来审查、推敲、润色所翻译的内容,尽可能地使文意传达的忠实与原文语音的保留和谐地融为一体。
2 表达风格:简洁凝练
从表达风格角度看,《内经》行文具有简洁凝练的典型特征。唐代医者王冰的《素问序》认为:“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朱震亨的《格致余论序》认为:“《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 ”①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217.这种词简义深的凝练文风一方面使得《内经》行文精炼,字字珠玑,另一方面也使其变得艰深难懂,甚至模糊歧义。这种简洁凝练的文风主要体现在省略、指代、单音节词在《内经》中的大量使用上。
2.1 省略的运用
省略既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法,也是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为了使文章精炼,古代学者在行文时常常删繁去冗,保存精华,力求以较少的文字表达较多的内容。《内经》在论述深奥医理时,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情况下,为使表达更加简练有力,省略了某些词、句乃至文意。其省略的情况较为多见,也较为复杂,几乎任何结构成分都有因上下文而省略的现象。②沙涛,刘维庆.《黄帝内经》中之省略例析[J].中医函授通讯,1994,(4).王治梅的硕士学位论文《阐释学视角下〈黄帝内经〉省略辞格的英译研究》通过标注检索,从《内经》汉语文本中统计出《内经》前34章中运用省略的频次有997次。其中,省略主语的有667次,约占 66.9%;省略谓语有 36次,约占 3.6%;省略定语有151次,约占15.1%;省略状语有21次,约占2.1%;省略连词有 122次,约占 12.2%。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主语的省略在《内经》中非常普遍,定语和连词的省略也占了很大的比重。③王治梅.阐释学视角下〈黄帝内经〉省略辞格的英译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8.如主语的省略:“肝气虚则恐,( )实则怒。 ”(《灵枢·本神》)本句承前省略了主语“肝气”。又如:“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素问·经脉别论》)本句中承上文的宾语 “精”、“肺”,省略了下文的主语“精”、“肺”。 再如连词的省略:“寒伤形,热伤气。 气伤( )痛,形伤( )肿。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本句中“痛”和“肿”的前面分别省略了连词“则”。除了主语、谓语、宾语、介词等各种句子成分的省略外,动词与形容词、数词的名物化也是一种语法上的省略。无论是语法还是修辞上的省略,都使《内经》的行文简洁凝练、言简意赅,使汉语表达的信息密度大大增加,但无疑给《内经》英译陡增障碍。
2.2 指代的运用
《内经》中代词的使用不仅普遍,而且丰富。古代汉语中的三类代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与疑问代词——在《内经》中均有使用。《内经》中第一人称代词主要使用“余”,在《素问》中共出现65次,且主要用作主语。④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374,376.第二人称代词只使用“汝”和“若”,如:“汝受术诵书。”(《素问·示从容论》)第三人称主要有“之”和“其”,使用极其频繁:“之” 在《素问》中共出现2586次⑤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382,378,383,397,401,192.,作句中主语;“其”在《素问》中共出现1684次,作句中定语。如:“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又如:“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素问·五藏别论》)近指代词常用的有“此”和“是”等。其中,“此” 在《素问》中共出现 314次,“是”在《素问》中共出现221次,均作为近指代词使用。如:“是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不治已病治未病,此之谓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远指代词有“彼”和“夫”。疑问代词有“何”与“安”等,其中“何”字使用频率相当高,在《素问》中共出现487次,作宾语、定语、谓语或状语。如作谓语:“人饮酒,酒亦入胃,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何也?”(《灵枢·营卫生会》)又如作状语:“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另外,《内经》中还使用有虚指代词“或”,无指代词“莫”,以及特殊指示代词“者”和“所”。 其中,“者”字在《素问》中共出现1469次,用于组成名词性词组。如:“静者为阴。 ”(《素问·阴阳别论》)“所”字在《素问》中共出现578次,主要用作指示代词。如:“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素问·宝命全形论》)《内经·素问》 全书仅约 78000 字,“之”、“其”、“此”、“是”、“何”、“者”和“所”使用频次却分别高达3.3%、2.2%、0.4%、0.3%、0.6%、1.9%、0.7%。这说明代词在《内经》中的使用极其频繁,指代在《内经》中得以广泛运用,从而无形中造就了《内经》简洁凝练的语言风格。
除了省略与指代的大量运用外,单音节词的大量使用也是形成《内经》简练文风的重要因素。如同先秦两汉其他典籍,《内经》中单音词占绝大多数,合成词使用较少,而且合成词又以双音合成词为主,两个以上音节构成的合成词极少。这同现代汉语中以合成词为主的词汇使用特征迥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简洁凝练的行文风格,虽使《内经》惜墨如金,字字珠玑,但信息密度过大无疑增加了《内经》翻译的难度,导致意译方法成为《内经》翻译的主要手段。意译方法侧重于医理的传达,而将原文的形式置于次要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内经》的凝练,造成了中医名词术语由于信息密度过大而难以进入现代科学术语体系。这也是许多中医名词术语至今难以有规范化、统一性的权威译法的内在因缘。
3 用词特点:灵活独特、善比同异
从词义分析视角来看,《内经》的用词表现出灵活独特和善比同异的特征。一方面,《内经》的词义引申具有因医学语境而产生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内经》善用同义词与反义词进行医理阐释。
3.1 灵活独特
钱超尘认为,内经之所以难读,词语艰深是最大障碍。①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215,218,222,226-227.他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著作的词汇,在特定语言环境的制约下,词义引申有时与中国古代文史著作不同,因而正由于《内经》词义引申的多样化以及它的某些引申义的特殊性,才使得《内经》的词语语义艰深难懂。如“内”字,除了作“里面”的普通意义外,它还可在不同语境中指 “向内”、“体内”、“房事”、“接纳”、“进针”等。 如以下例:
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引申为“向内”)
②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素问·移精变气论》)(引申为“体内”)
③治病之道,气内为宝。(《素问·疏五过论》)(通“纳”,意为“接纳”)
又如“其”字,除了用作人称代词外,还用作指示代词,意为“那”、“那里的”、“其中的”等。 一段话里可以出现几个“其”字,有时指代不同,如下例:“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灵枢·五变》)此句中,第一个“其”意为“那些”,第一个“其”意为“其中的”。
上述两字的分析表明,《内经》词义的引申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特殊性。钱超尘认为,《内经》的不少词义都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引申出来的。这些引申义,在医书中的使用,绝不是孤证,而带有普通性。
3.2 善比同异
作为一部自然科学著作,《内经》需要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作出尽可能明确、详细地说明,并要求分辨出疾病细微的差别。因而,《内经》中同义词的使用相当频繁,而且注意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如下例: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 (《素问·方盛衰论》)此句中,“净”同“静”。“清”与“净”,“神”与“明”,为同义关系。 其他如:征—兆、寥—廓、肇—基、变—化、流—行、魂—魄、津—液、盛—满、懈—惰、空—穴、糟—粕、移—易、分—别、调—和、坚—固、暴—烈、机—关、存—在、端—直、均—等、迷—惑、愠—怒、稀—疏、视—察、长—久、旗—帜、闭—塞等。①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208页.
另一方面,作为说理性文体著作,《内经》使用了相当多的反义词,且以单音节反义词居多。王波利的硕士论文 《〈黄帝内经·素问〉单音节反义词研究》通过对《内经·素问》文本的研究,认为构成反义词关系的单音节实词一共396个,分为198组,数量相对丰富,约占全书总字数的千分之2.5。从词性角度来看,名词41对,占总数的20.7%;动词68对,占总数的 34.5%;形容词 89对,占总数的 44.8%。从各类反义词所占的比重来看,形容词所占比重最大,动词次之,名词最少。②王波利.《〈黄帝内经·素问〉单音节反义词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9页.钱超尘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这基本上符合了先秦古汉语词汇的特点,正如蒋绍愚、何九盈统计的五部先秦典籍中的反义词所得出的结论:“从词性看,形容词最多,动词次之,名词又次之”。③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81页.《内经·素问》经常对举的高频率反义词如下:
标-本(65次) 表-里(33次) 长-短(26次)
沉-浮(32次) 得-失(21次) 肥-瘦(11次)
俯-仰(10次) 高-下(40次) 贵-贱(14次)
寒-热(274次) 寒-温(35次) 厚-薄(36次)
呼-吸(13次) 君-臣(10次) 急-缓(29次)
静-动(20次) 苦-乐(10次) 来-去(14次)
来-往(30次) 前-后(35次) 浅-深(36次)
屈-伸(22次) 日-月(20次) 入-出(33次)
塞-通(10次) 善-恶(12次) 涩-滑(30次)
上-下(381次) 少-多(105次) 升-降(31次)
盛-衰(43次) 盛-虚(44次) 实-虚(161次)
水-火(19次) 顺-逆(48次) 死-生(77次)
寿-夭(17次) 天-地(255次) 外-内(160次)
无-有(26次) 喜-怒(26次) 小-大(134次)
先-后(91次) 徐-疾(26次) 阳-阴(621次)
易-难(13次) 异-同(27次) 远-近(27次)
终-始(64次) 中-外(17次) 昼-夜(13次)
主-客(14次) 浊-清(38次) 左-右(157次)
泻-补(118 次)④王波利.《黄帝内经·素问》单音节反义词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34.
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这些出现频率高的反义词,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上仍然是常用反义词。这就是说在西汉初期常用反义词基本上传承为现代汉语的常用反义词。这说明了汉语词汇的稳定性与继承性。
《内经》文本用词的灵活独特,启示我们在翻译《内经》时要“循文定意”,即依据具体语境理解文句,进而选择合适之词传达原意。选词上的善比同异,体现了《内经》作为说理性著作的文体特征,也体现了《内经》在阐述医理时受到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思维影响的痕迹。这对于我们理解《内经》文本的某些难句与用词,进而选择更合适的对应词进行翻译有重要启示。
4 语法特征:语言固化
《内经》译者李照国认为,自《黄帝内经》问世以来,中医学从理论到语言都被钦定了。从那时到现在千百年过去了,中医语言基本上旧颜未改。这部分是由于文言文的使用造成的。⑤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17-18.我国的文言文系统,是以先秦语言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后人在写作中努力模仿先秦古书的词汇和语法,因此以先秦书面语言为基础的语法特点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相沿不衰。①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360,185,348.因而,成书于先秦两汉的《内经》,其词汇为中国后代医书的词汇奠定了基础。从语言演变的视角来看,《内经》确立了中医语言的典范,奠定了中医语言的基础,从而使中医语言固化为一种特有的专门用途语言,成为中医学特有的一种思想表达形式。《内经》语言固化的特征在词法上表现为词类活用,在句法上表现为语序倒置:宾语前置和定语后置。
词类活用属于语法范畴的词法现象,包括动词与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与动词作状语,名词与形容词用作动词,动词的被动用法,数词的使动用法等类型。钱超尘认为,在《内经》里,词类活用以名词用作动词、名词作状语、动词与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较普遍。名词用作动词如下例:
灸之则瘖,石之则狂。(《素问·腹中论》)
“灸”与“石”,本属名词,此处均用作动词,后面带有宾语“之”,意为:“用针灸治”,“用砭石刺”。
名词作状语可表示比喻、工具、处所等。如下例:
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素问·离合真邪论》)
“波”与“陇”均为名词,此处用作状语,分别修饰后面的动词“涌”和“起”。
《内经》中,动词的使动用法主要由不及物动词来承担。如下例:
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灵枢·痈疽》)
此处第一个“腐”字意为“使腐烂”,属使动用法。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如:
上焦开发,宣五谷味,薰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 (《灵枢·决气》)
“薰”、“充”、“泽”,本为形容词,此句中均用作动词,意为:“温煦”、“充实”、“润泽”。
有学者认为,词类活用现象具有语法与修辞的双重意义,其修辞作用就是使语言表达 “新奇简炼”、“意味无穷”。②于仪农.医古文修辞与语法关系举要[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6).词类活用不仅可以高度浓缩语义,还可以使语言表达形象生动,如:“一以参详,群疑冰释。 ”(《素问·王冰序》)此处一个“冰”字就使释疑的过程形象易解了。
古汉语中有少数特殊的词序是现代汉语所没有的。这些特殊词序是先秦时期口语中的常规形式,但汉代以后就逐渐从口语中消失了,然而《内经》中却保留了这些特殊词序,如宾语前置和定语后置。宾语前置主要包括疑问代词作宾语、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代词复指等情形。③徐珊.谈《内经》中的特殊词序——三种宾语前置句式[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4,(4).
①疑问代词作宾语,常放在动词或介词之前。例如: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何谓也?(《灵枢·营卫生会》)此处疑问代词“何”须置于谓语动词“谓”之前。
②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可放在动词前面,特别常见于“不”、“未”、“毋”、“莫”修饰的否定句中。如:神有余则写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素问·调经论》)此处作宾语的代词“之”被置于谓语动词“斥”之前。
③代词复指的凝固格式“此之谓”,起强调宾语作用。例如:“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谓也”。(《素问·离合真邪论》)
为了强调宾语,《内经》有时会把定语修饰语放在名词中心语之后,从而形成定语后置的特殊语序。如:脉之见者,皆络脉也。(《灵枢·经脉》)古汉语的定语后置一般的标记为:中心词后都有助词“之”字,定语后面都有“者”字。其中,助词“之”字可以省略,但“者”字则极少省略。④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357.再如:以流水千里之外者八升,扬之万遍。(《灵枢·邪客》)
《内经》语言固化的特征,昭示现代中医译者必须精通中国古代的文言文表达系统,特别是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的医古文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内经》文本的深刻内涵,进而使我们的目标语言表达更为精确、传神。
5 修辞风格:文学表达
《内经》既是一部医学经典,又是一部语言巨著,其突出特点就是在阐述深奥医理时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因此,《内经》成为中国古代医籍中运用修辞的典范。多元化修辞格的运用,不仅使其语言表达生动形象,而且恰当地呈现出中国文化“医文互通、医文互用”的独特风格。①杜福荣,张斌,王治梅.《内经》常见句式变化修辞格英译[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0,(10).《内经》使用的修辞格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大,以更好地阐述医理为目的。比喻、借代、互文、错综、避复、省略等40余种医古文修辞手段在《内经》中均得到了运用。②赵阳,施蕴中.《内经》修辞格及英译实例分析[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9,(5).班兆贤先生所著的《〈黄帝内经〉修辞研究》作为一部专门研究《内经》修辞的论著则阐述了《内经》中所运用的25种常见修辞方式。他将这25中修辞格分为五大类:形象生动的辞格——比喻、比拟、借代、摹状、示现,整齐醇美的辞格——对偶、排比、层递、反复、对照,婉转流畅的辞格——联珠、合叙、错综、避复、回环,精警夸饰的辞格——警策、夸张、引用、自释、讳饰,以及简约明快的辞格——省略、设问、复用、举隅、互文。③班兆贤.《黄帝内经》修辞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目录.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常见修辞格有比喻、借代、摹状、对偶、排比、反复、对照、联珠、错综、避复、引用、讳饰、省略、设问。
比喻辞格如: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之谓也。 (《灵枢·营卫生会》)此句中,“雾”、“沤”、“渎”分别喻指人体三焦。
借代辞格如: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 (《素问·上古天真论》)此句中,“春秋”指代年,即年岁。
对偶辞格如: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素问·六节藏象论》)此句中,“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为对偶中的正对。
排比辞格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灵枢·营卫生会》)此处,排比句“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构成“阴阳者”的谓语。
对照辞格如:得守者生,失守者死。(《素问·脉要精微论》)此处,“得守者”与“失守者”构成对比。
联珠辞格如: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酸伤筋,辛胜酸。(《素问·五运行大论》)
错综辞格如:厥阴有余,病阴痺;不足,病生热痺。(《素问·四时刺逆从论》)释义:厥阴之气有余,可以发生阴痹;不足则发生热痹。此为错综之错名。
回环辞格如: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此处,前句中的“寒”、“热”在后句中易位为“热”、“寒”,从而构成回环。
讳饰辞格如: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为何也?(《素问·奇病论》)此句中,“重身”讳饰怀孕。
互文辞格如:调其虚实,和其顺逆。(《素问·痿论篇》)释义:调和机体之虚实,调和气血之顺逆。此处,“调”与“和”构成互文关系。
多元辞格的广泛使用,使得《内经》文本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学色彩。由于华夏民族的崇古心态,作为中医经典与滥觞的《内经》,使得文学化的表达成为后世中医语言风格的一大特点。显然,在阐释深奥抽象的医学理论时,多种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能够使话语表达具体化、形象化,从而方便读者理解。但文学化表达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在增强话语表现力、阐释生动性、易理解性的同时,话语表达的准确性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因而,多种文学修辞手段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内经》及中医学的语言表达与基本术语的模糊性、歧义性、非规范性等弊端。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显然,这对《内经》的现代传译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这也是造成当前中医翻译界关于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等翻译方法诸多争论的重要原因。
6 内容表达:医哲交融
中国古典哲学巨著《周易》充分展现了先秦时代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周易》所阐述理论的巨大影响,作为后世中医经典的《内经》不可避免地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受到了《周易》理论的深刻影响。明代医者张介宾由此提出了“医易同源说”。他在《类经附翼》中明确指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①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99,105,100,101.“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艾,咸寓尊生之心鉴。”②兴旺.中药如何克服文化障碍进入欧美市场[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20.因此,他认为《周易》为研究医学之指南,医理存乎《易》理中。基于这种认识,他用《周易》解释《内经》,并进而指导医学理论的研究。唐代医者王冰也深知医《易》相关之理,在注解《内经·素问》时亦常援引《周易》的理论来解释《素问》之医理。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阴阳合,故能有子。 ”王冰《素问》注曰:“《易·系辞》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之谓也。”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王冰注曰:“《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内经》以《易》理阐释医理在其《天元纪大论》一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璇。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生,品物咸章。”这段话中的很多词句,源于《周易》的乾卦与坤卦。乾卦《彖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坤卦《彖辞》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畺,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再如:“气”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被中国古代哲学家用来说明世界的本质。而作为中医经典的《内经》使用“气”字则高达近三千次,“气”的涵义也由此变得十分复杂。③龙桂珍.中医英语的文化体现与遗漏[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总体来说,“气”在《内经》中是一个说明人体生命现象的概念,它既保留有古典哲学“气”之范畴的基本内涵,又具有医学语境的特殊含义。
由于《内经》的理论建构受到以《周易》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巨大影响,大量的哲学用语于是被输入到《内经》的语言体系中,用以表达中医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范畴。随着《内经》医学经典地位的确立,这些哲学用语逐渐成为中医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华夏民族的崇古心态与文言文千年绵亘的使用,《内经》最终钦定了中医的语言体系。源自先秦古典哲学的大量用语也随之成为中医语言系统的基本成分。因此,“医哲交融”,即医学内容的哲学用语表达,成为《内经》这部医学经典的突出特征。大量哲学用语用于医学内容的表达,一方面丰富了中医语言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哲学语言的抽象与模糊性,使得中医语言变得模凌两可、晦涩难懂,成为中医学基本概念歧义性的历史根源。④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4.中医术语的歧义性与模糊性,使中医语言具有强烈的人文学科色彩,无形中给中医译者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给目标读者增加了理解的障碍。不过,“医哲交融”的特征,也启示我们在翻译《内经》与中医著作时要注意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刻影响。当然,如何规避“医哲交融”带给中医翻译的困境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7 结语
通过从音韵学、文体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与阐释学等角度对《内经》语言的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内经》语言具有如下特征:(1)从音韵学视角看,《内经》形成了“散中带韵”的文体风格。音韵的大量使用,增强了《内经》文本的可读性与文字的表现力。(2)从表达风格角度看,《内经》文本具有简洁凝练的突出特点。“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①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217.集中体现于省略、指代、单音节词的大量使用上。(3)从词义分析角度来看,《内经》的用词表现出灵活独特和善比同异的特征。一方面,《内经》的词义引申具有因医学语境而产生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内经》善用同义词与反义词进行医理阐释。(4)从语法特征与语言演变的视角看,《内经》具有语言固化的特征,体现在词法上为词类活用的普遍性,表现在句法上为语序倒置的大量使用。(5)从修辞学视角来看,《内经》善用文学手法表达医学内容,即在阐述医学理论时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方法。多元辞格的广泛使用,使得《内经》文本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学色彩。(6)从阐释学视角来看,由于《内经》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受到以《周易》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巨大影响,大量的古典哲学用语得以进入《内经》的语言体系中。因此,“医哲交融”,即医学内容的哲学用语表达,成为《内经》这部医学经典的突出特征。
毫无疑问,《内经》语言的这六大特征对《内经》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显然,大量韵文的存在、简洁凝练的文风、多元辞格的广泛使用、古典哲学的巨大影响,都对《内经》的翻译提高了要求,增加了《内经》翻译的难度,导致意译方法成为目前《内经》与中医翻译的主要手段,造成了中医名词术语由于信息密度过大而难以进入现代科学术语体系,使得许多中医名词术语至今难以有规范化、统一性的权威译法。《内经》用词的灵活独特,要求《内经》翻译要“循文定意”,即依据具体语境理解原文文句,进而选择合适的词语传达原意。《内经》语言固化的特征,昭示现代中医译者必须精通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的医古文体系,从而使我们的目标语言表达更为精确、传神。
[1]徐珊.谈《内经》中的特殊词序——三种宾语前置句式[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4,(4).
[2]沙涛,刘维庆.《黄帝内经》中之省略例析[J].中医函授通讯,1994,(4).
[3]于仪农.医古文修辞与语法关系举要[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6).
[4]赵阳,施蕴中.《素问》韵英译研究[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9,(4).
[5]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6]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7]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8]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9]姚春鹏.黄帝内经(第1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班兆贤.《黄帝内经》修辞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黄素华】
The Impact of Inner Canon’s Language Feature on its Translation
YANG Yong-pingMAO He-rongZHANG Cheng-peng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Wuhan 430065,China)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Inner Canon’s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onology,stylistics, lexicology, grammar, rhetoric and hermeneutics, to find that it has a variety of features.Various language features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in producing a good English version so that free translation is widely used,thu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a standardized and authoritative English ver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erms.
inner canon of Huangdi; linguistic;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Chinese medicine translation
H159
A
1671-9565(2015)01-080-09
2015-02-28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中医语言的特征及其对中医翻译的规约”(编号13q073)的最终研究成果。
杨勇萍(1982-),男,河南商城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化、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等方面研究;毛和荣(1979-),男,江西上饶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北中医药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与中医英语翻译方面研究;章程鹏(1980-),男,湖北黄冈人,研究生,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医养生康复学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