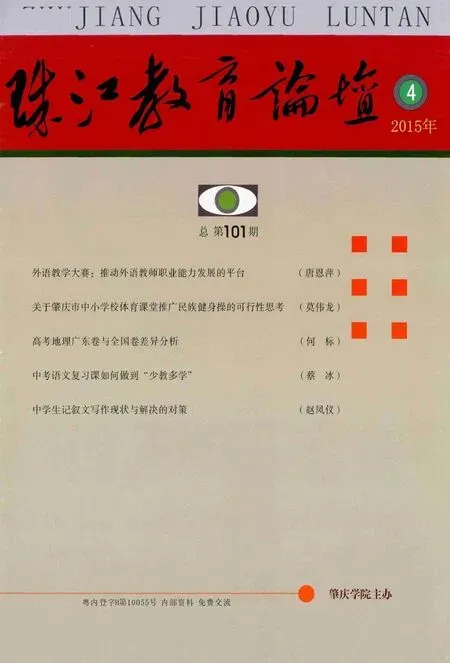现当代文学中的青春叛逆形象比较分析
——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家》《白鹿原》为例
周红枚
(三板小学,广东 珠海 519090)
“五四”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身心得到解放。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等思潮与观念深入作家心灵,小说创作中开始出现叛逆主题,这些作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深化了对青春叛逆问题的思考。
一、青春叛逆主题的出现
历史条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帝制余孽、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存在。
经济条件:沿海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民族工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为文学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文学条件:文学作为政治改良、社会革命的工具,这一文学观念在近现代时期得到广泛认同。适应当时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新青年》出现,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阵地,其聚集起众多作家和作品,促进了文学活动的繁荣。叛逆主题与叛逆形象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
二、青春叛逆的三种艺术典型
(一)黎明前的绝叫者
莎菲,被茅盾评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
她在一个“真找不出一件令人不生厌心的”环境里生活,以一个叛逆苦闷的现代青年女性的姿态出现,蔑视封建礼教,追求真正爱情和自我个性解放,性情孤傲怪癖,内心却充满狂热的幻想。大革命失败,她思考生活,发现自己与黑暗环境格格不入。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只是男性的附属品,缺少独立地位,更鲜有勇敢追求爱情者。《红楼梦》中,林黛玉追求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莎菲需要的是精神与肉体完美统一的爱情,她说:“如若不懂我,那我要那些爱和那些体贴做什么”。她知道自己不爱苇弟,甚至不喜欢苇弟对她百依百顺得软弱无能,她仅仅拿他当弟弟,“我相信在我的平日一举一动中,我都很能表现出我的态度来。为什么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呢?难道我能直接地说明和阻止他的爱吗?”莎菲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和爱情,苇弟对她再好,她也不会因为同情而和苇弟在一起,更不会因为苇弟的感情而困住自己。她敢于拒绝不适合自己的爱。凌吉士的出现,搅乱莎菲的心。“他那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可以诱惑许多爱美的女子,并以他那娇贵的态度倾倒那些还有情爱的。”她的心时时想着凌吉士,“难道我能说得上是爱上那个南洋人了吗?”她在反复的纠结后,大胆地向心仪的人吐露心声,这一举动对身边的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这正体现了莎菲的叛逆倾向。在与凌吉士交往后,她发现凌吉士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灵魂如此不堪!她离开了。她痛苦地告诉自己:“人生这玩艺儿,而心灰而又想到死;至于痛恨到自己敢于堕落,所招来的,只是最轻的惩罚。”莎菲,为了寻觅人生的意义,寻求自己的纯洁爱情,鄙视世俗,这个过程是不被周围人所理解的,其孤独的心灵倍受折磨。她不会因为朋友的劝说而改变自己的爱情观、人生观,她宁愿被当成一个叛逆人,也不愿意去随大流。“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我清清楚楚的”,由此可以看出,莎菲重视的是比爱情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那就是精神的结合,思想的融合。这也是历史投射在一部分知识青年身上的影子。
(二)晨曦中的觉醒者
16岁的觉慧是高家大院的第三代,高老爷宠爱,觉新大哥抵挡封建礼教的第一股强波,和觉新相比,觉慧虽有高家少爷的身份,却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一旦接受新思潮的冲击,就有胆量放手去反抗。作为高家的少爷,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家庭给予的一切。相反,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习新知识,对自己的家庭产生质疑,感到家庭的腐朽,家人的懦弱。在高家,他就是一个另类!可贵的是,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尽管遭到家族势力的压制、亲人的呵斥,仍然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对未来充满希望。
高老爷的病情不见好转,陈姨太和克明三兄弟请道士来家里驱鬼,兄弟姊妹知道这是无用之举,但都只有顺从,唯有觉慧站出来说:“哪个敢进我的房间,我就给他一个嘴巴,我不怕你们!”由此可以看出觉慧对封建思想的抵触。可以说,他是封建家庭坚决的叛逆者,坚持自己的理念,用行动反抗封建行为,这就是叛逆者的精神!无论面对多大阻碍,都坚定自己的信念。面对大哥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他坚决反对;面对家庭的一出出悲剧——大哥不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在“孝”的枷锁下,牺牲自己和身边的瑞珏、梅表姐,梅表姐遇人不淑,嫂子因为封建礼教血光之灾的说法去郊外难产而死,自己心仪的鸣凤投湖自尽——他痛苦不堪,态度更加坚决,喊出自己内心的愤怒:“这个家,我不能住下去了!”看清社会的混乱、家庭的狰狞,他萌生离开家的想法,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为自己寻一条出路,并劝说家里的兄弟姊妹,一定要站起来反抗,不要为了封建礼教而委曲求全。觉新曾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里,就只能做牺牲者的资格”,而觉慧则说:“如果牺牲是必须的话,做牺牲品绝不是我。”[2]189他深知反抗这条路是艰辛的,每走一步都是荆棘,会流血,他还是离开高家大院,走进上海,接受新世界的挑战,寻求自己理想的生活。觉慧,一个敢于走出封建大家庭、不为物质所迷惑的少爷,思想上比莎菲更丰富的叛逆出走者。
(三)夕阳下的叛逆者
田小娥,“她是一个在众人眼中没有生存权利的人”[3]72。命运面前她无路可逃,但她也并不是一味顺从,当她把泡枣放在尿盆里时,她的叛逆心理已经露出了端倪。遇见黑娃,她内心涌起骚动,不为郭举人家的物质所动,向短工黑娃示爱,她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愿意。”仁义村,一个被儒家思想包裹的村庄怎么能容得下他们这点卑微的要求。她不气馁,不怕苦,不怕累,与黑娃在村外的窑洞里住下。这是她叛逆的第一个高潮。后来,黑娃参加农民运动,失败了,给田小娥带来巨大的灾难。生存,人的本能需求,在鹿子霖的诱奸下,也出于对当时白嘉轩不准她进祠堂侮辱她的报复,开始第二次反抗,引诱白孝文,后来演变为两情相悦,所以当她看到白嘉轩晕倒时,她并没有快感。于是,她醒悟了,不愿意鹿子霖再这样占据她的身体,踹了鹿子霖,并尿了鹿子霖一身。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女子,手无缚鸡之力,竟然敢这样做,这是出人意料的。她对命运越反抗,命运对她的打击越惨烈,不管她是死在谁的手里,终究是被封建礼教害死的。即使是死了,她仍然不甘心,要为自己申诉,进行第三次反抗。她的魂魄附在鹿三身上,那段长长的痛诉——“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别人一朵棉花······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的烂窑子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就不敢进去了,咋还不容俺呢?”——正是田小娥最后的心声,引起读者深深的反思。她的一步步坠落,谁是后面的黑手?生活不给她生路,她不放弃自己,与命运作斗争,即使遍体鳞伤。她一个个卑微的希望一次次被命运、被社会的各种势力以及封建礼教所熄灭,她不是一味叹息自己的苦难,而是用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生命去抗衡。
三位叛逆者中,莎菲的叛逆,是对爱情、对感情、对精神的追求,渴望灵魂与肉体的统一,这对田小娥来说,是一种奢侈。田小娥的叛逆,不仅是对感情,更是对生存的一种渴求。觉慧则是对封建家庭及其约束的一种叛逆。觉慧和田小娥都是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叛逆者,他们是时代的思考者,也是时代的警醒者,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对制度的不满,对黑暗现实的不满。
三、青春叛逆的价值
青春叛逆的价值,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价值。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类劳动的两种尺度。他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已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无论是莎菲、觉慧还是田小娥,他们都在追求自身的存在感,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去体现个性生命的价值,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鲜活,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人最重要的权利是生存与发展,所以他们才会为了个体的价值去拼搏,去反抗。叛逆者,以一种倔强的生命形式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艺术魅力。
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一切都处于不断的变化更新之中。无论是莎菲、觉慧还是田小娥,他们身上都带有当时社会的印记,虽时代变迁,他们的叛逆形象仍彰显着独特的魅力,他们的青春叛逆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石娟.“叛逆的绝叫者”——再论莎菲女士的爱情悲剧[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1(2):189-190.
[2] 刘剑丽.一个从隐让逐渐走向坚决反抗的叛逆者——试论《家》中的觉慧形象[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08-110.
[3] 徐贵芳,郭海燕.凄艳的“恶之花”——田小娥形象分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12):72.
——重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解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