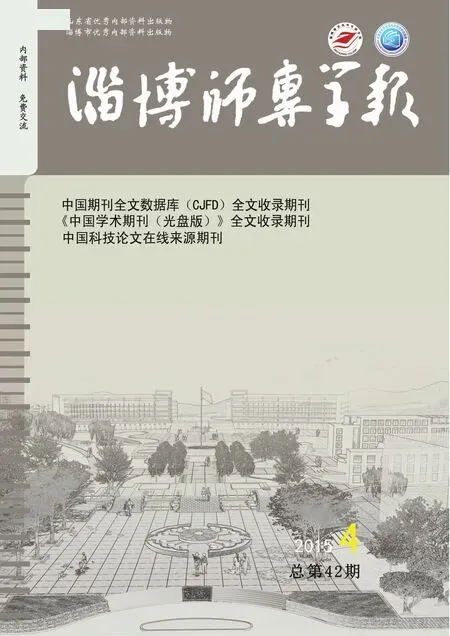“细节研究”对聊斋故事“真实性”的支撑
李学良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聊斋文化研究
“细节研究”对聊斋故事“真实性”的支撑
李学良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日益受重视的聊斋故事“真实性”,包括“事件真实”与“文化真实”两方面的内容。“细节研究”是确证聊斋故事里“事件真实”与“文化真实”的重要支撑,“细节研究”也给古代小说研究带来诸多启示。
聊斋故事;事件真实;文化真实;细节研究;启示
一、聊斋故事的“真实性”日趋受重视
“聊斋虚构论”曾深植于人们观念当中。但事实上以“神异性”著称的聊斋故事,却有着相当的“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可以分为“事件真实”与“文化真实”。 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被发现,聊斋故事“真实性”的议题也必将成为研究热点与学术增长点。
(一)曾经根深蒂固的“聊斋虚构论”
《聊斋志异》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而著称于世,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聊斋志异》所载故事的“真实性”。大多数人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聊斋”就是“神异”,“神异”就是“虚构”。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给《聊斋志异》题诗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聊斋志异》给大家的印象,似乎就是“姑妄言之”的“孤坟鬼狐”故事。在相信科学、反对迷信的观念成为主流的当代中国,往往与迷信相伴生的“神异性”,也顺理成章地被与“虚构”乃至封建迷信画上等号。具体到《聊斋志异》,读者一方面被聊斋故事所打动,另一方面却视神异的聊斋故事为虚构。总之,“聊斋虚构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这种根深蒂固的“聊斋虚构论”业已受到挑战。
(二)央视《地理中国》对聊斋故事“真实性”的展示
2013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组来到淄博,与淄博市委宣传部、淄博师专合作,拍摄了一期《揭秘聊斋异象》节目,并于2013年7月24日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引起了良好反响。这期节目的核心思路是认为《聊斋志异》里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并且可用现代科学加以解释。节目里选取的三个事件分别是离奇难解的江中光亮、名闻遐迩的奂山山市、惊心动魄的地震记录。《聊斋志异》的“江中”篇记录了江中出现奇怪光亮的事件,经过节目组探讨,认定这是特殊环境下的发光藻类在作怪。“山市”篇记录了淄川奂山的山市蜃楼,节目探讨展示了山市蜃楼的发生机理。“地震”篇记录了蒲松龄亲历的一次大地震,节目组认定这场地震是康熙年间以鲁南郯城为震中的大地震,并考察了枣庄熊耳山地震遗迹以为佐证。
在节目里蒲泽先生说:“《聊斋》里面的大量作品,就是他亲历亲见,或者亲闻,它的真实性非常强……” 这期节目紧扣几个事件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观众心目中的“聊斋虚构论”,成为展示聊斋故事“真实性”的一个典型样本。
(三)聊斋故事“真实性”的学术研究
学术界对聊斋故事的“真实性”问题,也一直进行着或有意或无意的探讨与考证。有考察聊斋里类似时事新闻的篇章,如《〈聊斋志异〉时事短篇考析》;有考证聊斋里的故事原型,如《〈聊斋志异·鬼哭〉本事考》;有考察聊斋里的人物原型,如《“邵临淄”原型邵嗣尧考》《〈聊斋志异〉素材来源五则》;有考察聊斋故事的真实社会文化背景,如《〈聊斋志异·金和尚〉的史学及民俗学价值》;有考察聊斋里的“事件真实”,如《论聊斋故事的“真实性”》……上述所列论文仅是略举一端,旨在证明聊斋故事的“真实性”在不经意间已成长为一项学术议题。
(四)聊斋故事里的“事件真实”与“文化真实”
从聊斋故事“真实性”的内容上来分,大致可分为“事件真实”与“文化真实”两类。
“事件真实”,是指一些聊斋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客观存在。这些事件虽然看似不可思议,但据其中一些蛛丝马迹可推定出其具备一定的“事件真实性”,例如“咬鬼”篇等。“文化真实”,是指一些聊斋故事,在现实中固然未曾发生过,但却展示了真实的文化存在,而绝非讲述者随意虚构,相关的聊斋故事就具有了“文化真实性”。举例而言,鬼神虽不存在,但“鬼神文化”却是客观存在,并且这种文化因其内在逻辑而构成有机整体,绝非个别人所能虚构出来的,例如“王六郎”篇等。
(五)聊斋故事“真实性”的现实条件
聊斋故事的“真实性”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条件作支撑,现分述如下:
1.《聊斋志异》搜集整理的成书方式
《聊斋志异》就体裁来讲是“笔记体小说”。如果说中长篇小说有鲜明虚构特征的话,“笔记体”却缺乏这种明显虚构的特征。与“笔记体”相对应的是“搜集整理”的成书方式。关于《聊斋志异》的成书,广为流传的是:蒲松龄在路边摆案设几招待过往行人茶水,并要他们讲述一些奇闻轶事,蒲松龄加以记录整理,从而写成《聊斋志异》。此种传说,“虽于事实无稽,而于事理却有征,具有相当高的‘通性之真实’”[1]。蒲松龄也自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2]( P1)(纪晓岚在述《阅微草堂笔记》由来时,也有类似表述)。《聊斋志异》又有多篇有“某某言”的字眼,更可作为“搜集整理”的直接证据。《聊斋志异》的“搜集整理”成书方式当无异议,蒲松龄“搜集者、整理者、编写者”的因素比重大于创作者的比重。所以大多数聊斋故事肯定非蒲松龄所虚构。
2.古人“文学虚构观”的薄弱
聊斋故事可不可以是原讲述者的虚构呢?答案是: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微弱,这是由古人文学虚构观的薄弱造成的。今古的文学观念有巨大不同。现代人习惯性地认为小说虚构是天经地义,但古代小说的“虚构观念”却是较晚才形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即唐时小说创作才有了较为明确的“虚构观念”。但即便到了明清时期小说的“虚构观念”较为强烈了,却也只是适用于中长篇小说,而不适用于“笔记体小说”。聊斋故事的提供者,多为三教九流,绝非擅长“虚构”的小说家。里面诸如“孙太白尝言、沈麟生云……”等,其中虽有文人,但也不至于自降身价到从事被视为小道的小说创作。我们看到,其中更多故事的讲述者是普通村民、客商,他们更不晓得什么“文学虚构”。所以聊斋故事提供者的身份,也导致了虚构可能性的降低。
3.聊斋文本里的一些确凿证据
《聊斋志异》“搜集整理”的成书方式,“笔记体”创作中虚构观念的薄弱,还只是为聊斋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基本前提,但尚缺乏聊斋故事里的确凿证据。笔者认为这些确凿证据就隐藏在聊斋文本里,等待我们逐渐去发现。发现这些证据的核心手段之一,是对聊斋文本进行“细节研究”,下文将举例进行阐释。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本文回避了那些论证较复杂的案例,所举多为简单易解的细节研究案例。
二、“细节研究”对“事件真实”的支撑作用
(一)“细节”对“事件真相”的提示作用
在侦探小说里,给名侦探提示真相的,毫无例外几乎都是细节。同样,聊斋文本里的一些“细节”也是提示我们故事真相的宝贵线索。
例如“偷桃”篇记录了儿童缘绳上天偷桃,肢解后起死回生的神奇事迹。故事内容看似荒诞不经,但却有一细节提示此事的“真实性”,那就是“余从友人戏瞩”一句,也即蒲松龄自称“偷桃”一事为其亲睹。这一细节让读者陷入两难的困惑:假如说“偷桃”实有其事,但是此事实太过神奇,令人难以接受;假如说“偷桃”并无其事,那就说明蒲松龄在肆意欺骗,同样令人难以接受。但当我们进一步发现现实中的印度戏术(以及中国的茅山戏术)里确实有“通天绳”这种魔术道具类似于“偷桃”所记;而“偷桃”篇里的“起死回生”又类似于魔术里的“大变活人”时,“偷桃”故事的“真实性”也就板上钉钉了。进而可推知,“偷桃”篇的本事来源乃蒲松龄亲睹,而并非对古代类似故事的改写(如《嘉兴绳技》等)。
再如“婴宁”篇里记录“会上元,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方至村外,舅家有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遨。”藉由这段细节描写,可做出如下推断:王子服所居的罗店村近旁,在上元节前后有庙会举行。理由是:古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游女如云”的场面,一般只有庙会上才可见到;王子服“方至村外”就看到“游女如云”,可知庙会必在罗店近旁举行;“会上元”里的会,可以是恰逢,也可以是临近的意思,故庙会举办时间当为正月十五前后。由细节推导出的这些信息,似乎并无用途,但当我们要确定作为“婴宁遗迹”的“莒之罗店”具体所在的时候,就成为了核心线索或证据(事实上确曾有莒之罗店符合正月十五前后村旁就有庙会的特征)。
又如“种梨”篇在叙述道士表演“瞬间种梨”的神奇“法术”时,有“(道士)把核于手,解肩上鑱,坎地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的细节描述。这里“解肩上鑱”四个字其实已经提示了道士“瞬间种梨”一事必有猫腻。理由是,我们都熟知道士的形象,但恐怕从未见过肩上扛鑱的道士。退一步讲,即便偶尔真有个道士肩上扛鑱,而这把鑱随即就能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由此细节可推知,道士种梨绝非偶然触发,而是早已“有备而来”。顺着这个细节提示,就有可能发现“种梨”背后的戏术与骗局真相(可参看《〈聊斋志异〉中“种梨”篇的魔术解读》,连云港师专学报2010年第2期)。
(二)“细节”对“事件真实”的印证作用
例如“龁石”篇里当我们推测王嘉禄的“龁石”可能即“服云母”方术时,就需要篇中一些细节来做最后一锤定音的印证。“龁石”篇里“向日视之,即知石之甘苦酸咸”的细节,与《云笈七笺》里记录的“云母乃有八种:向日视之……”[3] (P464)吻合;“龁石”篇里“如啖芋然”的细节与《云笈七笺》里记录的云母制法“欲为粉者,便漉取令燥作熟……出曝干,革囊,槌便成粉”相吻合[3] (P464),又与《池北偶谈》里“仙人煮石”[4] P399)的说法吻合。这些细节上的吻合充分印证了“龁石”正是道教的“服云母”方术。
再如“地震”篇所记的“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从这一时间上可直接推断,这是1668年发生在山东省南部郯城的8.5级大地震。而“地震”篇里记载地震发生时“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的细节,则更确证了此记录的真实性。因地震发生时的轰隆声,是从震中发出向周边散射,蒲松龄虽不懂“震中”一说,但他听到声音是从东南来,往西北去,这就与郯莒震区在临淄东南的事实完全吻合。由此细节也可窥见蒲松龄的细致观察能力及其尽量忠于事实的写作原则。
又如“咬鬼”篇,当我们推测“咬鬼”可能实为一次“鬼压床”(睡眠瘫痪证)事件的记录时,也需要篇中细节给予印证。其中的细节之一是老翁“力龁其颧……龁益力……急呼有鬼”,这里老翁做了咬的动作,然后就能够呼喊了(此前他是“急欲号救,而苦不能声”的)。通过“咬”而获得解脱的细节,完全吻合中西医关于“从小处着手运动”可以摆脱“睡眠瘫痪”的理论,因而成为证明“咬鬼”实为“睡眠瘫痪”的一项有力证据。①
三、“细节研究”对“文化真实”的支撑作用
(一)以“细节互见”印证“文化真实”
不同于“事件真实”,“文化真实”往往需要在彼此互见中才能相互印证其“真实性”。
例如“阎王”篇里记载:“李久常,临朐人,壶榼于野,见旋风蓬蓬而来,敬酹奠之。”这个细节已提示我们,古人认为鬼神常以“旋风”方式出行。如果仅此个案,尚不足以支撑起这种说法的“文化真实”。但是在“王六郎”篇里,已升职为土地神的王六郎两次现身阳世分别是“俄见风起座后,旋转移时,始散”,“送出村,歘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风盘旋久之,乃去。”这样“阎王”篇与“王六郎”篇里的鬼神驾旋风出行的说法就彼此互见,相互印证。无独有偶,在其他笔记小说中也多次出现鬼神驾旋风的记录,《阅微草堂笔记》里有“后聂每上墓,必携饮食纸钱祭之,辄有旋风绕左右。”[5](P137)“张氏姑妇同刈麦,甫收拾成聚,有大旋风从西来,吹之四散。妇怒,以镰掷之,洒血数滴渍地上……妇苏而旋风复至,仍卷其麦为一处。”[5](P223)……这么多的案例彼此互见,足以支撑起鬼神文化体系里认为“鬼神常驾旋风出行”的“文化真实”。
又如“贾儿”篇里记录,贾儿欲困住狐妖时,“以砖石叠窗上……两窗尽塞,无少明。已乃合泥涂壁孔……伺母呓语,急启灯,杜门声喊。久之无异,乃离门扬言,诈作欲搜状。有一物,如狸,突奔门隙。急击之……”这段细节提示我们,贾儿认定狐妖能变化身形从缝隙中穿过,却无法从密不透风的墙壁穿墙而过。如果仅此个案,当然不足以支撑此说的“文化真实”,但是在“狐入瓶”篇里,记录有“扉后有瓶,每闻妇翁来,狐辄遁匿其中……一日,窜入。妇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燂汤而沸之。”可知此村妇所持见解,正与贾儿同。又“胡四姐”篇里,记录有捉狐术士捉到狐妖后,“猪脬裹瓶口,缄封甚固……四姐又曰:‘勿须尔,但放倒坛上旗,以针刺脬作空,予即出矣。’”又可与前二案例互见互证,故足以支撑起狐仙文化体系里认为狐妖虽可变化身形,却无法穿墙而过这一说法的“文化真实性”。
(二)“细节”对“文化真相”的提示作用
例如“王六郎”篇里,讲到渔民许生“每夜,携酒河上,饮且渔。饮则酹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饮。’以为常。他人渔,迄无所获,而许独满筐。”表面看这只是许生的奇怪习惯,其实这是宗教文化里的“施食”方术。所谓“施食”,是指施舍食物给孤魂野鬼吃。佛道宗教认为,孤魂野鬼受施食恩惠后会感恩图报,暗中帮助施食者,于是就有佛道信徒主动去施食以求获得回报,这就是“施食祈福”方术。从细节上来看,许生的“施食”层次已远高于市面流传的施食方法,主要表现在:其一,许生在晚上而非白天施食,因古人认为白天阳气盛,鬼不敢出,许生选在晚上施食,当然是深知其中内情;其二,许生选择“施酒”而非“施食”,因古人认为不同神鬼各有所好,要求神鬼之助,就得投其所好,所以许生的“施酒”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嗜酒之鬼);其三,许生明确表述施酒对象为河中溺鬼,这表明许生并非如市面流行的给阴间众生施食,而是专门针对河里的溺鬼,这种专一性就有点接近宗教文化里的“修护法”方术了;其四,许生施食完毕后就去打渔,这一细节已明白提示,其施食目的就是为了让被施食者帮自己打渔,因而也难怪“他人渔,迄无所获,而许独满筐。”通过这些细节给我们提示的文化真相,我们发现了许生其实相当精明这一隐藏事实,这与其表面上的傻乎乎相去甚远。但这还只是初步,后文许生远行几百里去拜谒升任土地爷的王六郎的事件细节,提示给我们更深层的秘密和文化真相,但因篇幅所限,姑且留待另文撰述。
又如“瞳人语”篇里记录有丫鬟“掬辙土飏生”,方栋遂目翳失明的事件。表面看此事为叙事者虚构的一个咒诅方术,但“辙土”这一细节却隐含着少为人知的文化真相。“辙土”就是以前土路上马车压过的车辙痕迹里的土,相当坚实。按《本草纲目》所记,“辙土”又名“车辇土”,主治恶疮出汁等病症。“辙土”也用在“咒禁”方面,在《太平广记》里记载:“唐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襕,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苦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乃捻辙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阳杂俎》)”[6](P2530)无论是中医典籍还是咒禁术里都认为,辙土多用于出汁、出血不止之类病症,也即取辙土对溢出物的“阻塞”作用。因被车碾压过多次的辙土更致密厚实,所以壅塞作用更强。这正是古人“象形取意”“医者意也”理论的实践(虽然这种理论未必正确)。这么一来丫鬟取“辙土”而非其他土施法于方栋双目的原因也就水落石出了。由这一细节可以推断,故事编者并非随意编造,而是比较精通方术文化并基于此而进行构思,后文里的诵经解厄、瞳人、重瞳等叙事细节,更能进一步证明这一推断,留待另文撰述。而单就“辙土飏生”一事来讲,“事件真实”里固无其事,“文化真实”里却实有其理。
四、“细节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
藉由上述案例,可初窥“细节研究”对聊斋故事“真实性”的支撑作用之一斑,也给我们带来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些相关启示。
(一)基于“真实性”信念展开细节研究
研究聊斋故事的“真实性”,首要的其实是确立对聊斋故事“真实性”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坚信聊斋故事并非随意编造,其中一部分故事是基于“事件真实”写成,另一部分故事则基于“文化真实”构思而成。任何一篇聊斋故事,基本上都可用“事件真实”或“文化真实”来囊括与阐解。如果未能发现此篇的“事件真实”或“文化真实”,那是研究深度不够,而不是此篇缺乏“真实性”。这种对聊斋故事“真实性”的信念固然偏颇,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重视聊斋文本的细节,进而发掘出聊斋故事的“真实性”。
研究聊斋故事的“真实性”,还应具备一些相关知识背景。如前述案例里推论“婴宁”篇里罗店村外就有庙会,就要有古时女子出行与庙会的相关知识;推论“种梨”实为戏术,就要有魔术的背景知识;推论“咬鬼”实为“鬼压床”,需要有“睡眠瘫痪症”的背景知识……
(二)“细节”能提升研究的“趣味性”
对聊斋文本进行“细节研究”固然有一定难度,却也因此使得研究工作妙趣丛生。岂但聊斋文本的研究如此,其他古代小说的研究也是如此。在此举聊斋之外的一例以作说明。《二刻拍案惊奇》里有“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一卷,写到被抓获的神偷两次给狱卒行贿,分别说“我有一主银两,在岳庙里神座破砖之下……还有一主东西在某处桥垛之下……”[7](P395)狱卒两次去取,果然皆有银两。这里把银两藏在庙宇神座下面,藏在桥垛之下的两处细节,很多读者可能一眼扫过,这就错过了其间隐藏的文化真相,也即神偷为何会选择把银两藏在神座下面和桥垛下面。其实推理开来,小偷藏银两求的是安全保险,所以当然不敢藏在家里(因怕犯事被搜查),藏在外面就要找相当保险之处。之所以藏在神座下面,盖因百姓惧怕神灵,极少有人敢去窥视神座下面,当然安全;之所以藏在桥垛下面,因水中难看清东西,入水又较危险,故不必担心有人发现。并且,桥垛一般相当坚固,故不必担心银两被洪水冲走……可知此篇虽非事件真实,却因其细节描述中隐藏了盗贼藏匿赃物的经验技巧这一真实存在的江湖文化而具备了“文化真实性”,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收获了趣味性。事实上在“真实性”上远胜于“三言二拍”的《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的细节研究,其趣味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细节研究”要求重视“原始文本”
因“细节研究”要仰赖于可靠的文本记录,这就决定了其必须着重以“原始文本”为研读对象,而不可拿白话翻译乃至改编作品来取代之。如上文所述“瞳人语”篇里的“辙土”细节,经由翻译之后,很容易将此不起眼的细节省略或者扭曲。我们手头上就有一个白话版本,将此处译为“顺手抓起一把车轮下的尘土向他撒去”,这就与“辙土”细节的本意有了一定距离。如果据此白话翻译做细节研究,当然难以做到准确无误。类似白话翻译偏离原意的例子不在少数,所以聊斋文本的“细节研究”,当以《聊斋志异》的原始文本为研究对象(校注本则无妨)。
注释:
①参见《〈聊斋志异〉中“咬鬼篇”的真实性考证》,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1.(3)。
[1]王光福.浅谈“聊斋学”史料中的几则“稗官家言”[J].《蒲松龄研究》.2015,(1).
[2](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宋)张君房.云笈七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4](清)王士禛.池北偶谈[M].文益人(校).济南:齐鲁书社,2007.
[5](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M].吴波(等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
[7](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李志红)
The tales of Liaozhai are draw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whose reality includes “event reality” and “cultural reality”. “Detailed study” can strongly support the “event reality” and “cultural reality”. It also brings great enlightenment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novels.
tales of Liaozhai; event reality; cultural reality; detailed study; enlightenment
2015-09-16
李学良(1979-),男,山东莒县人,文学博士,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历代笔记小说的文化阐释研究。
I207.419
A
(2015)04-0061-05
注:本文为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重构以‘真实性’为核心的‘聊斋文化品牌’”[20142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