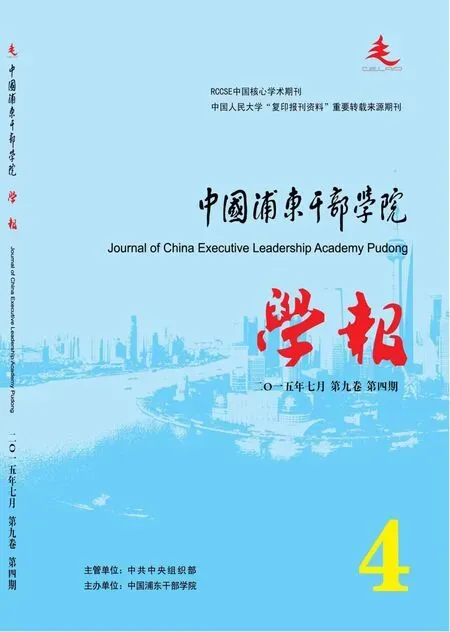西方的曲解:“中国认同”的实态
肖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西方的曲解:“中国认同”的实态
肖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中国”的概念在中国的形成至少经历了从地理意义到文化意义的演变,再从文化意义到主权意义的变化,时间跨度达五千多年。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中国,也是一个从单一民族认同向多民族认同转变和走向世界大同的“中国”,是一个主张用先进的文化改造自身,同时也积极影响世界,以“教化”之名行先进文化启蒙之实为特点的中国。在“中国”认同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在汉代与唐朝主要是通过“和亲”加强和兄弟民族与周边国家的相互认同和建立互安和互信关系,尤其是到了唐太宗时代,更是主张并充分地实践了华夏与夷狄平等。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却有另外的思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追求“中华王国”、“中央帝国”的霸权和强权目的。
中国认同;西方世界;中央王国
一、引言
“中国认同”可以说是一个最古老但又是最年轻的命题,说它最古老,是因为从概念的产生看,至少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说它最年轻,是因为中华民族作为人类历史上生命力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在世界政治中的重新崛起,引起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或者“中华民族”概念和地位再度高度关注和重新定义的新局面。不同的学术领域对“中国”的新认识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角度,但都有一个核心背景,就是中国的再度崛起,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它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它们是通过什么角度认识今天的中国的?它们在确定中国崛起时打算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应对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探讨。毕竟我们不能在对中国之外对华观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和世界打交道,如果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大家在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彼此打交道,中国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所推动的新外交战略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我们就等于是在干瞎子摸象、不得要领的事情。《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中国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和谐相处也是一场“战争”,但如果中国是在不知己和不知彼的情况下发动为友好与和谐而战的“战争”,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二、西方世界的“中国”观
“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是西方国家就其对中国的认识而发明的措辞,中国周边的日本和韩国类似的称呼是“中华思想”。根据日本出版的《百科事典》解释,“中华思想”的含义是,中国为宇宙之中心,中国自负其文化和思想为神圣。以这样的思维,汉族从古至今持续着本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而自我标榜。把和汉族不同的周边边境的民族贬低为文化低下的禽兽,由此逻辑出发,产生了华夷思想。且夏、华夏、中国和中华同义。很明显,这是严重歪曲中国而无中生有的日本人的中国观。如果说中国王朝时代确实在文化上中国主流的思想界确实存在对文化落后的外邦有鄙视的一面,但在今天则完全没有。难怪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宫家邦彦根据他多年对中国的了解指出,“很多日本人,围绕中国之种种恶行之根源是源于‘中华思想’而深信不疑。但是,在普通的中国人中,他们自身完全没有按照‘中华思想’来采取行动的意识,在汉语中,也根本不存在‘中华思想’这一说,恐怕这完全是日本人创造的词语罢了。”[1](P1)通过在日语“yahoo”输入繁体“中華思想”搜索,竟然有1,690,000条之多。“中华思想”观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恐怕其中与日本《百科事典》理解相一致的认识观占主导地位,普通的日本人中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而查阅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华思想”相关的研究,竟然无一篇论文。也就是说,我们对日本以“中华思想”观为主导的中国观可以说几乎完全不了解,简直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同样,我们的学术圈,似乎对西方世界的“中央王国”观也几乎未予重视,相关的系统研究也很缺少。
(一)以自己的民族特性为标准衡量中国的观点
中国人自身的“中国认同”是在中国活生生的历史中反映出来的,是铁一般的事实。但是西方国家,包括在古代历史中和中国有过广泛交流的日本,对中国认同持非常极端的观点。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日本观点很极端的《世界日报》就说,“中国是企图通过举办北京奥运会使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中华化’。”[2]这种认识很明显是建立在日本人自认为“大和民族”为单一民族认识的基础之上,并按照日本的标准来认识“中华民族”也应该是由汉族单一性才能构筑“中华民族”的推理之上的。有理性的日本人应该认识到,民族确实存在单一性,正如“大和民族”,姑且可以认为日本是“大和民族”这一单一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当然严格论证的话,日本人并非纯而又纯的大和民族,朝鲜族、中国人的后裔也占相当的比重),但也不能否认民族构成的多样性,正如“中华民族”,这是起码的常识。日本人以自己的民族认同观“规范”其他民族认同观,除了明显的无知之外,恐怕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就是在舆论上制造分化中国,达到削弱中国日益崛起势头之目的。就在2014年9月19日苏格兰独立投票后独派失败之际,日本《世界日报》的评论更是煽动地说,“在亚洲,中国的维吾尔族和藏族等,由于受到镇压,宗教和固有的文化被抹杀之,甚至民族本身之生存都被抹杀之。对他们而言,想为自己权益而投票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希望获得更多自由与自治,日本应该高度关注之。”[3]其反话正说的恶意宣传是何其毒也!其无中生有的心态是何其昭然若揭!管窥见豹,我们可以从日本人的这一简单化的思维推知整个西方世界极端思维派恐怕在“中国认同”上相同或者相似的逻辑,以及这样一种逻辑——通过制造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离心离德的假象——意图的分化作用。也就是说,中国认同的国际环境某种意义上说是恶化了,因为像日本这样经济文化实力强大的国家甚至都加入到以种种手段分化中华民族的罪恶行动中,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政不确定性就必须特别地加以重视了。国际政治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处在强势恢复(或崛起)过程的大国,其前进的道路上总是会遇到种种的障碍和困难,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决不会出现列国夹道欢迎你崛起的局面。无论中国作出怎样的解释,那些自认为实力和你相当,或者过去比你强但你强劲发展的势头要超越它的国家,它心里决不是痛快的高兴的,相反只要有机会可以利用,它都要使出各种招数来破坏你的发展。其实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化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的做法就是冷静地对待之,平心静气地接受之,甚至“笑纳”之。对一些国家激怒你的言论和行为,尽最大努力忍之。而决不能因此乱了阵脚,正如《易经》损卦所云:“君子以惩忿窒欲。”孙子说过,“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4]日本、菲律宾,甚至和中国具有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越南等周边国家,在图谋单极霸权的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和挑动下,都干了不少企图激怒中国的坏事,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安国全军”之道,从国家兴亡的根本出发,没有“以怒而兴师”,也没有“以愠而致战”,正在以无比高超的国际政治智慧引领着中国,以强有力的外交战略和谋略,拓展和巩固着中国外交新的空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常态正在形成,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稳步地按照中国的既定发展目标前进。
(二)比较柔性的怀疑观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也这样描述中国:“中国的谈判战术反映了中国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本地区的支配者而演变为殖民主义牺牲品的历史经验,因此,中国的外交展示了两个同时发展的模式,一个是作为中央王国的继承者(As heirs of the Middle Kingdom),中国的外交官是非常迷人的(ingratiating),对方则被奉承为中国‘俱乐部’的成员而兴高采烈。”[5]
基辛格在14年前心目中的“中央王国”,不过是很不起眼的中央王国,他说,“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一贯地被估计过高为世界大国和思想的来源,实际上,她经济上是相对次要的小市场,军事上她不如苏联那样成为(美国)全球性的对手而只是实力类似于伊拉克那样的,只能造成地区性的威胁(regional menace)的国家,政治上其影响是弱小的(puny),这个中央王国是中等水平的国家。”[6]这里不排除基辛格从谋略上希望淡化“中国威胁”论,以便美国等西方世界和中国建立某种比较放心的安全关系的考虑,但作为全世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的基辛格恐怕也未曾想到时光只不过才过去十几年,中国已经成长为另外一个具有全球性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大国和强国,相信他不再会说中国和伊拉克的水平旗鼓相当了。
西方的重要媒体和重要学术期刊很关注以“中央王国”为特色的“中国认同”逻辑,并对中国这个“中央王国”所造成的影响力甚为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就说,“中国时常被指责怀有‘中央王国’情结——这是一种认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信念。”[7]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形容:“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不再是秘密,她在非洲这个大陆撒钱以追求影响和自然资源,结果,多达750,000中国人到非洲工作,现在,极少有人知道的现象出现:因中国繁荣的机会的吸引,一个日益增长的非洲移民移居到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8]《新闻周报》形容:“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如果我们都相信这样的夸张表达(hyperbole),中央王国正在苏醒,她要求其作为一个贸易、文化和商务之全球的支配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东方的外包的生产或者是试图利用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财富,西方商界绝对不可忽视这个正在发生的转变。”[9]这是明显地从正面认识中国影响力的观点。颇为同情中国的观点认为,“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个中央王国有超过3,000年孤立主义的历史。”[10]美国桑佛德大学(Samford University)全球中心主任威廉(William R.O’Brien)曾经就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在国会众议院有关贸易的小组会上陈述,“任何西方的企业如果不承认中央王国的心态(the Middle Kingdom mindset)将面临重重障碍(rocky road),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政府,应该设想能和中国在一起工作,简单地来自教化(an Enlightenment)和改造(Reformation)的心态意味着在21世纪将充满误解。中国是一个正在加强自己的思想和力量的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日益地发展着,她也在加强自己的中心,那就是世人皆知的中华王国心态。”[11]很明显,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对中国自身的“中华王国心态”的分析应持客观和理性态度,而不能简单化下结论。
(三)认为今天的美国是古代中国“中央王国”的化身,今天的中国在治理模式上将成为美国的化身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认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她是古老的中华帝国——中央王国的新的化身,她是以世界为她所吸引之方式建构世界,美国的资产之中,不但有强有力的先进军事技术和贸易政策,构思政治与战略的定义,而且以至高无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能力输出由美国的经验构成的,描述和分析世界的概念和范畴。”[12]今天美国的很多对外政策行为、对外政策思维和对外价值导向,和中国西汉时期汉武帝和唐朝太宗时代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人在这里所引以为荣的是,她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堪比中国最强大时期的存在。换言之,古代最强盛时期的中国,在地球上发挥着与今天美国相同的以至高无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能力输出的,且由中国的经验构成的,描述和分析世界的概念和范畴之作用。从反思和总结中国古代的对外政策行为而言,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国际政治思维。和美国是古代强盛时期中国的化身的逻辑一样,也有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将演变为今天美国的化身。早在1994年,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所长的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扬言,“中国是一个处于杂乱无章状态的‘中央王国’,北京抓住远离其中心的外部帝国——包括西藏、新疆和蒙古——已变得脆弱。但这些远离其中心的外部帝国比较地方主义引起的内部帝国的挑战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因而,华南是处于最危险的状态,这似乎是持续的权力下放,某种意义上,北京将自称统治了省,而省也自称为北京统治,结果就是一个似乎是更加宽松的美国式的中国或者一个中国经济共同体。”[13]这是预言中国内部治理上权力将会出现分散化,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将会向地方分权化的方向发展。这大概算得上是比较中性的观点,至少不认为中国会走向“崩溃”。而最近美国的舆论则兴起“中国崩溃”论的思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作出和他以前的学术观点矛盾,表现得非常情绪化且耸人听闻的观点,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习近平反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和反腐败只能是把中国带向接近最后崩溃的时间节点(breaking point)”。[14]借用《晋书·陈頵传》晋元帝太兴元年陈頵在给德高望重的重臣王导的信所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华之所以被颠覆破坏,正是因为选择人才失当,徒有虚名的优先而做实事的却靠后,竞相追逐浮华,互相荐举,言过其实者先显达,说得少一点儿的后录用,于是互相推波助澜,导致国家衰落。”中国要衰落也好,崩溃也好,陈頵对王导的告诫在今天仍然有用,而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造成“中华倾弊”,“四海土崩”的问题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行动加以整治,“中国崩溃”论将再次破产。
(四)断言中国追求“中央王国”就是谋求霸权
前美国驻华大使、前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普理赫(Joseph Prueher)在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前曾经表示,“中国人正在寻求复兴中央王国这个古老的概念,那就是中国是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the dominant power)。”[15]这是明显认为中国寻求亚洲霸权的逻辑推理,把中国追求“中央王国”地位视之为恶的表现和行为。斯里兰卡裔美国人学者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认可中国是历史上世界的中心,而今天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他以中国正在推动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例说,“斯里兰卡是北京海洋战略之皇冠上的宝石(crown jewel),中国将投资超1亿美元在科伦坡建造南亚最高的大厦Lotus塔,据传此塔在新德里都能瞧见,这个佛教风格且高耸云霄的电信塔不仅象征北京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之口号,而且也投射了来自曾经的中央王国辐射权力之意味,对于这个现实,突然地唤起美国和为一条珍珠链环绕的印度对中国之神机妙算的冒险和中国对印度洋可能隐藏的意图之担心。”[16](P54)
(五)贬低性的但也是某种意义上值得重视的观点
早在2000年,西方学者甘姆博就十分嗤之以鼻地认为,“外国的中国观察家经常关注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支配中央王国的问题,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包括膨胀的人口,环境退化,正在增长的民族关系的紧张,中国和邻国不安的关系。而这个国家还存在着更令人不安的直到今天为世人很少注意到的直接的问题:北京很少能收到其税。”[17]
(六)比较少见的乐观的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央王国”美国未来必定让位于中国
今天的“中央王国”美国未来必定让位于中国,中国将成为新的“中央王国”。而这个未来的中央王国,将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也必将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认为中国在借助激发民族主义来建构新的“中央王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FSI)亚太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亨利·S.罗文(Henry S.Rowen)是持中国崛起乐观论的学者。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书评直接用“中央王国之中心错位”(Off-center on the Middle Kingdom)的标题,指出美国两位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美罗斯·芒罗(Ross H.Munro)在他们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所大肆鼓吹的中国威胁是不真实的。书评提到,“由于在1994年中国共产党高层的一个报告中宣布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hegemonist power),是中国的敌人。1989北京风波美国的间接作用、美国直接导演的苏联解体,导致北京不再把美国的力量看作是对亚洲有益的(beneficial)存在。美国的海湾战争刺激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由于近代以来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带来的民族耻辱,反美主义已成为中国恢复民族尊严(national dignity)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罗文认为中国对美态度的变化和中国军事现代化并不表明中国必然成为美国的威胁。书评认为21世纪中国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数十年后,中国也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18](PP101-104)
三、从“中国”自身认同的再解读
“中国”的概念表现的是对文化的认同优于对种族的认同,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①参见:《论语·八佾》,用现代汉语来说,此段话的意思是:“夷狄虽有君主却没有礼仪,还不如华夏诸国没有君主却保留着礼仪好呢。”的意思主要也是文化意义的,有没有文化和制度,成为衡量你属于华夏还是夷狄的唯一标准,种族特性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而“夷狄”是完全可以通过“教化”等文化和文明的启蒙将其改造成华夏的,而绝不会是文化落后的夷狄改造华夏。其原因,可能存在过度的文化自信、文化优越感之外,也确有希望华夏的文明成果能为夷狄所接受,这样,慢慢地夷狄也会向华夏转变,从而给夷狄带来巨大的好处和利益。所以《晋书》说,“礼乐兴,四夷宝”,[19]就是这个道理。孟子就曾以他对华夏文明高度认同的文化自信坚定地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0]孟子思想的这种合理成分,对我们今天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和守住我们的文化主权底线,都是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如果说把种族看得太重,也就不会有“和亲”的政策了,而当时的夷狄,在“种族”与文化之间,也是倾向于认同文化的力量,接受种族融合的(主动要求)。夷狄之类的称呼也只有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概念,而决不存在种族和文化上的歧视。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对印度就没有“夷狄”之类的称呼,原因是,古代中国觉得印度也是“文化大国”,文化上和中国一样先进。也就是说,中国历来是文化认同超越种族认同。此外,中国理解的先进文化,往往并非是同质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重视的是如何使不同的文化之间能够交流。
(一)“中国”的概念,一开始就有“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含义
比如《战国策》之“义渠君之魏”篇中义渠国国君来到魏国,公孙衍对义渠国国君说,“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21]这个地方的“中国”指的是关东六国,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在“范雎至秦”篇中的“中国”,就赋予了天下中心的概念,范雎劝秦王说,“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22]
在《战国策》之“武灵王平昼间居”篇中的中国,就成了天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代名词了。赵武灵王的儿子因父王改穿胡服而劝说道:“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23]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才成为列国向往之地,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和“中国”建立密切的联系,谁为“中国”所认可,谁就具备起码的正统性和生存的合法性。而相反,谁被当时的中国所边缘化,谁就会很没有面子,弱者只好忍气吞声,而强者就会挑战“中国”的权威。例如,《资治通鉴》记载,前362年,“秦献公薨,子孝公立。……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24]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他就成了“中国”的继承者。这可以从李斯和秦始皇的一次对话看出。“昔秦皇帝并吞战国,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靡敝中国(战争使中国国力耗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25]也就是说,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在李斯看来,已经合法地继承了中国的正统。
古代中国政治家主张中国应该是一个非强制推动“教化”的国家。西汉名臣贾捐之曾经进谏说,如果“中国”衰弱,首先背叛她的,一定是夷狄,中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说:“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正因为有“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者,不是采取军事手段,而是文化和宽大的心胸,使蛮夷克服包括语言上的重重困难,到中国来朝贡。而秦王朝“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他还引用《诗经》“蠢尔蛮荆,大邦为雠(仇)”的诗句启发君王,《诗经》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通“叛”。背叛;叛变[betray]),自古而患之。”[26]中国衰乱,外族首先叛乱,这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都能找到很多的事例,内忧外患,内政外交,皆可从此例中得到启发。贾捐之主张用道义的力量来对待蛮夷,明显地也是从国家利益来考虑的,主张中国的教化绝不能采取强制的方式,而是应该在人家心甘情愿的基础上才能推动之。主张软实力才是一国立国之根本。这样,即使你并非拥有广大的领土,你的影响也会波及四方,他举古之大仁人武丁、成王的例子加以说明,说他们“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但影响则达到“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之境界。
(二)在力量不济的情况下,首先是确保中国核心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唐朝政治家、大诗人张九龄有诗云:“义无中国费,情必远人安。”其所表达的就是如何通过道义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并通过真情使“远人”平安的思想。在汉朝,“不以劳中国”是一切对外用兵的先决条件。在充分保证中国繁荣和安定之基础上,才对外用兵。中国是重中之重。公元前27年,杜钦向大将军王凤献计说:“即以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27]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内政优先,对外政策的推动是以内政的和谐为前提。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朝廷要开通西南夷而要在东方设置苍海郡的同时,在北方要建立朔方郡。这事公孙弘开始时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对中原的牺牲太大。在武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耐心劝说下,公孙弘终于理解了武帝“安远”的苦心,同意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朔方郡成为汉代的北方边郡之一。其重要的军事据点鸡鹿塞是汉与匈奴和平交往的出入关塞。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王朝,结束了汉与匈奴间的战争状态。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朝汉,受到汉宣帝隆重热烈的款待,赐给其各种实用的物品,使呼韩邪单于北归,此后呼韩邪单于做了很多积极配合汉朝安边之策的事情。呼韩邪单于后来还自愿请求和亲,王昭君出塞的故事,成为中国与匈奴关系的一段历史佳话。朔方郡从设置到废弃,共经历了约260余年,在历史上确实是达到了“安远”以固我“中国”之积极作用。
唐朝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陆贽进言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28]他深刻地分析了大唐实力远远在吐蕃之上,但也注意到吐蕃还有余力对大唐的安全可能构成的威胁,这其中包括军事体制的不同,后勤保障的差异,中国内部的“争相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专门干琐屑悭吝的事情”和贪官污吏横行等问题。
(三)中国是知道满足的中国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重之际,规劝太宗停止东征高丽,他引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教诲,提醒唐太宗“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应“重人命”。如果高丽违背臣属的礼节,侵扰老百姓,“他日能为中国患”,则消灭之,如若在“此三条而坐烦中国”不存在的情况下对高丽动武,则大错特错。因此应该允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29]
(四)中国“治安”好,则“四夷”自然宾服
这是古代中国人辩证地对待国际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是内政治理好以达到积极影响外部世界的上上之策,以“强中国稳外裔”,“振中国之威”,以“寝狡寇”,这样“遗笑外番,轻中国”之尴尬就不会发生,这样,“中国必安”,“而后四方万国必顺附”。如果“罢中国而事外夷”,则只能是“获虚名而受实祸也”。唐太宗贞观三年,10月16日,靺鞨遣使入贡,唐太宗说:“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30]唐朝诗人陶翰盛赞四夷自服云,“奉义朝中国,殊恩及远臣。乡心遥渡海,客路再经春。……礼乐夷风变,衣冠汉制新。青云已干吕,知汝重来宾。”在陶翰看来,“治安”好中国,能够达到使“夷风”向文明方向发展等积极的作用。反之就会出现如唐朝诗人陈陶的诗所云的,“隋炀弃中国,龙舟巡海涯。春风广陵苑,不见秦宫花”这荒凉的景象。唐朝诗人王昌龄诗“无道吞诸侯,坐见九州裂”所表达的,就是那种内政上“治安”无道,则国家分裂必现。而内政不治的南宋,国家安全形势真的出了大问题,正如南宋大诗人陆游在他的《晓叹》中所描写的大宋已经是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一鸦飞鸣窗已白,推枕欲起先叹息。翠华东巡五十年,赤县神州满戎狄。”同样唐朝诗人顾非熊的“风沙万里行,边色看双旌。去展中华礼,将安外国情”的诗句,表达的是怎样用中国自身修炼完善的重要软实力“礼”的文化,去积极影响外国,使它们变得文明进步,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明朝开国之初的洪武二年,作为宫廷“迎天神”所奏的《中和之曲》中有“内而中国,外及四方”唱词所表达的,就是管好自己的事务的前提下,再去拓展对外事务。洪武三年宫廷《抚四夷之曲》中有“海波不动风尘静,中国有真人”唱词所表达的,同样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中国有能力和信心,而这个能力和信心完全来自中国本身内政大治,德才兼备的人各得其位,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正如《晋书》中所说的“辅臣强,四夷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采取“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的安全政策,其《祖训》更是明确列出15个永不攻打的国家。当然,中国安全思想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比如,大清王朝最强盛时代,不但自身疆域在中国所有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中为最大,藩属国也最多,而藩属国在安全上的作用非同一般,而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则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晚清重臣刘长佑在云贵总督任上时向咸丰皇帝上疏,“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31]今天的中国已无任何藩属国,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只能靠自身的强大和稳定,同时努力和周边国家建立主权平等、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双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周边国家的安全状况,因为周边国家是中国安全之“藩篱”,对此不可不细察之,即古人所说的,“候细微,则国安”。如果这个“藩篱”不稳,则必然直接影响作为“门户”的相关边陲省份的安全,相关边陲省份的安全出了问题,就会直接导致作为“堂室”的中央地位的不稳,进而演变为整个中国的不稳,从而导致中华杼轴之困。所以,经营周边,不是要简单地发展和它们的经贸文化关系就够了,而是要帮助它们包括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努力提高它们各方面的发展层次和水平,使它们自身更安全,内政更和谐。只有这样,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才能有保障,从而造就唇完齿暖的良好局面,使纲维振于九州并进而使万邦谐和。
(五)中国又是多民族融合的“中国”
公元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时,汉朝征调车辆二万乘前往迎接,可是因朝廷无钱,只得向民间赊购马匹。有的老百姓将马匹藏匿起来,结果马不够用。汉武帝大怒,要斩杀长安县令,右内史汲黯①汲黯(?-前112),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汉武帝时,任东海太守,继为主爵都尉。以直言切谏闻名。后出为淮阳太守,在任十年死。汲黯在文史圈子里很有名气。譬如杜甫有诗云:“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又譬如曾国藩曾自称“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可见,对他们来说,汲黯是一个值得作为参照或者对照的人物,所以知名度可想而知。言道:如此兴师动众地为胡人打算不值得,因为这样会造成“天下骚动”,“罢敝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但是“汉武帝默然”。汲黯认为武帝优厚胡人的做法是“庇其叶而伤其枝”的行为。[32]汉武帝并没有答应汲黯的建议。
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官员看来,中国与匈奴是树枝与树叶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是根本,匈奴次之,但是汉武帝则希望把匈奴改造为“新中国人”,没有接受汲黯的建议。可见汉武帝开始产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概念,至少已经产生了这种思维。
在中国认同的历史回顾中,也存在过民族排挤主义的思想。比如,由于历史所形成的原因,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成为一种常态,是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趋势实际上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狄扰乱华夏,宜早绝其原,因此作《徙戎论》以警示朝廷:说夷、蛮、戎、狄,过去都住在要服荒服地带,他们“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戎、狄乘“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而“得入中国”,从此“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秦始皇则使“中国无复四夷”。但汉朝则将戎、狄引入关中,以至于造成今天之“夷、夏俱敝”的局面。江统认为“关中土沃物丰”戎、狄’无资格在此地居住,因为他们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其生活在畿服之地,久而久之,他们必然“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因此,应该将他们赶走,让他们回到他们该回的地方,只要“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图谋华夏之心,有战争的警报,因其“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也不大了。[33]晋惠帝没有采纳其建议。
(六)通过变革制度来巩固“中国”认同,主要是能够安天下的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还处在半华夏和半夷狄状态的诸侯国,总是通过建立战功等积极维护“中国”即周天子的威望的手段,以赢得“中国”的认可和加封,而如果种种努力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则一切努力就几乎付之东流。正如齐桓公所抱怨的,“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34]此段的白话文是: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呢?”齐桓公如此重视周天子认可,主要就是因为周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以礼乐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和文化。春秋时代晋国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利益着想的法官祁午对当时晋国的卿大夫,政治家、外交家,为国鞠躬尽瘁的贤臣赵文子说,“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讟,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35]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段文言的意思是,“在宋国的盟会,楚国人占了晋国的先。……两次会合诸侯,三次会合大夫,使齐国、狄人归服,使华夏的东方国家安宁,平定秦国造成的动乱,在淳于修筑城墙,军队不疲弊,国家不疲乏,百姓没有诽谤,诸侯没有怨言。天不降大灾,这是您的力量。”这是公元前541年发生的事。这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认为包括晋自己在内的“东方国家”已经是华夏之一部分了。而在此前110多年前的齐桓公时代,文明程度比当时的晋国要高得多的齐桓公还入不了华夏,还为自己被打入另册而愤愤不平,一百多年的光阴,至少晋已经感到自己是华夏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夷狄”或者是半夷狄。这里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进入春秋末期,中华大地上的“华夏”认同进入了快车道,一方面是行为上诸侯不服“周”,自己纷纷称王称霸,而另一方面,崛起的诸侯越来越在思想观念上把自身视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同时努力学习和吸收包括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传承下来的核心文明成果,兢兢夕惕,以经略四方。
古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始终注意创立先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国际交往方式,以此吸引列国对中国产生仰慕之情和对中国的高度认同。汉武帝因过度宠爱皇太子而使其能力衰退,汉武帝发现之后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36]大唐的贞观之治的一大特色,就是天下诸侯都向往大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唐有一套吸引和教化天下诸侯的先进制度文化。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盛赞之:“御宇恢皇化,传家叶至公。华夷臣妾内,尧舜弟兄中。制度移民俗,文章变国风。开成与贞观,实录事多同。”达到唐朝诗人王履贞所描述的“异方占瑞气,干吕见青云。表圣兴中国,来王谒大君”之盛况。
(七)强调对“夷狄”讲道德、正义和诚信,是中国之福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37]孟子“以德服人”的思想,实际上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对外政策的根本法则,所以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中国应该是德义和正义掌握在中国手中,而不是在对方手中的中国,失信的在对方而不在我方。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在中国和敕勒部落首领薛延陀关系尚处于良好的情况下,契何力上书“不可与薛延陀通婚”。太宗同意,并设计使对方反以自己失信放弃通婚。为此,褚遂良上疏反对这样不讲信用的行为,他说,唐太宗对薛延陀“玺书鼓,立为可汗”和“许其姻媾”之事,就连“中国童幼”都一清二楚。他强调应该继续保持“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的美德,因此背约实在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就不能善始善终呢?龙沙城以北,薛延陀的部落众多,“中国诛之”,终究不能全都消灭干净,因此“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38]很可惜的是唐太宗不听其谏议。
中国是以德服远的中国。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结骨自古未通中国,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首领失钵屈阿栈到唐朝。太宗在天成殿宴请结骨首领,失钵屈阿栈请求封他一个官职,说“手执王笏归国,实在是百代的荣幸”。唐朝于是以结骨所在地为坚昆都督府,任命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属于燕然都护。又在阿史德时健部落所在地设置祁连州,隶属于营州都督。当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辛酉(初十),太宗召见各国各族使者,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39]
公元前60年,主管外交事务的大鸿胪萧望之响亮地提出“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的思想。[40]他在汉宣帝时代的公元前57年,力排众议,反对“因其坏乱,举兵灭之”的政策,他认为先前的“单于慕化乡善(仰慕中国的教化,一心向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如果“今而伐之”,则“是乘乱而幸灾也”,他们“必奔走远遁”。他主张如果“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不可乘人之危,而是应该“辅其微弱,救其灾患”。这样,“四夷闻之”,则“咸贵中国之仁义”。[41]他的主张为宣帝采纳。
要树立一个讲仁义道德的中国形象。礼仪之邦大概就是这样慢慢树立起来的。
只要能够达到捍卫“中国”的形象的目的,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对夷狄表达真诚之意。比如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单于派使臣到长安,要求作为人质的儿子回国。朝廷想派遣卫司马谷吉送郅支太子回国,御史大夫贡禹等人认为郅支单于所在绝远,又归化之心未彰,建议朝廷使者送郅支太子到边塞就可以了。而卫司马谷吉上书说,“中国与夷狄的恩义绵延不绝,现在已经在国内养其太子十年,德泽甚厚,如果不把人送到老家,有弃捐不顾的意思,会使匈奴忘记前恩而生怨心。我有幸能成为使臣,肯定要勇敢前往。万一匈奴杀掉臣下,肯定会畏罪远逃,我国边境就会安宁清静。死掉一个使臣而使百姓安乐,正是为臣所愿。”[42]结果确实是谷吉到达目的地之后,真的发生了“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的惨剧。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仁义之邦和讲信用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屹立不倒,这和历代仁人智士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国家形象关系很大。中国人对待蛮夷应该做到仁至义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感化他们,使他们归顺,并最终得到教化。
(八)中国又是一个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气概面对好战而强大的外敌的中国
中国最早的4000多年前就产生的地理文献《尚书·禹贡》,在讲到古代王畿外围疆域之一的“绥服”时,就提出“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意思是在绥服内三百里范围内着力发扬文教,在外二百里的范围内要奋力发展国防,且提出作为软实力的文教的发展和作为硬实力的国防发展在不同区域应各有其重点的谋略安排。这样,“荒服疲中国”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在汉朝之初大一统的中国形成的过程中,匈奴等强敌林立,中国依靠武力是很难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的,除了保持抵御外敌的硬实力之外,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中,当时的中国更是在谋略等软实力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比如,公元前169年,“匈奴寇狄道,时匈奴数为边患”,除了使用“良将”之外,“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43]可见,当时的中国,也是一个谋略取胜的中国。强调“中国”应该是谋略和发挥自身的长处以取胜的“中国”,是谋略上更强大的中国。元朝至元五年颍州同知归旸,进士出身,他向皇帝提出“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44]的谋略,这是来自知识分子比较早期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谋略,只是未被采纳。
(九)以不疲惫它国的求实精神而非形式主义确保中国的稳定和安宁
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文武百官又请行封禅大礼。开始时唐太宗不以为然,但群臣不停地劝说,动摇了太宗。但魏徵认为,这样做不光劳民伤财,而且可能会把一个刚刚稍有些许安定的“中国”又弄得很不稳定。涉及到国际政治的问题上,唐太宗和魏徵有过一番对话。唐太宗问魏徵:“中国未安邪?”“四夷未服邪?”魏徵有“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的回答,他认为这样还会造成“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等严重后果。[45]
(十)少数民族对自己是中国人也有高度的认同
中国不光是汉民族的中国,也是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也称自己为“中国”。我们从北魏名臣高闾的上表中可以应证。北魏建武二年(公元495年),高闾上表,“天时尚热,雨水方降,愿陛下踵世祖之成规,旋辕返旆,经营洛邑,蓄力观衅,布德行化,中国既和,远人自服矣”。[46]“踵太武之成规,营皇居于伊洛。畜力以待敌衅,布德以怀远人,使中国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镇,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远。”“臣闻《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从容伊瀍,优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国缉宁,然后向化之徒,自然乐附。”“汉之名臣,皆不以江南为中国。且三代之境,亦不能远。”[47]
这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对自己身份的很关键的认同。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非单一民族而是多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上的确定和认可。这种对自己身份认同上界定自己为“中国”的民族心理,对今天各个少数民族认同自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和中国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蒙古族统治中国的元朝至元元年,大臣徐世隆向皇帝奏道:“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庙。”元朝皇帝“从之”,很快建好了庙,把祖宗神御迎进去。这表明,蒙古族统治者也有高度的中国认同意识。
(十一)“中华正统”观为核心的中国认同价值取向
前秦苻坚和苻融兄弟,在民族认同上,内心深处有强烈的自卑感,在他的王朝决定入侵东晋之时,其弟苻融这样劝说他:“‘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48]“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的认识,在文化心理学中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首先,如得“中华正统”传承,则属不可战胜之力量;第二,“中华正统”不但代表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代表文明的最高水平,其中军事文化也应该处于最高境界,而“蛮夷”不可能随便挑战的;第三,如果失去“中华正统”的地位,则情形另当别论。在日本等国的一些人看来,由于蒙古人和满人曾经统治过中国,因此,在蒙古人和满人统治下的中国,实际已经失去了“中华正统”的地位,而是由仍然保持着儒家文化的日本、朝鲜甚至越南继承之,它们反而成为“中华正统”。
(十二)把“中华”与“夷狄”视为平等的关系
西汉重臣萧望之在公元前52年,力排众议,反对丞相、御史所说的“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成例,不认为“匈奴单于朝贺”,其礼仪必然在诸侯王之下。当时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他还引用《尚书》中“戎荒服”,朝贡以否任其自然的道理,来说明平等对待“戎狄”,是万世之长策也。皇帝以“朕之不德,不能弘覆”的谦卑心态采纳了他的建议。当然,萧望之对“荒服”的政策,应该是受到荀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就是荀子思想的实践版本。荀子说,“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49]萧望之的平等对待“敌国”的主张受到主张强权政治的荀悦①荀悦(148-209),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幼时聪慧好学,因家贫无书,每到人家,遇书即读,过目成诵。12岁时,能说《春秋》,尤好著述。灵帝时,因见阉官用权,托疾隐于家中。献帝时,应曹操征召,历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的反对和批评,荀悦认为萧望之的壮举是“僭度失序,以乱天常”的行为,认为如果只是“以权时之宜”,则可“异论矣”,而如果是战略性思维,则是万万使不得的。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平等思想——萧望之的国家间平等思想的实践。应该说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今天对外政策的一个历史文化基因,非常宝贵和重要。
唐朝诗人杜审言的诗句“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所表达的,其实就是国家间应该平等相处和平等来往的思想。古代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可以算得上是真正实践“中华”与“夷狄”同等对待思想的帝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四方夷族君长到宫阙来,请求唐太宗做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都向唐太宗高呼“万岁”。此后在赐给西北君长玺书中,都称唐太宗为天可汗。[50]在今天看来,“天可汗”算得上是名义上的“世界领袖”。这一荣誉如何得来?其实就是唐太宗对外政策上讲平等和相互尊重。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亲临翠微殿,问身边的大臣:“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唐太宗说:“不然。……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1]
(十三)决不囿于自身文化的先进性,也努力吸收外来文化丰富“中国认同”
宋朝诗人度正有诗云,“来为中国用,往往四夷出”。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再也明确不过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外国有很多好东西,引进中国来能够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金代思想家哲学家李纯甫曾断言,“西方有中国书,中国无西方书。”显示他过度的文化自信。他说,“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意思是说外国只有文教,而中国有高于文教的“心学”,他的心学概念和今天的哲学概念相似。这一方面确实有华夷观在作怪,但今天看来,以《周易》、《道德经》、《庄子》等为代表的哲学经典,就其哲学层次来说,即使和古希腊哲学相比,恐怕思想性的哲学层次都要高于它们。但是过度的文化自信发展到极端也会走向保守和僵化,晚清的官方中国文化排外性和严重保守性,就是一个突出的佐证。而正是“西方有中国书”,它们充分吸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又加上充分发扬了西方自身的文化优势,所以使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发展史越是往前推,开放度越高。也就是说,文化的开放性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以胡服骑射为例: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在进攻中山国途中决定带头改穿胡服。当时反对者劝道,“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这是僵化不懂得变通。赵王认为,“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赵王以赵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军事的复杂性及胡服骑射对战争胜利和国家安全的意义劝说之,最后达成共识,改变服装,赵王正式下达改穿胡服的法令,提倡学习骑马射箭。从赵王决定胡服骑射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认同”,也不仅仅是陶醉于自己文化完美的认同,同时也是努力吸收华夏之外优秀民族文化的过程,因为这不仅仅是丰富自身文明的需要,也是保障社稷平安的需要。
四、如何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认同。“中国”的概念,一开始就有“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含义。不但如此,中国地理空间的扩大,主要依靠的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的影响力,就连中国第一个似乎是武力完成的秦王朝的大统一,在实现天下统一之后,它都是首先抓统一文字和统一度量衡等文化的统一,用文化的统一巩固地理和土地的统一;在传统中国政治精英的思维谱系中,自身力量不济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在内政上搞好自身核心区域的安全与繁荣,认为“中国治理好,则‘四夷’自然宾服。”这不但体现了历史上的中国不但是知足的中国,也是非常懂得内政与外交“和平辩证法”的中国,而不是像罗马帝国那样用对外战争来“弥补”自身的虚弱,这种思维,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在发挥着重要影响。比如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中国经历“文革”而造成的一定程度的“虚弱”局面下采取的主要是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的思路;中国的概念也决不是汉族一统天下的中国,而是汉族以外的众多民族团结融合的“中国”,中国文化也决不是儒家文化的单一文明,而是任何有利于中华民族团结与和谐的多个具体的不同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和谐共处,相互容忍,相互借鉴的文化共同体;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十分重视通过主要是能够安天下的制度文化来巩固“中国”认同,因此这样一种制度文化是稳定的、有继承性的,而且是在中国产生积极影响的,因此在今天也是有重大积极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充分继承了自秦朝到清朝结束政治制度合理成分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最明显的变化是废除了皇权,而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基本上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并在传统基础上增加了表达人民地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从理念的层次上讲,也是几千年来“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制度文化不可能接受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那是因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确实存在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巨大差距,就正如西方世界也不可能照搬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一样;中国历史上强调对“夷狄”的诚信,不但是承诺,而且更是几千年来对外关系的实态,而且在唐朝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中华”与“夷狄”的平等关系,那时的仁人智士,只要能够达到捍卫“中国”的形象的目的,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对夷狄表达真诚之意。这种诚信观,完全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自然继承,而且应该说是更加完善了。比如说“夷狄”观早就从今天中国的外交词语中抛弃了,并不像西方某些国家,不但在国家事务中经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随意地戴上“流氓国家”之类的“桂冠”;中国又是一个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气概面对好战而强大的外敌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而历史上那些用侵略挑战中国的种族,不是彻底地削弱了,就是消失了。今天也一样,任何企图用侵略战争灭亡中华民族的外邦,其命运也是彻底的削弱甚至面临灭亡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家主张中国应该是一个非强制推动“教化”的国家。以求实而非形式主义的方式确保中国的稳定和安宁的理念在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是以德服远的中国,所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不但赢得了当时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而且少数民族对自己能够成为中国人也感到自豪。古代的“中国认同”,同时也是开放的认同,努力吸收华夏之外优秀民族文化以丰富自身的认同。
五、结束语
以上所述历史上中国“中央王国”的实态与西方主流对中国“中央王国”的认识的反差之大是何其地明显。造成这种实态与认识反差之大的原因,最简单和最不负责任的说法就是西方所谓的“阴谋”论。公正地说,主要还是西方世界确实不了解中国的完整的历史,当然地就不了解中国具有国际政治历史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加上西方世界从它们基于人性恶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经常得到确认)对所谓的历史规律的一般判断,这种判断应用在历史传统和哲学思想与西方有很大差别的中国自然是错误的。解决这个认识上的矛盾的办法依靠中国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中国完整的历史,特别是几千年来展开国际政治活动时的价值观,但最主要的工作还不是宣传,而是中国持续地努力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实践几千年来业已运行良好的国际政治模式和理念。其实现代的中国总体上实践的国际政治,除了若干容易导致误解的局部性行动“印证”了西方的价值判断(比如说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朝鲜战争,中印战争等),但总体上中国给世界留下的印象还是一个崛起过程中完全不同于西方崛起的路径。只是这些积极的认识可能还只是一些支流,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洪流。当然,这些积极的支流,十分值得我们珍惜。西方世界最走红的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说,“至少是从1622年以来,当欧洲著名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来到‘中央王国’以图使中国人皈依罗马天主教,西方人图谋按照自己的形象重构中国,但是他们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并非是中国没有变化,而是中国总是要为重新获得权力而战斗,这个权力对所有的大国都是很珍视的,要定义她自己的价值,在不受梵蒂冈的别动队(va alien interference)干涉梅毒侵害的情况下,梦想自己的所梦想的世界。”[52]比如西方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华中心心态对外国企业在华利益并无破坏性影响。也许是美国企业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和中国发展更多的商务关系,所以它们面对中国的中央王国心态,并不感到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有什么大的不利影响。他们指出,西方的企业不认为中央王国心态(the Middle Kingdom mindset)将意味着障碍重重的道路(rocky road)……中国是一正在加强自己的思想和力量的国家,她以自己的方式日益地发展着,她也在加强自己的中心。那就是世人皆知的中华中心心态。”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以《中国:中央王国,世界之中心》为题,描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现状与动态,说事实上,北京当局所欲乃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其中中国享有举足轻重地位,但非龙头角色,中国政府寻求的是国际影响力之提升,而非主宰称霸,此诚非表面委婉辞令,吾人犹当记得,公元11至17世纪间,中国国力处于历史鼎盛期,非但拥有全球最庞大舰队,且经济科技实力坚强,但却未曾扩张侵犯其他文明,与当时欧洲列强大相径庭。日本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也指出,“试着读读中国人的历史,基本上没有什么主动侵略他国的事。当然,也有到印度支那半岛、朝鲜半岛甚至想来日本的情况,但是没有像欧洲以及欧亚大陆西侧那样治乱兴亡那么严重的行为。这是由于汉民族存有中华思想,在意识上满足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有着家长观念,认为如果自己强大对方会来朝贡,来朝贡的都是好孩子,所以要给予其礼物的,中国就是这样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讲,难道中国不是与欧洲很不一样吗?”[53](P169)2008年8月《耶路撒冷邮报》的一篇题为《中国与西方再相遇》的文章还算是找到了正确理解中国的思维,文章指出:“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地区主宰。它的软实力扩展到东亚最边陲,它的富庶引来西方胆大的探险者。‘中央王国’长久以来都被视为领导。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外国入侵者摧毁了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对一个传统地区强国来说,国土被外国列强分割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耻辱。现在,中国人正恢复过来。”[54]
[1]宮家邦彦.存在しない「中華思想」という言葉[M].PHP出版,2013.
[2]北京五轮/中国は主催国の品格示せ[N].世界日报,2008-07-29.
[3]弱かったスコットランドの独立の切実さと大義[N].世界日报,2014-09-21.
[4]孙子兵法·火攻篇第十二.
[5]Henry A Kissinger.Face to face with China[N].Newsweek,Apr 16, 2001.
[6]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J].Foreign Affairs,Sep/Oct 1999.
[7]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美国衰落值得中印庆幸吗[N].金融时报,2008-10-02.
[8]Malia Politzer.Passage to China[J].Foreign Policy,Jan/Feb 2008.
[9]“BUSINESS INSIGHT: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N].Design Week,Jun 21,2007.
[10]“Mail Call:A Waking Dragon”[N].Newsweek,Jul 4,2005.
[11]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rade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Hearing on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and Renewal of China’s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EB/OL].http: //waysandmeans.house.gov/legacy/trade/105cong/6-17-98/6-17obri. htm,June 17,1998.
[12]Stanley Hoffmann.Pensees on U.S.power[J].Foreign Policy,Nov/ Dec 2001.
[13]Segal,Gerald.China’s changing shape[J].Foreign Affairs,May/Jun 1994.
[14]Shambaugh,David.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N].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New York,N.Y]07 Mar 2015:C.1.
[15]Richard Halloran.Reading Beijing[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 25,1999.
[16]Mendis,Patrick.The Sri Lankan Silk Road:The Potenti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4.2(Fall 2012).
[17]William Gamble.The Middle Kingdom runs dry[J].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00.
[18]Henry S Rowen.Off-center on the Middle Kingdom[J].The National Interest 48(Summer 1997).
[19]晋书:志第一·天文志上.
[20]孟子:滕文公上.
[21]战国策:卷四·秦二.
[22]战国策:卷五·秦三.
[23]战国策:卷十九·赵二.
[24]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二.
[25]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
[26]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八·汉纪二十.
[27]资治通鉴:卷第三十·汉纪二十二.
[28]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四·唐纪五十.
[29]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记十五.
[30]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
[31]清史稿·列传第三百十四·属国二.
[32]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
[33]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三·晋纪五.
[34]管子·小匡.
[35]左传·昭公元年.
[36]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
[37]孟子·公孙丑上.
[38]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39]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
[40]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汉纪十八.
[41]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
[42]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八·汉纪二十.
[43]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
[44]元史·列传第七十三.
[45]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唐纪十.
[46]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齐纪六.
[47]魏书·列传第四十二·游雅·高闾.
[48]资治通鉴:卷第一百零四·晋纪二六.
[49]荀子·正论.
[50]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
[51]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
[52]Garten,Jeffrey.Rogue elephant rampant?[N].Financial Times,Oct 21,1997.
[53]中曾根康弘,梅原猛.政治と哲学[M].PHP研究所,1996.
[54]Assaf Lichtash.China and the West revisited[N].Jerusalem Post-Jerusalem,Aug 20,2008.
[责任编辑闫明]
A Misinterpretation of“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hina”Hel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XIAO Gang
(School of Law,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Guangdong,China)
In the long course of China’s five thousand years’history,the connotation of“China”had extended itself from a geographical scope to a cultural one and then to the symbol of sovereignty.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a single ethnic nation to a multiracial one,China has set up its national image of peace loving through the advancement and worldwide promotion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Han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the intermarriage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way of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ethnic minorities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The reign of Emperor of Tang Taizong of Tang Dynasty was a critical period in which ethnic equality and the co-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had been highly valued.However,a misinterpretation has also been held by some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view the rise of China as a pursuit of hegemony of the“Central Kingdom”.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hina;the western world;the“Central Kingdom”
D82
A
1674-0955(2015)04-0094-15
2015-05-26
肖刚(1959-),男,湖南新宁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