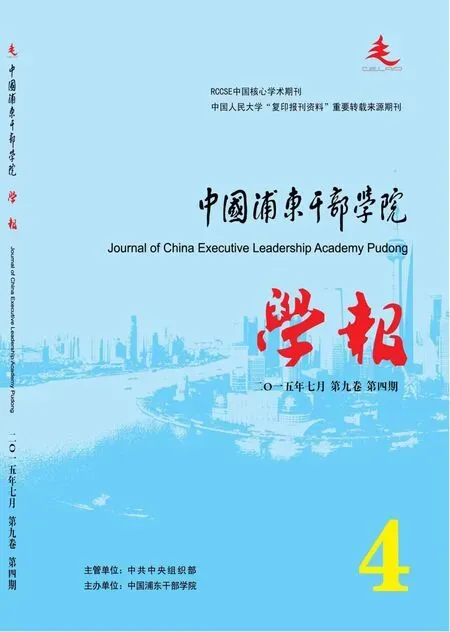“人的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赵泉民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上海201204)
“人的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赵泉民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上海201204)
国家在强调“人的城镇化”之后,又首次提出“人的新农村”,凸显了对新农村建设“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表明中央对农村建设方向在硬件建设基础上重点加强“软件”方面的投入。“人的新农村”一方面包括健全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关爱“三留守”群体、留住乡土文化和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另一方面也包括农民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素质能力、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与提升。而要建设“人的新农村”,需将“人的问题”贯穿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改革事项之中,诸如制度安排走出“重工轻农”的“偏向思维”;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社会对于农民的职业认同感;鼓励各种农民组织发展,促进村庄社会治理结构的“再造”。一句话,“人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冲破工业化、城市化的思维定势形成的“农村观”、“农民观”,强调在“共享的人性”的理念下重新审视“农民”身份的“单一”、“唯一”框定。否则,其最终也只能在事倍功半中折腾式前行。
人的新农村;现代化;制度设计
现代化带来了中国的“转型社会”,①按照社会学家金耀基的观点,“转型社会”是指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的存在可能时间很长。也即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见秦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所以,“转型社会”与“社会转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绝不能混为一谈。其给农民的“重大冲击”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及福利的客观条件变化,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二是农民渴望的上升。两者交织,加之社会流动性加剧和各种形式现代传媒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化”,在不断将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现代性质素带给乡村的同时,也驱使了“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对村落社区的浸润与改造。而在此过程中,农民正在蜕变成为“被遗忘的人群”,不再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城乡之间“断裂”的原因与后果。基于此,2006年中央开启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新蓝图。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城乡关系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国家在继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强调“人的城镇化”之后,又首次提出建设“人的新农村”,凸显了对新农村建设“更新”和“更高”的要求。笔者拟对此做一解析,以有资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
一、何为“人的新农村”?
要理解“人的新农村”的内涵,其基本前提是先要理解“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论点认为,工业化进程与某些普遍的社会政治转型紧密相连,在此之下,“所有社会都会朝向一种可预见的‘现代’或者‘工业’社会模式发展。经济发展与一系列转变征候相关联,不仅包括工业化,还包括城市化、大众教育、职业分工专业化、官僚化以及通信的发展,然后它们又与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及政治转变相关联。”[1](P3)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全面进步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更是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当然,言此并非是在否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本原目标”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要使所有的人能够达到丰裕富足的生活水平,即人是所有领域发展的“最高目标”。正如迈克尔·P.托达罗(Michael P.Todaro)所言:“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2](P50)易言之,发展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不仅是社会系统的全面进步和外部性最小化的社会全面发展,而且也是社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木桶理论”就典型地说明了孤立、片面的发展即外部性问题普遍存在的发展都最终会阻碍社会的前进。所以,时至今日,已很少再有人主张仅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个人收入的多少为标准去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进步。[3]这其中缘由就在于,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归根到底取决于其人口的素质特点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发展最终要求的是人在素质及生活质量方面的提升,这种提升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化无论是何种层面,也不管是哪个领域,其始终都回避不了一个“共同课题”,即人的现代化和民众幸福指数的提高。正是如此,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4](PP4-8)一语以蔽之,社会发展的最终都要归结为人的现代化或人的发展。可以说,任何一项发展战略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涉及到的人的因素而非其他。
“人的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离开了人的发展,一切的发展都将失去依托。以“人为中心”来论,现代化至少要有四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以人为本”;二是必须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即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现代化;三是包含着制度创新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在规定;四是坚持社会可持续性。凡此种种都指向了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近年来提出了“人是发展的中心”、“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诸多理念。当然,这里的“人”是指所有的人,是没有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差别的人,没有供体和受体之分的平等的人。其中,自然也就包括广袤乡村和为数众多的农民在内。“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5](P1)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言,对于农民的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更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的“普遍性议题”。社会学家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发展规划的失败”,“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中,农民至少占人口的3/4。……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够实现。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的多数人口必须改变生活方式。”[6](PP320-321)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社会,若是要良性发展,就必须要研究农民和关心农民,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发展战略或部署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对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且农民依然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基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命运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前途。而且,农村现代化核心是村域之中人的现代化,也即农民现代化。简而言之,农民现代化既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必要条件”,又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这一高度来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中央提出“人的新农村”的要义所在。
“人的新农村”理念的提出,凸显出现代化中“人”是最终发展目的之思想。也表明未来国家对农村的建设方向与过去相比要进行重大调整,在硬件建设基础上重点加强对“软”的方面的投入。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针对“农村空心化问题”极为严重,着力建设关爱“三留守”人员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养老、教育、医疗等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作兜底,让“三留守”人群在生活和精神上有依靠、有保障。目前对留守群体关怀的“软性的制度”还不完善,需要相应投入推进。二是针对村容村貌脏、乱、差和环境污染严重,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村庄管理水平,形成一套类似城市的建设管理制度,如对垃圾分类管理、河道污染治理、养殖污染清理进行制度化规范等,筑就新农村的生态文明根基。三是针对农民还是依靠传统经验种地、种植规模小和闲置劳动力较多的现实,建构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培养与大机器、大设备、大技术、大市场有机组合的现代职业农民,让他们有机会成为高级技术人才,提升农民职业化水平与职业荣誉感。四是针对“空心村”、“千村一面”和乡土文化“荒芜化”等现象,加强村落文化保护,出台相应政策法则规范村庄规划及整治,力求按照村庄原有格局进行,让村庄记得住乡愁和后代有历史的记忆。
综合起来,从理论上讲,国家治理的好坏首先要看其不平等程度,社会平等及提高全体人口的福利是衡量一个国家成就的关键指标。[7](P29)这也就决定了健全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关爱农村“三留守”群体、留住乡土文化和建设农村的生态文明,必然是推进“人的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尽管不是全部。另一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素质能力、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也都必须是“人的新农村”所要考虑内容。因为“农业现代化的中心总是在于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即从不愿冒风险和‘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行为者——资本家式的农民”。[8](P458)总之,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已经到了要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的“新阶段”。
二、为什么要进行“人的新农村”建设?
实际上,“人的新农村”建设命题的提出,不仅昭示出人们对新农村建设十年的“反思”,体现了社会对所谓的“新农村”认知的“深化”,而且也意味着政策层面正在由过去单纯的“物的建设”过渡到“物”与“人”的建设“同步推进”,从先前的“一条腿走路”演进为现在的“两条腿并行”。其中缘由就在于:过去十年,尽管新农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农业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但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较大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农业还是“五化同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同步发展)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9]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远未确立,权利意识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中“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越发严重。所谓“农村空心化”,具体在人的层面就是“人口空心化”,即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致使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断“外流”,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村庄出现“人走房空”现象,并以此为基点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客观言之,此种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资金等要素资源自由配置的结果。但下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农村空心化,与国际社会有着极大不同,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特殊体制背景下,政府长期重视工业和城市,导致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过度汲取”的一种必然。长期以来,国家制度安排的“城市偏向”和二元结构的“遗留”,表现在农业上,就是计划经济的“剪刀差”结构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后遗症”;具体到农村建设上,就是公共财政支出及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体现在农民权益上,就是各种权利以及国民待遇上的非平等性。城乡、工农之间这些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比较劣势”,自然会造成经济增长成果很难被回馈传递到那些输出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乡村,加上农民理性化和农业吸引就业的竞争力弱,最终驱使大批青壮年农民离乡入城以寻求更高的非农收入。即便是取消农业税和实行“四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系列惠农政策实施后,在乡务农收入还是远低于城镇务工收入。许多农民无可奈何地说,“辛辛苦苦种一亩田,不如外出打两天工”。即或是现在,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脚步并未放缓,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8年进城务工农民数量为2.25亿人,六年中逐年攀升,2013年总量达2.69亿人,2014年为2.74亿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10]然而,在城镇务工农民工既不同工同酬,又不能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出于经济收益权衡最终也只能把部分妇女、小孩和老人留在农村,形成了独特的“三留守”群体,继续着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留守妇女达5000万人,留守老年人约有5000万人,且总体规模继续呈扩大之势。从“三留守”群体的数量上,我们不难看出,村庄空心化已成为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二,农民的个体化、功利化的“过度膨胀”与对村庄认同感的“极度弱化”,导致乡村社会正在呈现出“整体性衰败”。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市场经济理念对乡村社会浸润的处不在,正如论者所分析的,市场化改革致使中国(包括农民在内)“更加追求自由、独立,呈现较为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特征”和“开始表现强烈个人主义的特征,并对自身权利有着强烈的认知”。[1](P35-36)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从家庭、亲属关系、单位或集体、社群(社区)和阶级等结构性藩篱中解脱出来,日益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不仅如此,他们的行为逻辑和道德观念已深受市场经济原则的影响,一方面越发趋于理性和算计,另一方面表现出对财富追求的狂热,“发家致富成了其支配性的价值信仰”。[11](P57)在此之下,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趋向于现实利益的交易,甚至在一些农村,人际交往完全为“利益原则”所驱使,而问题就在于村民个性和自主性在私人领域过度膨胀又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社区意识瓦解,“对群体及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12](P260-261)由于村落中每个村民的立足点始终是如何实现个人及其家庭的福利和利益的最大化,都在盘算着如何从集体行动中获得好处,都在想“搭便车”和坐享其成,同时尽可能地推卸和逃避社区的公共责任,致使农村内生性社区组织的消解和衰落,人际关系越来越私密化。笔者在调研中,乡村干部普遍反映,现在的农民是“给啥啥都要,要啥啥没有”。因而,与农民个体化进程紧密相系的,必然是乡村的“社会形态解体”(disintegration of social forms)。比如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相比,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不管是在乡还是离乡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对乡土及基层共同体的认同正在减弱,对农业活动、农村一些习惯和传统表现出现不认可、甚至是批评的态度,心生的是城市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农村生活的“厌恶之情”,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拥抱”城市。[13](P61-256)概括言之,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农村必然会进入到生态恶化、生产衰败和社区社会关系日趋瓦解、乡土文化体系性消亡的“整体性危机”之中。
第三,新农村建设政策目标“被曲解”而导致的实施中过分注重“物的建设”的偏差。应该说,“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体现了国家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及政策本意和目标,试图通过该项制度安排来推动六项具体任务:即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造就新型农民;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显然,新农村建设至少在政策层面上有着全面、系统和完整的内容,而且在推进中也要求重视各个方面的统筹协调,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但在具体实施中,许多地方把新农村建设变为易见成效的村容村貌改善,侧重于改善基础设施或是“涂脂抹粉”、“以点盖面”等,“钱多盖房子,钱少刷房子,没钱立牌子”,对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态、培育文明乡风等投入大、见效慢的工作重视不够。有的地方更是忽略了农村特点和农民需求,把发展城镇思路简单套用到农村工作上,以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农民住上楼房、通上水电暖就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9]笔者在许多地方实地调研中也深切感受到这一点,谈及新农村建设,县乡干部头头是道,然内容及工作重心多是聚焦在村庄整治、改水改厕、修路栽树和美化绿化村庄环境等方面,至于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则或多或少地有着畏难情绪。发展农村经济,面临行政推动不灵、工作没抓手等难题。无需置疑,经济基础对于农村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物的新农村”,农村必然落后。但若多数地方用较多精力给予“物的新农村”以较多关注,那么“人的新农村”建设力度自然就会“被弱化”或是“边缘化”。然而,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除了对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文化、公共服务等诸多层面的需要。新农村建设本意受到歪曲,政策目标被曲解,就会“在一些范围内出现政策微效现象”,[14](P35)即“制度文本”与“实践效果”之间差距造成了新农村建设“制度堕距”:农民主体地位未得到尊重,农民主体作用未得到发挥,农民的心声未得到倾听,农民的利益诉求未得到满足,农民的潜力未得到挖掘,农民的生活水平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最为严重后果是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如党群、干群关系,社会公平与公正及制度信任等方面的“倒退”,甚至是许多村庄因此已陷入到信任、价值、伦理和治理等新的危机之中。
第四,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上看,也需要注重“人的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基层、最坚实的脊梁,农村和农民发展程度决定着我国的整体发展。若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梦首先应是“农民梦”,也理应包含他们的中国梦,而且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他们的参与。只有实现了“农民梦”,才能更好实现“中国梦”。实现“农民梦”,决不单纯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致富梦”,而是让每个农民平等享有成长进步、“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终达全民共同富裕的“美丽乡村梦”。所以,“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也就是说,“中国梦”落实到农民身上,就是要切实解决好农民生活的实际问题,真正考虑农民的心声,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这也就要求新农村建设中特别注重对“人的服务”:一方面需要针对特定的服务对象存在的一些困难或问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给予具体的援助及提高服务效果;而且还要帮助有问题的或陷入困境的人(如“三留守”群体,不能或不愿进城打工的“在村农民”及农民工等)发现并发展其人生价值,恢复其生活信念与能力。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农村正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中,对于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正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阶段的农民而言,我们若是依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已到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及自我实现等“非物质性需要”的急速“上升期”:包括满足主体——人心理方面的需求,如安全感、自由、防御实力、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需要;同时也包括参与感,如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等。这于无形之中自然也要求国家或社会关注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民,保护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给农民以应有的人文关怀,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否则,农村社会就会进入到幸福不再,乡土气息不再,乡愁也不再的衰败的“恶性循环”之中。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远比其他国家更复杂、更严重”。特别是农村普遍存在的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其不仅表现为农业生产主体的缺失、农村土地和房屋的闲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匮乏,也显示出农村社会治理基础的弱化、虚化和异化。而且其与“三留守”现象,城乡社会不平等的扩大①现今社会一直在以缩小城乡差别为己任,然而事实未见好转。这方面表现最为显著的,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是在加大,尽管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每年都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但两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仍然继续在扩大,2010-2014年两者之间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3190元、14893元、16649元、18059元和18952元。可以说,扩大之势明显。及农村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交织杂糅在一起,弱化了农民对改革开放在物质层面上“获得感”的同时,也对人的成长、生活及情感、心理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久而久之,对农村文化及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剧。不管做何而论,新农村建设都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如果过于强调物的作用,忽略了人的建设,就必然会在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出现落差和问题。正如论者强调的,“严重的不平等状况不仅会带来与社会差异相关的所有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分裂性的等级偏见,而且还会削弱社区生活、减少信任,增加暴力。”[7](P44)
三、如何进行“人的新农村”建设?
应该说,“人的新农村”命题的提出,显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也不是为了与“物的新农村”及“人的城镇化”对称,而是因为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突出的“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也仍然是在农村。毫无疑问,要解决好这一“短板”,“人的问题”才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它贯穿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改革事项之中,这是“人的新农村”的要义所在。所以,建设“人的新农村”,自然也就不应当是仅仅聚焦于农村的“新”,而是要基于人的“新”。
首先,政府的制度安排要走出“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偏向思维”和“路径依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农民被歧视的现象,“但在我国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时间持续之长也是世界比较少见的。”[15](P192-193)之所以会如此,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尽管国家对于农业、农村,特别是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一直在以缩小城乡差别为己任,但受制于原有的“路径依赖”及以“都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强势逻辑之影响,“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惯性施政思维在现实中并未消除殆尽,政府部门仍然在有意无意地沿袭着旧体制的衣钵;加之发展主义导向指引下,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多将“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两者的交织更加强化了各级政府“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市民轻农民”的社会等级发展理念,最终导致城乡之间的“制度差距”,即“一国多制”下的对于农民的“制度性歧视”。据粗略统计,城乡居民的待遇差别高达47项。具体包括生产资料占用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就业用工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兵役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生育制度、居住迁徙制度、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等。基于此,要想真正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其基本前提就必须是政府施政理念的调整:首先,要转变先前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思想意识,改变对农的“白眼”政策;其次,党、政府的各个工作部门要明确在新农村建设中职责和任务,视野不能只盯着城市、工作也不能仅停留在城市,应更多地向农村及农民倾斜;再次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尤其是对政府在“三农”的领域绩效评估应从传统的产出和结果转向服务质量和农民满意度,探索以农民的“满意度”和对农民服务质量高低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一个指标。在此理念转换的基础之上,需要提高政府系统的制度供给能力,强化“人的新农村”建设制度安排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如在体现地方特色和乡村气息的村庄规划,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化服务,城乡一体的就业制度及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土地运作,房屋产权管理,建筑物安全、避险与环保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安排与统筹,健全和完善“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化”。不仅如此,在制度供给过程中,还要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16]以此来提高农民对制度乃至于政府的信任,“当政府工作良好时,人们就相信自己的领导人。他们对政府表现的判断反映了他们对具体人格、机构和政策的评价。……如果一个政权要有大的作为,但执行的是不受欢迎的政策,就会降低人们拥护的程度”。[17](P311-312)
其次,培育农民权利意识与塑造公共精神,促使传统农民意识向现代农民意识转化。如上所言,“人的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关注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民,保护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需要在制度方面增强对农民群体关怀之外,更多地还是需要强化农民自身的权利意识或者是“公共精神”的培养与塑造。农民的权利意识,是农民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主体所应具备的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精神与法律价值观念,也是在现代生活中对权利和义务的价值判断及其规范化的认同。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所谓的“新型农民”,也就不能仅停留在强调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经济层面,更不应停留在一般性地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上,而是对农民的民主素质提高给予足够多重视。基于此,就需要我们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参与机制,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有助于公民意识提高的社会实践:一是加强农民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健全完善农村地区的选举、听证、信息公开、参与立法、社区矫正、陪审等制度;二是完善农民参与的直接、间接渠道,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众定期议事制度、行政复议制等。有条件村庄可尝试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网上沟通互动平台或决策信息的手机发布,实现所谓“电子民主”;三是提高农民参与的自觉性、主动性,促使动员型向自主型转变,避免新农村成为“政府的新农村”、“村长家的新农村”。如新农村建设中一些项目要围绕着所在地区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特征来进行,充分尊重农民在建设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并通过生产、生活技能培训对农民赋能。如此,新农村建设才能转变成为广大农民具有主体意识的一种“自觉行动”,新农村建设制度设计的本意方能彰显,目标才能实现。同时,通过类似这样的政治参与,农民能够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在得知和开始重视他人要求的同时,升华自己的公民意识。[18]实际上,这也就是农村社会学者在分析农村社会组织时所得出的判断:“组织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组织成员进入新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结束旧的关系、迁徙、改变自己的角色、权力和等级的自由就越大。”[19](P594)一句话,保持权利和义务、自由与规范、个体意识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各地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着眼点”之所在。
再次,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增强整个社会对于农民的职业认同感,让农村生活更有意义、农业生产更有价值。农民是建设和管理新农村的主体,建设“人的新农村”,实质就是要培育出真正在村的“人”,也只有村庄社会有了人气,资源才能回流。客观言之,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外流和农田“抛荒”现象,既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也是农业效益低,就业缺乏足够吸引力的表症。我国目前的农业,不仅产业结构单一、就业吸纳力低,且效率低下、务农收入少,农业就业缺乏吸引力。因而,为遏制农村青壮年劳力的过度流失、避免生产主体的缺失,政府可以对从事农业的青年农民进行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增强扶持力度和扶持效率,尤其是注重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生态旅游农业,以提高农业的经营收入、比较效益和现代化水平。其次,持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力度,弥补此方面的历史欠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在村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村庄生活提供便利。最后,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使在村农民感到生活有意义,生产有价值,这样才能长久破解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尤其是要把青年农民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使其收入多于至少等于外出打工农民。笔者曾专门针对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要回乡务农收入不低于外出打工收入,会有35.6%的人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直白言之,村庄社会的功利化和已深陷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的农民,唯一关注的只是如何增强自己和家庭的经济利益以及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可以说,个人权益成为驱动农民进行各类活动的一个“基本动力”,基于此,惟有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和政策倾斜的力度,真正让农业经营有效益和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增强农业就业的吸引力,才能逐渐富裕农民和提高农民,最终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最后,鼓励并支持各种农民组织发展,促进村庄社会治理结构的“再造”。国内外众多的研究和事实表明,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和农民集体行动是农民理性的体现形式。不仅如此,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农民自己的各种生产组织、信息咨询机构、经济研究机构、信用社和合作社等广泛的社会网络、社会组织,有利于农民实行自我保护。比如合作社组织,其在经济上是“对市场交易中谈判权力垄断者的抗衡力量”,实现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具体到今天,村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农民赋权,扩大农民的能力和资本来参与、协商、掌握影响他们的机构,即重构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来源。而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必须能够自我表达、获取信息,拥有更多的社会包容和参与,更多的责任和组织力量。农民合作社组织尽管在许多村落之中还不够强大,但需要看到的是,无论如何,它还是当前最有经济实力的组织之一,在“乡”及“村”地域之内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还是能够程度不等地影响到“管理层”决策。其以“集体的力量”在对村庄公共权力运行及国家权力运行形成“制衡”与“监督”的过程中试图去维护村庄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无疑改变了乡村原有的治理格局,并给现有乡村治理秩序增添了“新的博弈主体”,促使村域层面的“多方参与、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治理机制的形成。[20]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合作治理模式,相当大程度上可彰显“人的新农村”的内涵:强调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多元参与、民主协商、协同治理与均衡发展;强调拓展民间文化和民间团体的生长空间,突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农民本位、地方特色、民间本性和历史韵味。
总之,农村曾经是、现在仍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可以断定它在未来可见的相当长时段内,也必然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绝对回避不了的“议题”。农村的现状,靠城市的现代化覆盖不住,甚至靠城镇化也消除不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必然是要改变乡村,而且其改变的不仅是乡村的外在形态,还包括乡村的文化和农民自身。所以,从长远来看,农村必将是一个被现代化洗礼后与城市紧密相系的农村,或者是越来越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知识也必然会发挥其本该起到的作用,成为农民融入现代化重要而不是唯一的手段,故而农村的问题必须靠农村建设本身来解决。正是因此,也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物”的建设,同时也更需要注重软环境和软实力的建设,将“‘新’物”与“‘新’人”有机结合起来,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他们不仅仅只是在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的“获得感”。要做到这些,一方面需要国家战略更为均衡和稳定,中央政策要有足够的宽度与厚度,打破工业化、现代化的思维定势形成的“农村观”、“农民观”的偏见,更要在强调“共享的人性”的理念下重新审视“农民”身份的“单一”、“唯一”的框定;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系统自上而下转变政治文化,特别是制度安排中更加注重人的因素,回到对“人”的关切,才能为执政积累足够的道德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当然,对人的关切,并非只是简单地人性化,而是一切要以“人”为支点,或以“人”为目的。因为“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会比我们中的人目前所生存的极度不平等的社会更具可操作性。……降低不平等程度在最基础的水平上是从受地位竞争驱使的分裂性的、自利的消费主义社会整合性和从属度更高的社会发展。较高的平等水平有助于我们发展公共道义,有助于我们致力于为解决那些威胁所有人的问题而共同努力。正如战争时代的领导人所知道的,一个社会如果要同仇敌忾,政策必须是公平的,收入差距也必须缩小。”[7](P200-216)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考虑问题,不仅仅是农村问题,而是“转型社会”中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首要基点。
[1][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印金强,赵荣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3][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阮江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4][美]阿列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M].王晓毅,王地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7][英]理查德·威尔金森,等.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M].安鹏,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8][美]费景汉,拉尼斯.增长与发展:演进的观点[M].洪银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韩长赋.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12/23/content_1890469.
[10]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 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11]吴毅,吴克伟,等.转型中的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实证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1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3]吴理财.公共性的消解与重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4]郑传贵,卢晓慧.社会认知、实践机制与制度绩效——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5]卢现祥,等.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6]赵泉民.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3(1).
[17][美]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M].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8]赵泉民.农民的公民意识与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J].社会科学,2010(8).
[19]苏国勋、刘小枫.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III——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0]赵泉民.合作社组织嵌入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转型[J].社会科学,2015(3).
[责任编辑缪开金]
The People-oriented Countryside:A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ZHAO Quan-min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Shanghai 201204,China)
With the process of“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the input in talent cultivation,which reflects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untryside.The construction of“people-oriented countryside”ha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issues,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in public services,subsidies for the elderly,women and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In addition,the construction of“people-oriented countryside”also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thoughts,ability and behaviors.Viewing people’s livelihood as a starting poin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oriented countryside should ensure a proper resource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In addition to a cultivation of farmers’civic 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ncourage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mode with a higher level of self-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people-oriented countryside”requires a breakthrough of the typical perception of“rural area”or“farmers”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old-fashioned perception of“farmer”should be revised according to“a common humanity”,otherwi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oriented countryside will get trapped in unexpected twists and turns.
people-oriented countryside;modernization;system design
F320
A
1674-0955(2015)04-0043-09
2015-04-1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社组织与乡村社会互构研究”(09CSH034)系列成果之一。
赵泉民(1972-),男,河南省灵宝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博士;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