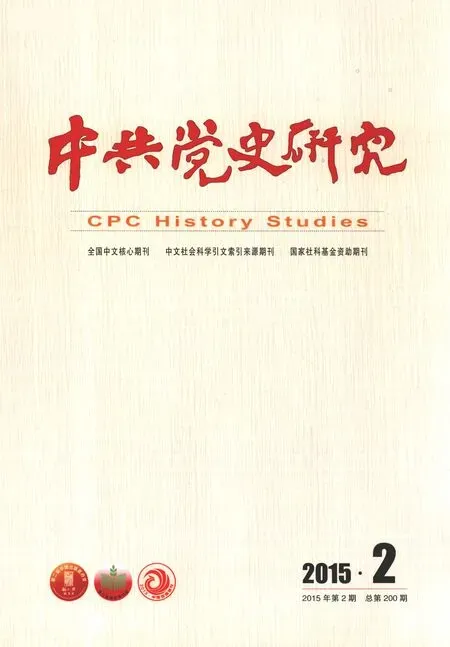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传播研究述评*
陈 红 娟
·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传播研究述评*
陈 红 娟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其翻译与传播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不过,上世纪的《宣言》研究或以学理性不强的撰写学习体会为主(50年代至70年代),或侧重于解读《宣言》观点、挖掘其当代价值(80年代至90年代),以翻译传播为专题的研究较少。新世纪以来,《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史料挖掘、新研究方法运用和新领域开拓方面涌现出许多新成果。本文试图对新世纪以来《宣言》翻译历程、汉文全译本考证、陈望道译本的专题研究、译词和译句考究、《宣言》传播等五个方面的研究状况加以梳理评价,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宣言》翻译历程
《宣言》在中国经历了30余次翻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译介(摘译、译述、缩译),一种是全译。《宣言》翻译历程的早期研究主要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史料梳理,散见于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学说翻译传播的著作之中①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专题研究较少。新世纪以来,学者们以《宣言》为个案,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大背景,试图从翻译的历史语境、主体选择、翻译策略及成因等多个角度展开专题研究。不少学者分析了《宣言》从只言片语的翻译到章节段落翻译再到全文翻译的过程②参见孙玉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4期;黄忠廉:《〈共产党宣言〉汉译考》,《读书》2009年第4期。,其中不乏资料详细、论证缜密、富有真知灼见之作。
方红和王克非从翻译学视角梳理了《宣言》在中国早期翻译的过程,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谁翻译了什么及为什么选择翻译这些内容等问题。文章指出,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文人蔡康雅对《宣言》的翻译,是一种“西译中述”式的合作翻译模式,附载在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中,随着“西学东渐”的背景进入中国。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主要从中国自有传统思想中选取了可对应的概念,如“大同”“均贫富”“安民/养民”等。李提摩太之所以引介马克思学说,主要是将其纳入他所提出的“安民”策略之内,成为他宣扬“新学”的一部分。③方红、王克非:《〈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外国语文》2011年第6期。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王海军④参见王海军:《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以〈共产党宣言〉为个案的分析》,《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
陈家新不仅将《宣言》翻译划分为清末民初的译介、“五四”时期的传播、1920年至1949年《宣言》在中国出版完整译本三个阶段,而且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特点:清末民初有11篇文章涉及对《宣言》的翻译,但多是只言片语和段落章节的翻译,属于自发的、初步的介绍;“五四”时期有七种《宣言》译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翻译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质,处于一种自觉研究介绍阶段;1920年至1949年则处于深入探讨阶段*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
禹雪运用“描述翻译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操控理论”“翻译准则理论”,结合《宣言》在中国近现代从初步引入到大规模翻译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探讨《宣言》翻译活动中所受到的历史、意识形态等“翻译外因素”的影响,从语言和修辞层面比较《宣言》各时期的翻译版本,探讨造成版本差异的原因*禹雪:“从描述翻译研究派理论看《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系,2005年,第v—vi页。。
二、《宣言》汉文全译本考证
与以往对单个译本展开碎片式研究不同,当前,学者们将《宣言》汉译本视为一个整体,不仅对大陆出版的多个《宣言》汉译本的作者、出版日期、参考蓝本等展开详细考证,而且在港台译本的甄别方面取得初步进展。
杨金海提出12种译本说——“从1920年到现在(撰文日期为2011年——引者注),我国大陆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共有12个独立版本。”这12个译本包括:新中国成立前6个,分别为1920年8月版陈望道译本、1930年3月版华岗译本、1938年8月版成仿吾和徐冰译本、1943年版陈瘦石译本、1943年版博古译本、1948年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新中国成立后6个,分别为1958年8月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1964年9月版译本(收入1972年5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1978年版译本(收入中共中央党校编《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并于1992年3月出版单行本)、1995年6月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2009年12月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1978年11月还出版了成仿吾的新译校本。*杨金海:《〈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光明日报》2008年7月3日;杨金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头一瞥——从〈共产党宣言〉重要语句的中文翻译说开去》,《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高放对杨金海的论述进行了补充,提出23种译本说。他补充了11种译本,分别是:东京的2个译本,即1907年留日学生署名“蜀魂”和1908年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用文言文出版的《宣言》汉译本;北京的1个译本,即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莫斯科的1个译本,即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1卷中的《宣言》译本;香港的3个译本,即1948年为纪念《宣言》出版100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乔冠华校译本,1998年4月香港新苗出版社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而出版的译本,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9月出版的译本;台湾的4个译本,即1998年4月1日台湾《当代》杂志刊载的译本,2001年7月10日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唐诺译本,台湾启思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译本,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的管中琪、黄俊龙译本。*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王保贤提出10种译本说。在明确“译本”与“版本”“版次”,以及“中译本”“汉译本”等概念的基础上,他列举了10个汉译本,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和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中央编译局译本、成仿吾译本、唐诺译本、管中琪译本。*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
全译本统计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尚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第一,杨金海和王保贤均没有提及东京的两个汉译本,那么,这两个汉译本是否存在?是否应该纳入研究?黄国秋和田伏隆在考证蜀魂的《宣言》译本时,肯定了这是我国最早的全文翻译,但也指出:“蜀魂翻译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是否已正式出版倒很难说。因为:第一,至今还没有关于蜀魂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几本书已被正式出版的任何线索。第二,据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些老同志回忆,他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所读到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都是陈望道同志译的。”*黄国秋、田伏隆:《蜀魂是我国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文章发表距今已30余年,但仍没有找到蜀魂译本,是否能够找到则需存疑。此外,陈家新指出,蜀魂译本并非译自《宣言》原著,而是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虽然这完全可以称之为独立译本,且是较早的汉译本之一,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该译本确实出版发行过。总之,无论从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还是从其所参考的蓝本来看,该译本的研究价值有待商榷。
对于民鸣译本,高放曾写信请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帮助查寻日本各图书馆是否藏有这一译本,但并无收获*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而金建陵考证最早的《宣言》全译本时,查阅了刊登民鸣翻译广告的《天义报》第16卷至第19卷合订本,但只发现了《宣言》第一部分译文。他推测可能由于篇幅较长,本打算分几次刊完,后来因故未能刊载完毕。因此,他认为民鸣翻译的《宣言》中文全译本是存在的,只是尚未寻见,其历史地位暂不能完全确定。*金建陵:《寻访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2期;金建陵、张末梅:《南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国内多数学者因当前只能查到民鸣在《天义报》刊登的第一部分译文而将其视为片译文而非全译本。笔者认为,要进一步考证民鸣译本是否存在并出版发行,还应结合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1908年以后遭受打压的情况以及《天义报》在此政治环境下停刊改版的命运来考虑。
第二,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究竟如何界定?当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宣言》汉译本研究较多,译本甄别方面基本达成共识,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宣言》译本,则由于缺乏对新史料的挖掘,研究比较薄弱。学界对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存在两种划分方法:一种认为应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即统称编译局译本,王保贤指出,“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可简称为‘编译局译本’),历经多次修订,通常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1998年以后,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过(到目前为止,该社已在两个时期出版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但这两个出版社出版的编译局译本,也只能算作一种译本,而不能把它们统计为多种译本”*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另一种认为中共中央编译局每一次修订都可以算一个新译本,持此观点者包括杨金海、高放等。那么,究竟如何界定更为科学?笔者认为,应该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转变为“国家行为”、中央编译局采用“集体翻译”方式这些事实来重新审视,而不能再采用按译者划分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前译本主要采用此种界定方法)。
此外,王保贤查阅195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译后记”以及1958年1月根据莫斯科版重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卷末的“重印后记”等资料,指出,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本、1954年译本、1958年译本均由谢唯真翻译、校译,将1958年版归为中央编译局版本有待商榷*王保贤:《编译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那么,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本、高放增加的1954年译本、杨金海所列的1958年译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1954年译本、1958年译本能否算作独立译本?这里一方面可以考证每个译本产生的背景与过程,进而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可以开展三个译本的文本比对工作,通过统计译本间的差异率进一步展开论证。
第三,港台中文版本如何梳理与甄别?港台译本为译本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但学者们对到底哪些港台译本可称为独立译本存在分歧。王保贤指出,高放所列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港台6个译本中,“只有唐诺译本和管中琪译本够得上称独立的汉文译本”,其他4个汉译本“都是由编译局译本移植而来的——尽管有的译本改动达百余处,但因为基本上都是相关同义词的置换(比如启思出版集团版把引言中的‘教皇’改为‘教宗’、‘当权’改为‘当政’、把第一章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改为‘各民族精神活动的创造物’)”,“这几种译本,是够不上称独立译本的”*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王保贤:《编译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高放则将6个译本单列,且与王保贤的评价不同,例如他认为1998年4月1日台湾《当代》杂志刊载的译本“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58年的第一次译文,但是又修改了几十处,也应该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那么,我们评判港台版本的标准是什么?研究港台版本的价值在哪里?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此外,在香港出版的乔冠华译本能否认定为独立译本还有待考证。陈家新“曾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本书原件,与成、徐译本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发现改动的地方达105处”*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范鸣强指出:“成仿吾、徐冰译本被乔冠华改动了160多处(不包括标点符号改动的170多处)”*范鸣强编:《红色经典第一书:〈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第305页。。高放表示,经过粗略比较,发现“改动竟有近百处之多”,提出“本书尽管乔木谦虚地仍然署名成、徐译,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校译本”*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三者均将乔冠华的校译本作为独立的新译本单列,而王保贤提出的《宣言》全译本则并没有包括校对本。那么,我们判断一个版本能否成为独立译本的标准是什么?经过大幅度改动的校对本能不能认定为新的独立译本?如果能的话,是否只要不同的译者进行了修改、校对就能称之为新的独立译本?修改幅度达到怎样程度的校译本才能认定为独立译本?除此之外,是否还应该考虑译本本身的特色和影响力?显然,厘清这些问题是学界进一步开展《宣言》译本考证的前提。
三、陈望道译本的专题研究
新世纪以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对某一具体译本进行专题研究。其中,对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研究较多*参见白鹤:《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赵英秀:《〈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广饶传奇》,《党史纵横》2012年第2期;黄显功:《〈共产党宣言〉中文初版问世的经过》,《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6日。。以往对陈望道译本的研究侧重于翻译传播的史料性介绍,以及对陈望道本人经历和贡献的零星梳理。当前的研究则更加注重结合历史背景探究译本产生的必然性。对陈望道本人的认识也逐渐由只言片语的描述转变为科学探究式的系统分析。许黎英、朱顺佐等探讨了陈望道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做的工作,如继续协助邵力子把《觉悟》副刊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抨击、批判张东荪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指导各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中国共产党等*许黎英、朱顺佐:《简论陈望道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建党活动》,《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宁树藩:《陈望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一稿的回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研究者在陈望道翻译《宣言》参考的蓝本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是英译本说。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写道:“陈望道主要根据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再参考日文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陈振新:《陈望道与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中华书局,2011年,第69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杨金海、胡永钦、邓明以等*参见杨金海、胡永钦:《解放前〈共产党宣言〉的六个中文译本》,《纵横》1999年第4期;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据叶永烈考证,陈望道的《宣言》译本主要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其依据是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与他交谈时指出,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问及《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依据英译本译的*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9页。。王东风和李宁则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因为译文中不少名词的后面都用英文做了标注,这是译本所据语言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
二是日译本说。陈望道接受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同志访谈时说,“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宁树藩、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生前谈话记录》,徐萱春、倪菊花主编:《陈望道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进一步指出:“陈望道翻译时依据的底本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收录的幸德、堺(即幸德秋水、堺利彦——引者注)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但他也承认两个版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日文译本中的恩格斯《致英文版序》在陈望道译本中并没有译出,而且译语也不尽相同,比如日文译本中的“绅士”,陈望道译本译为“有产者”,日文译本中的“平民”,陈望道译本则译为“无产者”。*〔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3—34页。陈力卫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陈望道译本将‘绅士、平民’分别译为‘有产者、无产者’,可能是受早期河上肇作品翻译的影响,即河上肇著作里出现的‘有产者、无产者’被原封不动地挪用到中文里”。“有些叙述说陈望道的译本以英文为主,参照日文,但我们在比较其语词对日语词的沿袭程度后,发现陈译本依据1906年日文版是不争的事实。”*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8年,第193—194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王东、陈有进等*参见王东、陈有进、贾向云:《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其实,要想厘清蓝本问题,还应该开展英文版、日本版和中文版《宣言》译本的比对工作。另外,就词汇相近问题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很多词汇都是由日本传入的,日语是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一个重要来源*参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该书中专门论及源自日语的社会主义语词。。不少译者在翻译时都曾借鉴日文中的汉字,“中国的理论翻译,凡有日文译本可供参考的,都从中得到不少方便,因为日译的名词、概念的用语大量采用汉字表达。在中国当时的译界,不采用日译用语的,实在非常少见”*侯外庐:《〈资本论〉译读始末》,《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73页。。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词汇多少来判定其蓝本。当然,陈望道的《宣言》译本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翻译时是否受到河上肇影响,与幸德秋水、堺利彦翻译的日文译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其译文中哪些是深受日文版本影响而产生的日语借词,哪些是借助英文翻译产生的新词汇,哪些又是由中国古典术语演变而成的?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宣言》译词、译句考究
新世纪以来,《宣言》研究逐渐呈现出具体化、精细化的趋势,《宣言》中的重要术语和译词的语义变迁、关键语句的译法以及翻译的准确性等问题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一)重要术语考证
“词义辨析,决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与思路》,《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2期。学者们不仅梳理了《宣言》译本中重要术语的变迁,而且尝试结合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挖掘术语生成的原因。
邱捷考察了“绅士”“绅士阀”等概念,探讨陈振飞《宣言》译文中使用“绅士”译法的缘由。在陈振飞的《宣言》译文中,虽然标题里的“bourgeoisie”被译为“绅士”,但内文中译成“资本家”的有38处,显然译者已经意识到“资本家”比“绅士”更为准确。然而,当时《民生日报》对占有农村土地的“富人”特别是农村的士绅持强烈的抨击态度,认为绅士阶层是共和民国的敌人,是社会改造的障碍,希望把思想武器用于同绅士的斗争,所以陈振飞翻译《宣言》的时候,明知把“bourgeoisie”与“bourgeois”译成“绅士”并不确切,也要用来做标题。*邱捷:《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译文》,《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马天俊分析“Gespenst”从1907年到1995年88年间获得汉语表达时的修辞学问题,结合东西方文化,比较了九个对应“Gespenst”的汉语词汇,即异物、妖怪、怪物、巨影、幽灵、精灵、怪影、魔影、魔怪等。他认为“异物”“妖怪”“怪物”似乎更为切合中国文化传统,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言语形态上背靠着西方形而上学史和基督教精神,同时这种言语又指向公众特别是无产阶级,指向特定社会行动。一方面,“Gespenst”因为讲了汉语,它在汉语读者这里便不能不发生某种变化而不复保持其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必定是诠释,是修辞学的再创造;另一方面,汉语因为讲述了作为“Gespenst”的共产主义的内容,汉语思想本身也渐渐发生变化,因为作为诠释的翻译只能是有意的创造。*马天俊:《对〈共产党宣言〉中国化的一点反思——Gespenst如何说汉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文中“Gespenst”是1995年《宣言》中译本第一句中“幽灵”的德文对应词,原文为“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陈长安认为,中译《宣言》“nation”译语,总体上经历了从“国民”到“民族”的译法变迁,而共产国际对中共民族革命路线和民族纲领的影响、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以及基于这种概念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这种译法变迁的重要背景*陈长安:《东亚马克思研究新进展——“东亚马克思研究的到达点与课题国际会议”综述》,《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这种结合词义、翻译的历史语境以及译者意图来探讨《宣言》重要术语转化成因的方式,为当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学者通过梳理重要术语在《宣言》文本谱系中的变迁,进而探究了语词运用背后的“用意”。陈力卫梳理1906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日文译本、陈望道译本、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译本、1958年中央编译局译本的关键词在翻译中对应“译语”的变化,发现“消灭”“反动”等词汇呈递增趋势,进而指出,中文版《宣言》在改译过程中,通过译词尖锐化迎合了突出阶级矛盾、提高阶级意识、凸显革命和暴力的时代趋势*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第190—210页。。
无论是对术语生成语境(文化、社会环境等)的考证还是对不同译本的比较,都可以说明一个道理——翻译即阐释。在翻译的过程中,通常会涉及译者身份、翻译意图、译文载体、历史情境、文化渊源、政治导向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那些参与著作写作过程的读者实际上处于一种强势地位,他们会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到著作中,也会通过著作来建构自己的政治立场”*〔英〕特雷尔·卡弗著,江洋编译:《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当然,《宣言》翻译传播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生成、再造、接受的过程。“当涉及观念跨文化传播时,除了必须注意该观念在原有文化中关键词的意义演变外,还必须分析中文里用于表达外来观念的关键词的原意,研究人们何时以及为何要用该词表达新观念。如果该词是翻译时新造的词汇,则需分析该观念在何时传入以及定名和普及的过程。”*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页。笔者认为,针对这些术语怎样诞生、怎样转变为具有“中国特点”的语言,同一词汇在不同译本中是否发生意义变迁,中国式的语言如何被接受等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关键语句辨析
理论界关于《宣言》重要译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消灭私有制”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两个句子上。
1.关于“消灭私有制”译法的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宣言》中“消灭私有制”译法不准确,应该将“消灭”改为“扬弃”。2000年,李桐通过对“Aufhebung”德文语义和“消灭”“扬弃”中文语义的考证,指出:“为了消除误解,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我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李桐:《〈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h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书屋》2000年第9期。董辅礽分析“Aufhebung”的具体含义,专门请教德国朋友,并联系《资本论》第3卷内容,提出:“在汉译《共产党宣言》中讲的‘消灭私有制’准确地说应译作‘扬弃私有制’。”*董辅礽:《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评于光远同志对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的论述》,《经济导刊》2002年第2期。张殿清认为,《宣言》里“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句话成了我们消灭私有经济的理论依据,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不是这样的,是中文版将它翻译错了。在《宣言》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张殿清:《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高放也曾在文章中说译为“消灭”是“误译”。但后来他的态度略有调整,并发文表示上述评论不当,应该收回,“只能说译为‘消灭’不如译为‘扬弃’更好”。*高放:《从〈共产党宣言〉的一处误译看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兼评〈两个“必然”及其实现道路〉一书》,《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高放:《〈共产党宣言〉对我国的深远影响及其核心思想辨析》,《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高放:《〈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辨析》,《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一部分学者肯定既有译法,认为译作“消灭私有制”是正确的。中央编译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的译法正确,无需修改*参见殷叙彝:《“扬弃”私有制还是“消灭”私有制——关于〈共产党宣言〉中一个重要译语的争论》,《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4期。。顾锦屏根据《宣言》上下文内容的一致性、两个英法权威译本中的译词、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提法等肯定了“消灭私有制”译法的正确性*参见顾锦屏:《〈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3期;顾锦屏:《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不朽著作》,《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王振中、韦建桦等*参见王振中:《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译法的正确性》,《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2期;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2.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法的争鸣
新世纪以来,随着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面世,有些学者注意到其中特别提醒人们留意一点,即1888年《宣言》英文版出版时恩格斯在末尾把“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改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ies, unite”*参见《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2年第2期;述弢:《先哲的遗言——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随笔》2005年第3期;等等。,进而展开了一场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讨论。俞可平随后专门撰文澄清,指出:“在《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其意义是相同的。”*俞可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从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修改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但这并没有在学界达成共识,2008年学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法的争鸣。
高放考证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74种译法,其中1908年至1933年有19种文言译文,1919年以来有55种白话译文。在考证、评析了百年来74种不同译法后,他以德文、英文、法文为原型分析所有译句主语、谓语、定语、语气助词译法,并结合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郑重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该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建议。*高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考证评析》,《文史哲》2008年第2期;高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可否改译》,《北京日报》2008年3月17日;高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3期。之后,《文摘报》刊出该文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均进行了转载。郑异凡随后发表文章,对高放的建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无产者是劳动者的一种,但劳动者并非只有无产者。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个特点就是阶级对立,而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不是一般的劳动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如果把“无产者”改为“劳动者”,《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则会改为“资产者和劳动者”,那么整篇文章就会变调。译文中的“全世界”这一译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强调的不是无产者的国家和民族属性而是共性,没有必要改为“所有国家”。最后,郑异凡指出:“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口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译文上都改不得。理由很简单,译文本身是准确无误的,而这一改动,其含义就变得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了。”*郑异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无需改译——与高放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2009年初,高放又撰文反驳了郑异凡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改译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他认为:无产者、工人与劳动者三者从狭义理解是同义词,因此“无产者”可以改译为“劳动者”;“全世界”的译法是意译,《宣言》最后一句话的德文原文、英法俄日等译文都是用“所有国家”*高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可以改译——敬答郑异凡、奚兆永先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
王保贤评论了郑异凡与高放的论争,认为高放把当今的现实情况作为改译的理由和根据,违背了翻译中“信”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应该联系的不是中国当前实际,而是《宣言》的“实际”,而且中国当前的实际与其他国家的实际也不同。他从“信”的原则出发,结合《宣言》的原文原意,指出高放在论证中存在引文片面、改译理由不充分等方法上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译法“符合《共产党宣言》原文(德文)的原意,是准确的”。*王保贤:《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问题——兼评郑高之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即使文本是以读者的母语写作的,由字面文字获得含义的解读活动也必然包含一个翻译的过程”*〔美〕卡弗著,张秀琴译:《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这就必然引起对经典著作翻译、解读的多面性。上述争论不仅关乎翻译的准确性,还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不同解读。争论中,一方注重历史视野,注重文本自身的“背景”,突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尽量使用一些让作者看起来“像那个时代的人”的词汇,译本突显的是相应的历史性;另一方则注重当代阐释,尤其是结合中国经验,从经典文本中获取含义,将翻译与当下所处的环境、对话的群体以及政治需要等因素相联系,结合“当前”境遇解读文本*参见〔美〕卡弗著,张秀琴译:《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第148页。。前者容易将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解为固定的历史存在,且文本语境、话语与当下的差异会导致文本难以大众化;后者则容易产生文本的过度诠释,导致文本原初意义的丧失。如何恰当、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实现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宣言》译词、译文的科学理解,是今后中国学人面临的重大课题。
五、《宣言》的传播
以往研究注重对《宣言》传播历程的概述,将传播史等同于翻译史。当前学界则逐渐从传播学、文本研究等多个角度探讨《宣言》传播的过程、特点、渠道等问题。
唐建阳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五W”模式是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P.Lasswell)在1948年提出的传播模式。该模式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描述传播行为: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分析了《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具体包括: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等等*唐建阳:《从“五W”模式看〈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王海军、黄家茂则结合中国历史语境总结了《宣言》早期传播特点:翻译与传播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传播内容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通过多种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播;等等*王海军、黄家茂:《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传播特点——以〈共产党宣言〉为个案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蒲国良梳理了自1899年《万国公报》刊登《大同学》到1998年发行《宣言》纪念版和珍藏版这100年间《宣言》翻译传播的历史过程,指出了《宣言》传播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如应重视对早期《宣言》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范围等的研究,对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没有转化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孙中山、戴季陶、宋教仁、廖仲恺等人的贡献应给予公正评价等*蒲国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
聂锦芳从文本学角度探讨了《宣言》成为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著作的原因。其一,就《宣言》自身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序列中,它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又是具体政治组织纲领,与《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大部头著作相比,易于流传,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接受;其二,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政治家成为主角时,他们的评价形成了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难以起到的影响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当大规模的出版、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时候,在普通民众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马克思主义画上等号了*聂锦芳:《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马拥军撰文反驳了聂锦芳的观点,他认为任何文本对后世的“影响”,不但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因素,而且还取决于读者的因素、受众的因素。评判一个文献是否经典,主要看它与读者产生了多大程度上的共鸣、能否与实践紧密结合,而不是篇幅大小、写作时间、政治家的影响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决定了判断某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单纯从文本学视野研究有其局限性。*马拥军:《〈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读法——与聂锦芳先生商榷》,《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
杨金海、胡永钦从出版和发行组织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宣言》的传播过程。文章指出,1920年李大钊组织的“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斋”即书舍)、1923年的上海书店、1929年的华兴书局、1931年的北方人民出版社、1931年的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8年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三联书店等翻译、出版机构都在《宣言》的发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杨金海、胡永钦:《〈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54页。。
无论是运用传播学理论还是文本分析,抑或是以发行组织、出版社为视角的研究,都推动了《宣言》翻译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剥离”,促使《宣言》传播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分支更加成熟。相信随着马列著作翻译传播研究的深入*参见王海军:《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翻译与传播的历史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5期;吴文珑:《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翻译与出版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胡为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学者们通过挖掘和掌握新材料,将对《宣言》传播展开更深入、系统的分析。
六、研究展望
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宣言》翻译传播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但总体来说,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入。
第一,突破学科界限,拓展研究领域。当前,《宣言》研究主要以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基础展开,学科界限较为分明,研究内容相对单一。虽然不少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宣言》展开探讨,但其中有深度的力作仍旧稀缺,一些研究成果在观点上重复或雷同,特别是研究的广度还有待拓展。比如《宣言》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领导人方面,普通民众、国民党中的传播研究还较为薄弱。其实,《宣言》除了对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国民党人朱执信、戴季陶等产生过影响外,也影响了其他国民党人。蒋介石1920年至1923年间的阅读书目,就包括《马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籍*王奇生:《蒋介石的阅读史》,《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4期。。而且,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俄考察,其间蒋介石较集中地阅读了有关马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那么,《宣言》在普通民众、国民党中是如何被接受、理解的?不同时期主流报刊、知识分子等对《宣言》的理解存在怎样的变化,反映着怎样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变迁?又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把德语、俄语、英语、日语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翻译成汉语文本,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那么,《宣言》译本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是如何实现中国化的?
第二,加强文本研究和比较研究。《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一系列文本基础之上的,文本资料的掌握与研读是研究的前提,但研究中仍存在忽视文本解读的现象。尽管已有学者尝试从文本学角度展开分析,然而就整体来说,对《宣言》文本的研究尚不充分。就单个文本而言,研究主要集中于陈望道译本,其他译本的写作过程、生成背景、版本源流、文体结构、传播路径、影响与价值等问题有待深入考证;就系列文本的整体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于文本的认定与鉴别,《宣言》基本范畴、核心概念、关键语句在不同译本中的对应词、语义、表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不同译本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宣言》文本思想的重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都有待深入探讨。此外,比较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同是1943年翻译的《宣言》译本,非共产党员陈瘦石在国统区翻译的译本与中共理论家博古在延安翻译的译本在话语表达、思想阐释等方面存在哪些异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对《宣言》的理解有何差异?《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理解与在苏联、日本相比有什么特色?诸如此类的文本与比较研究,不仅能深化对《宣言》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突显《宣言》在中国翻译传播的独特性。
第三,增强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就翻译历程而言,研究者大多采用历史性研究视角,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论述为基础,研究《宣言》的翻译、传播与影响,而借鉴文化学、传播学、翻译学、发生学的相关理论展开探讨的成果则较少。例如,源自西方的《宣言》如何通过翻译传播影响中国革命实践,如何在跨文化与跨语际基础上通过对文本事实在语言上的重新表述促使阅读者增强革命意识,甚至采取革命行动?这类问题涉及对文本、语言所蕴含的话语力量的分析,可以借鉴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理论等。就《宣言》译词、译句而言,除了用历史学方法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考察不同译本之间的变化之外,还可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卡弗关于翻译和阐释马克思词语的理论、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理论”、解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等。这些理论方法的借鉴不仅能拓宽研究视野,而且能够改善以往研究中重史实描述、轻理论分析的状况,加强史论结合的力度。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赵 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课题“《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14CKS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