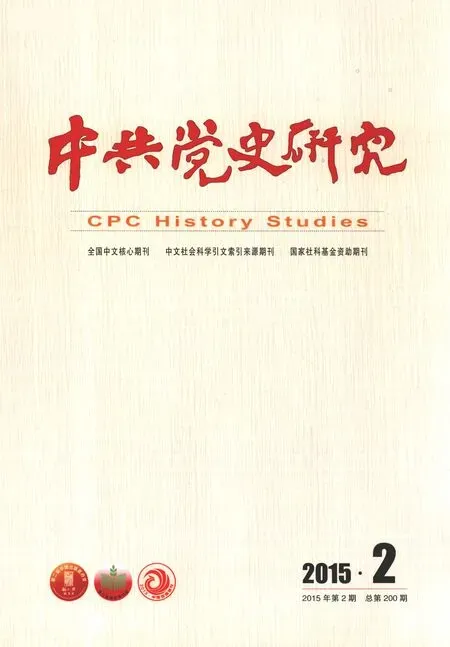传统、革命与性别视域下的华北妇救会
王 微
传统、革命与性别视域下的华北妇救会
王 微
抗日战争伊始,在动员全民抗战的浪潮中,中共的妇女工作在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展开,妇救会作为妇女工作的主要载体也随之在该地区广泛建立。在该组织进入乡村及之后开展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革命与传统、革命与性别的冲突层出不穷。为了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保证抗战大业的顺利进行,华北地区的妇救会不断地进行探索与调试。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让位于传统、性别让位于革命。同时,在战争中被妇救会动员起来的乡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相较于传统发生了诸多改变,但此种变化并非根本性的,而且战争、传统以及革命自身都使这些变化举步维艰。
华北抗日根据地;妇救会;乡村社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将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作为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为了最大限度地组织团结广大妇女群众,中共在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广泛组织各阶层妇女联合的团体——妇女救国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教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465页。关于抗战时期妇救会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其中不乏力作,但多是就组织谈组织,很少涉及参与该组织的主体——妇女。*参见黄晓瑜:《抗日救亡中的妇女组织》,《历史教学》1986年第9期;丁卫平:《国统区妇女救国会和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6期;丁卫平:《南京妇女救国会——全国第一个救国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探析》,《长白学刊》1994年第5期;张小云:“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7年;郭晓磊:“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2012年,等等。这种研究视角不但没有展现出妇救会工作的曲折性和妇女生活变迁的复杂性,而且也在一个重要层面冲淡了中共革命进程的艰难性。由此,本文试图以革命、性别、传统多重视域为聚焦点,运用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循序展现华北各根据地妇救会初入乡村、维护妇女切身利益、组织妇女参加抗战活动等历史图景,以求展现“人”的历史,呈现历史的立体性与多面性,并进一步加深对传统与革命、性别与革命、妇女角色变迁等问题的理解。
一、进入的曲折
新兴的妇救会之于传统的华北乡村社会,对双方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经历与尝试。在最初阶段,彼此之间充斥着摩擦与矛盾。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华北乡村妇女面对初入她们生活的新型组织,有着不同的因应与选择。有些“妇女热心关切国事而苦于无组织。遇见妇女工作同志就拉住询问:打鬼子这两天怎样了?什么时候能打走?妇救会是干什么的?什么时候组织?我也参加”*《组织广大妇女到抗战中来》,《新华日报》1939年1月9日。。有的妇女面对被动员、被组织很积极地说:“咱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人给咱们做主了!”*中共中央妇联会:《北岳四分区阜平城南庄抗战时期妇运简史》(1948年9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80-10。然而,这部分积极的妇女群体,在抗战伊始,并不是作为主体出现在宏大的战争视域内。从实际来看,那些保持缄默之姿、甚至持拒绝之态的妇女群体才是当时场景中的主角。具体来考究这类群体,可以发现,致其远离组织与动员场景的原因亦呈多样。
首先,就华北乡村妇女自身而言。其一,她们的生活空间较为闭塞。虽然当时的华北乡村正经历着战争烽火,但多数村妇仍然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而且囿于成长环境的危险性,一般妇女也不敢出来活动。*参见冀南区党委妇救总会:《冀南区参议会上妇女的活动》(1939年10月1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20-3。其二,她们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不易接受新东西,以至于她们不了解妇救会是做什么的,不敢也不愿参加妇救会。*参见三专区妇救会:《平山妇女工作考察材料》(1940年3月20日),河北省平山县档案馆藏,档案号4-1-76。其三,她们缺少参加组织和集体活动的习惯,因此她们认为没有必要参加什么组织。*参见冀南区党委妇救会:《妇女救国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常委会对今后妇女工作的意见》(1939年10月2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20-2。其四,华北地区战时环境恶劣,她们“对新旧军的区别尚不清楚”,作为良家妇女很惧怕走出庭院。*参见竹邨:《一个妇女工作团的工作总结》,《抗战日报》1941年6月19日。以上几方面原因使得乡村妇女在面对中共的组织动员时,有的隐藏逃跑;有的认为女干部是女兵,怕被招兵而不敢接近;*参见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烽火巾帼》,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第13页。有的为不参加妇救会,而隐瞒年龄。*参见黎城二区:《北流村妇女工作调查材料汇集》(1948年8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8-4。
其次,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阻力也直接影响着妇女的抗日积极性。从家庭内部来讲,有些妇女本来是真心愿意加入妇救会的,只是因为怕婆婆和丈夫反对不敢而加入。*参见竹邨:《一个妇女工作团的工作总结》,《抗战日报》1941年6月19日。当时的普遍情况是,因为千百年以来封建习俗的束缚,华北农村群众的思想极不开化,“女人出家门,父母不放心,兄弟怕议论,丈夫更是百般阻挠”*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4辑,内部发行,1986年,第257页。。老年人不让年轻的妇女出门,说:“你们大闺女出去,跟男的呆一块,学不好,学疯了。”*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婆婆对媳妇的管教也特别严,“媳妇和婆婆在一起时,即使听得狗叫,也不敢向窗外探望,也不敢随意讲话,一见妇救会的同志去,婆婆连忙告诉说:‘你不用和他(她)讲话,我的媳妇是傻子,不会讲话,甚(什么)也不懂’。”*竹邨:《一个妇女工作团的工作总结》,《抗战日报》1941年6月19日。赵树理笔下孟祥英的婆婆就是较为典型的代表,当妇女干部去动员孟祥英时,她婆婆反复强调:“‘她不行!她是个半吊子,干不了!’左说左不应,右说右不应,一个‘干不了’顶到底。”*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烽火太行半边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从传统华北乡土社会来看,对妇女的固有偏见使得妇女们在试图进入一个全新的组织时产生了诸多非议。有人说:“男女干部在一起工作是男女混杂,‘不正派’。”*《烽火巾帼》,第13页。有人说:“好人家的妇女不干那个(指妇救会)”,“她们(指妇女干部)都是疯子,她爹妈死得早没管教,才出来跑工作”。有人说:“这是什么世道,让妇女出来东跑西颠的”。*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4期,内部发行,1985年,第44页。有人说:“娘们孩子有何用?”*冀南区党委妇救总会:《冀南区参议会上妇女的活动》(1939年10月1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20-3。还有人说:“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妇女瞎折腾顶什么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4期,第44页。此类言语还有很多。乡土社会对妇女角色的定位依旧古老而传统,一些观念已经根植于人们的生活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由此看来,传统因子的存在更增加了乡村妇女参与组织的阻力。
再次,部分外来妇女干部作风轻佻,其所树立的负面形象也加重了乡村妇女对妇救会的误解。最初下到基层从事妇救会工作的都是些小知识分子或女学生,她们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生活方式都与华北乡村民众的生活传统、习俗不相契合。从穿着上来看,当时下乡的“工作员大部分是穿着小裙、大褂、短发、抹得脸上红是红,白是白,脚上还穿着半高跟鞋”*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工作》,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75-2。。也有妇女干部下乡穿旗袍的。*参见《烽火巾帼》,第13页。例如,黎城县县妇女干部就是“下乡骑牲口、打旱伞、穿洋裙”。当时群众反映说:“青年不敢参加,怕当女兵,到村青年藏,只见老年人。”*《黎城妇女工作简史》(1948年4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10-2。“群众见了远而避之,称之谓‘洋学生’,后一些时候,改穿了军装,群众称之谓‘女兵’”*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工作》,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75-2。。在言行上,她们说起话来满口学生腔。干部们的浪漫举动尤其让群众难以接受。*参见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工作》,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75-2。大家反映说“男女干部乱开玩笑”;*左权第四区救联会:《左权第四区车庵编村五年来妇女工作总结》(1942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66-1-137-1。加之个别妇女干部作风不检点。于是,“妇救会是破鞋会,是女游击,里边全是癞(坏)女人”等流言不胫而走。*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内部发行,1985年,第385页。群众看不惯妇女干部们的“浪漫”举动,“有的不愿叫在他们家住,有的背后在嘲笑、谩骂”。群众更怕妇救会把他们的年轻媳妇或闺女拐跑了,若真有跑了媳妇的事,也都会首先迁怒于该组织。当时群众已对妇救会形成刻板的印象,说她们“这一伙子疯疯癫癫的娘们,不是没爹没娘,就是挨打受气的!”*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工作》,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75-2。
上述诸多方面的原因都使华北乡村妇女远离妇救会组织的场域。即便是有些妇女参与其中,也尽是些应付公事的白发老妪,至于青年妇女则皆躲避,不见踪影。*参见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工作》,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75-2。由于乡村妇女的抗拒,所谓组织起来的妇救会员也多是登名造册、村中户册子的变形而已。例如,黎城二区北流村发展的100个妇救会会员都是按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规定直接抄名册入会的。*参见黎城二区:《北流村妇女工作调查材料汇集》(1948年8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8-4。又如,冀南区妇救总会成立后不久,便有数万会员的统计,但多数是区县妇救会干部到一村开村民大会,然后由村长协助,提出正副主任,登记几十个会员的结果。*参见冀南区党委妇救总会:《冀南区参议会上妇女的活动》(1939年10月1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20-3。这种变相强拉入会的组织方式造成很多会员对妇救会认识不够,甚至有的地区本人还不知道就成了登记在册的会员。*参见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妇女工作分会:《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第37辑(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一,内部发行,1983年,第110页。并且由于当时干部缺乏动员妇女的经验,华北乡村的妇救会多是一个个空洞的组织,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参见《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358页。大部分村只是几个干部整天一起忙着征收会费而已。*参见《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第37辑(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一,第110页。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产生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在冀南某县,妇救会会员曾发展到3.4万余人,但敌人来到后,不敢承认自己是妇救会会员者占到了一半,而且由于该县从未组织这些名册中的会员开过会,很多会员都不清楚妇救会的作用。*参见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内部发行,1983年,第169页。即便是对妇救会有所了解,大多数人也只是知道该组织为抗日的团体,只有个别人知道它是妇女自身求解放的组织。妇救会会员对会费的认识更差,有的甚至认为:收上去的钱“是给谁家小孩子收锁子钱呢?”*三专区妇救会:《平山妇女工作考察材料》(1940年3月20日),河北省平山县档案馆藏,档案号4-1-76。
既然妇救会会员是造册登记、强迫的结果,其干部也就自然是指定的。例如,左权县四区车庵编村、黎城县二区北流村的妇救会会长都是由区妇救会直接指定的。*参见左权第四区救联会:《左权第四区车庵编村五年来妇女工作总结》(1942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66-1-137-1;黎城二区:《北流村妇女工作调查材料汇集》(1948年8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8-4。这些被指定的妇救会主任,大都性格倔强、作风泼辣、能说会道,而且多是“村中非常风流的妇女,社会人士所认为名誉不好的‘破鞋’”。在抗战之初,这些生活作风并不为乡村社会所接受的早期的基层妇救会干部,对于中共在乡村社会所进行的妇女工作的确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中共通过她们“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名词传播于农村,使之影响了一般妇女”。但在妇救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妇女违背传统道德的行为及作风也加剧了人们的误解。*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85页。有些地方的村长为了应付差事,就用钱把这些作风不良、敢说敢干的妇女送去受训。这些人受训后,有的进步很快,洗掉了旧的习气,但大多数还带着过去生活的痕迹,这使得一般妇女对于“不正经”的妇救会主任多敬而远之。*参见《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359页。例如,北岳区望都三堤村指定的5个妇女干部,其思想作风、生活都有点不正派,在群众中影响极坏,老实群众都不愿让家里的妇女出来,怕染上坏风气。*参见中共中央妇联会:《北岳望都三堤村妇女工作典型总结》(1948年9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80-7。
传统观念的束缚、有名无实的组织方式、良莠不齐的组织成员以及妇女干部背离乡俗的浪漫言行,使得广大乡村妇女对妇救会了解甚少,难言认可,参与度不高。基于此,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在吸取前一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其工作开始进行调整,目的是充分吸纳广大妇女进入组织,让更多的妇女为战争贡献力量。调整的要旨主要是尊重乡村实际情形、继承与利用传统,使革命与传统乡村能够很好地实现融合。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
首先,清理组织中的“破鞋”。尽管在传统的华北乡村中,两性关系较为宽松,但“破鞋”仍不为人们所认可。于是,华北各根据地的许多妇救会将整顿、改选组织,洗刷、改造组织中的“破鞋”作为一项指示而提出:“要拒绝吸收为群众所仇视的‘破鞋’参加(妇救会),以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与赞助。经过多方教育后,妇女对‘破鞋’有了初步的认识与转变,可个别吸收并改造‘破鞋’。”*谢忠厚:《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冀中妇救会在巩固与整理组织后,克服了紊乱现象,其工作也逐步深入,逐步正规,那些未好转的妇女也随之被洗刷出去。*参见《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6页。其中,冀中九分区的妇救会经过改选,推选出作风正派的抗日积极的劳动妇女,使得工作也逐渐得以开展。*参见《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34页。随着妇救会的改组与人员调整,朴实、正派的农村妇女干部也多了起来。
其次,立足实际,运用灵活的工作方法,以贴近妇女为最终目的。华北各根据地妇救会基本上一改过去靠开会生硬灌输大道理的工作方式,转为从生活习惯、语言口吻、宣传内容上适应农妇,从乡村妇女的实际生活着手来拉近与妇女们的距离。为了接近乡村妇女,很多妇女干部学会了纺线、推磨、做饭、抱孩子等本领。在宣传时也相对灵活,如完县妇救会在“宣传时,并不打锣召集人;而是遇见妇女,便由家中事情谈起”*《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348页。。从内容方面而言,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调整与应对。如发现被虐待的妇女就对其进行教育,提高其觉悟,帮助其解决问题。*参见《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4期,第23—24页。如遇见不善言谈的寡妇,便向她解释妇救会的主要任务,并告诉她遇到难事可找妇救会。遇见年老的妇女,又是另一番内容及口吻。此时的妇救会干部也不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她们的语言和态度都发生了改变。以对妇女们的称呼为例,年老者一律是婶子、大妈,年轻者一律是嫂子、姐姐。*参见《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348页。还有的干部“利用认干娘、拜干姐妹的方式和农村妇女建立感情,开展工作,深入到各家各户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的宣传教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4期,第23页。这些贴近妇女生活的组织方式、宣传内容取得了很大成效,使得妇女们抗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再次,充分改善、利用乡村原有的社会关系建立妇救会。由于最初华北乡村民众对妇救会的接受程度不高,青年妇女还不能完全自由地走出家门参加该组织,所以当时华北乡村许多的妇救会是从组织老年妇女入手,以老年妇女带动青年妇女。例如,“有的村是挑选在本村有点威信的老大娘,把青壮年妇女宣传动员出来……她们不仅在本村有号召力,对周围村庄妇救会工作的开展也起了积极的影响”*《烽火巾帼》,第137页。。再如,有的地区专门召开了婆婆会,在会上宣传妇救的主张。*参见竹邨:《一个妇女工作团的工作总结》,《抗战日报》1941年6月19日。这些老年妇女被组织起来后,对妇救会有了一定的认识,自身觉悟也有所提高,对青年妇女走出家门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严防死守、完全禁止。这样,大量年轻妇女的进入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救会的年龄构成。另外,进入乡村的上级妇女干部还号召干部家属起模范作用,并通过她们做宣传、解释工作。例如,在完县二区东峪村,“区妇救会干部多次下去都碰了钉子,区农会主任便同妇救会干部一起到该村,召开农会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如何建立村妇救会,要求每个农会会员都要动员自己的妻子参加村妇救会,并且由村农会一个干部的妻子担任村妇救会主任,这样才把村妇救会建立起来,逐渐发展了200多名会员”。*《烽火巾帼》,第137页。
由于组织动员方式的改变,华北各根据地内的妇救会有了一定的发展。自日军第一次“扫荡”后到1940年,山东妇女工作突飞猛进,会员从几万发展到几十万,“并且有三分之一的组织是比较巩固的”*山东省妇联宣传部编:《山东妇运资料选》,内部发行,1983年,第52—53页。。同年,“晋察冀边区的妇救总会,拥有会员十余万人,这些人都是自觉地报名参加妇救会的,她们在参战、慰劳、生产各项工作之中,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晋东南妇救总会,则拥有二十余万的会员,虽然这个数目字中,有少数的名字是被用行政方式登记在名册上的,然而她们各种参战和生产工作中,确实也曾起了伟大的作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康克清文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年,第9页。根据1941年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7个抗日根据地的不完全统计,“当地妇联或妇救的会员,平均占了妇女总人口的百分十二”*《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页。。在近1年的时间内,晋冀豫区妇救会会员总数增长了15%,发展会员最多的一个区新发展的会员数量是原有会员数量的1.5倍(见表一)。1944年,晋察冀边区冀晋二专区妇救会会员总数增长了62%(见表二)。1941年至1942年,晋冀豫区新建立的区级妇救会是原来的1.8倍(见表三)。1944年,晋察冀边区冀晋二专区拥有妇救会的村庄占到行政村总数量的68%(见表二)。

表一 晋冀豫区1941—1942.4妇救会会员发展统计表
资料来源: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

表二 1944年晋察冀边区冀晋二专区妇救会相关信息统计表
资料来源:《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447页。

表三 晋冀豫区1941—1942.4整理组织统计表
资料来源: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
二、困境中的发展
在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同时,华北各根据地的各级妇救会都很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积极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主,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买卖婚姻和虐待妇女等原则,这些也使妇女解除家庭的束缚轻装上阵,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妇救会在解决这些妇女切身问题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观念,增强了她们对妇救会的认可度,而且还将她们从婚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参与到妇救会组织的社会工作中去。
在传统的华北乡村中,打骂妇女的现象十分普遍。妇救会以此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大量地解决妇女挨打受气的问题。例如,清苑县冉庄北关的李某无故打了他的嫂子。妇救会知道情况后,联合工会组织,对李某进行了游街斗争,并给以物质处罚。随后,妇救会还召集妇女们,讲妇女求解放的道理,把李某上交的东西分给参会的妇女们。这件事在当时震动很大,给原本认为在家庭内受虐待和殴打无可厚非的妇女们撑了腰。*参见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发行,1982年,第64页。当时,很多青年妇女都认为妇救会就是她们的娘家,经常有受压迫的妇女去找妇救会解决问题。例如,临北县一个月内有32件、兴县半年内有38件的家庭纠纷都得到解决。*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811页。在解决妇女的婚姻问题上,妇救会还一方面宣传婚姻自由,一方面帮助要求离婚的农妇离婚。妇救会对妇女婚姻问题的解决在群众中所造成的影响很大。例如,定襄县师家湾郝某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常受丈夫的打骂,想离婚,却遭到娘家和婆家的极力反对,并被扬言“活是婆家的人,死是婆家的鬼”。县妇救会主任多次调解均无效,最后只好领着郝某到县司法部门办了离婚手续。此事件后,“妇救会是为妇女解除痛苦的”这个观念为多数民众所认同,当地许多青年妇女有苦即到妇救会去诉说,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妇救会的威信。*参见《烽火巾帼》,第154页。
在妇救会所进行的反虐待、反买卖婚姻、婚姻自主的斗争中,乡村妇女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参加了社会活动的青年妇女,有了一定的认识与觉悟,从老、壮年妇女的亲身体验和经历中感受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的痛苦。不想再被父母包办婚姻,因此,婚姻自由的条例在颁布后很快就被妇女们接受。青年妇女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不管穷富只要人性好就行(不大普遍);工作积极的干部;家里过的来,年纪相仿佛;知道痛(疼)咱,两人心思对得来”;而且,“自主结婚的,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寡妇。据平北里峪一个村的统计,1941年共有6对夫妇完全是自主结婚的”。*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那些之前承受不合理婚姻的妇女也纷纷提出离婚。例如,榆社县自婚姻条例颁布后,在政府所处理的86件离婚案件中,有84件是由女方提出的。*参见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由于妇救会在解决妇女切身问题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取得了广大妇女的信任,也扩大了妇救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使得广大妇女敢于走出家庭,积极参加妇救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救会工作的开展。
乡村妇女找妇救会解决问题的日渐增多,本身是一件好事。然而,妇救会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孤立地将“性别革命”凌驾于“阶级革命”之上,随之造成的“片面的妇女主义”的言论及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却破坏了传统乡村稳定的社会秩序,造成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紧张,最终又影响到乡村社会对妇救会及其妇女工作的理解接纳。
首先,在处理家庭纠纷时,如果是男女之间的问题,妇救会往往不问事实,总站在女方立场上来说话,如果是婆媳之间的问题,则往往是偏向青年妇女。*参见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工作》,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75-2。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也是只强调斗争,不知和解。有些地方不管是妇女与家庭因生活琐事产生的口角,还是家庭对妇女一时的打骂,都机械地进行反对或斗争。*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791页。有些地方存在着为斗争而斗争、为解决而解决的情形。例如,有的干部到村里工作时向妇女说:“我是来替你们改善生活的,谁有痛苦快说!”*《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8—19页。在一些工作较为激进的地方,妇救会甚至“提出用‘开展斗争来保证工作的开展’,以‘斗争’多少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临县一月开展了40多次‘斗争’,方式又多为大会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813页。。而斗争方式也多是侮辱人格的。有些地方在斗争某些所谓顽固的婆婆时,采取的方式是给她们戴高帽子、画脸、游街等。*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78页。例如,某村妇救会在斗争一个虐打媳妇并且不让媳妇参加妇救会的婆婆时,先把纸帽子给她戴上,牵着她游庄子,然后鉴于该婆婆仍不承认错误,就用皮带抽,但她还是一声不吭,最后妇救会主任就罚她在太阳下暴晒了几个钟头。民众对此颇有怨言,说:“世界真变了,为着一点儿家常小事,竟这样对付一个老年人——带(戴)高帽子,游街,挨打还要当众晒太阳,这算什么样子呢?”*叔孙:《不是好办法》,《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6日。
其次,在解决婚姻问题时,有的妇救会不仅将婚姻问题当作发动妇女的唯一手段,而且把离婚当作唯一的出路,认为要满足妇女的要求,便只有解决离婚问题*参见晋冀豫区妇救总会:《关于反对买卖婚、争取自主婚的初步总结》(1942年8月3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5。。例如,北岳区宛平县马栏村开始只有20个青年妇女参加妇救会。因为当时的宣传是谁参加妇救会就给谁解决困难,所以,在参加妇救会的这20个妇女中有14个是要求离婚的。*参见北岳三地委:《三分区妇女运动概述》(1948年5月2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8-1-49-2。也有些地方甚至以离婚的数量来衡量妇女工作的优劣,*参见张志永:《政治与伦理的统一:华北抗日根据地和睦家庭的建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还有些地方形成了为离婚而离婚的局面。*参见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结果,这些地方的妇救会被看成是挑拨离婚的机关,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另有些地方,妇救会帮助离了婚,妇女却又后悔,自动又回去了,结果对妇救会的威信有很大损害。*参见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
正是由于妇救会在处理家庭纠纷和婚姻问题时的偏向,使得某些地方的妇女以为已经得到了“解放”与“自由”,在言行上出现了一些过激之处。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有的媳妇出去玩耍一天,回家反骂婆婆不给做饭。*参见岫岩:《华北妇女运动的新方向》,《新华日报》1941年3月7日。有的青年妇女开会、下学后不回家,在半路玩耍,等婆婆做好饭菜再回家吃,婆婆一批评抱怨,她们就跑到妇救会反映婆婆落后,要开会斗争婆婆。*参见《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3页。一个青年妇女当了副村长后,甚至不管婆婆叫娘,而叫起名字来了。*参见新晨:《北岳区妇女工作的检讨与意见——速记张文秀同志在妇女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17日。还有的妇救会干部在家里和丈夫公婆处处讲“平等”,家中一切琐事,都要和丈夫轮流去做。*参见张平:《正确解决婚姻问题》,《抗战日报》1942年5月21日。还有一些乡村中好吃懒做的妇女试图利用妇救会的力量结束所谓的痛苦,争取所谓的平等。*参见沁源县妇女联合会:《沁源县妇女运动史资料选》,内部发行,1987年,第100页。在处理婚姻问题上,妇女亦发生了错觉,认为解放了就要离婚,就要在外面乱搞,于是,就不好好生产了,也不受家里管了。*参见太行六专署:《太行第六专署司法科婚姻问题的综合报告》(1949年1月1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6-1-78-1。由于某些妇女将解放与婚姻自由等同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华北乡村“妻休夫”的热潮。*参见江沛、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这些过激的行为、举动显然是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相违背的,即便革命的势头再猛烈,传统也不会一味妥协与退让。事实也如此,传统并非只是被动地受冲击,它也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击革命。
首先,在革命势头的冲击下,妇女公开受打骂虐待现象减少了,但很多老年妇女都抱怨说:“‘娘呀!这还了得!’妇女要求解放,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这不反了?媳妇家,婆婆不许打,丈夫不许打,该叫谁来打?难道就能不打吗?”*《烽火太行半边天》,第160页。类似的言论与观念在华北各根据地的乡村中一直在潜滋暗长,肉体虐待方式虽然逐渐转入地下,但精神虐待又成为一种新的家庭用来管制妇女的方式。例如,涉县索堡村一个妇女过去常受婆婆丈夫的打骂,后告到区署妇救会,经过双方几次说服与斗争后,婆婆丈夫一天到晚都对她不理不睬,丈夫也不同她住。她回娘家时因脚小走不动路,拿不了东西,抱不了孩子,丈夫婆婆也不管,使她处处为难而没办法。*参见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这种精神虐待对妇女的影响也很强,以至于“有个别妇女感觉如此不打不骂还不如打骂痛快些”*左权二区救联会:《堡则村五年来妇女工作的总结》(1942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66-1-137-2。。
其次,相当一部分男性农民也有抵制情绪。当时响应妇救会号召而提出离婚的大多是贫农的妻子,且多因嫌家贫想改嫁而离婚。结果,很多男性贫农因离婚而受到极大的损失,他们恨妇救会,对婚姻法也十分不满。*参见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再加之,某些地方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时不调查,只听妇女一方片面的反映,致使男性农民与妇女作对。*参见北岳三专妇联会:《三个月妇女工作总结》,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8-1-50-1。有的男性贫农为防止老婆离婚,而采取各种办法来阻碍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参见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3页。有的男性农民认为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婚,就是死了骨头也得托一把,所以多采取硬猛的手段对待提出离婚要求的女人。*参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通报》(1945年10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6-1-82-15。有的男性农民甚至以自杀来反抗离婚。例如,和西县“堡下村一妇女告夫坏,与夫离婚,气的(得)丈夫喝大烟死了”*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
无论是妇救会较为过激的工作方式,还是乡村妇女在误解“解放”后一些过激的举动,都打破了使乡村社会得以稳定的重要因素——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秩序。道德秩序的破坏造成乡村的悸动,进而波及抗战大局。基于此,中共开始进行方针上的调整,不再一味地对传统家庭进行颠覆与改造,而是着手和睦家庭的建设。在具体措施上,“将妇女参加生产作为突破口,并再三强调乡村妇女参加根据地的生产事业要与参加家庭经济生产相一致,其社会与政治的活动也要兼顾家庭生产,以此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为妇女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创造条件”*参见王微:《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形象的重塑》,《河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家庭和睦运动付诸实践后,一方面缓和了此前中共进行的婚姻革命所引起的乡村社会冲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消除乡村中普遍存在的虐待妇女的现象。*转引自〔澳〕李木兰著,方小平译:《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9页。但实际而言,中共的此种举措,主要是服务于战争与革命的需要,乡村妇女的利益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因此,性别之间的矛盾也就始终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三、艰难的变革
妇救会的出现,给乡村妇女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变化。在妇救会的号召下,乡村妇女从庭院和锅台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在战争中,她们有的做着缝制军衣、军鞋、军袜等类似庭院内的传统工作;有的做着先前根本不属于她们性别范畴内的事务,如站岗、放哨、送信、破路等。实际上,她们承担起了更加丰富的社会职责,扮演着传统妇女从未有过的社会角色。
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经济条件,中共华北各根据地的部队普遍没有被服厂,更没有军鞋工厂。这样,做军鞋、军袜和军衣便成为乡村妇女首先并且主要承担的支前任务。这些衣物都是由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的,开始都是义务做,后来鉴于战争的长期性、任务的艰巨性,便改为有计划地分派进行。*参见《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84页。一般来说,先是由县、乡、区级妇救会作为任务下达给村妇救会,然后通过各村妇救会组织所有妇女进行缝制,并提出规格、质量要求和收缴期限。妇救会也把组织发动妇女做军衣军鞋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例如,冀南二分区妇救会就规定每年每人做几双鞋、几双袜,做好后统一交到妇救会进行质量检查。*参见《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85页。在武乡县李荷香的回忆中也提到,当时检查很严格,“用上鞋的锥子往里一钩,看你做得好不好,里面是不是褙了什么。用锥子挑,有的用刀剁,看你做的鞋里是什么东西,钩出来要是草、纸袼褙一类的东西,还得补做。鞋做得好好的,交上去。做好,村里先检验了,区里县里也要检查了”*《山西抗战口述史》课题组:《山西抗战口述史》第2部(呐喊·觉醒·抗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页。。由于此种工作在完成时间、质量、数量方面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辛勤而繁重的劳作给部分承担此项工作的妇女身体上留下了永远也磨不掉的印迹。
不难看出,妇女们在战争中被组织起来后所做的一些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很像是女性传统的家庭作用的延伸,诸如吃喝拉撒睡;洗衣、救伤、宣传、征粮、扩红、支前、被服厂……即所谓‘后勤’”*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导言”第6页。。但在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她们不再单单是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所付出的也不再仅仅是为了相夫教子,所承担的也不再只是家庭的责任,她们所缝的衣、洗的被、做的鞋也因为受益对象的改变和扩大而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含义。
随着妇女们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展,其传统的性别角色也逐渐得以改变。战争、革命、妇女组织给长期沉寂于传统生活模式的华北妇女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欢愉,也使得她们一向平静的生活出现了许多涟漪。很多人对妇救会所组织的类似传统性别承担的支前工作持一种积极和愉悦的态度。在访问那些经历过抗战的妇女时,很多老人都表达了这样的体验:“愿干,高兴着哩。你说那会儿,心真齐呀,你说吃不上,穿不上,那时候真是积极呀,一心埋在工作上,不图钱,不图利。你说做起那军衣、军鞋,你说也不困,你说也不累,那时候怎么干活也有精神,比干自个的活兴致大多啦”*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263─264页。;“她们每次交活时都高兴地说:‘子弟兵穿上我们做的鞋狠狠打鬼子,也算我们为民族解放事业添了一份力量。’”*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中法大学校友编委会:《平西儿女》,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至于在问到当年的想法时,她们激情地回答道:“为救国哩,不是老宣传救国呀,抗日救国。”*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264页。可见,从传统氛围中走出来的女性,在参与革命、战争的政治活动中体会着一次次欢聚的感受。*参见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妇女投入战争、参加组织,摆脱了传统的孤立地位,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参见〔瑞典〕达格芬·嘉图著,杨建立等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84页。
除了这些类似庭院内的琐事外,华北乡村中被妇救会组织起来的妇女们还承担起站岗、放哨、破路、抬送伤兵、坚壁清野、掩护抗日工作人员等任务。当时许多地区的妇女,已切实地代替了男子站岗放哨的工作,并且很负责任。如在献县的妇女中,“健康的老壮年站岗、盘查行人,没有通行证者领到区公所,叫男自卫队帮助审讯”*中共中央妇联会:《献县妇女工作简史》(1948年9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80-11。。有的村还设有妇女锄奸小组,承担清查汉奸、特务与叛徒的任务。如宛平县金鸡台村妇女除奸组就以姐妹关系清查出从房山县西北部的大安山派到当地来的女特务。*参见北岳三地委:《三分区妇女运动概述》(1948年5月2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8-1-49-2。许多“三寸金莲”还奔波于烽火和硝烟中,甚至还拿起武器打击敌人。其中事例比比皆是:在武邑县北区,就有60多岁的老太婆到敌区送信;*参见冀南区党委妇救总会:《冀南区参议会上妇女的活动》(10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20-3。武乡县凹窑科村的姑娘张月梅从1942年起就当地下交通员,以女扮男装来递送情报;*参见《烽火太行半边天》,第239页。晋县妇救会自动发起破路,造成破路热潮;*参见冀南区党委妇救总会:《冀南区参议会上妇女的活动》(10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20-3。献县在组织妇女参加破路运动时,一般长达20来天,男女分工协作,还开展男女竞赛;*参见中共中央妇联会:《献县妇女工作简史》(1948年9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80-11。南宫县妇救会员领导游击小组经常在城外扰乱敌人,*参见冀南区党委妇救总会:《冀南区参议会上妇女的活动》(10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20-3。游击小组中的女组员也和男子一样去袭击敌人,还到敌据点内去扔手榴弹。*参见张文淑:《对一九四一年妇女工作的期待》,《新华日报》1941年1月17日。为了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华北乡村许多农妇还冒着生命危险当“堡垒户”。另外,在妇女参政的热潮下,阜平、平山、望都、唐县、曲阳、完县、定县等地不仅有妇女当选为村民代表,而且还有妇女当了村长、副村长,“仅唐县的村民代表中妇女就占三分之一,定县的二百六十九个村长中女村长就有三十多个。由于妇女干部是在斗争实践中锻炼,因此成长得很快,不仅普遍参加了基层政权的工作,而且也走上了区、县政权领导岗位”*《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79页。。
毋庸置疑,虽然乡村妇女的角色、生活空间都发生了许多改变,但由于残酷的战争、根深蒂固的传统及妇女工作的不完备,这些变革都显得十分艰难。
抗战时期,华北各根据地经济萧条,物资极度匮乏,支前所需资源多由妇女自己解决。许多经历过支前的妇女后来回忆起那段岁月时,都会或多或少提到在缺少原材料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工作的情形。其中,有的是“拿自己织的土布做。织下土布,从山里头拿些黑叶叶熬了,把叶子捞了,把土布染一下,就做鞋”;*《山西抗战口述史》第2部(呐喊·觉醒·抗争),第86页。有的是“拆旧衣,洗旧棉花,把旧衣结实的部分剪下来,做成鞋面、鞋底,把洗净晒干的棉花打成夹支,经过细加工做成一双双‘崭新’的鞋,交给上级”。*《平西儿女》,第155页。然而,在残酷的战争中缝制军衣军鞋,乡村妇女不仅要面临布料短缺的问题,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因为一旦被敌伪搜出这些衣物,就会以私通八路的罪名遭到逮捕、处死。*参见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261页。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她们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也要经受心灵和身体上的磨难。关于这些方面的战争体验在她们的回忆中也多次被提起:“那时候一说消息不好,你就得赶紧走。现在的人受什么罪?(我们受了)那么多罪,(我们)野地里睡了多少”;*《山西抗战口述史》第2部(呐喊·觉醒·抗争),第86页。“怕有日本鬼子、汉奸看见,暴露了。黑介(夜间)把这窗户搭上被子,怕有了灯明,搭上被子”。*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263页。除了这些庭院内的工作需要承受高风险外,她们被妇救会直接拉入战争场域后所从事的工作危险性更高。一个小脚妇女在回忆起抗战时期交公粮的经历时说:“有一回,过铁道让敌人发觉了,一扫射,这个也‘爹呀,’那个也‘娘呀’。妇女们胆量小多喽,本身跟男的就不一样,净是哭的呀,狼哭鬼叫的呀。我说忙(快)别嚷了,忙别嚷了,一嚷暴露了目标,着(招)机枪给射喽!忙着跑过去了。喘得这心慌,这处都痛呀(用手指肋下)。”*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266页。
在硝烟四起、原本属于男性领域的战争中,华北乡村的众多妇女在被妇救会组织起来后,其所发生的在生活空间、社会角色等方面的改变不单只受到战争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传统力量的百般阻挠。
妇女参政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了更好地发挥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赋予妇女参政等方面的政治权利也成了其中必要之手段。妇救会在选举过程中起了核心的推动工作。妇救会除了事先慎重地准备竞选人外,还在会员中详细介绍竞选人,并保证每个妇救会会员都参选。对于当选后的妇女,妇救会还发动全村妇女庆祝拥护并帮助解决困难,从而提高了参政妇女的威信和工作的信心。*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348页。
尽管妇救会在原本这个“母鸡不司晨”的乡土社会中做了大量妇女参政的推广宣传工作,但是一般的乡村妇女对参政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她们参政的表现还不够积极,参政议政的人数也很少。如山西栗城村共有188名妇女,其中有政治活动、有立场的仅有10个。*参见《栗城村妇女问题调查》(1943年3月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66-1-137-7。就某些乡村妇女而言,她们不但认为实行民主、进行村选是不合理的,而且还把这些都看作是男子的事,不想也不愿去管。*参见张维琪:《如何动员妇女参选?》,《太岳日报》1941年8月21日。她们自己本身也缺乏自信。有的说:“妇女□(原文模糊不清——引者注)能干了事吗?女人说话不顶事!”有的认为做个代表还可以,要当村长那就是妄想了。尤其是老年妇女,在选举时除了个别较开明的以外,一般都不投妇女候选人的票。在登记公民时,有些妇女死也不肯讲名字。问急了,便随便取个怪名,什么“狗不衔”啦,“狗嫌臭”啦。“有的老太婆说:‘记下来也不顶事’。”*竹邨:《河曲×家寨妇女参选经过》,《抗战日报》1941年8月3日。即便是最后当选了,也有个别当选人要求退选,“不愿参政或当场和选民吵架,不准选民选她”*《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349页。。
在传统根深蒂固的乡村社会中,还有许多普通民众对妇女参政持有偏见,怀疑并轻视她们。有些公婆不赞成媳妇参加工作。有的老汉听到点女人的名字,摇摇头说:“女人名字也要唤,真是!”在选代表和村长时,除了一两个开明的以外,男人总不愿选女人。在领导村选的干部中,对妇女参政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知。有的干部认为:“妇女参加行政工作,还应是二三年以后的事,她们现在什么也不懂得!”即使妇女当选代表或村干部后,在工作中仍会面对很多困难。如果在许多男干部中只有一个女的,她便不习惯,怕羞,也不敢讲话;家里有孩子的妇女还脱不了身去从事下乡工作,也不能夜间开会。*参见竹邨:《河曲×家寨妇女参选经过》,《抗战日报》1941年8月3日。还有个别的女村长,专门的任务和工作就是给其他人做饭吃,男干部就这样给她分配工作,而女干部也没有异议就这样接受。*参见孙文淑:《对一九四一年妇女工作的期待》,《新华日报》1941年1月17日。
可见,此时乡村妇女生活空间的扩展、社会角色的承担都是在不改变传统的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传统的家庭结构方式依然存在,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性别模式依然存在,那么,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的承担也就依然存在。这样,试图在传统尚未解构时就将女性拉出性别角色束缚的努力,也就势必枉然。
除了战争、传统两方面的因素外,就妇救会自身的问题而言,其僵硬的组织形式、空洞的组织内容、武断的组织方式也对发生在妇女身上的变革有着负面的影响。
首先,妇救会作为一种新注入乡村的革命力量,对于华北乡村妇女的传统生活缺乏必要的认知与了解,把农妇当作城市女工与学生来组织、发动。虽然她们的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革,但同时原有的生活轨迹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势必会对妇救会失去兴趣,同时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失去信心。以开会问题为例,乡村妇女在加入妇救会后“要过组织生活,尤其在巩固组织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大都规定每十天或一周开一次小组会,再加上其他活动,平均每周至少开两次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页。。若一两次不到会即开除会籍,而且这种连续的会议也不顾及家庭琐事对妇女的束缚,*参见山西省武乡县妇女联合会:《武乡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集,内部发行,1983年,第4页。使有的妇女从早忙到晚,脱离了家庭操作,造成与家庭的对立。*参见安修:《打破妇女运动中的主观主义》,《新华日报》1942年5月17日。有的妇女孩子生病也得开会。还有的妇女不能来,说公公婆婆不让来,于是干部就处罚公婆,让他们戴纸帽游街,而且还喊诸如:“某某老婆顽固,不叫媳妇参加开会!我们要打倒这顽固老婆婆!”“打倒某顽固老公公”等口号。*中共中央妇联会:《晋绥临县五区白文镇抗战时期妇运概况》(1948年9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80-9。从内容方面看,开会往往讲的又是农村妇女难懂的内容,结果是浪费她们的人力与时间。另外,在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时,不论见了大娘大嫂还是大姐,内容与模式变化不多,老百姓对此早已厌烦。*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50、375页。妇救会还以自己的“革命”愿望去衡量妇女群众,不顾及家庭妇女身体、生活上的限制。如强调小脚妇女集体开荒、修渠;*参见安修:《打破妇女运动中的主观主义》,《新华日报》1942年5月17日。让妇女投弹、刺杀、出操;让男子在家做事。*参见肖岩:《关于妇女工作》,《解放日报》1945年4月6日。许多妇女都感到妇救会的政治味道过于浓厚、组织形式过于生硬,对参加这个新的组织不感兴趣,*参见安修:《打破妇女运动中的主观主义》,《新华日报》1942年5月17日。即便是已经加入的妇女,也有感到难以完成会员的义务而要求退出的。*参见《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页。
其次,妇救会发动妇女参加各种支前活动中的工作方式也存在一些不当之处,尤其是把耐心艰苦的宣传动员工作变成了单纯的命令。例如,北岳区望都县三堤村妇救会建立初期在组织妇女站岗、放哨、募集、做军鞋、做军衣、挖交通沟时,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就表现得很严重。罚东西、罚苦工等是其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参见中共中央妇联会:《北岳望都三堤村妇女工作典型总结》(1948年9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2-1-180-7。在这种强硬的组织下,妇女群众有时候感到妇救会只懂得向她们要东西,从中并无利益可得,妇救会与她们的实际生活是疏远隔离的。*参见《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6页。以至于有部分妇女把慰劳工作当作无可奈何的应付差事,还说:“以后要鞋袜告诉我们就好了,不必多开会了,免得麻烦。”动员的次数过多,也引起了妇女们的反感。还有的地方发生了强迫摊派的现象。例如,清苑县的张景芝在回忆中就提到:“那时候妇救会干部可敢干啦,黑界(夜间)送去那衣裳,她谁也不敢不做,那会儿带强制性的,不做也不行,这家做多少,那家做多少”;“有的说,你给我送这么多,当下做不上了呀?我就说限你几天,做不上你晚上做,超过了也罚你”*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262页。。另外,当时要求妇救会员交的会费大部分也是形式主义、缺乏教育意义的,造成了妇女们的负担。例如,某村收会费时也不开会,村干部挨门挨户要。“妇女问:交一毛钱干什么?干部说:‘不知道,人家上级要’”。有的妇女没有铜元,只好给毛票,而且连毛票也是借的。*参见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3。
战争是残酷的,女人也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但战争对于沉闷千年的女性生活可能是一次变革的契机,也可能为妇女走出传统性别的藩篱而打通道路。*参见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导言”第4页。但这种转变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也并非如历来的宣传中所言的那般壮志豪情,其间满是传统、革命、战争所带来的荆棘与坎坷。
结 语
在民族命运遭遇危机和人力、物力极度缺乏之时,妇救会背负着妇女解放与战争动员的双重使命来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乡村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然而,由于传统的束缚,以及妇救会违背乡村习惯与现实等问题的存在,使得这个新的社会组织所走的每一步都步履维艰,传统也就成为革命得以进行的绊脚石。在此种情势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及时做出调整,并将革命的发生建筑于乡土社会习俗、传统的基础上,才使得乡村逐渐接纳了这个全新的组织。
起初,妇救会只是设想通过解决乡村妇女切身的婚姻与家庭问题,用较为激进的方式打破以父权制为主导的乡村秩序和以伦理观念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从而将妇女从家庭中彻底解放出来,并将她们带入宏大的战争场域,但是,此种不考虑传统、习俗的浪漫主义举动并不符合当时华北乡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不但影响了普通乡村家庭的稳定,而且使乡土社会对妇救会和中共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到抗战大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转变妇女工作的方向,将“性别革命”让位于“阶级革命”,使得妇女作为性别的利益被搁置,甚至最终被放逐。
当妇救会发动乡村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到战争中后,她们的生活空间、社会角色都发生了许多改变。然而,血雨腥风的战争、延续千年的传统、尚未完备的革新制度都使得发生在妇女身上的变化受到抑制。
革命与传统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围绕着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中共的妇女工作一直在探寻前进的方向,摸索让妇女与中共自身都获利的途径。就实际而言,中共在民族、阶级利益面前暂时搁置了女性的利益,并将女性的解放最终依托于民族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上。妇救会作为中共妇女工作的一个具体实践组织,在革命与传统的博弈中艰难地生存着,而华北各根据地乡村妇女的生活也在这两者的摩擦中艰难地改变着。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王志刚)
Women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Vision of Tradition, Revolution and Gender
Wang Wei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in the tide of motivating the nation-wide resistance, women’s work was developed in the base areas of north China, and then Women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was also established in the area. After the association entered the rural area and developed the specific work, the conflict between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revolution and gender happened again and again. In order to keep the stability of rural areas and guarantee the resistance war, Women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continuously explored and adjusted it. The final result was that revolution yielded to tradition, and gender yielded to revolution. Meanwhile, the life space and social role of the country women motivated by Women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was somewhat changed. However, the changes were not radical, and war,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tself made them difficult.
D231;K265.1
A
1003-3815(2015)-02-0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