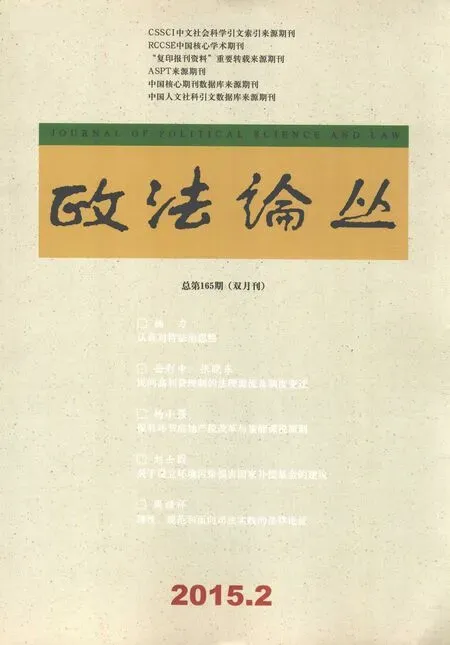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
徐梦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
徐梦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为论辩思维确立了逻辑导向。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断言的证成需要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规范性作为支撑,从而推进特定合理意图作为决策要素的参考性甚至规范性要素。论辩对话在言说当中直接针对表述本身,而表述背后发挥规则性与机制性引导作用的,主要是论辩主体的论辩逻辑思维。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建立在论辩前提或者依据针对特定立场的论证力量上。盖然性推论普遍存在于证成结论而诠释因由的言说当中。通过层次性呈现论证推导的隐含前提,有助于论者识别、分析和评价其推论模式及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法律论证 推论规则 盖然性推论
法律论证属于言说互动,但其规范性期待维持的稳定性、系统性和明确性,主要从法律论证的推论结构中进行探索。这是因为论辩思维探寻言说规律和逻辑体系的时候,不但要在形式化的论辩框架当中确立清晰和严谨的思维路径,还要在情景依赖的论辩对话当中推进多元的意义演进。总的来说,将法律论证视为推论结构的思维,应在论证情境基础上,依据分析意图保持其稳定性、同一性和普遍性。这种思路在面对法律论证这种特定类型的论辩对话模式时,主要是将法律论辩视为推论框架,从而通过形式化思维,推进论辩程序内在的程式化、阶段化、模型化探析。维持在语义推进的思维,使论辩的互动本质隐含于一致、严格、确定的结构化思维当中。
一、表征为推论结构的法律论证
论辩从思维层面和言说层面可以作为推论结构和对话模式。在前一种意义上,论辩内在地包含根据一个或多个理由和依据支撑或说明的结论。逻辑方法构成了建构论辩本质和标准的规范体系的规则;在第二种意义上,论辩主要作为对话性互动,主体通过言说性商谈意图达到解决意见或者立场分歧的结果。对话理论构成了推进对话论辩本质和标准的规则。当然,并非只有作为推论结构的论辩模式才能够予以形式化分析,①并且即使是逻辑推论引导下的论证结构也需要在对话当中建立起来。论证逻辑的分析是为了更好地在论辩对话当中推进推论结构的适用性及其明晰性,从而使两重意义上的论辩分析从对抗分裂走向协调整合。
形式化论证逻辑的前提,是将论辩本身视为推论结构。逻辑分析模式通过不同类型的逻辑推论,来呈现不同的论证模式。逻辑推论的论证模式反映出论证前提到结论的依据性关联该视角能够适用于论辩互动的分析当中,推进论辩型式的明确性和同一性。[1]P30逻辑论证体系对论辩的建构建立在是否能够说明或者反驳特定结论的基础上,对结论本身的强调超越了对歧见和纷争的整体性关注。新的信息呈现决定了推倒原有论证的反论必然层出不穷,即论证的可废止性。相互冲突的论证P和Q之间包含了两者之间矛盾的并非意义一致的关系。P和Q之间的胜负或者说证成力量的强弱应当结合论辩主题的内容予以判断。依据论题内容、论辩依据和论者目的来看,可以区分出论者推翻对方结论的方式,即直接证成相反结论、阐明特定推论规则的例外、针对前提予以反驳等。推论规则内在地设定了某种论辩陈述在意义上的论证力量,并容许势均力敌境况存在的可能性。
二、推论规则在法律论辩中的意义和反思
(一)推论规则在法律论辩中的意义
推论规则表征论辩的逻辑思维脉络,同时也镌刻在论辩进程的理性原则当中,使论辩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前提到结论的推进具备了基本的依据。论辩作为若干个由特定理由导出结论的若干步骤的序列,认同特定理由基于情境或者论者意图,导出不同结论的可能性,以及相同结论基于证成依据的属性和范围,由不同理由得出的可能性。据此,论辩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独立性。有学者将规则视为理由和结论之间,在论辩情境下表述出来的关系。[2]P74这种特性使推论规则效力的普遍性得以明确,同时也使探寻前提或者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关系的过程有了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模式。在法律逻辑当中,推论规则主要是“为司法判决或裁判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其基本设想是提供一套(法律)逻辑推论规则给诉讼博弈的裁判者进行司法裁决。”[3]显然,推论规则并非拘泥于作为思维模式的形式逻辑中,特殊的法律推论规则也必不可少。熊教授认为,法律逻辑中的推论规则主要表现在分离规则和证明责任规则。前者包含严格的和可废止的分离规则,分别表示为:
严格的分离规则:(∀x)(Px→Qx),Pa,∴Qa
可废止分离规则:(∀nx)(Px→Qx),Pa,∴Qa
这两个规则的内容都意味着通常情况下,对于所有X而言,如果P,那么Q,P,因此Q。前者不允许例外,而后者则认同例外发生的可能。显然,实践法律论证当中的推论规则是无法避免例外情形发生的,不同心理动机以及理念指向的多样化与独特性决定了每一个案件都独一无二。“立法者不可能为每个具体案件都准备好现成的法律答案,法官们不得不在法律不确定条件下探寻解决当前案件的裁决理由。”[4]那么在面对普遍性原则与规范的对应时,发现例外情形表现为一种常态。例外指向的是一种关于规则与论证的可批判性与可反思性。任何原则都有例外,而这些例外本身可能又根据某种相关性准则连接到一起,形成新的原则。例如对存在应当判处死刑的刑事犯罪行为,裁判主体需要将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除非手段特别残忍以外的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适用死刑情况的例外。
规范的例外,通过类型化与符号化的整合,形成系统的论题结构,在法律规范当中形成融贯而又明确的规则体系。严格的分离规则,在熊教授看来,仍然可能通过论辩负担的分配得以适用。引入证明责任规则,可以刻画严格分离规则在可废止的诉讼论证当中的运作。证明责任规则可以表述为:“在诉讼博弈中,负有证明责任一方若无法履行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明责任,那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该规则将特定主体未能有效履行法律分配的证明责任的情形,视为该主体的立场或诉求不成立,或者对方的立场或诉求成立的必要条件。基于某种价值追求的比较,等级和排序,论者特定立场可以进行预先设定,从而避免更加严重的社会后果的发生。这种预设可以根据特定规范的认同而确立,如“无罪推定原则”;在司法场域以外,也可以由论辩主体将特定命题设定为共识性前提。在这里,论辩主体在面对依据的充分性和相关性,无法确立命题在绝对层面上的真实性时,就不得不将事实认知的准则降低为:
“当无法证明P为真时,则P为假。”
或“当无法证明P为假时,则P为真。”
这种认知模式,在法律当中通常表现为特定命题P表征的社会问题。假定安全价值在特定案件当中需要首先考量,那么步枪里是否有子弹这个问题,就需要做出肯定性的设想,使试图证明步枪里没有子弹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5]P47对应实践当中,就存在较为严重的危险性;或这种危险性发生的概率较高;或认定举证责任时起诉方居于弱势;或易于证明特定情形的资源和信息主要由对方所有等情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况,就有可能需要将证明责任超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使对方作为应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我国法律规范当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基于特定价值导向,对认定某种命题或者情形是否为真,确立了假定性预设。②
(二)推论规则在法律论辩中的反思
法律论证当中的推论规则,为论辩思维确立了逻辑导向。在逻辑学当中,推论规则表征为由前提根据特定语法、句法、秩序或者关系属性,导向特定结论的功能。在经典和许多其他的非经典逻辑的语义学当中,前提为真的情形,通常可以导出结论为真。例如肯定前件论式modus ponens即表述为:If p then q,p,then q。推论规则包含典型语义性质的真值。通过前提推倒出来的命题,需要通过推论规则进行验证,但这种验证仅仅是逻辑思维层面的,同时需要面临实质层面的考察。一方面是因为法律领域当中主要的论证模式,通常会存在法律规则作为不可否认的前提的情形。因而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③就无法适用于由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的演绎推理当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宏观上讲,推论规则本身并不能和法律论证规则划等号,前者主要是在思维层面,确立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经常被运用于数理逻辑问题的分析。事实上,“人类对于规范的态度与规范本身都不容许进行数值描述。”[6]P233因而有必要从诸多推论规则中,确立逻辑推论的四种基本规则。尽管并不限于法律领域的论辩或者推理,但却鲜明而有效地表述了法律思维当中,通过论辩言说确立某种结论为真,并使该结论对应法律规则预期的某种社会效果的过程。因而,试图确立法律论证特有的推论规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论辩前提和预期结论的关系,通常情况下需要结合规范体系、日常经验、商谈共识等多重要素予以辨别。拘泥于这种关系无法对法律论证提供直接、具体的引导性规范。
推论规则的研究,不但可以从预设规则体系的认知当中,探讨其应用和效力,也可以从规则调整或者干预对象的属性,遵循开放性思维,在规则所处的具体情境当中寻找其道德根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无论是关于健康,还是和行为或者何者对我们有益相关的问题,并非一成不变……主体不得不在每一种情形中认真揣度,何者对该情形来说具备恰当性。”[7]言说规则内在的情境依赖性,决定了从前者入手的分析,或许很难获致对法律论证规则精髓的理解。然而,两种思路却是不可分割和相辅相成的,后者因此只是取得了相对重要的理论地位。这不但是来源于实践智慧对特殊性的认知,也源于将其确立为“合乎逻辑、真实并且是依据人之善意而行为的一种能力。”[8]据此,法律论证规则建立在法律实践当中,自然无法固守于将其视为完善的、协调的、静态的和自足的规则体系这种理念。
从法律方法的范式转型角度来看这种理念将主体和客体、事实与价值分割开来,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可以在摒弃价值判断的情况下达到对真理的获取;试图通过形式逻辑思维将规范解释与事实认定切割开来,将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分离,并把规范调整对象作为可兹控制的客体。这决定了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往往很难实现对称性和协调性。如果仅仅是为了将案件事实强制归类,并切割成为符合规范要件的若干情节与模块,试图通过严格确立特定命题陈述,来决定法律思维的批判模式,就有可能掩盖甚至消除案件中关键的涉及裁决公正性的重要细节。因而,法律发展变化的多重可能性,以及生活世界语言游戏规则的自发性被否定了。法律本身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但社会生活的发展并不可能遵循法律本身的模块化预期,任何价值的认知与排序、需求的变更乃至科技的进步和精神层面的动向,都有可能使原有规范预设的行为指向和互动方式变得过时和陈旧,直至被人忽略。法律论证结论并不具有排他性。证成特定立场的方法具有多重性,论辩结论及其效果的呈现也是如此。因此,法律论证规则无法要求特定论证互动得出最佳的结果,而是认同一种情景开放的,可错的,非单调的,同时也是多主体在诸多环节的论辩互动以后,得出的并非绝对、永久、唯一“正确”的共识性认同。这就决定了法律论证规则无法像规定“一加一等于二”那样,能够根据线性的纵深思维,走向一种确定稳固的答案。这是因为不同的符号运用,依赖的智识基础并不一定总是因循自然规律,有时主体意图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荷兰法学家Scholten看来,法官的裁决是否具备可接受性,需要根据他(或者她)是否确定无法再做出任何不同的裁决。[9]P113他承认该观点中并没有蕴含着对特定裁决结论唯一正确性的肯定,因为有可能其他法官可能就同一案件做出其确认为正确的裁决,并且认同该裁决无可替代的信念。这种观念在提出他者或者第二或第三人称,就法律决定在论辩合理性检验基础之上的认同,也保留了互动层面上的可废止性的认同。显而易见的是,依据主体自我确认的标准,却仍然有可能得出相互矛盾,但得以证成的陈述或者结论。
当然,如果将法律论证基于结论效果以及立场合理性的判断,走向极端的相对性,并且对有效法律理论或者规范性引导对法律论辩的约束作用产生质疑,认为这些理论无法表征合法性基础,而仅仅是法官个人的自我确信,④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论辩在规范性约束下的可废止性,但却有一定道理。法律论证内在的言说规则,能够帮助说者确认论辩话语在证成特定立场中的作用,并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严谨而又开放、精准而又灵活、清晰而又通达地铺陈依据,陈述理由,从而有效地平衡规则约束与言说自由的空间,通过可信的论辩赢得即使是表面上失势的案件。⑤
三、法律论辩实践中的逻辑推论分析
法律问题的分析主要借助法律论证内在的批判性反思得以推进,任何法律断言的评价都离不开对其证成力量强弱的评估。而评价的结果往往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特定法律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断言的证成需要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规范性作为支撑,从而推进特定合理意图作为决策要素的参考性甚至规范效力。在司法实践当中,论辩对话在言说当中直接针对表述本身,而表述背后发挥规则性与机制性引导作用的,主要是论辩主体的论辩逻辑思维。如果说法律问题本身以及问题解决的程序本身揭示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运作理路,那么逻辑推论思维及其针对的对象的意义陈述,也体现出论辩强弱评价对应的不同系统性方法。更确切地说,这种思维能够作为验证说明性要素或者理由,在说明前提到结论之间关系的证成力度。具体到法律实践当中的言说论辩,在对规范和事实进行有效逻辑剖析,并对其中的规范性元素进行对应整合的时候,逻辑推论思维对法律论证的开展提供了清晰的推进系统。
(一)法律断言表述的说明性结构
任何法律断言需要通过特定理由或者依据予以说明或者证成,即当R1→C1,对C1的宣称应当以对R1的证成为前提。当然,在前提并非明确或者尚未得到有效的支持或者认同,或者没有特定权威机制予以保障从而确认其可接受性的时候,论者需要诉诸一种内在的依据性断言⑥或者所体现为某种保证来说明特定断言所包含的,命题R能够对于另外一个命题C提供某种理性支持。这种支撑性关系,或者说对于包含不同说明关系的符合命题的宣称或者断言,在论者负担说明、证明或者说服义务的时候,应当作为完整的断言性宣称,促使论者为其发掘、整合与呈现说明依据。假定这种说明关系P,即R1→C1需要通过命题Q予以证明,这种论证思路就可以表示为:Q→(R1→C1)或者Q→P。在论证进程约定的容许范围内,反方仍旧可以进一步追问该第二阶段的说明关系的依据。通过对前提到结论的证成关联的不断反思和追问,论辩推理当中涵盖的缺省依据得以明确化,同时也通过论题在逻辑思辨的层面上不断演进,最终证成初级层面的论辩立场和意图,同时也最大化程度地发掘出可能的证成特定命题,在各个层面上的证据和理由。作为推论结构的法律论证,认为任何可被识别与确认的论证都具备某种逻辑形式,即使是这种逻辑结构的呈现并非清晰明确。[10]P171-184此外,该理念也认同依赖特定证据或者理由的法律断言都包含着可以深入发掘的,不断探寻其深度缘由或者说明性要素的盖然性推论。这就是通过呈现特定逻辑形式的,作为推论结构的法律论辩。通过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的法律断言分别予以探讨,有助于推进这种逻辑推论结构的明确化。
1、实体法相关的法律断言
实体法律是直接决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体系。特定法律断言无论是从规范向度阐述的抽象性宣称,还是具体的事实向度的描述性宣称,都能够通过剖析其内在的逻辑推论结构,来明确特定法律断言应当对应和符合的前提条件。这里通过《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的表述为例进行分析。本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本规范对善意取得制度中包含的逻辑构成要素可予以分析、解构和明确,其中主要包括:
Pn1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
Pn2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Pn3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Pn4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Pn5 法律没有另外进行规定。
Pn6 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据此该规范性法律断言的逻辑结构整合为:
If(Pn1 & Pn2 & Pn3 & Pn4 & Pn5)Then Pn6
论者在试图证成特定情形下主体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善意取得的过程中,显然需要为Pn1到Pn5中的每个要件通过特定证据或者理由予以说明。对方可以反驳第1到第5中的任意要件来推翻对方的观点。无论确认特定结论的前提之间是析取还是合取关系,都应当诉诸逻辑推论模式的清晰呈现,严格地依照规范要件确认的内容来为特定结论或者立场的说明提供依据或者理由。这不但是因为法律论证要求严谨、权威、明确和稳定的规则为论辩思路提供清晰的“路线图”,而且实体规范当中确认的权利义务认定和分配方案都和个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此外,特定前提的证成,在深入到特定语义诠释的过程时,论者必须为其理解特定术语对应实际语境解读的合理性或者可接受性予以论证。实践中经常出现针对法律术语诠释的范围和意义发生争议的情形。⑦如在上例的分析当中,要件Pn2和Pn3中的“善意”和“合理”对于论证来说,并不像提供证据以明确事实认定那样存在直观性、鲜明性并且思维导向的目的比较单一。论者在符合上述证成要件的充分性和相关性之后,显然很有可能使论辩推进的焦点集中在对上述术语应当如何诠释这个问题上。
2、程序法相关的法律断言
程序法主要包含证据识别与适用的规范化,以及法律诉讼论辩的程序,反映实质法律问题应对和处理的阶段、模式和进度。程序法确保实体法的运作和实现,实体法的规范性内在地要求其效力得以实现的过程的规范性。作为规则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诉诸证据规则来确认特定法律问题本身,也是需要通过特定证据对照的表述或者断言得以实现的。这种断言不同于实体法相关的法律宣称。程序法相关的立场,主要针对特定法律程序或者证据,或以其为对象,从验证不同证据试图证明的事实或者问题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信度。例如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即第53条的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⑧
本条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包含的逻辑构成要素也可予以分析、解构和明确,主要包括:Pn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Pn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Pn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Pn4证据确实、充分。
据此可以将该规范性法律断言的逻辑结构整合为:If(Pn1 & Pn2 & Pn3)Then Pn4
与上文当中实体法相关的法律断言的逻辑结构相类似,本规定特定法律问题或者案件认定对应的,关于证明标准的立场的真值或者有效性,同样要以Pn1到Pn3全部为真作为前提。从结构上看,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的法律宣称具备统一的逻辑推论结构,但相对来说后者从论辩思维及其抽象程度等方面,更加趋近于对前提到结论之间说明或者证成关系的论证。显然对于Pn1、Pn2 和Pn3来说,论者同样需要诉诸更进一步的证据及其内在包含的理由,假定为Sn1、Sn2和Sn3,其无论是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相关的法律问题当中,都发挥保证的作用,但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其面对问题的属性存在差异。相对于实体问题当中更加注重确认实际权利义务分配的可能决策,程序问题中特定立场的确认和证成,直接关联思辨性、抽象性和规范性,即直接进入到论辩规范性的反思当中。最能反映该属性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即要求对证据予以查证属实,全面综合地判定特定事实认定或者其他法律问题,是否能够面临反驳和质疑而不被推翻。“合理怀疑”的认定更多从属于主观层面,依赖认知和识别能力以及主体价值观的问题。
(二)从证据入手分析法律论辩的可废止性
法律规范当中涉及的命题判断具备可反驳性或者可废止性,使法律论证由前提到结论存在一种“跳跃性”,即结论的确定是由一系列相互支撑的理由架构得出的“似真”或者“视为真”的判断。在缺少严格的形式逻辑推导的思维进程时,由若干理由直接跳过可兹争议的“鸿沟”直接认定结论性判断的正确性;这种刻意的冒险是基于这种认识,即针对特定结论的说服力在特定理由陈述的内容来看未必是单向的,有的理由同时能够产生反作用力,涉及到该命题的相关性资源在充当说服性依据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推翻该结论。因而,可反驳性也意味着论辩主体以及裁决者要衡量不同理由之间的“作用力”,法律命题的可反驳性是推进制度发展的语用前提,同时也是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基础。形式逻辑恒定的“真-假”二分理念受到冲击,因而受到关联信息变更的影响,以及推导合理性程度预期的评估。[11]因而,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建立在论辩的论证力量上。
通过证据来确认特定命题作为前提对不同假设的证明,不仅在演绎论证中得以体现,更多的是在归纳论证、溯因论证或者类比论证中得以体现。鉴于间接证据较于直接证据更易获取,并且特定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证明通常需要建立尽可能完整和充分的证据链条,因而归纳推论或许通过证据进行的法律论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无论是采取何种推论模式,上述论辩都具备可反驳性和可废止性。论者对此种属性应当维持一种谨慎、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从而有效地推进缺省推理当中隐含的预设和前提的可接受性。可废止性论证的前提无论通过何种逻辑模式推出结论,都需要预估、关注和反思其他可能前提对该结论产生的反作用力,或者违背己方预期的证明或者论证效力。论证的可废止性因而拓展了论者论辩反思的范围,提高了对其谨慎防范和严密维系其立场的要求。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即使P1到Pn能够证成命题C,也仍然存在即使是潜在的否证或者延迟其效力认同的Pn+1,导致特定前提推进、确认和证成特定假设的可接受性有所打折,甚至消灭殆尽。这也说明法律论证可废止性无法避免。对2014年年底再审确认无罪的呼格吉勒图案进行简化和明晰的分析,可以反映出针对证据进行反驳的逻辑脉络:
论证一:
p1:呼格吉勒图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p2:呼格吉勒图左手拇指的指甲缝当中附着与被害人血型相同的O型人血;
p3:呼格吉勒图和闫峰聊天时,曾流露过某些关于性的想法;
因此,呼格吉勒图是本案凶手。
论证一通过诉诸若干证据作为前提做出结论,试图依据证明前提的真确保结论之真。这里需要反思到底p1到p3均为真的情况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认证据指称的预设或者假定属实。尤其是当接下来分析的这些前提即p4到p8同样为真时,p1到p3为真为最终结论的认定又可以呈现多大程度的证成力量,都是值得考究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实践法律论辩在事实和规范问题的整合、确认、探究和论证当中,必须严格因循证据或者依据的脉络走向,有针对性地从不同说明性要素当中,发掘对于论题涉及争议产生有效论证力量的阐述方式。
论证二:
p4:呼格吉勒图关于犯罪手段的供述与尸检报告存在矛盾,无法对应一致。
p5:呼格吉勒图的有罪供述存在不稳定之处。
p6:办案人员对呼进行了刑讯逼供。
p7:血型鉴定结论,以及呼格吉勒图的日常言论不具有排他性,无法独立证实呼的犯罪行为,且更加关键的证据例如精斑样本莫名丢失。
p8:2005年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主动交代其1996年犯下本案。⑨
据此在上述论证当中,两者显然属于可废止性论证。论证二针对论证一当中的依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论辩的规范性深刻体现在从论证一到论证二的过度之中。该规范性主要体现在针对论题的明确性,即呼格吉勒图是否该案凶手;涉及论题争议的不同意见的明确性,即存在正方和反方针锋相对的观点。论者不应对于呼格吉勒图定罪问题存在模棱两可的态度或者立场不明确的情形,但在证成其立场的同时论者更应当认同其立场被反驳甚至推翻的可能性,即论者应当确信:“我可能是错的,但是我能够为自己坚持的立场提供充分的、相关的、正确的和合法的依据。”这种态度并非矛盾,而且反映出理性论辩当中批判性思维模式的主导意义。论辩的可废止性因而并非是客观存在的辨识准则,而是像“可接受性”一样包容特定评价性和不同意见的加入,使其作为论辩具备的某种特点包容被推翻的“自我否认”的可能性,即使是实际上尚未或者最终未能被否认。
四、盖然性推论(enthymeme)在论辩思维中的呈现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修辞式推论”,又可以称为为缺省推理或者enthymema(恩提摩玛),即演绎三段论的非形式化处理,实质上则是日常语言当中基于意义传达的便捷性和效率期待所常用的方法。通常缺少了确保论证效力的某一或者某些前提,或者结论。其最为经典的论辩例证,就是“所有人都会死,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该论证将命题“苏格拉底是人”这一点视为无需表明的假定,并且预期所有理性主体都能够认识到该命题是论辩的有效前提。enthymeme并不排斥传统的演绎和归纳思维,而是将他们融入到了语用探讨和可能性辩证考察的过程之中,因而成为了思维的连接点或者推断性要素。论辩言说中的预设前提能够对特定立场或者结论具有说明、证成和其他推动作用,能够提升听者依据这些前提对该立场或者结论的信服与认同。语用预设包含了这种说明性前提,尤其是在诠释某种结果的缘由和证成某种结论的依据的时候。事实性预设通常则可以通过证据予以证明。作为一种论证方式,缺省推理不但可以省却论辩整理所有前提,标明所有预设的负担,而且能够在言说互动当中帮助听者考察对方基于预设的论辩策略,并对此予以反思和质疑。
盖然性推论普遍存在于证成结论而诠释因由的言说当中。论辩结论包含评价、预测、断定、承诺、祈使、允诺等言语行为类型,对这些言语行为的解释要在论辩程序中,诉诸实质和逻辑相关联的依据。逻辑相关性说明证据E与前提h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性,当且仅当在法官看来,证据E具备使h具备比不存在证据E时更强或者更弱的可能性的特质。这些依据往往有可能称为进一步推证的切入点,从而使论者直接深入到争议焦点的探讨当中,从而能够更有效率地推进争议的解决。论证立场存在评价性要素的情形能够作为典型的例子予以说明,假定论者针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好坏”予以论辩,不同论者做出的解释依赖各异的隐含前提:
论证A: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害的,因为如果在任何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体制就会崩溃。
论证B: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害的,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全面适用可能增加司法成本。
论证C: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害的,因为其认定过程存在难度,非常复杂。
显然在上述三重论证中涉及的隐含前提在共识范围上存在差异,A1:“司法体制崩溃有害”,B1:“增加司法成本有害”和C1:“复杂的认定过程有害”这三项立场都构成了不同论辩当中充实和说明不同逻辑相关性的要点。反驳这三重论证的切入点也是由不同理由、依据而展开。面对同一结论的不同诠释显示出在语义层面上的多元性,同时也促使论者从不同向度尽可能充分地结合特定立场发掘诠释依据,从而提升对方反驳的难度。
除了对比针对特定立场的不同论证,通过单一证据针对结论的逻辑相关性通过盖然性推论的模式,能够更加直接地予以呈现。美国证据学家Edmund Morgan就提供了逻辑相关性链条依据enthymeme的模式呈现的例子。[12]P175-202假定主体S被控告谋杀T,检方提出的唯一证据就是S给T的妻子写了情书。该证据似乎无法直接与他谋杀T提供依据,但是通过层层推进的盖然性推论呈现,就能够使对方发掘出其论辩意图、规划与构思。在本例中:
En:S给T的妻子写了情书。
Cn:S实施了谋杀T的行为。
本例体现出来不同命题之间的逻辑相关性对于确证某种假设来说,还需要至少在思维上或者论辩理路上呈现出怎样的推论链条,该进路是否包容多重可能性的判断和推理等。在美国的证据规则体系当中,法官应当解构(unpack)从En到Cn之间的盖然性推理的思维进路,从而尽可能更加充分地将其论辩过程呈现出来,从而推进对En到Cn的逻辑关联性。Edmund Morgan依据该案例揭示了逻辑相关性链条的论辩思路:
1、(E1)S给T的妻子写了情书。
2、(C1/E2)S爱慕T的妻子。
3、(C2/E3)S期望T的妻子处于单身状态。
4、(C3/E4)S期望除掉T
5、(C4/E5)S计划除掉T
6、(C5/E6)S通过非正当手段杀害T从而实施了除掉T的计划。
7、(C6)S实施了谋杀T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该论辩思路的盖然性推导中从第二步到第六步中的假设,同时也承担着作为依据或者证据的功能。相互连接的两个命题之间表明了这种依据和假设的关系,从命题的标志中可以发现,E1为证成C1提供依据,E2为证成C2提供依据,以此类推,从而使该论辩思路中的每一重假设都实质相关。在Morgan看来,每一步思路的推进都表征为盖然性推论(enthymeme),因为深入到不同前提之间的说明关系当中,仍然存在隐含的推翻或者中断推导链条对情景要素的可能性要素,有待论者在面临反驳或者其他需要承担说服或者证成义务予以进一步说明。如在上例的分析当中,法官依据其秉持的经验积累、知识背景、价值观念⑩的解读获取上述逻辑推论的“解离”其中包含着以下隐含前提,或者说在批判性反思当中仍待深究的隐含预设或者前提:
1、(E1→E2)通常一个男人给女人写情书意味着他爱慕这个女人。
2、(E2→E3)通常一个男人爱慕一个女人时,他或许希望这个女人没有配偶。
3、(E3→E4)通常一个男人期待爱慕的已婚妇女单身时,或许希望除掉她的丈夫。
……
上述隐含前提和前置性假设共同构成了盖然性推理中缺省的部分,这不但是因为上述前提的识别、意会甚至认同相对容易形成,而且即使缺省推理可能依据诠释性反思的持续而层层推进,基于论辩效率和程序性考量通常也没有必要继续求证。尽管如此,很难说上述命题构成了能够充分说明结论的前提集,或者说排除了任何合理怀疑或者反证的可能。Morgan虚构的这个案例说明了论辩作为推论结构在法律思维中的逻辑推进,呈现出因循语形符号的意义推导的论辩框架,再现了依赖证据说明特定问题的方向和结构性脉络。最重要的是,论者能够借助该思路发掘出对方可能试图省却或者隐藏的“先在性认知”;有效评估证据对应法律问题的争议包含的态度假设,是否具备逻辑相关性和实质相关性;是否具备确认假设Cn的充分性,以及权衡不同证据针对该假设的张力。无论是基于程序性约束还是其他限制,法律人可能都无法绝对完整地将论辩的推论结构呈现出来,但这无疑有助于论者识别、分析和评价其推论模式及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因为不同的推论模式依赖不同的思维进路,具有不同的认知和认同效力。
无论是将论辩逻辑结构予以明确呈现,还是据此将其归为论辩的逻辑推论规则模式,都不足以说明论辩规则的完整内涵。“将适用广泛和复杂的法律论证进行精确的形式刻画,如同把法律论证看做单纯的逻辑推演过程,视为逻辑学在法律领域的简单应用,”[13]主张法律制度作为封闭逻辑体系的看法是偏颇和不全面的。然而需要承认的是,将命题陈述的逻辑结构(例如肯定前件式)可以将不同陈述命题具体例子中的表述结构抽离出来,形成一个稳定的逻辑推论体系,但这种归纳模式形成的仍然属于形式逻辑规则的传统模型,并且未能达到和突破逻辑对话规划的反思性推进。尽管保证或推理规则不是论证的一部分,这绝不会减弱其对论证评估的重要性。的确,我们不能说论证的前提构成相关的和充分的理由以接受结论,除非推论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靠的。静态化的推论规则,在法律情境中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和构成性,并且注重分析法律思维的逻辑演进及其规律性。通过形式化的逻辑推论规则在法律言说互动中的意义的分析,不但可以使论辩情境避免走向矛盾和混乱的风险,也能够完整呈现从抽离时空要素和静止孤立的思维,向情景依赖、语用商谈和认知协同的论辩规范性跨越的必要性。
注释:
① 论辩的形式对话体系研究参见:C.L. Hamblin. Mathematical models of dialogue. Theoria,37, 1971. pp130-155. J. Woods & D.N. Walton. Arresting circles in formal dialogue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7. 1978, pp.73-90. and J.D. MacKenzie. Question-begging in non-cumulative system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8, pp.117-133.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③ 表征为Modus Tollens。“If P, then Q,not Q,Therefore, not P”。
④ 参见:R. M.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law review. 1983, 96, pp.561-675.
⑤ 参见:A. R. Lodder. DiaLaw- een dialogisch model voor juridische argumentatie, in: E. T. Feteris et al. (eds.), Op geode Gronden, Ars Aequi Libri, Nijmengen, pp. 138-145.
⑥ 参见:Scott Brewer. Logocratic method and the analysis of arguments in evidence. Law, Probability and Risk(2011) 10, 175-202.
⑦ 法律规则是立法主体基于权威性地位确立的制度体系。法律本身作为一种包含权力要素的“宣称性”言语行为,其效力有时并不一定表现为明确的关系调整和资源配置,而是需要照顾规范指涉的关系类型本身的语境敏感度。立法者对规则的建构在意图实现特定的社会效果的同时,有时也为了避免其他结果的发生,因此含混性的用语通常无法避免。立法者对含混性规范术语的运用,使对规范的解释本身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含混性,其中包含是否运用含混性谓词,或者是否要对含混谓词指称的边界性情形进行参照性分析等。规范内涵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案件当中,法律人对于规范的理解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根据实际情形进行变通性和延伸性理解,调整类似关系类型的法律规范,或者具有同种类型化标准的法律范畴在理解和认定过程中,往往可以以该类型作为思维导向,如数量、进度甚至情境叠加等类型化标准的递增或递减,从而对规范效力的具体实现效果产生影响。法律内容含混性的外在来源也可以归结于不同类型法律渊源之间对特定问题,或同类对象的理解、诠释和运用上的不同,或者不同部门或同一部门的不同法律条文之间对特定谓词外延的界定存在区别。参见:徐梦醒:《语用学视野下的法律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42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
⑨ 该案例的详情,参见:“呼格吉勒图案现在怎么样了”, http://www.laoren.com/law/2014/404170_3.shtml,2014年11月21日。
⑩ See J. Thayer,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 265(1898), Regarding the source for a judge’s ‘unpacking’ of an evidentiary enthymeme, see source cited supra,note 11 and accompanying text.
[1] I. Rahwan & G. R. Simari.(Eds.) Argument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rlin: Springer, 2009.
[2] Harry Bart Verheij. Rules, Reasons, Arguments. Formal studies of argumentation and defeat. Omslag: Grietje Verheij en Charlot Luiting, 1996.
[3] 熊明辉. 论法律逻辑中的推论规则[J]. 中国社会科学,2008,4.
[4] 王洪. 法的不确定性与可推导性[J]. 政法论丛,2013,2.
[5] Douglas N. Walton, Informal Logic, New York/Port Chester/Melbourne/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丹麦]阿尔夫·罗斯. 指令与规范[M]. 雷磊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7]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II, chap. 2[1104a].
[8]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VI, chap. 5[1104b].
[9] P. Scholten, Mr. C. Asser’s handleiding tot de beoefening van het Nederlands burgerlijk recht, Algemeen deel, Tjeenk Willink, Zwolle, 1974.
[10] Henry Prakken. Argumentation without arguments. Argumentation, Volume 25, Issue2
[11] 徐梦醒. 法律论证的规范性融贯研究[J]. 法学论坛,2014,6.
[12] Edmund Morgan. Basic Problem of Evidence, 1961. pp.185-88. From Scott Brewer. Logocratic method and the analysis of arguments in evidence. Law, Probability and Risk,2011.
[13] 张晓光. 法律论证的逻辑取向[J]. 政法论丛,2008,6.
(责任编辑:孙培福)
Reference Rule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XuMeng-xing
(Law Schoo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nomis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The rules of inference in legal argumentation has formulated the logical orientation for the thinking of argument. The justification of legal claims within legal practice requires the normativity as precondition from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laws, thereby prompting the reasonable intention as critical even normative factors for decision-making. The argument in discourse acts as and against statement itself, and it is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arguer works under the statements as regularity and guidance. The defeasibility of legal argument establishes itself on the strength of argumentation toward certain standpoint of premises, evidences and reasons. The enthymeme is widespread in development of utterance on justifying certain verdict while explaining the reasons and causes. By representing from various aspects the implicit premises of inference, it would be easier for arguer to identify,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inference model of legal argument and its reasonableness and effectiveness.
legal argumentation;rules of inference;enthymeme
1002—6274(2015)02—152—09
徐梦醒(1986-),女,河南许昌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政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学方法论。
DF0-05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