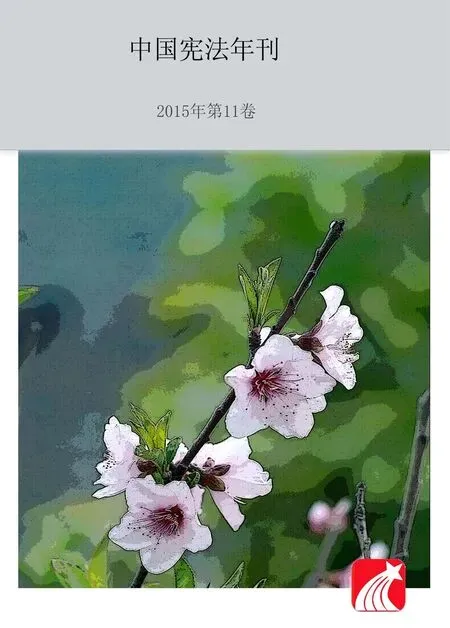2015年英国宪法学焦点
——《1998年人权法》的存废
屠 凯
2015年英国宪法学焦点
——《1998年人权法》的存废
屠 凯*
继2014年苏格兰公民投票引发的热议之后,《1998年人权法》(The Human Rights Act1998)的存废成为2015年英国宪法学界的焦点。
众所周知,《1998年人权法》以制定法的形式和位阶在英国原有的普通法司法审查机制内引入了具有准凌驾性的欧洲人权法规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提升了对所谓“违宪审查”英联邦模式的期待。因而,2015年在特定政治条件下出现的英国《1998年人权法》存废问题也就不仅仅是该国自己的焦点,其还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并可能为我国宪法学界提供某些启示。
英国宪法学界的当代主流作品普遍谈及《1998年人权法》的制定、功能和比较法价值。而对《1998年人权法》的专门研究亦有不少。扬(Alison L.Young)的《议会主权与人权法》(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一书系统分析了《1998年人权法》对英国过去奉行的“议会主权”原则的冲击。①按照传统观念,“议会主权”意味着位于西敏寺的英国议会可以制定或者修改任何法律,但《1998年人权法》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英国议会的立法权,要求英国制定法在国内法的范围内也不得与《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相冲突。卡瓦纳(Aileen Kavanagh)的《英国人权法下的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 under the UK Human Rights Act)一书则研究了《1998年人权法》对英国所谓“违宪审查”机制的塑造。②除了这些新出杰作,英国宪法学界还有一些专著和编著对《1998年人权法》引发的其他法律问题。③2015年英国宪法学界对《1998年人权法》存废问题的讨论则集中于英国宪法学会的官方博客。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①Alison L.Young,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Hart Publishing,2009.
② Aileen Kavanagh,Constitutional Review under the UK Human Rights A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③Helen Fenw ick et al.(eds.),Judicial Reasoning under the UK Human Rights A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我国宪法学界很早就注意到《1998年人权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何海波在10年前的《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一文中将《1998年人权法》创设的法律监督机制概括为“议会立法自身授权法院的审查”的类型,并强调《1998年人权法》“使得英国法院能够名正言顺地审查议会立法。它对于司法审查短期内的实际影响也许不是很大,但对英国宪政的影响极为深远”。①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李蕊佚在细致研究了英国《1998年人权法》后主张,“英国弱型违宪审查的制度和原理为其他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国家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②李蕊佚:“议会主权下的英国弱型违宪审查”,载《法学家》2013年第2期。王锴注意到《1998年人权法》的通过使英国议会制定法被置于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审查/违宪审查下,冲击了传统的议会主权观念,并引起英国宪法学界的一些担忧。③王锴:“政治宪法的源流——以英国为中心”,载李林、莫纪宏主编:《中国宪法三十年》(中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何永红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梳理英国宪法学作品的基础上做了回应。④何永红:“政治宪法论的英国渊源及其误读”,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结合上述研究,本文将对《1998年人权法》存废牵扯到的若干宪法问题做出介绍和分析。以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1998年人权法》所创造的英国法律监督、法律解释机制的介绍,这一机制的肯綮允许普通法法院对议会制定法做出(与《欧洲人权公约》权利)“不一致”的宣告;第二部分将综述《1998年人权法》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主要是英国保守党的政治打击,并解释为何《1998年人权法》已成覆水难收之势;第三部分将提及《1998年人权法》与英国权力下放进程的错综复杂关系,提醒读者注意人权法规范和地方自治规范在宪法上可能制造的紧张冲突。第四部分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一、《1998年人权法》创造的英国法律监督机制
毋庸赘言,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审查的建立原本是基于制定法的“越权无效”理论的,即以议会的立法目的和范围约束其他公权力机关。⑤何海波:“‘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英国学界一场未息的争论”,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今天亦有基于普通法的司法审查理论,即以普通法法院为普通法的发现者和“移植者”、本社会本文化基本价值的监护人,希望直接以普通法约束除议会以外的公权力机关。⑥Turpin,Tomkins,“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itution:Text and Materia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57-658(6th ed.2007).但无论如何,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审查不能代替公权力机关做出实质判断,这与根据制定法具体条文进行的审判和“复议”相区别,约等于我国所谓“法律监督”。⑦Id.,p.656.在这种法律监督机制下,普通法法院可以实现根据制定法对附属立法、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也可以实现根据附属立法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在缺乏制定法和附属立法时,也可以对一部分行政行为根据普通法予以审查。但普通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制定法优先,即理论上不应存在普通法法院仅仅根据普通法对制定法的审查。对于这种机制下的普通法法院而言,制定法冲突是比较棘手的,理论上应当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处理,理由就是议会改变了之前的主张和立法,普通法法院简单服从即可。综上,这一机制看似也能对绝大多数行政行为予以控制,未尝不是一种成熟的法律实践。但是,现实中由于英国的西敏寺议会制,行政机关即“内阁”本身即议会中执政党前座议员的集团,且行使一部分行政权的枢密院也由执政党大臣掌握,所以根本上,不能控制议会的普通法法院也不能控制行政机关。
1951年《欧洲人权公约》的签订为英国改变上述司法审查机制埋下了伏笔。1998年基于公约产生的欧洲人权法院成为全日制机关,并开始直接受理全部欧洲人权法申诉,这一变化直接促使英国制定《1998年人权法》。实际上,在1998年之前,欧洲人权法院已有判决宣布英国制定法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但英国是一个实行二元制的国家,《欧洲人权公约》不能自动在英国国内生效。过去,普通法法院遇到《欧洲人权公约》与英国制定法冲突时,都“假设议会无意违反国际法,特别是特定的国际法义务”,并据此处理,当遇到制定法解释问题时,也尽量求得与《欧洲人权公约》相一致。①Turpin,Tomkins,“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itution:Text and Materia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71.至于《欧洲人权公约》与普通法的关系,则比较复杂。普通法法院中,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上诉法院倾向于认为《欧洲人权公约》实际上澄清了普通法中一直存在但尚未清晰的原则。在英国最高法院创设之前,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则明确表示《欧洲人权公约》与普通法在内容上不尽相同。②Id.,p.271.至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虽然该法院并不像普通法法院一样秉持“遵循先例”原则,但是各国本地法院基于对欧洲人权法院对于不同国别的类似案件倾向于同样审判的信念,一般会对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像对《欧洲人权公约》一样尊重。
《1998年人权法》通过将《欧洲人权公约》的主要文本以制定法的形式纳入英国国内法,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法律监督机制。具体而言,《1998年人权法》规定,议会制定法的解释和效力应当尽可能视为同《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相符,但是,一旦普通法法院无法得到上述见解,则可以宣布议会制定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当然,这种宣布不影响制定法的效力或者行政机关继续依法执行,是否修改制定法由议会决定。《1998年人权法》还规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否则将遭到司法审查。至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1998年人权法》并未将其一并纳入英国国内法,但允许普通法法院在判决时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既有判决。也就是说,虽然《1998年人权法》并未授权普通法法院废止议会制定法,但是相比于过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扩张了普通法法院的权力,允许他们做出“不一致”宣告,并且允许他们基于人权规范对行政机关行为展开广泛的司法审查。在英国成熟的法治环境中,如果制定法遭到“不一致”宣告,执政党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一般会及时采取措施,修改或者废止被宣告“不一致”的制定法。《1998年人权法》甚至还要求内阁部长在向议会提出法案时说明法案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这也避免了后续制定法与《1998年人权法》乃至《欧洲人权公约》的冲突。
那么,《1998年人权法》的这种“准凌驾性”是否赋予了该法某种“宪法”性质呢?在英国,发现宪法渊源一直是个难题。以往,没有任何制定法具有凌驾性,遑论普通法原则或者宪法惯例。英国因而成为采取所谓“不成文宪法”制度的典型国家。英国宪法学界总有人希望确定某些制定法的“宪法”属性,而《1998年人权法》显然是排名极为靠前的候选者。高等法院行政法庭的劳思法官(Laws LJ)在著名的“叟邦”案[Thorburn v.Sunderland City Council[2002]EWHC 195(Adm in)]中确实提出,英国法上存在宪法性制定法与普通制定法的区别,前者非经明文不得废止。劳思法官补充说:“一部宪法性制定法需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这部法律宏观地处理公民和国家的法律关系;第二,这部法律扩大或者限制了我们今天所谓基本权利或者宪法权利。”法官本人眼中的宪法性制定法就包括几部涉及权力下放的制定法、1972年欧共体法,以及并非出乎意料的——《1998年人权法》。①C.Mac Amhlaigh,“HRA Watch:Reform,Repeal,Replace?A Referendum on Repeal of the Human Rights Act?Why not?”,UK Const.L.Blog(25th May 2015).但是,诚如论者所指出的,劳思法官的这段论述不过是普通法判决中的附属意见,并无法律效力。②A.Perry and F.Ahmed,“Are Constitutional Statutes‘Quasi-Entrenched’?”,UK Const.L.Blog(25th November 2013).与此相关,就所谓宪法性制定法,冰翰和霍夫曼法官在“罗宾逊”案(Robinson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Northern Ireland[2002]UKHL 32)曾经主张予以灵活解释及目的解释,就所谓普通制定法则根据普通法的一般标准解释。③A.Tomkins,“Confusion and Retreat:The Supreme Court on Devolution”,U.K.Const.L.Blog(19th Feb 2015).但英国最高法院霍普法官在“AXA保险”案(AXA General Insurance v.Lord Advocate[2011]UKSC 46)中坚持对《1998年苏格兰法》予以一般的制定法解释,并不另眼看待。④Id.可见,英国对于哪部制定法算是晋升宪法之列尚无通说。所以是否可以将《1998年人权法》所创设的法律监督机制直接称为“违宪审查”,也尚存疑问。
二、《1998年人权法》:内外挑战和覆水难收
《1998年人权法》自诞生之初就面临这一系列内外挑战。就《1998年人权法》的规定本身而言,有几个问题是它自始即无法轻易驾驭的。第一,《1998年人权法》并不解决一般性的制定法冲突。它只能处理其他制定法与《1998年人权法》上的欧洲人权法规范的冲突,并要求其他制定法与《1998年人权法》取得一致。但是,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可能发生在其他规范上,这在英国法上仍然只能靠老办法解决,或者仍然无法解决。第二,对于附属立法、行政行为也是一样,《1998年人权法》并不过问欧洲人权规范之外的司法审查。第三,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1998年人权法》并不处理私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或者所谓“宪法权利”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其成文宪法很可能包括大量的人权规范,笼罩全部公私生活,如果他们恰好又有强大的违宪审查机制,则当部门法无法处理私行为对宪法权利的侵害时,受害人仍可求助于宪法。这一点是《1998年人权法》无从做到的。如果欧洲人权法上的这些权利也存在于普通法上,那么私行为的侵害就可以得到普通法法院的救济;如果并不存在,那么受害人就没有通过诉讼得以救济的可能;换言之,也就是说没有遭受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这和人们的直觉可能不太一致。
《1998年人权法》面临的外部压力则更大。英国首相卡梅隆直陈,给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投票权使他感到恶心。①S.Lambrecht,“HRA Watch:Reform,Repeal,Replace?Criticism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A UK Phenomenon?”,UK Const.L.Blog(27th Jul 2015).其实,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只是给保守党扩散欧洲怀疑论提供了又一个借口。麻烦在于,在2015年的英国大选中,卡梅隆领导的英国保守党获得大胜。保守党在竞选大纲中已经承诺,切断英国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正式连接,要求国内的“最高”法院决定人权事项。在2015年新一届议会的女王演讲宣谕(Queens’speech)中,政府进一步承诺将要提出英国权利法案(British Bill of Rights)的草案来落实竞选大纲。②H.Fenw ick,“HRA Watch:Reform,Repeal,Replace?Backing Down on HRA Repeal in the Queen’s Speech?De-railed Plans for Rapid Introduction of a British Bill of Rights”,UK Const.L.Blog(29th May 2015).人们于是认为,英国权利法案将成为《1998年人权法》的替代品,后者在此政治条件下已经走到生命尽头。
不过认真分析即可发现,这种想法其实过于简单。首先,《欧洲人权公约》本身并未要求各国建立国内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之间的任何“正式连接”。而且《1998年人权法》也只是要求英国的普通法法院“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并未要求普通法法院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奉为圭臬,按照“遵循先例”原则一体适用。所以,究竟如何以一部新的“英国权利法案”达到“切断英国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正式连接,要求国内的最高法院决定人权事项”之目的其实堪虞。
实际上,《1998年人权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法律体系,显现出覆水难收之势。
当然,也有论者指出,《1998年人权法》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英国,不单有《1998年人权法》在保护人权,其他一系列制定法、普通法都是人权的捍卫者。而且在同样实行西敏寺制的英联邦国家,没有可供司法审查的人权规范或者只有很弱的人权规范也都没有妨碍民主进步和法治发展。③G.Gee and G.Webber,“HRA Watch:Reform,Repeal,Replace?ConventionalWisdom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UK Const.L.Blog(15th Jun 2015).实际上,澳大利亚普通法法院的权力比英国就小得多。当澳大利亚普通法法院发现制定法可能和人权规范不一致时,他们可以做出一个“不一致解释”(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宣告,而非像英国普通法法院一样做出“不一致”(incompatibility)宣告。“不一致解释”宣告意味着普通法法院只是得出了和议会不同的法律解释,并不证明议会已经以制定法的形式违反了基本人权。①G.Williams,“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on the UK Human Rights Act Debate”,U.K.Const.L.Blog(27th Oct2015).新西兰的《1990年权利法案》(New Zealand Bill of Rights Act1990)也没有授权普通法法院宣告“不一致”。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真的自始至终没有《1998年人权法》,英国当然可以像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一样延续过去的实践,但是《1998年人权法》已经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广泛影响。英国普通法法院已经根据《1998年人权法》作出了一系列关涉公民权利的重要判决,这些判决所体现的原则和思考,即便《1998年人权法》被废除,也不会被英国普通法法院突然之间弃如敝履。英国最高法院现任首席大法官廖柏嘉(Lord Neuberger)曾说,如果没有《1998年人权法》,我相信普通法也很可能朝着相同的方向做出相应的改变,毕竟普通法本身就是随时而变的。②A.Tucker,“HRA Watch:Reform,Repeal,Replace?The Anti-Democratic Turn in the Defence of the Human Rights Act”,UK Const.L.Blog(6th Jul 2015).用英国的谚语说,这就是金酒倒出瓶子,很难装回去了。
三、《1998年人权法》与英国的权力下放进程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废除《1998年人权法》意味着该法立刻失效。但在苏格兰,由于英国的权力下放安排,问题变得比较复杂。实际上,在决定向苏格兰整体下放权力的《1998年苏格兰法》中,《1998年人权法》只被简单地提到两次。《1998年苏格兰法》第126条第1款规定,所谓“(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的含义应当与《1998年人权法》一致。《1998年苏格兰法》附件4的第1(2)(f)段规定,苏格兰议会无权修改的制定法包括《1998年人权法》。那么,如果《1998年人权法》被英国的西敏寺议会废除,在苏格兰,直接的结果就是《1998年苏格兰法》的上述条款失去意义。但是,在苏格兰落实《欧洲人权公约》仍然是英国议会的保留权力,苏格兰议会本身是无权制定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的法律的。③I.Jam ieson,“HRA Watch:Reform,Repeal,Replace?The repeal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Sewel Convention in Scotland”,U.K.Const.L.Blog(11th June 2015).
一方面,如果《1998年人权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部新的英国权利法案。按照苏格兰法的规定,英国议会在未征得苏格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不在权力下放事项上为苏格兰立法。那么,这部新的英国权利法案因为十分可能涉及苏格兰权力下放事项,所以多半无法在苏格兰生效。这样一来,等于过去由《1998年人权法》施加于苏格兰的限制就被一下子取消了。根据英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苏格兰议会制定的自治立法不能按照一般的普通法方式予以司法审查。一个看似荒谬的结果就是,从此苏格兰议会可以制定不顾《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的自治立法,随便被侵权人选择去欧洲人权法院起诉英国政府。
另一方面,这一荒谬结果可能不会发生,因为《1998年苏格兰法》也要求苏格兰议会根据第35条通过的自治立法以及苏格兰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英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英国中央政府的国务大臣有权监督苏格兰议会和政府履行国际义务。过去,由于《1998年人权法》的存在,《欧洲人权公约》义务被排除在上述国际义务之外。如果《1998年人权法》被废除,那么《欧洲人权公约》义务就又成了苏格兰议会和政府必须遵守的国际义务。①I.Jam ieson,“HRA Watch:Reform,Repeal,Replace?The repeal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Sewel Convention in Scotland”,U.K.Const.L.Blog(11th June 2015).甚至因为《欧洲人权公约》的牵涉是如此广泛,结果可能就不是苏格兰议会的自治立法权被扩大,而是恰恰相反,从此英国中央政府的国务大臣可以借口《欧洲人权公约》国际义务持续不断地干涉苏格兰议会的自治立法行为和苏格兰政府的行政行为,多方限制和缩小苏格兰在英国权力下放进程中已然享有的自治权力。实际上,主权国政府以人权规范控制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英联邦国家中,加拿大的《权利法案》曾经遭到魁北克政府的抵制,并被后者视为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扩权阴谋就是典型的案例。就这一点而言,废除《1998年人权法》可能恰恰是近年来与英国中央渐行渐远的苏格兰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至于苏格兰法院,在《1998年人权法》出现以前,他们对《欧洲人权公约》的态度实际上是相对消极的。所以,不能简单断言苏格兰普通法在应对《欧洲人权公约》及其权利时会做出像英格兰普通法同样的变化。
四、余论
对于我国宪法学界而言,2015年英国出现的废除《1998年人权法》论争可能令人惊讶甚至失望。英国议会虽然基于“议会主权”原则,保有随时废止包括《1998年人权法》在内的任何制定法的权力。但在2015年之前甚至直到今天,英国内外的普遍预测仍然和10年前何海波的判断一样:“议会废止《人权法》,更因受内在和外在的限制,几无可能。”②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但这一动议能够出现于保守党政纲和女王宣谕,并在英国宪法学界引发煞有其事的讨论,这本身就值得我国瞩目。李蕊佚曾经分析,“抵制法院的判决将面临的政治后果、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英国政府败诉后将承担的法律后果、三个分支之间的礼让传统以及英国公众对法院的尊敬,构成了‘不一致宣告’的实际效力。英国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共同产生的影响,使得‘不一致宣告’成为司法限制议会侵害公民权利的有力手段”。③李蕊佚:“议会主权下的英国弱型违宪审查”,载《法学家》2013年第2期。在此前提下,论者认为,英国的“违宪审查”模式虽然表面上尊重了自称拥有全权的立法机关,但实质上可以达到和所谓“强违宪审查”模式趋同的效果,以保护基本人权。但2015年英国关于《1998年人权法》存废的论争显示,西敏寺体制下拥有全权的立法机关暨行政机关并不是任人敲掉牙齿的颟顸古兽,仍然可以抓住机会随时启动政治议程,而司法机关因为早已驯顺于“议会主权”的神主牌下并无置喙的机会。你方暗度陈仓,他已洞若观火。
而在2015年英国关于《1998年人权法》存废的论争中出现的另一理论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作为对政治力量的反动,英国宪法学界和司法人士纷纷提出所谓《1998年人权法》已然创造出“既成法理/判决”(entrenched human rights jurisprudence),将《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规范以自身为桥梁实现了“英国化”或者“普通法化”。应当说,这才是这类纳入人权规范条款的制定法的威力所在。实际上,我国宪法学界早已遭遇这种学说。根据香港临时立法会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不承认港英时代制定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自行宣布的凌驾性,予以废止。可是,香港回归后特区的普通法法院仍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关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对特别行政区的制定法予以司法审查并宣布无效。有学者随即指出,在香港普通法中围绕着经由《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落实的国际人权规范的“既成法理/判决”。此时,即便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全部废除,甚至中断它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关系,恐怕也无济于事。可见,普通法法院面对强势的政治力量、立法和行政机关并非没有反抗手段。这种反抗的基础并非立法机关施舍的某个制定法,而是由普通法法院独断的普通法本身。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普通法的依靠,仅仅是一个意图有为的司法机关,其施展空间十分有限。南橘北枳,理所当然。
此外,在2015年英国关于《1998年人权法》存废的论争中凸显的人权规范与地方自治规范冲突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适度注意。当单一制国家落实权力下放安排时,统一的司法体系往往成为维系国家整合的机制。实践证明,英国和西班牙的中央司法机关都是国家统一的支持者,特别是西班牙宪法法院,已经成为抗衡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固堡垒。①屠凯:“西方单一制多民族国家的未来——进入21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而司法体系的统一也有其显而易见的合理性,公民不分地域和民族可以得到国家司法机关对其被侵害权利的平等救济,合乎国际人权规范的要求。所以,当司法机关也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被地方所俘获时,人权规范就成了主权国的最后保证。有了人权规范,一国公民即便身处自治地方行政区域,也可获得与该区域主体居民大致不差的对待。而一旦人权规范无法束缚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往往会以自治为名义,大肆侵害区域内非主体居民的合法利益。这一问题当然并非无足轻重。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制定一个保守党色彩浓厚的“英国权利法案”,倒不如行之有效的《1998年人权法》更能收拾早已罅隙显露的英国自治地方民心。这一层关节虽然是英国中央的保守党政府之前未曾深思的,但却可能影响他们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