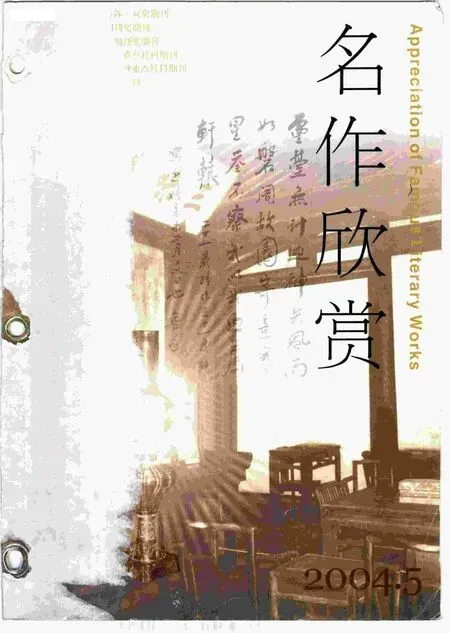论《呼兰河传》中时间的“裂”痕
⊙于 淼[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呼兰河传》文章开篇就用了一小段描写自然环境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用了简单的几句话勾勒了一幅北方极寒天气下大地的表象。作者从不同的视角用八处“裂”来描写了地“裂”的状态,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再没有这样集中地用过这个字,笔者认为作者所刻意强调的“裂”字虽然在后文中并未集中体现,但是这种意象和感情基调贯穿了全文,并在全文有着更深层次的作用和深刻的内涵。这种意象集中表现在时间上的“裂”。米克·巴尔所说:“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对于叙述节奏是很重要的。当空间被广泛描述时,时间次序的中断就不可避免……并因此而能被看作事件。”①也就是说“时间顺序总是因空间显示而被破坏”。时间的发展由于对于空间的表现和描绘而被中断,时间被空间所切割,这是叙述中的某种不可避免性。葛浩文认为:“由于萧红的作品没有时间性,所以她的作品也就产生了‘持久力’和‘亲切感’。”②但笔者认为《呼兰河传》具有时间性内涵,而这种时间性的表现是断裂的,这种断裂的时间性使小说充满了神秘的内涵。
一、四季变换的“裂”
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到春夏秋冬,这四季似乎成了作者对于呼兰河人生活独特的阐释依据,也是作者对人生的深刻领悟。“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③“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④“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⑤小说第一章中重复了三次关于呼兰河人春夏秋冬的生活状态描写,季节的转换是一种封闭循环,而不是波浪式前进的状态,因此使这种转换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假定性的时间。呼兰河人就在这种封闭的时间状态下周而复始地向死而生。萧红深刻体悟到了这一点,她试图打破这种封闭的时间循环状态,希望它可以朝着波浪式前进的状态转变,所以小说在不同的章节都没有按照正常的春夏秋冬这样的时间变换来描写和叙述文本,而是跳跃式的,作者根据自己童年视角的回忆性时间来随意地安排这四季的变换,这就造成了文本中时间的断裂感。
如小说在第一章开篇就描写了“严冬”这一具有明显季节时间性的场景,这一季节的设置为全文奠定了一种冷色调。接着描写“大泥坑”是夏季。到第二章在描写呼兰河的盛举时,时间的跳跃和断裂就更明显。跳大神夏季居多,七月十五的放荷灯是秋季,野台子戏也是秋季。但是到了第二章的结尾,作者却写了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是在初夏季节。第三章开头以夏季为背景,描写叙述人与祖父在后园劳作的场景,接下来描写了秋天、冬天,在这一章里作者在第四节里又一次描写了夏天。第四章作者又以夏天开篇,最后结尾处又写到秋天。第五章以小团圆媳妇为叙述对象,描写了其悲惨的生活遭际,作者依然以夏季为开篇,并以小团圆媳妇的死为结束,但是时间却截止到“还没有到二月”,也就是说小团圆媳妇没有活到春天就死了。第六章中作者以有二伯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也是以夏夜晚饭后的闲聊为开篇,中间秋末有二伯偷东西被“我”发现,结尾却在一片白雪的冬天。第七章作者以冯歪嘴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夏季植物攀爬了冯歪嘴子的窗户为开篇,接着就是在寒冬里叙述人发现冯歪嘴子的儿子和女人。尾声作者所怀念的依然是夏秋之时的后园。从以上描写看出作者叙述小说事件大多发生在夏季,夏季似乎对于萧红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夏季的后园,夏季的院子,还是作品中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都以夏季为出场背景,在这样繁盛的季节里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生命狂欢,可是这生命随着秋冬的来临而变得消散荒芜,这种生命的意义被季节所消解。而季节时间的断裂也造成了文本中人物生命的终结。在作品中作者没有关于春天的描写,作者为何有意回避描写春天?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可是作者并没有对它做描绘,而是在开篇之时以冬季为时间背景来进行叙述。是否在作者眼里看不到春天?其实作者对于呼兰河城乡间的生活并没有感觉到希望,而所充斥的都是繁华到败落的悲凉。这与作者对于中国乡土的想象密切相关。作者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乡间是没有生机的,甚至连死都没有任何的激情,如死水一般无法泛起任何涟漪。作者刻意打乱了时间的排序,采用了孩童的视角,这使得作者对于童年的记忆停留在了最繁华和热闹的季节里,并主观地认为事件的发生都集中在夏秋的季节里,这使时间具有了想象性、虚构性的特点。
二、女性成长时间的断裂
小说里我们很少看到叙述人成长时间的准确过程,时间和年龄大多以虚写的方式呈献给读者,并且这种成长的时间大多集中于小说的第三章:“我生的时候……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⑥“我想……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⑦“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⑧“我在一两岁的时候,大概……可是长到四五岁,反而不认识了。”⑨“等我生来了……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⑩。从所给的信息中我们不难发现,叙述者对于自己三到五岁时的记忆多与祖父有关,在其余的六章里,都没有关于叙述者年龄的表述。祖父作为家族的大家长给了叙述者无限的爱和庇护,在作者的成长记忆里这段时间是最为美好的,也是对作者影响最深的一段真实记忆。叙述者说自己在三岁时就开始记事,长到五岁时应该就已经相对懂事了,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叙述者已经从无知婴童时代向女孩过渡。作者没有具体地提出年龄的阶段,只是用模糊的时间来概括成长历程,在第三章的结尾处作者说“祖父再也抱不动我了”,这暗示了“我”作为独立个体成长的开始,“我”对祖父的依赖随着岁数的增长而渐渐疏离。然而时间并没有往前推进,而是在这里停止断裂。萧红刻意在此将时间截断,是希望时间停留在年幼时与祖父在一起的时光里,锁住美好的记忆。她拒绝成长,拒绝成为女人,因为就作者的成长经历来看,在随后的日子里,作者一直过着“逃荒”似的生活,这与祖父在一起的快乐和稳定是截然不同的,作者失去了快乐,只剩下寂寞与荒凉。但是时间是流动的,虽然文本中没有提到随着叙述者年龄的增长,“我”与祖父的关系如何,但是“我”从女孩到少女的成长已经悄然开始了。
尾声中“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祖父一过八十,祖父就死了。”[11]小说从六岁开始到二十岁之前的时间段都没有做任何描写,而是在结尾处又重复了在第三章第一次提到的年龄。作者习惯性的重复叙事,是为了强调对祖父的记忆,同时也是对时间做了一个封闭的回旋,让时间重新回到了四五岁的年龄段,将读者的记忆拉回到后园中,拉回到与祖父的时间里,同作者一同回味记忆中美好的但已消逝的时间。但是作者没有止于此,而是说自己没有长到二十岁,这就说明祖父与叙述者从开始一直相处到了祖父去世,这段时间是叙述者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叙述者的少女时代,祖父作为大家长的庇护和爱也止于祖父的死亡。时间在此再一次断裂,直到现在成年的“我”回忆起那段呼兰河的日子所经历的时间也都是虚无的,但时间的过程却是真实存在的,祖父的死预示着“我”美好的少女时代的结束。克里斯多娃曾经说:“如果女性主体置身于‘男性’价值的构建之中,那么,就某一时间概念来说,女性主体就成了问题。这一时间概念是:计划的,有目的的时间,呈线性预期展开:分离,进展和达到的时间。这种时间内在于任何给定文明的逻辑的及本体的价值之中,清晰地显示其他时间试图隐匿的破裂,期待或者痛苦,这已经得到充分证实……因回忆导致的癔病(男人的或者女人的)更多的从先前的时间形式(循环的或永恒的)中识别自身。”[12]作品中的时间断裂都是在回忆之中完成的,最终这种时间的断裂止于了祖父的死,作者将记忆切割了,将时间的盲点置于无边的荒凉之中。“在一定范围内,故事中的时间如果在向度上属于‘过去’,便常常会赋予文本一种感伤的色彩。”[13]写此作品时的萧红已是疾病缠身,她将成长中的时间盲点与她自身的现状联系起来,用模糊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这种隐秘性充满了对女性个体成长痛苦难于直说的无奈之感。
三、历史时间的“裂”
萧红对时间的理解与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有所不同,她所写的不是全民族共有的历史时间,而是一种寂寞的个体时间,在这里社会性时间基本是缺席的。这里的“个体”不仅仅是萧红自身,也是另一种眼光下的苦难乡土中国。
作品中唯一提到的历史事件就是日俄战争,有二伯所回忆的毛子人屠城的故事,他不厌其烦地对别人讲这个故事,似乎在炫耀着自己是一个有血性和有胆量的人,“有二伯常常说……那真是杀人无数。见了关着的大门就敲,敲开了,抓着人就杀。”但是在祖父面前他却又用这个故事求得祖父的帮助和救济:“人是肉长的呀!人是爹娘养的呀!……眼看着那是大马刀,一刀下来,一条命就完了。”[14]作者在安排这个历史事件时并没有把它的整个历史过程展现给读者,或是以这个历史事件为整个叙述故事的时间背景,只是截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段,而这个时间片段是充满血腥的沉痛的历史记忆。这是一段回忆中的回忆,时间里的时间,作者将这种断裂的历史时间消解在呼兰河人普遍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二伯讲故事和祖母房间的摆设)。小说在第三章描写祖母房间时,提到“很古怪很古怪的挂钟”,在这个挂钟里面有一个“毛子人”,“毛子人”在这个具有时间象征意义的挂钟里永久地“呆着”。“毛子人”所做的事情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停留在了过去中,也逐渐被人所遗忘,作者将这段历史时间物化到了某个特定的空间里,展现给读者。“历史的空间化不仅在于小说叙述话语的有意设置和使用,同时被引进了‘轮回’‘再生’的民间文化概念……显然消解了历史的时间含义。”[15]时间的延展性被切断,事件停留在被切割的时间段中不断的重播,就连有二伯对于毛子人屠城的事情也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趣味奇谈,缺少了庄重与悲苦感。就如同茅盾所说:“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在呼兰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6]
时空是一种束缚,萧红远隔万里,似是思念家乡,却也排斥家乡,有人说萧红向往回到故土,可笔者却不这么认为,在她经历了如此多的沧桑和等待以后,家或者家乡这个概念对于远在香港、病痛缠身的萧红来讲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她所向往的不再是在荒凉的院落中等待,在寂寞中枯萎,她渴望生如夏花般的人生,可是那所谓的繁华并没有带给她预想中的幸福,当繁华脱去它华丽的外衣,剩下的也只是一片秋风带过的碎屑,所以萧红带着那颗充满裂痕的心缓缓前行,在呼兰河城外的世界里过着与城内一样的生活,这种伤感和裂痕最终都无处弥补。
①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述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②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4] 萧红:《呼兰河传》,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第86页,第94页,第111页,第113页,第114页,第119页,第120页,第207页,第177页。
[12]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露丝·依利格瑞:《性别差异》,朱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13] 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15]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16] 茅盾:《呼兰河传序》,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